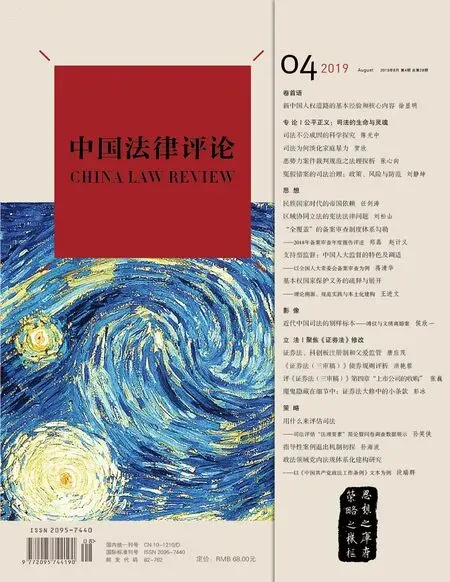司法為何淡化家庭暴力*
賀 欣
香港大學法學院教授

為什么離婚訴訟中幾乎不認定家庭暴力或判付經濟賠償金?反家庭暴力法律的發展也沒有改變這一情況。本文揭示那些使法官超越法律審判的動因——法官淡化家庭暴力的做法與他們身處的制度約束相關。
人身安全是文明社會的最基本人權,1Custody of Vaughn. 1995, http://masscases.com/cases/sjc/422/422mass590.html; Andrew Schepard, Children, Courts, and Custody: Interdisciplinary Models for Divorcing Famil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85.但是很多中國女性的這項基本權利沒有得到保障。根據官方報道,約1/3的家庭存在暴力。2"Domestic Violence Increases in China",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9-03/07/con tent_7551147.htm.一項政府調查表明,1/4的婦女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3周淵:《“家事”立“國法”——專家解讀我國首部反家暴法》,載 https://whb.cn/zhuzhan/jiaodian/20160302/50721.html,2016年; CCTV:“25% of Married Women Suffer Domestic Violence in China”,available at http://english.cctv.com/2017/03/02/VIDEsd8TYsYQVyXgo86BjANx170302.shtml。盡管任何人都可能成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但是報道中近90%的案件是關于婦女遭受丈夫的虐待。4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司法大數據專題報告:離婚糾紛》, 2018年,載http://k.sina.com.cn/article_5880306529_15e7e5b6100100584p.html?cre=ne wspagepc&mod=f&loc=4&r=9&doct=0&rfunc=3,2019年5月20日訪問。登記離婚的案件中60%和家庭暴力有關。5"Focus: Domestic Violence on the Rise", China Daily, September 19,2003, availabe at http://www.chinadaily.com.cn/en/doc/2003-09/19/content_265604.htm.尋求從丈夫暴力中解脫的婦女是民事訴訟當事人中數量上升最快和社會中最脆弱的群體之一,這體現在離婚訴訟中對家庭暴力的普遍訴求。最高人民法院發現27.8%的離婚訴訟原因是家庭暴力,家庭暴力成為離婚訴訟的第二大事由;6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司法大數據專題報告:離婚糾紛》,2017年,載 http://www.court.gov.cn/upload/file/2018/03/23/09/33/20180323093343_53196.pdf,2019年5月20日訪問。另一項最高人民法院報告表明10%的故意殺人案起因也是家庭暴力。7《最高人民法院召開司法干預家庭暴力有關情況新聞發布會》,載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4/02/id/1220942.shtml,2019年5月20日訪問。巫若枝研究了310例華南某縣1950年至2004年的離婚案件,發現幾乎在所有案件中妻子一方都聲稱自己受到了丈夫的虐待。8巫若枝:《當代中國家事法制實踐研究——以華南R縣為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 203頁。
然而,法院很少認定家庭暴力,更不用說給予經濟賠償。9Michael Palmer, "Domestic Violence and Medi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Medi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Coninuity and Change, Wildy, Simmonds & Hill Publishing, 2017, pp. 286-318.基于重慶市某區基層法院起訴的家事案件的實證研究發現,在458個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中僅有3個案件(0.66%)獲得經濟賠償。10陳葦、段偉偉:《法院在防治家庭暴力中的作用實證研究——以重慶市某區人民法院審理涉及家庭暴力案件情況為對象》,載《河北法學》2012年第8期。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的所有提交家庭暴力證據的案件中,只有17.3%的案件被認定有家庭暴力。11高鑫:《家暴認定僅一成,舉證不力是關鍵》,載《檢察日報》2016年11月2日。
為什么離婚訴訟中幾乎不認定家庭暴力或判付經濟賠償金?反家庭暴力法律的發展也沒有改變這一情況。本文揭示出那些使法官超越法律審判的動因——法官淡化家庭暴力的做法與他們身處的制度約束相關。他們需要保護自己,用安全的方式、有效率地結案。案結事了是他們的最高目標,這遠遠大于法律的要求。本文首先介紹反家庭暴力法律的演變并表明立法保護的顯著進步。然后圍繞法官處理離婚訴訟的兩個方式,即調解和審判,文章指出,即使法官已經確信存在家庭暴力,他們仍然在調解進程中視而不見;雖然這一情況在以判決結案的案件中有所改善,但差別不大。判決書中經常不認可家庭暴力的證據,而在一審中已經認定的證據也經常在二審中被駁回。此外,在法院就明顯無法復合的婚姻判決不予離婚時,也常常忽略家庭暴力對婦女產生的人身威脅。作為一項新設立的機制,人身保護令并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總之,法庭對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保護微乎其微。
一、家庭暴力法律制度的發展
過去,中國受害女性起訴到法院后遇到很多困難,執法人員并不特別關注家庭暴力投訴,12Liu Donghua, "Five-Year Consulting Report", (2001) Center for Women's Law Studies and Legal Service of Peking University, pp.6-7;Cited by Engle Merry, Human Rights and Gender Violence : Translating International Law into Local Justi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p.149.他們把這類糾紛歸為“夫妻吵架”或“家庭矛盾”。由于和諧社會中的儒家思想和中國人普遍不想介入他人的“家庭問題”,受害女性的家庭成員、朋友、同事和親戚一般都不會指證丈夫的暴力行為或出庭作證,13徐昕:《法官為什么不相信證人?》,載《中外法學》2006年第3期; 馬靜華、陳一鳴:《柑村糾紛解決實踐中的解紛主體——以川東北某村的考察為中心》,載徐昕主編:《司法:糾紛解決與社會和諧》(第一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192頁。“即使是受害婦女的兄弟姐妹都覺得介入其中是不合適的”。14Supra note 12.
然而,家庭暴力已成為一個越發嚴重的社會問題,被政府列為官方議程和公共話題。例如,在2008年,全國人大代表、中華女子學院教授孫曉梅說:“家庭暴力是一個跨越所有社會階層的社會現象,并且變得越來越普遍。立法刻不容緩。”15Jiao Xiaoyang, "Call for Legislation on Domestic Violence", (2008)China Daily,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8npc/2008-03/13/content_653273.htm.2010年,我國最大的婦女社會組織“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宣布其全國各地分支機構共收到52,000例來自受害女性的家庭暴力申訴,16Jiao Xiaoyang, "Call for Legislation on Domestic Violence", (2008)China Daily,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8npc/2008-03/13/content_653273.htm.它還進一步表示“家庭暴力嚴重威脅到中國婦女權益。”17Supra note 2.
政府長期將兩性平等作為一項基本社會目標,但是直到2001年修訂《婚姻法》,“家庭暴力”一詞才出現在法律中。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將家庭暴力定義為家庭成員之間以“毆打、捆綁、殘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經常性謾罵、恐嚇等方式”實施的身體、精神等侵害行為。《婚姻法》第3條規定,禁止家庭暴力。第32條規定,如果法院發現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應準予離婚。第46條規定,因實施家庭暴力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修訂后的《婚姻法》規定受害婦女可通過民事訴訟得到救濟,盡管這種保護很有限。
2000年,大量保障兩性平等的法律條文出臺。這些全國性的法律包括《婦女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和《殘疾人保障法》。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發布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審理指南》是保護婦女權益和對抗家庭暴力的重要進步。例如,與一般民事訴訟舉證規則相反,原告提供證據證明受侵害事實及傷害后果并指認系被告所為的,舉證責任轉移至被告(第40條)。盡管審理指南不能作為法官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據,但可以在判決書的說理部分引用(前言)。省級立法也迅速發展。截至2008年9月,已有20個省、市和自治區運用法律手段制止家庭暴力。至2008年10月,有23個省、市和自治區通過了婦女權益保障法的實施計劃,重點關注家庭暴力問題。18Robin Runge, "Operating in a Narrow Space to Effect Change: Development of a Legal System Response to Domestic Violence in Chin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Gender Violence: Lessons from Efforts Worldwide, ed. Rashmi Goel and Leigh Goodma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35.
二十多年來,婦女權利組織和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一直呼吁加強保護家庭暴力受害者,最終促成《反家庭暴力法》于2015年頒布。公眾普遍認為這部反家庭暴力法律是“社會和法律的一個巨大進步,它表明國家認可家庭暴力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家庭暴力作為一種違法行為在中國不再被歸為私人問題”。19Supra note 9, p.310.它宣示“國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相較之下,之前的法律如《婦女權益保障法》并沒有為受害者提供切實的法律救濟。《反家庭暴力法》規定了一系列新的法律保護措施,最重要的是它第一次在國家法律中定義何為家庭暴力。該法第2條規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員之間以毆打、捆綁、殘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經常性謾罵、恐嚇等方式實施的身體、精神等侵害行為”。
最值得注意的是當受害者“遭受家庭暴力或面臨家庭暴力危險”時可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第23條)。根據《反家庭暴力法》,帕默(Palmer)列出“公安機關(第20條)和醫療機構(第7條)應法院要求應當提供侵害的證據”。“法院受理保護人身安全申請后應當及時作出決定(第28條),及時作出人身保護令需要有明確的被申請人和具體的請求”。20Supra note 9, p.311.另外,法院還需要有證據證明遭受家庭暴力或面臨家庭暴力現實危險的情形(第27條)。人身安全保護令可以禁止被申請人實施騷擾、跟蹤或接觸申請人或責令被申請人遷出申請人住所(第29條)。國家組織和相關機構應當協助法院執行(第32條)。違反人身安全保護令的罰款最高可達1000元或15日拘留,甚至面臨刑事責任追究(第34條)。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共同發布《關于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旨在打擊相關犯罪。
理論上,這些法律法規表明我國正在向保護弱勢婦女和兒童不受虐待的方向不斷發展。為回應社會對家庭暴力的關注,國家正通過法律方式保護婦女免受家庭暴力侵害。盡管目前仍存在諸多不完善之處,但從2000年家庭暴力法律的空白到2015年單獨就家庭暴力立法,對一個具有根深蒂固的兩性等級觀念的國家而言,這樣的進步無疑是巨大的。那么,法官如何應對家庭暴力問題以及受害者權利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保障?
二、司法調解對家庭暴力的忽視
以調解結案的離婚案件最能體現司法審判對家庭暴力的淡化。21Supra note 9, pp.312-313; Han Sulin, "China's New Domestic Violence Law: Keeping Victims out of the Harm's Way?",(2017), available at https://law.yale.edu/system/files/area/center/china/document/domesticviolence_finalrev.pdf; Xin He and Kwai Hang Ng, "In the Name of Harmony: The Erasure of Domestic Violence in China's Judicial Medi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Policy and the Family, Vol.26(2013), 97-115.2015年實施的《反家庭暴力法》仍然允許以調解的方式解決涉家庭暴力的離婚訴訟。事實上,實證研究表明這類案件以調解或主動撤訴方式結案的比例高達62%。22陳葦、段偉偉:《法院在防治家庭暴力中的作用實證研究——以重慶市某區人民法院審理涉及家庭暴力案件情況為對象》,載《河北法學》2012年第8期。
調解的形式包括主動撤訴、調解離婚以及調解和解。主動撤訴是指第一次申請離婚時,法院不準予離婚;如果雙方堅持離婚,他們需要重新起訴。對當事人而言,主動撤訴的法律效果和判決駁回一致;但對法官而言,這是一個調解案件。調解離婚意味著離婚糾紛的解決:雙方當事人同意離婚和其他相關事項,其法律效果和判決離婚一致;然而調解和解是指夫妻雙方和解并繼續生活在一起。在這類案件中,法院不考慮家庭暴力的問題。以下將討論主動撤訴和調解離婚,闡釋法官在不同動態關系背后的相同邏輯。
1.主動撤訴
在主動撤訴的案件中,家庭暴力問題總是被忽視,就像它們從未發生過。由于夫妻雙方仍屬一個家庭,沒有必要進行金錢賠償。法官可能會口頭教育或說服侵害人停止施暴,但也僅此而已,沒有任何法律后果。
一位20多歲的年輕女性第一次起訴離婚,指證婆婆毆打她以及夫妻性格不合。她的丈夫27歲,每月收入2600元人民幣,拒絕離婚。丈夫的哥哥是聾人且沒有工作,婆婆有精神問題。妻子兩年前從陜西到上海打工(上海農民工案件),法官懷疑她可能有外遇,想擺脫現在的家庭負擔。然而,她的律師說真正的原因是“那男的有點毛病(暗示性無能),不能有正常的性生活。作為一個年輕的男人,他釋放欲望的方式是抓擦她的外陰。這種傷害很嚴重,以致她沒辦法走路。但她不能去外面說”。但這些沒有說服法官,直到丈夫要求妻子和他一起回家。她很憤怒,“我們每晚都打架。你相信我們能生活在一起嗎?我現在看到你就覺得恐懼!”丈夫的臉霎時變得難堪。
起訴狀提到婆婆的家庭暴力,法官并沒有追尋家庭暴力的問題,畢竟女方主要關心的問題不是家庭暴力。她真正想要的是離婚。對法官而言,其目標是找到案件的解決方案,要避免那些旁枝末節的問題。法官未加思索地向妻子的律師說明她的決定:
這段婚姻不可能存續,但是這次她不能離婚。我們必須尊重丈夫最后的尊嚴。盡管他的要求沒有法律依據,但在這個時候我們不能抹殺他對整個家庭的希望。我們必須保持這段婚姻的形式。讓我們給丈夫的家庭一點時間,讓他們從心理上做好失去她的準備。
原告最終“主動撤訴”。當然,原告并不是自愿這么做的,而是在法官的要求下。盡管法官沒有作進一步調查,但法官看起來是認可存在家庭暴力的。不過,法官已經作出了不準予離婚的決定,便沒必要調查婆婆或丈夫的家庭暴力行為。法官沒有采取任何行動解決這個問題:沒有人身安全保護令,也沒有書面報告。23帕爾默(Palmer)三十年前分析一個類似案件,法院只是駁回訴訟請求。這類案件中法院的判決并沒有改變太多。Michael Palm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ome General Observations on Family Law" , Journal of Family Law, Vol.25(1986),pp.41-68.在聽到法官的強硬建議后,婦女和她的律師是配合的,就像大多數農村地區的當事人一樣。
如果家庭暴力問題在受到法官壓力而撤訴的案件中沒有得到處理,在完全主動撤訴的案件中自然也會被忽略。在一個新加坡外出勞工案件中,法官說明一些實際問題之后,妻子便主動撤訴。在他們的對話中,妻子詳細地講述了春節期間她丈夫從新加坡回家后毆打她的經過:
原因是錢。我們總是為了這個問題爭吵。我想讓他直接寄錢給我而不是他父親。打我的那天,他喝醉后很晚才回到家。他敲門時孩子們已經睡下了。我打開門后,他踢掉周圍所有的箱子,踩在女兒們的玩具上罵我。我叫他小聲點不要吵醒鄰居。他向我扔了個杯子,我躲開后,杯子碎了。我的大女兒被吵醒了。她在她的房間看著我們,不停發抖。他便開始罵女兒,說“我會殺死你們”,他還想要弄壞女兒們的房門。我擋在他前面,他便開始打我。他往我臉上揍了一拳,用手抓住我的頭發。我沒有回擊,因為我當時想要保護孩子們。他打到筋疲力盡才停止,回他的房間睡覺。那天晚上我待在孩子們的房間,和兩個女兒一起哭。第二天,我發現我的臉腫了,雙眼充血。我休息了三天才能走出家門。
她說,丈夫打她的真正原因是她沒有生兒子。不管原因是什么,法官對家庭暴力的指控并不感興趣。法官沒有追究丈夫的死亡威脅,也沒有調查妻子所說的發腫的臉或有傷痕的眼睛。法官直接問:“離婚后你可以養兩個女兒嗎?”在傷心哭泣和慎重思考后,兼職商場收銀員的妻子決定撤訴。和訴訟一起消失的是她關于家庭暴力的故事,在案卷中找不到一點蛛絲馬跡。
法官很有技巧,引導女方想到她脆弱的經濟能力,假設離婚,她需要獨自支撐自己和兩個孩子的生活。法官沒有提到的是,根據法律規定,法院可以判決準予離婚。與此同時,法院可以要求在新加坡有體面收入的丈夫撫養孩子。如果女方知曉這個選擇,她可能不會撤訴。然而,這種建議是愚蠢的,因為這樣做的結果不是結束一個案件,而可能是制造一個新的案件。
兩種“主動”撤訴的區別僅在于法官遇到的抵觸程度不同。在不情愿撤訴中,法官可能無法說服當事人接受撤訴的決定。這是為什么在上海農民工案件中,法官首先向女方律師解釋自己的決定,律師多次代理離婚訴訟,能夠更好地理解法官的考量。在自愿撤訴案件中,法官面對的阻力很小。新加坡勞工案中的妻子在仔細考慮自己經濟能力后撤回訴訟。法官的意見很有影響力。不管是不情愿或是情愿撤訴的案件,法官對家庭暴力采取的方式是一致的:無動于衷,就像所有案件落入聾人耳中。法官們的想法很容易理解:只要訴訟雙方當事人愿意撤訴,對法官而言這是最好的結果,為什么要管其他的?他們的工作是找到結案方法。
2.調解離婚
在調解離婚案件中,即使法院已經確定事實,家庭暴力問題也被忽略。在下面這起離婚案件中,夫妻已經分居多年,丈夫和另一名女性同居;妻子提供了警察報告和傷痕的照片,證據表明丈夫實施過家庭暴力并有婚外情。夫妻雙方同意離婚,爭議的焦點在于如何分割夫妻共同房產和承擔對兒子的撫養義務。13歲的兒子一直和母親居住。和其他許多離婚案件一樣,這對已經疏遠的夫妻在法庭調查環節糾纏于種種指控而爭執不休。庭審的第一個小時氣氛緊張,雙方對峙不下。由于法官想要阻止對抗進一步升級,她在沒有宣布調查和討論環節結束的情況下,直接進入調解環節。事實上,她沒有正式詢問雙方是否同意進行調解,而這個問題大部分法官都會在庭審討論結束時就詢問。她知道雙方無意停留在失敗的婚姻上。經過30分鐘的反復協商,就女方放棄夫妻共同房產而獲得的補償費用,法官計算出一個數額。
除了房產分割問題外,子女撫養問題也存在分歧。原告(男方)愿意每月支付500元撫養費,但被告(女方)要求每月800元。法官迅速決定促成雙方以600元達成一致。出乎法官的意料之外,原告拒絕增加100元,這讓法官犯愁。她已經向雙方提供了一個她認為公平的讓步,將妻子要求的800元降低了200元。她以為這樣可以解決,但原告的頑固讓事情陷入僵局。
根據賀欣和吳貴亨文章中的詳細描述,為達成協議,法官用盡各種方法說服男方。24Xin He and Kwai Hang Ng, "In the Name of Harmony: The Erasure of Domestic Violence in China's Judicial Medi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Policy and the Family, Vol.26(2013), 97-115.法官提醒說這筆錢是用于撫養男方的兒子,而不是一個陌生人;她還提到他的兒子已經13歲了,這筆撫養費用不算高,因為他只需要支付到兒子18歲為止;她甚至還質疑男子工資的真實性,因為根據法律規定,收入是計算孩子撫養費的基數;她勸說男方,撫養兒子是一個父親應盡的責任。從我們的研究角度看,最值得深思的是,法官從未提及家庭暴力。根據修改后的《婚姻法》第46條的規定,難道男方不應該為自己的暴力行為負責嗎?難道這不足以促使男方接受額外支出100元撫養費嗎?
上述策略不是特例。在女銷售員案件的庭審過程中,法官成功證實了家庭暴力的存在。然而,在調解環節中,法官嘗試在充滿怨忿、對峙的夫妻間進行“調解”,從未提起家庭暴力。25Ibid.在巫若枝描述的另一個案例中,妻子不斷提出家庭暴力問題,出具警察報告證明她受了輕傷,26巫若枝:《當代中國家事法制實踐研究——以華南R縣為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 277—281頁。但丈夫否認這些傷是自己造成的。在調解中,妻子私下對法官說:“我不敢向家庭以外的人透露任何事情。有時我被打得很慘,全身青紫。但當別人問我怎么會有傷時,我說是自己摔倒了。我也不敢告訴我父母真相。”法官回答道:“如果雙方可以談妥,我會讓你們簽署一份調解協議。如果不能,法庭會進行判決。我們會盡力。調解到這里結束了。”
這些對話表明法官不想觸及妻子提到的家庭暴力問題。正如調解這個詞語的含義,雙方在調解中盡力達成合意。法官作為調解者,需要跳出過錯和違法行為的審判框架。為了取得調解結果,法官很小心地保持一種較和諧的氛圍。過多指責家庭暴力會招致男方的否認或抗拒,從而削弱調解的效果。換言之,為達成調解,法官應避免使用譴責性的話語。
法官以結案為主導的思維在發現犯罪行為的離婚訴訟中體現得也很明顯。法官沒有報告刑事違法行為,而是將犯罪作為達成協議的籌碼。在另一個案件中,卡車司機第二次起訴離婚,他聲稱25歲的妻子已經超過一年沒有回家。丈夫和孩子生活在一起,孩子患有先天性疾病,需要每隔一年進行一次昂貴的手術。她還很懶惰,不做家務。夫妻雙方同意離婚,但對撫養權和財產分割存有爭議。女子堅稱她有權分割80,000元土地拆遷補償款,但丈夫一家只同意補償10,000元,并堅持要孩子的撫養權。
和大部分離婚案件中的妻子不同,這名女子精力充沛,她身材矮小但很結實,有一張健康棕褐色的圓臉。很難想象她會像丈夫所說的懶惰。這位婦女私下告訴法官,她的公公曾經兩次試圖強奸她,這是她堅持自己訴求的原因。法官和丈夫的訴訟代理人討論了這個問題。丈夫的家人馬上妥協并達成協議:丈夫一家同意支付40,000元,但沒有對孩子的撫養權作出決定。
法官仍然只關心結案。被配偶以外的家庭成員強奸,無論成功與否,都是極其惡劣的犯罪。至少,根據《反家庭暴力法》規定,它是一種家庭暴力行為。然而,法官并不想去證實這一行為。她的公公沒有出現在法庭上,但從家庭成員總是詢問他的意見來看,他應是一個身強體壯且很強勢的男人。但是,強奸僅僅是法官用于迫使男方改變主意的籌碼。
很多夫妻愿意接受法官主導的調解,并不是因為他們想坐下來談,而是法官促使他們調解,他們之間還有很多可討價還價的地方。調解過程通常關注孩子撫養權和婚姻財產分割,但在這一過程中,家庭暴力無可避免地被忽視。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在涉及諸如離婚的家庭糾紛法庭程序和早前人身安全保護令的司法試點中,法官迫于壓力需要“視而不見和輕描淡寫”配偶的虐待,從而促使司法調解。27Han Sulin, "China's New Domestic Violence Law: Keeping Victims out of the Harm's Way?", (2017), available at https://law.yale.edu/system/files/area/center/china/document/domesticviolence_finalrev.pdf.法院對調解方法的廣泛使用遭到許多批評,因為調解無法確定責任和懲罰施暴者,從而導致中國女性長期遭受家庭暴力的現象持續存在。
3.法官的邏輯
上述分析表明,即便法庭調查中已經提出、討論并確立了家庭暴力事實的存在,最終都會被遺忘,在法庭調解環節中尤其常被忽略。當法庭調查環節審查家庭暴力行為時,雙方當事人會激烈對峙,當事人之間相互指控、侮辱和否認是常事。如果法官仍然糾纏在家庭暴力問題上,可能會損害和解的氛圍而無法成功達成協議。
從法庭調查到法庭調解的演變過程,科布(Cobb)稱為“轉型”(transformation)過程。28Sara Cobb, "The Domestication of Violence in Mediation", Law & Society Review, Vol.31(1997), pp.397-440.法庭調查階段適用法律性規則,關注的是權利和義務,以現有證據為依據;但法庭調解階段適用調解性規則,關注的是當事人的需求。在調解環節,調解性規則迅速占據主導,擴張其權威性和管轄范圍,將法律權利和道德指責排擠出去。科布指出,“調解的目標是達成協議,實現當事人的需要,而不是實現一條道德準則。事實上,調解的目的在于調和相互沖突的道德標準:沒有絕對‘正確’的道德,除非能夠認可和強化相對性”。29Ibid., p. 413.家庭暴力調查中的權利導向(rights-based focused)在調解過程中被需求導向 (need-based focus)所取代。
同時,法恩曼(Fineman)在分析撫養調解時指出,由于對話由“最佳利益說”所主導,父母的權利在子女的需求面前坍塌。30Martha Fineman, "Dominant Discourse, Professional Language, and Legal Change in Child Custody Decisionmaking",Harvard Law Review, Vol.101(1988), pp.727-774.因為調解的目標是達成合意,它必須滿足個人需求,因此它的話語總體上是務實的。事實上,正如希爾貝(Silbey)和薩拉特(Sarat)所說的,調解通過區分權利和需求的實踐而正當化:權利話語適用于以等級和權力主導的正式場景中;需求話語適用于以參與性而非權力主導的調解程序。31Susan Silbey and Austin Sarat, "Dispute Processing in Law and Legal Scholarship: From Institutional Critique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Judicial Subject", Denver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66(1989), pp.437-498.調解程序為糾紛雙方提供了一個架構,允許雙方以平等的社會、法律身份共同參與到糾紛解決中。在這一過程中,各種暴力,包括家庭暴力,尤其是因缺乏證據和模糊法律規定而導致的糾紛,都必須讓位于維護關系和經濟安全,最終不斷被邊緣化,直至消失。
國際實踐中,是否對存在家庭暴力的家庭糾紛案件進行調解,長期存在爭議,這是因為調解會威脅受害人安全。32David Greatbatch and Robert Dingwall, "Selective Facilitation: 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a Strategy Used by Divorce Mediators", Law & Society Review, Vol.23(1989), pp.613-642.學者普遍擔憂,調解沒有考慮受害者和施暴者之間的權力不平等,以及在施暴關系中經常出現的造成受害者恐懼和戰栗的脅迫問題。西方學者研究表明,社區內的調解程序經常邊緣化家庭暴力問題。33Lisa Lerman, "Mediation of Wife-Abuse Cases: The Adverse Impact of Informal Dispute Resolution on Women", Harvard Women's Law Journal, Vol.7(1984), pp.57-114; Janet Rifkin, "Mediation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Promise and Problems", Law and Inequality, Vol.2(1984), pp.21-32; Austin Sarat and Thomas Kearns, "A Journey through Forgetting:Toward a Jurisprudence of Violence," in The Fate of Law,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1, pp.268-269; Supra note 29;Ibid.格雷特巴奇(Greatbatch)和丁沃爾(Dingwall)認為“邊緣化” (marginalization)指的是家庭暴力的指控被“忽略或淡化”,暴力事件被表述為“關系性的而非犯罪性的”。34Supra note 32, p.187.在法院主導的調解程序中,情況并沒有更好。正如特林德(Trinder)等人對英國制度的研究發現的,家事審判人員一直在邊緣化家庭暴力的指控,有些案件甚至對堅持指控這一問題的婦女實施懲罰。35Liz Trinder, Alan Firth, and Chrstopher Jenks, "'So Presumably Things Have Moved on Since Then?' The Management of Risk Allegations in Child Contact Dispute Resolu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Policy, and the Family, Vol.24(2010),pp.29-53.
中國的情況更嚴重,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由于調解由法官主導,法官有權以更多介入的方式邊緣化家庭暴力的指控。相較于邊緣化或馴化,我國家庭暴力的忽略更具強制性;部分原因是法官和糾紛當事人的權力懸殊明顯。36Supra note 28 and note 32.在營造調解的氛圍中,法官積極且強勢;相較之下,社區調解員顯得更隱晦些,主要是因為司法調解是在審判架構中進行的。選擇調解結案的受害者以為自己得到了法律救濟,但實際上他們在達成調解協議時也不知不覺放棄了自己的法定權利。第二,當他們選擇司法調解時,他們也窮盡了所有的法律救濟,再沒有其他方式可以選擇。政府最終意識到家庭暴力作為一項社會問題的嚴重性,然而,司法機關受制于效率和保護社會弱者的沖突目標中,很難從體制上系統和全面地解決這一問題。
三、審判對證據的不認可
對家庭暴力低確認率和低賠償率的一個普遍解釋是受害者無法提供充足的證據。37前引注11。然而,張劍源發現,47%的受害者提供了證據。38張劍源:《家庭暴力為何難以被認定?》,載《山東大學學報》2018年第4期。正如前面提到的,只有10%的家庭暴力申訴得到認定,39前引注7。只有17.3%提交的證據得到承認。40前引注11。受到家庭暴力的陳述是最普遍的證據形式,但法官大多不理會,因為它們是單方證據,對方當事人也經常否認。下一個問題是,法院認定家庭暴力的證據標準是什么?
一般來講,“誰主張,誰舉證”,民事案件的舉證責任在原告(《民事訴訟法》第63條)。法律規則是,只要提出訴訟請求,就應當提供證據。然而,就家庭暴力而言,《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審理指南》規定,受害人的陳述比被告的陳述更可信(第41條)。當原告提供受傷害的證據,并主張是被告的行為導致的,舉證責任應當轉移至被告(第40條)。41參見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審理指南》,2008年3月發布。
《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審理指南》是由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最高人民法院下屬的非司法機構——頒布的。從法律上看,審理指南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司法解釋,至多算是最高人民法院下屬機構的一個指引。它不是法律,因此法官不必遵守,有些法官說他們甚至不允許在判決文書中引用。根據現行的證據規則,如果受害者不能提供強有力的證據(如醫療傷害鑒定或警察報告),便不符合指控施暴丈夫的舉證責任要求。在這些案件中,大部分法院沒有辦法,只能不去理會家庭暴力的存在。42Phillip Huang, Chinese Civil Justice, Past and Present,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0, pp.133-134.無論如何,法官對此享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權。法律并沒有明確“多嚴重的虐待”是家庭暴力。所有輕傷都是家庭暴力嗎?打一下是嗎?如果不是,多少次才是足夠的?打多長時間?法律對這些問題沒有明確規定,而是留給法官自由裁量權。另外,法官就是否親自收集證據也有自由裁量權。《民事訴訟法》規定,原告需要對其訴訟請求提供證據,但是法官在認為需要時可以依職權收集證據。盡管如此,法官很少走出法庭收集證據。43Xin He, "Routinization of Divorce Law Practice in China: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Influence on Judicial Behavi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Policy and the Family, Vol.23(2009) ,pp.83-109; Ibid; Margaret Woo, "Shaping Citizenship: Chinese Family Law and Women", Yale Journal of Law & Feminism, Vol.15(2003), pp.99-134.
法官在自由裁量權下如何判決家庭暴力的訴訟請求?以下事件是發生在反家庭暴力的試點地區珠江三角洲的一次審判。妻子指控丈夫在很多場合打了她。她出示了警察的到訪記錄、醫療報告和傷痕照片。然而,她的丈夫是一位大學老師,決心反駁每一項指控。他也出示了醫療報告和自己的傷痕照片,聲稱是妻子打了他。當法官問起事件的細節時,女方說:
……他抱怨我關門太大聲,可能會弄壞門。為此我們吵了一架。他對著我的頭指過來,這是打我的前兆。我躲過了他的手,跑到客廳。他追著我,揍了我五次。接著,他抓住我的頭發,把我頭往地上撞。我的前額腫了,我申請人身保護令時向法官展示過。接著我舉起凳子向他反擊,直到小區保安到達。
男方回復道,“是的,當我指著她時,她拿書砸我。我一直在猛低頭。緊接著她抓起東西就向我砸過來。我試圖阻止她,然后她舉起了凳子。”
當法官問他,女方頭上和額頭上的傷是哪里來的,他首先說他不知道,接著說,“是她抓我和傷我的。我有照片為證。我沒有打她。我有可能在自衛時傷到了她。”
在這段對話中,盡管女方提供了詳細的陳述,男方仍把自己說成是受害人。他避開了女方提到的“他追著我,揍了我五次”,他說,“她拿書砸我”,“緊接著她抓起東西就向我砸過來”,以及“她舉起了凳子”。他不承認女方的所有傷害指控,盡管他可能無法解釋她前額和頭部傷痕的原因。他提到在自衛時可能傷到了她。法官并沒有引導男方承認實施家庭暴力。當法官問他關于原告的每一處傷痕時,他說“我不知道”或者“我沒有看到”。顯而易見,這個男人很狡猾且難以對付。另外,他很有經驗地保留了前臂、胸口和手指上被抓咬的淤青和劃傷的醫療報告。
盡管如此,妻子提供的證據更具說服力。記錄顯示,妻子在被丈夫打后報警,她的頭腫得比較厲害。她的醫療報告表明她右腿、左膝和左眼青紫,全身多處軟組織挫傷。她左手拇指有傷,頭上有腫塊,大部分傷痕是撞擊和毆打形成的;而丈夫的傷痕更像是妻子自衛留下的。
此外,法官在證據上更傾向于相信女方。和上一代的離婚法官一樣,她沒有詳細調查夫妻的鄰居或單位,但是她有五份當事人和兒子的證言。這些證言表明撫養權和家庭暴力的問題。以下是法官和11歲的當事人兒子的對話片斷:
法官:你媽媽之前受傷過嗎?
兒子:是的。一般我爸爸會把她推倒在地,然后踢她。我媽媽的頭受傷了。
法官:你父母打你嗎?
兒子:有的,兩個人都有。
法官:他們怎么打你的?
兒子:我媽一般用筷子打我的手,我爸甩我巴掌。
法官:打得厲害嗎?
兒子:我爸爸打我打得嚴重。他把我的頭撞到墻上。
法官:你爸爸多久像這樣打你?
兒子:不常這樣。但另外一次,他把我的頭撞到地上。
法官很專業:她的問題包含是否存在毆打、如何發生、頻率和誰更暴力一些。總體而言,兒子的證言表明他的父親比母親更暴力。他“把她推倒在地,然后踢她”。同樣地,他也打自己的兒子,把他的頭撞到墻上和地上,而母親只是“用筷子打我的手”。
實際上,另一個錄制于兩個月前的證言表明,當丈夫知道兒子選擇和母親生活在一起時,丈夫打兒子并強迫他錄制視頻,讓他說想和父親生活在一起。
證據并不絕對有利于女方。男方有自衛的傷痕記錄,從而抵消了女方證據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然而,丈夫更可能實施家庭暴力:他身強體壯;女方的重傷很難用自衛來解釋;兒子的證言也表明“我爸爸打我打得嚴重”。由于兒子是中立方,他的證言更有說服力,如果不是被逼或引導,他沒有說謊的動力。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審理指南,這類證據應當認定為“重要證據”。即使根據民事審判的證明責任規定,這樣的證據程度也足以支持女方的請求。
最終,法官勇敢地判決準予離婚并將撫養權判給妻子,雖然這是第一次離婚訴訟。法官同情妻子和兒子,希望他們盡快擺脫暴力的家庭環境。然而,法官并沒有認定存在家庭暴力。法官告訴我們她的想法:
簡單說,不認定家庭暴力是因為這個丈夫麻煩、難對付。我們通常稱這種需要給予特殊關注的人為“貴賓”。我想,離婚和孩子撫養權能夠幫助妻子和兒子脫離暴力環境。我希望在沒有認定家庭暴力的情況下,丈夫不用戴著施暴者的帽子,比較容易接受這些決定,也會愿意放妻子和孩子走。
這個故事說明法官經常使用平衡術。她已經支持了妻子兩個主張——離婚和撫養權,也應該讓男方在家庭暴力問題上有所得。她希望男方接受這樣的結果,不要上訴。如果輸掉所有,精明且暴力的他肯定會上訴。這是一個有成效的妥協,因為妻子關心的主要問題是離開男方和兒子更平穩地生活。如果法官認定家庭暴力并且支持女方的全部請求,男方可能會用各種訴訟技巧拖延程序,對妻子來說結果可能會更糟糕。這樣的考慮不是沒有依據的。事實上,男方仍然不滿意撫養權的結果而選擇上訴。二審法官撤銷原判,改判撫養權給他。雖然在撫養權問題上有不同判決,兩級法官對家庭暴力的相同策略是:安撫男方;雙方能夠接受的決定比家庭暴力的法律標準更重要。因此,社會效果取代法律效果——法律規則服從于法官的制度約束。
該審判發生在反家庭暴力的試點地區,絕不是個別做法。就家庭暴力的認定而言,其他地區的處理方式更不利于女方。一位陜西法官告訴我,她只處理那些發生在庭審中或庭審后的家庭暴力。審判前發生的暴力事件只是判斷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一個因素。一旦原告撤訴,有些法官會把糾紛當作沒有發生。44李瀟瀟:《我國民事一審撤訴的程序設計研究》,載《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Ethan Michelson,“Decoupling: Marital Violence and the Struggle to Divorce in China”, (2018), p. 48,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3245030.張劍源發現法官不愿意認定家庭暴力,即使受害人已經提供大量證據。45前引注38。判決文書中有一段這樣寫道:
經審理查明:……2014年9月24日,原、被告雙方發生矛盾,在雙方推搡過程中,被告汪某甲對原告肖某右臉龐部擊打一下,致原告肖某右臉龐部青腫。本院認為:……本案中,原告肖某向法院提交的證據僅證明被告汪某甲僅有一次毆打行為,又未造成一定后果,屬于原、被告夫妻之間的日常吵鬧、偶爾打鬧且尚未造成后果的家庭糾紛,故不能認定為家庭暴力。
張劍源評論道:“‘一次’是法官不予認定家庭暴力的重要標準,即便這“一次”打的后果是‘右臉龐部青腫’。試問,臉被打得青腫,這后果算是嚴重還是不嚴重呢?”46前引注38。張劍源在另一個案件中進一步發現,法院認為司法鑒定機構評定“輕傷”不足以成立家庭暴力,因為“它沒有造成嚴重的后果”,即使傷痕已經符合刑事責任的標準。47前引注38。在另一案件中,法官不顧警察發布的“家庭暴力警告信”,認定家庭暴力的證據不足。48前引注38。他的研究表明大部分法官并不重視受害者陳述。此外,在13%的家庭暴力訴訟請求中,法官很少關注受害者提供的其他有力證據。
在這樣一個案件中,原告指控丈夫經常“把她打得青一塊紫一塊”。尤其是2014年5月28日那一次,她的丈夫把她往死里打,之后她打“110”報案,第二天向婦聯求助。她繼續指控2014年7月8日被告差點把她掐死,當她打他的手時,他才放開。她提交醫療記錄作為支持其家庭暴力指控的證據。被告質疑證據無法證明是他造成的傷害,是她先把食物潑他臉上讓他看不見的。49Ethan Michelson, "Decoupling: Marital Violence and the Struggle to Divorce in China", (2018), p. 46,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3245030.
即便如此,法院仍不準許離婚。雖然該片斷沒有明確提及法院是否認定家庭暴力,但可視為“沒有認定”,因為家庭暴力是離婚的法定理由,沒有離婚意味著沒有家庭暴力。盡管有“幾乎把她掐死”的陳述和警察與婦聯記錄的“醫療文件”,法院還是做出了決定。
四、罕見的“成功”
我在田野調查時收集的所有案件中,只有一例認定家庭暴力的案件,至少是在一審。這類案件的罕見,已經說明法院認定家庭暴力的困難。即使在這個案件中,我還必須給“成功”加上引號,這是因為二審法院最終撤銷了一審支持受害者的判決。雖然在特定環境下,受害人有機會成功,但這樣的機會少之又少。這個案件表明法院無法通過執行法律保障婦女權益。
38歲的原告起訴和魚販丈夫離婚,主要是因為“他打了我無數次”(魚販案件)。本次婚姻之前,她曾和一名吸毒者結婚,有一兒一女。第一段婚姻所生的女兒和原被告同住,現在的這段婚姻兩人育有一子。庭審的核心問題之一是家庭暴力。原告說:
從孩子出生那個月起他就打我。他用鐵管打我。他說我是個離婚女人,沒有人要我,無處可去。他娶我是因為他同情我。所以他想什么時候打我就什么時候打……我們因小事爭吵,然后他開始打我。他用很大一根鐵管打我的腰,用磚頭敲我腦袋。
被告回答,“原告要打我,我逃跑。她便在街上追我,踩到一塊香蕉皮摔倒了”。此外,被告在離婚訴訟答辯書中提到,“原告脾氣火爆,她用啤酒瓶打我。在我幾乎失去意識時,她拿刀來追我。后來鄰居把她制止了”。
原告提交了醫療報告和警察所準備的協議:原告支付給被告1500元后,被告便從他們的公寓中搬出去了。在警察的建議下,她申請了人身安全保護令。事實上夫妻兩人已經分居超過四年,四年間被告多次打原告。
法官的判決有利于原告:
原告指控被告向其實施家庭暴力并提供醫療報告和警察準備的協議。從醫療報告中看,原告頭部后面有兩厘米傷口,頭皮上的皮膚擦傷,肋骨斷了,全身多處軟組織挫傷。這些傷痕不可能像被告所說是因摔倒造成。相反,這些傷痕與她指控被告用大管子打她腰部和用磚頭打她的頭是吻合的。被告聲稱原告打他,但他沒有提供證據。被告在身形上比原告大。原告不太可能攻擊到被告。作為一個成年人,被告應當知道打別人頭的嚴重后果。用磚頭打原告的頭表明他不能控制自己的暴力行為,這構成了嚴重的個人安全威脅。因此我們支持家庭暴力的存在。
由于家庭暴力成立,盡管這只是第一次起訴,法官準予原告離婚。她還把15歲兒子的撫養權判給了母親,因為家庭暴力實施者不適合養孩子。盡管如此,法官沒有判予任何金錢補償,顯然是為了平衡訴訟雙方當事人。如果另一方已經獲得撫養權,就不能再要求撫養費。
這是家庭暴力得到承認并寫在判決書中的少數案件,這樣的成功取決于兩個原因。第一,受害人的強有力證據:醫療報告,詳細的傷痕情況,與受害人陳述吻合;警察準備的和解協議;以及人身安全保護令。和其他面對家庭暴力指控的男方一樣,他不承認所有的指控,但是他的辯護不夠聰明。他說原告踩著香蕉皮滑倒了,這和醫療報告上顯示的原告腰上、背上的傷情不符。他聲稱女方用啤酒瓶和刀等暴力工具打了他,但他沒有提供任何傷情或其他可以支持指控的證據。第二,法官想要幫助受害人。法官年輕、有性別意識、有能力以及專業,她同情女方,希望把她從暴力丈夫那里解救出來。她引用了詳細的醫療報告證明那些傷是由毆打形成的,不可能是摔倒形成的。她還提出尖銳的分析:男方體形上有優勢,女方不可能攻擊得到他。正如賀欣和吳貴亨已經發現的,法官收集證據的技巧和意愿對保障家庭暴力受害者至關重要。50Supra note 24.
但是到了最后,原告這個罕見的勝利僅維持了很短時間。被告上訴后,盡管二審法院同意一審發現的事實,為安全起見,法官還是判決駁回了離婚請求。“在這個案件中女方是第一次提起離婚訴訟。雙方已經在一起生活了10年,還育有一子,再加上女方上一段婚姻帶來的女兒,說明他們之間還有一定程度的感情基礎。上訴期間,男方拒絕離婚且要求法院調解和解。因此我們認為雙方的感情尚未完全破裂。”
不準予離婚的上訴判決駁回了一審法院的家庭暴力認定,它說明離婚案件的日常實踐很難被改變:大多數一審案件判決不準予離婚,即使是已經實施嚴重家庭暴力的案件。51See He (note 44); See Michelson (note 50).二審法官的行為很容易理解:不準予離婚,為什么還要去探究家庭暴力的問題?
案件被駁回后,一審法官之后是否改變她的策略?換言之,如果二審法院并不支持她的判決,為什么她要支持女方?她所在法院的院長告訴我,他們對法官們在這類案件中被二審法院駁回的情況比較寬容。然而,在大多數其他法院,案件被駁回會影響法官考核,為什么法官要冒險呢?如果這個案件不能代表全國的情況,其他法院保障婦女權益的情況只會更差。法官更多考慮自我保護,不太愿意收集家庭暴力的證據,或者激怒施暴者。
在很多其他案件中,受害人沒有這么幸運。一位北京的男法官說:“我知道女方提到的家庭暴力是真實發生的,但是她沒有提供證據,沒有證據我便不能支持她。為什么法官必須要收集證據?首先,我太忙,無法收集;其次,這不公平。法律明確提到誰主張誰舉證。”對這個法官來說,保持公平是無動于衷的借口。一位北京女法官的觀點更有代表性:“除非證據非常強有力,否則我會在第一次起訴時判決不準予離婚。畢竟,我必須要考慮二審法院的意見。即便準予離婚的理由很充分,二審法院很少推翻我們不準予離婚的判決。但是,他們對判決離婚的觀點不同。當案件上訴后,二審法官很緊張,他們不擅長處理那些麻煩的人,于是就推翻我們的判決。”對二審法官來說,推翻一審法院的意見可能會招致一審法官的不滿,但是不安撫麻煩的當事人可能會對職業前景和工作安全產生不利影響。在這點上,法院無法認定家庭暴力是一個系統性問題。一位特立獨行的法官不可能改變總體情況。
大部分法官沒有在判決中提到家庭暴力,是因為考慮到效率和社會穩定。尤其是對二審法院推翻判決的擔憂,很大程度上影響對家庭暴力的認定。這些法官受到上級法院的嚴格審查,不想在沒有充足證據的情況下作出判決。制度環境使法官們選擇一條安全的路:忽視家庭暴力的存在。法官小心處理這類案件情有可原,自我保護可能是最重要的心理因素。下一級法官長期受到上訴率的困擾。由于錯誤判決,年輕法官可能受到紀律處分或其他壓力。例如,1999年,約50%的案件上訴。在這些判決中,只有大約四分之一(26.6%)的案件維持原判。52Jianhua Zhong and Guanghua Yu, "Establishing the Truth on Facts: Has the Chinese Civil Process Achieved This Goal?,"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and Policyp, Vol.13(2004), p.428.
五、拖延判決中的延續暴力
如果上述論述已經反映出因調解和判決所生成的暴力,那么處理案件的過程也會產生暴力。如前所述,盡管夫妻感情已經破裂,拒絕首次提出的離婚申請是法院處理離婚案件時一種固有做法。事實上,對于任何爭議很大的案件,即使當事人不是首次提出離婚,拖延裁決也是法院普遍會采取的一種策略。多項研究表明,53前引注38;See Michelson (note 50 above); Jian Wang, "To Divorce or Not to Divorce: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Court-Ordered Divorce Mediatio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Policy and the Family, Vol.27(2013),pp.74-96; Yu Wang and Kwai Hang Ng, "By the Law? - How Chinese Judges Rule on Contested Divorces", (2019) Forthcoming, Manuscript with author。即使家庭暴力已經被承認或確立,一些法院仍拒絕判決離婚。法院的判決忽略了這一部分,直接判決駁回;關于家庭暴力問題的更多討論將無可避免地降低駁回判決的合法性,甚至與之相矛盾。
這種表面中立的拖延做法,會在受到家庭暴力威脅或已經成為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婦女中加劇兩性不平等。只要不準予離婚,婚姻仍然完整。在人身保護令制度之前,法院對家庭暴力的指控不做任何有效處理。一些法官可能會進行形式化的口頭警告或勸說。更多的情況是,沒有警告,也沒有補償,什么都沒有。這是令人反感的官僚主義。不準予離婚的判決似乎支持了那些拒絕離婚的男人的請求。男性對女性的仇恨和報復可能會通過進一步的家庭暴力得到釋放。許多人向他們的妻子吹噓說:“你想和我離婚?連法院也對我無能為力,它站在我這一邊。你還能做什么?”因此,一些被告可能會因為原告提起離婚訴訟而對原告進行報復也就不足為奇了。同時,為了離婚,女方可能會使沖突升級,以便為下一次起訴收集更多證據。雖然案件各有不同,但都具有同一種模式:家庭暴力持續存在,并在某些案件中加劇。俗話說得好,遲到的正義非正義。
大量訪談材料、法庭文件,甚至是法庭判決,都可以看到不準予離婚的可怕后果。一份第二次起訴書中寫道:54See He (note 43).
如果上次離婚申請得到批準,就不會發生下面這些事情:2000年12月28日,我不在家時,另一方(丈夫)的情人來到我的公寓。當他們發生性關系時,他們把我女兒鎖在了公寓外面,那是在寒冷的冬夜,我們仍是夫妻。當我第二天在他的工作單位指責他的這些行為時,他用木棒打了我。我的脖子、腰和脊柱都受了重傷,甚至站不起來。即使花了2萬元到3萬元接受各種治療,我仍然幾乎癱瘓。結果,我喪失了工作能力。我現在只想離婚。
一份人身保護令的申請中寫道:“在法院駁回了第一次提出的離婚申請后,被告仍不思悔改。相反,情況變得更糟。他威脅我,詛咒我,打我。即使現在,我的身體和頭部仍然有傷疤。”
陜西一位保護令申請者在接受我的電話采訪時說道:“有一天我失去了知覺,住進了醫院。我懷疑他給我吃了過量的安眠藥。他患有精神分裂癥,因此可能試圖在我失去意識后和我發生性關系。但我沒有證據證明,法院駁回了我的離婚申請。我回到娘家,他說,只要法院不批準離婚,我就仍是他的妻子,我必須和他一起回家;否則,他會在我娘家鬧事。有一天,當他用力抓住我時,我媽媽擋在他前面。他把我媽媽推倒了。”
這名女性的經歷再次表明,拖延判決的后果可能是災難性的,它把受害者置于危險之中。由于無法提供安眠藥的證據,這名女性的離婚申請被駁回。與偶爾有暴力行為的丈夫待在一起意味著她的生命處于危險之中,她可能會被強奸。這個男人更加自信了,甚至吹噓他會打他的岳母。
另一位因首次判決駁回離婚申請而提起上訴的陜西婦女告訴我:“我害怕回家,因為他每次喝醉都會打我。現在我住在出租房里,做臨時工,很難養活自己。他拒絕離婚,因為他聽說一旦離婚,一大筆土地補償費將歸我所有。法院駁回了我的離婚申請。我提起上訴,但是將近6個月過去,我沒有從上訴法院得到任何消息。我給上訴法官打電話,但只有他的書記員接了電話。書記員說我應該等等,因為安排庭審需要時間。在我打了四次電話后,書記員變得不耐煩,掛斷了我之后的電話。”
目前還不清楚為何在該案上訴6個月后法官仍未安排庭審。面對麻煩的訴訟當事人,法官只會拖延庭審,延長判決時間。這可能就是為什么法官甚至不接原告電話的原因,結果是這位婦女一直不敢回家。
很難知道這些事件的發生在多大程度上是因為不適當的駁回裁決。然而,對于許多案件,法官們第一眼就知道,僅僅通過給予6個月的冷靜期不能使雙方和解。盡管如此,只要有證據表明這對夫婦仍然可以住在同一屋檐下,他們就會做出不準予離婚的裁決。雖然這類法庭判決偶爾會挽救一段破裂的婚姻,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判決只會進一步惡化夫妻之間本已緊張的關系,而且他們之間的沖突可能會升級。55梅戈飛:《設置“離婚冷靜期”法院也得“冷靜”》,載《四川法治報》2017年3月23日,http://www.scfzbs.com/kf/201703/55859636.html。畢竟,當原告決定向法院提起離婚時,他們一定已經爭論了多次。當他們最終克服了猶豫,決定在法庭上與另一半對簿公堂時,挽救這段婚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田野調查顯示,在被判決駁回離婚請求后,原告對另一半的信心會進一步下降。56同上注。
拖延策略與性別有關。由于提出明顯虐待指控的原告中有90%是女性,她們因這種拖延做法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鑒于約70%的原告是女性,她們的訴訟請求更有可能被拖延。
六、人身保護令的有限作用
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于2016年3月1日起生效。我有十位受訪者已經從陜西法院和珠三角法院獲得了這樣的保護令,她們認為人身保護令是有效的。她們大多數人都生活得謹慎小心、脆弱且無助。有些人能幸運地回到她們的娘家,其他人則不那么幸運。男人會在她們的工作場所騷擾她們,一些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對所有這些受害者來說,法院的人身保護令是她們的救命稻草。一位申請人說:“保護令下達后,他就不再騷擾我的娘家人了。”另一個說:“他被法庭傳喚去談話后,就不再在我上班路上攔截我了。他也不會在我的工作場所鬧事。”還有一個說:“他不再給我發辱罵和威脅的短信,我們也不用住在一起。”一名廣東法官告訴我,人身保護令限制男方回家。顯然,他誤解了其中的含義:人身保護令只是禁止男方接近起訴人,并不一定禁止男方回到自己的家。撇開誤解不談,這個故事揭示了人身保護令的威力。法官們認為,人身安全保護是有作用的,甚至對那些認為自己有充分權利毆打妻子和拒不改變自己行為的男人也是有效的。
這樣的積極評價并不能掩蓋整體上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實施上的慘淡:統計數據和我的田野調查表明,人身安全保護令的申請和批準數量極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顯示,過去5年期間,全國法院僅發布2154條保護令,而受理的離婚案件有850萬件。考慮到中國有3000多家法院,這意味著在過去5年里每家法院平均發出的人身安全保護令不到一項。57周強:《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2018年3月9日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載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lh/2018-03/25/c_1122587194.htm,2019年8月2日訪問。另一份報告估計,從2016年3月到2017年6月,全國法院只發布了1284條保護令。58《〈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家庭暴力法〉實施監測報告》, 載http://www.equality-beijing.org/newinfo.aspx?id=69,2019年6月1日訪問。同樣,在16個月的時間里,每家法院平均只發布了半個人身保護令。陳葦和段偉偉發現,重慶市地方法院在過去三年里只發布了兩項人身保護令。59前引注10。在我進行田野調查的所有法院中,發布人身保護令的情況很少見。早在《反家庭暴力法》頒布之前,珠三角法院就已是這一措施的試點法院。盡管接收了500多起離婚案件,但珠三角法院每年只下達三份人身安全保護令。陜西省法院被譽為實施該機制的典范,在兩年多的時間里下達的人身安全保護令也才不到10份。
數量如此之少的一個原因是受害者對該保護令缺乏了解。例如,在魚販案中,直到警方介入,女方才了解到這種機制。在過量服安眠藥婦女案中,法院駁回她的離婚申請,男方一直跟蹤她到娘家,之后她才從鄰居那里了解到這個機制。
但是,這樣的解釋是不充分的。有關這一制度的信息可以在各種媒體上找到,許多政府大樓和辦公室都懸掛著反家庭暴力的海報。一個更合理的解釋是,法院的激勵機制不利于發布這樣的命令:發布這樣的命令為法官增加了額外的工作,降低他們的效率。下達保護令不是一個單獨的案件,這是離婚案件的一部分。然而,發出和執行這類命令的工作量并不亞于處理另一宗沒有這類問題的離婚案件。為了批準這樣的請求,法官必須進行調查,口頭警告被指控的施虐者,并另外向所有相關方傳達命令。為了決定是否批準,法官必須評估家庭暴力的證據。更麻煩的是執行過程。60闞凱、劉劍平:《論〈反家暴法〉人身保護令的困境與出路》,載《知與行》2017年第 5期;李秀華:《人身保護令準入反對家庭暴力立法維度的困境與對策》,載《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13年;易前、黎藜:《人身保護令制度的入法思考——以長沙反家暴審判實踐為視角》,載《人民司法》2017年第7期。與財產執行不同,人身安全保護令的執行涉及人身權,人身權是流動的,法官通常沒有能力監督這一過程,必須尋求警察和街道或村/居委會的幫助。雖然村/居委會接到命令沒有什么問題,但警方更抵觸:似乎法院在給警察下命令,這與他們在三大政法機關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太一致。無論如何,這是警方不愿承擔的額外任務。警方在這個問題上的不作為是有據可查的。61闞凱、劉劍平:《論〈反家暴法〉人身保護令的困境與出路》,載《知與行》2017年第 5期。一位法官告訴我,根據相關規定,警方和居委會也要向法院反饋執行人身保護令的情況,但她從未收到過警方的任何反饋。
這些問題都讓法官頭疼,因此,法官會勸申請人不要提交申請,或者法官會以家庭暴力證據不足為由拒絕批準。62魯瀚陽:《試論人身保護令制度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的適用——以實際案例為視角》,載《法制與社會》2016年第36期;壯金燕:《人身保護令在反家暴中的法律初探》,載《法制與社會》2014年第 3期。《反家庭暴力法》第27條規定,該保護令在兩種情況下發布:一種情況是發生家庭暴力時,一些法官對“是否有家庭暴力證據”的要求比在訴訟過程中更高;另一種情況是“有家庭暴力的現實危險”,這個定義很不明確。法官經常利用這個模糊的定義,說服申請人撤回他們的申請。他們這樣回應女方的請求:“你們在一起這么多年了,為什么你們不能再在一起待幾個月呢?”,或者是“你們就要離婚了,你為什么還需要這樣的人身保護令?”事實上,許多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的受害者本應在訴訟過程中被告知有這一制度,但法官沒有將人身安全保護令告訴他們。正如那位服藥過量的女性所述,她是通過她娘家的鄰居,而不是通過法官,知道這個制度的。
總之,一旦批準,人身安全保護令是有效的。如果不是法官考慮效率問題,這一機制本應得到更廣泛的應用和更早的批準。盡管如此,考核指標和法官的考量損害了一個本意良好的制度的有效性。法官不愿下達這樣的命令,是人身安全保護令發布數量有限的主要原因之一。
七、結論
我們很難說法官們沒有遵守法律。畢竟,他們確實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也因此,家庭暴力的證據被駁回。當他們采取調解并允許消除家庭暴力問題時,他們的決定是正當的,因為法律允許調解,而訴訟各方包括受害者,已經同意了這點。當他們勸說潛在的受害者放棄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時,受害者不管情愿與否,都會接受他們的勸說。家庭暴力很少與是否同意離婚、監護權之爭或財產分割的決定有關,僅僅因為法官裁定雙方的感情沒有破裂到不可挽回地步。邁克遜(Michelson)甚至認為:“法院最好的情況是視而不見,最差的情況是濫用法律駁回女方離婚申請。”63Supra note 49,p.2.
我也許不完全同意邁克遜的觀點。但是,法官確實沒有足夠努力保護受害者的利益,結果是家庭暴力被淡化,法律的規定沒有得到履行。他們可以采取更強硬的立場。他們為什么不呢?答案就在問題的反面:他們為什么要這樣做?他們有什么動力這樣做?如前所述,他們的目標是以一種安全、高效的方式解決這些案件。對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說,家庭暴力只是婚姻是否應該繼續的一個邊緣證據。如果受害人提出有力的證據,他們可能接受。如果沒有,法官們很少做出特別的努力。為家庭暴力取證只會增加法官的工作量。未被充分應用的保護令只是一個例子。這意味著只有具有兩性平等意識、有能力和負責任的法官才會為家庭暴力收集證據,魚販案中的法官是例外而非常例。只要案件能夠和平、安全地結束,一些證據注定永遠被埋葬。當離婚申請被駁回時,就沒有必要調查家庭暴力問題。肯定要離婚時,無論是調解還是判決,主要的問題是確定監護權和財產分割,為什么法官還要關注家庭暴力?當雙方都接受離婚,他們為什么還要糾纏于家庭暴力問題?此外,許多施暴者性情惡劣、精神不穩定或有暴力傾向,他們的仇恨可能會從妻子身上轉移到法官身上,法官為什么要引火上身呢?因此,若想加強法庭對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保護力度,未來或許需要對法官身處的考核機制進行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