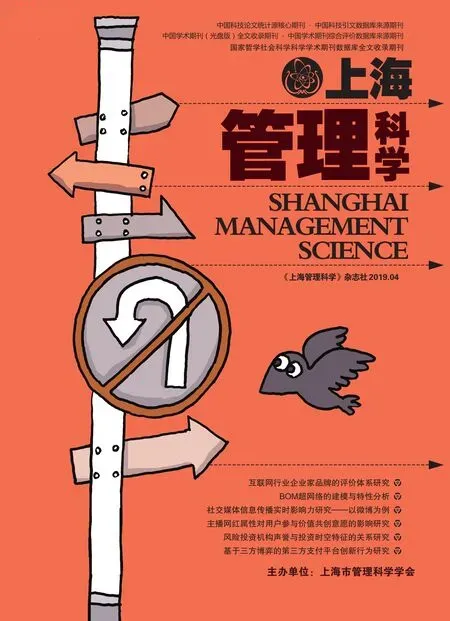新生代工人主觀幸福感、組織公民行為以及離職的關系研究
劉昊雯 沈 克
(上海外國語大學 國際工商管理學院,上海 201620)
1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1.1 離職
離職(Employee Turnover)的概念包括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Price (2001)的廣義定義認為,離職是個體在組織中職位狀態的改變,包括入職、晉升、降崗、內部轉崗以及流出等。Mobley等(1978) 的狹義定義認為,離職是指在組織中獲取物質收益的個體終止其組織成員關系的過程。后者強調了組織與員工雇傭關系的中斷,又將下崗等從此概念中分離出來。Mobley的離職構成模型認為,工作中的不滿會促使員工開始思考辭職的事情,然后員工會權衡找到新工作的優勢與辭職需要付出的代價(例如假期、發展前景、年終獎等因素),當員工認為換新工作的收益能夠完全彌補辭職所帶來的損失時,員工會決定尋找新職位并付諸行動(Wright & Klotz, 2017; Siu & Cheung, 2014; Huffman & Casper, 2014)。員工的離職無疑是對公司前期培訓資源投入的巨大浪費,他們帶走的不僅是顯性的人才,也包括隱性的公司資源、技術、力量、文化、力量等(葛優,2019)。
1.2 主觀幸福感與離職行為
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 是個體對自身生活產生的評價具體化。Diener(2003)將幸福感定義為“主觀幸福感是指人們以自己主觀而非客觀上的標準為依據,對其生活各領域的滿意度的界定,是評價者自己對其生活質量滿意程度和情感體驗方面的評價”。Diener及其同事將幸福感劃分為四個維度:(1)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生活的滿意度;(2)積極的情感體驗;(3)消極的情感體驗;(4)對生活各方面的滿意度。當前的已有研究發現主觀幸福感的結果變量包括工作績效、工作滿意度、缺勤率、離職傾向與組織認同等。Mobley的離職構成模型認為,工作中的不滿會促使員工開始思考辭職的事情,然后員工會權衡找到新工作的優勢與辭職需要付出的代價(例如假期、發展前景、年終獎等因素),當員工認為換新工作的收益能夠完全彌補辭職所帶來的損失時,員工會決定尋找新職位并付諸行動(Wright & Klotz, 2017; Siu & Cheung, 2014; Huffman & Casper, 2014)。根據Diener的主觀幸福感維度劃分,工作與生活中的滿意度與積極情緒是個體主觀幸福感的主要構成部分,工作滿意度既是主觀幸福感的結果變量,又是主觀幸福感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可以推測個體的主觀幸福感與員工的工作離職行為成負相關關系,由此提出假設1:
H1:員工的主觀幸福感水平對其離職行為的發生概率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
1.3 組織公民行為與離職行為
1983年Bateman & Organ正式提出了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簡稱OCB)的概念。他們認為組織公民行為是一種有利于組織的角色外行為和姿態,不是正式角色強調的,不是勞動合同引出的,而是由非正式的合作行為構成的。1997 年Organ 又將組織公民行為的定義修正為“一種類似于關系績效的,能夠對組織社會和心理環境提供維持和增強作用的行為”。
在對組織公民行為維度的研究中,Organ的五個基本維度影響最大。這五個基本維度(Organ 1988)包括:一是利他主義,例如幫助同事完成與組織相關的任務的行為;二是運動員精神,例如員工愿意實施如加班等額外責任的行為;三是責任意識,例如主動提出改進工作的建議的行為;四是禮節,例如主動避免在工作上與他人發生爭端;五是公民道德,例如忠誠于組織、主動維護和提升公司形象。組織公民行為更多的是員工意志的表現(Shore & Barksdle,1995)。根據認知一致性原則,即當個體的認知與其行為不一致時,會帶給個體強烈的不適感,所以在認知一致性的驅動下,“組織公民”會降低實際離職行為的發生概率(Saraih et al., 2017; Saif-Ud-Din & Adeel, 2016; Memon et al., 2017)。
根據社會交換理論,管理者會因為員工表現出的組織公民行為給予員工員工更多的組織資源支持與更高的績效評價,而“組織公民”會因為組織的獎勵繼續維持自身的組織公民行為,這樣實現一個良性的循環。但是離職行為的出現毫無疑問會打破這個循環,給員工自身與企業帶來負面的收益。因此,降低員工自身的離職意愿與離職行為的發生概率是組織公民行為最主要的結果變量之一。由此推斷,員工表現出的組織公民行為水平越高,其離職的可能性越低。因此,我們得出以下假設:
H2: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對于其離職行為具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
1.4 組織公民行為的中介作用
當前已有的研究證明組織公民行為對于組織的發展有著十分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讓許多學者開始關注誘發組織公民行為的因素。對于組織公民行為有影響的前置變量如下:(1)員工的人格特質(Shaffer et al., 2015);(2)員工態度(Yildirim,2014);(3)員工的公平感(Ekowati et al.,2013);(4)領導行為(Ugwu et al., 2016);(5)任務特點(Astrauskaite et al., 2015)。其中,員工的人格特質是主觀幸福感的主要決定因素,而員工態度最主要的是指員工的工作滿意度,工作滿意度是主觀幸福感的主要構成因素。推導得出,主觀幸福感是誘發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重要因素之一。
組織公民行為的結果變量同樣是學者研究的重點之一。從個人層面而言,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能夠提高自身的績效評價、獲得更多的組織支持、降低自身的離職意愿與離職行為的發生概率;從組織層面而言,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能夠提高企業的產能、增加企業利潤、降低企業的運營費用,并提高企業的運轉效率(Murtaza et al.,2016)。Fredrickson(2001)認為快樂情緒能夠在工作中發揮積極的作用,可以使員工拓展人際交往的范圍,并且降低缺勤率和離職率。處于積極情緒狀態的員工會采取積極的行為來維持自身的情緒狀態(Ng et al.,2016),這更有利于其進行社會互動,實現其與周圍同事與環境的整合(Diener et al., 2015;Zelenski & Nisbet,2014)。這種積極互動的有益反饋會促使處于積極情緒狀態的人更加利他,實現一個良性的循環過程。并且Rego et al.(2010)在其研究中發現幸福的員工更傾向于幫助他人、更有同情心,更容易表現出組織公民行為。善于表現組織公民行為的員工往往對于組織具有更強的認同感與忠誠感,會降低其離職行為的發生概率(蘇方國, 趙曙明,2005)。積極情緒能夠促使員工對“工作真諦”有一個更深刻的認識(Rego et al.,2014),認識到努力工作不僅僅是為了更高的薪酬或者事業的成功,更重要的是享受努力工作本身帶來的樂趣,組織公民行為是實現這種狀態的一種途徑。綜合以上推導,提出假設3:
H3:組織公民行為在主觀幸福感與離職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
1.5 主觀幸福感的性別差異研究
在研究個體的主觀幸福感對其離職行為的影響時,需要考慮個體的性別差異。
從家庭模式來看,已婚的男性和女性承擔著不同的家庭角色,通常丈夫的成功往往與他們的事業聯系在一起,以養家糊口為義不容辭的責任,他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和社會地位上,更多受社會地位、工作性質和經濟收入等因素的影響。在如此的社會角色期待下,男性的幸福感往往建立在事業與經濟收入的成功之上,而這往往需要耗費大量的精力,因此對于男性而言當一份工作過多地耗費其精力時其通常會選擇離職以保持更多精力。
而對于女性而言,其生理結構相對于男性更加脆弱,對于壓力的承受能力更弱。并且,從社會文化與家庭模式的角度而言,社會賦予女性的角色更主要的是撫育后代、照顧家庭。Allen et al. (2001)的研究表明:女性的幸福感更多地與外表吸引力和家庭等因素密切相關。無論是從撫育后代的角度,還是從自身的發展而言,身體健康對于女性都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當工作本身危害到女性的身體健康時,相對于男性,其更容易做出離職的選擇。
無論從生理結構、社會文化與家庭分工模式上,男性與女性都有很大的差異。對于男性而言,充沛的精力、物質生活方面的成功與高質量的工作更能帶給其幸福感,而失業與離婚對其幸福感的負面影響更強。對于女性而言,家庭生活是否和諧、養育子女與對健康的擔憂程度則是其主觀幸福感的有效預測指標(Plagnol,2014;Uglanova,2014;Tiefenbach & Kohlbacher,2014)。由此,我們提出本文的最后一個假設:
H4:基于性別差異,主觀幸福感發揮作用的維度不相同。
2 研究設計與方法
2.1 被試
此次的研究對象是制造型企業中的新生代工人,主要是為“80 后”“90 后”,年齡在18 歲到35之間的這一群體。被試為國內不同制造型企業的一線工人,從地域上看,主要有北京、上海、天津、四川、廣東、江蘇等。問卷發放形式主要是電子版、紙質版兩種形式相結合的方式。本研究共發放問卷450份,回收問卷434份,回收率為96.4%。其中,不符合要求的問卷38份,所以最終收到的有效問卷為396份,有效回收率為88%。
被試的平均年齡為(22.18±3.29)歲;男性243人,占比61.4%,女性153人,占比38.6%;初中及以下學歷者22人,占比5.6%,高中及中專學歷者324,占比81.8%,大專及以上學歷者50人,占比12.6%;已發生離職行為的被試有78人,占比19.7%,尚未發生離職行為的被試318人,占比80.3%。
2.2 變量測量
本研究的三個變量(自變量:主觀幸福感;中介:組織公民行為;因變量:離職行為)和三個控制變量(性別、年齡和學歷)的數據均來源于不同受測者,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由領導評價,離職行為來源于員工客觀離職數據。在進行區分性別的中介效應檢驗時,對于男性,本文引入的自變量是主觀幸福感的精力變量,而對于女性引入的自變量則是對健康的擔憂程度。
2.3 測量工具
2.3.1主觀幸福感量表
本文的主觀幸福感量表采用基于Diener的主觀幸福感概念與維度開發,由美國國立統計中心開發的主觀幸福量表(General Well-Being;GWB)。該量表在1997年由段建華翻譯漢化,并進行了基于本土文化的修正,問卷一共包括6個維度,18個題目,采用Likert 6點量表計分,1=完全不同意,6=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明被試主觀幸福感越高,其Cronbach′s α為0.861。
2.3.2組織公民行為
本文選用樊景立教授1997年在臺灣文化背景下對組織公民行為維度研究的成果,問卷共有5個維度、15道題目。組織公民行為的度量采用 Likert 5點計分,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示被試的組織公民行為水平越高,其Cronbach′s α 為0.904。
2.3.3人口學問卷
基于研究主觀幸福感、組織公民行為與離職的關系的目的,以及前文根據對文獻綜述分析后提出的假設,考慮到年齡差異、性別差異以及學歷差異可能對研究變量主觀幸福感及組織公民行為產生影響,于是本研究的人口學問卷主要收集被試的人口學信息中包含年齡、性別與學歷三道題目。
2.4 概念模型的建立
本文將結合相關數據,著重探討制造業的新生代員工主觀幸福感、組織公民行為與其離職行為之間的關系。本文的理論概念模型是在Mobley (1978)離職中介鏈模型(見圖1)和Steers & Mowday (1981)離職模型(見圖2)的基礎上,根據調查問卷設計改進得來的(見圖3)。

圖1 Mobley離職中介鏈模型
資料來源:Mobley, W. H., Griffeth, R.W., Hand, H.H. & MEGLINO, B.M. Review and conceptual analysis of the employee turnover proces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79(86):493-522.

圖2 Steers & Mowday離職模型
資料來源:Steers, R M, Mowday, R T., Employee turnover and post-decision accommodation process. [J]. In: Cummings, L. L., Staw, B. M., ed.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1981:235-281.

圖3 本文概念模型
3 數據分析與結果
本研究采用SAS 9.3進行所有統計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在程序控制的基礎上,檢驗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首先,采用驗證性因子分析法驗證量表之間的區分效度,在本次研究中3因子模型的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為(χ2(528)=918.72,RMSEA=0.058,RMR=0.041,CFI=0.95),表明問卷之間區分效度良好。然后,采用Harman單因素檢驗法,將六個變量的所有題目作為整體一起進行因子分析,在特征值大于1以及未作任何旋轉的條件下,最大因子的貢獻率為10.334%,遠低于50%。據此,本研究可以不考慮共同方法偏差的影響。
3.2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
如表1所示,離職行為與幸福感、組織公民行為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r=-0.223,P<0.001;r=-0.263,P<0.001),個體的幸福感越強、組織公民行為的水平越高,發生離職行為的概率越低。幸福感與組織公民行為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r=0.521,P<0.001),個體的幸福感越強,組織公民行為的水平越高。
3.3 變量的假設檢驗分析
3.3.1組織公民行為對離職行為的回歸分析
如表2所示,在控制住性別、年齡與學歷3個人口學變量后,組織公民行為對實際不離職行為(1為離職,2為不離職)的概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β=0.8136,OR=2.256,P<0.001),組織公民行為(均分)每提高一分,留職的概率便會提高2.26倍。

表1 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和相關系數(N=397)
注:*P<0.05;**P<0.01;***P<0.001
3.3.2組織公民行為的中介效應檢驗
如表3所示,在控制住人口學變量性別、年齡與受教育程度后,主觀幸福感對于實際不離職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M1,β=0.898,P<0.001);主觀幸福感對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M2,β=0.771,P<0.001);將主觀幸福感變量與組織公民行為一同代入對離職行為的回歸方程,主觀幸福感變量的系數不再顯著(M3,β=0.299,P>0.05),組織公民行為變量的系數依舊顯著(M3,β=0.71,P<0.001)。通過bootstrap檢驗中介變量系數95%的置信區間為[0.382,1.316],并不包含0,方程的擬合程度由0.249上升到0.297。

表2 離職行為對組織公民行為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
注:*P<0.05;**P<0.01;***P<0.001
3.3.3區分性別的組織公民行為的中介效應檢驗
將被試按照性別進行分組,分別對男性被試與女性被試進行組織公民行為的中介效應檢驗。
如表4所示,在男性的離職行為分析中,主觀幸福感中的精力變量對于不離職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M4,β=0.518,P<0.001);精力變量對于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M5,β=0.809);將精力變量與組織公民行為變量一同代入對不離職行為的回歸方程中,精力變量的系數不再顯著(M6,β=0.252,P>0.05),組織公民行為的系數依舊顯著(M6,β=0.799,P<0.001)。通過bootstrap檢驗中介變量系數95%的置信區間為[0.37,1.455],并不包含0,且方程的擬合程度由0.3上升到0.36。組織公民行為在精力與離職行為之間起完全中介的作用,如圖4所示。

表3 組織公民行為的中介效應檢驗
注:*P<0.05;**P<0.01;***P<0.001
在女性員工的離職行為分析中,在控制住人口學變量后,主觀幸福感中對健康的擔憂變量對其不離職行為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M7,β=0.334,P<0.001);健康變量對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M8,β=2.149,P<0.001);將健康變量與組織公民行為共同代入對離職行為的回歸方程,健康變量的顯著性降低(M9,β=0.291,P<0.05),組織公民行為變量的系數顯著(M9,β=0.635,P<0.05),

表4 基于性別差異的組織公民行為的中介效應檢驗
注:*P<0.05;**P<0.01;***P<0.001

圖4 男性員工組織公民行為中介作用
通過bootstrap檢驗中介變量系數95%的置信區間為[0.028,1.443],并不包含0。組織公民行為在對健康的擔憂與離職行為之間起不完全中介作用。根據侯杰泰提出的直接效應算法,計算出對健康的擔憂對離職行為影響的直接效應為51.14%,間接效應為48.86%,如圖5所示。

圖5 女性員工組織公民行為中介作用圖
4 研究結論
4.1 員工的主觀幸福感對新生代制造業員工的離職行為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Nimon et al.(2015)通過對42篇文章中來自36個公司的數據進行元分析,發現隨著工作滿意度的下降,員工的離職傾向上升。本文在此基礎之上進行了進一步的驗證,發現基于新生代制造業員工的特殊群體,隨著其主觀幸福感的上升,發生離職行為的概率會顯著降低,對此理論進行了有益的補充。
4.2 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對其離職行為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根據認知一致性原則,即當個體的認知與其行為不一致時,會帶給個體強烈的不適感。所以,在認知一致性的驅動下,“組織公民”會降低其離職傾向,降低實際離職行為的發生概率(Saraih et al., 2017; Saif-Ud-Din & Adeel, 2016; Memon et al., 2017) 。本文在此基礎上進行了進一步驗證,發現了新生代制造業員工隨著其組織公民行為水平的升高,其離職行為概率會顯著降低。
4.3 組織公民行為在主觀幸福感與離職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
首先,根據數據分析得出,個體的幸福感越強,組織公民行為的水平越高。主觀幸福感另一個重要的維度為積極情緒,主觀幸福感水平高的個體經常處于積極的情緒狀態而較少處于低落的情緒狀態。處于積極情緒狀態下的個體更傾向于做出利他的行為,更多地承受工作帶來的不便與困難,而這是組織公民行為的重要維度。本文的結論進一步驗證了該假設。
4.4 基于男女性別差異,主觀幸福感發揮作用的維度并不相同
本文對當前研究的一個有益補充是發現了在組織公民行為發揮中介作用的過程中性別的重要影響,在主觀幸福感對離職行為影響的分析中,對于男性員工而言,發揮顯著作用的是精力維度,而對于女性而言則是對健康的擔憂維度。
從家庭模式來看,已婚的男性和女性承擔著不同的家庭角色,通常丈夫的成功往往與他們的事業聯系在一起,以養家糊口為義不容辭的責任,他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和社會地位上。在如此的社會角色期待下,男性的幸福感往往建立在事業與經濟收入的成功之上,而這往往需要大量的精力。因此對于男性而言,當一份工作過多地耗費其精力時,其通常會選擇離職以保持更多精力。
而對于女性而言,其生理結構相對于男性更加脆弱,對于壓力的承受能力更弱。并且,從社會文化與家庭模式的角度而言,社會賦予女性的角色更主要的是撫育后代、照顧家庭。Allen et al.(2001)的研究表明:女性的幸福感更多地與外表吸引力和家庭等因素密切相關。無論是從撫育后代的角度,還是從自身的發展而言,身體健康對于女性都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當工作本身危害到女性的身體健康時,相對于男性,其更容易做出離職的選擇。
5 研究局限與管理啟示
首先,本研究采用問卷調研的方式,共回收有效問卷396份,其中實際發生離職行為的被試只有78份,離職行為組的問卷相對較少,對于研究來說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可能導致差異性的研究不夠全面透徹。此外,由于被試的地域分布不均,各個制造業的類型分布不均,導致研究結論的局限性。最后,在本次的研究中,所有的數據采集均來自自我陳述式的問卷測量且都為橫截面數據,使得在推斷因果的過程中說服力不足。
本文的創新點在于在幸福感的結果變量方面考慮了性別差異對研究帶來的影響。無論是生理結構、社會文化,還是家庭分工模式,男性與女性都有很大的差異。對于男性而言,物質生活方面的成功與高質量的工作更能帶給其幸福感,而失業與離婚對其幸福感的負面影響更強。對于女性而言,家庭生活的和諧、養育子女與身體健康則是其主觀幸福感的有效預測指標。
本研究有效地擴展了幸福感結果變量的研究,并基于性別差異給予企業以管理啟示:在人員流動本身就已經很頻繁的制造業,留住流動意愿強烈的新生代員工需管理者關注員工的主觀幸福感,并且區分性別,對男、女員工進行差異化管理。對于男性員工,若想降低其離職行為的發生概率,促使其表現出更多的組織公民行為,則應對其實施合理的精力管理,從身體、情感、思想和精神四個方面全面關注男性員工的精力,并保證其精力在周期性消耗后能夠得到恢復與彌補。而對于女性員工,則更應該關注其身體健康與工作家庭平衡,實行定期的體檢與對哺乳期的婦女給予更多的關懷,這些對于降低其離職行為的發生概率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