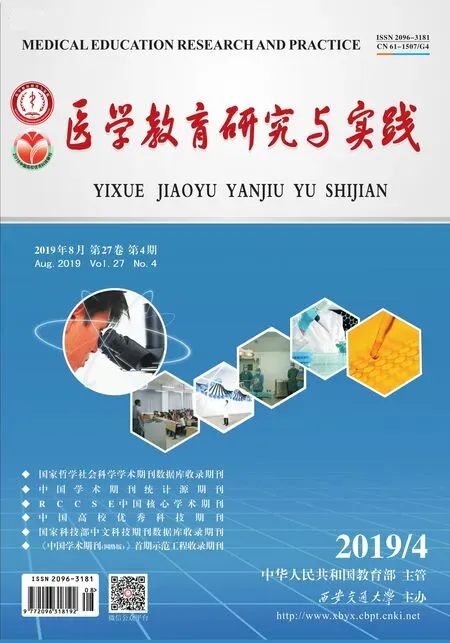戴維·格芬醫學院基礎醫學教育課程分析
馬淑蘭,曾文姣
(復旦大學基礎醫學院:A.實驗教學中心;B.病理學系,上海 200032)
隨著醫學科學的發展,醫學知識極大豐富,學生需要掌握的新知識越來越多。知識的無限性與醫學院校教育時間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整合式課程打破了學科間界限,解決課程內容膨脹問題,在國外已實踐多年,較為成熟,備受國內醫學教育界關注[1-3]。國內已經有少數院校進行了整合課程改革[4-6]。但與歐美及其他地區醫學院校成熟的模式和經驗相比,國內醫學課程整合的改革依然面臨諸多問題,包括:缺乏科學規范的頂層設計,教育目標不夠明確,重形式而輕內涵;組織管理機制尚未真正理順,跨學科協調難度大;師資培訓不到位,激勵政策缺乏;對改革的效果缺乏科學的評估等[7-8]。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戴維·格芬醫學院(David Geffen School of Medicine,DGSOM)1951年開始招收第一批學生,歷時60余年的發展,已經成為全美最好的醫學院之一。DGSOM的羅納德·里根醫學中心連續14年被評為美國“西部最佳醫院”。DGSOM于2003年起,采用“多器官系統”為基礎的整合式教學[9],經過多年的運作和不斷改進,該教學模式獲得了廣泛的認可。本文以該校一年級學生“人體生物學與疾病”第2板塊“心血管、腎臟和呼吸醫學I”的教學為例,深度剖析DGSOM的基礎醫學教育,著重分析理論課課程結構及實踐類課程的組成,以期能為國內醫學院校正在進行的教學改革提供參考和借鑒。
1 DGSOM課程安排簡介
美國的醫學院校入學的學生需要先完成大學教育,有意學醫的學生大學期間課程最低限度應包括1年的生物學、2年化學、1年物理,通過MCAT考試(Medical College Admission Test)后再申請醫學院校[10]。該階段學習的知識相當于國內醫學院校的第一階段大類基礎課。

表1 DGSOM“人體生物學與疾病”課程安排
DGSOM的醫學教育采用以人體器官系統為中心的整合式課程。4年醫學院的學習包括:2年的“人體生物學與疾病”(Human Biology and Disease)課程和2年的“核心臨床實習”(Core Clinical Clerkship)課程。前2年的“人體生物學與疾病”課程有9個板塊。1~5板塊在第一年學習,側重于人體的生理過程;6~9板塊在第二年學習,側重于疾病的病理過程見表1。第3年開始進入臨床階段學習,第4年的醫學生主要進行各科臨床實習。
2 DGSOM“人體生物學與疾病”板塊2課程分析
本板塊為“心血管、腎臟和呼吸醫學I”,涵蓋心血管、腎臟和呼吸醫學的基礎知識。該板塊的教學目標有:了解心臟和循環、腎臟和肺部的解剖和正常生理功能;了解其相互關系,及作為一個多器官系統發揮的功能;領會自主神經系統在其功能和調節中的作用;熟悉其體檢方法;理解主要疾病狀態對器官結構和功能的影響;了解一個器官功能的干擾如何影響其他器官的功能;理解評估診斷測試和治療干預的統計原則;通過提問的方式,學習心血管、腎臟和呼吸系統疾病患者(年輕人和老年人)中存在的獨特問題。
2.1 課程組成
本板塊分為8個主題,共197學時,其中理論課123學時,實踐課74學時見表2。上午的課程以理論學習為主,下午的課程則側重于實踐教學。學生考試包括每周的自評測試(周末自行網上完成),板塊中期考試和末期考試。
基于問題的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是整個教學的中心環節,該板塊有7個PBL病例,其涉及的醫學基礎知識就是該周的教學內容見表3。除PBL外,理論課還包括講授新知識(占63%,78/123)、案例學習、自評講解(評點學生每周自評測試)。實踐課包括兩大類:一類是基于傳統的教學實驗室的學習,占44%(32.5/74);另一類是基于“患者”的學習占56%(41.5/74),見表2。

表2 DGSOM“人體生物學與疾病”板塊2課時分布

表3 DGSOM“人體生物學與疾病”板塊2授課主題和PBL病例
2.2 課堂授課教師的學歷背景
本板塊由2名教授擔任主任,負責安排教學活動,分別是心臟病醫生和肺病醫生。DGSOM的PBL導師來源于一個200人左右的PBL導師庫,有退休教師、兼職招聘人員、附屬醫院的醫生,培訓中的住院醫生以及三、四年級的醫學生。這些PBL導師主要為志愿者。
參與理論課教學的教師共有25人,表4顯示了其學歷及授課時數,近80%的課是由具有MD學位的臨床醫生講授見表4。分析每位教師的總課堂授課時數見圖1。2位板塊負責人分別講授了29、23學時;有2位教師講授了8學時,分別是藥理學教授和腎臟病醫生;2位教師講授了6學時,分別是講授腎臟生理的副教授和心臟生理的教授。這6位教師講授的課程占整個理論課時數的76%,是整個板塊教學的核心成員。部分理論課由2位教師共同講授,包括4次新知識,5次案例學習及2次自評講解。
參與實踐類課程教學的教師有105人,表4顯示具有MD學位的臨床醫生(占77%,81/105)亦是實踐課授課的主要力量,完成了88%(65/74)的實踐課教學。

表4 DGSOM“人體生物學與疾病”板塊2授課教師學歷及授課時數
備注:如一節課由兩位教師共同授課,則給每位教師各記1學時;PBL導師未統計入本表格。其他包括MPH(公共健康碩士),M.Div(神學碩士),M.Ed.(教育學碩士)

圖1 理論課教師授課時數分布

圖2 各系統“新知識”授課時數分布
2.3 課程授課結構分析
理論課的“新知識”部分是學生通過課堂聽講獲得理論知識的主要途徑。我們著重分析78學時的“新知識”的內在結構,以更好地了解教學內容的設置。圖2顯示“新知識”課堂授課中心血管系統學時最多,其次是呼吸系統和腎臟。有10學時的課同時涉及2個或3個系統,表5列出了交叉課的授課題目。另有11學時的“新知識”課堂授課不屬于這3個系統范疇,但與整個醫學知識結構的構筑相關,表6列出了其詳細信息。

表5 板塊2中系統交叉“新知識”課堂授課題目
實踐課形式多樣,有基于傳統的教學實驗室的學習和基于“患者”的學習兩部分。基于“患者”的學習包括行醫(Doctoring)、臨床技能(Clinic Skills)、患者接觸(Patient Encounter)和模擬實驗室(Simulator Lab)。本板塊行醫教學的重點是醫患交流,具體主題見表6。在臨床技能課中,學生學習體格檢查,包括心血管、腎和腹部,以及肺和胸部檢查。在患者接觸課上,學生由主治醫師的帶領進入醫院,接觸真實的患者,包括1位心血管疾病患者,1位腎衰患者和1位肺部疾病患者。模擬實驗室教學中,采取的是以團隊為基礎的學習(Team-based Learning,TBL),包括基于模擬系統(如心血管循環系統)和基于模擬患者(如肺栓塞患者)的學習。表7分析了3個系統實踐課時分布情況,從中可見:與理論課“新知識”部分類似,心血管系統在實踐課中所占學時最多(35%,21.7/62);系統交叉在實踐課中也普遍存在,有14.5學時的課涉及2個及以上的系統(23%,14.5/62)。

表6 板塊2中不屬于心血管、腎臟和呼吸系統的授課內容列表

表7 板塊2實踐課各系統學時列表
3 啟示
正如DGSOM“人體生物學與疾病”課程板塊2教學大綱所寫:雖然掌握器官系統的結構和功能對理解人體正常生物學功能和疾病至關重要,但幫助學生越過單純的記憶事實,去抓住復雜的內在聯系,并用邏輯思考進行鑒別和診斷,是醫學教學的目標。該板塊課程的設計和安排充分達到了該目標。以下從理論課程、實踐課程、師資及教學互動方面,分析DGSOM教學的特點和成功之處。
3.1 理論課程設計
DGSOM的醫學基礎階段課程“人體生物學與疾病”由多個板塊組成,第一年側重于人體的生理過程學習,第二年側重于疾病的病理過程的學習。該課程安排從正常到異常,從生理到病理,從認識疾病到診斷和治療,有助于學生循序漸進地學習。
與國內部分醫學院校實施的整合式課程不同[4-6],DGSOM基礎醫學課程的每個板塊不局限于單一器官系統,而是將數個功能上關聯密切的器官系統放在一起。本文分析的板塊即是將循環、泌尿和呼吸結合在一起,三者在調節血壓、體內水鹽代謝、酸堿平衡上相互協同。該板塊圍繞臨床問題,精選8大主題,按照內在的邏輯聯系安排學習內容,不僅很好地解決了課程膨脹的問題,且更有助于學生學習和理解。
DGSOM將PBL教學方法融合到課程里。選擇的PBL案例與教學內容緊密配合。每周一開始的2學時為PBL小組討論課,逐步給出案例,學生自己提出需要學習的問題。課后查閱各種書籍和文獻,自我學習,此外案例涉及的知識也是該周課堂授課的主要內容。每周四之前,學生會將各自準備的問題答案發到學習系統上(學校建設的教學網絡),由導師進行評判和指導。每周五2學時PBL課再對案例進行討論和總結。學生每周都會經歷“討論病例-提出問題-自學-課堂學習-完成作業-導師指導-病例討論和總結”的過程,逐步完成自我知識體系的構建。
PBL是建構主義所提倡的一種教學方式。學習者在教師創設的情境下,借助已有的知識和經驗,主動探索,積極交流,構建自身知識體系[11]。國內許多醫學院也開展了PBL教學,已從初期的探索試行階段進入總結反思和完善規范的階段,但均存在一些普遍的問題,如教學思路和學習目標不夠清晰、學生主動學習的意識有待加強等[12]。DGSOM設計的PBL案例密切配合理論課的教學,使得教學思路和學習目標清晰而明確,學生的學習興趣也高;周四作業提交和導師的指導進一步推動了學生的自主學習。DGSOM將PBL教學方法融合到課程的方式,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3.2 實踐課程
關于DGSOM傳統的教學實驗室教學,已有文章進行了介紹[13],國內高校對醫學功能整合實驗也在探索之中[14]。筆者感觸最深的是該校的教學實驗室不再開展動物實驗。在展示運動對生命體征的影響時,自告奮勇的學生志愿者接上各種傳感器,騎上健身自行車,學生們可以直接看到志愿者心率、呼吸、血管收縮壓和舒張壓的變化。在展示心臟運動和血液流動的實踐課上,心臟超聲儀直接顯示志愿者心臟的結構、心腔在收縮和舒張時期的大小,學習計算每博輸出量,并比較運動前后的變化。藥理學工作坊采用計算機教學。DGSOM將大量藥物在人體使用后的數據收集起來,自行研發了一個系統。學生上課時,分組記錄電腦上看到的不同藥物使用后對機體各指標的影響。這些實踐課程與傳統的動物實驗相比,學生學習的興趣高,課堂學習效率高,觀察到的數據更客觀和接近人體的真實情況。
DGSOM非常注重學生臨床能力培養。56%的實踐課時是基于“患者”的學習。這些實踐課程,使剛進入醫學院的學生就可接觸臨床。學生通過患者、標準化病人以及模擬病人,把醫學理論知識貫穿和運用到“患者”或臨床情景中。
行醫是DGSOM醫學教育前兩年開展的實踐教學,運用經過培訓的正常人或慢性病患者來“扮演”模擬患者(即標準化病人)。采用小組學習形式,每組由2名教師和8~9名學生組成,兩名教師中一位是有臨床經驗的醫師,另一位是心理學醫師,每次3小時。第1年教學內容主要強調醫患關系、訪談技巧和人際溝通的能力發展;第2年除了醫患溝通能力,進一步加強學生臨床推理、診斷技能和文化交流能力[15]。國內的醫患溝通教育剛剛開始探索。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于2015年開設了“從醫之道”選修課,教學中采用大量的基于標準化病人的情境模擬訓練,對醫學生進行溝通技能的培養。通過學習,學生能夠有意識地去關注患者的語言、語氣、行為、表情、情緒等各方面的細節內容,體會共情的含義;即使面對一些棘手、存在敵意的情境,也能使其積極尋找應對之策。所有學生均對該課程滿意,不僅提高了醫患溝通的能力,還增加了其學習醫學知識的興趣[16]。我校同類的課程還有“醫患交流技巧”和“走近臨床—醫護初體驗”,但均為選修課,授課容量極為有限。希望該類型的課程能盡快擴容,惠及每一位臨床醫學生。
DGSOM在模擬實驗室教學中,采取的是以團隊為基礎的學習(Team-based Learning,TBL)。臨床實踐中對患者的診療往往需要一個團隊共同努力來完成。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模擬實驗中心非常推崇TBL的學習方式,未來考慮將來自醫學院與護理學院的學生聯合組建醫護團隊,進行模擬教學。TBL是在PBL基礎上改革創新并逐漸興起的一種有助于促進學習者團隊協作精神的教學模式。在TBL模式中,教師制定教學目標,選擇教學內容,提出學生要解決的問題,引導學生運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學生的收獲來自于圍繞實際問題的討論以及老師就該組討論的及時反饋[17]。TBL教學法在我國醫學教育應用有上升趨勢,特別是在實踐性較強的臨床學科,其引導學生自學,培養學生團隊合作能力的教學宗旨得到我國教師認可,應用越來越廣泛[18]。
3.3 師資及教學互動
DGSOM非常重視醫學生的教學工作,選擇經驗豐富的臨床醫生擔任板塊的負責人。教師上課都很有激情,善于抓住學生的注意力,部分課程甚至有2位或3位教師共同講授。板塊的核心教師旁聽了每一堂理論課,也親自參與了實踐課的教學,全面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和狀況;與此同時實踐課老師也會來旁聽理論課,這樣更了解學生的知識結構,實踐課時更能有重點地指導學生。這種方式客觀上起到了督促授課講師提高授課質量的作用,還促進了不同學科或領域教師之間的交流。
DGSOM非常關注學生是否真正掌握了知識,真正實現了“教”和“學”的良性互動。雖然理論課為大班授課(180名學生),但是學生非常認真聽講,有疑問的地方主動提問(教學設備保證每2位學生有一個話筒)。教師也鼓勵學生提問,幾乎每講完一個知識點就會問學生是否有問題。通過這種授課中的直接互動,實現了知識的有效傳遞。理論授課除了有78學時“新知識”,還安排了17學時的“案例學習”和“自評講解”,通過臨床案例習題幫助學生掌握學到的理論知識。此外,PBL導師每周會對每一位學生的PBL問題答案進行評判和指導。
學校還建立了內部學習網站,發布每周課程安排、教學大綱、參考資料、以及實踐課的大綱和目標。細致到每節實踐課需要準備的基礎知識,都有提示。在教室里上的理論課全程錄像,放上網,供學生復習或給沒有到場的學生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