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西山水冊(上)
何宇軒
一
我坐在從羅滕堡回慕尼黑的火車上,精神恍惚。
昨夜教堂邊酒館小酌,怡然自得。怎知今日早起仍感微醺,頭腦脹痛,于是雜念擾緒,幻覺襲思。黑夜剛“走”,此刻車窗外晨光初泄,巴伐利亞鄉(xiāng)間小景如夢如幻。霎時(shí),眼前驚現(xiàn)吳冠中筆下那樣“皎潔”的東方樓臺(tái),耳邊乍起拉威爾的鋼琴組曲《鏡子》——兩重毫無關(guān)聯(lián)的疊念無縫銜接。也怪這若有似無的悠意作祟,我竟不知深淺地寫下幾句小詞:
長夜離席,朱曦爍堤,碧瓦玉池縱游魚。錦鯉鮫鰻說情怡,顰笑言語皆庸慮。
琴閣如靈,畫坊似縷,僻寥仙居徒幽閉。人聞青衫嘆恃孤,何嗟此生多真理。
也許,在我無知的懸想里,印象派的一幫子人有古代文人的意氣,儼然一席青衫、不與世俗的精神貴族模樣:在心底與周遭人群(池中游魚)隔離,不與那種虛偽的人——表象友好,其實(shí)各自心懷鬼胎,滿是庸俗的私慮——同流合污,但也不加以強(qiáng)烈的攻擊與嘲諷,只是躲進(jìn)自己的藝術(shù)院落,“幽居世外”,尋求人們不屑的孤獨(dú)與真理。
法國現(xiàn)代派詩人波德萊爾在《惡之花》中語:
一旦墮入笑罵由人的塵世,威猛有力的羽翼便寸步難行。
這是非常現(xiàn)代的一句話,它代表著藝術(shù)家的“個(gè)性”——與“眾”背離,甚至是帶有對抗情緒的審美傾向。如今讀之,習(xí)以為常:藝術(shù)家最重要的不就是“個(gè)性”嗎?但對應(yīng)脫胎于十八世紀(jì)的十九世紀(jì),這些詞匯便顯得“大逆不道”,幾乎偏離了歷史。“幽居世外”對于東方文人來說已是司空見慣的逍遙:“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的陶潛世人皆曉,大隱于山水的“竹林七賢”令一眾玄學(xué)名士終身向往。然而,對于西方藝術(shù)家來說,自絕浮世的選擇實(shí)在有些新穎大膽。波德萊爾的這句話似乎預(yù)示了十九世紀(jì)文化走向的分水嶺——藝術(shù)家開始與大眾背道而馳。“威猛的羽翼”必須脫離“笑罵由人的塵世”才能自由地飛翔!
如此思索也引出另一番疑問:為什么是印象派在繪畫和音樂領(lǐng)域成了現(xiàn)代藝術(shù)的先驅(qū)?德彪西這位并不那么有斗爭性格的印象派“大佬”,是如何成為現(xiàn)代音樂開拓者的?

翻找唱片,打開音響,怡然品聆,德彪西于1912年創(chuàng)作的《游戲》(Jeux)似乎是對《惡之花》輪回般的回應(yīng)。耳旁響起的是布列茲與克利夫蘭管弦樂團(tuán)演奏的版本,他們塑造出一種幻覺般的現(xiàn)代節(jié)奏,似是齒輪的轉(zhuǎn)動(dòng)。音律虛實(shí)交錯(cuò),主題模糊,整曲聽來,那些迷霧層疊的音色“光影”猶如架空心靈的摩登城市。《游戲》的妙處正在于此:樂音的走向不斷向前,仿佛不再停止的態(tài)勢,形成一種永動(dòng)機(jī)般的機(jī)械運(yùn)動(dòng)的感覺。聽者能有如上聆感,其實(shí)是源于作品結(jié)構(gòu)的特殊性——在傳統(tǒng)的管弦樂作品中,這樣的結(jié)構(gòu)只能算作是一個(gè)過渡段,但在德彪西筆下卻作為一個(gè)龐大的整體而存在。西蒙·拉特說,德彪西是在音樂中實(shí)現(xiàn)現(xiàn)代電影概念的探索者。許多音樂家和愛樂人也都認(rèn)為《游戲》是德彪西最好的作品。可現(xiàn)實(shí)是,作為舞劇的《游戲》從問世至今從未成功過,對于任何一個(gè)演出團(tuán)體來說,它都是永恒的災(zāi)難。這部作品走進(jìn)了藝術(shù)的異度空間——像是大衛(wèi)·林奇導(dǎo)演的懸疑劇《雙峰》中扭曲時(shí)空的紅幕房間——無法遁入凡世,人們找不到打開它的鑰匙。它的“品格”太過“高尚”了,完全沒有理會(huì)時(shí)代的變遷,在時(shí)代的夾層中一聲不響地發(fā)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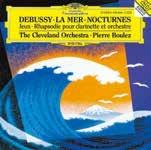
《游戲》的劇情極其無聊,甚至可以用簡短的幾句話來概述:一天黃昏,正在花園里打球的男孩和兩個(gè)女孩弄丟了網(wǎng)球,于是便在灌木叢中翻來覆去地尋找,并隨之玩起了捉迷藏。后來網(wǎng)球被找到了,三人開始愉悅地舞蹈。突然,一只神秘的手出現(xiàn)了,將另一個(gè)網(wǎng)球扔向花園。他們嚇壞了,四散逃去……



如今,歌劇、舞臺(tái)劇、芭蕾舞劇的當(dāng)代藝術(shù)化已是“兵家常事”,舞臺(tái)上經(jīng)常可見不明所以的布景、時(shí)代錯(cuò)亂的服裝,甚至造型乖戾的妝容。數(shù)月前,我在巴伐利亞國立歌劇院觀看最新制作的《后宮誘逃》,親眼看著一堆晃來晃去的沙發(fā)“演”完全程。可即便是這樣,三個(gè)演員從頭至尾地尋找網(wǎng)球、打網(wǎng)球,又被網(wǎng)球嚇跑的“表演”還是讓人們無法接受:德彪西到底在干什么?為什么在他的創(chuàng)作“清單”里會(huì)突然出現(xiàn)這種讓人看不懂的藝術(shù)?看不懂了,還有意義嗎?
英國藝術(shù)史學(xué)家貢布里希提出過一個(gè)觀點(diǎn),他認(rèn)為由印象派引發(fā)的十九世紀(jì)藝術(shù)變革的源頭是商品市場的變化,這種變化導(dǎo)致了傳統(tǒng)供應(yīng)關(guān)系的破裂。從前,音樂或繪畫的創(chuàng)作就像其他工作一樣,是自然而然的社會(huì)功能,藝術(shù)工作者有與之對應(yīng)的雇主——教堂、宮廷、貴族、商人等等,創(chuàng)作者的任務(wù)是按照雇主的要求訂做“貨品”。且這樣的“生產(chǎn)”過程也并不是聽起來的那么沒有藝術(shù)性。貢布里希寫道:
的確,他可以干得稀松平常,但也可以干得無比絕妙,使接手的差使不過是一件卓越佳作的來由而已。
……
然而他一生中的職業(yè)多少還是安全的。而藝術(shù)家在十九世紀(jì)失去的恰恰是這種安全感。
傳統(tǒng)關(guān)系的破裂大大提升了藝術(shù)家創(chuàng)作的自由性。雇主消失了,他們開始自由支配自己的作品,贊助人也由自己選擇。“訂做時(shí)代”逐漸落幕,創(chuàng)作的手法和風(fēng)格完全轉(zhuǎn)由藝術(shù)家自我定奪。選擇范圍的擴(kuò)大使藝術(shù)家的志趣逐漸與大眾偏離,形成“有意”而為之的極端審美。其實(shí),這種“有意”大部分來源于時(shí)代巨變的慣性,縱使德彪西、拉威爾的本意并非挑戰(zhàn)公眾趣味——印象派本質(zhì)還是根植于浪漫主義的——亦會(huì)由于慣性的導(dǎo)引將才華抒發(fā)在具有挑戰(zhàn)性的創(chuàng)作上,造成對大眾“不友好”的作品的出現(xiàn)。
與此同時(shí),作為大眾和藝術(shù)家連接媒介的贊助人或經(jīng)紀(jì)人,其品位依然偏向大眾一邊,只不過大眾在新時(shí)代換了個(gè)名稱,叫作“市場”。而由于藝術(shù)家志趣的不斷偏移,他們與贊助人之間的矛盾就愈發(fā)增大了。一旦藝術(shù)家因經(jīng)濟(jì)或者其他因素而不得不向贊助人的審美趨近,他就會(huì)認(rèn)為自己沒有遵從內(nèi)心,是在向“市場”妥協(xié),變成了沒有個(gè)性、沒有尊嚴(yán)的創(chuàng)作者。但顯然,過往時(shí)代的藝術(shù)家絕對不會(huì)這么認(rèn)為,他們創(chuàng)作結(jié)構(gòu)相似的宗教音樂,抑或主題雷同的耶穌受難畫也不會(huì)覺得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受眾喜歡這些,雇主喜歡這些,他們自己也喜歡這些,況且這也并不阻礙自己才華的施展和審美的展現(xiàn)。從十九世紀(jì)的印象主義開始,這個(gè)邏輯已不再適用,個(gè)性的與眾不同成了藝術(shù)的“真諦”,“藝術(shù)”與“個(gè)性”成了一對雙胞胎。
如果沿這個(gè)思路推索下去,大眾似乎也沿著“破裂”的慣性,與愈發(fā)“高傲”的藝術(shù)領(lǐng)域逆流淌去,形成不斷坐實(shí)既定審美,甚至厭惡極端審美的一種姿態(tài)。“噢,這幅畫真難看,根本讓人看不懂!”是我們在現(xiàn)(當(dāng))代美術(shù)館里經(jīng)常聽到的評論。在大眾看來,一切挑戰(zhàn)其通俗易懂的既定審美的東西都是差勁且失敗的,理所應(yīng)當(dāng)?shù)貙⑵淇醋魇恰肮逝摗钡漠a(chǎn)物,這也是德彪西的芭蕾舞劇《游戲》至今無法成功的原因。藝術(shù)家和大眾審美情趣從印象派時(shí)代的分離已然轉(zhuǎn)化為當(dāng)今時(shí)代的嚴(yán)重對立,且仍在加劇。
“藝術(shù)”一詞在我們心目中已經(jīng)具有一種不同的含義,而十九世紀(jì)的藝術(shù)史,永遠(yuǎn)不可能變成當(dāng)時(shí)最出名、最賺錢的藝術(shù)家的歷史。反之,我們卻是把十九世紀(jì)的藝術(shù)史看作少數(shù)孤獨(dú)者的歷史,他們有膽魄、有決心獨(dú)立思考,無畏地、批判地檢驗(yàn)程式,從而給他們的藝術(shù)開辟了新的前景。
——貢布里希《藝術(shù)的故事》
印象派藝術(shù)家被決心分裂的審美浪潮推到了最前列,德彪西也隨著《大海》卷起洪波前的浪花。“現(xiàn)代音樂開拓者”的帽子算是給他戴上了,可他自己當(dāng)真知道、當(dāng)真情愿么?
二
幾周前,紐倫堡的朋友來慕尼黑看我。可那時(shí)我正學(xué)業(yè)繁忙、工作擾身,一并出游根本是奢侈之談。思來想去,最后只得相約“下館子”了事。
我與他相識(shí)不久,雖脾氣相合,但并不知曉其個(gè)人志趣。當(dāng)日飯局一聚,三言兩語便發(fā)現(xiàn)兩人同好古典音樂,可謂難得摯友,好不快活。
“你經(jīng)常寫音樂文章,平時(shí)喜歡讀什么音樂讀物?”飯菜剛剛上桌,他隨口問道。
我語塞片刻。想來慚愧,近來我?guī)缀醪蛔x音樂讀物。它們之于我總有種詭異的特性——音樂讀物從來沒有“音樂”,讀著它們,你其實(shí)聽不到音樂本身。
可人在飯局,筆墨律音總歸閑聊之物,一桌子飯菜擺著,鼻子是等不了的。此刻雙目無文,雙耳也無樂,只嗅得滿滿的香氣。我想起陳立寫的2000年西諾波利(Giuseppe Sinopoli)攜家人在北京吃飯時(shí)的場景——一桌子中國菜給指揮家端到跟前,老爺子立刻神采飛揚(yáng)起來,那狀態(tài)、精氣神與指揮交響樂團(tuán)時(shí)的樣子無異:
大師對“酥鯽魚”下定義說道:“哦,這很像勃拉姆斯,味濃而柔和。”
… …
隨后他又對使他七竅貫通的辛辣“芥末墩兒”做了個(gè)唱高音C的夸張手勢說道:“羅西尼!羅西尼!很給勁,很通透。”當(dāng)“譚家菜”最拿手的一道名菜,需要烹制七十多小時(shí)的“黃燜鯊魚翅湯”端上來時(shí),大師僅嘗了一口便歡呼了起來:“Bravo!Bravo!實(shí)在是太甘美了,就像普契尼。”
… …
接下來,西諾波利將“清蒸桂魚”稱作拉威爾,“因?yàn)樗岷蛥s不夠浪漫”;稱“酥乳鴿”像莫扎特,“因?yàn)樗舾卸p快”。當(dāng)他品嘗到“板栗野鴨”時(shí),西諾波利沉思良久,稍許他猛然說道:“太棒了,這是貝多芬!”
——陳立《音樂家訪談錄》
一想到這,我就顧自感嘆起來:怪不得人家是指揮大師,吃飯也能“聽”到音樂。眼見巴伐利亞香腸裝盤的我,腦子里的音樂家卻只有“香腸”本腸。
我從其他形式轉(zhuǎn)換得來音樂感受的時(shí)候不多。有時(shí)猛然想聽某個(gè)曲子,心里確也會(huì)默誦起一段,但總覺得不過癮。唯有拾起耳機(jī),打開音響,或者走進(jìn)音樂廳,樂聲真實(shí)入耳,這才算了事,好像完成了一個(gè)心愿。
若要細(xì)致回溯,樂聲“突襲”的經(jīng)歷確有二三。那是從賞中國山水詩詞的少許經(jīng)驗(yàn)得來——明明無樂,卻總感有樂,“無為而為”的音律從天而降。其中尤以宋詞為甚,讀之、感之,耳邊總能“響”起德彪西、拉威爾的音樂。
柳永的“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妙有德彪西《大海》那種氣壯的鋪排感;秦觀的“漠漠輕寒上小樓,曉陰無賴似窮秋,淡煙流水畫屏幽”好似德彪西《意象集》一般云煙霧繞;“絳綃縷薄冰肌瑩,雪膩酥香。笑語檀郎,今夜紗廚枕簟涼”的李清照映照了拉威爾《達(dá)芙妮與克羅埃》的蜜戀情長;更有筆鋒突轉(zhuǎn)的辛棄疾,“最喜小兒亡賴,溪頭臥剝蓮蓬”的偶發(fā)情志,猶如拉威爾給孩子們作的《鵝媽媽》童稚“踏來”……若要細(xì)舉,恐怕是一整章節(jié)也列不完的。看來,音樂上的中西“聯(lián)誼”,不止飯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