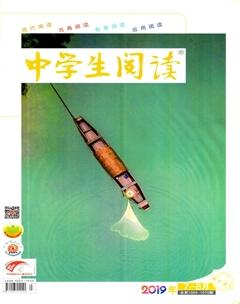聽,種子在翻身
2019-07-16 01:39:56湯朔梅
中學生閱讀·初中·讀寫
2019年8期
湯朔梅
那一年因為帶二弟,我輟學在家。白天無聊時常在村口呆立,或朝河面甩幾片瓦片。人們都下地了,小伙伴們已開學。四野里很靜,但不空。村里還有撒歡覓食的雞鴨貓狗。風輕得幾乎感覺不到,但那風沒有明確的方向感,時而東南,時而西北,猶猶豫豫,欲說還休。側耳諦聽,遠處似有微微的震動聲,似遠在天邊,又像近在身旁,令人捉摸不透,但又確確實實地存在。那是來自杭州灣的潮汛嗎?那是發自大地寬博的胸腔嗎?
發呆間,眼梢的余光發現側后方站著一個人。哦,那是老農。老農是我爺爺輩的種田能手,因之大伙都叫他老農。他出名地寡言,即便開口也是惜字如金。除他在給村里的孩子擤鼻涕、束褲帶時才覺得他和藹外,大多時候我們有些怕他。不僅我們怕,隊長也有些怕他,曾見過隊長遭老農呵斥后一副唯唯諾諾的樣子。但老農有一個習慣,那就是笑。他的笑也特別,不是大笑或者對他人笑,而是無端地獨自微笑。有時見他倒背著手,低頭微笑著一路行來;或者夾著煙遠望莊稼地微笑,以至于煙灰不斷變長,燒到指尖才驚醒。直到我長大后,才知道只有內心世界豐富的人方能這樣。
此刻,我們都站在母親河北岸的橋堍旁。他向南天遠眺著,意味深長,而我則側過身來望著他,怯怯地自語著打問:“這是什么聲音呢?”
“那是種子翻身的聲音。”老農咳嗽了兩下后冒出一句。
種子翻身的聲音?種子也會翻身?我正納悶間,他卻反問:“不是種子翻身的聲音,你說是什么?……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