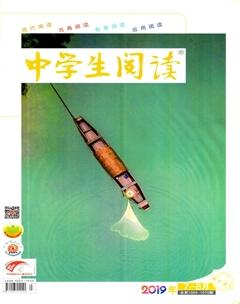老爹的茶壺
2019-07-16 01:39:56翟貴梅
中學生閱讀·初中·讀寫
2019年8期
翟貴梅
老爹煙酒不沾,獨愛喝茶。
從記事起,我就知道老爹有把銹跡斑斑的茶壺,銹不是鐵銹,是茶銹,因為它只是一把泥壺。一把沒有任何來歷的普通茶壺,卻被老爹珍愛了大半輩子,一直把它帶在身邊。家里的老屋幾次修葺,很多老物家什都弄丟了,唯獨這把茶壺被完好無缺地保留了下來。
母親說,茶壺是在我出生的第三天買的。那天是離我們村五里之外的潮河村大集。天蒙蒙亮,老爹就出門去趕集買菜,中午家里來客人。
時隔這么多年,母親仍清楚地記得老爹當時身上帶了七塊錢去趕集。兩人再三盤算著怎么花能圓滿地置辦一桌菜,家里除了母親養的幾只蘆花雞還爭氣地下了幾個蛋,實在拿不出像樣的菜來招待客
人。
沒想到老爹一到集上就先花一塊二買了個茶壺,余下的錢再拿去買菜,于是被母親在家盤算了半天的一桌子菜,單薄了許多。
那幾天老爹一直低眉順目,對母親的大聲小氣也是逆來順受。
不是老爹做不了一塊二毛錢的主,而是那個年代,一個普通的茶壺已是奢侈品了。在母親看來,與其買個不能吃不好看的茶壺,真不如多買塊肥肉犒勞犒勞我那兩個長身體的哥哥。
花一塊二買個茶壺只是那些苦日子里的一個小插曲,母親嘮叨幾句也就過了。在仍有許多溫暖的物資緊缺的日子里,我慢慢長大。
也許是因為最小,又是家里唯一的閨女,自小爹就最疼我。
小時候的我特別能“作”。上墻爬屋、揭屋檐掏家雀兒……,各種男孩子做的我都做過。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