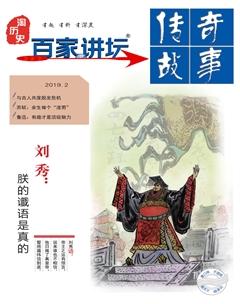不予良辰
薛淺
今年的春日來(lái)得極早,程昇在京師耽擱久些,自從回到戎城,就不停地給易卿卿賠罪。其實(shí)易卿卿并不在意,偏他內(nèi)疚得不行,偷偷找了數(shù)十家戲班,單揀那些歡喜的戲唱,只求逗她一笑。
臺(tái)上傳來(lái)咿咿呀呀的戲腔,易卿卿裹著狐裘,端坐在檀木椅上,也未細(xì)聽(tīng),只是癡癡地盯著那翻飛的傀儡,想起初遇許安平那年,他唱的也是這場(chǎng)戲。她緩緩笑了起來(lái),笑得無(wú)比凄涼。
記得那日,她就站在聽(tīng)雨樓的堂內(nèi),怯怯地倚著鴇母,瞧著臺(tái)上的傀儡,驚奇不已。鴇母說(shuō),許安平是戎城傀儡戲的第七代傳人,妙音繞梁,就連梨園的老先生都曾盛贊過(guò),她若能隨他學(xué)幾出戲,日后必能一舉奪魁。
她雖無(wú)奪魁之心,卻真的很喜歡唱曲,聽(tīng)到他的婉拒時(shí),難過(guò)地低下了頭。正欲離去時(shí),他偏又收下了她。后來(lái),她問(wèn)過(guò)許安平很多次,為何獨(dú)留下她。他只是淡淡一笑,無(wú)論如何都不肯說(shuō)。
聽(tīng)雨樓每月不過(guò)幾場(chǎng)戲,日子過(guò)得很拮據(jù),清粥野菜,自然無(wú)法與吹笙閣相比,然而她不曾抱怨,日日狼吞虎咽,仿佛吃的是世間珍饈。每到聽(tīng)雨樓開(kāi)戲時(shí),她就幫忙倒茶,然后站在遠(yuǎn)處的角落里,看著戲臺(tái)上的傀儡行云流水般的動(dòng)作,聽(tīng)許安平用婉轉(zhuǎn)的戲腔道盡平生。
許氏素有不收外徒的家規(guī),所以許安平不許易卿卿稱他“師父”,也不許易卿卿碰他的傀儡,只是教她唱曲。他平日待她極好,獨(dú)在戲上萬(wàn)分嚴(yán)苛,若錯(cuò)了半句,戒尺便毫不留情地落在她的掌心,等她唱好這支曲子,許安平才心疼地為她抹藥。
直到兩年后,易卿卿唱曲已是爐火純青,許安平才將戒尺收了起來(lái)。
驚蟄這日,易卿卿正在抄寫(xiě)曲譜,看到許安平走過(guò)來(lái),連忙捂住了字。他皺著眉掰開(kāi)她的手,看到她的字后,那難以言述的表情,仿佛眼睛都受到了侮辱。察覺(jué)到她的窘迫,許安平?jīng)]再說(shuō)什么,繞到她的身后,握住了她的手。
溫?zé)岬臍庀⒃诙股希X(jué)得臉都燒了起來(lái),再無(wú)暇顧及他說(shuō)的書(shū)法要領(lǐng),感受著他掌心的溫度,思緒早已飄遠(yuǎn)。在這個(gè)陽(yáng)光明媚的午后,她終于明白了自己心意。
易卿卿學(xué)成歸去的那晚,許安平飲了許多酒,臉色潮紅地坐在聽(tīng)雨樓樓頂,陪著易卿卿看戎城夜景。 “安平,你以我的模樣做個(gè)傀儡好不好?”許安平看著她的眼睛,一字一句道: “我的傀儡可是要給未來(lái)娘子的,你還要嗎?”
“安平若是偏要給我,那我不要豈不是傷了安平的心。”易卿卿的臉上滿是笑意,才略帶調(diào)皮地說(shuō)完,就被許安平摟在懷里。她羞澀地閉上眼,他的唇便落了下來(lái)。那是他們的第一個(gè)吻,也是此生最后一個(gè)。
“安平,不如我們私奔吧?”看到眉頭緊皺的許安平,易卿卿突然笑了出來(lái),“我逗你的。”說(shuō)罷便轉(zhuǎn)過(guò)頭去看萬(wàn)家燈火,好似方才真的只是開(kāi)了一個(gè)玩笑。
16歲那年,易卿卿回了吹笙閣,因唱許安平所作的《嘆良辰》,成了新晉花魁,一時(shí)風(fēng)頭無(wú)兩。如此絕色美人,賣(mài)藝不賣(mài)身都成了妄想,鴇母雖疼易卿卿,卻迫于程異的淫威,默許了他,芙蓉帳暖,一夜春宵。
她走的那日.許安平曾送給她一只信鴿。他說(shuō),若是不開(kāi)心了,便寫(xiě)信給他,他一定會(huì)去看她。她想見(jiàn)他,卻又不忍讓他破費(fèi),直到程舁之事,她將一腔委屈述諸筆端,等到寫(xiě)好后,紙都被淚打濕了。可惜等了一日又一日,許安平都杳無(wú)音訊。
后來(lái),易卿卿每日都會(huì)寫(xiě)一封信,從淚眼婆娑地訴說(shuō)委屈到追憶往事。許安平一定沒(méi)看到這些信,否則為何不來(lái)看她呢?
半個(gè)月后,易卿卿終于尋到機(jī)會(huì),收拾了細(xì)軟,從吹笙閣逃了出去,因跑得太急扭傷了腳,她只好一瘸一拐地走到聽(tīng)雨樓,最終在聽(tīng)雨樓樓頂找到了許安平。
“安平,帶我走好不好?”易卿卿費(fèi)力地爬到樓頂,看到散落在他身旁的信,強(qiáng)壓下心中的委屈,低聲乞求道。許安平眸光微暗,坐在那里沉默不語(yǔ)。她突然紅了眼,“安平,你不是說(shuō)好來(lái)看我的嗎?”
“卿卿,我去了又能怎樣昵?”許安平對(duì)她苦澀一笑,便又低下了頭。他幼時(shí)曾勤學(xué)苦讀,本欲考取功名,卻因許氏一脈單傳,被父親逼著入了下九流。程異乃戎城首富,便是在京師中也頗有人脈,若得罪了程異,那戎城傀儡戲豈不是毀于他手。“卿卿,等我賺好多好多錢(qián),贖你出吹笙閣,好不好?”
“許安平,難道你要我等你一輩子嗎?帶我走吧,去哪兒都好。”易卿卿滿眼是淚地站在樓頂,看著許安平沉默地坐在那里,直到淅淅瀝瀝的小雨將一襲春衫打透,最終踉踉蹌蹌地下了樓。
那一夜,她不記得是如何回的吹笙閣。冰涼的雨打在身上,無(wú)數(shù)次跌倒在水洼里,然后帶著滿身的污泥爬起來(lái)。回到吹笙閣后,她便生了一場(chǎng)大病,等到痊愈時(shí),嗓子已經(jīng)毀了,她與許安平的最后一絲牽扯也仿佛斷了。
她依舊寫(xiě)信,寫(xiě)了一封又一封。她想,只要他肯來(lái)帶她走,她就不怪他了,可惜他從不曾來(lái)過(guò)。
程昇浪跡歡場(chǎng)多年,身旁的女子更是不計(jì)其數(shù),故而易卿卿毀了嗓子后,不知有多少人等著看她的笑話。誰(shuí)料程異卻仿佛動(dòng)了真心,不僅為她請(qǐng)了最好的大夫,還時(shí)常守在她床邊噓寒問(wèn)暖。綾羅綢緞、胭脂水粉,更是一箱一箱地送。
旁人都道易卿卿好福氣,只有她冷眼旁觀,很少與程異說(shuō)話,更從不曾對(duì)他笑過(guò),程異也不勉強(qiáng)。他曾經(jīng)虧欠過(guò)一個(gè)人,如今只能將這些溫柔都給這位與她眉眼相似的姑娘了。
第二年初春,程異下聘,強(qiáng)娶易卿卿為平妻。花魁高嫁,整個(gè)吹笙閣都透著喜氣。鴇母笑著清點(diǎn)聘禮時(shí),易卿卿漠然地坐在樓梯上,看到許安平抱著一個(gè)木匣走了進(jìn)來(lái)。一年不見(jiàn),他的下巴上有了很多胡茬,眼神也是疲憊不堪, “這是我的賀禮。”
“多謝許先生。”易卿卿臉上掛著笑,接過(guò)他手中的木匣,隨手遞給身后的鴇母,再不肯多看一眼。許安平靜靜地瞧了她許久,然后轉(zhuǎn)身出了吹笙閣。
易卿卿或許永遠(yuǎn)不會(huì)知道,她出嫁那日,許安平躲在吹笙閣旁的垂柳后,哭得像個(gè)孩子。他一直都記 得,父親跪在他面前聲淚俱下地求他將戎城傀儡戲傳下去的樣子,就連彌留之際都還死死抓著他的手,直到他拿起身旁的傀儡,才肯閉上眼睛。
他也不想啊,可他又能怎樣呢。那年,他之所以會(huì)留下易卿卿,就是因?yàn)榭吹搅怂劾锏碾y過(guò),讓他想起自己被迫放棄詩(shī)書(shū)時(shí)的苦。他本想在揭開(kāi)她蓋頭的那一刻,才將那個(gè)似她模樣的傀儡送給她,如今卻是不能了。
這一年,17歲的易卿卿嫁給了26歲的程異,明媒正娶,十里紅裝,不知羨煞了多少人。只有易卿卿知道自己心里有多難過(guò)。
“謝老爺、夫人打賞。”聽(tīng)到許安平的道謝,易卿卿才回過(guò)神來(lái),一身紅衣的他正對(duì)著席間作揖,身旁還站了個(gè)孩子,正怯生生地打量著她。聽(tīng)說(shuō)許安平娶了個(gè)盲妻,有了兒子,想必就是這個(gè)孩子吧。
程昇見(jiàn)易卿卿眼圈通紅,忙道: “卿卿,那年我就說(shuō)了,以后的春日都有我陪你,我斷然不會(huì)再爽約了。”程異鄭重地舉著左手起誓,看到易卿卿點(diǎn)了點(diǎn)頭,笑著將她摟在懷里,回了內(nèi)室。許安平將賞錢(qián)都放到許行手中,隨著同行們出了程府。
他聽(tīng)說(shuō),易卿卿懷過(guò)一個(gè)孩子,只是深宅大院里有太多見(jiàn)不得光的事,不過(guò)才三個(gè)月,就流掉了,自此傷了身子,再不曾有孕。
他還聽(tīng)說(shuō),程異年少時(shí)尋花問(wèn)柳,處處留情,但自從娶了易卿卿之后,除了過(guò)年時(shí)回京與原配、獨(dú)子團(tuán)聚,便極少在外留宿了。
自那日別后,縱然浮生漫漫,他的人生想再與她相關(guān),也都只有“聽(tīng)說(shuō)”了。
“爹爹,明明是一場(chǎng)歡喜的戲,為什么程夫人卻哭了啊?”許行跟在許安平身后,不解地問(wèn)道。“許是想起故人了。”許行還想再問(wèn),卻看到許安平眼里有了濕意,便沒(méi)敢開(kāi)口。
許安平常常在想,許氏一族最初唱傀儡戲時(shí),必是出于喜歡,只可惜累世經(jīng)年,到他時(shí)卻已成了負(fù)擔(dān)。如今他收了眾多弟子,若是有朝一日,許行有了所喜之事、若愛(ài)之人,他定順從其心意,許行再不必似他那般,為許家所累了。
轉(zhuǎn)眼已過(guò)數(shù)十載,多少愛(ài)恨都隨風(fēng)而逝了。只可惜那一年,春寒料峭,細(xì)雨如絲的深夜,他終究辜負(fù)了深愛(ài)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