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批評視角下的《外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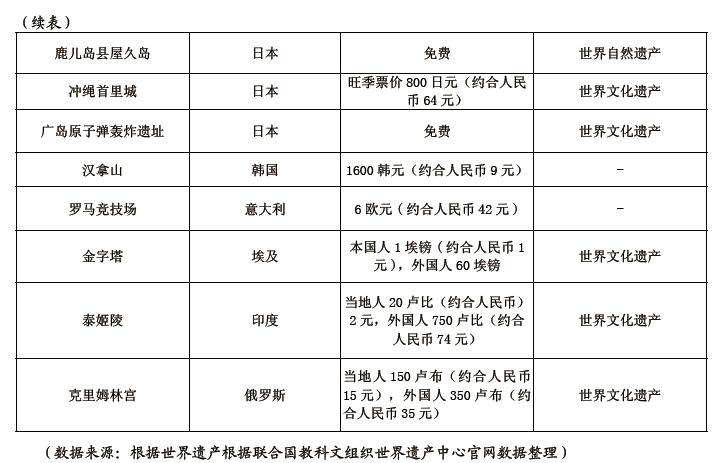
摘要:果戈里的《外套》一部小人物命運控訴的先驅作品,它在敘事視角的選擇、空間結構的安排以及情節設計等多個方面都獨具匠心。本文將從敘事批評的視角出發,選取敘事視角、敘事空間以及荒誕的敘事情節三個方面出發,探索《外套》的敘事奧秘。
關鍵詞:敘事視角;敘事者;敘事空間
《外套》是果戈里的一篇短篇小說,講述了十九世紀俄國等級森嚴的官僚制度下小人物的悲慘命運。他的作品往往表現為文學的一種雙向“重構”,將生命關懷和靈魂關懷的理念寫進小說,通過對俄國當時社會環境的敘寫以及形形色色人物的塑造,使他們成為表現宗法社會民族性庸俗和集體性荒謬的經典。《外套》在敘事上設計的獨特精巧,富有深意,結尾處采用了荒誕的手法,使主人公靈魂復活,這是在繼普希金“小人物”史上的又一個偉大的超越。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和陀斯托耶夫斯基共同說過一句話:“我們都是從果戈里的《外套》里走出來的。”
一、敘事視角與敘事者
敘事視角和敘事者都是從“講述”(telling)的角度出發的,然而“角度”一詞的含義十分復雜、寬泛,同19世紀詹姆斯提出的“觀察點”這個術語十分相像,是一個很籠統的概念。法國結構主義敘事學家熱奈特曾批評說,“角度”這個概念過分強調視覺的含義,即誰看得問題,卻忽視了另外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即誰講。所以羅鋼在《敘事學導論》中提出了“敘事情境”這個概念,來闡述敘事者與故事之間的種種復雜關系。
《外套》采用的是第一人稱敘事情境,以一句“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亞卡基·亞卡基耶維奇是在三月二十三日深夜降生的”開始了故事的經過,在寫主人公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巴什馬奇金名字來歷的時候寫道:
“我們這樣交代,為的是讓讀者可以明白,事情的趨勢不得不如此,給他另外起個名字是決計辦不到的。”敘事者以一種非聚焦的視角,向讀者交代某種隱含的原因。
同樣,文中提到,在彼得堡的每一個人,都存在著一個強大的敵人,“這個敵人不是別人,就是我們北方的嚴寒。”敘述者是存在于虛構的小說世界之中的,它存在于19世紀的俄國,存在于彼得堡,存在于阿卡基生活的那個部、團、辦事處的小公務員環境之中,它的世界與阿卡基的世界是完全統一的。
隨后,便將敘事視角放在阿卡基身上,以他的活動和遭遇來窺探、表現外在的世界。
“總之,即便是大家都竭力去尋歡作樂的時候,阿 卡基·阿卡基耶維奇也從不找個地方去消遣。誰也說不上什么時候在晚上遇見過他了。他盡 情地抄寫夠了,就躺下睡覺,一想到明天就暗自微笑:老天爺明天又會賜給他什么東西抄寫 呢?一個年俸400盧布、對自己的命運心安理得的人,就這樣平靜地打發著日子,或許本來 可以活到垂暮之年,可是人的生活道路總是多災多難,不僅九等文官,就是三等、四等、七 等文官和各式各樣的顧問官,乃至徒具虛名、從不理事的官員都概莫能外。”
敘事者想要向讀者傳達的是,在阿卡基所處的時代和空間中,無論官職位于哪個等級,痛苦和磨難都是人生常態。但這些都不是阿卡基這個人物的感慨,是一個隱含作者而表達出來的,這個隱含作者正是敘事者。阿卡基僅僅作為一個安于現狀的小人物出現,敘事者隱藏了此人內心深處的想法,代之以簡單化的行為,所以出現了敘事者和人物的雙重聲音。沒有賦予阿卡基過多的活動空間和話語權,降低了其對外界的感知,卻使人物形象更加豐滿化,輪廓更加清晰。
在結尾部分的荒誕情節中,敘述者的視角發生了位移,位移到了大人物高級官員身上。敘寫大人物對死后阿卡基的回憶以及內心懺悔,增加了他的內心戲碼,意在表現官場人物身上殘存的善念,只是被環境的強化而掩蓋,同時也看得出作者對社會轉變仍存希望。
二、敘事空間結構
敘事文里的行動必須在一定的時空中發生,這其實強調了環境在敘事中的重要性,環境是一個時空綜合體,除空間外也包括時間因素,以下主要從空間因素入手分析小說的敘事結構。
“當全體官員散布在朋友的小屋子里打惠斯特牌,捧著杯子喝茶,啃著廉價的面包干,從長煙斗里噴出煙來,在發牌時講著只要是俄國人就不能不向往的上流社會傳出的流言蜚語。”
從宏觀上來講,整個敘事過程就是發生在這么一個“狹小”的空間——官員群體,文中明顯地將其與上流社會分離開來。主人公阿卡基出生在一個小官員之家,在這種空間環境之下自己也最終成了一名九等文官。在小說中出現的所有環境空間在物理關系上是層層嵌套的。
“早晨一過了八點鐘,正是滿街泛濫著上部里去的人的時候,它開始不分青紅皂白,對準所有的鼻子狠命地、刺一樣地鉆起來,簡直叫那些可憐的官員們不知道把鼻子往哪兒擱才好。在這連大人先生都凍得腦門發疼、眼淚汪汪的時候,可憐的丸品文官們有時簡直是毫無防御的。”
首先,最大的外部空間是寒冷的彼得堡,敘述者把阿卡基以及其他的九等文官的活動都限制于其中,這是裹在所有人身上的一個“外套”。它是一個復雜的網狀世界,這些官員可以透過這層“網”窺探外面的世界,盡管他們羨慕又心生向往,可他們的身份地位以及自身的格局層次又使他們不得不牢牢地被套在這層破舊寒冷的“網”里面。其次,緊緊嵌套在這個“網”里面的是一些并列的空間個體,“政府機構”“裁縫店”“街上”“晚會”。
“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起初得走過兒條燈光暗淡的荒涼的街道,可是越走近官員的住宅,街道就變得越熱鬧、人煙越稠密,燈光越亮。行人越來越多,衣服華麗的淑女開始出現,男人們也有穿海貍領子外套的了。……他懷著一種不由自主的恐懼走到廣場上,仿佛他的心早已預感到有什么不祥似的。他往后,又往左右瞧了瞧:周圍簡直是一片茫茫大海。”
“街上”和“廣場”往往是阿卡基產生新想法乃使情節發生轉折,甚至命運轉變的重要空間,他在這里看到了貧富帶來的待遇差別,也是在這里最終被打回原形,也是人物生存空間轉變的過渡點。
最小的空間層次就是披在阿卡基身上真實的破爛的的“長衫”和真正的“外套”,在這個空間之下,阿卡基的命運也發生了極具戲劇性的起伏和轉變。而“長衫”是其中最破爛最寒冷的一個空間,“它的確有一種奇怪的構造:領子一年比一年縮小,因為裁下縫補它的別的部分去了。”這個空間,不僅給了阿卡基自卑,還讓他成了同事們的笑柄,于是他從中得到一種激發,然而這種激發并不是沖動式的,是他把這件長衫仔細觀看,多次嘗試縫補無效之后產生的,使他從中過渡到了另一層空間——“新外套”。這個空間有兩個特點,或者說是兩種好處,一來暖和,二來好看;隨后引來了大家的圍觀和祝賀,甚至收到了高級晚會的邀請。阿卡基的身份地位好像也隨著空間的變化而發生了變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和尊重,甚至可以開始接觸到上層社會。
直到阿卡基的這層外套在晚會后的廣場被搶,他最后一層溫暖的生存空間失去了,開始變得“不懂規矩”,重新被人恥笑。阿卡基于是“這樣暈了過去,渾身發抖,搖搖晃晃,再也站立不穩”,由于生存空間的被剝奪而變得“很不自在,甚至也開始感到了恐懼”。
第二天他發了高燒。由于彼得堡氣候的慷慨的幫助,病情進展得比預期的更快,當醫生趕到的時候,摸了摸脈門,除了開一張戳藥的方子以外,一點辦法也沒有了,連這也只是為了讓病人不至于受不到醫術的恩惠罷了;然而立刻又宣布,頂多再過一天半,非完蛋不可,然后他對房東太太說:“老太太,您不必白操心了,現在就給他預備一口松木棺材吧。因為橡木的他買不起。”
最終高燒不醒,一命嗚呼,恐懼的他最終躲進了“棺材”里。
因此,從敘事空間上來說,果戈里有意將阿卡基所在的空間創造成一系列狹小、黑暗以及寒冷的地方,華麗的溫暖的外套僅僅存在了一天,卻導致阿卡基的心理空間發生了嚴重扭曲,讓讀者意識到這些個層層嵌套的外在物理空間的虛偽和黑暗,這也是作者從中流露出來的批判和同情。只有最后一層外套——棺材才可以讓阿卡基這種小人物安穩的長眠。
三、結尾的荒誕敘事特征
阿卡基死后,果戈里用荒誕的手法讓其靈魂復活,以反邏輯的情節透視事情的真相以及人們的靈魂。
“忽然謠言傳遍了彼得堡,說是在卡林金橋畔和附近一帶地方,一到晚上,就有一個官員模樣的死人出現,在尋找一件被劫的外套,并且以外套失竊為借口,不問官職和身份,從一切人的肩上剝掉各種外套……總而言之,剝掉凡是人們想得出用來遮蓋自己的皮肉的各式各樣的毛革和柔皮。”
阿卡基在尋找自己丟失的外套同時,也在實施報復,這種扭曲的人格使他不放過在街上遇到的每一個人,終于找到了曾經那位說自己不懂規矩,直接導致自己離開人間的官員。這里的情節會讓讀者認為結局是這位官員遭受到了死人給他的懲罰,然而果戈里對小說情節來了個劇烈反轉。
“他魂飛魄 散,驚恐萬狀,只聽得死人一迭連聲地說:‘哼!到底找到你了!我到底那個,揪住你的領 子了!我要你的外套!你不想法子找回我的外套,還痛罵我一頓,——現在把外套給我!可憐的大人物差不多嚇了個半死。”
死人搶走了他的外套,并說出了自己心中的怨恨。結尾這部分荒誕的情節讓讀者記起并且更深刻全面的解讀這位大人物官員,他是不乏同情心的,他的心里懷有許多善良的感情,只是官銜時常不讓它們表露出來。他的腦海中經常浮現出阿卡基那受不了嚴詞痛斥那蒼白可憐的模樣,并讓讓手下去打聽阿卡基的情況,想要給予一些幫助,得來的結果讓他震驚且備受良心的譴責。這給反邏輯性的真正的大結局提供了某些合理性,這位大人物得到的懲罰是言行上的轉變,甚至是人格上的改過自新。
“這件事對他的刺激太大了。他甚至很少對下屬張口閉口說:“您怎么敢如此放肆?您明白站在您面前的是誰嗎?”之類的話了;即使偶而要說,那么也 要先弄清事實真相才說。”
顯然,果戈里呈現給了一個讀者樂于接受的事實,這個荒誕的事實同時也體現了作者內心的某種希冀,而這種希冀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又是荒誕的,也許作為俄國寫實主義作家的先驅,只有荒誕才能緩解他及其筆下人物在非理性的官場空間之下那無處躲藏的憂懼和恐慌。
這個結局其實是小人物和解式的控訴,它荒誕地寫出了對一個美好社會的期待,而不是仇恨的報復死去的九等文官最終與曾經壓制他的高級官員以及體制和解,與這個寒冷讓人窒息的社會和解,找到了合身的外套,從此以一種最舒適的狀態重新存在于原來的空間環境之中。這種荒誕的敘事結尾不僅顛覆了人類既有的敘事邏輯模式,而且從思想上反映了當時社會底層的人們荒謬的生存狀態,這同時也是果戈里面對現實世界所感同身受的。
四、小結
《外套》的敘事背后是果戈里的匠心獨具、切身感受以及精華積淀。首先,從敘事視角和主體來看,“我”或者“我們”不僅是故事的編撰者,更從一個上帝的視角全面窺探了阿卡基的活動,無死角地將其全部行為動作展現給讀者,唯獨蔭蔽其心理空間,這是一種非聚焦模式。從敘事空間來看,阿卡基所處的空間環境是一系列嵌套的個體,這些個體又都是現實復雜網狀世界的投射,無處沒有空隙,卻實為堅固,它們為每個人帶來的是心理環境的變形和扭曲。因此作者只能在結尾采用荒誕的敘事手法來緩解這種普遍性的恐懼,這種荒誕是雙向的,它誕生于荒誕的現實社會環境之中。
在真個敘事過程中,所有的人都存在某種“疾病”,阿卡基無疑是“病”得最嚴重的,去世是因為一件外套,靈魂復活之后的復仇也僅僅是尋找外套,作者通過向讀者展現這個小人物的眼界和格局來實現某種意義上的控訴。
故事的最后,阿卡基“完全隱沒在黑暗的夜色里”,他曾困于黑暗,陷于黑暗,最終獻身于黑暗,甚至泯滅了“逃跑”的意識,隨后就是安于其中。阿卡基是官僚制度之下無數小人物的一個典型,作者透過他,采用精心而獨特的敘事表現了社會對人性的吞噬。
注釋:
(1) 果戈里:《外套》,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
參考文獻:
[1]羅鋼.敘事學導論[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2]胡亞敏.敘事學[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
作者簡介:巴蕾,華中師范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2016級本科在讀。熱愛文學,樂于寫作,發表學術論文和文學作品多篇,出版專著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