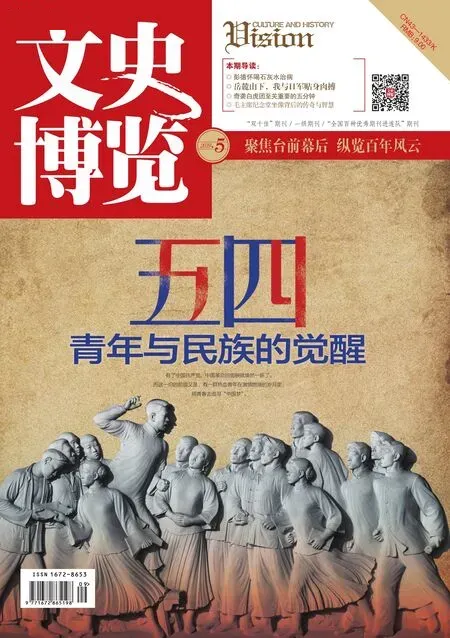巴金送我三瓶酒
20世紀80年代,研究巴金(1904—2005,原名李堯棠)的人漸漸多了起來,有關巴金的著作、論文發表了不少,新的見解、新的材料也陸續出現。可以說,巴金研究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中成績比較突出的一個方面。因此就有一些巴金研究者與我商量,想成立一個巴金研究會,舉行巴金研討會。文藝界領導陳荒煤、羅蓀等也幾次要我牽頭把巴金研究會搞起來。我以為很有必要:既可總結檢閱這些年巴金研究的成果和經驗,又可互相交流研究心得。只是后來,聽說四川省社科院正籌備在1985年春舉行一個“陽翰笙、巴金、沙汀、艾蕪”研討會,于是便把我們單獨舉行巴金研討會的想法暫時擱下了。
“四老會”的會場設在成都東風賓館。1985年6月我到會場住地時,就見到上海文藝出版社李濟生、上海作協魏紹昌兩位老人,都是熟人。濟生叔是巴老最小的弟弟,我因為與巴老家的人熟了,也就跟著小林(李小林,巴金的女兒——編注)他們喊濟生叔為“小叔叔”。老魏在我寫《巴金評傳》時,在資料方面曾給過我很大的幫助。他們那時都是已近70歲的老人了,除老魏的背佝僂得厲害外,身體都還健朗。
一見面后,濟生叔就拉著老魏和我上街去吃小吃。我們就近找了一家招牌名字很雅氣的叫“珍珠圓”的小店。我是第一次來成都(幼時來過,早無印象),覺得什么都很新鮮。濟生叔點了七八種點心,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紅油水餃”,那餃子完全浸泡在紅辣椒油里面,顏色鮮紅,樣子極為可愛,吃到嘴里,熱辣辣的,滲透著濃烈的鮮味,使你不得不產生好感,以至顧不得那刺激的“痛苦”,竟還想吃。濟生叔問我印象如何,我說:“吃得我又愛又怕!”
這次會議,“四老”中數巴金研究者人數最多,所以單獨編成一個小組活動。這也是巴金研究者頭一次相聚,氣氛非常熱烈友好。我在會上作了一個題為《巴金,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發言。會后活動:游青城山、峨眉山。大部分時間,我都和濟生叔、老魏及其他幾位朋友做伴在一起。可能就是在這樣的游玩閑聊中,不知怎么說到喝酒了。我無意中說了一句“現在市場上五糧液很難買到,真假難辨”。濟生叔就問我:“你想買五糧液?”我說:“我平時不喝酒,無所謂的,不過到成都了,如碰上不妨買一瓶。”
濟生叔聽了這話,就記在心上了。他說:“這事我有辦法。我每次到成都來,親友們都會送我一些酒。到時候,我給你想辦法。”
我看濟生叔認真了,怕給他添麻煩,就再三說:“請不要費神,我并沒有喝酒的習慣。”這確是事實。
哪知那時五糧液還真的非常緊俏,連成都也買不到。濟生叔就把親友送給他的“瀘州老窖”轉送了我一瓶,這也是好酒,并不亞于五糧液。我堅辭。濟生叔就是不許。我只好再三感謝收下了,但真是不好意思。
沒有想到的是,這事過去了一年后,1986年5月22日,我到上海出差,去探望巴老時,說了一會兒閑話,巴老忽然對九姑媽微笑著說:“去,把五糧液找一瓶給他,還送他一本書。”
我很意外,巴老怎么想到送酒給我?我自言自語說:“一定是小叔叔說了,咳!我平時就沒有喝酒的習慣。巴老,我沒有孝敬您,怎么還好意思讓您送酒給我喝呢!這不可以的!”確實,我平時去巴老家,總是兩手空空的,幾乎不曾送過什么禮!所以我當時非常窘困,不知說什么好。
“哪里來的五糧液啊!”九姑媽說。
“有,你去找找!”巴老肯定地說。九姑媽就起身去找,一會兒,找來一瓶。
“我現在不喝酒。這酒也是人家送的。”巴老大概看出我的不安,就笑著安慰我。他那高興的神情似乎還帶著一點玩笑的成分。
在這之后,1987年,1989年,我兩次去巴老家時,巴老又各送我一瓶酒,一次是“瀘州大曲”,一次是“文君酒”。就這樣一件小事,巴老竟一直記在心上。就像我在一篇《巴金和書》的文章中所說的那樣:巴老不僅愛買書,讀書,藏書,還愛送書。除了慷慨贈給朋友們有關他的新作外,凡知道你在做什么工作(無論寫作或翻譯),只要他那里有相關的書,就會主動送給你或借給你,供你參考使用。他說:“書印出來就是給人看的。”所以見到巴老的人,無論陌生的或是熟悉的,都常有機會得到巴老的贈書。他總是想著別人,事無巨細,都放在心上,幫助你,支持你,關心你。我是受惠最多的之一吧!但這也是我感到最有愧的地方。
記得巴老送我第二瓶酒,是在1987年2月27日。我在上海辦完公事,到巴老家去辭行。那天巴老家里人少,濟生叔是我打電話約他來見面的。《隨想錄》合訂本樣書剛剛收到,小娘娘(巴金的十二妹)正在檢查頁碼。巴老對我說:“我送你一瓶酒。我不喝。都是別的朋友送的。”我聽了,心里著急:得了一次,已經過分,怎能無休止地在巴老那里拿東西呢!
但是,巴老已經起身,步履蹣跚地特意上樓去取。過了一會兒,他一手扶著樓梯,一手抱著一瓶酒,顫巍巍地走下樓來。等我反應過來時,濟生叔已經趕前一步去把酒接了過來,交給了我。我當時真有點無地自容的感覺,覺得罪過至極!我再三對巴老說:“酒,您不要再送我了!我平時真的不喝酒。我倒想跟您要一本《克魯泡特金自傳》。”這是巴老年輕時非常喜愛并把它翻譯出來的一本書。
巴老說:“可以。書可以送你,不過我不簽名了。不要讓人家覺得我還在宣傳無政府主義。”稍過一會兒,他又說:“現在風氣很壞,小事情不注意,讓有些人做文章,犯不著!”
那天,正值二月嚴寒,室內也還溫暖。巴老家本來是有火爐的。“文革”中,什么都沒有了。這次,巴老生病住院后,市里才專門批了一些煤(那時煤是定量供應的),給安裝了暖氣。巴老因自己生病,也就接受了。
這里順便還說兩件小事。一次是巴老來北京時,對我說:“我替你買了一套《辭海》,太重,這次沒有帶來。”起因是,中國作協舉行中篇小說、報告文學、新詩優秀作品評獎活動,邀請巴老主持并致辭。巴老給羅蓀回信說:“評獎會只要不找我去開會,不講話,掛個什么名是可以的。我的理想是關門寫作。”
后來中國作協開頒獎會時,要用巴老名義搞個書面致辭,就把這個任務派給了我。我只得模仿巴老的語氣和思路擬了一個草稿,寄給巴老。巴老審改了幾處后定稿寄回,由作協在大會開幕式上讀了。以后又有報刊發表,寄了稿費給巴老。巴老就用這筆錢買了《辭海》。因為這書像磚頭一樣沉,無法隨身帶來,最后還是從郵局寄給了我,20年來成為我的案頭常用的工具書。
就是這件事,也使我不安了好長時間。說實話,我從工作以來,不知給領導起草過多少文稿,卻從不見有誰想到過我。巴老在錢物方面,只有饋贈給別人、接濟別人、給予別人,其中有同事、朋友,有認識的,也有不認識的,甚至完全是陌生的人,也長期接受他的經濟上的幫助,可他卻從不去沾別人的光。巴老的情太重、心太細,即使別人的小事,他也放在心上,一清二楚。
這樣的事,后來又有過一次。那是1984年年底,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的開幕詞,也是作協要我起草的,經巴老修改定稿。報刊發表后,巴老就把稿費如數轉寄給了我。我知道巴老的脾氣,也就不再說什么,只好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