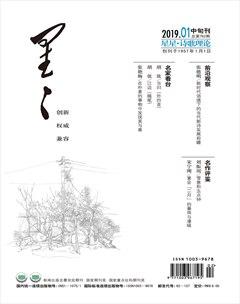無限、有限的隔離與和解
2019-06-25 10:11:04余修霞
星星·詩歌理論
2019年1期
余修霞
尼采認為:“生活是一面鏡子,我們努力追求的第一件事,就是從中辨認出自己”。李元勝的部分詩歌,試圖從生活的無限中辨認自我的有限。二者經過互換,生活定格于詩意的某個瞬間,自我升華成無限的集合體,最終達到和解。
辨認自我的起因常常是隔離感:“比如我的,夕陽/只不過給手中的咖啡/盤旋在心里的/和世界之間的隔離感/耐心地勾上金邊”。在骨子里頭,詩人李元勝喜歡無意識地進行自我隔離,靜靜地將“我”擺放在一個只有自己才可以感覺到的空間中,把所見所感放置在一個特殊距離的處所,甚至將所見的人、物、詩蒙上一種輕紗,使之成為精神存在的朦朧形態。再經過主觀思維加工外物或自我,塑造一個巨大的自我,輕而易舉就能夠掙脫主觀意識的世俗束縛。等讀者揭開輕紗,就會發現日常生活露出驚喜的真容,諸如咖啡被容器隔離卻被夕陽勾上金邊。普通景象搖身一變,成為詩意存在。隔離感,可以創造出其不意的意象美。
隔離感在李元勝的詩歌中被反復折疊,像劇本,像時間本身,像詩人原本年輕卻被隔離到有新意的衰老之列:“這一生,是讀舊了的劇本/這一年,只有衰老略有新意/它們來了,我伸出了手/中間隔著我的身體,這古老的柵欄”。李元勝把身體比喻成“古老的柵欄”,就是最典型意味無窮的一種詩性隔離手法。身體把思想隔離起來,思想卻沖破柵欄蜂擁而來,無窮無盡,顛覆著讀者對詩歌的預期推測。……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