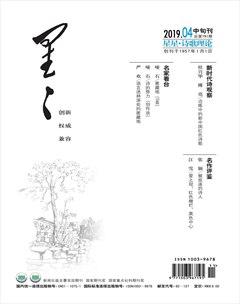抑郁的隨想
2019-06-25 10:13:03阿貝爾
星星·詩歌理論
2019年4期
阿貝爾
冬 天
冬天有綿長、飄揚的東西。像酒,但不是酒。與酒有關。像女人,但不是女人。與女人有關。冬天里的人恰恰沒有睡眠,而是睜大眼睛醒著。不是因為寒冷,不是因為身體被包裹,不是因為悠閑,是因為靈魂的過。自由與迷醉。渴望與冒險。
凱爾泰斯
在我的感覺中,凱爾泰斯·伊姆萊比卡夫卡要親切。讀《另一個人》,我能感覺到他靈魂和語言的質量。我還不曾這樣與某位作家一見鐘情過。
凱爾泰斯不是多產的克隆型作家。他不愛多產,更不接受克隆。這只能說明他不靠寫作生存,不靠寫作存在,不靠寫作站立。為什么寫作?那就是無法不在的表述的欲望,就是那些無法忘記的記憶,就是作為一個特殊年代的猶太人經歷的苦難和對苦難的咀嚼。
讀凱爾泰斯,不能不想到我們當今作家的寫作狀態(tài)——多產、克隆、名利、時尚化、市場化。急功近利葬送了他們本來就有限的才華。
活 著
活著,軌跡卻是既定的,無論如何創(chuàng)新,都擺脫不了傳統和社會的慣性。一個人到底有沒有所謂靈魂,我現在開始懷疑了。據說世界是物質的,那么靈魂也應該是物質的。物質的,就該有質量。我不知道如何測量靈魂的質量。家政里包含了社會學和動物學。管理三個人的吃喝拉撒。三個人又有血脈的關系。管理社會的細胞,掙取鈔票,分配鈔票,為了細胞核、細胞膜和胚芽。社會的道德的東西貫穿進來,不時攪得細胞內部天昏地黑。每一個人都先是自然的,后是社會的。成了社會的人,細胞必然失衡,必然庸俗。……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