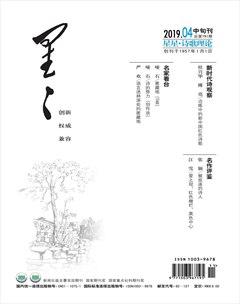寫或不寫,我早已準備了一顆失敗的心
2019-06-25 10:13:03季風
星星·詩歌理論
2019年4期
關鍵詞:生活
詩是詩人的個人心靈史,是對不斷出現的萬事萬物詩意的證明和澄清,是現實的照耀和時代的后視鏡。詩是詩人自救的稻草,是一個人夜晚的那一線光亮,她不斷救贖我們并不高貴的靈魂。她分析底色的能力和揭露真相的無畏,讓人類時常羞愧。
敬畏詩歌,她有神性,我從來不敢懈怠。想寫時我廢寢忘食;寫不出來時,我就一個字不寫。能在大刊上發表當然開心,不能發我也不會嫉妒他人,寫詩,是自己內心的事情。我熱愛那些從村莊展翅的飛鳥,泰戈爾式的飛鳥,是它們連接了原汁的生活和詩意的美學,讓我與詩歌生死相依。
剛寫詩的時候,心里就夢想著做詩人,但又顧忌“志大才疏”做不了詩人。工作后在一個小學教書,更恐懼我的上司因我的“不務正業”而招他譏諷式批評。我用我姓名后面兩個字的諧音“季風”作為筆名,以此拉開了我一生的游擊戰。于是,我在這世上便活成了兩個人,“馬繼峰”是工作生活中的我,“季風”是詩歌中的我。我從不愿暴露這兩個“我”之間的關聯,長期以來,這兩個“我”在別人看來是毫不相干的。很多同事多年來不知道“馬繼峰”是寫詩的“季風”,詩界有很多朋友也不知道“季風”是一個地方小吏“馬繼峰”,我和另外一個的我在兩片天空下同時活著。這兩個“我”私下相互取暖,也互憐互愛。
2001年之后我的詩歌越寫越少,2007年以后的十余年里,一行詩都沒有寫。名利場上的詩人,像極了精神潛伏的賊。貿然出頭,我怕被這個世界遺棄;……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風流一代·經典文摘(2018年1期)2018-02-22 09:00:43
黨的生活(黑龍江)(2017年12期)2017-12-23 17:01:20
求學·文科版(2017年10期)2017-12-21 11:55:48
求學·理科版(2017年10期)2017-12-19 13:42:05
民生周刊(2017年19期)2017-10-25 07:16:27
特別文摘(2016年19期)2016-10-24 18:38:15
爆笑show(2016年3期)2016-06-17 18:33:39
37°女人(2016年5期)2016-05-06 19:44:06
爆笑show(2016年1期)2016-03-04 18:30:28
爆笑show(2015年6期)2015-08-13 01:45:40
- 星星·詩歌理論的其它文章
- 詩人與世界
- 新世紀,詩歌依然自在
- 抑郁的隨想
- 我與兒童詩
- 西昌過年,吃李小腸燒烤
- 顏 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