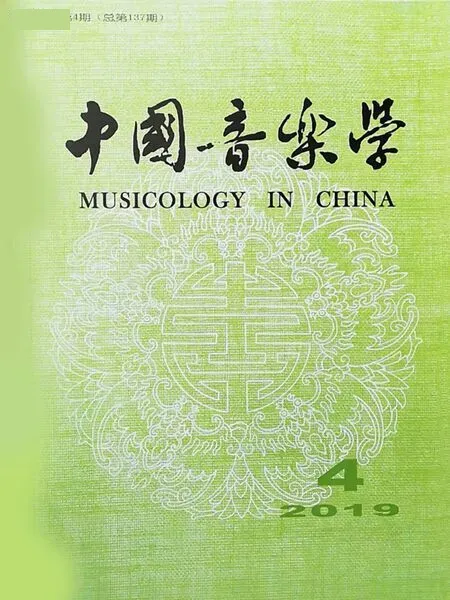試論春秋晚期樂鐘隨葬制度的變革
——以曾國、晉國為中心
周代社會奉守“禮樂并重”的治國原則,各類編鐘、編磬與青銅禮器一樣,成為貴族身份等級的重要標識,并形成一套獨特而嚴格的樂鐘制度。歷經西周至春秋時代的發展,至春秋中晚期階段,周人已經構建起完備的由鈕鐘、甬鐘、镈鐘所構成的三元組合編鐘系統,而不同等級的貴族也形成了各自有別的樂鐘組合形式。①唐蘭:《古樂器小記》,《燕京學報》1933年第14期;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下編第四章“樂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王世民:《春秋戰國葬制中樂器和禮器的組合情況》,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編鐘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8頁;Lothar Von Falkenhausen.Suspended Music:Chime-Bells in the Culture of Bronze Age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李純一:《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文物出版社,1996年;《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大象出版社,1999年;王子初:《中國音樂考古學》,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方建軍:《中國古代樂器概論(遠古——漢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王清雷:《西周樂懸制度的音樂考古學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陳荃有:《中國青銅樂鐘研究》,上海人民音樂出版社,2005年;邵曉潔:《楚鐘研究》,人民音樂出版社,2010年;王友華:《先秦編鐘研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等等。《左傳·襄公十一年》記載“鄭人賂晉侯,以……歌鐘二肆,及其镈磬”,即諸侯等級使用兩列歌鐘與一列镈鐘,而晉侯僅賞賜重臣魏絳兩肆樂鐘(歌鐘一肆、镈鐘一肆),說明二者的用樂組合是顯然不同的。考古資料對此亦多有反映:如河南葉縣舊縣M4許靈公墓便隨葬甬鐘兩組各10件、镈鐘兩組共8件(分為有脊镈4件和無脊镈4件)、鈕鐘一組9件(圖1);①平頂山市文物管理局、葉縣文化局:《河南葉縣舊縣四號春秋墓發掘簡報》,《文物》2007年第9期。新近發掘的山東沂水紀王崮春秋墓同樣隨葬甬鐘9件、镈鐘4件、鈕鐘9件;②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沂水紀王崮春秋墓出土文物集萃》,文物出版社,2016年。其他像壽縣蔡侯墓、輝縣琉璃閣甲墓、沂水劉家店子春秋墓、邳州九女墩三號墓、曾侯乙墓等貴族墓葬中也都采用了類似的多元編鐘配列,③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安徽省博物館:《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科學出版社,1956年;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沂水縣文物管理站:《山東沂水劉家店子春秋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第9期;孔令遠、陳永清:《江蘇邳州市九女墩三號墩的發掘》,《考古》2002年第5期;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輝縣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1956年;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說明這已成為此時各地高級貴族們的共識,而中小貴族用樂則依次降差。④音樂史學者對此已經多有討論,考古資料的梳理亦可參看張聞捷《周代葬鐘制度與樂懸制度》第二節的討論,《考古學報》2017年第1期。

圖1 葉縣舊縣M4出土三元組合編鐘系統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考古所見周代的編鐘多出土于墓葬之內,迄今未見宗廟中樂鐘的實際組合情況。而墓葬的營建與隨葬品的選擇、陳設,又受到墓室空間、生死觀念、財富多寡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往往呈現出與宗廟禮制不同的特點,所以當我們主要通過考古資料來探討周代樂鐘使用方式的變化時,無疑將其定義為樂鐘的隨葬制度更為準確,而不能簡單地等同于貴族生前的用樂模式。當然,這二者之間又并非是絕然割裂的,僅從青銅禮器的角度看,無論是形制、紋飾還是組合、制度等,葬器都受到了生前用器的強烈影響,同樣是身份等級的重要反映。所以,基于這一原則,我們也可以從樂鐘隨葬制度的角度來粗略窺探貴族用樂觀念的宏觀變化。
實際上,春秋末年,由于列國政局急劇動蕩,社會政治、經濟結構均出現了顯著的變革,相應地,禮樂制度亦隨之革新。通過考察南方曾國與北方晉國的一系列貴族墓葬隨葬樂鐘,可以發現兩點迥異于此前時代的全新樂鐘隨葬制度:其一是逐漸興起的對單類編鐘的偏好,并成為戰國樂鐘葬制新的典范;其二是新的隨葬樂鐘擺放形式的出現,折曲鐘磬逐漸成為各地貴族的新興風尚,而這又與禮制文獻的成書息息相關。今試分析如下。
一、隨葬編鐘配列方式的變革
編鐘配列方式是指在整套編鐘內,不同類型的樂鐘遵循音律要求,選用特定的數量并按照相應的排列方式懸掛組合。通常來講,等級較高的貴族其鐘型配備亦更為豐富,鐘列結構更為復雜,即前文所述的三元組合編鐘系統,而等級較低的貴族則常常僅有兩類或一類樂鐘,以此形成身份等差。但是,當高等級貴族墓葬中所見編鐘的配列方式亦普遍只采用一類樂鐘時,必然意味著一種新的隨葬樂鐘選擇理念的出現。
A.曾國的甬鐘偏好
首先來看曾國墓葬中新的編鐘配列方式。在新近發掘的隨州文峰塔M1春秋晚期曾侯輿墓中,共出土樂鐘10件,其中5件完整,5件殘缺,均為甬鐘。依據器形特征及鐘體銘文可以將編鐘分為三組:A組鑄于“惟王正月吉日甲午”,器形碩大,長甬、長枚,衡部與甬體飾浮雕蟠魑紋,舞部與鼓部飾浮雕蟠龍紋,銘文按“右起左行”分布,全文共169字,敘述曾侯克定楚難、改復曾疆的功績;B組鑄于“惟王十月吉日庚午”,器形略小于A組,長甬、長枚,衡部飾渦紋,舞部與正鼓部飾浮雕蟠魑紋,銘文亦采用“右起左行”模式,全文經補足為38字,記敘曾侯定曾土、做鐘“以祈眉壽”;C組器形最小,長甬,鐘枚呈上細下粗的圓柱體,頂端弧突,飾渦紋。兩面正鼓部均用紅銅鑄鑲圓渦紋或鳥云紋作為敲擊標志,甬體及鼓部飾細小的蟠螭紋。鐘體銘文同樣采用“右起左行”模式,全文共36字,記述鑄鐘的用途主要為宴樂“吾以及大夫、肆士”。①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隨州文峰塔M1(曾侯輿墓)、M2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14年第4期。所以無論從器形、紋飾,還是銘文內容來看,這均是三組不同階段鑄造的甬鐘臨時被拼湊在一起,與曾侯乙編鐘的中層情況十分相似(詳下文)。雖然這座墓葬曾被盜掘,但也很難想象會僅盜走镈鐘、鈕鐘而仍剩下完整的并帶有長篇銘文的甬鐘,且在迄今所見采用三元組合編鐘系統的例子內,也沒有見到同時配備三套甬鐘的。所以更為合理的推測是,曾侯輿就只使用了三套(或者更多)甬鐘隨葬,采用的是全套甬鐘的配列方式,其中A組應是替代此前盛行的镈鐘組合,而B、C組則是分作兩列的主體樂鐘。這又可以得到其他曾侯墓葬的印證。
隨州擂鼓墩一號墓為戰國初年曾侯乙之墓,出土九鼎八簋組合及完整編鐘、編磬各一套。編鐘皆出于中室,共計65件,分作三層,上層懸掛19件鈕鐘,中層懸掛32件甬鐘(又分為9、11、12三組),下層懸掛13件甬鐘及1件大镈鐘。從鐘型配備來看,似乎亦是三元組合編鐘系統,但其實最下層的镈鐘僅有1件,并不成組,而且音律上也不與其他13件甬鐘搭配(替換掉原有的“姑洗之大羽”甬鐘),顯然是考慮到作為楚惠王贈送的特別之物而臨時被添加、拼湊進來的(原打算共裝4件),并不屬于原有的鐘列之內;最上層的19件鈕鐘則被分隔在三個不同的小鐘架內,分為6、6、7三組。譚維四、馮光生先生曾指出,上層二、三組鈕鐘實際是從中層最左側短梁上被撤下的14件鈕鐘內挑選而來,但分組時缺少一鐘。而上層一組鈕鐘則是從另一套完整鈕鐘內抽出6件加入的,也就是說,這些鈕鐘完全是拼湊形成的結果,②譚維四、馮光生:《關于曾侯乙墓編鐘鈕鐘音樂性能的淺見——兼與王湘同志商榷》,《音樂研究》1981年第1期。且各組在音律上也是十分紊亂,“音列結構都不符合演奏樂曲的要求”③李純一:《曾侯乙墓編鐘的編次和樂懸》,《音樂研究》1985年第2期;黃翔鵬先生在《先秦文化的光輝創造——曾侯乙墓的古樂器》一文中亦指出曾侯乙編鐘實際用于演奏的僅有中、下兩層樂鐘,《文物》1979年第1期;有學者指出上層樂鐘為定律之用,但實際上19枚樂鐘中僅有9枚標有樂律銘文。總體上諸家學者都贊同上層樂鐘樂律混亂、無法演奏的結論。另可參看潘建明《曾侯乙編鐘音律研究》,《上海博物館集刊》1982年第2期。,與鐘虡上所標音高也無一對應,同時距離地面過高(高2.65—2.75米),也未見演奏它們用的鐘槌出土,所懸之虡上又無標音銘文,表明這些編鐘也是按照某種特定的需要后加的,而非演奏之用。④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從這些跡象看來,曾侯乙編鐘的演奏實際是僅依靠甬鐘來完成的,是一套以甬鐘為核心的配列方式,只是在喪葬活動中由于特殊的原因而臨時將鈕鐘、镈鐘加入進來,卻并不具有實際的用途。
發掘報告中還進一步指出,該編鐘中層短梁上有已經被填塞的14個長方形榫槽和小方孔,表明其曾懸掛過14件鈕鐘,后來,鐘梁被截短、填塞,重新髹漆著彩,改掛上11件甬鐘。但因鐘梁被截短(受墓葬空間所限),而被迫將兩件甬鐘懸掛在梁端銅套上,⑤同上注,另參看鄒衡、譚維四主編《曾侯乙編鐘》(上冊),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7年,第159頁。由此亦可見墓主人對于甬鐘鐘型的偏好。
戰國中期的隨州擂鼓墩二號墓因為同樣出土了升鼎9件、方座簋8件,所以也是一代曾侯之墓。墓內編鐘皆為明器,故未被盜掘,共計36件,全為甬鐘。其中8件體型較大,28件體型較小,音律紊亂,無法演奏。與曾侯乙編鐘一樣,這些樂鐘在墓葬內也呈特殊的折曲形式擺放,所以他們在樂鐘葬制上是一脈相承的,⑥隨州市博物館:《隨州擂鼓墩二號墓》,文物出版社,2008年;許定慧:《擂鼓墩二號墓編鐘及其音率測試》,《黃鐘》(武漢音樂學院學報)1988年第4期。只是擂鼓墩二號墓的墓主不再有喪事中的諸多調整,而直接以明器編鐘隨葬,這也是戰國之后日趨普遍的現象,但僅用甬鐘配列的方式卻無疑是曾國特有的樂鐘葬制。
依據這些墓例可以看出,從春秋晚期開始,曾侯墓葬中盛行僅以多套甬鐘搭配的編列方式,即全套樂鐘只見甬鐘,取代了傳統的三元組合編鐘系統,成為區域性的新的樂鐘葬制,我們可以稱其為“甬鐘偏好”。這一方面當然是得益于樂鐘鑄造、調音技術的進步,使得甬鐘亦可以達到镈鐘、鈕鐘的音律要求,而另一方面又折射出曾國高級貴族對于古老的甬鐘形態的偏好。張昌平先生曾提及曾國墓葬對于甬鐘具有特殊的喜好,①張昌平:《曾國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20—222頁。現在又可以進一步得到考古新資料的證實。
由此,我們又可以來進一步解答曾令人倍感困惑的王孫誥編鐘的問題。在淅川下寺M2國令尹薳子馮墓中,曾出土有一套著名的“王孫誥編鐘”,共計26件,未被盜擾,但鐘型卻全為甬鐘,分為大型8件、小型18件,在墓內成兩列分布,②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這與已知的春秋時期楚國樂鐘葬制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特點:像下寺M1隨葬9件一組的鈕鐘,下寺M10隨葬8件镈鐘、9件鈕鐘,淅川和尚嶺M2蒍子受墓(春秋晚期)隨葬8件镈鐘、9件鈕鐘,淅川徐家嶺M3、M10同樣隨葬镈鐘8件、鈕鐘9件,固始侯古堆一號墓隨葬镈鐘8件、鈕鐘9件等③邵曉潔:《楚鐘研究》,人民音樂出版社,2010年。,未見一例只使用甬鐘的現象。而在明晰了曾國新的樂鐘葬制特點后,我們便可以知曉“王孫誥編鐘”其實是借鑒了這一時期的曾國樂制而設計、鑄造的,與楚制無涉。那么,王孫誥就與薳氏家族的樂制風格截然不同,這對探討他的身份無疑提供了新的啟示。
B.晉國的镈鐘偏好
與曾國貴族僅用甬鐘來構成全套隨葬樂鐘所不同的是,這一時期北方的晉國公族墓葬又盛行镈鐘編列,即全套隨葬編鐘內只見镈鐘,而全不用甬鐘和鈕鐘搭配。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當屬山西太原金勝村M251,墓主為春戰之際的晉國公卿趙簡子或趙襄子,七鼎級別,未被盜擾。隨葬樂鐘共19件,卻全為镈鐘,按照器形、紋飾分作兩類,分別為體型較大的夔龍紋镈鐘5件和體型較小的散虺紋镈鐘14件。我們知道,5件一組的镈鐘遵循的仍是傳統的镈鐘器用制度(北方地區一般以4—5件成組),而14件一組的镈鐘卻采用的是鈕鐘的數量組合方式。④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太原晉國趙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王子初:《太原金勝村251號春秋大墓出土編镈的樂學研究》,《中國音樂學》1991年第1期。也就是說,從傳統樂鐘搭配來看,墓主人應該使用镈鐘5件、鈕鐘14件的配列,但很顯然,他更傾向于采用雍容華貴的镈鐘來取代鈕鐘,從而形成了14件镈鐘成組這樣一種全新的隨葬樂鐘組合形式。
此外,像山西侯馬上馬村M5218為春秋晚期晉國5鼎貴族墓葬,出土镈鐘13件,分為獸形鈕4件(明器)和環形鈕9件(以镈代鈕),未用鐘虡,與編磬及其他青銅禮器一起疊放在墓室西側;⑤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馬墓地》,文物出版社,1994年。上馬村M1004為春秋晚期5鼎貴族墓葬,出土雙獸鈕镈鐘一套9件(以镈代鈕),成一列置于棺槨南部;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馬墓地》1994年。山西屯留車王溝春戰之際墓葬中出土一套編镈鐘9件,底面平,鐘體飾夔龍、蟠魑紋,乳釘狀鐘枚,并搭配編磬一套9件;⑦項陽、陶正剛:《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山西卷》,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72頁。新近發掘的山西臨汾陶寺北墓地M1五鼎貴族墓中出土編鐘一套8件,均為镈鐘,形制相同、大小依次遞減;⑧承蒙發掘者告知,謹致謝忱。臨猗程村M0002為春秋中晚期晉國7鼎貴族墓葬,出土镈鐘一套9件(以镈代鈕),同時又搭配一套鈕鐘9件。⑨趙慧民、李百勤、李春喜:《山西臨猗縣程村兩座東周墓》,《考古》1991年第11期。上述例證呈現出新、舊兩種樂制共存的狀態,因此啟示我們,這種镈鐘配列方式可能正是源于晉國內部。
另在戰國初年的河南汲縣山彪鎮一號墓中,墓主為五鼎級別的魏國貴族,也恰出土了镈鐘14件,分為兩型,較大者5件,較小者9件,與趙卿墓中的樂鐘情況較為相近。而根據郭寶鈞先生所提供的墓葬平面草圖來看,這些樂鐘正作兩列排布,較大的5件在墓內西南角,而較小的9件則在其東南側另成一列分布。①郭寶鈞:《山彪鎮與琉璃閣》,科學出版社,1959年,第46—47頁;關于汲縣山彪鎮一號墓的年代及國別,陳昭容《論山彪鎮一號墓的年代及國別》對諸家意見有較好的梳理,《中原文物》2008年第3期。
從這些墓例可以看出,在春秋晚期階段,部分晉國公族也開始擺脫傳統樂鐘葬制的束縛,而偏好將镈鐘作為核心樂器,以镈代甬或以镈代鈕,形制上取用镈鐘形態,而數量上又遵循甬鐘或鈕鐘的規范。這樣全套隨葬樂鐘就僅以镈鐘構成,不見甬、鈕鐘。與南方曾國的甬鐘偏好一起,他們形成了這一時期各具特色的隨葬樂鐘組合形式,共同揭開了樂鐘葬制變革的新篇章。
當然,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并非所有的曾、晉兩國貴族墓葬皆采用的是上述甬鐘或镈鐘的配列方式,新、舊禮制的更替絕非一日之功。像棗陽曹門灣M30曾國貴族墓便出土的是一套10件的鈕鐘,②方勤、胡剛:《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曹門灣墓區考古主要收獲》,《江漢考古》2015年第3期。而山西長治分水嶺M269隨葬甬鐘9件、鈕鐘9件,M270隨葬甬鐘8件、鈕鐘9件等,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長治市博物館:《長治分水嶺東周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便仍遵循的是傳統的樂鐘葬制。但是當新的隨葬樂鐘配列方式出現之后,便迅速盛行起來,并對戰國之后的樂鐘埋葬制度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我們將在后文中重點論述這一問題。
二、隨葬編鐘擺放形式的變革
編鐘使用需按照一定的形式展開,這既是為演奏之便,同時也可以成為彰顯身份等級的又一工具。西周至春秋早中期,貴族墓葬中的編鐘多成列分布,或者為節約空間,而簡單疊置或套置在一起,并未出現將隨葬鐘磬折曲擺放的現象。像北趙晉侯墓地M93疑為“晉文侯”墓中,共出土16件甬鐘,分為大小兩組,已是西周樂制發展的巔峰。這些樂鐘在出土時“大型一套8件,南北排列,甬均朝東,小型的一套8件,位置偏南,被大鐘所壓”④北京大學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晉侯墓地第五次發掘》,《文物》1995年第7期。,說明正是分作兩列直線分布的。甚至當出現不同類型的樂鐘相互搭配使用時,也仍然遵循這樣的線性擺放原則:如隨州葉家山曾國墓地M111(曾侯犺)中,共隨葬4件甬鐘與1件镈鐘,出土時“皆鐘口朝下,一字排開”⑤方勤:《葉家山M111號墓編鐘初步研究》,《黃鐘》(武漢音樂學院學報)2014年第1期;方建軍:《論葉家山曾國編鐘及有關問題》,《中國音樂學》2015年第1期。,證明即是成一列擺放的;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國祭祀坑K5(春秋早期)中,出土8件甬鐘與3件镈鐘搭配,但镈鐘與甬鐘仍是成一列擺放(圖2)⑥早期秦文化聯合考古隊:《2006年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祭祀遺跡發掘簡報》,《文物》2008年第11期。。春秋之后,樂制繁復,镈鐘、鈕鐘相繼成為獨立的編列,但也仍是分作不同的鐘列成上下式直線分布。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河南新鄭禮樂祭祀坑,其中K1、K4、K5、K7、K8、K9、K14、K16之內均為镈鐘4件、鈕鐘20件,且分作三列陳設,即镈鐘一列、鈕鐘兩列各10件。鐘虡痕跡仍在,正為上、中、下三層結構,未見任何折曲。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鄭祭祀遺址》,大象出版社,2006年;新鄭金城路編鐘和城市信用社編鐘也是如此配置,參看趙世綱《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河南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

圖2 甘肅禮縣大堡子山樂器坑出土甬鐘與镈鐘
但春秋晚期之后,與墓葬中編鐘的配列方式變革一起,許多貴族開始將隨葬的鐘磬成90度折曲擺放,進而形成了一種特別的多面“樂懸制度”。曾侯乙編鐘的折曲形制早已被學界所熟知,其出土編鐘、編磬皆位于中室,編鐘鐘虡成90度折曲,6件鈕鐘、11件甬鐘與3件大型甬鐘成上、中、下三列懸掛于南側鐘虡上,其余編鐘則位于西側鐘虡上,一組編磬又位于北側,單獨成列,這樣恰構成了一個三面長方形的曲尺空間(圖3),①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與西周至春秋早中期的直線式擺放截然不同。

圖3 曾候乙編鐘的折曲鐘磬
實際上,近年來我們又陸續發現了眾多如曾侯乙編鐘一樣的折曲鐘磬實例,從而認識到這是春秋晚期之后各地興起的一種共通的隨葬樂鐘擺放現象,今試依年代差別分述如下:
淅川下寺M1為春秋晚期早段楚國令尹蒍子馮之夫人墓,屬5鼎大夫級別。此墓隨葬樂鐘保存較好,共為鈕鐘一套9件(敬事天王鐘),皆位于墓內中部東側。其中6件(標號20-25)呈南北方向一線排列,3件(編號26-28)呈東西方向一線排列,二者相連并正成90度折角,而編磬則基本散置于三件編鐘的一側。與曾侯乙墓不同的是,編磬是與其中若干件編鐘置于同一側,而非自成一面。②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51頁。
淅川和尚嶺M2為春秋晚期蒍氏家族成員墓,墓中殘存銅鼎7件,系5件箍口鼎(口沿下部有一圈凸棱承蓋)與2件子母口鼎拼湊而成,故亦屬大夫級別。隨葬樂鐘保存完好,計有镈鐘一套8件、鈕鐘一套9件,是這一時期較為常見的樂鐘組合形式。其中6件镈鐘與9件鈕鐘分上下兩列沿墓葬南壁放置,正如發掘報告所述(這些銅鐘)“在隨葬時均懸掛在木質的鐘架上,鈕鐘在上,镈鐘在下”,但另外2件體型最大的镈鐘(編號1、2號)卻單獨放置于東壁南角,與南壁的兩列編鐘相接并正成90度折角,同時一套編磬12件則位于2件編鐘的對面,這樣便也構成了一個三面長方形的曲尺空間(圖4)。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著:《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46頁。而且使用編磬自成一系的做法亦與曾侯乙墓相近,但將本為完整的成套镈鐘拆散開來,分置于轉角兩側的舉措又與上述下寺M1類似,說明葬鐘在折曲陳設時是較為隨意和多樣的,此外,墓主人顯然并非諸侯等級,這又體現出其在等級制度上的紊亂。

圖4 淅川和尚嶺M2出土編鐘與編磬的折曲擺放
固始侯古堆一號墓(春戰之際)隨葬樂鐘包括镈鐘8件、鈕鐘9件。這些銅鐘皆被置于陪葬坑的東南隅,未被盜擾,出土時“呈東西相并排列……銅镈鐘8枚,靠南壁6枚,另外最大的兩枚放在東壁與南壁的拐角處……銅編鐘9枚,置于編镈的北側,東西排列在一條線上”,同時鐘架痕跡尚存,正為兩條平行的彩繪橫梁(編號18-1、2),且18-1橫梁上的長方形孔皆與鈕鐘相對,說明其正是懸掛這些鈕鐘的,那么18-2自然配屬于镈鐘編列,鐘架座也僅有兩個(編號18-3、4),分布于南側兩列編鐘的兩端(圖5)。由此可見其排列方式與上述和尚嶺M2基本一樣,主體編鐘成上下兩列陳設于南壁,并有鐘虡遺痕,而兩件體型最大的镈鐘則單獨放置于東壁南角,二者構成90度的折曲形式,但特別的是,這座墓葬中并未見到編磬搭配。①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固始侯古堆一號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48頁。

圖5 固始侯古堆M1出土編鐘的折曲擺放
淅川徐家嶺M10為戰國初年蒍氏家族成員蒍子昃之墓,墓中出土束腰平底升鼎5件,故同屬大夫級別,隨葬編鐘亦為鈕鐘9件、镈鐘8件。鈕鐘皆置于墓內東南角,成一列分布,镈鐘則位于其前方,其中6件成一列平行分布,而另有兩件較大者(編號7、8)成90度置于東側,與和尚嶺M2、固始侯古堆一號墓中的葬鐘擺放形式幾乎一致,均將镈鐘拆解為6+2兩組,只是一套編磬散置于編鐘西側,由于出土位置凌亂,尚難以辨認其與編鐘的具體位置關系。不過這座墓葬中保存的鐘架座也僅有兩個,分別編號66、67,位于南側編鐘的兩端,而在東側2件編鐘的附近是并沒有見到鐘架座或鐘架遺痕的(圖6),表明它們是被特意取下來放置于此。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2004年。

圖6 淅川徐家嶺M10出土編鐘與編磬的折曲擺放
前述戰國中期隨州擂鼓墩二號墓所出36件甬鐘在墓內也呈折曲擺放:29件在槨室南部靠南壁成列式兩排陳設,其中16件甬鐘自成一列,而其他7件甬鐘則與6件镈鐘同列,且5件甬鐘塞于94號大鐘鐘體內,應當是為了節約空間之用。另有7件編鐘(2件大鐘、5件小鐘)又被單獨置于墓內西壁,亦成一列擺放,故發掘者推測應是使用了曲尺形鐘虡。不過與上述諸墓不同的是,該墓編鐘是將上下兩列皆成折曲擺放,而且為了適應墓葬空間的限制,而有意將原本成列的編鐘打亂,疊置在一起。此外該墓編磬主要與南壁編鐘平行放置,而并未如曾侯乙墓、淅川和尚嶺M2一樣形成獨立的一面樂懸(圖7)。③隨州市博物館:《隨州擂鼓墩二號墓》。

圖7 擂鼓墩二號墓出土編鐘的折曲擺放
安徽蚌埠鐘離君柏墓中,隨葬樂器皆位于南槨室,為鈕鐘一組9件,形制相同、大小相次,編磬一組12件。編鐘成一列沿北壁放置,而編磬則自北向南平行于東壁陳列,正與編鐘形成90度折角。①闞緒杭主編:《鐘離君柏墓》,文物出版社,2013年。這種由編鐘、編磬各自構成獨立的折曲形式又與曾侯乙墓相近。
近來發掘的湖北棗陽曹門灣M1可能亦是春秋時期一代曾侯墓葬,并出土有鐘虡遺痕,恰成90度的折曲形式,只可惜編鐘皆被盜擾,配列方式不明,故不再贅述。②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苗與南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十二五”期間重要考古收獲》,江漢考古編輯部,2016年,第79頁。這座墓葬的年代屬春秋早期,如果折曲鐘虡遺痕確定無誤的話,那提示我們曾國可能在折曲擺放鐘磬的實踐上具有重要的開創性意義。
其實這種折曲鐘磬的形制不僅多見于南方楚地,中原地區亦有發現。如山西潞城潞河M7為戰國早期五鼎級別貴族墓葬,隨葬樂器包括鈕鐘8件、镈鐘4件、甬鐘16件(分為兩組)以及編磬10件。由于木質鐘架易朽,故并未使用鐘虡而全部取下成列放置,這也是北方地區隨葬鐘磬的常見做法。其中8件甬鐘分布于墓內北部,沿北壁成列放置,而其余鐘磬則皆成一列置于墓葬南部,沿南壁放置,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晉東南地區文化局:《山西省潞城縣潞河戰國墓》,《文物》1986年第6期。從形制上看,正構成了一個對向分布的樂鐘空間。
洛陽西工區M131為戰國中期5鼎貴族墓葬,出土甬鐘16件,分為兩組各8件,是這一時期較為常見的樂鐘組合。其在墓葬內的擺放形式亦頗為特別:其中8件甬鐘成一列分布于墓內東側,從北向南依次由小到大,而另8件甬鐘則成一列分布于墓內南側,從西向東依次由小到大,兩列編鐘恰成90度折角,而一列編磬則位于東側編鐘的北部④蔡運章等:《洛陽西工131號戰國墓》,《文物》1994年第7期。。由于墓內僅隨葬了青銅禮樂器,所以節余空間十分寬敞,樂鐘陳列并不受到空間的限制,那么如此特殊擺放顯然是頗具禮制深意的。
東部地區則可舉江蘇邳州九女墩M2、M3徐國貴族墓為例。九女墩三號墓為春秋晚期徐國王室墓葬,雖然出土銅鼎三件,但隨葬樂器卻有甬鐘4件、鈕鐘9件、镈鐘6件、編磬13件,在墓中亦成折曲形式陳設:1號镈鐘與編磬位于北側成一列擺放,2—6號镈鐘與9件鈕鐘在東側成一列擺放,4件大型甬鐘則在南側成一列擺放,所有樂器恰構成一個長方形的曲尺空間(圖8);⑤孔令遠、陳永清:《江蘇邳州市九女墩三號墩的發掘》,《考古》2002年第5期。而在戰國初年的九女墩二號墓中,亦出土銅鼎三件,但隨葬樂器僅有镈鐘6件、甬鐘8件及編磬一套。不過這些樂器同樣被有意擺放成長方形的曲尺形狀,即每列镈鐘、甬鐘與編磬各占一面,镈鐘在北側,甬鐘在東側,而編磬在南側。雖然樂鐘組合有別,但擺放的形式卻與九女墩三號墓是十分相近的。⑥南京博物院等:《江蘇邳州市九女墩二號墩發掘簡報》,《考古》1999年第11期。
從上述諸多實例可以看出,在春秋晚期至戰國初年,不同地區的貴族都開始將隨葬鐘磬折曲擺放,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葬儀。尤其是許多貴族墓葬內空間其實仍十分寬敞,隨葬樂器并不受到空間的限制,但仍然作如此特殊的陳設,顯然是蘊含了深刻的禮制含義。雖然目前這種擺放形式僅見于墓葬資料,并不能夠完全等同于貴族生前的樂鐘使用方式,且數量上也并非十分巨大,但至少能夠表明,這些貴族在生前已經具備了將金石之器多面環繞的意識,并在死后繼續如此展現。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上述墓葬中的折曲鐘磬其實缺乏統一的形式規范,既有將镈鐘拆解開來分兩面擺放的現象,也有將甬鐘與镈鐘共置于一面的情況,同時編磬是否作為單獨的一面樂器也是因人而異、各有不同,可見雖然貴族們逐漸接受了折曲鐘磬的擺放原則,但在具體展現形式上卻頗具彈性,而沒有絕對一致的標準。當然,這也是由于墓葬這一特殊載體的制約,既有空間上的特定要求,同時也與不同貴族如何看待生死的觀念息息相關。
三、樂鐘隨葬制度變革的影響
如上所述,春秋晚期的樂鐘葬制變革具體表現在兩方面:其一是對單類樂鐘的偏好。以單類樂鐘所構成的葬鐘編列逐漸取代傳統的三元組合編鐘系統,在南方以曾國的甬鐘偏好為核心,全套葬鐘內只見甬鐘,而在北方則以晉國的镈鐘偏好為核心,全套葬鐘內只使用镈鐘;其二是新的隨葬樂鐘擺放形式——折曲鐘磬逐漸成為各地貴族們的共識。這兩種樂鐘埋葬制度的變化又對戰國禮制產生了深遠影響,同時也為戰國時期禮典文獻的成書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首先,從樂律的角度看,全套甬鐘或镈鐘配列的出現,意味著音律對于樂鐘類型的束縛被消除,鈕鐘、甬鐘、镈鐘不再囿于高、中、低音的限制,同一類型的樂鐘即可滿足各種樂律要求。因此,戰國之后,不同類型樂鐘之間相互替代的現象便層出不窮;同時,編鐘尺寸也不如昔日一樣,遵循鈕鐘、甬鐘、镈鐘依次增大的趨勢,而呈現出多樣和隨意的局面。
在上舉邳州九女墩M3中,便可以見到體型最大的不再是傳統的镈鐘,反而是4件甬鐘,而且以4件成組的方式在這一時期也是屬于镈鐘的器用制度(甬鐘基本以8—10件成組),所以墓主人應是以甬鐘來替代镈鐘使用。①孔令遠、陳永清:《江蘇邳州市九女墩三號墩的發掘》,《考古》2002年第5期。再如河南陜縣后川M2040(七鼎貴族)中,出土編鐘包括陶甬鐘16件(分為2組)、镈鐘9件、鈕鐘9件,但又有大型的甬鐘4件,尺寸遠大于其他的樂鐘,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陜縣東周秦漢墓》,科學出版社,1994年。故而也是“以甬代镈”的現象,而9件一組的镈鐘又采用的是以镈代鈕的做法,顯示出其與晉國禮制系統的深厚淵源。
類似的現象亦頻繁見于南方楚地,像湖北棗陽九連墩M1戰國中期楚國高級貴族墓中(升鼎5件),據發掘者王紅星先生介紹,北室出土編鐘34件,“有上、下兩層,下層甬鐘一組12件,上層鈕鐘二組各11件”③湖北省博物館編:《九連墩——長江中游的楚國貴族大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9頁。。而在等級相近的荊州天星觀M2邸陽君潘乘夫人墓中,也恰出土了34件編鐘,但編列結構卻為鈕鐘兩組各12件、镈鐘10件,分作兩列懸掛于一架鐘虡之上。這兩套樂鐘內的鈕鐘均采用“咬合式銜接法”,形成帶有“商角”“羽曾”“商曾”等偏音的七聲音列,④湖北省荊州博物館:《荊州天星觀二號楚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但與主鐘搭配的既可以是12件甬鐘,也可以是10件镈鐘,說明它們可以實現相近的音律要求,自然這些貴族在選擇鐘型時就不再存在絕對的標準了。
另在業已發掘的廣州象崗南越王墓、山東洛莊漢墓(樂器坑)和江蘇大云山一號漢墓等漢代諸侯王墓葬中,均出土5件甬鐘、14件鈕鐘搭配的樂鐘組合,分作上下兩列陳設,⑤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西漢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濟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東章丘市洛莊漢墓陪葬坑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8期;王子初:《洛莊漢墓出土樂器述略》,《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第4期;方建軍:《洛莊漢墓14號陪葬坑編鐘研究》,《音樂研究》2007年第2期;王清雷:《章丘洛莊編鐘芻議》,《文物》2005年第1期;南京博物院等:《江蘇盱眙縣大云山西漢江都王陵一號墓》,《考古》2013年第10期。應是漢代這一等級常用的樂制。而如果回顧兩周時期的樂鐘制度,便可以知道5件一組實則是镈鐘的編列方式,但漢代之后镈鐘消失,工匠們便用甬鐘來代替镈鐘使用,而且在樂律上也同樣僅起著節音的作用,⑥南京博物院等:《江蘇盱眙縣大云山西漢江都王陵一號墓》,《考古》2013年第10期。可見春秋晚期以來的樂制變革理念一直持續影響至漢代。
其次,曾、晉等國這兩種新的葬鐘配列方式無疑開啟了一種將隨葬樂鐘簡化的趨勢,無論是鑄造者還是演奏者,當只需關注于一類樂鐘的鑄造和演奏時,自然會節約相應的資源、時間和精力。因此,戰國之后,這種理念持續發酵,進而催生出另一種新的葬鐘配列方式——鈕鐘配列,①需要說明的是,春秋時期以來單純的鈕鐘配列就已經出現,像侯馬上馬M13便只出土了9件一組的鈕鐘,不過這一時期主要局限在較低等級的貴族墓葬內,與高等級貴族所采用的三元組合編鐘系統形成等級上的差異。而這里提到的戰國時期的鈕鐘配列則主要是指高等級貴族在簡化樂鐘的理念下,所使用的一種編列方式,而替代了原有的多列組合編鐘系統。也就是高級貴族墓內的全套編鐘只有鈕鐘,而不再采用各種類型樂鐘混搭的模式,同時編鐘列數也簡化為一列。如著名的信陽長臺關M1、M2中,均只出土了13件一組的鈕鐘(M1為銅質、M2為木質),懸于一虡鐘架之上。且M1遣策中(簡2-018)正記為“樂人之器,一槃桯首鐘,小大十又三”,可知并無缺失。這兩座墓葬的主人均屬于楚國的封君,等級上高于上述淅川和尚嶺M2、徐家嶺M10、九連墩M1等墓葬,所以若依照傳統禮制,自然應是甬、鈕、镈鐘三列齊備,但在戰國時期新的樂鐘埋葬理念下,就僅被簡化為一列的成套鈕鐘了。②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此外,像河南上蔡楚墓(封君級別,13件鈕鐘)、山東臨淄商王村M2(14件鈕鐘)、河北平山M1戰國中山王墓(西庫內出土一組14件鈕鐘)、四川涪陵小田溪戰國墓(14件鈕鐘)、傳世羌鐘(14件鈕鐘)等出土編鐘莫不如此配置。③駐馬店地區文化局:《上蔡發現一座楚墓》,《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淄博市博物館、齊故城博物館:《臨淄商王墓地》,齊魯書社,199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墓——戰國中山國國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5年;四川省博物館、涪陵地區文化局:《四川涪陵地區小田溪戰國土坑墓清理簡報》,《文物》1974年第5期。如果不明晰春秋晚期以來的樂鐘葬制簡化趨勢,自然就無法理解這些與身份等級不相匹配的樂鐘組合,實際上他們的制度源頭皆在春秋晚期,遵循的是曾、晉兩國開啟的樂鐘埋葬制度的變革理念,并持續影響至漢代。
最后我們再來看折曲鐘磬的擺放形式在樂器制度史上的重要意義,顯然他與禮制文獻中的“樂懸制度”聯系最為密切。在《周禮·春官·小胥》篇中有關于這一制度的簡略記載:“正樂懸之位,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辨其聲。凡懸鐘磬,半為堵,全為肆。”自漢世以來,這一制度便深受歷代注經者的關注。鄭玄引鄭眾之說釋為“宮懸四面懸,軒懸去其一面,判懸又去其一面,特懸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墻,故謂之宮懸。軒懸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懸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玄謂軒懸去南面,辟王也。判懸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懸懸于東方,或于階間而已”,即天子使用四面鐘磬,諸侯、大夫、士等級依次降差。但是,由于經文簡短,并未言明各懸的實際構成情況和音律搭配原則,是以后世在樂懸制度的具體形式上諸說迭出,莫衷一是。清代學者江藩曾作《樂懸考》一文,簡略梳理了歷史上的樂懸諸說,“公彥以八音八風釋康成二八之義,是已……自有服(十九鐘)說,而編磬、編鐘之制,紊亂不倫:有設十二鐘于辰位,四面設編鐘、編磬者,北齊也;以鐘磬七正七倍而懸十四者,后周也;以濁倍三七而懸二十一者,梁武也;以鐘磬參懸之,正聲十二、倍聲十二而懸二十四者,魏公孫崇之說也;主十六枚之說,又加以宮商各一枚者,隋牛宏之說也。言人人殊,茫無定說”,足見這其中的混亂局面。④[清]江藩:《樂懸考》,轉引自曾永義《儀禮樂器考》,臺灣中華書局,1986年,第112頁。
其實在《儀禮》書中的《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禮》諸篇也有關于周代貴族宴饗用樂的記載,尤其是《大射禮》更涉及演奏時鐘、磬、笙、鼓的具體擺放位置,故可成為探討樂懸制度的重要補充:“樂人宿懸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镈,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镈,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簜在建鼓之間,鼗倚于頌磬西纮。”⑤胡培翚:《儀禮正義》,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臺灣學者曾永義即根據這一記載,對“樂懸制度”的不同擺放形式做出了很好地復原,主要遵循以下三個重要的原則:一是樂懸諸面的鐘、磬、镈基本對稱,數量相當;二是樂懸諸面并不連接,各自采用獨立的鐘虡,這樣方能便于移動和演奏;三是樂懸制度中編鐘與編磬均是處于同一面上的,不存在將編鐘、編磬拆解為兩面的現象。①曾永義:《儀禮樂器考》,臺灣中華書局,1986年。
但實際上,如果我們再檢視上述考古資料的話,可以發現幾乎沒有與禮經記載相一致的例子,無論是具體擺放形式還是等級差異上,現實情況都呈現出頗為多樣、隨意的局面,僅以軒懸制度而言,就可以看到曾侯乙編鐘、薳子受編鐘、九女墩M3、M2等四種截然不同的擺放形式,而身份也包含了諸侯、卿大夫等不同層級。這一方面固然可以部分歸結于墓葬資料的特殊性,但另一方面也表明,禮典文獻的記載雖然是以現實的禮制實踐為藍本,但其編撰卻又是一時、一地之功,并很可能摻入了后世學者的一些理想化成分,所以并不能完全涵蓋現實中的諸多禮制現象。我們可以說,經書中的“樂懸制度”確是依據春秋晚期以來的禮制實踐而創作、整理的,②陳公柔:《士喪禮、既夕禮中所記載的喪葬制度》,《考古學報》1956年第4期;沈文倬:《對士喪禮、既夕禮中所記載的喪葬制度幾點意見》,《考古學報》1958年第2期。并進而說明《儀禮》《周禮》中相關篇章的成書當在戰國之后。但同時,我們又不能盲從于文獻所述,而應充分認識到現實禮制實踐的多樣性和禮制文化的多元性。
結語
春秋晚期階段,貴族墓葬中的隨葬樂鐘出現了兩方面顯著的制度性變革:一方面是對單類樂鐘的偏好逐漸取代了傳統的以甬鐘、鈕鐘、镈鐘所構成的三元組合編鐘系統,在南方的曾國墓葬出現了全新的甬鐘編列方式,即全套編鐘僅以甬鐘構成,而北方的晉國墓葬則出現镈鐘編列方式,全套編鐘只用镈鐘而不見甬、鈕鐘。這兩種革新性的葬鐘組合方式對于戰國禮制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僅使得樂鐘類型之間的約束被打破,鐘型相互替代的現象層出不窮,也導致了戰國中期之后隨葬樂鐘組合的不斷簡化,以致如羌鐘一樣的全套鈕鐘編列方式的盛行,這其中蘊含的樂制變革理念自然是一脈相承的。另一方面,從春秋晚期開始,隨葬編鐘的擺放形式亦出現顯著變革,折曲鐘磬逐漸成為貴族們的共識并在各地涌現,雖然它們之間缺乏統一的形式規范,但無疑是貴族們將金石之器多面環繞的禮制意識的反映,并為戰國之后禮典文獻中有關“樂懸制度”的創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葬鐘配列方式與擺放形式的雙重變化是春秋晚期樂鐘埋葬制度變革的核心體現,不僅為探討戰國樂鐘葬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資料,亦為理解這一時期的“禮崩樂壞”局面開辟了全新的視角。
當然,還需補充說明的是:首先,我們所使用的主要是墓葬中的樂鐘資料,但墓葬作為一類特殊的物質載體,其隨葬品的選擇、陳設自有其法度、準則,并受到空間、財富、政治以及觀念(如明器編鐘)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并不能直接等同于貴族生前的禮儀活動,葬制不能涵蓋禮儀活動的全部。所以我們既不能簡單依靠墓葬資料來嘗試復原周代祭祀、宴饗等禮儀活動中的用樂制度,也不能簡單憑借統計分析來解釋問題,而需充分意識到墓葬資料的多樣性。雖然一些貴族墓葬中并未采用上述的樂鐘配列或擺放形式,但并不表明他們就不具備這樣的禮制意識;其次,東周列國文化雖然同出一源,但亦“漸行漸遠”,各地禮樂制度的差異性是不容忽視的。而禮典文獻的創作又是一時、一地之功,勢必無法全面地涵蓋各地的禮制實踐情況,所以我們在對待考古資料與文獻記載時,既不能盲目地苛求一致,更不應該互相否定彼此,而應意識到他們之間必然存在的差異性,進而可以利用這種差異性來探討禮制文獻的成書等問題。
附言:在山西臨汾陶寺北墓地2016年發掘的M1五鼎貴族墓中出土編鐘一套8件,均為镈鐘,形制相同,大小依次遞減,也屬于晉國典型的镈鐘編列,但M2同屬五鼎等級,編鐘卻是鈕鐘9件一套。另在信陽長臺關發掘的戰國中期M9中出土完整編鐘一套,經博物館實地查驗,其由9件镈鐘、9件鈕鐘共同組成,分上下兩列懸掛。镈鐘9件一組顯然遵循的是甬鐘或鈕鐘的編列制度,所以這里也是以镈代甬(鈕)的現象,同時镈鐘呈折曲形制擺放,2件較大者在一側,7件較小者在另一側,與上述和尚嶺等諸楚墓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