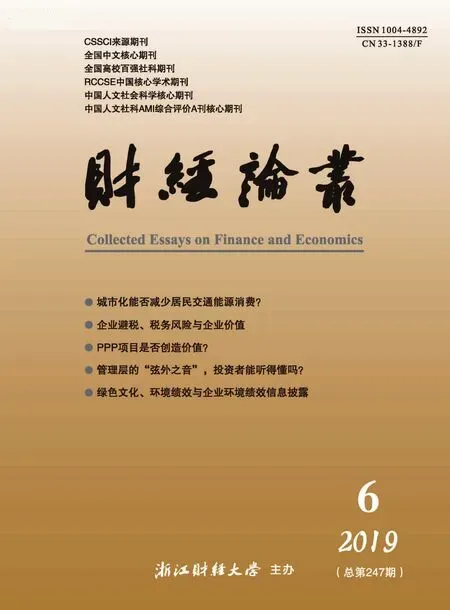城市化能否減少居民交通能源消費?
——基于中國城鎮住戶調查微觀數據的分析
張麗華,葉 煒
(1.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上海 200092;2.興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200120)
一、問題的提出
環境污染和能源消費是世界范圍內最為重要的社會經濟問題之一。能源的過度消耗不僅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也是對地球資源的不合理利用,不利于全球的可持續發展。目前,中國的能源消費量位居世界第二,且國內能源生產的增長速度趕不上能源消費,預計2020年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將高達60%。由于能源對外依存度過高和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節能減排已成為事關我國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大事。
據測算,城市人均能源消費大約是農村人均能源消費的8~9倍[1]。由于我國正處于快速城市化過程中,大量人口從農村轉移至城市,因而這一過程勢必造成能源需求的大幅度上升。盡管城市化本質上反映的是農村人口在空間上向城市的轉移,但從最終的空間形態來看,城市化可表現為城市人口密度提高和城市空間規模擴張兩個方面。如果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在總體上提高了能源消費量,但不同的城市化空間模式顯然具有不一樣的能源需求含義。進一步地,由于對城市道路交通需求的不斷增加及私人汽車的普及,城市化對交通能源消耗造成的壓力尤為明顯。且相較于總體的能源消耗,城市化的空間形態對交通能源消耗具有更為直接的影響。理論界對這一問題有較多的研究和討論,但針對我國的實證檢驗卻十分有限。如何評估我國不同的城市化空間形態對居民交通能源消費的影響,從而選擇和規劃合理、有效的城市發展空間模式,是當前我國在實現可持續的城市化發展過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因此,本文將就這一問題展開研究。
二、城市規模及城市密度對居民交通能源消費的影響機制
綜合現有文獻,我們將城市人口密度和城市空間規模影響居民交通能源消費的作用途徑分別梳理如下:
(一)城市人口密度與交通能源消耗
Newman and Kenworthy于1989年發表的兩篇著作最早研究了上述問題。他們使用全世界主要大城市的樣本,檢驗人均汽油消費量與人口密度之間的關系,發現二者存在明顯的負相關關系,即城市密度的增加使人均汽油消費量顯著下降。在具有最高密度的城市里,小汽車的使用率低而公共交通的供給充足[2][3]。這一結論為城市人口密度與交通能源消耗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對此,有較多學者提出質疑。Gordon等(1989)認為美國近年來就業呈現逆中心化的趨勢,與原有的居住郊區化相配合,使郊區之間的通勤模式替代郊區與市中心之間的通勤模式,從而通勤時間和距離總體趨于下降[4]。由此可見,盡管人口的郊區化降低城市平均的人口密度,但并沒有提高居民的通勤需求,進而增加居民的交通能源消耗。這里的重要機制在于考量城市人口密度與交通能源消耗之間的關系時需結合具體的城市空間結構,即居住區與就業區的重疊或分離狀況。
Cervero and Murakami(2010)對370個美國城市的研究發現,城市密度的確降低人均通勤里程數,但其中的重要機制是提供低于平均的道路公里數、更多的自行車騎行道路和人行步道及社區內零售服務設施。也就是說,只有依賴上述這些條件,高密度城市才起到降低人均通勤里程數的作用[6]。
另外,由于人口密度高、擁堵現象嚴重、私家車出行的時間成本畸高,高密度地區停車空間有限或停車成本高昂,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私家車的使用,促使居民更多地使用公共交通系統或出租車。而公共交通的供給在高人口密度地區同樣是比較充分的,因此可實現居民交通方式的轉換、提高交通能源使用效率。
通過以上梳理,我們發現較高的城市人口密度可從根本上降低居民的日常通勤距離,同時通過提高私人汽車的使用成本和公共交通的供給,促進居民通勤方式的內部轉換。然而,如果綜合居民長短期交通出行之后的總消耗,高密度地區并不具有降低居民交通能源消耗方面的優勢。即使僅考慮短期效應,城市密度降低居民交通能源消耗的作用發揮也需嚴格的前提條件,在我國多數城市目前仍無法滿足。因此,我們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設:
假設1a:在城市人口高密度地區,私家車使用將減少,公共交通使用將增加。
假設1b:城市人口密度的提高將增加城市居民總的交通能源消耗。
(二)城市地理規模與交通能源消耗
ECOTEC(1993)的研究表明,隨著城市規模的減小,通勤的平均距離呈現上升[7]。Shim等(2006)對韓國城市的研究得到了相似的結論[8]。然而,這些研究均采用人口指標來度量城市規模。在土地財政的刺激下,我國當前的“土地城市化”問題嚴重,即一味強調城市土地邊界的擴張,但城市集約性較低。“就地城市化”和“城中村”等現象本質上也反映了這一問題[9]。地方政府往往首先強調擴大轄區面積,在此基礎上再考慮產業的導入。鑒于我國城市化的現實背景,本文主要從空間結構維度考察城市化問題,重點探究城市空間規模與居民交通能源需求之間的關系。
首先,從直觀感受上來看,城市地理范圍越大,居民日常的活動空間也越大,各類設施的空間布局更為稀疏,居民日常通勤的平均距離就越長,對交通能源的需求也就越大。特別是,在較大的城市空間規模與嚴重的職住分離現象兼具的情況下,長距離的日常通勤帶來嚴重的交通能源消耗問題。其次,公共交通的供給力度往往與城市人口規模或密度相關,與單純的城市空間范圍沒有明確的相關關系。進一步考慮到城市空間規模較大的地區,停車空間充足,使用私家車的成本較低。在空間規模大的城市中,公共交通對私人交通工具的替代作用弱于高密度城市。因此,我們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設:
假設2a:城市空間規模越大,居民的總體交通能源消耗越高。
假設2b:相對于高密度城市,大空間規模城市中公共交通對私家車的替代作用更小。
三、實證研究方案
(一)計量模型
本文需要檢驗的計量模型可表示為:
yit=α0+β1scaleit+β2densityit+β3householdcontrolsit+β4citycontrolsrt+εit
(1)
其中,i代表不同的家庭戶,t代表不同的年份,r代表i家庭所在的城市,被解釋變量y為城市居民家庭的各類交通費用支出,scale為城市規模,density為城市密度,householdcontrols為家庭層面的控制變量,citycontrols為城市層面的控制變量,εit為假定服從獨立同分布的誤差項。
(二)指標選取
1.被解釋變量
鄭思齊等(2010)在對北京的調查研究中發現,公共交通工具滿足了31.4%家庭的通勤需求,32%的家庭選擇私家車完成日常通勤,26.6%的居民選擇自行車和步行等出行方式,9%的居民選擇出租車或單位班車完成日常通勤[10]。由此可見,乘坐私家車已成為我國大城市居民日常通勤的主要方式。但相較于歐美發達國家,我國居民對私家車的總體依賴程度更低、出行方式更加多樣化。結合學者們指出的城市空間結構對居民交通消費的長短期綜合影響,本文在私家車的基礎上進一步考慮居民家庭的總體交通費用支出,分析公共交通費用在日常交通費用中的占比,從而檢驗城市空間特征的相對能源效率。因此,本研究將主要使用以下三個被解釋變量,分別是:
(1)交通能源費支出。該指標對應《中國城鎮住戶調查數據》中的第F5121項,包括汽油、柴油、機油、電瓶及電瓶充電費。由于城鎮家庭使用柴油的情況較少,家用電瓶充電費金額也相對較小,因此將F5121項數據作為私家車的汽油費支出,從而度量城鎮居民家庭交通出行中私家車的使用情況。
(2)總交通費用支出。與西方國家不同,我國城鎮居民的出行方式更加多元,對私家車的依賴程度相對較低。因此,在F5121的基礎上加入居民的交通費支出額(F5144),得到居民家庭包括日常和非日常通勤在內的總交通費用。F5144指家庭成員乘坐各種交通工具支付的交通費,包括飛機、火車、長途汽車、市內公共交通及出租車等。因此,上述兩項數據合并基本涵蓋了城鎮居民需支付成本的所有交通出行需求。
(3)市內公共交通費用支出在日常通勤支出中的占比。我們將居民需支付費用的日常通勤方式歸納為私家車、公共交通工具和出租車三類,居民家庭的公共交通費支出(F5144)除以上述三項費用的總和(F5121+F5144+F5145)得到日常通勤方式中公共交通的占比。公共交通費支出項F5144是指家庭成員乘坐市內交通工具出行的車票費(如公共汽車、地鐵等)。
2.解釋變量
(1)城市密度。對城市密度的度量指標較多,本文使用各市的城區人口/市轄區建成區面積來反映城市密度的變化情況,以《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中“城區人口”來體現城市人口規模。該指標是指劃定的城區(縣城)范圍的人口數,統計中估算的是市區范圍內的人口數量,而不是整個地級行政單位的人口,從而能更好地與分母的面積單位相匹配,以較準確地度量城市人口密度。
(2)城市規模。本文使用市轄區建成區面積予以度量,建成區范圍一般是指建成區外輪廓所能包括的地區,即該城市實際建設用地所達的范圍。從數據來看,研究時間段內各地級市市轄區建成區的面積在不斷增加,體現了城市化進程中城市規模的變化。
3.控制變量
顯然,除城市空間形態外,影響家庭交通能源消費支出的因素還有很多,這里主要考慮以下的家庭層面控制變量:家庭收入對家庭能源消費總量和結構的影響顯著,高收入家庭往往使用較多的能源,而低收入者的能源消耗較少;家庭規模同樣具有明顯的影響,因為被解釋變量均是以家庭為單位的交通費用支出,在通常情況下,家庭規模越大,其交通費用支出也越大。
同時,地區層面的控制變量主要體現地區差異對居民交通費用支出的影響,這里主要考慮地區的名義GDP水平。可以預期的是,地區的GDP水平越高,公共交通的建設更完備、供給更充分。同時,通過引入地區的名義GDP水平,部分控制地區間物價水平的差異及同一地區不同年份之間的物價變化。
(三)數據來源
實證檢驗使用的主體數據來自2002~2009年《中國城鎮住戶調查數據》(UHS,Urban Household Survey)。它是現有最完整的全國范圍的微觀變量數據,主要用于研究教育回報率、收入不平等、家庭消費和家庭金融等問題。該數據集是追蹤數據并采用面訪的方式獲取,因而數據的真實性相對較高。
需要指出的是,該數據集存在樣本輪換的問題,即一相樣本調查每三年進行一次,為二相樣本提供抽樣框。調查城鎮中的經常性調查戶每年輪換1/2,兩年之內輪換掉所有調查戶。基于這一特征,我們不能使用標準的面板數據,而需將不同年份針對不同家庭的調查數據組合成一個較大的橫截面進行回歸。
城市層面的相關數據來自相應年份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通過每個地級城市唯一的地區代碼,將居民數據與城市數據進行匹配,從而得到完整的研究數據集。回歸中涉及的變量統計性描述見表1所示。

表1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研究結果及分析
(一)總體回歸結果
本文使用Stata13.0軟件對數據進行橫截面回歸。在控制時間固定效應和省份固定效應后,基本的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回歸結果
注:括號中是t值;*表示p<0.10,** 表示p<0.05,*** 表示p<0.01。下表同此。
從表2的結果來看,城市的建成區面積越大,居民私家車使用越多,居民家庭的總交通費用支出更高,居民使用公共交通方式在日常通勤中所占的比重也越高。這與我們的理論預期相符,因此假設2a得到驗證。也就是說,在居民的日常通勤中,盡管城市規模越大,居民私家車的使用量和公共交通費用支出都更大,但城市規模使日常通勤中公共交通支出的比重上升,這從城市規模對各項交通出行方式的作用參數絕對值大小上可觀察得到。
城市人口密度顯著降低居民的私家車使用量,這與已有文獻的研究結論一致。由于人口高密度地區的停車空間有限、費用高昂且堵車情況嚴重,降低了居民使用私家車出行的意愿。與此同時,城市密度降低私家車的使用,增加公共交通費用支出,使日常通勤中公共交通的比重顯著提高,因此假設1a得到驗證。由于城市密度的提高,居民家庭不僅使用公共交通替代私家車,也以出租車來替代私家車,因此城市密度對公共交通占比的提升程度略低于城市規模的作用,因此假設2b沒有得到驗證。最后,高城市密度的確使居民的總交通費用支出增加,因此假設1b得到驗證。
比較城市規模和城市密度的回歸結果,發現高密度城市中其他日常通勤方式對私家車的替代效應更為明顯。但由于存在出租車對私家車的替代,從日常通勤能源節約的角度而言,城市密度的作用甚至小于城市規模的作用,且城市密度并沒有顯著降低居民的總交通能源消耗。現有文獻指出城市密度降低居民交通需求的一個主要原因在于居民的工作與生活地點較近,從而不會產生大量的日常通勤需求。然而,反觀我國人口密度高的城市,通常都出現居住地與工作地相分離的狀態。潘海嘯(2010)在對上海的研究中指出,上海在新城建設中工業園區缺少配套的居住區,導致新城和產業園區的就業人口與居住地點分離,造成居民的長距離出行[11]。柴彥威等(2011)的研究認為中國大城市的居住與就業空間關系發生明顯變化,職住分離現象逐漸凸顯,而住房市場的改革和大城市商品房價格的攀升是形成這一格局的重要因素[12]。鄭思齊等(2007)認為與西方國家的城市相比,中國大部分城市就業集聚度高,偏向于單中心狀態,而居住郊區化則逐漸明顯,由于中心地區的高房價,中低收入居民在顧及房價的同時只能忍受不相稱的高額通勤成本[13]。在此基礎上,如果考慮Nss等學者提到的高密度城市居民有更高的非日常長途出行需求,那么城市密度必然顯著增加居民家庭的總交通費用支出。
在控制變量方面,家庭收入水平使私家車使用量和總交通費用均上升,但降低了居民家庭在日常通勤中的公交使用比例,這一結果較為合理。家庭規模越大,居民家庭的公共交通支出越大,這是由于公共交通是按人頭收費的,家庭規模直接影響其公共交通費用支出。與此同時,家庭規模越大,私家車的燃料費和出租車費等支出更少,因而人口規模較大的家庭在日常通勤中公交費用支出占比更高。地區的GDP水平越高,該地區居民家庭的私家車燃料費和公共交通費等支出也越高,因此地區GDP對居民日常通勤中公共交通所占比重不產生顯著影響,這也與我國城市發展的現狀相符。
在此基礎上,內生性是本文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由于家庭層面的樣本更新替換速度較快且沒辦法識別固定的個體家庭,因此以各城市每個家庭的平均能源消耗量為被解釋變量,采用廣義矩估計方法對模型進行內生性檢驗。目前,廣泛接受的對實證內生性問題的解決方法主要有兩類:一是工具變量;二是系統廣義矩估計法(SYS-GMM)。本文樣本是典型的大橫截面、小時間跨度的面板數據,比較符合SYS-GMM要求的數據特征,相關的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從表3的回歸結果來看,AR(1)和AR(2)的值表明差分后的殘差只存在一階自相關、不存在二階自相關,即模型中不存在序列自相關問題,這符合SYS-GMM估計方法的假設條件。薩根(Sargan)檢驗的P值較大,說明SYS-GMM估計中的工具變量不存在過度識別問題,所選用的工具變量正確。總體來說,SYS-GMM模型對內生性問題的控制是有效的。同時,主要解釋變量的系數與基本回歸一致,考慮內生性后模型的符號并沒有發生變化,因此模型較為穩健。
(二)分地區的回歸結果
已有研究認為城市化對能源消費的影響在我國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據此,在總體回歸的基礎上,我們將所有樣本劃分為東中西部地區并分三組分別回歸,結果如表4~6所示。
分地區的回歸結果顯示,在東、中部地區,城市規模增加各項交通費用支出,且相對更多地增加公共交通費用支出,使日常通勤中公共交通支出比例隨著城市規模的增加而增加。有趣的是,西部地區城市規模進一步擴大將減少居民的總交通費用支出,這可能與另一個結果高度相關,即西部地區城市規模擴大對公共交通占比的提升程度在三個地區中是最大的,公共交通的單位花銷最小,因而顯著降低居民的總交通費用。人口密度在三個地區均表現為減少私家車的使用,增加居民家庭的總交通費用,并提高日常出行中公共交通的比例。其中,西部地區城市密度對公共交通支出絕對量及占比的拉升作用最明顯,東部地區城市密度的提升在增加居民公共交通支出的同時以更大的程度增加出租車費支出,因此東部地區城市密度對公共交通占比的拉升程度弱于西部地區。

表4 東部地區的回歸結果

表5 中部地區的回歸結果

表6 西部地區的回歸結果
家庭收入水平在不同地區形成的影響也是一致的,即增加各項交通費用支出,顯著減少居民家庭出行中乘坐公共交通的比重。家庭規模在東部地區對家庭總交通費用支出不產生影響,但顯著減少中、西部家庭的總交通費用支出。
中部地區城市GDP水平的提高,對私家車的使用具有最為強烈的刺激作用。西部地區總體上經濟欠發達,區域內部經濟較發達的地區也沒有條件廣泛使用私家車。東部地區私家車的普及程度本已處于高位,隨著GDP的繼續上升,進一步推動私家車購買和使用的作用并不大。而中部地區不僅有相應的經濟實力購買私家車,同時其使用成本相對低廉。在三個地區中,唯有中部地區的城市GDP水平對公共交通費用支出不產生顯著影響,這可能是由于中部地區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或公共交通供給在國家層面處于相對穩定階段導致的。因此,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而言,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盡管私家車使用多,但公共交通網絡發達,居民對公共交通的使用頻繁;全國經濟最不發達的地區,區域經濟的發展還不足以對私家車的使用產生促進作用;而全國經濟處于中等發展水平的地區,區域經濟的發展大幅度提升了私家車的使用,但公共交通網絡的建設力度又低于東部地區,這些地區對私家車的使用相對而言可能是全國最高的。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使用《中國城鎮住戶調查》的微觀數據,將城市化空間發展模式的兩個維度——城市空間規模和城市人口密度放在同一個框架中考察,發現城市規模的擴大將增加居民家庭私家車的燃料費支出,而城市密度則降低私家車燃料費支出,城市規模和城市密度的提高都增加居民的總交通費用支出,高密度城市中其他交通方式對私家車的替代效應更為明顯,但由于高密度地區同時存在出租車對私家車的替代,因此城市密度并沒有大比例提高居民日常通勤中公共交通的占比。總體來看,城市密度對居民交通能源消費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日常通勤方式內部結構的調整,但并沒有降低居民的總交通費用。這一現象可能是由于高密度地區居民進行更長距離的假期出行,高密度城市的中心區房價過高及城市規劃中缺乏產業區周邊的居住地塊配套,導致嚴重的職住分離現象。
分區域結果中較為明顯的差異在于東、中部地區城市規模進一步擴大將增加居民的總交通費用,而西部地區則相反。由于西部地區城市規模擴大對公共交通占比的提升程度最大,而公共交通的單位花費最少,有效地降低了居民家庭的交通費支出。對居民私家車的使用沒有產生有效的刺激,但這一刺激作用在東、中部地區十分明顯。東、中部經濟發達地區居民使用公共交通的比重更高,而西部地區的經濟發達程度對居民公共交通使用比例不產生顯著影響。
城市化過程中的空間模式選擇是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議題。“攤大餅”式的城市化發展模式由于嚴重損害城市集聚效應的發揮而廣受詬病。結合本文的研究結果,一味攤大餅式的擴張城市規模并不利于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與建設可持續發展城市的目標相悖。更進一步,理論界和政策界都推崇通過提高城市密度發揮城市集聚效應。然而,在交通能源消費方面,這一效應的發揮需具備一定的前提條件,即城市的空間規劃應避免嚴重的職住分離,從源頭上降低日常通勤需求。因此,在城市空間規劃中需形成多個就業中心,在各就業中心附近規劃相應的居住用地及教育、醫療和生活娛樂等配套設施,在增加城市密度的同時有效降低居民的日常通勤距離,真正實現城市集聚經濟。
——以防城港市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