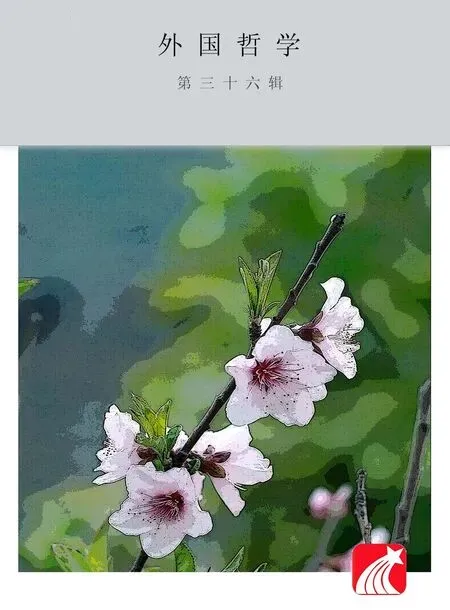哲學中的對話
——與戴卡琳教授商榷
何狄穆(Tim Heysse) 著
張楠、張堯程** 譯
在《歐洲大學中的“中國哲學”:三種面向的“無”托邦》一文中,戴卡琳教授批評歐洲大學在制度上對于中國及其他“非西方”地區系統性地排擠。在文中,她以魯汶大學的歷史學系和哲學學院(我本人很榮幸地就在這所學院中工作)為例,來佐證她的發現。我的能力大概并不足以回應戴卡琳所提出的諸多重要問題。我正好處于Schwitzgebel 所說的“惡性循環”當中—既對非西方哲學一無所知,又缺乏相應的語言能力。因此,關于非西方文獻的討論,我確實無法從哲學專業的角度加以評析。然而,在戴卡琳教授的文章中我還是找到了可以回應的部分。戴卡琳在她文章的結尾提出了若干建議;這些建議牽涉到更大的議題,其中包括哲學與政治的關系。因此,除了簡要回應一些魯汶大學哲學院在學制設置上的細節問題,我在本文中主要想質疑戴卡琳在哲學、政治關系上抱持的觀點①這并不意味戴卡琳教授在媒體上試圖揭露此問題時所遭遇的封鎖就是對的。參見戴卡琳教授在她《歐洲大學中的“中國哲學”:三種面向的“無”托邦》文中1.2“未成為討論對象的研究場所‘歐洲’”部分以及該文第16 條尾注(見本書第81 頁注釋①)所提到的。,并試著將討論引向一個用來支持中國哲學或其他非西方哲學的可能更有道理的論述。
戴卡琳教授在她文章中所不滿的是,以地區、語言為導向的“非西方”研究,以及人文、社科領域的學科專業之間存在著一道藩籬,歐洲大學學制在這兩者之間設下了一條太深的鴻溝。為了刻畫這個學制上的藩籬,她舉魯汶大學歷史學系的現況為例。確實,那些研究非西方文獻的學者,會因為學術體制的劃分而在學科領域的夾縫之間生存不易(特別是在尋求研究資助、出版著作以及在權威期刊上發表文章的時候)。不過,戴卡琳的主要關切點還是在教育方面。在現有學制下,那些對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或歷史感興趣的學生,大可以在欠缺中文能力的情況下(例如進入歷史系學習),或欠缺相應研究方法的情形下(例如進入漢語系學習),依然完成學業。
我無法斷定這樣的藩籬是否真實存在,雖然我也沒有什么理由去支持這份質疑。不過,我認為,對于以三年為期的本科學制而言,要求學生去掌握那些研讀非西方文獻時所需的語言能力和背景知識,實在是有些強人所難。畢竟,魯汶大學在各領域都設有所謂的“銜接學程”①例如,可以參見http://www.kuleuven.be/toekomstigestudenten/publicaties/.html (2016年11月26日訪問)。;獲有中文學士或日文學士等學位的學生可借此直接就讀政治科學的碩士學位課,而不用另外取得相關的學士學位。或例如在哲學系,已經有其他學士學位的學生亦可以再花一年的時間取得哲學學士學位。
戴卡琳教授主要關切的是例如魯汶大學哲學院這樣的哲學院系的現況。她在此一問題上深刻又銳利的評論確實無可辯駁。雖然魯汶大學的哲學學院開設了非西方哲學方面的選修課程,但是這里的學生確實亦可在不研習這些課程的情況下順利畢業。而這里的碩士生雖然也可以選擇非西方哲學的題目來撰寫畢業論文,但她們很大程度上就只能仰賴自己,因為魯汶大學缺乏相應的師資,來指導這類論文的寫作。
然而,哲學院也正開始朝著戴卡琳教授建議的方向有所改進。有鑒于研究非西方哲學的人員僅占教研人員委任總數的一小部分,例如將1/10 聘雇一名教授的經費用在阿拉伯哲學研究上,我院開始修正一些可能有誤導性的措辭。例如我們在院系網站上將自己營銷成一個“全面性”的哲學學系,涵蓋“哲學研究中的各類領域”。這一點被戴卡琳精心挑出并被批評為名不副實。雖然我們原先想表達的僅僅只是學生可以在魯汶大學哲學院內同時學習到分析哲學和歐陸哲學;但是這樣的表述確實有可能誤導讀者,仿佛我們學院把非西方的思想都排除在“哲學”的定義之外。所以,我院在2016年的“教學目標要點”中明確承認我院提供的教學內容僅限于西方哲學,同時并不否認非西方哲學的存在和重要性。①參見https://www.kuleuven.be/onderwijs/cobra/portaal/2015/nl/visies/facultaire- onderwijsvisie-enbeleidsplan-hoger.pdf (2016年11月26日訪問)。
對于非西方哲學的支持者們而言,這些措辭上的改變顯得太微不足道,來得又太遲。在他們看來,我在第一段中所坦承的對非西方思想及語言的無知,恰恰反映了哲學院中教研人員的典型情況。就事實而論,他們是對的。但是,我對此還有兩點補充。首先,我絕不認為那些我不知道的事物就不值得去了解。例如,我很希望能夠對戴卡琳教授在她文中列舉的那一長串中國哲學家有進一步的了解(“下列先賢或著作在哲學院一律無人問津:他們之中包括孔子、墨子、孟子……”)—誠然,我們不應該在定義“哲學”一詞時,把這些人排除在外。其次,我希望自己能知道的東西不計其數,但我們不可能了解一切事物。每一個從事哲學、歷史學或其他人文學科研究的人都應該會坦承自己某方面的無知:或者是對那些值得了解的材料一無所知,或者是沒有時間讀遍那些值得研究的書籍或畫作;如是種種,不一而足。因此,我對于非西方哲學及其語言的無知雖是難辭其咎,卻也是不可避免。
然而,對于戴卡琳教授而言,哲學系的情況卻是在另一個意義上難辭其咎:非西方哲學在歐洲大學哲學院系中遭受到的悲慘境遇起于不公正的排擠和不理性的抵制。在發覺理性論辯“純屬徒勞”之后,在我看來,戴卡琳不再期望能在這個議題上進行理性討論。這一點在她文章的發展上也看得出來。在她文章的開端部分(1.1 節),戴卡琳列舉出支持中國哲學的七種論述。而到了文章結尾,她的要求只剩下政治方面的論述—多元價值的維護、對于“他者”的尊重,以及中國與印度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哲學性或思辨性的論述都被棄之不顧。因此,在她結尾部分的建言中,戴卡琳呼吁政治性的干預,希望透過政治力量的介入來促使哲學學院“接納非西方思想”。
透過呼吁政治干預并將討論停留在政治層面上,戴卡琳教授凸顯了一個常被哲學家忽略的張力,這個張力恰恰體現在組成我院名稱的兩個字眼之上:“學院”和“哲學”。①學院的全名譯為“哲學高等研究院”,它在原先作為該學院教學語言的法語中被稱作“Institut Supérieur de”。作為一個教育機構,魯汶哲學學院是公民教育系統的一環,而這個教育系統是公共于全體公民的。這意味著,用以維持該系統運作的資金幾乎都來自弗蘭德斯地區政府稅收。因此,無論是哲學學院自身,還是其所提供的教育,都不可避免帶有政治考慮。此外,考慮到弗蘭德斯當地的政府是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這個政府有權強制推行一些經民意一致通過的政治舉措。戴卡琳教授的一些建議,包括強制我院雇傭特定員工或開設某些課程,就屬于此列。
作為一個認同民主價值的公民以及一個自由民主國家中的公職人員,我必須接受哲學學院在大的原則上應配合政府政策。但同時,作為一個有幸獲取教職的哲學學者,我又不得不反對政治力量過分介入哲學研究。雖然政府大部分的政治作為在哲學上都饒富趣味,但哲學議題或哲學文獻的重要性卻不該由國家政策單方面決定。作為一個哲學家,我深信并捍衛哲學的獨立性。
不過,我們應該謹慎一點,不要用那種傳統的論調來看待獨立性的概念。傳統的論調認為哲學之所以獨立于政治權力,乃是由于哲學只為普遍的理性發聲。在戴卡琳教授看來,持有這種觀點的正是她的一些反對者;這些人聲稱自己“擁有開放的心靈”,從事著“不分地域”的研究工作“并致力于突破局限”。戴卡琳正確地對如下一點做出質疑:既然這些人把哲學理解為一個追求普遍知識的事業,那么他們又有什么理由把非西方哲學從哲學領域中排除出去?
這種老掉牙的論調并不是我所理解的哲學。我認為,哲學的歷史實際上并不全然是一個理性而開放的過程:它部分地受“操作學術體制而閉門自守”影響,也受到那些決定眾人研究走向的“主流的學科典范、福柯所謂的‘真理政權’(regime of truth)以及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謂的‘象征暴力’(symbolic violence)”影響。此外,這一過程中也有民族中心主義的一面。盡管哲學總是試圖與掌控國家與公共討論的人保持一定距離,并時不時地在這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西方哲學畢竟是歐洲歷史的一部分,其中當然也包括長達數世紀之久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
我無意為上面描繪的哲學形象進行辯護,但即便如此,我仍然認為哲學唯有在某種形式的獨立性之上才能夠獲得價值。這種獨立性正是米歇爾·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所闡述的對話的獨立性①參見Michael Oakeshott, “The Study of ‘Politics’ in a University: An Essay in ppropriateness”和“The Voice of Poetry in the Conversation of Mankind”, in Michael Oakeshott,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new and expanded edition,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91。。根據奧克肖特的觀點,對話是多種聲音的交匯之處;在其中,不同的聲音與話語“相互承認”。②Michael Oakeshott, “The Voice of Poetry in the Conversation of Mankind”, in Michael Oakeshott,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new and expanded edition, p.198.誠然,奧克肖特認為人類文明中的對話是由一些反映人類活動的基本話語所組成:這些基本的話語類型包括社會實踐、科學、詩歌及歷史。但我認為組成人類對話的話語類型不止以上四項。人類文明中的對話也不止一種模式,不同模式的對話不間斷地在各個地方同時發生。如此一來,“對話”一詞除了可以用來描述人類文明的整體歷史,同時也可以描繪那些整體歷史底下更為具體的個別歷史,例如藝術史、文學史或哲學史,甚至是某個特定地區的哲學史。一旦“不同話語的特殊之處”失去了它的多樣性,這樣的對話恐怕都將不復存在。哲學作為一種對話,也必須包含各種不同的聲音才得以成立(戴卡琳教授所刻畫的“典型西方”“部分西方”“非西方”之間的不同也是其中一種多元性)。
而在一場對話之中,每一個參與者也都有他“適合發聲的時機”。曾經在上一場對話中成功的(例如妙語如珠地轉變話題、鞭辟入里的分析或雷厲風行的批評),在下一場對話中或許不再有同樣的效果。在對話中,一個特殊的話語之所以“有道理”,正是因為這個話語應時而發,并開啟了特定的對話方向。①Michael Oakeshott, “The Voice of Poetry in the Conversation of Mankind”, in Michael Oakeshott,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new and expanded edition, p.198.時機的適切與否,便構成了“對話的規范性”;一時適當的表述,以后可能不再適當。然而,此一規范性亦尊重不同的聲音。這種規范性“不要求也不認為一種聲音會吞沒另一種聲音”;它也不認為在對話中只能有單一的目標(例如發現真理、證明某一結論等)或單一的標準:
不存在主持人,亦沒有仲裁者,更沒有誰會去把關你發言的資格。每位參與者的價值皆由他們具體的表現而定。只要能在思緒的湍水中一同流動,任何話語都能夠被接受。各類聲音不分貴賤,高低無別。②Ibid.
為了理解哲學在政治之外的獨立性,我們必須首先了解對話的規范性。首先,奧克肖特雖然說各類聲音無貴賤之分,都有發言的資格,但這并不意味任何人都可以參與到對話之中。大多數的對話都是由“特定圈子內的成員”所進行(例如,太太們在茶會上對話時,負責倒茶的男仆并不能參與其中)。再者,一個對話的成功與否只取決于對話中的內在因素。它的成功仰賴于那些在對話中能夠引起他人興趣并進而獲得接受的修辭性力量。正是言語所能喚起的他人的興趣,使得對話的發生得以可能,進而左右對話的走向。對話的規范性與修辭的作用緊密相關,它其實是一種與興趣相關的規范性。
正是這個與興趣相關的規范性確保了對話得以獨立于權力之外。無論多么大的政治權力,也無法貿然介入對話之中,在它身上強加話題,甚或決定對話的走向。權力能做到的只不過是中斷對話或帶來尷尬的沉默。當然,把哲學的發展史視作一場對話,并不是要否認哲學的政治性,以及它在閉門自守、制度性排斥以及其他權力機制下所受到的影響。這個觀點所要強調的是:一個主題唯有通過成功引起哲學家們的興趣才能真正參與到哲學對話之中。話題、想法或論述也只有當它們在哲學中找到聽眾時才能真正開啟與他人的對話。這個緩慢的過程有時需要一兩個世代的時間,其中也不乏對異己觀點的排斥和打壓。即使在理想的情況中每個人都能參與到對話,也不可能每個人都能夠談他們感興趣的話題或是把對話引導到他們喜歡的方向。因此,基于政治現實或社會倫理的考慮,我們固然可以動用政治權力強迫一個哲學院系接納中國哲學。但是這樣的強加卻依然無法讓中國哲學憑借自身真正地進入到哲學當前的對話之中。
堅持哲學作為一種對話的獨立性,并不必然地與戴卡琳教授的建議產生沖突:雇用非西方研究的專家,以及開設非西方哲學方面的必修課不必然會威脅到哲學的獨立性。因此讓人驚異的是,像她對中國哲學這么了解的專家,竟會在論證中有這么明顯的疏失;除了政治層面的論述之外,戴卡琳甚少展開哲學層面的論述。她在哲學層面所提到的論述只是寬泛地提到非西方思想與文獻有其毋庸置疑的價值,與陌生思想(“他者”)的接觸十分有益,有助于我們發現自身文化中所固有的預設并促使我們反思自己。①研習非西方哲學,是獲得這類反思的最好方式嗎?一門嚴苛的形式邏輯課程肯定可以迫使哲學系新生“脫離舒適圈”。我們不應該不假思索地認為只有在接觸異域思想的時候才能對自己原先的信念產生懷疑和反思。
支持非西方哲學的一方需要產出更具體的論述來激起哲學家們對它們的興趣。我們現在確實也已經有了這樣的論述。以最近的兩項研究為例,Richard Kim 展示了當代道德心理學是如何與當下的早期儒學研究相互影響的。②Richard Kim, “Early Confucianism and Contemporary Moral Psychology”, Philosophy Compass, 11(9),2016, p.474.Polycarp Ikuenobe 則透過非洲思想的視角,提出了一個更加強調社群共同體與責任而非個人權利的“尊嚴”概念。①Polycarp A.Ikuenobe, “The Communal Basis for Moral Dignity: An African Perspective”, Philosophical Papers, 45(3), 2016.另可參見David B.Wong,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Status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U.S.Graduate Programs”, APA Newsletter on Asian and Asian-American Philosophers and Philosophies,15(2), 2016, pp.9-10。
誠然,對當今的哲學家而言,有很多話題是他們不太明白該如何去討論的。然而,只要能夠推動原地踏步已久的對話再一次前行,不僅新穎的觀點、概念、見解和論述可以獲得討論的空間,甚至那些舊的觀點、概念、見解和論述也不會再被輕易忽視。但為了促成這一結果,這些新舊觀點需要在哲學界捕獲自己的聽眾,將對話再一次地引導至新方向。一旦達成了這一點,并且非西方思想也能夠證明它確實保有能豐富哲學對話的可能,那么自然會有越來越多的學生想要去學習非西方思想,以及研究這些思想所需的語言技巧和專業知識。這個時候,哲學教授們個人的研究興趣便已是無足輕重。這個時候,學院一定會添加關于非西方思想的課程,但這并不是政治力量的介入所致,乃是因為哲學的對話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