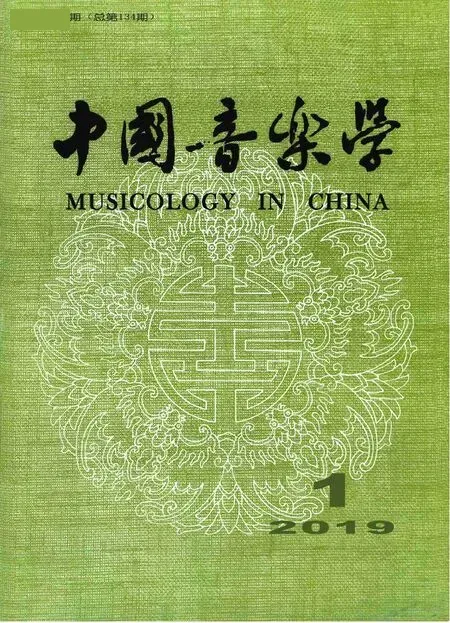中國音樂表演理論話語體系的整體架構
□項 陽
一、關于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
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與中國音樂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在2017年主辦了“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學術研討會”,旨在對傳統音樂文化整體意義進行有效梳理。會議由浙江師范大學音樂學院承辦。參加研討會的有來自中國音樂史學會、中國傳統音樂學會、音樂批評學會、樂府學會、西方音樂學會、中國樂律學會、中國旋律學會、音樂教育學會、東亞樂律學會等十多個學會的學者。大家意識到系統梳理中國傳統音樂理論話語的時機已經成熟,從不同視角思考相關問題,高質量學術論文引起各學術刊物和相關學術媒體的關注,據不完全統計,發表在《中國音樂學》《音樂研究》《音樂藝術》等多種期刊上的論文有十數篇,《中國社會科學報》和《中國文化報》既對會議集中報道也辟版面刊發會議論文精煉版,會議文集也正在出版中;2018年,音樂學界多個學術研討會設置了與“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相關議題,學術思考走向深入。
音樂理論話語體系,應考量傳統音樂文化所涉及的不同領域,以顯整體意義。諸如音樂本體之律調譜器、音樂表演各個門類、音樂創作、音樂體裁及其演化、音樂功能屬性、音樂與社會、音樂教育、音樂機構、音樂觀念、音樂審美與文化心理、音樂制度、音樂交流、音樂術語、多族群音樂形態各自存在及對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貢獻、社會發展對音樂文化的影響與制約關系、音樂學研究方法等。而全方位研討,則要調動或稱整合音樂學各界、相關領域乃至跨學科的研究力量,在對所涉學術論域整體把握下分類考辨,整合起來定會對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形成系統性認知。分類探討須建立整體性理念、系統性認知,否則就事論事難現整體。建立中國傳統音樂理論話語體系,要挖掘其深層內涵,認知某一門類在何時產生,在演進過程中有怎樣的發展,某個時代、具體事件、某個族群和個人、某種形態對于體系的創造性貢獻、豐富性意義和重要影響。建立體系觀念、圍繞體系考量,對理論話語體系的有效梳理,使中國音樂文化的創承和研究群體在明了傳統內涵、或稱厘清發展脈絡的前提下明確研究的自身意義。
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非一朝一夕所成,是這個區域人群在有文化認同前提下創造出以音聲為主導的技藝形態、在發展過程中固化理念、豐富裂變、代繼薪傳,后人有依循并不斷前行而形成具有厚重內涵的系統性存在。體系縱橫交錯,我們研究的對象是中國傳統音樂文化,要從國家意義之邏輯起點進行綜合考量。國家為有制度制約的政體,音樂文化有制度保障或支撐,涉及與音樂形態相關的方方面面。換言之,應既把握音樂形態自身,又考量形成音樂形態的機制;以國家為首要認知前提,會看到作為民族、區域(涵蓋地理)等對國家音樂文化整體一致性下區域豐富性影響;國家用樂在類分前提下的互動意義;明確前提應看類分為脈的發展演化,國家對其發展提供了怎樣的保障,區域人群對其有怎樣的支撐和影響,群體與個體對其發展演化有怎樣的貢獻;哪些形態在哪些階段創造產生,其后怎樣因循前行;哪些階段融進“外來”因素,這些因素怎樣融入傳統;早期理念在發展過程中的變化,與初義是否相通、相同、甚至相異,都需整體把握。所謂體系,應是立坐標,明確各自門類、各參與群體創造出的諸種形態在坐標系中的意義和作用。
中國傳統音樂文化體系應從大樂學概念認定,把握國家制度下用樂涉及哪些層面。在周代,國家理念下樂為“六藝”之一種——“禮、樂、射、御、書、數”,按當下理解屬學科門類。樂作為以音聲為主導的藝術形態,本歌舞樂三位一體,在發展過程中或裂變獨立、或隨時代前行以具豐富性,所有后發都在此基礎上展開。圍繞藝術形態以行認知,便是樂學整體意義。周人之《樂記》23篇,可認定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的邏輯起點,由此把握發展演化路徑中豐富性。
《樂記》存11篇,但產生之時輯錄有23篇,是周代“立學”時對樂的把握。漢儒輯錄,“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漢書·藝文志》)反映出時人的樂學觀念。《樂記》之“樂本”“樂言”“說律”“樂器”當指樂本體構成,“樂作”應為樂之創制,“奏樂”“師乙”主論樂之表演,其余篇章彰顯樂的功能性意義及形而上認知,涵蓋當下所謂音樂美學、音樂社會學、音樂心理學、音樂教育學、音樂哲學、音樂評論等論域。《樂記》屬《禮記》有機構成,可見禮樂和俗樂兩條主脈,首先是“其本一也”,并有“古樂”與“新樂”之論,《樂記》之學為后世傳統樂學之發展設置了整體視角,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的整體意義,把握兩脈可顯與時俱進。在制度相對完備基礎上呈國家用樂邏輯起點,為“中國樂學”體系意義。不考慮邏輯起點,則顯迷失,以西方、或稱歐洲專業音樂理念為本,或稱以此為主導,難以看清中國傳統音樂自身發展脈絡。把握西方傳入之理念與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關系,融入中國傳統之后的發展演化十分必要。
二、禮樂形態之音樂表演理論話語
音樂表演理論話語,是傳統樂學體系的有機構成,是樂人對樂之本體所成形態的技藝展示、展現。樂為音聲技藝為主導的藝術形態,當有了國家意義上禮樂與俗樂類分,國家重儀式為用的禮樂,如此有非儀式為用的俗樂與之對應,形成禮與俗兩條用樂的主導脈絡。官書正史重禮樂的記錄和闡釋,野史稗編和文人筆記等更多對俗樂把握。儀式和非儀式為用,其“表演”既相通又有較大差異,這體現在表演風格和技巧運用,創作理念、作品詮釋乃至審美和心理感受等諸多層面。
樂之儀式為用更需規范“表演”,以現藝術感染力和震撼力,如此孔夫子在齊國聞《韶》大發感慨:“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韶樂》在周屬六樂之一種,“國之大事”中用于四望之祭,孔子在魯國亦參與該種祀典,但卻不似在齊國感受如此深刻,儀式結束后還沉浸其間,以致“三月不知肉味”,說明齊國有司訓練有方,其樂師和樂工將《韶樂》詮釋到應有的高度,凸顯禮樂震撼力。社會中人們有情感的儀式性訴求且以禮樂表達。禮樂首重祭祀——吉禮為用,繼而拓展至嘉、軍、賓、兇多種類型,以展現人們敬畏、虔誠、歡抃、哀緬、威武等豐富的儀式性情感訴求,每一種訴求為用自當與情感內涵相合,并制造相應的儀式氛圍,“樂由中出,禮自外作”。這儀式用樂其樂語具指向性,與儀式諸儀程相須為用,為群體性、固化形態,表演者無需刻意展示自我,卻要保證整體性用樂形態的技巧、技能,創造出相應儀式氛圍,從創作、表演、與儀式關聯系統性把握,深層認知中華民族用樂傳統中作為禮樂一脈的內涵。
禮樂的樂制分雅樂類型和非雅樂類型。歷史地看,這兩種類型都具歌舞樂三位一體樣態,周人對樂整體把握其后出現分化。雅樂類型這歌舞樂三位一體一直存在,非雅樂類型在發展過程中呈現帶演唱的形態和純器樂形態。對于雅樂類型,歷朝歷代必有舞在其間,六樂如此,后世亦然,所謂“佾舞”等級為用。周代佾舞,王、侯、卿大夫、士四級擁有,文獻顯示,漢魏以降國家保留了最高禮制儀式為用的八佾和王侯等級的六佾,禮部治下太常在太樂中為用的雅樂和唐宋以降各級地方官府為用同為雅樂類型的《文廟祭禮樂》,舞不可或闕。樂本體由于缺失樂譜和舞譜難以把握,但有樂譜和舞譜未創制節奏與時值符號亦難準確認知,有了節奏與時值符號系統后更能顯現雅樂本來樣貌。對雅樂應有相對細膩的辨析,這畢竟是中華禮樂文明傳統的寶貴財富,何況雅樂當下亦有活態傳承。我們應認真探究兩百年前由瀏陽人士邱之稑在《丁祭禮樂備考》中記錄的《文廟祭禮樂》樂譜、舞譜以及活態傳承意義。20世紀50年代楊蔭瀏先生率領的團隊對瀏陽文廟所傳《文廟祭禮樂》活態進行了嚴格記錄(當下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國家雅樂一支的地方性存在,應重視其歷史和現實意義。結合歷史文獻,諸如歷代官書正史、《太常續考》、《叛宮禮樂疏》等更能顯現雅樂一脈的整體意義。①參見項陽《以〈太常續考〉為個案的吉禮雅樂解讀》,《黃鐘》2010年第3期;《一把解讀雅樂本體的鑰匙——關于邱之稑的〈丁祭禮樂備考〉》,《中國音樂學》2010年第3期。雅樂重敬畏與贊頌,其樂與舞以怎樣的技藝和形體語言表現需整體認知,亦應依照《詩經》之“頌”來考量雅樂中的歌唱形態,這是群體性演唱頌歌體的展現。
我們應該考量非雅樂類型在禮制儀式哪些類型、哪些場合為用,宮廷和各級官府各自為用類型和等級意義。宮廷中非雅樂類型為用涵蓋吉、嘉、軍、賓、兇五禮所有禮制儀式類型。作為非雅樂類型,漢魏以降以鼓吹樂類型最為穩定,應把握其與金石樂懸為主導的樂制類型的差異性。從宮廷到各級官府,從祭祀到慶典、軍旅、迎賓、哀緬、道路,這鼓吹樂成為五禮儀式用樂的中堅力量。宮廷中還有更多禮制儀式為用的樂制類型,諸如《大唐開元禮》中嘉禮為用九部伎在場等。當我們辨清不同樂制類型的應用場域,則應把握不同禮制儀式所表達的情感訴求,感知情緒與風格差異,這是在儀式為用中應關注者。
20世紀初,延續數千載的國家傳統禮樂制度解體,但禮樂文明之“余緒”在民眾有文化認同情狀下、國家禮樂觀念和禮樂形態還在當下鄉間社會中有選擇地接衍為用,諸如吉、嘉、賓、兇諸禮儀式和用樂,禮樂相須理念、其樂制類型和樂曲被當下鄉間社會各縣域數以千計的職業和半職業樂人團隊延續承載,為中華禮樂文明活態存在。對于傳統國家禮制儀式和儀式用樂之“表演”深入辨析,有助于中國傳統音樂文化整體性認知。本次學術研討會約請多地鄉間禮俗用樂承載者到現場展示,展現形態豐富性,涉及晉冀魯豫和新疆等省和自治區,以顯傳統儀式和儀式用樂的多地存在,他們出色的演奏技藝既使得禮俗儀式“鮮活”,也為民眾儀式性情感代言。我們應認清樂的性質與歸屬,在吉禮、嘉禮和兇禮儀式中吹鼓手們“表演”自然明確風格差異。應重視這一脈用樂當下存在的整體意義,儀式用樂內涵、承載者“表演”值得我們認真挖掘與歸納總結。當我們明確禮俗用樂中儀式用樂與中國音樂文化大傳統的關系,需在探討中國音樂表演理論話語體系時刻意關注,關鍵是建立禮樂與俗樂兩條主脈為用的理念。
以民間禮俗用樂為生存方式的藝人們,得到鄉民認同需具備幾個條件,首先要有嫻熟和精湛的技藝,這得益于長期訓練,許多藝人為“世家”;其次熟諳各種民間禮俗儀式,對儀式諸程序中該奏怎樣的曲、用怎樣的調“門兒清”,區域性固化為用;再次是對不同禮俗儀式類型明確樂曲表現的氛圍與情感,將現場人們帶入其中,這需長期積累;為民間禮俗“上事宴”者,一般需一至數日,諸儀程有特定時間,在儀程中間的空閑部分,為俗樂表現空間,民間職業樂班需兩種“貨色”齊備,這儀式“留白”處給民間藝人展示俗樂技藝空間,民眾喜聞樂見且在當下流行的形態都可在場。
中國傳統社會中禮樂一脈延續當下。現在音樂院校中缺失了樂以儀式為用特定內涵,所謂“禮樂”存在的認知,更多從個人情感體驗視角以把握。數年前某音樂學院音樂學系請來河北冀中音樂會社,這會社屬半職業群體構成,且多與廟會吉禮和兇禮之喪禮儀式相須,一套樂曲形成清亮典雅、舒緩平穩之風,由于非炫技,因此稍見冷遇。當大家了解樂社屬“善會”“圣會”性質,專事儀式為用,入會者跟師傅學唱工尺,以所習樂器承載,數十年乃至數百年“一貫制”,其樂曲和演奏風格以成固化,絕不允許個人炫技,音樂會眾恰恰是對此有精準把握,在場者起立致敬,這是儀式用樂“表演”風格之一種。當然,同樣曲目、同樣儀式為用,北京智化寺屬下職業樂人所奏,功力得彰。我們真是應對儀式用樂一脈“表演”風格的豐富性內涵整體認知,研究中國音樂表演理論話語不可或闕。
三、俗樂形態之音樂表演理論話語
俗樂屬非儀式用樂一脈,貼近人們日常生活,不與儀式相須,重在表達個體豐富性的情感訴求,無論引吭高歌還是吟唱低回,聲情并茂、形神兼備、唱念做打、各有韻味,胸臆直抒既可自娛更適合娛人,以情感人重技巧與技能表現,直抵受眾心靈深處,沉浸其中曼妙絕倫。制度下生存的專業樂人群體與時俱進不斷創造,從體裁形式到內容不斷新創,姹紫嫣紅美不勝收。作為俗樂形態,個體與群體并在,這給樂的發展以極大空間。職業群體重娛人,以此為業者若非技藝過人,斷難引發共鳴與追捧。俗樂在發展中裂變出多種形態,諸如歌舞、器樂、說唱、戲曲等,所有這些從職業角度在歷史上都歸國家用樂機構管理,換言之,這些都為樂。國家雖重禮樂,用樂機構所轄卻禮俗兼具。當隋文帝將太常樂類分為雅部樂和俗部樂,這俗部樂中既有儀式用樂,亦有非儀式用樂。唐代教坊設立,將俗樂從太常中析出,在國家意義上明確有了專置俗樂的機構,中國俗樂一脈進入了大發展期,說唱和戲曲都在教坊脈下發展成熟。唐代教坊從大曲中裂變出“雜劇大曲”,宋代雜劇以成熟樣態面世。一般講來,這曲藝或稱說唱概念在先,戲曲在后,宋代諸宮調雖為說唱卻是戲曲先聲。這諸宮調與戲曲之關系確應認真解讀。學界認定這是兩種不同的藝術類型,都可演繹故事,但說唱屬一人多角兒、跳進跳出的表演形態,而戲曲則為一人一角兒并逐漸分立出行當。作為音樂表演的意義,以人聲表現和以器樂表現,舞蹈亦為樂的有機構成,樂舞類型中肢體語言與樂的關系等等,都需整體考量。
這些藝術形態至少在宋代“分道揚鑣”。但應明確,這是唐代設置教坊之后以成,并歸教坊統籌,所謂“十三部色”①[宋]吳自牧《夢粱錄》“妓樂”條:“散樂傳學教坊十三部,唯以雜劇為正色。舊教坊有篳篥部、大鼓部、拍板部。色有歌板色、琵琶色、箏方響色、笙色、龍笛色、頭管色、舞旋色、雜劇色、參軍等色。但色有色長、部有部頭,上有教坊使、副鈐轄、都管、掌儀、掌范,皆是雜流命官。”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20頁。者。教坊初為俗樂而設,開元間分立,此前“雅俗之樂,皆隸太常”。“開元二年(714):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②[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百十一,中華書局,1956年,第6694頁。開俗樂機構專立之先河。應辨析俗樂與“俗部樂”的差異,隋文帝時期太常屬下俗部樂是儀式和非儀式為用的綜合體,而教坊之俗樂定位為非儀式用樂。在俗樂歸太常統轄期間,太常重禮樂功能,官書正史對俗樂著力不多,但絕不等于涵蓋宮廷在內的社會各界對俗樂如同官書正史一樣把握。陳旸《樂書》兩百卷,對禮樂和樂圖論以及五禮論說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份額,而對“女樂”“宮伶”以及“雜樂”項下的散樂、百戲、劇戲、俳倡、參軍戲、假婦戲等記錄甚少,但社會訴求絕非依這種比例,如此在于撰者努力維系禮樂的國家權威。雖給俗樂小的篇幅,卻未失位,值得肯定。
無論宮廷還是各級官府、軍旅,禮樂是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特定儀式對象的行為,顯然不會時時在場。《唐會要》載:“寶歷二年(826)九月,京兆府奏:‘伏見諸道方鎮,下至州縣軍鎮,皆置音樂,以為歡娛,豈惟夸盛軍戎?實因接待賓旅。伏以府司每年重陽、上巳兩度宴游,及大臣出領藩鎮,皆須求雇教坊音聲,以申宴餞。今請自于當巳錢中,每年方圖三二十千,以充前件樂人衣糧。伏請不令教坊收管,所冀公私永便,從之。”③[宋]王溥:《唐會要》卷三十四,中華書局,1955年排印本,第631頁。諸道方鎮、州縣軍鎮都置音樂,日常為歡娛。大臣領藩鎮,亦求雇教坊音聲。這里的教坊音聲真有可能指藩鎮之地。唐代藩鎮自睿宗景云二年(711)始設,從邊地逐漸拓展到內陸,有數十個之多,這是說遍及全國的官衙皆有音樂,恰恰是國家“輪值輪訓制”意義,保證了國家用樂的相通一致性內涵。①參見項陽《輪值輪訓制——中國傳統音樂主脈傳承之所在》,《中國音樂學》2001年第2期。兩唐書對此有明確記述,這個群體的承載既可從官書正史,亦可從多種文人筆記認知,文人雅士喜好,亦對各地音樂形態產生實質性影響。《全唐詩》《全宋詞》等記述文人與樂人的關系,描述樂人演技,多為俗樂表述。文人非都聚于宮廷與京師,地方官府中官屬樂人應以“府州散樂”“衙前樂營”“府縣教坊”把握。《唐會要》以及多種文獻的記述,應與教坊相聯。教坊雖在唐代宮中設立,但教坊樂是否僅宮廷為用頗有疑問。在下以為,宮廷、地方官府乃至軍鎮都有俗樂需求,文獻說得清楚,更何況宮廷教學機構所教之樂有大曲、中曲、小曲之分,難說都用于儀式。因此,我們應對地方官府和軍鎮中俗樂為用相關機構辨析,把握教坊樂屬性以成“樂系”意義。教坊在發展進程中雖逐漸形成“禮俗兼具”②參見張月《由俗及禮,禮俗并用——唐宋教坊職能演化探研》,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2017年5月打印本。,但社會對教坊司為“倡優之司”③[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徐子仁寵幸》卷四:“臣雖不才,世家清白,教坊司倡優之司,臣死不敢拜。”中華書局,1982年,第133頁。的認知一以貫之,我們真是應對教坊司屬下特別是俗樂一脈進行認真而細致的梳理,特別把握教坊樂人和相關體裁類型構成,教坊自分立之初所存在的音聲技藝形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創造、裂變所成新類型,諸如歌舞、說唱、器樂、戲曲。這些形態如何表演,在哪里表演(宮廷、京師與地方官府之存在),其體裁和技藝怎樣不斷積累成熟,不同時代專業樂人在表演意義上有怎樣的創造。既依不同門類考辨,又把握不同門類表演相通性,如此方能將“脈絡”和“筋骨”架構以成。不同時期的新變化,當然依靠時人記述去把握“血肉文本”。至于教坊在發展過程中與禮樂的關系也是考量目標,我們的音樂史著作認知教坊多指唐代,而對后世上千載教坊機構上下相通的承載關注不足,令人遺憾。實際上,教坊樂系與社會世俗日常生活中用樂更為緊密,若不刻意把握中國音樂文化傳統整體,既關注官書正史,亦關注文人筆記;既關注唐代教坊確立,亦認知教坊樂系延續一千又數百年的意義,難以將地方官府中禮樂、俗樂與國家用樂相接。
雍正禁除樂籍,遍布全國的專業樂人群體從官養轉為“官民共養”,導致社會對曾經國家用樂群體的認知越來越“民間化”,其承載體系內多種藝術形態由于“恩主”改變越來越呈現區域化。歷史上高級別官府所在地官屬樂人承載的傳統音聲技藝類型相對齊全,積淀深厚,20世紀下半葉國家對傳統音聲技藝活態普查,各地學者以地方視角對其命名,成為區域樂種、曲種、劇種、歌種、舞種的主要存在,殊不知在樂籍存續期這些多在教坊體系內且上下相通,從律調譜器甚至作品內涵顯現一致性。探討音樂表演既應關注一時一地、一腔一種,又要對同地多種以及異地多種、甚至異地同種進行整體把握,如此顯體系化意義;一個世紀以來西方音樂觀念和音樂形態對以城市為中心的中國音樂文化形成了至關重要的影響,甚至形成了以中西融合為特征、“體用論”下所謂“新傳統”④項陽:《中國音樂文化的“大傳統”與“小傳統”》,《天津音樂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特別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以城市為中心、重審美欣賞用樂與當下國家用樂理念這一脈相合,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中國音樂文化兩條主脈為用,使傳統之一脈消解。研究音樂表演理論體系不應忽視中國傳統音樂文化中兩條主導脈絡并行不悖互為張力的發展樣態,更何況對傳統文化有深厚積淀的廣袤鄉間社會在當下依舊是禮俗兼具活態為用。對中國音樂表演理論話語體系的研討,應對論證的對象及其演化脈絡有整體把握,如此方明確“體系”化內涵。
四、從體系意義把握表演理論話語
中國音樂表演體系既應厘清脈絡又應把握當下活態,這是我們強調有歷史視角的理由。如同建筑高樓,打好地基以立骨架,進行填充與修飾,呈現不同風格特色,尚需從多視角觀察,方能展現整體樣貌。表演體系應是不同門類、不同體裁和作品整體意義上的架構,這些都由人創造,思想理念、功能屬性、技巧技藝、風格特征等需全盤考量。
中國音樂表演理論話語體系,當然要依不同門類把握其術語、技巧、技能的創造性發展和積累,把握多種門類藝術表演的共性、個性與區域特色,同一門類下風格與流派的形成。須建立坐標方能認清當下存在有怎樣的承繼和發展。樂的實施為表演,但表演并非都是審美。試想,當舉行家奠禮儀式,家族成員在凄清樂聲中淚眼婆娑向祖輩靈柩叩首,很難想象他們(包括在場者)的奏樂僅為欣賞意義,但民眾認定此時樂不可或闕。儀式用樂并非沒有審美和欣賞意義,在吉禮儀式中為“獻”,即將世俗社會美好的東西奉獻于儀式對象。儀式用樂中,演奏者以技藝營造出儀式氛圍,非僅為審美、欣賞功能。俗樂表演重審美與欣賞,這毋庸置疑。
體系是在藝術形態發生與發展不斷積淀下的歸納與總結,涉及多層面非單一線性,要看到某一體裁類下依作品深層把握所顯現的技巧與技能表達;樂原本“三位一體”,作為表演應有形體意義,且應把握樂的個體技藝和整體表現、個人技藝與群體技藝相結合,無論禮樂還是俗樂均如此。
禮樂一脈,樂本體與儀式相須為用。儀式者,有儀成式,有儀軌與儀程,依制固化,現立體與動態,儀式調度和樂在儀式中展示,呈整體感。禮樂有不同類型,應把握情感訴求的豐富性和差異性。雖然在國家意義上傳統禮樂少見蹤影,但我們應從當下非物質文化遺產類下把握多種儀式類型用樂的活態存在。禮樂之表演在中國音樂表演話語體系中不可或闕,這是傳統所在。
我們應向舞蹈界的劉青弋先生和音樂界的田耀農先生致敬。十多年前他們二人領軍的團隊依托杭州師范大學音樂學院探索唐宋雅樂舞的復原和展演,推動歷史上國家儀式性樂舞本體活態再現,若調整理念推進,會對學界認知歷史上的雅樂形態有極大助益;我們應向清代道光年間瀏陽的邱之稑先生致敬,作為雅樂一支的《文廟祭禮樂》在國家頒行的紙質文本中未記錄節奏與時值,使把握雅樂活態成為畏途。邱之稑聞聽宮中太常寺官員到闕里教授《文廟祭禮樂》,即赴闕里學習,用“總譜”和分譜乃至舞譜形式,并運用《律呂正義后編》業已創制的節奏與時值符號系統對《文廟祭禮樂》相對準確和全面地記錄,由瀏陽樂舞生代代傳承,如此楊蔭瀏先生在20世紀50年代對瀏陽孔廟丁祭禮樂考察用現代樂譜記錄時慨嘆此地有雅樂活態①楊蔭瀏:《孔廟丁祭音樂的初步研究》,《音樂研究》1958年第1期;邱之稑:《丁祭禮樂備考》(卷上),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藏,道光二十一年刻本;項陽:《一把解讀雅樂本體的鑰匙——關于邱之稑的〈丁祭禮樂備考〉》,《中國音樂學》2010年第3期。,當下瀏陽丁祭禮樂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相對準確把握清代道光年間國家雅樂一支的活態存在,對研究有重要意義。
依據《太常續考》《律呂正義后編》《丁祭禮樂備考》等,學界真是能夠對明清以來宮廷和地方官府為用、有儀程儀軌和樂本體形態者進行復原,結合民間禮俗,由此認知雅樂表演話語。儀式用樂強調群體性情感,重意境和氛圍渲染,依儀式對象為用,有敬畏、喜慶、威儀、慰緬等等,情感不會單一,這樣的禮樂承載該如何“表演”,值得深入挖掘,畢竟傳承了數千年。從中華樂文化邏輯起點意義上把握,對禮樂一脈中專用體裁、形式,諸如“頌”“贊”等該怎樣表現值得深入研究,關鍵要有這樣的理念并借助文獻認知活態。總結中國音樂表演理論話語,一定要有歷史縱深感,當下社會人們依舊有儀式性情感訴求,作為禮樂文明亦需有整體把握和總結。
我們還應向遍及全國的樂戶后人及其弟子和全國各地對民間禮俗有文化認同的鄉民致敬,你們對傳統的敬畏與堅守,方使中華禮樂文明的實質性內涵得以展現,使我們能對傳統吉禮、嘉禮、兇禮之儀式及其用樂有活態把握。從傳統國家宮廷與地方官府依制上下相通意義上考量,至少我們能夠部分認知歷史上的禮樂活態,認知本體形態與儀式相須的整體意義,感知禮樂實質性內涵。令人唏噓的是,當下許多地方不顧民眾對傳統文化的情感,“移風易俗”硬將儀式用樂承載群體革除,將水中生存的魚置于岸上,實為不智。
禮樂作為中國傳統音樂表演理論話語體系屬不可或闕。當厘清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整體意義,依托相關文獻對當下活態存在有認同與把握,能夠真正建立中國音樂表演理論話語體系,否則像維納斯屬殘缺美,應避免這種情狀出現。探討體系應在認知傳統的前提下先搭框架,建立坐標,學界同仁共同建言獻策,使系統得以完善,取得認同以成合力,既認清歷史傳統,又把握當下;既明確禮樂又把握俗樂,依兩條主脈梳理,認知中國音樂表演理論話語的深層內涵。把握禮樂儀式性、群體性、豐富性和固化意義,認知雅樂類型和非雅樂類型的差異性存在;認知俗樂體裁、類型、區域、風格、流派、時代演化、程式化存在、形體表達、多種音聲技藝形態表演和表現的內在關聯,多角度、多層面辨析,從表演心理和接受心理等層面考量,這是架構中國音樂表演理論話語體系的要義。
形成合力,意指從事理論、表演的諸君雖分工有自,卻需有“體系化認同”,否則自說自話,缺失整體感。通過學術會議校準方向,音樂表演家準確把握所從事表演行當在中國音樂表演理論話語體系中的位置,歷史脈絡,前輩藝術家在技巧、技能、技法等多方面的創造性貢獻,有哪些能夠超越前人,是否能在中國音樂表演史上畫上濃墨重彩的一筆,不知前輩貢獻則會過于強調“自我”,實屬遺憾。當然,對作品的揣摩和感受融進自己的理解也屬新創;同一部作品,不同感悟及自身技術和樂感的底蘊,都會對作品深層詮釋形成自己的特色,“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確為中國音樂表演理論話語體系的奉獻。然而,我們應考量哪些能真正進入“音樂表演史”。一線表演藝術家有著豐富和出色的表演技藝,對當下存在與總結十分必要,但怎樣將有特色的表演技藝融入“體系”需要明確。從事音樂表演史學研究者更是應對中國音樂表演傳統有整體把握下對某一表演領域系統認知,還要把握不同歷史時期形成的音樂藝術類型、生成背景和發展演化,如此認知當下多種音樂表演類型創造的實際意義,以學術合力建構起中國音樂表演史的學術大廈。
演唱基本技巧和技能有共通性,某種體裁演唱會形成特色,所謂唱法與風格意義,應對先民的演唱技術理論歸納總結。諸如《樂記·師乙篇》:“故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樂府雜錄》謂:“善歌者必先調其氣,氤氳自臍間出,至喉乃噫其詞,即分抗墜之音。”尚有“氣動于腹,聲立于頸”之論,這都是歌唱基本理論。至于《唱論》,更是元代人對歌唱技術理論的精到總結。哪些是在中國演唱技法前提下的發展,哪些是汲取外來演唱技法,諸如西方演唱技法后的進步,哪些屬中國固有之特色,應有所辨析。在不同歷史階段形成不同音聲體裁之時,圍繞這些體裁所成演唱風格,更是應刻意關注。諸如唐詩、宋詞(含豪放與婉約)、元曲之演唱(此處重只曲意義,把握南北之差異),以及戲曲之演唱(不同行當及同一行當和角色不同表演所成流派意義,潤腔所成特色;水磨腔形成之后既對一個劇種整體風格的影響,又對一個時代,甚至其后數百年相關劇種演唱風格的影響)等,既體現創腔技法又把握風格。應把握整體意義和個體差異。至于因文化地理、方言所成演唱特色以及特有曲種、劇種專用聲腔的演唱應刻意關注。值得思考的是,一些傳統音聲形態可能在一定時段內會成就輝煌,當社會轉型,雖然傳統音聲形態也有專業人士承載,卻很難超越。撰寫音樂表演史應刻意關注,如此顯現時代特征。有位摯友從廣播電臺搞到某種蜚聲全國的曲藝形態20世紀分流派的成套錄音,欣賞之余并與當下藝人之演唱比較慨嘆今不如昔,這種現象并非單一,應對產生這些現象的深層意義進行辨析。
在樂籍存續期,經職業訓練的樂人在體制內表演有相通性和差異性(或稱豐富性)。所謂相通都在體制內,屬職業傳承,所謂相異在于南北東西文化地理差異,有所謂“南腔北調”之論。樂籍制度解體后,曾經的官屬樂人在承繼既有演唱技法前提下與時俱進,越來越具區域特色,這種豐富性意義值得挖掘和考量。既為表演,不能僅在演唱技巧層面,還應辨析諸如戲曲的“手眼身法步”、歌舞中的形體意義。
我們以歷史上主流發展脈絡立論,還要考慮區域民歌演唱由于方言層面導致地方音調和演唱特色,區域人群(涵蓋族群)對這些演唱特色的提煉和升華。顯現中華民族音樂表演體系在演唱方面的豐富性,撰述者有主觀選擇,但構架之多層面考量不可或闕。
器樂表演在社會發展過程中越來越具獨立性,當下綜合性樂種,其中亦有專門的器樂構成,諸如木卡姆中的器樂段落以及福建南音中“譜”的意義。當一種樂器在發展進程中趨于成熟,在區域人群認同下主流為用,圍繞這種樂器的制作材料、演奏形態、所生發的技巧創制、特殊奏法、專業創作以及更適合表現怎樣的情感等多方面都應納入音樂表演視域。這種樂器在樂隊組合中的地位、在說唱和戲曲等樂隊中所起的作用,諸如伴奏、主奏與獨奏,樂器演奏者與演唱者之互動等,都應是音樂表演的論域。任何一種進入大眾視野且成為區域和跨區域人群特別是專業人士關注的樂器都可寫一部表演專著,實際上學者們已然實施。我們厘清這些樂器的源流脈絡(出于坐標系的把握),則可以歷史視角關注當下,這是音樂院校應設置樂器史課程的道理。
20世紀以來,人們從世界范圍關注“樂系”,諸如王光祈先生對三種樂系的認知。以樂系相稱,定涉及整體意義,因文化差異顯現音樂表演的差異性,諸如同一支嗩吶,由新疆和內地演奏家定會以不同風格展現樂曲。問題在于,中國傳統社會有著數千年的文明傳統,且在國家意義上形成從王庭到地方官府具相通性的用樂制度,涵蓋音樂本體(律調譜器)、體裁和作品的創造,當然也會有相通性的表演內涵,說形不成體系難以自圓,這就是我們觀察中國音樂文化傳統謂其“整體一致性下的區域豐富性”①項陽:《中國傳統音樂文化整體一致性下的區域特色》,《榆林日報》2006年8月5日第4版。道理所在,關鍵是怎樣對中國傳統樂文化中的音樂表演通過相關文獻進行總結和辨識。如果我們不把握中國音樂文化國家意義上的邏輯起點,厘清脈絡,僅從國家樂籍制度解體后考量以及從傳統音樂的當下存在認知,就會認定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如同散沙,難有體系意義。
五、西方文化影響下的中國音樂表演
從邏輯起點梳理,明確中國傳統音樂文化以中原文化自身創制主導發展以成“主流”、多族群共同創造并有國家制度制約,把握不同歷史階段多種外來文化融入,唐代宮廷形成“雅胡俗”三分局面。由于胡樂與中原音樂的差異,且國家設置專門機構依部伎以教以學,在“輪值輪訓”中播至全國各高級別官府所在地,對中國音樂文化發展形成實質性影響。既為國家用樂,不同朝代總有對中原音樂文化傳統固守的“衛道士”一群,至少在雅樂層面力圖保持周以來的中原傳統(確有周邊民族和外來文化因素融入)。但20世紀西方音樂進入后對中國音樂影響之巨,歷史上任何一個階段的外來音樂都無出其右。西方音樂文化強勢進入,以城市為中心對中國音樂造成了決定性影響。反映在音樂技術理論、創作觀念、思維方式、從音樂本體到體裁類型、表演形式等多方面,這是我們講中國音樂文化形成兩個傳統的道理所在。即歷史音樂文化大傳統和一個世紀以來受西方、特別是歐洲音樂文化影響融合以成的“新傳統”。如果說歷史音樂文化大傳統是兩條主導脈絡并行不悖,且在國家意義上重禮樂一脈,“新傳統”在確立支出淡化這種用樂理念,重“藝術”、或稱審美欣賞為主導,這實際上是歷史音樂文化大傳統中俗樂一脈概念。雖然前一種傳統在當下依舊存在,卻呈非主流樣態,如此在主流用樂中兩脈變一脈,注重當下不把握歷史難以廓清。需思考:國家要求全面復興傳統文化,是否將中國音樂文化固有之傳統用樂理念在與時俱進中摒棄?
由于西方音樂進入之時這傳統音樂文化多以“民間態”存在,當西方音樂家以及留學歸來的人士以城市為中心在團體、專業院校和中小學校進行傳授和傳播,培養出中國接受西方音樂觀念和技藝的中堅力量,進而在20世紀下半葉從國家制度層面全面推進,導致一說“高雅音樂”即指交響樂、歌劇乃至多種西方音樂體裁影響下的音樂形態,使得“新傳統”漸呈體系化。美聲唱法在院校中漸為主流,西方之合唱、聲樂套曲、歌劇、音樂劇、清唱劇等成為音樂院校和音樂團體的主要創作和表演類型;在器樂領域,鋼琴和小提琴的學習者其數量在城市中領軍。交響樂、室內樂、管弦樂、銅管樂等成為院校和團體創演的主流。我們有“民族樂團”,但樂器是中國傳統,音樂思維已經是西方,君不見從樂隊組合、編制、配器、和聲、對位等諸多層面都以西方創作技法和理念為中心。從音樂本體到音樂思維以西方為重心,我們的傳統音樂文化面對怎樣的沖擊?美術界一邊油畫素描,一邊水墨丹青;舞蹈界一邊足尖起舞,一邊秧歌盛行,能夠相對保持傳統的只有從傳統樂文化裂變出去的說唱和戲曲,被“瘦身”之后的音樂界從音樂本體和音樂思維等方面接受西方更為“徹底”。探討西方專業音樂對中國音樂文化形態的影響是為必須。
正視現實存在,應從中國傳統音樂文化數千年延續與近百年變化整體看待。傳統禮樂文化當下以非物質文化遺產形態存在,戲曲尚在“主流”中。最為要者,無論禮樂還是俗樂,兩條傳統主脈都活態存在,關鍵應從傳統音樂文化的整體以行認知,這對我們研究傳統音樂表演話語至關重要。器樂文化中有諸如鼓吹樂全國性存在,重點把握其如何為用是認知傳統禮樂文化的有效視角,其在不同禮俗儀式中為用彰顯情感豐富性意義,其表演顯然不會是一種風格。江南絲竹、潮州音樂、木卡姆、福建南音、冀中笙管樂、西安鼓樂等諸多形態在各地傳承,為我們辨析傳統提供了諸多活態樣本。至于多種綜合性樂種,諸如海州五大宮調、南京白局、揚州清曲、廣西文場、常德絲弦等,更應辨析其何以多種體裁并在以及表演的相通與相異性。目前國家音樂表演團體和音樂院校對傳統音樂的傳承難現整體,應明確他們承載的是傳統的哪一部分,哪些延續中國音樂文化“大傳統”,哪些屬一個世紀以來的“新傳統”。如此把握大傳統中的形態承繼、發展和“復興”。中國音樂表演理論話語體系,這數千年的傳統與百年新傳統其比例應怎樣安排,既然是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生成,都應納入視野,但所占份額應專題研討。
還應從風格和流派把握音樂表演理論話語體系,這同樣需要既把握歷史亦把握當下。從歷史視角應關注重要的歷史節點,首先把握周代狀況,繼而看漢唐間西域及周邊國度音樂形態進入中土在融入過程中導致國家音樂形態表演風格之轉型(哪些領域和哪些類型如此),畢竟音樂本體和結構彰顯差異和豐富性。再看西方音樂文化大規模進入對中國音樂表演風格的具體影響。應在建立相關理念的基礎上努力厘清,并專設表演史學課程,不把握歷史演化脈絡,怎能有中國音樂表演理論話語體系?否則如磨一般只在原地打轉。
從體系視角關注流派亦需縱橫結合。流派者,所謂流中之派,以流生派,不從源頭把握。但有源方有流,有流方生派。所謂開宗立派,是在承繼前人表演技藝基礎上有創造性和獨特性。諸如京劇旦角,同一出戲,不同表演者把握共性加入自我理解,獨特的潤腔以及形體使個性凸顯,在新創劇目表演之時延續獨特,派者——韻味與風格共在。
近期一種現象引發關注:多所音樂院校聘任了一大批表演學科的博導并開始招收音樂表演類的博士研究生,其目的應該是使相關專業學子提升整體素質,為社會培養高水平、高層次相關人才。但缺失博士階段應有課程層級的頂層設計,對表演類博士研究生的核心課程理解不深。學生們講,各自領域相關曲目在本科和研究生階段已基本完成。博士階段課程應怎樣開,是延續本碩階段教法,深化已經演奏過的曲目?畢竟從事音樂表演教學的教授們缺乏這方面的經驗和閱歷,若不對博士學位相關課程“科學論證”,明確表演學科博士應有的知識結構,難以培養出與博士學位相符的人才。
就表演學科撰寫學位論文,有教授提出詰問:寫好論文就能創作出好的作品、就能夠上臺表演嗎?言下之意表演、創作學科博士無需此環節。國家既設博士學位,必有相對統一學科要求,既然要獲得博士學位,應遵循其基本規范。純粹以舞臺為中心的培養可能更需要類似西方大師級表演證書,但作為博士其表演技能精湛自不待言,還應有較高專業理論素養,有宏觀視野,把握學科發展脈絡,使進入該層級的學生在表演技能基礎上對表演理論有整體認知與把握。高校設置相應的學位,需要頂層設計一系列與學位相適應的課程。導師須指導學生撰寫符合學科要求的學位論文,絕非僅教授技藝就能夠勝任博導。
學科建設至關重要。沒有整體意識,明確中國音樂表演理論話語體系設置的意義,難以真正建立起“學科理念”。在頂層設計中明確音樂表演專業的博士學位核心課程設置、涵蓋一系列提升素養的課程至關重要。其間如何提升中國特色值得考量,真應有中國傳統音樂(分專業)表演史等相關課程,不把握前人就不能很好地認知自我。遺憾的是,現在高校中還真沒有對中國傳統表演各門類的史學理論課程開出,亦缺失像許講真教授對中國傳統演唱理論有深層把握的課程,如果每一種表演門類都像許教授這樣對傳統演唱技藝活態存在從學理意義上相對系統總結,定對中國音樂表演理論話語的提升有重要意義。既然要設置這樣的學位方向,就要體現歸納、總結、提升與積累,強化學科意識培養相關師資,設置相關課程,諸如分門別類的音樂表演史等等,否則會出現車已開出卻未修好道路的情狀。建立中國音樂表演理論話語體系,真是應該專門課題論證,以課題組形式將各門類的表演藝術家、教授、音樂史學家等集聚一堂共同探索,建立理論構架,明確兩條主脈,看到各藝術門類的存在與發展,撰寫出適合高層次教學為用的中國音樂表演史教材。某音樂學院研究生教學評估中學者與在讀表演專業碩博研究生代表對話,強烈感受到大家的求知愿景和課程設置之間的差距,設計系列相關課程,以課題組方式攻關,培養能夠勝任相關教學的人才和撰寫出成型的教材刻不容緩。
中國音樂表演理論話語體系學術研討會舉辦的主旨是讓各界共同建立體系化創造意識,建立體系坐標,明確各自職能與定位,為建立中國音樂表演理論話語體系群策群力,在不久的將來將中國表演理論話語體系向學界、向社會、向世界整體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