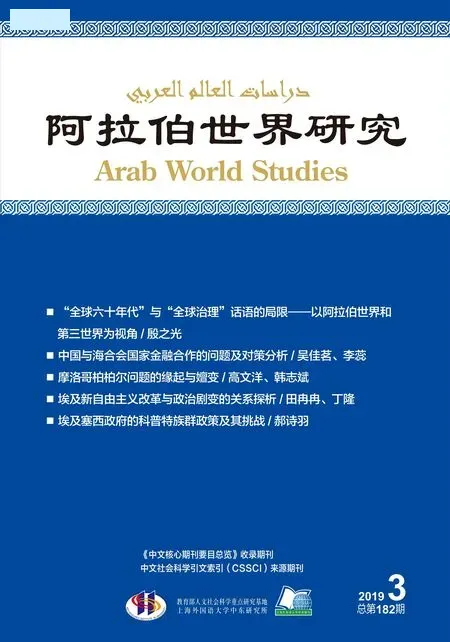“全球六十年代”與“全球治理”話語的局限——以阿拉伯世界和第三世界為視角
殷之光
導言: 全球治理的霸權邏輯
作為一種理論話語,“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在冷戰之后才正式受到美國國際關系與政治學界的關注,并很快影響了全球學界。但其問題意識的來源與基本理念卻并不新鮮。冷戰史研究者近來也將全球治理觀念中體現的以理性主義為基礎的大國協作處理國際關系問題、保障國際和平與發展的歷史追溯至20世紀60年代。一些學者提出,從1963年至1968年間,美國約翰遜政府圍繞越南問題、“六日戰爭”以及核軍控三個問題與蘇聯進行的溝通,體現了大國開展全球治理的基本理念,構成了后來冷戰“緩和”(détente)時期國際秩序的框架。[注]Hal Brands, “Progress Unseen: U.S. Arms Control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Détente, 1963-1968,”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0, No. 2, 2006, pp. 253-285。美國約翰遜政府最早對這種協作理性的表述體現在葛拉斯堡羅峰會上。1967年6月25日,美蘇領導人會談結束之后,約翰遜返回華盛頓并發表電視講話,他提出美蘇領導人之間“面對面、直接磋商的精神”加深了雙方了解,由于兩個超級大國責任重大,因此有必要在國際事務上“保持直接接觸”。約翰遜相信,這種“理性”交流的模式足以能讓這個“小世界”變得不那么危險。Lyndon B. Johnson, “The President’s Remarks upon Arrival at the White House Following the Glassboro Meetings with Chairman Kosygin,” June 25, 1967;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8320,登錄時間:2018年6月5日。這次峰會體現出的大國協調處理國際關系事務的理念被稱為“葛拉斯堡羅精神”(The Spirit of Glassboro),并成為之后冷戰緩和的重要基礎。關于葛拉斯堡羅峰會的綜述,參見William Conrad Gibbons,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Roles and Relationships, Part IV: July 1965-January 196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718-725。同時,這也為后來尼克松政府積極推動美蘇合作,正式形成冷戰“緩和”局面作了重要鋪墊。[注]關于冷戰“緩和”時期的研究汗牛充棟。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論述尼克松與基辛格的外交政策在促成美蘇合作進程中的關鍵作用。此類研究參見Raymond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from Nixon to Reaga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5; Keith L. Nelson, The Making of Détente: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Shadow of Vietna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Robert Litwak, Détente and the Nixon Doctrin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ursuit of Sta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John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不難看出,這種敘事的基本態度站在了大國中心主義的立場,將國際格局的演變視為大國協調的結果,是一種由杰出戰略家理性設計與精巧外交運作的“大戰略”。然而,這種理性主義與精英主義的歷史敘事掩蓋了此類外交策略與思想產生的復雜歷史背景,弱化了諸如以民族主義為動力的武裝沖突、反抗等事件與行動在國際秩序形成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實際上,這類行動不僅推動了諸如沃爾特·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注]羅斯托是約翰遜時期的美國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他提出,應當通過逐漸全方面施壓的手段來制約或威脅美國的敵人,這種由綜合行動形成的威脅要比軍事行動更為有效。其觀點轉引自:William Conard Gibbons,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Roles and Relationships, Part II: 1961-196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45。、基辛格等冷戰時期重要的國際關系戰略家做出相應思考,更在二戰結束后數十年間的國際舞臺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如何理解第三世界民族獨立運動在二戰之后世界秩序構成中發揮的作用,以及在冷戰歷史書寫中重新發現這一運動的主體性,構成了本文主要的問題意識來源。從時間上來看,本文聚焦20世紀60年代,并直接呼應目前在全球史影響下對“全球六十年代”(The Global Sixties)的討論。
本文使用的“全球治理”并非單指20世紀90年代產生的國際協作觀念,而是一種從維也納體系時便開始在西方世界出現的通過大國協商、共同制定并維護世界秩序的理性主義理想。[注]關于“治理世界”觀念自拿破侖戰爭以來在西方世界的發展與變遷,參見Mark Mazower, Governing the World: The History of an Idea, London: Allen Lane, 2012。的確,從大國的角度出發,國際秩序是一種“治理”的結果,是知識與政治精英自上而下對“世界問題”的認識與管理。[注]Alice D. Ba and Matthew J. Hoffmann, eds., Contending Perspectives on Global Governance: Coherence, Contestation and World Order,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 3-4.今天的冷戰史以及國際關系敘事也不斷強調這種精英主義世界觀。與維也納體系相比,“全球治理”理論體系不僅隨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深化將視野擴大到地理意義上的“全球”,而且在理論考察與制度設計中引入了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乃至有影響力的個體等行為體。從19世紀初的維也納體系到20世紀中葉的聯合國,主權國家在全球秩序的主動構建中都占有絕對的中心地位。而20世紀末期出現的全球治理觀念則將世界秩序的構成理解為一個多中心的活動。同時,在冷戰結束之后涌現出的美國政治學者還表現出使這一理論體系無所不包的野心。詹姆斯·羅西瑙(James N. Rosenau)將之表述為“人類所有層面上行為活動的諸種規則體系”,而在這些規則體系內“為實現目標而進行的所有操控,都能在全球層面上產生影響”。[注]James N. Rosenau, “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 Governance, Vol. 1, No. 1, Winter 1995, pp. 13-43.
21世紀初國際關系與政治學理論界開始關注“全球社會”(Global Society)以及“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對“全球治理”的討論也隨之從對主體能動性作用的工具理性討論,轉向了對更為復雜的權力關系的分析。[注]Michael 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1, Winter 2005, pp. 39-75.這被視為是國際關系研究中的重要轉向,研究對象從主權國家變為“全球社會”中更為復雜的能動主體。[注]Michael Barnett and Kathryn Sikkink, “Fro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Global Society,” 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63-84.對國際秩序本身的理解也從一個無政府狀態或是帝國想象下的等級秩序,演變成為一個多極、多層的治理網絡。[注]Jack Donnelly, “Rethinking Political Structures: From ‘Ordering Principles’ to ‘Vertical Differentiation’-and Beyond,”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 No. 1, 2009, pp. 49-86.
冷戰史的研究也受到同樣的政治與社會思潮的影響。近十余年來,越來越關心“全球冷戰”命題的學者們開始將注意力擴展到了主權國家之外,更多的研究開始討論個體、組織、活動、文化、觀念、思潮乃至運動等對象的“跨國性”,并嘗試勾勒一種更為豐富、動態的戰后世界格局。對“全球六十年代”的討論便在此背景下興起。[注]關于這一主題最新的討論,參見Chen Jian et al.,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Global Sixties: Between Protest and Nation-Building, New York: Routledge, 2018.在此主題下,學者們不但通過多語種史料進一步豐富了對包括越南戰爭、核軍控、蘇東劇變等傳統問題的理解,也開始將視角投向民權運動、泛非主義思潮以及“五月風暴”等原本不受冷戰史研究重視的話題。
上述現象提醒我們應當走出傳統冷戰與20世紀國際關系史研究的窠臼,在美蘇兩極對抗的關系之外展現一個更加豐富的世界秩序形成的動態歷史。但是,在這個豐富的全球網絡中,不少討論仍習慣性地將西方歷史中的關鍵事件作為原點,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討論固化為西方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影響”或世界其他地區對西方的“接受”研究。西方中心主義意識的危險在于,它很可能會遮蔽全球歷史動態中不同地區出現的其他事件所發揮的關鍵作用,進而創造一種虛假的普遍性,從而阻礙我們進一步探尋這些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的更復雜的歷史關系。
一、 “全球六十年代”及其問題
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蘇之間就“六日戰爭”進行的溝通無疑可以被視為一次全球性的治理行動,它呈現出了之后冷戰“緩和”這一宏大敘事背后所蘊藏的“全球治理”秩序觀的基本態度。一方面,這種敘事默認在全球秩序形成過程中,大國所扮演的作用是決定性的。而大國之間的溝通與協作則是通向全球有序理想的唯一途徑,所有對這種秩序的反動則被視為是需要被規訓的“反叛”。另一方面,我們卻很難將這一時期兩個超級大國的“全球治理”行動同他們的“國家理性”區別開來。同時,也正是這種霍布斯式的國家理性主張,使得當時全球治理的行動不可避免地帶有霸權政治的色彩。
然而,換一種角度來看,大國的決定性色彩便顯得不那么明顯了。有學者表示,對美蘇兩國來說這場戰爭出乎意料。法瓦茲·吉爾格斯(Fawaz Gerges)認為,兩個超級大國未能影響1967年“六日戰爭”的進程。[注]Fawaz Gerges, The Superpowers and the Middle East: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55-1967, London: Routledge, 1994.如果單純從治理與被治理的關系去理解“超級大國”與世界其它國家的關系,簡單地將國際秩序的構成視為霸權之間協調的結果,僅關注具有政治、經濟及軍事“影響力”的“大國”,而忽視“小國”特別是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歷史與政治主體性,那么我們便無法真正理解現代世界秩序形成的歷史以及國際關系發展動態中的復雜性。
20世紀60年代國際秩序的復雜性還體現在另一層面。我們無法僅僅把主權國家作為國際關系的分析單位去理解這一時期的國際秩序動態。在這一時期,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正在形成過程中,社會運動、團體組織以及各種思潮都在這一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注意到這類非國家行為體的重要性。在“全球六十年代”框架內,諸如第三世界民族獨立運動、美國反越戰示威、黑人民權運動以及包括“五月風暴”在內的一系列歐洲學生運動等都受到了極大關注。[注]Martin Klimke, The Other Alliance: Student Protest in West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Global Six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但是,這類討論多少都會以1968年“五月風暴”為中心。從歐洲中心的角度出發,這類討論將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反抗與群眾、學生運動視為“社會組織與政治行動的新形式”,并采用激進甚至暴力的方式對抗各類“權威”。[注]Daniel J. Sherman et al., eds., The Long 1968: Revisions and New Perspectiv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17.由此展現出的1968年有兩個特點:一方面,它被視為一場超越國家、超越意識形態陣營的“全球性運動”;另一方面,其政治結果卻被局限在西方民主政治敘事內部,成為“社會的覺醒”與“國家的危機”的標志。[注]Vladimir Tismaneanu, “Introduction,” in Vladimir Tismaneanu, ed., Promises of 1968: Crisis Illusion and Utopia,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3.也正是在此視角下,歐洲1968年學生運動所代表的左翼社會主義政治訴求的失敗,才被理解為“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的復興。[注]Agnes Heller, “The Year 1968 and Its Results: An East European Perspective,” in Vladimir Tismaneanu, ed., Promises of 1968: Crisis Illusion and Utopia, pp. 157-166.而美國反越戰及黑人民權運動則成為以個人解放和身份政治為中心的平權運動的開始。[注]Sharon Egretta Sutton, When Ivory Towers Were Black: A Story About Race in America’s Cities and Universitie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15.1968年被作為一場“震撼了世界”的左翼“人本主義”(humanism)運動融入了西方主流的歷史與政治敘事中。[注]Robert Spencer, “Postcolonialism Is a Humanism,” in David Alderson and Robert Spencer, eds., For Humanism: Explorations in Theory and Politics, London: Pluto Press, 2017, pp. 120-162.
支撐這一理論立場的是關于“全球六十年代”的歷史敘事。1968年作為這一敘事的原點,被視為一個“奇跡年”(annus mirabilis)[注]Carole Fink, Philipp Gassert and Detlef Junker, “Introduction,” in Carole Fink, Philipp Gassert and Detlef Junker, eds., 1968: The World Transform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其全球性的記憶圍繞著學生運動、毛主義、毒品與搖滾樂等反文化、性解放以及國家暴力等關鍵詞展開。[注]Martin Klimke and Joachim Scharloth, eds., 1968 in Europe: A History of Protest and Activism, 1956-1977,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這一系列行動被冠以“激進主義”的名頭,至今仍影響著人們對于社會抗爭與反抗運動的想象。當然,西方世界產生的物質現代化與技術進步使得一個同質化的1968年作為全球記憶成為可能。這種記憶將1968年簡化為一場全球性的“學生激進運動”。一份提交于1968年9月的中央情報局戰略報告認為,“青年持不同政見者……是一種全球現象”,其產生源自于“通訊技術、交通的革命以及全球性的社會進步”。[注]“Restless Youth,” CIA Report, No. 0613/68, September 1968, National Security File, Files of Walt Rostow, Box 13, Folder: Youth & Student Movements, Lyndon B. Johnson Library, Austin, Texas.然而,這種敘事中的西方中心主義特性顯而易見。1968年在全球范圍內的復雜性被縮減為一個從“巴黎—伯克利軸心”(Paris-Berkeley axis)衍生出來的網絡,這一歷史敘事是知識與政治精英共謀的結果。在這個“漫長的六十年代”中,似乎所有第三世界的政治變遷都必須圍繞著1968年歐洲學生運動而展開,其歷史記憶也必須透過福柯(Michel Foucault)、薩特(Jean-Paul Sartre)、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等西方左翼知識精英來表達。雖然與1968年相關的絕大多數歷史事件都集中在西方內部,學生“激進運動”及其所隱喻的個性解放與反抗權威的理想,則取代了20世紀上半葉的共產主義運動,成為了全球化時代“國際主義”概念的新指向。[注]Daniel Cohn-Bendit, Wir Haben Sie So Geliebt, Die Revolution, Frankfurt: Athenaeum, 1987, p. 15。另外,2018年5月23日,《雅各賓》(Jacobin)雜志紀念1968年的特輯編者按也直接指出,在自由主義者的評論中,1968年被視為通往“歷史終結”道路上一個“短暫的插曲”。參見“May Belongs to Us,” Jacobin, No. 29, May 23, 2018,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8/05/may-belongs-to-us/,登錄時間:2018年10月2日。在2018年5月的一篇紀念文章中,蘇哈拉·哈薩里辛格(Sudhir Hazareesingh)開宗明義地指出了1968年歷史敘事的西方中心性質,強調1968年在“西方想象中占據了特殊的位置”[注]Sudhir Hazareesingh, “The Fight Continue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May 2, 2018.。但是,這種對“全球六十年代”的敘事無疑消解了第三世界民族獨立運動的歷史主體性及其在世界秩序構成中的特殊意義。
二、 阿拉伯民族運動與“全球六十年代”
福柯曾經對圍繞1968年產生的歐洲中心歷史敘事作出如下批判:“與其說是法國1968年的五月風暴,不如說是1968年3月發生在第三世界的諸多事件改變了我。”福柯進一步回憶了他在突尼斯期間目睹的學生運動與哈比卜·布爾吉巴(Habib Bourguiba)政府之間激烈的沖突。這一經歷令福柯意識到,在這種無私且純粹的“犧牲”面前,一切理論都是次要的問題。[注]Michel Foucault, “Between ‘Words’ and ‘Things’ During May ‘68’,” in R. James Goldstein and James Cascaito, eds., Remarks on Marx: Conversations with Duccio Trambodori, New York: Semiotext, 1991, pp. 136-137.福柯對第三世界的“發現”無疑極大地豐富了其理論的內涵,并促使他開始嚴肅地思考“實踐”(praxis)與哲學理論思辨之間的辯證關系,以及這種問題在第三世界斗爭實踐中的意義。
20世紀60年代全球秩序形成歷史的復雜性體現在反抗任務的多樣性,以及在這種多樣性下各種力量之間在不同政治現實與任務語境下的分裂與整合。如果跳出西方中心的治理邏輯,便能發現,廣大非西方世界內的政治實踐及其歷史實際上體現了一種獨立的歷史與政治主體性。在此前提下,福柯提到的突尼斯學生游行,更應當被放在一個第三世界漫長的反帝反殖民斗爭脈絡中去理解。1967年6月5日,即“六日戰爭”爆發當天,《突尼斯視角》(PerspectivesTunisiennes)的領導人之一穆罕穆德·本·詹奈特(Muhammad bin Jannat)組織了一場反對英美支持以色列的游行,并遭逮捕。[注]Burleigh Hendrickson, “March 1968: Practicing Transnational Activism from Tunis to Par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44, No. 4, 2012, pp. 755-774。《突尼斯視角》創刊于1963年,是突尼斯左翼學生組織“社會主義研究與實踐小組”(le Groupe D’études et D’action Socialiste en Tunisie)的機關刊物。1964年,該組織將工作中心從巴黎轉移到了突尼斯,并在突尼斯大學中逐步取得了影響。《突尼斯視角》上的文章傾向展現出一種泛左翼的特點。突尼斯社會主義憲政自由黨(Parti Socialiste Destourien)、托洛斯基主義者基爾伯特·納徹(Gilbert Naccache)、突尼斯共產黨甚至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等都在該刊物上發表過文章。關于《突尼斯視角》與突尼斯民族獨立運動左翼分子之間的關系,參見Abdeljalil Bouguerra, De L’histoire De La Gauche Tunisienne: Le Mouvement Perspectives, 1963-1975, Tunis: Ceres, 1993, pp. 52-53。不久,本·詹奈特被判處長達20年的刑期,該判決立刻觸發了突尼斯國內的抗議活動。1968年3月15日,一場更大規模的學生罷課活動在突尼斯境內展開,抗議主要針對布爾吉巴政府治下日益增多的學生罪犯問題,并要求釋放包括本·詹奈特在內的所有被捕的社會活動人士。同年5月1日,礦工也加入到抗議活動中。福柯也就是在這個階段目睹了突尼斯的抗議活動。[注]George Katsiaficas, Global Imagination of 1968, the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Oakland: PM Press, 2018.
作為《突尼斯視角》核心人物的本·詹奈特當時還是一名宰圖納大學(Al-ZaytunaUniversity)的學生。在布爾吉巴時期,宰圖納大清真寺及其下屬的宰圖納大學被認為是突尼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大本營。[注]Burleigh Hendrickson, “March 1968: Practicing Transnational Activism from Tunis to Paris,” pp. 755-774.這些思潮看似互不相關,但是在中東地區的語境中,反帝與反殖民的共同政治訴求則成為連接這些思潮并確立它們“泛左翼”色彩的重要基礎。因此,與其將這場運動看作是全球學生“激進運動”的一部分,不如將其放在一個更廣泛與漫長的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運動的線索中理解更為合適。
在今天的國際關系史中,19世紀以來資本主義與殖民帝國在全球擴張的歷史被視為一種西方帝國對“全球秩序”進行塑造的歷史。然而,這種敘事邏輯容易使我們忽略一個事實,在這種秩序井然的“全球治理”實踐之外,對于秩序的反叛同樣也是一場全球性的運動。我們當然可以將此運動視為是國際關系無政府狀態的表現,或是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民族主義分子們發起的暴動。[注]關于無政府主義在19世紀末開始的民族解放運動中的重要作用及其作為一種全球性風潮的討論,參見[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全球化時代:無政府主義者與反殖民想象》,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不過,在20世紀后半葉的民族解放運動浪潮中,第三世界在知識、政治乃至歷史敘事方面,都開始表現出強烈的自覺意識。在這種反帝反殖民斗爭的歷史脈絡中,我們還可以清楚地發現在被殖民(或者被半殖民)的地區,各種來自被壓迫地區內部的思想與政治資源被積極調動起來,以各種方式對霸權秩序做出回應。隨著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霸權表現形式的變化以及技術與物質全球化的進程,在被壓迫地區之間的溝通與交流也變得更為普遍,其社會影響范圍也隨之加大。到了20世紀60年代,在民族獨立運動之間所形成的關聯,以及它們在制度、經驗、情感等方面進行的實質性交流,不僅構成了“全球六十年代”進程中的一股重要力量,而且在一個更漫長的“全球化時代”的歷史進程中,豐富了20世紀下半葉“國際主義精神”的內涵。
與前文所描述的那種被“學生激進運動”歷史敘事所規訓的“國際主義”或者是“世界主義”(Globalism)不同,如果將歷史敘事重心轉向來自亞非世界的國際主義互動,嘗試發現其行動上諸多超越種族、階級、文化與國界的特性,這種從全球史角度出發,對“不受治理者”(the ungovernable)歷史與政治的敘事甚至能夠進一步吸納西方內部“學生運動”,并能呈現出這類“學生運動”中反對不平等、追尋人類解放共同命運的重要面向。當然,我們很難從19世紀初開始涌現于世界各地的“反叛”中看到任何制度的共性。的確,一些西方觀察家指出,納賽爾政府“僅有理想,卻沒有意識形態”。[注]Doreen Warriner, Land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7, p. 10.這里的意識形態指的是知識分子對國家秩序及其未來的精巧設計,而當時的埃及缺少這樣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納賽爾政府僅僅是“一群純粹的民族主義者和革命者,在納賽爾少校的感召下,以行動為目標構成的聯合體”[注]Ibid.。這種因為臨時戰略利益而結合起來的松散政治聯盟不僅是埃及政府的特點,更體現了整個亞非民族獨立與反殖民運動的共同特色。
然而,理解這種“不受治理者”的反抗活動及其全球性,必須跳出自上而下的治理邏輯。在這類反抗的政治行動中,反抗者們不但從實踐上挑戰了全球的霸權秩序,更在理論層面自覺地對自身傳統資源以及各類來自“西方”的“意識形態”進行了梳理與闡釋。進入20世紀后,這種全球性的反帝反霸權運動隨著共產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開始逐漸構成一個相互聯系的情感乃至組織網絡。借用霍布森(John Hobson)的概念,這種在“不受治理者”之間形成的“共時感”同樣也為世界秩序的現代構成提供了一種“新的社會性”。[注]J. A. Hobson, “The Ethics of Inter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Vol. 17, No. 1, 1906, pp. 16-28.
希望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制定并推動一種國際秩序的意圖,本身便是一種全球的霸權邏輯,這種霸權的存在也造就了“不受治理者”抗爭活動的國際性。周恩來在1968年7月23日會見越南副總理黎清毅率領的越南政府經濟代表團時,回憶起1965年會見柯西金時的情形,當時柯西金提出“要搞一個聯合行動,把我們拴起來”,但這種“什么都想控制住”的心態,結果就是“造成對立”。[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47-248頁。盡管在不同地區,“對立”的結果與內在邏輯各有不同,但從更廣泛的全球史角度出發,正是在這種對自上而下的治理邏輯進行對抗的過程中,來自第三世界的反抗運動之間構成了一種相互間的共時體驗。
事實上,全球治理的理論發展脈絡里存在著霸權國家“支配世界”、“治理世界”的想象。[注]關于這一思想史脈絡的梳理,參見Mark Mazower, Governing the World: The History of an Idea, London: Allen Lane, 2012。“治理”邏輯將世界秩序視為全球精英團體與階層之間社會性多極互動的結果,其等級觀念反映在階級層面的支配與被支配關系。“支配”邏輯在國際秩序層面則體現了一種19世紀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沙文主義秩序觀念。隨著冷戰的結束,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在這種強權“支配”的意義上去理解帝國主義的全球性影響。“帝國主義”的內在豐富性進而也被簡化為超級大國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能力。在同樣的邏輯脈絡下,國際關系史學界描繪的后冷戰時期美國“一超獨霸”及其對世界的“支配”,很大程度上回到了20世紀初考茨基式的“超級帝國主義”(Ultra-imperialism)的命題。[注]關于這一問題較為深入的分析,參見Michael Hudson, Super Imperialism: The Origin and Fundamentals of U.S. World Dominance, London: Pluto Press, 2003。實際上,無論是世界秩序的“構建”還是“支配”敘事都呈現了霸權邏輯對世界歷史與現狀的規訓,這種高度修整過的歷史抽象把復雜的世界秩序變遷歷史簡化為霸權的更替與精英主義的設計。也正是在這種只重視支配者的歷史觀下,1968年的歷史被縮減為一場西方內部思想的新老交替,成為“個人主義對保守中產階級的文化革命”,以及對“美國資本主義與西方軍國主義的政治革命”。[注]關于1968年學生運動在西方社會中的意義,參見Sudhir Hazareesingh, “The Fight Continue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May 2, 2018。在今天的文化與歷史記憶中,西方世界內部的1968年運動傳遞出一種強烈的“新一代”反抗“老一代”的浪漫主義想象。
然而,對廣大的第三世界來說,20世紀60年代的歷史卻很難從這種浪漫主義的線性敘事中展開。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曾經直言不諱地表示,所謂1968年的標志性僅僅對第一世界與第二世界產生意義。[注]Arif Dirlik, “The Third World,” in Carole Fink, Philipp Gassert and Detlef Junker, eds., 1968: The World Transform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95-317.而1968年得以出現的重要前提則是舊的殖民霸權秩序、資本主義以及新興的以蘇聯為主要代表的社會主義在廣大第三世界遭遇的危機。這一系列全球性的危機使得第三世界內部的民族解放運動出現了轉機與新的發展。[注]“Foreword: The Third World in 1968,” in Samantha Christiansen and Zachary A. Scarlett, eds., The Third World in the Global 1960s,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3, p. viii.因此,與其將“漫長的六十年代”視為一個獨特的歷史時段,不如將其放在一個更加漫長的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的歷史中去理解,并從這一歷史進程中尋找其內在邏輯。
三、 歷史脈絡中的阿拉伯民族主義
對于阿拉伯世界來說,20世紀60年代影響集體歷史記憶與社會政治進程的關鍵事件是1967年的“六日戰爭”。在傳統的歷史敘事中,1967年的關鍵性是倒敘的產物。研究者習慣從1968年出現于幾個阿拉伯國家的學生抗議運動談起,并將這些抗議活動的原因歸結為1967年“六日戰爭”失敗后席卷阿拉伯國家的幻滅與反思情緒。在這一框架下,1968年的阿拉伯學生抗議運動被視為是對阿拉伯民族主義、特別是納賽爾主義及其國家的反抗。[注]Elizabeth Suzanne Kassab, Contemporary Arab Thought: Cultural Critiqu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19-254.戰爭的失敗令阿拉伯世界知識分子產生了兩種傾向,一種屬于納賽爾主義的堅定信仰者,他們將戰敗視為暫時性的“挫折”(naksa)。[注]例如,巴勒斯坦將每年的6月5日定為“挫折日”,以紀念“六日戰爭”的失敗。關于1967年戰敗作為阿拉伯國家暫時性“挫折”的討論,參見Fawaz A. Gerg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rab Politics,” in Wm. Roger Louis and Avi Shlaim, eds., The 1967 Arab-Israeli War: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285-313。這一“挫折”瓦解了阿拉伯地區的一體化進程,而造成這一結果的唯一原因則是外來的“帝國主義”及其在該地區的代表——以色列。[注]Ali Kadri, Arab Development Denied: Dynamics of Accumulation by Wars of Encroachment, London: Anthem Press, 2014, pp. 159-180.
另一種思潮則從文明論的角度出發,認為戰敗揭示了阿拉伯世界文明的內在問題,是一場徹底的“潰敗”(hazima)。在阿爾伯特·胡拉尼(Albert Hourani)看來,與戰爭勝利相比,戰爭的失敗更能引起人們的深入反思。對一些阿拉伯知識分子來說,這種反思的直接結果是自身文化傳統以及在這一傳統基礎上建立起的宇宙觀、秩序觀的動搖。[注]Albert Hourani, 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300, 442.這種打擊由于20世紀50年代納賽爾主義帶來的阿拉伯民族自信高漲而顯得更為痛苦。對諸如納吉布·馬哈福茲(Naguib Mahfouz)這一代世俗化的但卻持文化保守主義態度的阿拉伯知識分子來說,1967年戰敗的屈辱體驗更直接成為他們反思乃至批評納賽爾政府與納賽爾主義的助燃劑。[注]轉引自Fawaz A. Gerg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rab Politics,” pp. 290-293。一些在西方學術體系內成長起來的阿拉伯知識分子則提出了更為激進的意見。福阿德·阿賈米(Fouad Ajami)便認為,1967年的失敗揭示了“阿拉伯人在計劃、發展以及統一行動方面的無能”[注]Fouad Ajami, “The End of Pan-Arabism,” Foreign Affairs, Vol. 57, No. 2, 1978, p. 355-373.。在阿賈米對納賽爾泛阿拉伯主義的否定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伯納德·劉易斯(Bernard Lewis)的影響。這種否定從本質主義的角度出發,將納賽爾主義的失敗歸咎于“阿拉伯文化”的整體性問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持這種失敗主義情緒的阿拉伯知識分子并不在少數。相應地,這種從文明論邏輯出發對“阿拉伯文化”的徹底否定,也進一步掩蓋了阿拉伯世界內部的多樣性。“阿拉伯”從一個包含了多個部族、多種宗教的地理概念,轉變為本質主義的“伊斯蘭”的代名詞。這既是一個殖民宗主國文化帝國主義的結果,也是持這類觀點的阿拉伯知識分子自身關于伊斯蘭文化帝國主義敘事的表現。
近年來,一些阿拉伯知識分子開始對這種冷戰時期形成的敘事邏輯進行反思。亞辛·哈吉·薩利赫(Yassin al-Haj Saleh)強調,無論是“潰敗說”還是“挫折說”,實際上都阻礙了阿拉伯人對自身歷史的敘述。這種將1967年視為一種阿拉伯世界歷史發展斷裂的看法,不但遮蔽了阿拉伯世界歷史內在的延續性邏輯,更阻礙了人們深入理解1967年戰敗的原委。[注]轉引自Sune Haugbolle, “The New Arab Left and 1967,”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4, No. 4, 2017, pp. 497-512。事實上,1967年阿拉伯知識分子對納賽爾主義的批判乃至否定可以放在一條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線索中去理解。這種在19世紀殖民帝國主義背景中生長起來的民族主義思潮不僅融合了阿拉伯知識分子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以及伊斯蘭文化傳統的反思,也反映了他們從阿拉伯世界內部出發,對民族特性、伊斯蘭傳統、現代化以及社會平等與正義問題進行的追問。[注]關于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內在思想脈絡,參見Sylvia G. Haim, “Introduction,” in Sylvia G. Haim, ed., Arab Nationalism: An Anth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p. 1-72。關于伊斯蘭文化傳統中的社會主義特性的討論,參見Hamid Enayat, “Islam and Socialism in Egypt,”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 No. 2, 1968, pp. 141-172。在這個意義上,對于“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討論則更應當關注其內部的多樣性,乃至其內部矛盾,并避免將其視為一種同質化的、超越地理與歷史條件限制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力量。[注]Sylvia G. Haim, “Introduction,” in Sylvia G. Haim, ed., Arab Nationalism: An Anthology, p. 4.
如果我們將阿拉伯世界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民族主義政治放在一個較長的時段里,便能發現一些關鍵的主題。從19世紀開始,對于“阿拉伯意識”的挖掘始終在知識分子的討論中占據著重要位置,這種民族意識理論興趣的產生與當時全球性的殖民秩序擴張密不可分。許多來自西方的觀察家從西方中心主義的角度出發,將19世紀以來左右阿拉伯知識分子思考并推動“民族主義”討論的根本動力歸結為“在民族國家政治框架內尋求政治現代化”的愿望。[注]Bernard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Bernard Lewis,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es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4.這個論斷體現了兩個關鍵的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前提:首先,它假設了“民族國家”這種政治組織形式的普遍性,并將歐洲歷史中形成“民族國家”的歷史背景與理論動力推廣至非歐洲地區;其次,它又在同樣的語境中假設了“現代化”的普遍必然路徑與歷史發展目標。
然而,在歐洲歷史之外假設“民族國家”與“政治現代化”的邏輯關聯是危險的。對阿拉伯知識分子而言,傳統社會與政治秩序的迅速衰落是他們面對的基本政治語境。[注]Kemal H. Karpat, “Introduction,” in Kemal H. Karpat, ed.,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 in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New York: Praeger, 1982, pp. xix-xiv.但這種情況并不必然導致他們對西方中心式的“政治現代化”及其發展道路的天然認同。因此,在面對歐洲霸權秩序興起的壓力與本土政治秩序衰落的前提下,如何定義并面對“傳統文化”,如何處理“傳統”資源與當下政治和社會變遷的關系,如何理解民族或文化歷史的斷裂與延續等議題,基本構成了知識分子在討論“阿拉伯意識”這一問題時的緊張感,也構成了廣義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想歷史的基礎。
要理解這種復雜性,我們則必須回到19世紀所謂“阿拉伯覺醒”(Arab awakening)的歷史背景中。[注]“阿拉伯覺醒”這一著名表述來自黎巴嫩人喬治·安東尼斯(George Antonius)1938年出版的《阿拉伯覺醒》一書。19世紀,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治下的“伊斯蘭世界”受到了雙重壓力,一方面是歐洲霸權國家對奧斯曼帝國的政治挑戰;另一方面則是對作為信仰體系與生活方式的伊斯蘭的批判。在與“先進”的西方知識與技術的比較中,“伊斯蘭文明”落后與野蠻的刻板形象逐漸開始形成,而且這種形象很快也成為一種知識而被人們更廣泛地接受。
在這一基本語境下,哲馬魯丁·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注]阿富汗尼的原名是哲馬魯丁·阿薩德阿巴迪(Jamal al-Din al-Asadabadi, 1838-1897),作為一名出生在伊朗什葉派背景家庭的知識分子,主要在遜尼派地區活動的阿薩德阿巴迪用了“阿富汗尼”這個化名。開始宣揚穆斯林大團結的觀念。在巴黎,他與埃及教法學家穆罕穆德·阿卜篤(Muhammad Abduh)一起創辦了《牢固紐帶報》(Al-’Urwahal-Wuthq)。[注]這個概念直接取自《古蘭經》的黃牛章第256節。馬堅將該短語翻譯為“堅實的、決不折斷的把柄”。這段經文強調,所有不信惡魔而信真主的人都握住了一個堅實的把柄。阿富汗尼采用這一刊名的用意十分明顯。他強調,穆斯林的部落主義以及宗派主義(asabiyya)是應對歐洲入侵的唯一手段。來自早期伊斯蘭教發展歷史的經驗則證明,只有伊斯蘭教才能將分裂在阿拉伯半島上的各個部落整合起來。[注]Muhammad al-Makhzumi Pasha, Khatirat Jamal Al-Din Al-Afghani (The Opinions of Jamal Al-Din Al-Afghani), Beirut, 1931, p. 257。轉引自Sylvia G. Haim, “Introduction,” in Sylvia G. Haim, ed., Arab Nationalism: An Anthology, p. 13。阿富汗尼認為,先知穆罕穆德建立起的伊斯蘭帝國衰落的原因在于伊斯蘭教在阿拉伯人心中影響的衰落,這也就導致了阿拉伯人部落主義與宗派主義認同的回潮。對阿富汗尼來說,奧斯曼作為一個包含多個民族的伊斯蘭帝國,其在宗教基礎上建立起的龐大認同顯然要比“民族”(jinsiyya)認同優越得多。這是因為民族認同是人類作為一種群體動物的天然需求,[注]在阿語中,的名詞詞根本意指的是同類物的集合。它與英語中表示物種的species,表示類別的category,表示性別的gender,以及表示種族的race等概念類似。另外一個表示類似民族觀念的阿拉伯語詞匯是(qawm),指代同部落的人,與英語中的people概念類似。而不同的群體之間也會天然地卷入對財富和權力的沖突。因此,民族認同是不穩定的,它隨著人群需求的變化而消長。相反,伊斯蘭教能夠超越狹隘的民族認同,建立起更為穩固的共同體。[注]Sylvia G. Haim, “Introduction,” in Sylvia G. Haim, ed., Arab Nationalism: An Anthology, p. 13.
在面對西方入侵這一基本政治現實時,阿富汗尼對伊斯蘭共同體建設的敘述則表現出了更深的復雜性。他用阿拉伯傳統觀念中表示政治集合體的抽象概念“團結”以及表示團體與團體之間沖突與差異性的“民族”來描述阿拉伯世界內部的緊張關系及其政治未來。阿富汗尼承認,相比伊斯蘭這種宗教認同來說,民族/部族的認同更為“有效”。這種有效性體現在以下邏輯之中。阿富汗尼認為,西方的文化入侵比其政治與軍事入侵更為可怕。他強調“沒有文學的人民便沒有語言,沒有歷史的人民則沒有榮耀”,只有一個有效的權威才能夠保護語言并賦予人民以歷史。[注]Ibid., p. 14.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再引入阿富汗尼的另一個概念“祖國”(watan)。在一段對印度學生的演講中,阿富汗尼直接指出,“祖國”是世界上所有律法與準則的根源。與“民族”不同,“祖國”表達的認同關系建立在共同居住的土地基礎上,這一概念更關心管理土地的權威。“祖國”作為一種政治權威也是提供教育,特別是伊斯蘭宗教教育的基礎。[注]Sayyid Jamal ad-Din al-Afghani, “Lecture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Nikki R. Keddie, ed., An Islamic Response to Imperialism: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Writings of Sayyid Jamal ad-Din “Al-Afghan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101-108.與其將這個“祖國”等同于歐洲概念中以血緣為基礎的“民族”國家,不如將其理解為以土地為基礎產生的權力關系。至此,阿富汗尼設想了一條通往伊斯蘭共同體的藍圖,這個未來的共同體超越了狹隘民族認同,而通往這種共同體的途徑則是“國族”(wataniyya)認同。也正是在此基礎上,“團結”從一個策略性的手段變成一種尋求統一的普遍性政治理想。阿富汗尼所描繪的從建設(伊斯蘭)國族認同到伊斯蘭世界認同的藍圖,實際上也是20世紀絕大多數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的根本關懷。它將阿拉伯傳統中建立在部族聯盟基礎上的共同體想象,通過對于“國族”政治重要性的分析擴大到對于19世紀以來及未來阿拉伯乃至世界整體秩序的敘述中。
如何從分裂到統一,如何實現復興并建立整體性的世界秩序,實際上是這場漫長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的一個核心問題意識。作為這場思潮的政治表達,無論是泛伊斯蘭主義、納賽爾主義、“自由軍官運動”以及復興黨的出現,都能夠在這條線索中尋找到位置。[注]Hamid Enayat, “Islam and Socialism in Egypt,”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 No. 2, 1968, pp. 141-172.從這個意義上來說,1967年戰爭失敗給納賽爾以及納賽爾主義帶來的沖擊并不能被簡單地視為“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危機,而更應被視為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從尋求跨國政治統一轉向主權國家中心的開始。在1965年3月23日會見敘利亞外交部部長哈桑·穆拉維德(Hasan Mraywed)一行時,毛澤東將他所理解的阿拉伯國家主要政治任務歸納為兩點:“第一是反對帝國主義,第二是建設國家。”[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87-488頁。這里從阿拉伯思想內部嘗試梳理的基本任務即是如此,也正是在這種根本認同之下,中國與阿拉伯國家以及所有受壓迫的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國際主義共識才成為可能。
四、 結論: 被壓迫者的國際秩序
20世紀60年代在全球范圍內出現的對霸權主義的各類挑戰此起彼伏。在阿拉伯世界,隨著埃及在“六日戰爭”中的失敗,納賽爾主義提供的阿拉伯世界復興與統一方案受到巨大挑戰。在這種對納賽爾主義普遍的失望情緒中,左翼激進主義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開始逐漸獲得影響力。這一時期,阿拉伯世界對于游擊斗爭的熱情主要集中在兩個地區,即阿爾及利亞的反法獨立斗爭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導的針對以色列的斗爭。在這兩場斗爭中,都存在著左翼激進主義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相結合的色彩。[注]關于阿爾及利亞獨立斗爭以及之后的內部沖突,特別是它在1962年獨立之后內部伊斯蘭主義與社會主義傾向的沖突和之后向伊斯蘭主義的轉向,參見Robert Malley, The Call from Algeria: Third Worldism Revolution and the Turn to Isl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而由于阿拉伯世界左翼政黨的精英主義色彩,以及缺少必要的社會土地改革方案,伊斯蘭主義憑借其深厚的群眾基礎,總能取得最后的勝利。2011年所謂“阿拉伯之春”的發展方向也可以放在這一歷史脈絡中理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1967年的意義對阿拉伯地區乃至整個世界歷史發展的關鍵影響在于納賽爾主義的衰落與伊斯蘭主義的興起。在“六日戰爭”之后,以國家為中心的反帝斗爭一蹶不振。類似于法農(Frantz Fanon)那樣用歐洲語言寫作,從社會經濟與文化批判角度出發對殖民主義及其霸權的反思,開始逐漸讓位于諸如阿卜杜·阿齊茲·杜里(Abd al-Aziz al-Duri)、阿里·胡斯尼·哈爾布特利(Ali Husni al-Kharbutli)等在埃及、伊拉克、黎巴嫩、敘利亞等國工作并使用阿語寫作,嘗試從伊斯蘭思想內部尋找復興資源的阿拉伯學者。與之相呼應的是以伊斯蘭為動員模式的群眾游擊戰爭開始在阿拉伯地區大規模興起。
隨著“六日戰爭”的影響以及同一時期蘇聯與美國關系的調和,阿拉伯地區原本緊隨蘇聯步伐的共產黨與社會主義政黨也開始出現了根本性轉向。諸如喬治·哈巴什(George Habash)以及納伊夫·哈瓦特梅(Nayef Hawatmeh)等在巴勒斯坦地區活躍的馬克思主義組織領導人也開始強調要擺脫蘇聯影響,從伊斯蘭本土資源與阿拉伯地區社會經濟狀況出發,發展出一套適合自身的斗爭策略。[注]參見Walid Kazziha,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in the Arab World: Habash and His Comarades from Nationalism to Marxi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5.這類“阿拉伯新左翼”(Arab New Left)思潮強調暴力斗爭的重要性,[注]塔里克·伊斯梅爾將這種“阿拉伯新左翼”定義為“公開且明確表達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忠誠之心的新興政黨與組織”。參見Tareq Y. Ismael, The Arab Left,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08。近年來有學者則將之視為對現有狀況——特別是納賽爾領導的阿拉伯革命——不滿的政治團體與舊組織的新表達形式。參見Sune Haugbolle, “The New Arab Left and 1967,”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4, No. 4, 2017, pp. 497-512。因為“革命暴力”是“敵人唯一理解的語言”。[注]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PFLP), “First Political Statement,” Al-Hurriya (Beirut), December 1, 1967, ‘The Palestinian Revolution’ project, trans., 2016.在“六日戰爭”之后阿拉伯地區的整體政治環境下,通過游擊戰爭進行暴力革命的需求越來越有群眾影響力。這也使得阿拉伯地區的馬克思主義左翼政黨從行動上與伊斯蘭主義組織越來越難以區分,而在群眾調動方面,兩者的差別則更小。這一點從1967年8月法塔赫(Fatah)發行的14本宣傳冊子中便能略見端倪。其中,既有題為《如何發動人民武裝革命》、《革命與通往勝利之路》等充滿游擊戰爭意味的小冊子,也有直接表達對中國、越南、古巴革命敬意的小冊子。[注]轉引自Paul Thomas Chamberlin, The Global Offensive: The United States, the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Post-Cold War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0。
在20世紀60年代的全球政治語境下,中國對于自身屬于“第三世界”的認識無疑站在被壓迫者的角度,傳達了對霸權主義全球秩序的尖銳批判。在毛澤東看來,帝國主義在全球“中間地帶”的擴張,其目的同“反華的性質一樣”,都是“想控制世界”。[注]這是毛澤東1964年6月18日接見在華工作四年的桑給巴爾專家阿里和夫人時談到非洲人民的斗爭時講的一番話。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364頁。因此,在“中間地帶”進行的聯合,與整個世界反抗帝國主義霸權的目標是一致的。1967年“六日戰爭”期間,在會見錫蘭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桑穆加塔桑(Nagalingam Shanmugathasan)時,毛澤東進一步總結了對阿拉伯民族主義反抗運動的理解,以及對其內部出現的大聯合態勢的希望。他認為,這種發生在地中海和中近東、目的在于爭奪石油利益的局部戰爭,使得英美帝國主義處于相當被動的地位。阿拉伯國家可以通過封鎖蘇伊士運河、截斷運油管道的方式,對帝國主義進行嚴重的打擊。也正是在這種戰爭進程中,“阿拉伯國家的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僅僅是埃及、敘利亞這些阿拉伯民族主義國家之間,甚至包括沙特、約旦在內的“老殖民地國家”都開始團結起來,用聯合的方式進行斗爭。[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91頁。有趣的是,凱杜里也表達了類似的觀念,在他看來,只有阿拉伯世界超出西方民族主義認同建立聯合,可能才是阿拉伯世界現代化的希望。參見Elie Kedourie,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960年12月14日,從當代國際法的角度,聯合國大會1514號決議正式給予了殖民地人民獨立運動斗爭的合法地位。在《世界人權宣言》中,承認殖民地人民爭取自由的行動是一項“基本人權”。這一在當代國際法秩序形成過程中的斗爭是在第三世界展開的,然而,這一歷史過程卻被當代冷戰史敘述所忽略。同時,這一斗爭并未隨著國際立法行動而結束,相反,人權宣言所傳達的平等意義是在二戰結束之后開始的第三世界獨立斗爭中才真正獲得了實質性內涵。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全球激進反帝運動則是這個漫長歷史中的重要一環。這種在暴力革命基礎上構成的國際主義思想與組織互動反映了20世紀60年代全球反帝斗爭的基本特點。雖然全球范圍內被壓迫者的訴求與對世界未來秩序的認識各有差異,但是通過這種全球性的互動,全球各地各階層中間反對帝國主義霸權、尋求國內與國際關系平等秩序的訴求構成了一種富有啟發的世界性體驗。
在這個全球性的互動中,來自歐洲的學生“在斗爭中相互支持”[注]《歐洲北美學生在斗爭中相互支持》,載《參考消息》1968年6月6日,第4版。,諸如塔里克·阿里(Tariq Ali)這樣身處歐洲但卻來自第三世界的學生領袖們通過聲援越南、中國,批判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等行動,對西方陣營內部以及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政策的政治合法性提出了尖銳批判。[注]關于塔里克·阿里對20世紀60年代聲援越南活動的回憶,參見Tariq Ali, “That Was the Year That Wa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40, No. 10, 2018, pp. 3-10。而來自第三世界的武裝斗爭,則在戰略上成功地將美國“釘在樁子上”。[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618-619頁。這種從第三世界角度出發對全球歷史敘事的再詮釋,其意義是希望借此來反觀我們今天理解世界方法的局限性,以及這種世界觀背后歷史性的生成機理。從那些被壓迫者的反抗中,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今天影響我們理解世界、理解自我的零和強者邏輯是否是一種無可替代的唯一真理。在亞非拉地區發生的、以民族主義為基礎的國家誕生與帝國消解的歷史進程,并不是對17世紀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的簡單重復,其歷史意義更體現在一種面向未來的、對世界新的平等秩序的政治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