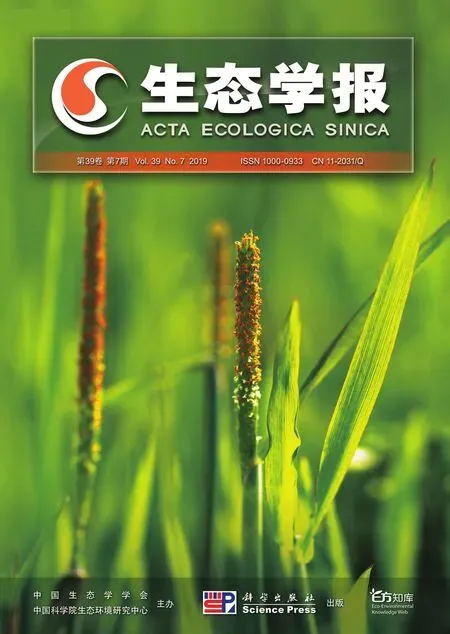庫布齊東段不同植被恢復階段荒漠生態系統碳氮儲量及分配格局
王 博, 段玉璽, 王偉峰, 李曉晶, 劉宗奇
內蒙古自治區林業科學研究院, 呼和浩特 010010
生態系統碳氮儲量是碳氮長期積累的結果,是植物碳氮、凋落物碳氮和土壤碳氮儲量的總和[1],其大小會因生態系統類型、區域環境條件以及人為活動干預而變化,這是人們通過土地利用/覆被變化提高生態系統碳氮儲量的理論基礎[2]。植物碳氮含量及儲量是植物參與生態系統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的主要組分,是衡量植被動態及其生態功能的主要參數[3-4];土壤有機碳含量及儲量是反映土壤質量的重要指標,土壤氮儲量作為評價土壤肥力的指標,其含量和密度直接影響植物凈初級生產力[5]。由于生態系統碳和氮氧化物排放是導致全球氣候變暖的直接或間接參與者,使得碳氮生物地球化學循環一直處于氣候變化研究的核心[6]。因此,明確荒漠生態系統的碳氮固存現狀,對合理利用和管理荒漠、評價荒漠生態系統碳氮固存潛力及生態服務功能具有重要作用。
我國是荒漠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荒漠化面積占國土面積的34%。庫布齊沙漠是我國第七大沙漠,位于鄂爾多斯高原北部和黃河南岸的狹長地帶,是我國北方主要的沙源地之一。對于荒漠生態系統,李玉強等[7]對科爾沁沙地植被-土壤系統碳氮儲量進行的研究表明以提高植被蓋度、促進沙地固定和改善土壤質地為目的的生態恢復和植被建設,能夠增加該生態系統碳氮儲量,從植被恢復的角度可以認為干旱、半干旱地區荒漠化土地有較高的碳氮固存潛力。但對于氣候、環境條件皆不相同的庫布齊沙漠,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土壤碳氮密度[8]、植被群落結構[9]、生物多樣性、生物量和碳氮含量[10],尚缺乏對該區域荒漠生態系統碳氮儲量的系統研究。因此,本研究依據人工建植方式、建植年代及植被蓋度,以空間代替時間,將沙地劃分為五個植被恢復階段,通過對植物、凋落物、土壤碳氮含量的測定,分析地上、地下部分碳氮儲量特征。旨在準確評估庫布齊荒漠生態系統碳氮儲量現狀及不同植被恢復階段碳氮儲量的變化,闡明人工建植促進植被恢復實現沙漠化逆轉對荒漠生態系統各組分碳氮固存的影響,為合理評價荒漠在陸地生態系統碳氮循環中的作用提供科學依據。
1 試驗地概況
試驗地點位于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境內的布爾陶亥治沙站(110°48′29.28″E,40°03′ 42.13″N),海拔1100—1300 m,屬庫布齊東段典型沙漠地貌類型。該區為溫帶大陸性氣候,季節變化明顯,干旱多風,晝夜溫差大。水熱同期,年均氣溫6.1—7.1℃,月均最高氣溫為7月達23.5℃,年均降水量240—360 mm,主要集中于7、8、9月,年均蒸發量2560 mm。年均日照時數3138 h,無霜期130—140 d,年均風速3.3 m/s。試驗區內土壤以風沙土為主,植被主要包括沙柳(Salixcheilophila)、檸條(Caraganakorshinskii)、楊柴(Hedysarummongolicum)、油蒿(Artemisiaordosica)等灌木,豬毛菜(Salsolacollina)、沙竹(Psammochloavillosa)、沙米(Agriophyllumsquarrosum)、狗尾草(Setariaviridis)、蒙古蒿(Artemisiamongolica)、霧冰藜(Bassiadasyphylla)、灌木亞菊(Ajaniafruticulosa)等草本。
2 研究方法
2.1 樣地設置
根據不同植被恢復階段劃分樣地類型,恢復初期的流動沙地(Md)為裸沙地,基本無地表覆被,風蝕嚴重;恢復中期的半固定沙地(Sf)因天然落種而少量生長先鋒灌木油蒿及其他一年生草本,風蝕減弱;經人工建植促進植被進一步恢復,地表覆蓋度增大,形成恢復后期的固定沙地,基本無風蝕,固定沙地根據不同建植方式和建群種又細分為3類:飛播后形成油蒿固定沙地(Ar)和檸條固定沙地(Ca),后者地表發育有藻類地衣混合結皮;沙柳固定沙地(Sa)為人工行帶式扦插沙柳枝條,促進植被恢復,形成沙柳優勢群落,且成林后地表發育苔蘚結皮。3類固定沙地地形基本一致,均處于沙丘迎風坡,氣候背景值和生長環境基本相同。各類型樣地隨機布設3塊10 m×10 m灌木樣地及5塊1 m×1 m草本和凋落物樣方進行植被特征調查,同時在每塊灌木樣地內隨機挖取3個土壤剖面,分層取土樣帶回實驗室測定相關指標,各樣地基本情況見表1。

表1 樣地基本信息
Md:流動沙地,mobile dune;Sf:半固定沙地,semifixed sand;Ar:油蒿固定沙地,Artemisiaordosicafixed sand;Ca:檸條固定沙地,Caraganakorshinskiifixed sand;Sa:沙柳固定沙地,Salixcheilophilafixed sand
2.2 植被層生物量及碳氮含量測定
每塊灌木樣地內分植物種統計所有灌木株高、冠幅、基徑、分枝數等生長參數并計算平均值,依此選擇標準株3株,采用全挖法獲取灌木地下根系,地上部分進行莖葉分離,分別測定根、莖、葉總鮮重并取樣。草本樣方地上部分采取刈割法,地下部分全挖,分別測定鮮重并取樣。凋落物采用收獲法獲得樣方地表所有枯枝落葉,測定鮮重并取樣。植被層所有樣品均取200 g(不足200 g則按全部計)帶回實驗室,烘箱內105℃殺青2 h,85℃烘干至恒重,由此計算樣本生物量。樣品經烘干、粉碎、過篩后進行有機碳、全氮含量測定,前者采用重鉻酸鉀-濃硫酸氧化外加熱法測定,后者采用凱式定氮法測定。
2.3 土壤層容重及碳氮含量測定
每個灌木樣地內分6層(0—10、10—20、20—40、40—60、60—80、80—100 cm)挖取3個土壤剖面,每一層采用環刀法測定原狀土容重,用以計算各層單位面積土壤質量。對每一層混合取樣后帶回實驗室陰干,粉碎、過篩后測定土壤有機質、全氮含量,測定方法同2.2。
2.4 碳氮儲量計算
(1)植被層碳氮儲量計算:
灌木(草本、凋落物)碳氮儲量=灌木(草本、凋落物)生物量×灌木(草本、凋落物)含碳率/含氮率
(2)土壤層碳氮儲量計算:
式中,SOC(N)為土壤層碳氮儲量(kg/hm2),C(N)i為第i土層有機碳或全氮含量(g/kg),Di為第i土層容重(g/cm3),Hi為第i土層厚度(cm),Gi為第i土層礫石體積含量(%)。
2.5 數據處理
試驗數據處理及作圖采用Excel及Sigmaplot 12.5軟件進行,并采用SPSS 20.0軟件進行統計檢驗,選取最小顯著極差法(LSD)進行差異顯著性檢驗(α=0.05)。
3 結果與分析
3.1 生物量分配格局
荒漠生態系統不同恢復階段植被層生物量差異顯著(P<0.05),并隨植被恢復及覆蓋度增加明顯增大,如表2,各階段生物量分別為:流動沙地(2.95 g/m2)<半固定沙地(63.13 g/m2)<油蒿固定沙地(300.08 g/m2)<檸條固定沙地(650.36 g/m2)<沙柳固定沙地(893.86 g/m2)。除流動沙地地表沒有灌木生長外,其他階段生物量均以灌木為主,且不同沙地灌木生物量差異顯著(P<0.05),占總生物量比例分別為:半固定沙地(51.56%)<油蒿固定沙地(83.79%)<檸條固定沙地(85.41%)<沙柳固定沙地(92.06%)。在不同恢復階段,灌木各器官生物量差異顯著且分配比例表現為:莖(49.86%—60.95%)>根(22.39%—31.80%)>葉(16.66%—18.55%),但因不同階段建群種不同,各器官分配比例隨植被恢復程度并無明顯變化規律。

表2 不同恢復階段植被層生物量分配特征
同列不同小寫字母表示差異顯著(P<0.05)
荒漠地區草本植物多為一年生且植株矮小、葉片退化,導致草本層在總生物量中占比較小,且呈現隨植被恢復而減小的趨勢:流動沙地(100%)>半固定沙地(34.83%)>檸條固定沙地(6.18%)>油蒿固定沙地(5.24%)>沙柳固定沙地(0.11%)。不同恢復階段草本層生物量差異顯著(P<0.05),器官分配均為地上部分(72.20%—83.64%)>地下部分(16.36%—27.80%),但分配比例隨植被恢復無明顯變化規律。流動沙地由于植被稀少且風蝕嚴重,地表無凋落物積累,而其他沙地隨植被恢復地表凋落物生物量逐漸增大且差異顯著(P<0.05),表現為半固定沙地(8.59 g/m2)<油蒿固定沙地(32.92 g/m2)<檸條固定沙地(54.44 g/m2)<沙柳固定沙地(69.98 g/m2),但由于灌木生物量的顯著增加,導致凋落物在總生物量中的占比逐漸減小。
3.2 植被層碳氮儲量分配格局
3.2.1植被層碳氮含量
不同種類植物和同一植物的不同器官中碳氮含量不同。植被層含氮率總體表現為:灌木(1.38%)>凋落物(0.87%)>草本(0.75%),含碳率為灌木(46.72%)>草本(44.29%)>凋落物(43.28%)。灌木各器官含氮率特征為:葉(2.18%)>根(1.03%)>莖(0.92%),含碳率為莖(47.65%)>根(46.45%)>葉(46.06%);草本各器官含氮率表現為地上部分(1.11%)>地下部分(0.39%),含碳率為地下部分(44.80%)>地上部分(43.78%)。不同恢復階段凋落物含氮率總體表現為:油蒿固定沙地(0.68%)<半固定沙地(0.81%)<檸條固定沙地(0.94%)<沙柳固定沙地(1.05%);含碳率為:沙柳固定沙地(38.23%)<檸條固定沙地(42.88%)<半固定沙地(45.28%)<油蒿固定沙地(46.72%)。
3.2.2植被層碳氮儲量
荒漠生態系統植被層碳氮儲量隨植被恢復不斷增大,各階段碳氮儲量差異顯著(P<0.05)。如表3,植被層碳儲量表現為:流動沙地(12.55 kg C/hm2)<半固定沙地(294.37 kg C/hm2)<油蒿固定沙地(1431.78 kg C/hm2)<檸條固定沙地(2997.30 kg C/hm2)<沙柳固定沙地(4114.05 kg C/hm2),植被層氮儲量為:流動沙地(0.37 kg N/hm2)<半固定沙地(6.63 kg N/hm2)<油蒿固定沙地(28.07 kg N/hm2)<沙柳固定沙地(67.43 kg N/hm2)<檸條固定沙地(99.46 kg N/hm2)。除流動沙地無灌木生長外,其余各階段沙地植被層碳氮儲量均以灌木為主,碳氮儲量平均分別占植被層的89.03%和88.02%。不同恢復階段灌木碳儲量差異顯著(P<0.05),沙柳固定沙地(3842.04 kg C/hm2)>檸條固定沙地(2584.24 kg C/hm2)>油蒿固定沙地(1207.79 kg C/hm2)>半固定沙地 (155.84 kg C/hm2);灌木氮儲量差異同樣顯著(P<0.05),檸條固定沙地(90.92 kg N/hm2)>沙柳固定沙地(59.99 kg N/hm2)>油蒿固定沙地(24.49 kg N/hm2)>半固定沙地 (4.42 kg N/hm2)。各階段灌木層各器官中碳儲量分配均以莖為主,平均占比為55.19%,根次之(27.55%),葉碳儲量最小(17.26%);各器官氮儲量分配不盡相同,半固定及油蒿固定沙地為莖>葉>根,檸條固定沙地為莖>根>葉,沙柳固定沙地則為葉>莖>根。
草本層碳氮儲量在植被層中占比最小,分別僅為4.14%和3.36%,并有隨植被恢復占比減小的趨勢,其中碳儲量表現為:流動沙地(100%)>半固定沙地(33.85%)>檸條固定沙地(5.99%)>油蒿固定沙地(4.90%)>沙柳固定沙地(0.11%);氮儲量為:流動沙地(100%)>半固定沙地(22.94%)>油蒿固定沙地(4.80%)>檸條固定沙地(3.47%)>沙柳固定沙地(0.12%)。各階段草本層各器官碳氮儲量分配均以地上部分為主,其碳儲量平均占草本層77.53%,氮儲量占89.96%。凋落物層碳氮儲量在植被層中占比略大于草本層,分別為7.84%和7.61%。在植被恢復過程中凋落物碳氮儲量逐漸增加,表現為沙柳固定沙地>檸條固定沙地>油蒿固定沙地>半固定沙地 。
3.3 土壤層碳氮儲量分配格局
3.3.1土壤層碳氮含量
不同植被恢復階段土壤有機碳和全氮含量差異顯著(P<0.05),且均隨植被恢復逐漸增加,其中有機碳含量表現為:流動沙地(0.24 g/kg)<半固定沙地(0.29 g/kg)<油蒿固定沙地(0.35 g/kg)<檸條固定沙地(0.48 g/kg)<沙柳固定沙地(1.17 g/kg);全氮含量為:流動沙地(0.02 g/kg)<半固定沙地(0.03 g/kg)<油蒿固定沙地(0.04 g/kg)<檸條固定沙地(0.06 g/kg)<沙柳固定沙地(0.07 g/kg)。土層深度對土壤有機碳和全氮含量能夠產生顯著影響,如圖1,二者均隨深度增加呈減小趨勢。

圖1 不同恢復階段土壤全氮和有機碳含量Fig.1 Organic carbon and total N content of soil at different stages of recoveryMd:流動沙地,mobile dune;Sf:半固定沙地,semifixed sand;Ar:油蒿固定沙地,Artemisia ordosicafixed sand;Ca:檸條固定沙地,Caragana korshinskiifixed sand;Sa:沙柳固定沙地,Salix cheilophilafixed sand
3.3.2土壤層碳氮儲量
荒漠生態系統不同植被恢復階段土壤層碳氮儲量差異顯著(P<0.05),如表4,土壤層碳氮儲量表現為:流動沙地(3308.42 kg C/hm2、346.32 kg N/hm2)<半固定沙地(4077.10 kg C/hm2、429.32 kg N/hm2)<油蒿固定沙地(4664.71 kg C/hm2、485.70 kg N/hm2)<檸條固定沙地(6559.50 kg C/hm2、826.85 kg N/hm2)<沙柳固定沙地(15374.49 kg C/hm2、914.68 kg N/hm2)。土壤容重和碳氮含量均為影響其碳氮儲量的參數,除流動沙地容重隨土層加深而增大外,其他階段沙地容重與土層變化并無明顯規律,但因為有機碳和全氮含量隨土層加深呈明顯減小的趨勢,導致土壤碳氮儲量同樣隨土層加深而降低。對相同土層而言,0—20 cm土壤碳氮儲量分別占土壤層總碳氮儲量的28.67%—48.00%、34.81%—43.58%,而80—100 cm僅占7.91%—15.20%、7.75%—11.57%。同時,0—10 cm土壤碳氮儲量又分別顯著高出10—20 cm 1.43和1.48倍(Md氮儲量和Sf碳儲量差異不顯著),土壤養分含量表現出明顯的表層富集性,且隨植被恢復富集性顯著加強。
3.4 荒漠生態系統碳氮儲量分配格局
荒漠生態系統總碳儲量為42834 kg C/hm2,氮儲量為3204 kg N/hm2,且碳氮儲量在不同植被恢復階段分配存在較大差異(Ca與Sa氮儲量差異不顯著)。如圖2,生態系統碳氮儲量呈現隨植被恢復不斷增大的趨勢,表現為流動沙地(3320.97 kg C/hm2、346.69 kg N/hm2)<半固定沙地(4371.46 kg C/hm2、435.95 kg N/hm2)<油蒿固定沙地(6096.50 kg C/hm2、513.76 kg N/hm2)<檸條固定沙地(9556.80 kg C hm/hm2、926.31 kg N hm/hm2)<沙柳固定沙地(19488.54 kg C hm/hm2、982.11 kg N hm/hm2)。不同恢復階段各層碳氮儲量分配比例不同,流動沙地為土壤層(99.62%、99.89%)>草本層(0.38%、0.11%),半固定沙地為土壤層(93.27%、98.48%)>灌木層(3.57%、1.01%)>草本層(2.28%、0.35%)>凋落物層(0.89%、0.16%),而油蒿、檸條和沙柳固定沙地均為土壤層>灌木層>凋落物層>草本層。總體來說,荒漠生態系統碳氮儲量隨植被恢復逐漸增大,處于植被演替初期的流動沙地碳氮儲量僅占整個荒漠生態系統的7.75%和10.82%,而植被蓋度最大、生境最穩定的沙柳固定沙地總碳氮儲量占比卻可達45.50%和30.64%;如圖2,土壤層是各恢復階段荒漠生態系統碳氮儲量的主體,碳儲量占比為68.64%—99.62%,氮儲量占比為89.26%—99.89%。


圖2 不同恢復階段荒漠生態系統碳氮儲量分配特征Fig.2 Carbon and nitrogen storage allo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esert ecosystem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recovery
4 討論
4.1 植被恢復對荒漠生態系統生物量的影響
干旱、半干旱地區的荒漠化土壤呈現高度粗粒化和單一化,較差的持水性和貧瘠的養分狀況限制了植物的生長,僅通過自然恢復力短期內很難實現沙漠化逆轉[11]。但通過人工植被的建立,可以有效促進荒漠生態系統植被恢復進程[12]。植被覆蓋度和生物量是衡量植物群落發展的量化參數,可以客觀反映荒漠化土地的植被恢復程度[13]。本研究中不同植被恢復階段地表覆蓋度和生物量差異顯著,從流動沙地到沙柳固定沙地,植被覆蓋度由2.7%增加到60.2%,總生物量由2.95 g/m2增長到893.86 g/m2,表明人工建植促進植被恢復可以顯著增加荒漠生態系統生物量,這與學者對科爾沁沙地的研究結果相同[7],毛烏素沙地通過飛播造林,在植被恢復過程中地上、地下生物量明顯增長[14],騰格里沙漠流動沙地封育后促進植被演替,植被蓋度和生物量隨封育年限逐漸增加[15]。荒漠生態恢復的最終目的是建立具有生物多樣性、抗逆性強的近自然植物群落,首要任務是選擇合適的建群植物種和建植方式,保證演替的快速良性發展[16]。本研究中通過人工植苗形成的沙柳群落植被覆蓋度和生物量均顯著高于飛播形成的油蒿和檸條固定沙地,這是因為沙柳作為庫布齊沙漠優良的固沙樹種,具有生長迅速、萌蘗力強、成活率高的特點,人為栽植后可在較短時間形成枝葉茂密的沙柳林帶,并擴展出發達的水平根系。另一方面,荒漠地表由于風蝕強烈和極端干旱,阻礙飛播后種子萌發和幼苗生長,導致短期內無法形成結構穩定的植物群落,減緩植被恢復進程[14]。郝璐等[17]在荒漠草原的研究也表明飛播或自然恢復短期內很難成林,人工植苗造林后的植被蓋度、高度和生物量均顯著高于前者,具有更強的物質輸入和能量固定。由此可知,適地適樹并選擇合適的建植方式,對于荒漠生態系統的植被恢復,地表植被蓋度和生物量的增加至關重要。同時,本研究中庫布齊沙漠東段平均生物量為382.07 g/m2,與北美Chihuahuan荒漠生態系統相似(320 g/m2)[18],但低于Sonoran沙漠(640 g/m2)[19]和全球荒漠生態系統生物量的平均水平(700—800 g/m2)[20],較低的生物量和凈初級生產力充分表明該地區生態系統十分脆弱,雖然已出現植被的正向演替,但很容易因氣候變化和人為干擾中斷演替甚至出現逆向演替[21],合理的土地利用和管理是防止沙漠化反復的重要措施。
4.2 植被恢復對荒漠生態系統土壤碳氮的影響
在植被恢復進程中,植物群落的發育和演替過程,實際上伴隨著植物自身對生境土壤的不斷適應和改造過程,二者是荒漠生態系統中緊密聯系的兩個子系統,通過相互促進協同作用實現沙漠化逆轉[22]。流動沙地土壤以松散易蝕、干旱貧瘠為特征,當植被開始恢復,植物生長固定土壤的同時會改變其理化性質并增加養分含量。土壤有機碳和全氮是土壤養分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生態系統物質循環的重要參與者[23],二者含量主要取決于碳氮元素輸入和輸出,輸入來源主要是植物殘體的形成和分解[24]。在植被恢復過程中,植被蓋度和生物量增加的同時返還地表的凋落物也逐漸積累,為植物殘體的形成提供充足基材[25]。而且植物的生長有效改善土壤水熱條件,為微生物的生長繁殖提供有利空間,提高生命活性,進而加速對植物殘體的分解速率,利于碳氮元素回歸土壤[26]。同時,風蝕容易造成表層土壤碳氮流失,但隨植被恢復,地表覆蓋程度增大和生物結皮的發育,可有效減弱風沙流活動,從而起到保護土壤碳氮的作用[27]。本研究中,從流動沙地到沙柳固定沙地,凋落物生物量由0增加到69.98 g/m2,土壤有機碳和全氮含量也因凋落物的累積顯著增加,前者由0.24 g/kg增至1.17 g/kg,后者由0.02 g/kg增致0.07 g/kg,充分說明植被恢復能夠有效提高荒漠土壤養分含量,促進土壤形成發育,這與齊雁冰等[28]的研究結果一致,李嘗君等[29]在塔克拉瑪干沙漠的研究也得到相同結論。當土壤水肥條件得到改善,又可為植物生長提供更多營養物質,使植被得以更好恢復,這種植被-土壤的協同作用、相互影響的反饋關系,成為荒漠生態系統良性發展的驅動力[30]。研究發現土壤碳氮儲量隨土層加深而逐漸降低,0—20 cm碳儲量占土壤層總碳儲量的(34.81%—43.58%),Veldkamp[31]也提出荒漠土0—30 cm土層碳儲量占比達到39%—70%,表明荒漠土壤具有明顯的養分表層富集現象,這是因為植物與土壤的交互作用主要發生在根際環境,而研究區中沙柳、油蒿等灌木根系70%生物量集中于0—30 cm土層,表層土體必然成為根系吸收養分和根系分泌物改造土壤質地的主要場所[32]。
4.3 植被恢復對荒漠生態系統碳氮儲量的影響
土地利用方式變化對生態系統碳氮儲量具有重要影響,尤其在荒漠生態系統中,通過人工建植加速植被恢復,可以有效提高地表植被覆蓋程度,且隨油蒿、檸條和沙柳等荒漠灌叢的生長,土壤資源聚集于灌叢下,形成水土氣生較好的“肥力島”[33],改變荒漠地貌類型,促使土壤沙漠化過程發生逆轉,增加生態系統碳氮儲量。本研究中,從流動沙地到沙柳固定沙地,生態系統碳儲量從3320.97 kg C hm/hm2增至19488.54 kg C hm/hm2,氮儲量從346.69 kg N hm/hm2增至982.11 kg N hm/hm2,表明在植被恢復過程中,荒漠生態系統碳氮儲量具有顯著增加的趨勢,這與周欣等[34]的研究結果一致,而趙哈林等[35]則從植被退化的角度證明沙漠化會導致生態系統碳氮儲量嚴重損失。植被層和土壤層是碳氮存儲的主體,植被恢復能夠顯著增加植被層和土壤層碳氮輸入,是影響荒漠生態系統碳氮儲量的直接因素,同時植被恢復是一個復雜的生物和生態過程,受到諸多環境因素影響,而這些因素也將成為影響荒漠生態系統碳氮儲量的間接因素。本研究中,在人工植被建立后,氣候是驅動植被向地帶性群落演替最重要的外在動力[36],決定著庫布齊沙漠碳氮儲量的終值;植物的生存策略是植被恢復演替的內在動力,植物的繁殖方式、生長規律、能量分配及植被-土壤協同作用決定了不同階段荒漠生態系統碳氮固存的速率[37],這是分別以油蒿、檸條和沙柳為建群種的固定沙地碳氮儲量存在差異的主要原因。
5 結論
庫布齊東段荒漠生態系統在植被恢復過程中,碳氮儲量具有明顯的隨植被恢復而逐漸增加的趨勢,不同恢復階段碳氮儲量差異顯著。從流動沙地逐步演變到沙柳固定沙地的過程中,地表植被蓋度和生物多樣性逐漸增大,植被層生物量和碳氮儲量亦顯著增加,其中又以灌木層為主體,草本層和凋落物層占比較小,并且灌木及草本層生物量及碳儲量的垂直空間分布特征均為地上部分高于地下。在植被恢復過程中,植物的生長及其變化影響土壤的形成和發展,改良土壤理化性質,從而增加土壤層碳氮儲量,且由于根系與土壤的交互影響及植物殘體的分解輸入,使得碳氮表層富集現象十分明顯。總體來說,荒漠生態系統通過人工建植促進植被恢復,可有效實現沙漠化逆轉,增加各組分碳氮儲量,具有較好的碳氮固存潛力,是陸地碳氮循環中重要的“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