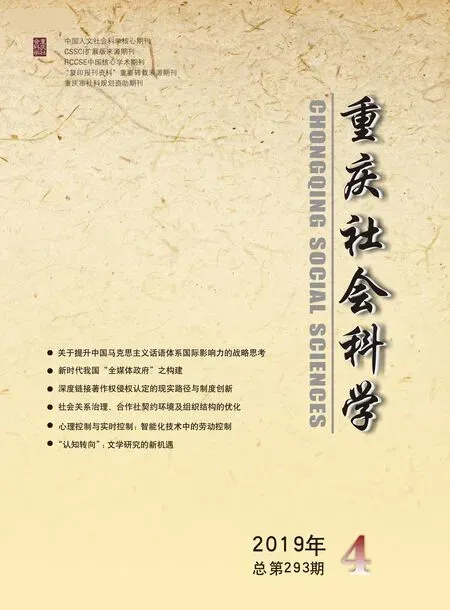深度鏈接著作權(quán)侵權(quán)認(rèn)定的現(xiàn)實(shí)路徑與制度創(chuàng)新
周 園 楊 珊
(1.西南政法大學(xué)民商法學(xué)院,重慶 401120;2.重慶理工大學(xué)重慶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學(xué)院,重慶 400054)
在互聯(lián)網(wǎng)科技廣泛應(yīng)用的當(dāng)下,司法實(shí)踐中使用新型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手段侵權(quán)的法律案件層出不窮。其中尤為引人關(guān)注的是以深度鏈接技術(shù)為代表的新型技術(shù)侵權(quán)案件不斷對(duì)我國(guó)網(wǎng)絡(luò)空間版權(quán)正版化秩序發(fā)起公然挑戰(zhàn)。由于我國(guó)目前對(duì)此尚無(wú)明確的法律規(guī)定,因而各地法院對(duì)個(gè)案判決的觀(guān)點(diǎn)不同、立場(chǎng)不一,學(xué)術(shù)界也分歧明顯、爭(zhēng)議頻現(xiàn)。故為定紛止?fàn)帲e極應(yīng)對(duì)科技發(fā)展變化對(duì)法律制度提出的挑戰(zhàn),有必要對(duì)處于持續(xù)爭(zhēng)議中的深度鏈接著作權(quán)侵權(quán)問(wèn)題進(jìn)行深入的研究。
一、深度鏈接侵權(quán)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之梳理與評(píng)議
就國(guó)外而言,針對(duì)深度鏈接涉及著作權(quán)侵權(quán)認(rèn)定,主流熱議的標(biāo)準(zhǔn)有:截然對(duì)立的“服務(wù)器標(biāo)準(zhǔn)”和“用戶(hù)感知標(biāo)準(zhǔn)”以及另辟蹊徑的“新公眾標(biāo)準(zhǔn)”。例如美國(guó)著名的“Perfect 10 訴Google 案”①See Perfect10 v.Google,416 F.Supp.2d 828,at843-844(2006),Perfect10 v.Google,508 F.3d 1146,at1160(2007).和德國(guó)經(jīng)典的“Paperboy 案”②See Paperboy,BHG,17 July 2003,IZR 259/00[2005]ECD R7.中,兩國(guó)各級(jí)法院經(jīng)歷了關(guān)于選擇“服務(wù)器標(biāo)準(zhǔn)”或“用戶(hù)感知標(biāo)準(zhǔn)”的徘徊,但最終均確定以“服務(wù)器標(biāo)準(zhǔn)”來(lái)分別判定各涉案深度鏈接行為構(gòu)成間接侵權(quán)或不侵權(quán)的結(jié)果。美國(guó)加州中區(qū)法院和第九巡回上訴法院拒絕采納“用戶(hù)感知標(biāo)準(zhǔn)”來(lái)認(rèn)定直接侵權(quán),而支持“服務(wù)器標(biāo)準(zhǔn)”認(rèn)定Google 構(gòu)成間接侵權(quán)的原因是:“用戶(hù)感知標(biāo)準(zhǔn)”忽視了網(wǎng)絡(luò)信息資源整合的技術(shù)特征,而“服務(wù)器標(biāo)準(zhǔn)”則通過(guò)嚴(yán)格區(qū)分作品是否存儲(chǔ)于服務(wù)器當(dāng)中來(lái)客觀(guān)認(rèn)定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侵權(quán)責(zé)任。德國(guó)最高法院與地區(qū)法院在判決時(shí)曾持不同意見(jiàn),但最終也選擇“服務(wù)器標(biāo)準(zhǔn)”的理由是:作品在設(shè)鏈行為之前即已存在于為公眾所可獲得的網(wǎng)絡(luò)空間內(nèi),且被鏈網(wǎng)站也并未采取合理有效的技術(shù)規(guī)避措施來(lái)防止他人的進(jìn)一步傳播,因此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深度鏈接行為作為一種互聯(lián)網(wǎng)傳播技術(shù)并未侵犯任何一項(xiàng)著作權(quán)。歐盟各國(guó)規(guī)制網(wǎng)絡(luò)作品的著作權(quán)侵權(quán)行為主要依靠“向公眾傳播權(quán)”來(lái)保護(hù)。在“Svensson 案”①See Nils Svensson,Sten Sj gren,Madelaine Sahlman and Pia Gadd v.Retriever Sverige AB,Case C-466/12.以前,歐盟各法院對(duì)此類(lèi)案件的判決也處在“服務(wù)器標(biāo)準(zhǔn)”和“用戶(hù)感知標(biāo)準(zhǔn)”兩者之間徘徊選擇的狀態(tài)。但在此案的審理過(guò)程中,歐盟法院開(kāi)創(chuàng)性地提出了“新公眾標(biāo)準(zhǔn)”來(lái)判斷深度鏈接是否涉及網(wǎng)絡(luò)版權(quán)侵權(quán)的問(wèn)題。通常情況下,深度鏈接因其技術(shù)性服務(wù)不構(gòu)成傳播行為。然而,一旦設(shè)鏈行為造成了比原網(wǎng)站能夠接觸到作品的網(wǎng)絡(luò)用戶(hù)擴(kuò)大化的后果,即假如存在作品傳播的“新公眾”時(shí),則可以認(rèn)定此時(shí)的深度鏈接行為就構(gòu)成了著作權(quán)法意義上的傳播行為,從而認(rèn)定其構(gòu)成侵權(quán)。
就國(guó)內(nèi)而言,關(guān)于深度鏈接涉及我國(gu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侵權(quán)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的理論研究發(fā)展脈絡(luò)大致可分為以下三個(gè)階段:(1)“服務(wù)器標(biāo)準(zhǔn)”與“用戶(hù)感知標(biāo)準(zhǔn)”法律適用沖突之討論;(2)“鏈接不替代標(biāo)準(zhǔn)”與“實(shí)質(zhì)呈現(xiàn)標(biāo)準(zhǔn)”不同理論視角之分析;(3)“法律標(biāo)準(zhǔn)”與“提供標(biāo)準(zhǔn)”回歸法律本質(zhì)之探索。
(一)服務(wù)器標(biāo)準(zhǔn)與用戶(hù)感知標(biāo)準(zhǔn)
“服務(wù)器標(biāo)準(zhǔn)”最早源于美國(guó)“Perfect 10 訴Google 案”,通常以是否通過(guò)上傳或其他方式將作品置于公開(kāi)的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器中從而使其能被相關(guān)公眾接觸作為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侵權(quán)與否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澳大利亞“環(huán)球音樂(lè)公司訴Cooper 案”②See Universal Music Australia Pty Ltd v Cooper[2005]FCA 97.、西班牙馬德里“Sharemula 案”③See Microsoft v.Sharemula.com ,1089/2006 28,Court of Instruction n.4 of Madrid(September 2007).、德國(guó)“Paperboy 案”隨后亦采用此標(biāo)準(zhǔn)[1]。在我國(guó),法院判斷是否侵犯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長(zhǎng)期以來(lái)同樣以“服務(wù)器標(biāo)準(zhǔn)”為主流意見(jiàn),且被多數(shù)司法實(shí)務(wù)工作者所認(rèn)可[2]。例如,在“快樂(lè)陽(yáng)光訴同方公司案”④參見(jiàn)北京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2015)京知民終字第559 號(hào)判決書(shū)。的二審判決中,北京市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曾明確將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的侵權(quán)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確立為“服務(wù)器標(biāo)準(zhǔn)”。“正東唱片訴百度案”⑤參見(jiàn)北京第一中級(jí)人民法院(2005)一中民初字第7978 號(hào)判決書(shū)。的二審判決也采用“服務(wù)器標(biāo)準(zhǔn)”判定深度鏈接僅作為技術(shù)服務(wù),并未涉及音樂(lè)作品上傳行為,故不構(gòu)成直接侵權(quán)。總而言之,國(guó)內(nèi)外法院大多采用“服務(wù)器標(biāo)準(zhǔn)”的理由是:符合技術(shù)中立規(guī)則[3]300。
“用戶(hù)感知標(biāo)準(zhǔn)”主要以普通用戶(hù)的一般感覺(jué)來(lái)判斷是否混淆了網(wǎng)絡(luò)服務(wù)的提供者和內(nèi)容的提供者。與“服務(wù)器標(biāo)準(zhǔn)”相反,它并未把提供作品的行為狹義理解為必須將作品上傳并存儲(chǔ)于服務(wù)器內(nèi),而是從用戶(hù)角度出發(fā),認(rèn)為即使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僅僅實(shí)施了設(shè)鏈行為,但只要能夠令相關(guān)網(wǎng)絡(luò)用戶(hù)誤以為獲取內(nèi)容是直接來(lái)源于設(shè)鏈網(wǎng)站,就可以認(rèn)定該網(wǎng)站未經(jīng)許可提供了作品內(nèi)容,構(gòu)成直接侵權(quán)。畢竟在上傳作品之后直到被刪除的一段時(shí)間段內(nèi),設(shè)置深度鏈接的行為已經(jīng)使得該網(wǎng)站用戶(hù)具備了獲得該作品的可能性[4]。例如:“北京三面向公司訴重慶涪陵圖書(shū)館”一案①參見(jiàn)重慶市高級(jí)人民法院(2008)渝高法民終字第146 號(hào)判決書(shū)。,重慶高院就曾以“用戶(hù)感知標(biāo)準(zhǔn)”來(lái)認(rèn)定涪陵圖書(shū)館應(yīng)當(dāng)對(duì)其設(shè)置深度鏈接行為承擔(dān)較高的注意義務(wù),從而判定其構(gòu)成侵權(quán)。
應(yīng)當(dāng)采用“服務(wù)器標(biāo)準(zhǔn)”亦或“用戶(hù)感知標(biāo)準(zhǔn)”一度在我國(guó)司法實(shí)踐過(guò)程中引發(fā)法律適用的沖突。如:“華納唱片訴世紀(jì)悅博案”②參見(jiàn)北京市高級(jí)人民法院(2004)高民終字第1303 號(hào)判決書(shū)。就出現(xiàn)過(guò)同案不同判的情況,一審和二審法院的觀(guān)點(diǎn)截然不同。客觀(guān)而言,“用戶(hù)感知標(biāo)準(zhǔn)” 因主觀(guān)成分過(guò)強(qiáng)且容易忽視用戶(hù)感知注意力和網(wǎng)絡(luò)熟識(shí)度等一些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而逐漸遭到摒棄。但是,隨著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超速發(fā)展侵權(quán)日益多樣化復(fù)雜化,“服務(wù)器標(biāo)準(zhǔn)”同樣面臨愈發(fā)難解決實(shí)際案件的法律適用問(wèn)題。正如已有學(xué)者提出質(zhì)疑,若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發(fā)展到了作品提供行為不需要經(jīng)過(guò)服務(wù)器的階段,又當(dāng)如何判斷網(wǎng)絡(luò)作品的提供行為[5]。
(二)鏈接不替代標(biāo)準(zhǔn)與實(shí)質(zhì)呈現(xiàn)標(biāo)準(zhǔn)
鑒于“服務(wù)器標(biāo)準(zhǔn)”和“用戶(hù)感知標(biāo)準(zhǔn)”在深度鏈接糾紛中法律適用的缺陷,我國(guó)司法界和學(xué)術(shù)界逐漸開(kāi)始將研究重點(diǎn)聚焦于案件事實(shí)的具體細(xì)節(jié)認(rèn)定上來(lái)。在我國(guó)首例深度鏈接著作權(quán)刑事個(gè)案“1000 影視侵犯著作權(quán)案”③參見(jiàn)上海市普陀區(qū)人民法院(2013)普刑(知)初字第11 號(hào)判決書(shū)。中,法院最終的判決從鏈接方式、服務(wù)內(nèi)容、對(duì)設(shè)鏈的影視作品的控制力以及經(jīng)濟(jì)利益等多個(gè)方面進(jìn)行了綜合考量。
此時(shí),有學(xué)者從經(jīng)濟(jì)學(xué)分析角度提出“鏈接不替代標(biāo)準(zhǔn)”。由于深度鏈接在不點(diǎn)擊被鏈網(wǎng)站作品的情況下就可以直接下載或播放作品,作品傳播利益由設(shè)鏈網(wǎng)站所竊取。社會(huì)成本大于社會(huì)收益的模式不符合經(jīng)濟(jì)效率原則,因此深度鏈接應(yīng)遵守“不替代原則”[6]。盡管這一標(biāo)準(zhǔn)為深度鏈接侵權(quán)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研究開(kāi)辟了新思路,但其僅從案件事實(shí)結(jié)果來(lái)判定侵權(quán),避開(kāi)了對(duì)涉及深度鏈接法律概念和技術(shù)細(xì)節(jié)方面的探究。故此標(biāo)準(zhǔn)僅具參考價(jià)值,難以成為確切的判定依據(jù)。
還有學(xué)者從作品傳播的具體方式角度提出“實(shí)質(zhì)呈現(xiàn)標(biāo)準(zhǔn)”。如果設(shè)鏈者通過(guò)加框鏈接將他人作品作為自己網(wǎng)頁(yè)或客戶(hù)端的一部分向用戶(hù)展示,使用戶(hù)無(wú)須訪(fǎng)問(wèn)被設(shè)鏈的網(wǎng)站,則設(shè)鏈者就應(yīng)當(dāng)被視為是作品的提供者[7]。這種無(wú)須進(jìn)入被鏈網(wǎng)站主頁(yè)即向用戶(hù)直接呈現(xiàn)他人作品內(nèi)容的行為完全符合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提供行為。其依據(jù)來(lái)源于我國(guó)《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侵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民事權(quán)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wèn)題的規(guī)定》第五條: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以提供網(wǎng)頁(yè)快照、縮略圖等方式實(shí)質(zhì)替代其他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向公眾提供相關(guān)作品的,人民法院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其構(gòu)成提供行為。因此,“實(shí)質(zhì)呈現(xiàn)標(biāo)準(zhǔn)”認(rèn)為,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行為并非僅僅是上傳作品的提供行為,還應(yīng)當(dāng)包括對(duì)作品的展示行為。若設(shè)鏈者通過(guò)深度鏈接將他人作品置于一種向相關(guān)公眾展示的狀態(tài),則設(shè)鏈者身份無(wú)疑將從“服務(wù)提供商”轉(zhuǎn)變?yōu)椤皟?nèi)容提供商”。
(三)法律標(biāo)準(zhǔn)與提供標(biāo)準(zhǔn)
隨著探討與研究的不斷深化,我國(guó)理論界觀(guān)點(diǎn)眾說(shuō)紛呈。但目前司法實(shí)踐中各法院對(duì)此卻并未形成統(tǒng)一認(rèn)識(shí),甚至各地法院裁判案件時(shí)出現(xiàn)法律適用混亂的現(xiàn)象。當(dāng)然,也有法院選擇謹(jǐn)慎采取回避態(tài)度,如“大眾點(diǎn)評(píng)網(wǎng)訴愛(ài)幫網(wǎng)系列案”④參見(jiàn)北京市第一中級(jí)人民法院(2011)一中民終字第7512 號(hào)民事判決書(shū)。在歷經(jīng)了一審、二審和再審后,最終的判決結(jié)果既未適用“服務(wù)器標(biāo)準(zhǔn)”也未采納“用戶(hù)感知標(biāo)準(zhǔn)”,反而將其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反不正當(dāng)競(jìng)爭(zhēng)法》的范圍進(jìn)行規(guī)制。因此,要求回歸法律本質(zhì)來(lái)解決司法困境的呼聲日益高漲,“法律標(biāo)準(zhǔn)”和“提供標(biāo)準(zhǔn)”隨之出現(xiàn)。
“法律標(biāo)準(zhǔn)” 認(rèn)為對(duì)深度鏈接侵權(quán)行為的判斷應(yīng)當(dāng)回歸到法律要求與事實(shí)特征相結(jié)合的標(biāo)準(zhǔn)上來(lái),凡是未經(jīng)許可行使他人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或者直接破壞權(quán)利人對(duì)其作品通過(guò)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的控制權(quán),均可構(gòu)成直接侵權(quán)行為[8]。對(duì)于是否屬于網(wǎng)絡(luò)作品提供行為,應(yīng)當(dāng)以是否構(gòu)成對(duì)著作權(quán)專(zhuān)有權(quán)的行使或者直接侵犯行為標(biāo)準(zhǔn)來(lái)進(jìn)行判斷。然而,對(duì)于深度鏈接是否構(gòu)成“提供作品”行為的具體判定,在我國(guó)現(xiàn)有法律框架下存在事實(shí)依據(jù)往往無(wú)法主導(dǎo)事實(shí)定性的問(wèn)題,仍待解決。
“提供標(biāo)準(zhǔn)”本質(zhì)上類(lèi)同于“法律標(biāo)準(zhǔn)”,但更加側(cè)重考察行為人是否實(shí)施向公眾提供權(quán)中的兩個(gè)構(gòu)成要素,即“提供行為”和“使公眾可獲得狀態(tài)”[9]。并且同時(shí)吸取“用戶(hù)感知標(biāo)準(zhǔn)”的合理成分,將用戶(hù)對(duì)作品處于可獲得狀態(tài)時(shí)的感知程度也納入判斷行為人是否提供作品的考量因素當(dāng)中。因此,在具備對(duì)涉案行為進(jìn)行侵權(quán)認(rèn)定的客觀(guān)性要件,同時(shí)主觀(guān)上也免除對(duì)具體技術(shù)細(xì)節(jié)的舉證要求的情況下,“提供標(biāo)準(zhǔn)”的法律適用的可操作性相對(duì)較強(qiáng)。
二、我國(gu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之本源回溯與檢討
(一)我國(gu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的來(lái)源背景
世界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組織《版權(quán)條約》(WCT)和《表演與錄音制品條約》(WPPT)是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探索版權(quán)保護(hù)的國(guó)際公約,其相關(guān)規(guī)定對(duì)成員國(guó)開(kāi)展網(wǎng)絡(luò)版權(quán)保護(hù)的立法和司法活動(dòng)均具有借鑒性指導(dǎo)意義。《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著作權(quán)法》(以下簡(jiǎn)稱(chēng)《著作權(quán)法》)第十條第一款第十二項(xiàng)對(duì)“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的定義①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即以有線(xiàn)或者無(wú)線(xiàn)方式向公眾提供作品,使公眾可以在其個(gè)人選定的時(shí)間和地點(diǎn)獲得作品的權(quán)利。主要是借鑒WCT 第八條②據(jù)世界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組織官網(wǎng)下載相關(guān)官方文件來(lái)看,其中文版本為:“第8 條——向公眾傳播的權(quán)利,文學(xué)和藝術(shù)作品的作者應(yīng)享有專(zhuān)有權(quán),以授權(quán)將其作品以有線(xiàn)或無(wú)線(xiàn)方式向公眾傳播,包括將其作品向公眾提供,使公眾中的成員在其個(gè)人選定的地點(diǎn)和時(shí)間可獲得這些作品。”其英文版表述為:“Article 8——Righ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authors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shall enjoy the exclusive right of authorizing any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of their works,by wire or wireless means,including the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of their works in such a way that members of the public may access these works from a place and at a time individually chosen by them.”對(duì)“向公眾傳播權(quán)”的相關(guān)表述。有學(xué)者將此條規(guī)定劃分為兩部分,認(rèn)為前半部分規(guī)定的是廣義的“向公眾傳播權(quán)”,后半部分規(guī)定的是狹義的“向公眾提供權(quán)”[10]。由此可見(jiàn),我國(gu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的來(lái)源是WCT 第八條后半部分有關(guān)“向公眾提供權(quán)”的表述。
由于WCT 第八條通過(guò)“傘形解決方案”進(jìn)行國(guó)際協(xié)調(diào),對(duì)成員國(guó)在線(xiàn)“向公眾提供”作品的權(quán)利僅提出最低限度要求,并不限定各國(guó)在此基礎(chǔ)上提供更高程度的保護(hù)[11]。當(dāng)前我國(guó)現(xiàn)行法律對(duì)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的保護(hù)除了上文提到《著作權(quán)法》定義式的概括規(guī)定,還有《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保護(hù)條例》(下文簡(jiǎn)稱(chēng)《條例》)及《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侵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wèn)題的規(guī)定》(下文簡(jiǎn)稱(chēng)《規(guī)定》)。其中《規(guī)定》第三條第二款對(duì)“提供行為”的解釋為:“通過(guò)上傳到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器、設(shè)置共享文件或者利用文件分享軟件等方式,將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置于信息網(wǎng)絡(luò)中,使公眾能夠在個(gè)人選定的時(shí)間和地點(diǎn)以下載、瀏覽或者其他方式獲得的,人民法院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其實(shí)施了前款規(guī)定的提供行為。”此處“提供行為”被狹義解釋為通過(guò)“上傳”或“以其他方式將作品置于信息網(wǎng)絡(luò)中”。這是“服務(wù)器標(biāo)準(zhǔn)”在我國(guó)司法實(shí)踐中作為主流標(biāo)準(zhǔn)長(zhǎng)期立足的根源。但是,從WCT 第八條中英文譯本的對(duì)比來(lái)看,我國(guó)對(duì)“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定義并未完全涵蓋WCT 第八條中前半部分對(duì)作者享有的“向公眾傳播”的權(quán)利。WCT“向公眾傳播權(quán)”設(shè)立的目的在于使得作品能夠?yàn)椴淮_定的多數(shù)人所了解和感知,而我國(guó)僅僅借鑒吸收狹義的“向公眾提供權(quán)”,難免出現(xiàn)對(duì)“向公眾傳播權(quán)”保護(hù)范圍理解的狹窄化。
(二)對(duì)“傳播”“提供”等關(guān)鍵術(shù)語(yǔ)的語(yǔ)義質(zhì)疑
我國(guó)借鑒國(guó)際條約進(jìn)行法律保護(hù)時(shí),應(yīng)當(dāng)對(duì)條文中關(guān)鍵術(shù)語(yǔ)表達(dá)的語(yǔ)義理解和翻譯精準(zhǔn)度高度重視。在追溯我國(gu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與WCT 向公眾傳播權(quán)本質(zhì)內(nèi)涵聯(lián)系的過(guò)程中發(fā)現(xiàn),關(guān)于“傳播”“傳輸”“提供”“展示”等幾個(gè)對(duì)法條含義理解起關(guān)鍵作用的術(shù)語(yǔ)表達(dá),我國(guó)從翻譯轉(zhuǎn)化角度而言并未清晰界定,導(dǎo)致其語(yǔ)義常常處于被混淆理解、混雜使用的狀態(tài)。
因《伯爾尼公約》最后一次修訂所處的時(shí)間仍是互聯(lián)網(wǎng)萌芽階段,該公約更關(guān)注復(fù)制權(quán)和發(fā)行權(quán)的問(wèn)題,對(duì)傳播權(quán)的相關(guān)界定并沒(méi)有形成統(tǒng)一觀(guān)點(diǎn)。實(shí)際上WCT 第八條“向公眾傳播權(quán)”立法初衷在于通過(guò)建立一個(gè)廣泛的傳播權(quán)來(lái)應(yīng)對(duì)互聯(lián)網(wǎng)數(shù)字技術(shù)的挑戰(zhàn)。作為對(duì)作者十分重要的一項(xiàng)著作權(quán)經(jīng)濟(jì)權(quán),傳播權(quán)應(yīng)當(dāng)是由表演權(quán)、放映權(quán)、廣播權(quán)等多項(xiàng)權(quán)能共同構(gòu)成的一個(gè)權(quán)利群。例如,德國(guó)的“公開(kāi)再現(xiàn)權(quán)”就是典型的廣義傳播權(quán)①德國(guó)的公開(kāi)再現(xiàn)權(quán)包括:朗誦權(quán)、放映權(quán)、表演權(quán)等。參見(jiàn)《十二國(guó)著作權(quán)法》。。由于我國(guó)現(xiàn)行《著作權(quán)法》對(duì)表演權(quán)、放映權(quán)和廣播權(quán)等進(jìn)行細(xì)致的分類(lèi)保護(hù),暫時(shí)并不存在一個(gè)囊括所有傳播行為的廣義傳播權(quán)。但是,在借鑒使用WCT 第八條構(gòu)建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時(shí),我國(guó)卻沒(méi)有注意到這一點(diǎn),未能充分考慮與國(guó)內(nèi)著作權(quán)體系的協(xié)調(diào)問(wèn)題。可見(jiàn),在借鑒WCT 第八條后半部分有關(guān)“向公眾提供權(quán)”時(shí)直接將其移植并翻譯為“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的做法實(shí)在有些欠妥,亦造成了之后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在我國(guó)司法解釋和適用過(guò)程中與廣播權(quán)等其他著作權(quán)專(zhuān)項(xiàng)權(quán)利不斷發(fā)生沖突和混淆。正如有學(xué)者考察伯爾尼公約各種語(yǔ)言的譯本后,提出我國(gu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當(dāng)中的“傳播”其實(shí)應(yīng)被理解為一種以技術(shù)手段向不在傳播發(fā)生地公眾的“傳輸”[10]。因此,關(guān)于我國(gu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這一命名本身就值得再度審視與探討。
此外,關(guān)于WCT 第八條中“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向公眾提供權(quán))的具體表述,事實(shí)上同樣存在翻譯轉(zhuǎn)化和語(yǔ)義理解混淆的問(wèn)題。從英文直譯來(lái)看,“making available” 強(qiáng)調(diào)一種使作品處于能夠被公眾“獲取”的“狀態(tài)”。首先,將這種“可獲取的狀態(tài)”對(duì)應(yīng)中文翻譯為“提供行為”,在專(zhuān)業(yè)術(shù)語(yǔ)對(duì)應(yīng)轉(zhuǎn)化的精確度方面尚且存疑。其次,在權(quán)利保護(hù)范圍的理解與解釋上,可獲取的“狀態(tài)”與提供“行為”之間顯然并非完全吻合。退言之,即使“提供權(quán)”已在國(guó)內(nèi)外司法學(xué)術(shù)界對(duì)公眾“可獲取”作品形成一種固定聯(lián)系表達(dá)。對(duì)于“提供”一詞的范圍理解也并非僅局限于前文所述我國(guó)《規(guī)定》“上傳”至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器的唯一樣態(tài)。因此,若回歸“making available”本質(zhì)內(nèi)涵,從“可獲取”角度來(lái)理解“提供行為”,勢(shì)必需要做出擴(kuò)大化的解釋。
(三)對(duì)“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行為”與“提供作品行為”的反思與檢討
深度鏈接行為引發(fā)我國(guó)司法界與學(xué)術(shù)界對(duì)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侵權(quán)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爭(zhēng)論的焦點(diǎn)在其法律屬性是否可以確立為“提供作品”的“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行為”。基于上文對(duì)WCT 第八條原文及相關(guān)術(shù)語(yǔ)的具體分析,探究我國(gu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的立法原意,應(yīng)當(dāng)是傾向于對(duì)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中通過(guò)“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行為”“向公眾提供作品”的著作權(quán)專(zhuān)有權(quán)提供一種類(lèi)似廣義傳播權(quán)的更為寬泛的保護(hù),以此來(lái)回應(yīng)數(shù)字化時(shí)代帶來(lái)的各種技術(shù)挑戰(zhàn)。
按照傳統(tǒng)“服務(wù)器標(biāo)準(zhǔn)”來(lái)解釋?zhuān)瑢?duì)數(shù)字作品的網(wǎng)絡(luò)基本傳播方式可以抽象概括為如模型1所示“上傳—鏈接—下載”的固定模型(見(jiàn)圖1)。在這種單線(xiàn)傳輸?shù)哪J较拢挥袑⒆髌吠ㄟ^(guò)“上傳”或“其他方式”置于向公眾開(kāi)放的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器當(dāng)中,才能構(gòu)成作品的“提供行為”,從而可以劃歸為法律規(guī)制的“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行為”。這種解釋對(duì)當(dāng)時(shí)嚴(yán)重依賴(lài)以服務(wù)器作為基礎(chǔ)物理?xiàng)l件的互聯(lián)網(wǎng)傳輸技術(shù)而言似乎并無(wú)不妥,因?yàn)槿魶](méi)有上傳行為,則后續(xù)數(shù)據(jù)傳輸都將無(wú)法進(jìn)行,故而中間的鏈接技術(shù)可以因其信息通道的純技術(shù)屬性而獲得免責(zé)。“上傳”這一要素似乎對(duì)于使作品最終處于“可獲取”狀態(tài)起到了唯一決定性的作用。然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上傳”行為僅僅是整個(gè)傳播過(guò)程的起點(diǎn),即“初始提供行為”或“首發(fā)傳播”。而中間的“鏈接”行為事實(shí)上體現(xiàn)為幫助作品處于“可獲取狀態(tài)”的進(jìn)一步傳播的效果,即“二次提供行為”或“繼發(fā)傳播”。如今數(shù)字傳播技術(shù)不斷發(fā)展的情形下,如模型2(見(jiàn)圖1)所顯示:首先,信源通過(guò)編碼形成信息,信息進(jìn)入信道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其次,信道技術(shù)包括鏈接在內(nèi)等傳輸方式正逐步實(shí)現(xiàn)與受眾的接收方式多樣化同步融合的狀態(tài)。由此可以看出,“上傳”行為已不再是對(duì)作品“可獲取”狀態(tài)起唯一決定性影響的要素。結(jié)合模型1 和模型2 的傳播進(jìn)程與方式的對(duì)比,深度鏈接技術(shù)中直接展現(xiàn)作品內(nèi)容的技術(shù)效果令人不得不重新審視上述模型1 中“鏈接”行為是否仍存在技術(shù)中立免責(zé)的現(xiàn)實(shí)基礎(chǔ)。按照模型2 中受眾獲取信息的多樣化方式來(lái)看,此時(shí)的“鏈接”方式對(duì)使作品處于“可獲取”狀態(tài)發(fā)揮越來(lái)越重要的作用,甚至有可能在未來(lái)直接取代“上傳”行為。因此,“提供”行為不僅涵蓋“上傳”等仍需借助物理?xiàng)l件完成的數(shù)字化復(fù)制行為,還應(yīng)包括但不限于“展示”等僅需通過(guò)虛擬管道就可以完成的數(shù)字化再現(xiàn)行為。
事實(shí)上,除前文所提到的《規(guī)定》中第三條第二款對(duì)網(wǎng)絡(luò)傳播“提供行為”進(jìn)行具體方式列舉,我國(guó)《著作權(quán)法》和《條例》中均未對(duì)“提供行為”做出任何明確的解釋。結(jié)合前文對(duì)立法原意的探索與思考,對(duì)我國(gu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行為”和“提供作品行為”的司法解釋和適用時(shí)在應(yīng)作擴(kuò)大化考慮。反觀(guān)當(dāng)前,我國(guó)對(duì)“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行為”和“提供作品行為”的法律理解和適用的主流觀(guān)點(diǎn)仍趨于“服務(wù)器標(biāo)準(zhǔn)”狹義化的解讀方式,未免有些保守滯后。可以預(yù)見(jiàn),服務(wù)器標(biāo)準(zhǔn)再難成為網(wǎng)絡(luò)著作權(quán)侵權(quán)認(rèn)定的唯一正確標(biāo)準(zhǔn)。而諸如“實(shí)質(zhì)呈現(xiàn)標(biāo)準(zhǔn)”和“提供標(biāo)準(zhǔn)”等順應(yīng)技術(shù)發(fā)展變化而不斷涌現(xiàn)的具有開(kāi)拓創(chuàng)新的觀(guān)點(diǎn),確實(shí)具有得到不斷實(shí)踐與論證的必要。

圖1 數(shù)字傳播模型示意圖
三、深度鏈接行為法律屬性和侵權(quán)責(zé)任的認(rèn)定
(一)深度鏈接“展示作品內(nèi)容”應(yīng)當(dāng)定性為“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行為”
正確界定“網(wǎng)絡(luò)傳播行為”是認(rèn)定構(gòu)成著作權(quán)直接侵權(quán)行為的前提條件[12]。但技術(shù)層面的鏈接技術(shù)和法律層面的鏈接服務(wù)并非同一概念[13]。因此,并非只要使用鏈接功能的技術(shù)就都可認(rèn)定為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服務(wù)商,從而適用技術(shù)中立原則來(lái)免責(zé)。著作權(quán)法上判斷某一行為究竟是單純提供管道服務(wù)行為還是內(nèi)容提供行為的經(jīng)驗(yàn)性規(guī)則,即看相關(guān)公眾接受該服務(wù)的目的是獲取特定著作權(quán)內(nèi)容,還是只是接受非內(nèi)容服務(wù)(比如存儲(chǔ)、信息定位、內(nèi)容發(fā)布等)[14]。將作品以上傳或以其他方式置于網(wǎng)絡(luò)空間之中,只是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過(guò)程中的第一步。事實(shí)上,直至讀者用戶(hù)獲取信息資源或作品內(nèi)容時(shí),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行為才真正結(jié)束。因此,除了狹義“提供作品”中“上傳”行為之外,應(yīng)當(dāng)認(rèn)為其他能實(shí)現(xiàn)網(wǎng)絡(luò)信息傳播目的的行為方式同樣也構(gòu)成“網(wǎng)絡(luò)傳播行為”。因此,深度鏈接行為雖然沒(méi)有涉及作品的“上傳行為”,但卻涉及作品的“內(nèi)容展示”,并且對(duì)使作品處于“可獲取”狀態(tài)發(fā)揮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故其法律屬性顯然不能僅被簡(jiǎn)單界定為提供搜索鏈接的技術(shù)服務(wù)。
如同前文所述,“繼發(fā)傳播”也是構(gòu)成“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行為”的一部分,“二次提供行為”若能實(shí)現(xiàn)使作品處于公眾“可獲取狀態(tài)”也是“提供行為”。深度鏈接行為“展示他人作品”的實(shí)際效果和損害后果已經(jīng)達(dá)到了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含義下與“初始提供”相同的侵權(quán)標(biāo)準(zhǔn)。因此,對(duì)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提供作品”進(jìn)行擴(kuò)大化解釋?zhuān)疃孺溄拥姆蓪傩詰?yīng)認(rèn)定其為對(duì)作品“提供內(nèi)容展示”的一種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行為。
(二)深度鏈接應(yīng)當(dāng)優(yōu)先適用“實(shí)質(zhì)呈現(xiàn)標(biāo)準(zhǔn)”認(rèn)定為直接侵權(quán)行為
世界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組織的互聯(lián)網(wǎng)條約(包括WCT 和WPPT)都只是從版權(quán)的權(quán)利與限制角度進(jìn)行了規(guī)定,并未涉及侵權(quán)責(zé)任問(wèn)題。因?yàn)樨?zé)任問(wèn)題復(fù)雜,需要在充分了解各國(guó)大量成文法和判例法之后,才能夠?qū)€(gè)案作出正確判斷,因此,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領(lǐng)域的國(guó)際條約都沒(méi)有對(duì)責(zé)任問(wèn)題作出規(guī)定[3]127。而我國(guó)網(wǎng)絡(luò)版權(quán)侵權(quán)責(zé)任制度比較復(fù)雜,一個(gè)重要原因是我國(guó)民商事侵權(quán)責(zé)任制度比較混亂[15]。盡管我國(guó)并沒(méi)有在任何正式的法律條文中明確地提出對(duì)直接侵權(quán)和間接侵權(quán)的制度設(shè)計(jì),但在一些司法解釋和司法實(shí)踐中,間接侵權(quán)責(zé)任認(rèn)定已經(jīng)被廣泛借鑒并運(yùn)用。例如:在上述《規(guī)定》中,在區(qū)分“提供行為”和“教唆、幫助行為”的基礎(chǔ)上,其實(shí)已經(jīng)相應(yīng)規(guī)定了直接侵權(quán)責(zé)任和間接侵權(quán)責(zé)任的判定①該規(guī)定第四、五、六條規(guī)定了提供行為構(gòu)成的直接侵權(quán)行為,而第七條則規(guī)定了教唆幫助行為構(gòu)成的間接侵權(quán)行為。。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在網(wǎng)絡(luò)著作權(quán)中較為寬泛地引進(jìn)間接責(zé)任能夠拓展著作權(quán)保護(hù)范圍,強(qiáng)化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中間人”的責(zé)任意識(shí),使其對(duì)所傳播信息內(nèi)容持相對(duì)謹(jǐn)慎的態(tài)度,特別是將其運(yùn)用于技術(shù)創(chuàng)新商業(yè)模式等互聯(lián)網(wǎng)經(jīng)營(yíng)行為中時(shí),更多去考慮著作權(quán)人的利益[3]126。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以英國(guó)、美國(guó)、日本判例為基礎(chǔ)構(gòu)建的著作權(quán)“間接侵權(quán)”理論存在一定的弊端,且缺乏與我國(guó)侵權(quán)責(zé)任法當(dāng)中關(guān)于共同侵權(quán)制度之間的溝通與縫合機(jī)制,因而也有學(xué)者提出,我國(guó)日趨完善的民事共同侵權(quán)制度之下,著作權(quán)間接侵權(quán)并無(wú)共存的必要和平臺(tái),應(yīng)當(dāng)構(gòu)建著作權(quán)共同侵權(quán)規(guī)則以化解“間接侵權(quán)”之困境[16]。
由于網(wǎng)絡(luò)著作權(quán)侵權(quán)責(zé)任認(rèn)定的復(fù)雜性,因此對(duì)深度鏈接行為侵權(quán)責(zé)任認(rèn)定問(wèn)題的探討反而更應(yīng)當(dāng)回歸到著作權(quán)侵權(quán)認(rèn)定的法律本質(zhì)上來(lái)。著作權(quán)保護(hù)的權(quán)利客體是作品,在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下,對(duì)作品的控制行為自然就成為權(quán)利保護(hù)的核心內(nèi)容。與之相對(duì),追究其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的侵權(quán)責(zé)任就是要看其是否實(shí)施破壞權(quán)利人對(duì)作品控制的行為,即“未經(jīng)授權(quán)許可”的“作品提供行為”。因此,深度鏈接侵權(quán)責(zé)任認(rèn)定的本質(zhì)也就在于清晰地厘定作品“提供行為”主體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的責(zé)任與義務(wù)。以“服務(wù)器標(biāo)準(zhǔn)”和“實(shí)質(zhì)呈現(xiàn)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比較而言,二者對(duì)“提供行為”范圍界定的差異決定了侵權(quán)責(zé)任主體、類(lèi)型的不同,同時(shí)也導(dǎo)致侵權(quán)責(zé)任分配的偏差。“服務(wù)器標(biāo)準(zhǔn)”將“提供行為”界定為“上傳行為”,實(shí)際上是將直接侵權(quán)責(zé)任人確定為通過(guò)物理?xiàng)l件完成對(duì)作品數(shù)字化復(fù)制行為的個(gè)體,而使用深度鏈接技術(shù)的網(wǎng)站,作為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商僅負(fù)有“法定注意審查義務(wù)”和《條例》所規(guī)定的“通知—?jiǎng)h除”責(zé)任。即使其主觀(guān)上存在過(guò)錯(cuò)或是合謀的意圖,也只能通過(guò)間接侵權(quán)、幫助侵權(quán)或是共同侵權(quán)來(lái)判定其責(zé)任。而“實(shí)質(zhì)呈現(xiàn)標(biāo)準(zhǔn)”其實(shí)是將“提供行為”擴(kuò)大至公眾“可獲取”作品的“展示行為”,也就是認(rèn)為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商已轉(zhuǎn)變?yōu)閮?nèi)容服務(wù)提供商,因而可以毫無(wú)疑問(wèn)地追究其作為直接侵權(quán)行為人的法律責(zé)任。
“傳播源”理論是“服務(wù)器標(biāo)準(zhǔn)”作為網(wǎng)絡(luò)直接侵權(quán)判定標(biāo)準(zhǔn)的基礎(chǔ)理論[10]。但在當(dāng)今互聯(lián)網(wǎng)數(shù)字模式下,快捷的傳播方式和低廉的傳播成本造成“傳播源”不再固定,作者對(duì)作品的控制能力逐漸下降,作品的流通逐步由以作者為中心轉(zhuǎn)變?yōu)橐宰x者為中心,著作權(quán)的保護(hù)重點(diǎn)也開(kāi)始由對(duì)作品的復(fù)制權(quán)轉(zhuǎn)向接觸權(quán)[17]。互聯(lián)網(wǎng)架構(gòu)的特性之一是“去中心化”。質(zhì)言之,互聯(lián)網(wǎng)只關(guān)心最終的效果,即把數(shù)據(jù)送達(dá)目的地,而不關(guān)心過(guò)程,即從哪條道路將數(shù)據(jù)送到[18]39。且互聯(lián)網(wǎng)中傳播權(quán)所控制的“傳播行為”是以不轉(zhuǎn)移作品有形載體的無(wú)形方式向公眾提供作品,使公眾在不占有“文本”的情況獲得和欣賞作品[19]。若按“服務(wù)器標(biāo)準(zhǔn)”僅將網(wǎng)絡(luò)傳播的“提供行為”局限于“上傳”等與數(shù)字化復(fù)制相關(guān)的形式中,則不僅會(huì)造成難以向多個(gè)不特定主體追究直接侵權(quán)責(zé)任的問(wèn)題,還容易加大對(duì)間接或幫助侵權(quán)責(zé)任主體的追責(zé)難度。“服務(wù)器標(biāo)準(zhǔn)”在客觀(guān)上弱化了對(duì)于提供深度鏈接技術(shù)的名為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商實(shí)為內(nèi)容服務(wù)提供商的責(zé)任主體的法律責(zé)任與義務(wù),且容易通過(guò)技術(shù)中立原則為其尋求開(kāi)脫責(zé)任的法律適用空隙。面臨著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下著作權(quán)人因控制作品能力弱化而加強(qiáng)對(duì)經(jīng)濟(jì)權(quán)利擴(kuò)張的訴求,“服務(wù)器標(biāo)準(zhǔn)”顯然無(wú)法滿(mǎn)足。而“實(shí)質(zhì)呈現(xiàn)標(biāo)準(zhǔn)”則擴(kuò)寬了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對(duì)作品“提供行為”范圍,將“內(nèi)容展示”同樣劃入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行為當(dāng)中,為技術(shù)發(fā)展導(dǎo)致的更多新型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侵權(quán)方式認(rèn)定預(yù)留了空間,使其能夠被包含和規(guī)制進(jìn)入網(wǎng)絡(luò)著作權(quán)侵權(quán)認(rèn)定領(lǐng)域,故而具備優(yōu)先適用的合理理由。
四、深度鏈接行為立法規(guī)制道路之開(kāi)創(chuàng)性探索
由于我國(guó)目前法律規(guī)定之中并未對(duì)深度鏈接行為作出明確定性,故在現(xiàn)有法律框架下,采納“實(shí)質(zhì)呈現(xiàn)標(biāo)準(zhǔn)”對(duì)深度鏈接造成的網(wǎng)絡(luò)著作權(quán)侵權(quán)行為進(jìn)行擴(kuò)大化解釋與適用是可行之法。但若忽視我國(gu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的現(xiàn)有制度缺陷,將無(wú)法應(yīng)對(duì)未來(lái)新技術(shù)發(fā)展帶來(lái)的新問(wèn)題。因此,以深度鏈接引發(fā)的著作權(quán)侵權(quán)認(rèn)定問(wèn)題作為突破口,正是對(duì)我國(gu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進(jìn)行立法完善的良機(jī)。
(一)我國(gu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存在的立法缺陷
前文回溯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立法淵源和分析我國(guó)網(wǎng)絡(luò)版權(quán)侵權(quán)責(zé)任認(rèn)定的過(guò)程中,發(fā)現(xiàn)當(dāng)前我國(guó)基于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保護(hù)網(wǎng)絡(luò)著作權(quán)的法律制度仍不夠完善,存在以下兩個(gè)方面的缺陷。
第一,對(duì)WCT 國(guó)際條約進(jìn)行借鑒移植,存在與我國(guó)法律體系不協(xié)調(diào)的問(wèn)題。我國(gu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來(lái)源于WCT 第八條,但并未完全吸收其進(jìn)行寬泛意義上對(duì)廣義傳播權(quán)的表述,實(shí)際上僅僅是對(duì)其后半部分關(guān)于向公眾提供權(quán)定義的移植。這導(dǎo)致我國(gu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在規(guī)制作品的網(wǎng)絡(luò)傳播侵權(quán)行為時(shí)處于有名無(wú)實(shí)的尷尬之境。另外,我國(guó)對(duì)“提供作品行為”與國(guó)際社會(huì)“使公眾可獲取作品狀態(tài)”之間的理解偏差還容易造成法律適用選擇沖突。
第二,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侵權(quán)責(zé)任認(rèn)定體系不夠清晰確定的問(wèn)題。目前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實(shí)際把我國(guó)侵權(quán)法上所沒(méi)有明確的“間接侵權(quán)”(或者說(shuō)是“幫助性侵權(quán)”)的問(wèn)題進(jìn)行了一些規(guī)定,但這種規(guī)定仍不夠明確。盡管目前我國(guó)也在嘗試構(gòu)建更為清晰的網(wǎng)絡(luò)著作權(quán)侵權(quán)責(zé)任認(rèn)定體系,但由于難以厘定和傳統(tǒng)著作權(quán)侵權(quán)之間的聯(lián)系和差異,因而仍處于研究探索之中。
(二)創(chuàng)設(shè)“信息網(wǎng)絡(luò)提供權(quán)”的立法構(gòu)想
著作財(cái)產(chǎn)權(quán)內(nèi)容頻繁變動(dòng)反映出過(guò)度依賴(lài)傳播技術(shù)的立法模式和傳播方式層出不窮的現(xiàn)實(shí)之間的深刻矛盾[20]。從長(zhǎng)遠(yuǎn)發(fā)展來(lái)看,法律制度保護(hù)應(yīng)當(dāng)適當(dāng)削弱權(quán)利內(nèi)容對(duì)技術(shù)的依賴(lài)度,例如有學(xué)者提出依據(jù)“作品使用行為構(gòu)成的獨(dú)立市場(chǎng)”來(lái)確定權(quán)項(xiàng)[21],或者簡(jiǎn)化權(quán)利體系去嘗試構(gòu)建“大傳播權(quán)”[22]。然而,因我國(guó)著作權(quán)立法條件尚不成熟等緣由,對(duì)廣義傳播權(quán)的重塑之事仍需審慎研究。故從眼前規(guī)制出發(fā),可以基于現(xiàn)有法律規(guī)定,優(yōu)先考慮采納“實(shí)質(zhì)呈現(xiàn)標(biāo)準(zhǔn)”并逐步擴(kuò)大其權(quán)限范圍,而后徐徐圖之。除此之外,本文認(rèn)為還可參考WCT“向公眾提供權(quán)”的概念重新定義現(xiàn)行“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通過(guò)創(chuàng)設(shè)“信息網(wǎng)絡(luò)提供權(quán)”的立法途徑來(lái)完善當(dāng)前的制度漏洞。
如前文對(duì)WCT 第八條“向公眾傳播權(quán)”的回溯分析所述,我國(gu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提法的合理性本身尚有存疑之處。由其后半部分“向公眾提供權(quán)”轉(zhuǎn)換為我國(guó)所對(duì)應(yīng)的合理表述應(yīng)當(dāng)是“信息網(wǎng)絡(luò)提供權(quán)”。因此,重新創(chuàng)設(shè)“信息網(wǎng)絡(luò)提供權(quán)”既可區(qū)別于我國(guó)已有的其他傳播權(quán)具體專(zhuān)項(xiàng)權(quán)能,有利于正本清源,肅清在法律解釋和理解過(guò)程中可能造成的各種混淆與沖突,同時(shí)又能夠在充分結(jié)合立法原意的基礎(chǔ)上,重新審視在網(wǎng)絡(luò)作品傳播過(guò)程中對(duì)于“提供行為”的具體規(guī)定,有利于明晰網(wǎng)絡(luò)著作權(quán)的保護(hù)范圍,規(guī)制新型互聯(lián)網(wǎng)著作權(quán)侵權(quán)行為。本文此處提出創(chuàng)設(shè)“信息網(wǎng)絡(luò)提供”之立法構(gòu)想來(lái)探索我國(guó)網(wǎng)絡(luò)著作權(quán)侵權(quán)的規(guī)制之道,事實(shí)上亦是回歸著作權(quán)侵權(quán)的法律本質(zhì)內(nèi)涵,即試圖規(guī)制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各主體是否未經(jīng)著作權(quán)人授權(quán)許可就向網(wǎng)絡(luò)公眾提供作品,使之處于隨時(shí)可以被獲取的狀態(tài)。此處對(duì)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下的“提供行為”進(jìn)行擴(kuò)大解釋?zhuān)笃洳粌H能夠涵蓋“上傳”等仍需借助物理?xiàng)l件完成的數(shù)字化復(fù)制行為,還要囊括類(lèi)似深度鏈接等技術(shù)可實(shí)現(xiàn)“展示”等只需通過(guò)虛擬管道即可完成的數(shù)字化再現(xiàn)行為。由此才能將以深度鏈接為代表性的名為技術(shù)實(shí)為侵權(quán)的一類(lèi)信息網(wǎng)絡(luò)提供行為納入網(wǎng)絡(luò)版權(quán)保護(hù)的法律規(guī)制當(dāng)中。
當(dāng)然,關(guān)于這種擴(kuò)大化保護(hù)可能帶來(lái)的權(quán)利擴(kuò)張,同時(shí)還需構(gòu)建合理使用等抗辯來(lái)進(jìn)行約束限制,從而適當(dāng)平衡權(quán)利擴(kuò)大化的濫用風(fēng)險(xiǎn)。正如美國(guó)最高法院Camphell 訴Acuff-Rose Music 案中曾指出著作權(quán)保護(hù)中設(shè)立合理使用制度的最初目的就是促進(jìn)科學(xué)進(jìn)步及有益文化[23]。所以當(dāng)設(shè)鏈網(wǎng)站是出于純粹公益目的(如在線(xiàn)教育、公共數(shù)字圖書(shū)館等情況)時(shí),則可以援引合理使用來(lái)作為抗辯事由。
五、結(jié)語(yǔ)
著作權(quán)的演變和擴(kuò)張以及權(quán)利的限制和例外,往往是由于技術(shù)的發(fā)展進(jìn)步而不斷推動(dòng)[24]。自印刷技術(shù)時(shí)代、電子技術(shù)時(shí)代直到當(dāng)今的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時(shí)代,作品傳播方式不斷發(fā)展,對(duì)著作權(quán)的保護(hù)也從“書(shū)面復(fù)制”走向“數(shù)字傳播”。深度鏈接本身并無(wú)復(fù)雜之處,只是恰逢當(dāng)今網(wǎng)絡(luò)信息時(shí)代,此類(lèi)新型快捷的傳播技術(shù)被充分開(kāi)發(fā)利用,直接打破了著作權(quán)人、設(shè)鏈網(wǎng)站、被鏈網(wǎng)站和網(wǎng)絡(luò)用戶(hù)之間的利益格局,從而導(dǎo)致網(wǎng)絡(luò)著作權(quán)侵權(quán)案件頻發(fā),急需合理規(guī)制之道。
“法律真正的益處在于它確保有序的平衡,而這種平衡能成功地預(yù)防糾紛。”[25]目前正值我國(guó)著作權(quán)法第三次修訂之際,也是解決法律滯后性問(wèn)題和填補(bǔ)制度漏洞的大好時(shí)機(jī)。深度鏈接等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所帶來(lái)的著作權(quán)侵權(quán)問(wèn)題,理應(yīng)被納入著作權(quán)法的調(diào)整范疇之內(nèi)。正如美國(guó)學(xué)者拉爾夫·歐曼所言:“信奉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擁護(hù)伯爾尼公約宗旨的人們,不應(yīng)將我們的工作看作是為數(shù)字市場(chǎng)的未來(lái)籌劃新的法規(guī),而是應(yīng)努力尋求途徑,將數(shù)字環(huán)境至于作者的控制之下。”[19]66因此,通過(guò)創(chuàng)設(shè)“信息網(wǎng)絡(luò)提供權(quán)”能夠拓寬我國(guó)現(xiàn)有著作權(quán)權(quán)利保護(hù)范圍,適當(dāng)削弱權(quán)利內(nèi)容對(duì)于技術(shù)的依賴(lài),從而實(shí)現(xiàn)網(wǎng)絡(luò)版權(quán)市場(chǎng)各方主體間的利益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