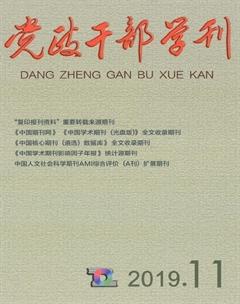多元決定與激進多元民主
彭小杰
[摘? 要]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論”和拉克勞、墨菲“激進多元民主”是西方馬克思主義陣營中兩股重要的多元話語思潮。它們之間存在復雜且隱晦的關聯,梳理兩種多元理論的詮釋進路,不難發現,兩者主要表現為方法論分歧、“多元”內涵的異質性及其處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不同,而保衛馬克思與貶斥主體性是它們共同的表征。全面科學地把握兩者的聯系與區別,旨在深化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與研究,以期更好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也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多元決定;激進多元民主;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解構主義
[中圖分類號]A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9)11-0019-05
阿爾都塞是法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和“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學派的奠基人物,其思想在國內外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產生了巨大又深遠的影響。而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直接催生了拉克勞、墨菲(下文簡稱拉墨)“激進多元民主”的萌芽,成為拉墨建構“后馬克思主義”(自我標榜)的重要理論源泉,并對后現代性的開啟也產生深刻影響。對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與拉墨的”激進多元民主”進行比較研究,全面科學地把握兩者的聯系與區別,旨在深化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與研究,以期更好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一、多元決定與激進多元民主的相同點
阿爾都塞“多元決定”思想是拉墨建構以“激進多元民主”為核心的新社會主義策略的重要理論源泉。拉墨的“激進多元民主”直接繼承了“多元決定”的某些理論特質,與阿爾都塞“多元決定”理論典型地表征出保衛馬克思和貶斥主體性。
1.保衛馬克思。阿爾都塞和拉墨雖然運用不同的方法重新解讀馬克思主義理論,但是,他們都基于同一目標指向:保衛馬克思,完善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增強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真理性,使馬克思主義理論更好地指導實踐。
阿爾都塞曾指出:“要是沒有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以及后來的自由化,我永遠不會寫任何東西”[1]4。針對當時出現的教條主義和蘇共二十大以后泛濫的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潮,阿爾都塞認為,馬克思主義受到了非科學化的規定,馬克思主義已面臨嚴重的危機,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有必要對這種理論形勢和政治局勢實行干預。他豪情壯志地提出:“保衛馬克思”。“多元決定”思想也正是在這種干預下的結果。基于理論形勢和政治局勢的促逼,阿爾都塞重新“癥候”馬克思原著,試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作一個科學的解釋和規范,肅清那些歪曲馬克思主義的非科學化思想。
馬克思主義理論在解釋后工業引發的新問題上一度失靈。拉墨認為,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社會主義策略在反對資本主義中業已失去原有的效力。為了解除馬克思主義面臨的危機,他試圖構建激進多元民主的新政治規劃藍圖,給左翼政治斗爭提供新的革命方案,最終達及馬克思的終極關懷取向——人類解放。于是,化本質主義為話語空間;化工人階級為多元身份;化革命政治為文化政治。拉墨原本懷著保衛馬克思主義的旨趣和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的美好愿望,但事實上,他們的激進多元民主是保守的政治,一種不科學的政治藍圖實現模式,其理論抱負成為與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策略相悖的空想。
2.貶斥主體性。“多元決定”的直接動因是批判加羅蒂把馬克思主義粉飾為黑格爾主義化和人道主義化。針對加羅蒂的扭曲,“多元決定”的生成力圖證明:社會歷史進程是多元決定的,人并非是歷史的主體。可見,“多元決定”隱而不彰地傳達對主體性的貶斥,壓抑人的主觀能動性,否定人的本性,駁斥了“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對人的本質的凸顯和曖昧。在“多元決定”理論的鋪墊基礎上,“理論上反人道主義”對人的主體性思想予以更明朗化和公開化,鮮明地表達:馬克思主義不是人道主義意識形態,而是歷史唯物主義科學。基于“多元決定”的輻射和牽引,阿爾都塞于1968年作了一篇《馬克思和黑格爾關系》的報告,其中提出一個著名的命題,即“歷史是個無主體過程”,從而進一步粉碎了人在社會歷史形態歷程中的主體地位,貶低人類主體的價值和作用。
阿爾都塞指出:“從1845年起,馬克思同一切把歷史和政治歸結為人的本質的理論徹底決裂”[2]222鑒于此,他指出,馬克思主義徹底批判傳統哲學的人道主義意識形態理論,摒棄了異化、類本質等純抽象思辨的概念,從而構建以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生產力、生產關系、社會形態等新概念為基礎的歷史理論和政治理論。以往主體性、理性主義、觀念本質等哲學范疇從馬克思的信條中清除出去,馬克思不再把人的本性或人的本質作為自己理論大廈的根基,“人的概念或范疇在馬克思那里已經不起理論作用了”[3]207,繼而以一個新的理論總問題式置換人性或人本質總問題式來重新解釋和實踐世界。阿爾都塞的評判并不無根據。的確,馬克思原文可資佐證:“我的分析方法……不是從人出發,而是從一定的社會經濟時期出發”[4]415,在此尚不作對阿爾都塞的評判。人類主體在社會歷史領域遭遇缺失,決定歷史發展的是多元性的結果,并不存在所謂固定、永恒不變的主體地位。那么,人在社會結構系統中究竟處在何種境地抑或被賦予何種使命和職責呢?阿爾都塞進一步闡發:“生產關系的結構決定生產當事人所占有的地位和所負擔的職能,而生產當事人只有在他們是這些職能的‘承擔者的范圍內才是這些地位的占有者。”[1]209
主體性的邊緣化在拉墨的思想域中被繼承與發展,他們對主體觀的批判和肢解比阿爾都塞表現得更加徹底和直白。拉墨直言不諱地講:“我們應該非常清楚地聲明……現在已經不可再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主體性和階級概念”[5]4。拉墨認為主體范疇存在會導致理性主義和二元對立的泛濫,在“人”范疇內引發的經驗與先驗、自由意志與決定論、科學與倫理等一系列對立現象難以解決。他們進一步指出:“無論什么時候我們在文本中使用‘主體范疇,在話語結構中都是在‘主體立場的意義上去這樣做的。”[5]128拉墨否認主體是社會復雜關系的本源,其存在的可能性要依賴于話語,從這個意義講,對主體范疇的考察應從“主體立場”角度出發,但是,“主體立場”的發生空間又是存在話語空間。因此,每一個“主體立場”都代表一種話語立場。在拉墨看來,社會是話語的社會,社會的意義在于話語的建構,而作為社會結構系統中的主體人自然也逃不出話語的“劫難”。這種將主體范疇延伸到話語空間,究其原因是,話語表征出開放性、差異性和分散性,毋庸置疑,這就自然而然地瓦解傳統主體所內含的統一性、普遍性和固定性。通過對話語空間中立場的剖析,導引出“主體立場”之間是平等的和多元的,他們進而將批判的角點聚焦在馬克思主義傳統革命主體——工人階級。“工人階級作為‘變化的歷史性力量的觀念已不再有效了”[6]66。對于工人階級的界定,這是馬克思的一種先驗性設定,即假設了一種先于一切社會活動的前定性和統一性的存在。“馬克思主義聲稱自己知道根本上被確定的歷史過程,對實際事件的理解只能意味著把它當成已經先驗地被決定了的現實演化過程的一個因素”[5]19-20。由此,這就和黑格爾預先設定的內在本原——絕對精神——的演進邏輯如出一轍。觀照現實,女權主義、反種族主義、生態主義等新型的對抗資產階級形式不斷涌現。拉墨認為,階級已不再存在,與之代替的是多元身份。
二、多元決定與激進多元民主的相異點
拉墨的激進多元民主雖然直接繼承了阿爾都塞“多元決定”思想的某些特質,表征出保衛馬克思和貶斥主體性的重合,但是拉墨不滿阿爾都塞對“多元決定”的運用,并對“多元性”發揮得更加徹底。因此,激進多元民主和“多元決定”也表現出如下差異性:
1.方法論分歧: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結構主義不再重點關注事物存在本身,轉而聚焦在事物與事物之間的密切關系的研究。阿爾都塞正是運用結構主義方法重新“癥候”馬克思主義原著,以至形成一支新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即“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拉墨的“后馬克思主義”的形成主要基于葛蘭西、德里達、阿爾都塞、拉康理論的鋪墊,從與阿爾都塞思想關系來看,除了存在吻合外,他們表征出更多的差異,這主要是由于他們在方法論原則上受益于德里達的解構主義。從方法論上看,“多元決定”和“激進多元民主”主要存在如下差異:
一是整體性與去總體化。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強調整體性,而拉墨主張消解整體性、去總體化。整體性是指各要素或部分組成一個復雜的結構系統,在結構的內部,要素之間是有規則、有秩序地緊密聯系在一起,形成一個內部相互融通、自我調節的系統。因此,整體性不是各部分或要素簡單相加的結果。“生產關系的結構規定著經濟本身,那么,一定的生產方式的生產關系的概念的規定,必然要通過社會各個層次及其固有的聯連的型式(即作用型式)的整體概念的規定才能完成”[7]292。在阿爾都塞看來,界定生產關系的概念時,并不是孤立地、片面地去理解和把握,而是將它置于它本身所處的復雜的系統中,通過與社會內部的其它各層次的相互聯結的關系來全面定義。
反之,拉墨極力反對和消解總體性,因為總體性會窒礙事物的發展,形成思想僵化的形而上學原則,抹殺個體的多樣性和活力。但是,它將促使社會的多元性、差異性和開放性的彰顯,為他建構“激進多元民主”政治創造條件。拉墨在《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策略》一文的開篇就直接指出:“領導權將暗示缺席的總體”[5]1。拉墨認為,領導權的邏輯意蘊著一種非總體化的偶然性邏輯,當與本質主義邏輯脫離后,更有利于人們對社會多元的認同,尤其是政治認同,并且這種認同不再是既定的事實,而是開放的、偶然的、非統一的。
二是因果性和隨機性。因果性意蘊著普遍性、必然性和規律性的特征。阿爾都塞反對歷史上兩類主流因果觀:一類是以伽利略和笛卡爾為代表的線性因果觀;一類是以萊布尼茨和黑格爾為代表的表現因果觀。為了消除由一個原因和結果構成的經驗主義或理性主義的因果觀,阿爾都塞提出具有異質性的馬克思主義結構因果觀。他指出:結構是內在于要素或它們關系的整體中,而非是外在的分離的。結構既是原因又是結果,作為隱而不彰的原因埋藏在復雜整體的深層,不是外在顯現物,而結果也不是先驗的對象要素抑或預先在結構區域空間留下自身的足跡,相反,結構內在于它的結果中。
量子力學的問世引發人們重新審視某些古老的哲學問題,例如,質疑因果性、普遍性、必然性和規律性的合理性,與之相對的隨機性和偶然性價值更加彰顯。拉墨也借用隨機性來支撐他的激進多元民主理論。他們建構一套話語理論試圖摧毀因果觀念,拒斥用因果性、必然性、可理解性來解釋社會歷史,強調社會歷史是隨機性、偶然性、不確定性和開放性。
2.處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不同。在處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關系時,阿爾都塞多次強調經濟基礎在社會歷史發展中起歸根到底的支配作用,與此同時也注重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力。一方面,它有效地回駁了庸俗的經濟主義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關系的扭曲;另一方面,阿爾都塞過分的夸大上層建筑的作用限度,認為在特殊的環境狀態下上層建筑成為和經濟基礎等量齊觀的有效決定因素。拉墨對阿爾都塞處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關系的行為表示不滿,究其原因是,阿爾都塞對“多元決定”發揮的不徹底性,保留了經濟基礎的歸根到底作用,必然會導致新的本質主義復發。于是,拉墨對經濟基礎實行徹底的瓦解,鏟除經濟基礎作為社會歷史發展的根基,并將上層建筑凌駕經濟基礎之上,給予“政治優先性”。由此可見,基于拉墨視域,上層建筑的地位業已超越了經濟基礎的支配地位。
阿爾都塞認為,在社會發展的歷程中,經濟基礎從來不是單獨的孤立的發生作用,是和社會結構內其它有效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例如,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特殊環境等對其的有效決定。然而,經濟基礎歸根到底的決定效果并不是固定的永恒不變的,而是隨著矛盾的多元決定及它們不平衡發展而發生相應的改變。“矛盾的這一‘方面(生產力、經濟、實踐)必定起主導作用,而另一‘方面(生產關系、政治意識形態、理論)必定起次要作用,卻不了解歸根到底由經濟所起的決定作用在真實的歷史中恰恰是通過經濟、政治、理論等交替起第一作用而實現的”[2]。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在推動社會進程時是交替“值班”即輪流起第一性作用。阿爾都塞特別突出上層建筑的反作用,以致使它與經濟基礎處在同等地位,但他并沒有像拉墨那樣將經濟基礎鏟除。
較之阿爾都塞,拉墨更加走向激進。他們首先肯定了阿爾都塞“多元決定”的價值,因為它開啟了某種新的連接概念的可能性,原本可以解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總體性,但是,這些都未能在預期范圍內演進。“多元決定”概念也就逐漸在阿爾都塞話語中消失,最終導致一種新的本質主義的生發。他們力圖攻破本質主義的最后堡壘——經濟,指出“經濟空間本身被結構化政治空間”[5]85。鏟除了經濟基礎的根基地位,留下的是空洞的話語邏輯,社會成為話語的社會。政治相對經濟而言被拉墨賦予了享有特例的優先性,并在社會生活的每個角落都起著支配作用,而脫離現實的物質活動的政治只能是一種抽象的空洞的虛幻。由此可見,拉墨的理論邏輯實質是在唯心主義范疇統攝下的演繹。
3.“多元”的理論根基和對象不同。阿爾都塞的“多元”具有某種解構“中心化”的傾向,為拉墨開啟“后馬克思主義”學派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不可否認,拉墨繼承了“多元”的某些因素,但是,除了某些重合點外,更加表現出明顯的差異:一是兩者的“多元”理論根基的異質性,二是對“多元”運用的程度和范圍不同。
一是“多元”理論根基的異質性。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是指“構成社會整體的各個社會領域是由異質的諸矛盾構成的異質的諸事件交互作用決定的復合體(結構),這種復合體(結構)的復合構成社會整體”[8]115。他的“多元決定”最終是屈服于“最后決定”,其理論根基仍然是歷史唯物主義。拉墨的“激進多元民主”的“多元”置于話語空間,經濟基礎根基被挖除。因此,他們的“多元”范疇的根基是歷史唯心主義。
二是對象側重性不同。阿爾都塞的“多元”是側重于矛盾的多元性。在社會結構整體中,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等多元矛盾形態,它們貫穿人類社會形態始終,規定社會的性質和基本結構。拉墨的“多元”主要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主體是多元身份的聯合,而不是專屬某個階級抑或團體,以及實現政治民主形式的多元性。最后,拉墨指責阿爾都塞對“多元”的運用不夠徹底,關鍵是對經濟基礎有所保留,認為阿爾都塞對“多元決定”使用的領域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為了清除阿爾都塞留下的諸如二元對立、本質主義等病癥,他們對“多元決定”思想發揮的徹頭徹尾,越走越偏離了馬克思主義航線。
三、幾點啟示
全面科學地把握兩者的聯系與區別,旨在深化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與研究,同時對今后我們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及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良好的啟示作用。
1.科學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的唯物論與辯證法、自然觀與歷史觀、科學性與革命性相統一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基于工人階級革命運動而產生的關于人類解放和人的全面發展的學說。但是,任何真理都是相對的,在一定具體的歷史的條件和范圍內適用,超出其存在的界域,就有轉化謬誤的傾向,作為時代精神之精華的馬克思主義也如此。在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后的當下,馬克思主義某些理論的確業已乏力應對新環境引發的諸多新問題和新矛盾。因此,馬克思主義學者試圖重新詮釋和解讀馬克思理論,以至完善和豐富馬克思理論體系,增強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真理性。但是,在理解與把握、繼承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時,要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不應踐踏馬克思主義原生態,偏離馬克思主義軌道。
2.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人學思想中國化的成果,它從后現代那種主張消解本體論,貶斥主體性,否定“邏各斯”和“在場”的思想域中跨越出,重新肯定人的“在場”,并且超越了傳統哲學本體論對“人”的界定。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建立在實踐基礎上,根據我國具體國情,依照人民大眾利益需求而提出的,與馬克思畢生的終極關懷取向——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相契合,也表明了黨和政府充分汲取了馬克思主義精髓,正確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實踐。由此可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以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因此,務必將這一理念貫徹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讓廣大人民感受到自身價值,增強精神力量,觸發人民大眾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而奮斗的激情。而任何企圖消解人民的主體性規定的行徑,都是與歷史和現實、理論和邏輯、人民根本利益和社會發展規律相悖的。人民群眾是社會復雜系統中的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既創造了物質財富,又創造了精神財富。正是由于人的實踐活動,世界的存在才變得有意義。
3.正確處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歷史唯物主義原理表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經濟基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作為社會歷史的基本矛盾,推動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實現人類社會形態由低級向高級演變。社會能否健康、有序、快速地發展關鍵在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是否和諧穩定。因此,著力把經濟基礎變革和推動上層建筑改革相結合,這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也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基本理論的必然要求。一方面,要承認經濟基礎的第一性,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產生、變化、發展以及性質狀態。另一方面,也要關注上層建筑的反作用力,尤其是在我國市場經濟逐漸完善后,作為上層建筑的政治機構、法律體系、意識形態等也應不斷的健全和完善,以便更好地推進市場經濟的發展。在我國改革實踐中,我們既要反對像阿爾都塞那樣把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等量齊觀的“溫和”,也要反對拉墨那種把鏟除作為社會發展根基的經濟基礎的“偏激”。
參考文獻:
[1]阿爾都塞,巴利巴爾.讀《資本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2]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3]陳越.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恩斯特·拉克勞,查特爾·墨菲.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走向一種激進民主政治[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
[6]周凡,李惠斌.后馬克思主義[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
[7]張一兵.問題式、癥候閱讀與意識形態[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8]金瑤梅.阿爾都塞及其學派研究[M].重慶:重慶出版社,2010.
責任編輯? 姚黎君? 魏亞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