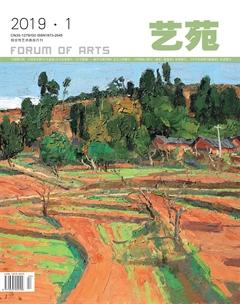“巫魔會”題材繪畫中的圈舞圖像
唐曉義

【摘要】 對近代歐洲早期“巫魔會”題材繪畫中的圈舞圖像進行探討。“巫魔會”既是一場魔鬼與巫師的狂歡,也是顛覆基督教世界的邪惡儀式,而舞蹈則是“巫魔會”的重要內容。圈舞不僅與異教諸神崇拜有關,而且適合表現集體狂歡的場景,常見于“巫魔會”題材繪畫中。作為“獵巫”手冊中的內容,圈舞表現狂歡的畫面比文字描述更為形象,有助于增強人們對魔鬼與巫師的厭惡及恐懼。
【關鍵詞】 魔鬼;巫師;圈舞
[中圖分類號]J23? [文獻標識碼]A
圈舞是指舞者們圍成一個圓圈,圍繞或不圍繞一個置于圓心,具有象征意義的實物共同起舞的形式。舞者們在跳圈舞時手牽手或將手置于其他人的肩部或腰部,或不進行身體接觸但按照統一的節奏共舞。舞者們舞動時既可徒手,也可手持器物。圈舞有著悠久的歷史,能夠反映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多元民族傳統文化,具有祭祀、儀式、社交、娛樂等功能。從藝術史的角度看,繪畫與舞蹈存在緊密的聯系。一方面,畫家通過繪畫再現某一舞蹈練習或表演場景,如法國印象派畫家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1834-1917)描繪芭蕾舞演員臺前幕后的多幅作品。這些作品中的舞蹈再現了現實世界中的場景。另一方面,繪畫中的舞蹈也能夠被用于表現宗教或神話中的場景,即畫家采用世俗的舞蹈場景表現某個宗教或神話題材。舞者并非現實世界中的人物,而是畫家通過自身的想象描繪出的擬人化的異教諸神或《圣經》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如意大利文藝復興畫家弗拉·菲利普·利皮(Fra Filippo Lippi,1406-1469)及法國象征主義畫家古斯塔夫·莫羅(Gustave Moreau,1826-1898)所描繪的莎樂美之舞,或是意大利文藝復興畫家安德烈亞·曼特尼亞(Andrea Mantegan,1431-1506)描繪的繆斯們在巴納斯山上曼妙的舞姿。
作為舞蹈的表現形式之一,圈舞也常出現在各個時期的繪畫之中,如文藝復興時期的多位畫家描繪圈舞以表現宮廷社交活動以及鄉間狂歡等世俗場景,或在宗教題材的畫作中以圍繞著神圣之光或圣母加冕起舞的天使襯托上帝“三位一體”的神性。表現世俗或宗教題材畫作中的圈舞多數會使觀者體驗到美、和諧、愉悅之感。然而,在近代早期歐洲的繪畫,特別是書籍的插圖中卻經常會出現使觀者無法感知和諧與美的畫面,表現為一個或多個頭上長角,身后有尾,長著蹄子,甚至長有翅膀,站立似人的怪物與人類共同跳圈舞。畫面中跳圈舞的舞者是何身份?圈舞襯托的是何場景?畫家為何采用圈舞而不是排舞或其他的舞蹈形式來表現繪畫主題?此類圖像為何在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的手抄本中難得尋覓,卻大量出現在近代早期歐洲的書籍中?畫家創作這些詭異、令人不悅的圖像目的又是什么?本文擬從文化史的角度對上述問題進行探討。
一、“巫魔會”中的圈舞
通過對繪畫的觀察,筆者分辨出畫中的舞者具有兩類典型的形象特征。其中一類為前文所述長相怪異的生物,具有擬人化的姿態。另一類舞者則明顯為人類。由此可見畫作反映的是怪物與人類共舞的場景。然而這些怪物及人類的身份何屬?為何而舞?雖然僅通過觀察繪畫難以得出舞者身份及其舞動目的的結論,然而這些繪畫是以書籍中的插圖形式得以呈現。關于插圖的注釋及書籍中描述的文字為筆者闡釋此類畫作提供了依據。
在這些插圖的注釋中常見的關鍵詞中,出現頻率最高的當屬“魔鬼”“巫師”或“女巫”,這也表明了舞者的身份。于1720年編著的《巫師史》中有一幅插圖的標題即為《與魔鬼共舞的女巫》(圖1);1688年創作的《黑暗王國》則描繪的是在吹奏樂器及歌唱的巫師伴隨下,魔鬼與女巫圍繞著一個圓圈跳舞的場景(圖2);1879年的《魔法史》插圖也描繪了女巫與魔鬼在安息日共舞的場景(圖3)。“儀式”一詞也與此類圈舞有關,如一本于1608年用拉丁文編寫的“獵巫”手冊中的插圖《巫師在安息日與魔鬼共舞》描繪了舞蹈為惡魔崇拜的一個重要儀式(圖4)。此外,一些插圖的注釋還特別描述了圈舞舞者們是圍繞著處于圓心位置的魔鬼共舞,如創作于1669年的《瓦爾普爾吉斯之夜》描繪了巫師與魔鬼在安息日相伴在一個宏大的場面中圍繞著端坐場地正中的撒旦共舞(圖5)。在一幅創作于約1600年的《女巫圍繞著魔鬼跳舞》中,不但女巫們圍繞著魔鬼形成一個圓圈舞動,而且處于圓心的魔鬼軀體相對女巫們而言十分巨大(圖6),突出了魔鬼在這一儀式中的重要地位。
根據文獻記載,這種魔鬼與巫師共跳圈舞表現的即“巫魔會”中的場景,即“女巫們參拜魔鬼,并在可怕的音樂聲中圍繞魔鬼跳舞,這些音樂來自一些古怪的樂器,如馬的頭蓋骨、橡樹木、人骨等”。[1]136-142“巫魔會”是指巫師集體敬拜魔鬼,從事褻瀆神明、非道德、淫穢下流、令人毛骨悚然的儀式,是關于異端集體作惡的一種幻想。[2]35-39 “巫魔會”中的魔鬼一般以黑衣人或黑色動物的現象出現,如“又高又黑,有腳有爪,驢耳,兩眼發光,牙齒咯咯作響,長著碩大的生殖器,渾身還散發著硫磺的味道”。也有將魔鬼形容為“長著兩只中等大小的角,一副全黑的面孔,上面只有嘴唇顯得蒼白一點;他的眼睛很大也很嚇人,全黑而無眼白,他還長著一個又大又丑的鷹鉤鼻,鼻尖上有三個點向外突出好遠”。[1]136-142與之相似,畫中巫師的形象也毫無美感,甚至被刻畫為小丑的形象。由此可見,書籍中出現描繪“巫魔會”的插圖,將魔鬼與巫師的形象刻畫的如此丑陋不堪,其目的既非審美,也非宗教藝術中的圣像崇拜,而是一種誘導,使人們看到此畫面即產生厭惡的情緒。
二、基督教世界對魔鬼與巫師的態度
在基督教神學的權威時代,科學發展尚處于萌芽之中,無論是神學家還是普通教眾都對魔鬼懷有深深的恐懼與敵意。神學家們引經據典,論述魔鬼對世界的威脅無處不在,而普通教眾則更為擔憂被魔鬼附體所造成的各類疾病。神學家推斷危害人類的自然現象多是由于魔鬼導致的。基督教著名神學家圣哲羅姆、圣奧古斯丁和圣托馬斯·阿奎那均認為暴風雨就是魔鬼所為。此外,神學家們也將疾病的病因歸咎于魔鬼對人的折磨。魔鬼會附于人類的軀體,使人罹患疾病,甚至導致精神錯亂。圣奧古斯丁指出:“基督徒的所有疾病都是由這些魔鬼所致。”圣格列高利則認為身體的疾患是由魔鬼引起的,醫學對它們無能為力,但是施加一些神圣的干預卻常常能醫治好它們。[3]714宗教改革運動領袖馬丁·路德也指出:“所有折磨人類的病癥都是撒旦引起的,因為它是死亡之王。”[3]738
除了時刻擔憂魔鬼附體對自身及他人帶來的生命威脅,基督教信仰也促使人們厭惡與反抗魔鬼。人們相信上帝是善的源泉,而撒旦是惡的禍根,兩者為爭奪世界而戰斗。直至近代歐洲,善惡對立之說仍根深蒂固。[4]23魔鬼與巫師所組成的“巫魔會”更像是一場顛覆基督教世界的邪惡儀式,必須加以鏟除。“巫魔會”不乏對于基督教褻瀆的行為,如“當魔鬼發言抨擊基督教時,出席者都大聲贊揚……門徒必須棄絕基督教,咒罵上帝、三位一體、圣母瑪利亞,踐踏十字架,并向受難耶穌像吐唾沫,最后以一場黑色彌撒結束儀式”。[4]18由此可見,近代早期的歐洲人所處的社會與基督教神學存在著緊密的聯系,而魔鬼與巫師正是基督教神學家們所認定的信仰之敵。
圈舞曾呈現于不同時期的繪畫之中,如在宗教題材的繪畫中呈現的描繪天堂中的幸福,使觀者更為虔誠的圈舞,或出現世俗題材繪畫中反映人們社交或娛樂場景的圈舞。人們在觀看上述繪畫時能夠體驗到舞者們所表現的和諧與對稱之美,或是舞者們舞動所象征的虔誠信仰,或是通過畫面中舞者的表情與動作對社交或娛樂場景感同身受。然而,“巫魔會”中的圈舞畫面顯然不能給觀者帶來上述感受。不僅如前文所述,對魔鬼與巫師丑陋的描繪使人厭惡,而且面對自然災害的襲擾、自身健康的擔憂、信仰之敵的觀念、神學家們的鼓動,人們更加抵觸“巫魔會”,恨不能對魔鬼與巫師除之而后快。
三、酒神的狂歡印記
為何插圖采用圈舞,而非其他的舞蹈形式以表現“巫魔會”?也許這與所謂的近代歐洲“文明人”對原始宗教信仰與生活方式的“野蠻人”的狂歡行為持消極態度有關。原始且屬于異教的儀式往往采用圈舞表現狂歡,將孤立的個體連接起來,形成能誘發熱情或狂喜的“集體歡騰”。這種儀式中的“集體歡騰”往往伴隨著神靈附身狀態,好似魔鬼附體一般。近代歐洲人常以“文明人”自居,受基督教教義與神學家們的影響,非但無法理解原始的“野蠻人”文化,特別是其宗教儀式,而且將狂歡歸于魔鬼、巫術、縱欲等與基督教宗旨背離的行為,通過描繪此類圖像并對其內容大加鞭撻也就不足為奇了。
此外,希臘神話中存在一位深受民眾喜愛的神祗,即酒神狄俄尼索斯。酒神的祭祀儀式通常涉及狂歡,而舞蹈是儀式中的一項重要內容,表現的是酒神信徒們披頭散發,揮舞著酒神仗,穿越森林,大聲呼叫著神的名字,最后達到了神明附身的狀態。作為異教諸神中的一員,酒神的存在與基督教宣揚的世上只存在唯一的神,即全知全能的上帝的理念相沖突。然而,與基督教存在緊密聯系的猶太文化卻將酒神的形象與耶穌相聯系,甚至將其認為是神格化耶穌的原型。[5]63基督教神學家則認為耶穌與酒神信仰互斥,應是一種對立的關系。神學家將“巫師”的罪名強加于猶太人之上,巫師的聚會甚至被稱為猶太人的聚會。[6]72民眾聚眾狂歡的行為本就為基督教神學家所批判,況且祭祀酒神的儀式又與異教神祗崇拜有關,更為基督教世界所不容,作為儀式重要內容之一的舞蹈也被賦予了消極的意義。圈舞在猶太傳統文化中占據重要的地位。希伯來文中的“bag”一字同時有“慶典”和“圍成一圈”的意思,許多猶太傳統慶典的原始形態就是人們圍成圈跳舞。[5]31或許正是因為對狂歡中的舞蹈持否定態度,以及對猶太文化的抵觸,使得畫家采用圈舞來表現魔鬼與巫師的狂歡。
四、推動“獵巫”運動的開展
在近代早期的歐洲,整個社會都對魔鬼與巫師的存在惴惴不安。神學家們認為魔鬼與巫師沆瀣一氣。魔鬼使人類罹患疾病,引發暴風雨等自然災害,而巫師則是各種危害人類生命行為的直接實施者,對魔鬼的惡行推波助瀾。此外,由于那一時期的氣候反常,直接影響農作物的生長,大眾的生活受到威脅,時常處于饑寒交迫的狀態,也將怨氣撒在被認為是罪魁禍首的魔鬼與助紂為虐的巫師身上。雖然人們卻無法懲罰魔鬼,驅魔人士也并不認為能將魔鬼徹底消滅,只能將其驅逐出人類的軀體,但是教會對巫師的審判卻獲得了大量支持。宗教法庭對被懷疑為巫師的嫌疑人嚴加審訊,甚至不惜屈打成招,處死了數以萬計的無辜者,其中大多數為女性。
為使世俗統治階級與民眾了解魔鬼與巫師存在的威脅,并為宗教法庭鑒別一個人是否為巫師,以及為確認為巫師的罪人提供量刑依據,包含“獵巫”內容的書籍在這一時期被大量出版。書籍中的插圖相對于文字能夠更形象地傳播信息,使讀者對于魔鬼與巫師的形象具有直觀印象。印刷技術的發展使得這些插圖能夠得到廣泛的傳播。雖然早在古埃及時期的《亡靈書》中就含有精美的插圖,然而直至中世紀時期,書籍中插圖所占頁面比例雖然越來越大,但其載體仍主要以手抄本的形式出現。這些由人工抄寫的書籍雖然制作精美,但費時費力,數量十分稀少,多數為世俗統治階級與教會所收藏,一些圖書館中的藏書不過百余本。自14世紀伊始,木板印刷逐漸應用于書籍插圖的制作和生產上,使得插圖無論從質量還是數量均有顯著的提高。近代歐洲印刷技術的發展為“獵巫”書籍的大量出版奠定了基礎,更多的人能夠讀到這些書籍,從書中的插圖了解巫師與魔鬼的形象。
如何描繪“巫魔會”中的圈舞場景依賴于畫家的想象。在一些插圖中,魔鬼的身形十分龐大,如同巨人,位于圓心,巫師則圍繞在周圍牽手共舞,不僅象征著巫師對魔鬼的崇拜,而且凸顯了魔鬼的支配地位。還有一些插圖則描繪了魔鬼與巫師具有大致相等的身高,攜手共舞的場景,更加具有世俗的特征。這表明巫師與魔鬼的形象不僅受到印刷技術的制約,如采用銅板印刷術制作出的插圖精細程度要高于木板印刷,而且與畫家的創作理念有關,或偏向宗教化或偏向世俗化。然而無論畫家如何描繪“巫魔會”中的圈舞場景,人們看到這樣的畫面也許都會對魔鬼與巫師的形象印象深刻,時刻威脅人類安危的兩大角色竟然如此歡騰,這種狂熱的儀式也許就是巫師與魔鬼密謀決定后續危害人類行動的前兆。觀看圖像產生的恐懼與厭惡可能會促使人們更加支持宗教及世俗機構開展的“獵巫”行動。
五、結語
圈舞既是魔鬼與巫師連接的紐帶,同時也是“巫魔會”中不可或缺的狂歡內容,代表了一種原始的、異教的文化。作為舞者,魔鬼的形象似人非人、令人可憎,巫師則是魔鬼的傀儡與作惡人間的代理。魔鬼與巫師共舞的場景使觀者更加意識到此類聚會對于人類社會的威脅,從而支持宗教機構與世俗統治階級開展的“獵巫”運動。
參考文獻:
[1]陸啟宏.禁欲與放縱: 魔鬼信仰與近代早期西歐的資本主義[J].史林,2007 (5).
[2]劉淑青,劉敏.歐洲近代巫術觀念的文化解讀[J].山東社會科學,2012(5).
[3]安德魯·迪克森·懷特.科學—神學論戰史(第二卷)[M].魯旭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4]薩爾曼.女巫: 撒旦的情人[M].馬振騁,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
[5]芭芭拉·艾倫瑞克.街頭的狂歡[M].胡訢諄,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
[6]沃爾夫岡·貝林格.巫師與獵巫:一部全球史[M].何美蘭,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