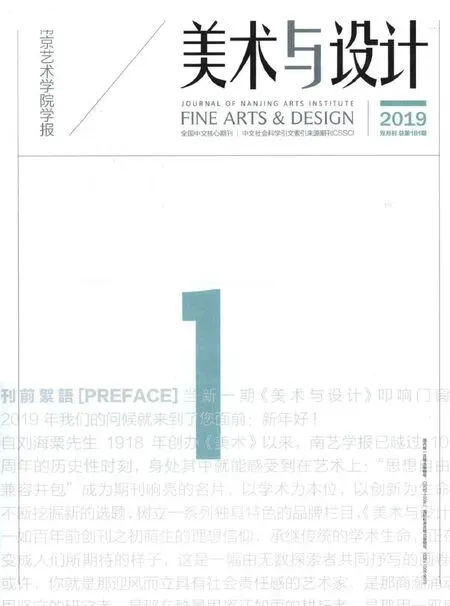從范疇、路徑與導向看設計學科的間性特質
——兼與祝帥兄商榷
周 志(清華大學 美術學院,北京 100084)
自設計學升為一級學科以來,設計相關研究廣受重視,成果頗豐,但同時也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究其原因,設計學研究的對象、方法、范式、導向的混亂不明是根本問題。作為一門年輕的學科,設計學研究本來就有其復雜性,而如果研究者對此不加審視,仍然維持混亂的現狀,對這門學科的發(fā)展是極其不利的。學科的發(fā)展,首先要明確自身的范疇,提煉內部各專業(yè)的共性,明確與其他學科之間的差異性,即學科自身的特性。而現在的問題是,設計學科還未趨同,內部專業(yè)卻先要求異。針對這些現狀,祝帥發(fā)表了《論設計研究的“學科間性”》[1]一文,首次在設計學研究領域提出了“學科間性”的概念,應該引起學界的重視。
從教育學的意義上講,學科有3層涵義:①作為學問或知識體系的分支;②作為教與學的科目;③作為學術組織。[2]如果進行學科間性的分析,自然是取義學科的第一層內涵,其主要表現在知識體系的構成特性,即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知識體系的內容與其他學科之間的差異上。的確如祝帥所說,目前,盡管已經升級為一級學科,但是目前國內設計學的研究對象、理論的效用以及研究方法的認識都并不明確,與其他學科的區(qū)別也較為模糊。正如中國美院的杭間教授所擔憂的,對“設計”認識的歧義,已經到了損害設計發(fā)展本質的地步。他進一步指出:“我們看見了從許多各自出發(fā)點認識的‘設計’,很多缺乏結構和層次,有的則不在一個層面上爭論問題。更令人警惕的是,隨著一些具有話語權的觀點或在傳播或在平臺上具有優(yōu)勢,非學術的利益集團似乎正在形成,并在試圖對觀點形成壟斷。”[3]在這一背景下,討論設計學的學科間性,確實是非常好的一個研究切入點。這一概念的提出,對澄清設計學本質有著重要價值。但是,對于祝帥文中提出的一些觀點,筆者卻不敢茍同。以下重點就學科范疇、研究路徑與學科導向三個方面的問題與祝帥商榷,以求更進一步厘清問題關鍵,也希望藉此話題引起學界更多同仁的關注。
一、學科范疇:工科論文屬不屬于設計學?
祝帥在文章中指出:“新版學科目錄實行五六年來,已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從工科領域進入到設計研究,并且有把自己所從事的‘這一個’門類的設計研究大而化之為整個‘設計學’研究的傾向。”并且認為,傳統(tǒng)的建立在人文學科藝術學基礎上的“設計藝術學”,大有被工科背景的“設計學”全盤否定和替代之勢。接下來,他又以《裝飾》雜志為例,認為現在大量談論計算機科學、工程學的論文和研究報告刊登在一份“裝飾”類刊物上,是一件耐人尋味的事情。[1]的確,祝帥兄所提到的工科背景論文對傳統(tǒng)設計藝術學造成巨大沖擊的現象,是近年來設計學科建設中出現的一個重大問題,筆者對此深有體會。但是,與祝帥意見不同之處在于,筆者認為此現象的嚴峻之處并不在于像《裝飾》這樣的“工藝美術類”期刊刊發(fā)工科類的論文。姑且不論祝帥對“裝飾”這個概念的理解是否存在偏差,僅從數據上看,就筆者根據關鍵詞與標題搜索統(tǒng)計,近十年來,《裝飾》刊發(fā)的論文中與計算機、機械、工程技術相關的論文僅有十余篇,遠遠稱不上“大量”。在知網后臺數據中,《裝飾》刊載的涵蓋上百個學科類別的論文中,計算機軟件及計算機應用、機械工業(yè)、儀器儀表工業(yè)、水利水電工程、農業(yè)工程等等類別的文章占比均在1%,甚至在0.1%以內。這非但難以稱之為“全盤否定”,反而顯示了設計學的綜合性與交叉性的學科特色。筆者認為,問題的嚴重性其實體現在另外兩種現象或者是趨勢上:1.工程設計類期刊開始大量刊載設計學論文;2.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中的大量設計學項目均以工程學項目為主。
第一種現象以《機械設計》《包裝工程》為例,前者由中國機械工程學會與天津市機械工程學會主辦,月刊,自2013年起開辟《工業(yè)設計論壇與資訊》欄目,大量刊發(fā)產品設計與工業(yè)設計的論文。后者是由中國兵器工業(yè)第五九研究所主辦的半月刊,自2010年起開辟《工業(yè)設計》《視覺傳達設計》《高校設計專題研究》等專欄,開始大量刊發(fā)藝術設計相關論文。由于設計學科很多開設在綜合類甚至理工類高校中,對于發(fā)表在這些期刊上的論文,學校不僅認可,甚至會鼓勵。但是,這些期刊對于藝術門類下設計學科范式的認識,以及論文的評審標準卻并不統(tǒng)一。
第二種現象在徐江等所撰寫的《設計學科相關領域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分析》一文中有詳細分析。[4]文章指出,無論從資助項目數量還是金額上看,“工程與材料科學部”的支持力度都位于各學部之首,達到144項(39.34%),“信息科學部”支持112項(30.6%),“管理科學部”支持 100 項(27.32%)。歸屬機械設計學(E0506)的項目數在所有二級學科中最多,達到 120 項(32.79%),經費總數為 5191.4萬元(34.38%)。該文總結認為,由于“現有NSFC資助體系下設計學科尚無明確歸口申請代碼,雖然自然促進了學科交叉和融合,但也導致申請多走彎路,迫于采取‘借船出海’的方式,不利于激發(fā)廣大設計科研人員的積極性”。
其實,以上兩種現象從某種意義上講仍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畢竟擴大了設計研究論文的發(fā)表渠道,對數以萬計的設計科研工作者來說是件好事。真正令人擔憂的是隱藏在其背后的另一種傾向:工程學科對設計概念認識對藝術門類下設計概念的巨大沖擊。這使得原本已經因為工藝美術、圖案、藝術設計、設計藝術、實用美術等等概念的混用搞得模糊混亂的設計學科陷入了范疇更加模糊、地位更顯弱勢的境地。這一點在國家學科目錄中“工業(yè)設計”相關學科的設置上體現得更加突出:作為藝術類一級學科設計學下屬的二級學科“產品設計”(130504)與工學類一級學科機械工程學下屬的“工業(yè)設計”(080205)存在著明顯的重疊現象。
何為工程學?近代科學誕生以后,具體的、局域性的工程活動才開始作為研究對象,并陸續(xù)建立起建筑工程學、水利工程學、道路工程學、化學工程學等眾多的工程學科。與目前被歸類到人文社會科學藝術門類下的設計學不同,這些學科普遍都被歸類于自然科學這個龐大的科學知識分支體系。[5]但是,工程學又在兩個主要概念上與設計學存在重疊認知現象——造物、設計。
首先,工程學與設計學中常常提及的“造物”概念有很深的淵源。如2002年,李伯聰在《工程哲學引論:我造物故我在》一書中便提出“科學-技術-工程三元論”的觀點,主張將科學活動解釋為以發(fā)現為核心的人類活動,將技術解釋為以發(fā)明活動為核心的人類活動,將工程活動解釋為以建造活動為核心的人類活動。[6]如此看來,工程學作為對人類造物活動進行研究的科學,確實與同樣關注造物行為的設計學存在著交叉的關系。
此外,“設計”這個詞匯在工程學科中早有應用。如果列舉帶有“設計”字眼的工程學期刊,隨便就能列出《工程設計學報》《工程建設與設計》《電子設計工程》《機械設計》《機械設計與研究》《計算機工程與設計》《化工設計》《飛機設計》等數十種,比藝術門類下的設計期刊要多得多。這一趨向其實亦源于西方學界,著名學者赫伯特·西蒙所稱之為“人工科學”的設計概念,其實指的主要就是工程設計。早在十年前,針對藝術設計理論界對西蒙設計理論的追捧和引用,祝帥就敏銳地看出其中的問題和隱患。他撰文指出,西蒙所說的設計科學,是一種看起來無所不包的“廣義設計學”“西蒙對設計模型、設計邏輯、資源分配、層級結構等具體論述,更多的是工程設計領域中的設計方法,……而恰恰忽視了作為設計研究中一個重要力量的藝術設計的工作情況”。[7]但在當時,設計藝術學與工程設計之間尚無明顯的交集,設計藝術學對感性工學等研究方法的引入,更多的是在試圖借鑒其他學科的方法,努力擴大自身學科的合理性與學術性,尚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而當設計學在2012年真正升級為一級學科之后,工程學和設計學的邊界開始模糊化,并且憑借自身雄厚的學術積累與資源,對設計學的研究領域造成了不可忽視的沖擊。此時,設計學科范疇的界定,以及與其他學科的差異性定位才變得空前關鍵起來。
針對工程設計與設計概念重疊的問題,蘇州大學教授李超德認為:我們不否認,設計既是藝術的,也是技術之解釋。但純粹是工程和技術性的設計應該剝離出來,這涉及設計學的學科評價標準。他進一步指出,廣義設計學(怎么設計,解決難題)和泛設計的理解,有害于設計學學科的正確評價和學科的良性發(fā)展。“狹義的設計學”(為什么這么設計,應該怎么設計,解決問題)研究領域,我理解為主要是圍繞涉及人們生活水平和民生的衣、食、住、行而展開的藝術設計活動和設計成果。[8]的確如李教授所說,在當前的背景下,過于推崇廣義設計學,模糊自身的邊界,實際上是對學科本身的傷害,這其實也正是強調設計學科間性特質的重要價值所在。
那么,藝術門類下的設計學的學科特質到底是什么?顯然,僅僅以其涉及的范疇是生活方式以及運用的藝術手法作為區(qū)分點是遠遠不夠的。如果僅僅把設計學理解為狹義上的“設計藝術學”同樣不利于學科的發(fā)展,甚至會在設計學與其他學科展開對話與溝通之際,將自己置于“美工”的弱勢地位,可能還不如音樂、美術更有話語權。筆者以為,設計學之設計概念,與工程學之設計概念的區(qū)別,不在于“狹”與“廣”,而在于研究對象范疇的差異。
如果比較一下《機械設計》與《裝飾》發(fā)表的涉及工程方面的論文不難發(fā)現,工程學的設計關注的是工程技術本身,即人工物自身內部結構關系的調整與優(yōu)化;而設計學的研究范圍雖然極為開放,但出發(fā)點都必定會涉及人,無論是我們常說的“形式”“造型”“審美”還是“互動”“包容”“體驗”,都是在對人與物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討。這里所說的人,包括使用者(消費)與制造者(生產);而物,則包括人工造物、自然環(huán)境,以及信息時代大背景下的虛擬世界。正是從這個角度來講,設計學無疑既具有自然和工程科學的創(chuàng)新、開發(fā)、成果轉化的特征屬性;又具有批判、反思等強烈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屬性。換句話說,設計學針對的問題既包括操作層面的“怎樣做”,也要考慮人文層面的“應該怎么做”“為什么去做”“這樣做對不對”。西方學者彭妮·斯帕克認為:“設計,既是變革的推動者,又是反映者。……設計既是文化構建過程的一部分,也是其反映。”[9]明確指出了設計的這一雙重屬性。李立新教授也曾經指出過設計的特性:“設計不能等同于自然科學,設計直接服務于社會人群,它的研究對象是人,設計又嚴格地受到生產方式的制約,它的生產形式是物。”[10]換句話說,設計正處在人與物的連接點上。故而,就筆者理解,設計學關注的核心問題不是造物的原理、技術的提升、生產的優(yōu)化,以及人的內心世界(哲學、文學、藝術)與社會組織關系(政治、社會、經濟),而是如何構建并思考人與造物、與環(huán)境、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以及如何在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工程科學之間搭建起和諧的橋梁(表1)。在這層意義上,原本被歸入工程科學的建筑設計、城市規(guī)劃、園林景觀等學科倒是應該歸屬于設計學科范疇。

表1 筆者設想的設計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
二、研究路徑:設計學研究的主流是不是理論?
一門學科的間性特質,除了研究對象上的區(qū)別,更體現在研究路徑與研究內容上。那么,具有人文科學屬性的設計學是否應該更多地借鑒哲學、美學、歷史,以及其他藝術學科的研究方法呢?就這一問題,祝帥在文中認為:“設計理論研究必須對于設計實踐的發(fā)生和發(fā)展做出引導,對于設計實踐的決策做出理論的依據,這樣的設計研究才有價值。當這個領域中絕大多數的學者都只能從文化、美學、哲學、倫理學或者美術史等視角從事一些從概念到概念的‘外圍研究’的時候,這個學科的格局肯定是出了問題。”[1]這一說法筆者是非常贊同的。但是,對于他接下來所得出來的結論,筆者卻不敢茍同。他認為:“從設計學的學科體系來講,設計理論研究應該是主流,而歷史研究是支流。”在此,他以法學為例進行了論證,“法律專業(yè)雖然也有研究法律史的,但法律史在法律系是副科,主流科目當然是理論,包括法律理論與實務、法律社會學理論等”。
對此說法,筆者并不同意,設計研究的主流確實不是歷史研究(關于設計史研究的地位和意義問題,筆者擬另文論述),但也非理論研究。理論研究盡管非常重要,但絕不能成為設計研究的主流,真正的主流應該是基于實踐的研究。祝帥所舉的法學的例子,應該說并不十分準確,法學的主流科目并非基礎性的法理學,而是憲法、刑法、民法等一系列法律實務研究。而且,如果與其他學科進行比較的話,另一門應用性很強的社會科學——管理學應該說更為合適。因為與設計學的研究目的類似,管理學同樣講求實效性與實用性,只不過其關注的焦點在于分析人與人之間關系,以提高組織管理活動的績效為導向。例如南開大學的王迎軍等就認為:“管理實踐是管理學研究的起點,從管理實踐的角度考察管理者如何運用管理知識,可以更好地認識管理學的學科屬性。”“在理論與實踐的互動關系中,管理實踐是中心,只有圍繞著這一中心,管理學才能找到自己的運行軌道。”[11]因此,在管理學中占大量比重的論文,都是針對實際案例的分析研究。如果把對比的學科擴展到醫(yī)學、建筑學、規(guī)劃學等更具應用性的學科,基于實踐、通過實踐的研究,或者說臨床研究的比重會更高。
按照通行慣例,理論研究是與應用、實踐研究相對應的。比如中國知網的《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年報》就將人文社科期刊的研究層次分為三類:理論研究型、應用研究型和實踐研究型。這樣的分類雖然比較清楚,但是實際上卻人為割裂了理論與實踐研究的關系,而且給人以研究層次的高低之分。在建筑學領域,孫暉、梁江曾撰文將設計理論研究分為描述型(Descriptive)研究和指導型(Prescriptive)研究兩類。他們認為,描述型的理論研究在于知,指導型的理論研究重在行。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理論是以描述型為主的,而建筑設計與城市設計理論則以指導型為主。[12]這一分類方法很有啟發(fā)性,但仍略顯籠統(tǒng),也沒有指明理論與實踐研究的關系。
筆者認為,理論研究可以大體分為三個類型:應用理論的研究(Research with Theory)、基于理論的研究(Research on Theory)、為了理論的研究(Research for Theory),分別對應理論在研究中的位置和作用:作為手段、作為內容、作為目的。第一類只是將已有的理論視為一種指導性的、工具性的手段、途徑,在嚴格意義上講并不算是理論研究。第二類雖然只是以理論作為研究對象,但其實與第三類一樣都是以理論作為研究的結果,應該屬于一般認識上的理論研究。兩者的區(qū)別在于路徑的不同,即到底是從理論到理論,抑或是從實踐到理論。當然,這兩類研究也有交叉之處。
好的理論簡單準確,不僅能夠解釋現象,更能夠發(fā)現規(guī)律、指導實踐、預測未來……但是,任何理論都不是紙上談兵,歸根到底都是源于實踐。放眼其他任何應用學科,無論是經濟學、管理學、法學,還是建筑學、工程學、醫(yī)學,真正的影響巨大的理論家無一不是該學科的優(yōu)秀實踐者。而真正完全從事理論研究,并還能夠產出優(yōu)秀理論成果的學者,在一個應用型學科中雖然不能說絕無僅有,但都只占很小的比例。必須要有大量的實踐研究對真實的行業(yè)實踐進行關注、觀察與分析,以此作為整個學科的學術積累,在此基礎上,方能產生優(yōu)秀的理論。同時,設計在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工程科學之間的位置,也決定了其文化性思考必須建立在創(chuàng)造性實踐基礎上,這也正如李立新教授所說:“設計要實現為‘人’服務的目標,那就必須關涉到不同文化、不同生活中的不同的人,也就是植根于中國設計實踐的土壤。”[10]而目前問題的嚴重性在于,國內設計學術界過于偏好前述第二種類型的理論研究。
其實,祝帥自己也曾經撰文指出過當前國內設計理論研究的諸多弊端,即“更多集中在歷史研究、文獻研究、人文研究,集中在對于美術史學科的模仿和復制,對當代問題關注不足、對產業(yè)實踐關注不足”。[13]對此,筆者深表贊同。只是與祝帥更強調設計理論研究的自身調整與轉變不同,筆者更堅持認為,這一改變,僅僅依賴設計理論研究者自身隊伍是不夠的,畢竟專門從事理論研究的學者人數有限、力量有限。設計學整體的發(fā)展必須要以來立足于實踐的研究成果作為主體。
進一步講,按照以上的分析邏輯,筆者認為實踐研究其實也可以分為兩類:基于實踐的研究(Research on Practice)、為了實踐的研究(Research for Practice)。前者以實踐為研究對象,后者以實踐為研究目的。與理論研究類似,僅僅從實踐到實踐,沒有理論依據與思維邏輯、沒有歸納整理與知識總結的項目報告并不值得提倡。真正的實踐研究應該或者以理論作為依據、工具或起點,或者能夠從實踐中揭示問題,或者總結出可信的、可傳遞的理論知識點,只有這樣進行的實踐研究,才能夠與前述兩種類型的理論研究之間架起橋梁,形成完整的研究鏈條。(表2)

表2 筆者構想的理論研究與實踐研究的關系
過于強調設計理論在整個學科研究體系中的地位,甚至以此作為評價標準,存在著兩方面的危害:
1.目前國內設計學研究的主體,也就是研究者,絕大多數是從事具體實踐的設計師,設計理論的學者僅占很小比重。如果夸大設計理論的研究傾向,甚至以此作為評判標準,大多數從事設計實踐的研究者將無所適從,會被動地、削足適履式地去從事原本自己并不擅長的從理論到理論的研究工作,反而會產生一大批空話連篇的文章,自己真正的研究成果反而沒有展示出來,沒能與同行溝通交流。
2.對于本身從事理論研究的學者,夸大理論研究的重要性會進一步拉大理論與實踐的距離。畢竟對于這部分學者而言,坐在書齋里東拼西湊、尋章摘句式地搭建理論框架,或者僅僅為了滿足學術好奇心,以主觀性很強的定性方法來做研究,要比走出象牙塔,面向真實社會情境,立足日新月異的行業(yè)發(fā)展來尋找課題,深入研究容易得多。缺乏豐富的實踐經驗,任何設計理論家都無法為真實的設計問題尋找到解決方法。
三、學科導向:設計學的基礎是不是審美?
祝帥還談到:“設計學學科建設還是應該立足于‘藝術學’這一學科門類本體的基本定位。……對于設計學的建設來說,有眾多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的加入,有利于把設計界的討論及時地與諸人文學科的成果相聯系,……但是分工、訓練的不同,其他學者的強項并不在于對于設計作品從藝術審美和視覺品位等方面直接做出判斷和評論,而這方面卻無疑是設計史乃至設計學科建立的重要基礎。只有從這一原點出發(fā),作為一門學科的設計學才能夠具備‘學科獨立’的條件。”[1]對于祝帥的說法,筆者同意一部分,即當有眾多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加入設計研究時,設計界必須要有自己的分工和強項。但是,這個分工絕不能僅僅限于藝術審美和視覺品位這一個方面。
誠然,人在接收信息時,80%的信息是通過視覺方式接收的,這也是為什么視覺美化手段會成為設計實踐活動的主要方式。但是,美化并不是設計的全部手段,或者說只是一種基本的手段。當面對真實社會情境時,設計師往往要解決復雜得多的問題,包括生產、制作、流通、消費等等各個環(huán)節(jié)。如果僅僅憑借“好眼力”“好手藝”和“好品位”,任何設計師在面對真實問題時都將會手足無措。
那么,設計師要解決的真正問題是什么?如果說設計的目的不只是“美”,那么它還包括哪些內容?歸根結底,設計學的真正“原點”,或者說學科導向是什么?
筆者在此仍以管理學為例進行比較。管理是指在特定的環(huán)境下,管理者通過執(zhí)行計劃、組織、領導、控制等職能,整合組織的各項資源,實現組織既定目標的活動過程。管理學的學科導向,或者說核心概念很明確,就是“績效”。“管理學研究的問題,都與組織績效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無論一種管理思想或管理模式,一種管理風格或管理行為,還是管理決策中的一項具體論斷,管理學研究關注的是它們對組織績效的影響,而不是其他的人類學或社會學方面的意義”。[11]有了目的,一項活動才能夠良性開展;有了核心概念,一門學科的研究工作才能夠順利進行。而反觀設計學,這個核心概念似乎始終都不是很明確,究其根源,正在于對設計活動本身的目標指向也始終是不確定的。

表3 日本優(yōu)良設計獎現行評審觀點

圖1 寺廟零食俱樂部
從設計歷史角度來看,如果籠統(tǒng)地把“好”作為設計的目標指向的話,那么這個“好”(Good)的內涵始終是極其復雜的,或者說一直處在變動發(fā)展中。盡管設計學被設置在藝術學的大門類下,但現代意義上的設計從誕生之日起,就沒有將“美”作為自己的核心訴求。以威廉·莫里斯為例,很多人對他的理解是他以藝術家的身份參加產品制造過程,卻沒有看到他另一個更重要的身份——社會主義者。他之所以被譽為“現代設計之父”,絕不僅僅是源于其在室內設計、墻紙圖案、書籍裝幀等方面的形式探索,而是因為他賦予了設計以更多的內容。在他的心目中,好設計并不等于僅僅有著美好形式的設計,真正的好設計包含著設計者的快樂、使用者的快樂甚至包括我們后代的快樂。比如,在他的理想中,真正的藝術品要在愉快中生產,并且在生活中愉快地使用,這兩者之間是相互關聯的。還比如,他在很早就提出類似于“藝術化生存”的觀點,富于遠見地指出藝術遲早要從純粹的藝術品擴展至日常生活用品,甚至擴散滲透至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盡管后來曾做過駐英國大使的穆特修斯把英國的設計思想帶到了德國,調整了好設計的標準,培育了一個以標準化為基礎,體現工業(yè)之美的制造業(yè)系統(tǒng),并有力推動了經濟的發(fā)展。但二戰(zhàn)后的德國設計界,再次對好設計的標準予以反思,并由迪特·拉姆斯推出了集現代主義設計思想之大成的“好設計十準則”(創(chuàng)新、有用、審美、易被理解、不顯眼、誠實、持久、關注細節(jié)、環(huán)境友好、盡可能少)。這十大原則幾乎涵蓋了真、善、美的所有范疇。在此之后,好設計的標準仍在不斷被補充或調整。其中,日本優(yōu)良設計獎(Good Design Award)的評選標準的變化就非常具有代表性。1957年,該制度初設時的評價標準有六條:以功能和形態(tài)的融合為目標,具有獨創(chuàng)性;適合量產;成功地將材料特性直接而有效地運用;立足于科學技術;經濟適用;符合人類使用(近代感覺與使用感)。可以說與拉姆斯的“十原則”有異曲同工之妙。而現行的評價標準則要求評委從“人類”“社會”“產業(yè)”“時間”四個視點切入,綜合考察參評對象(具體表述參見表3)。評審標準的變化,是時代變化帶來的對于設計要求變化的最直接體現。[14]2018年,優(yōu)良設計獎年度設計大獎被授予了發(fā)起“寺廟零食俱樂部(Otera Oyastsu Club)”(圖1)的凈土宗僧人松島靖朗。這一以守護貧困家庭為主要訴求的慈善項目可以說幾乎與傳統(tǒng)意義上的藝術設計毫無關系,但卻憑借其積極的行動力量和強大的人文關懷打動了所有評委。筆者認為,該項目的優(yōu)秀之處正在于它真正發(fā)揮了設計在聯結人與物的關系上的無窮潛力與巨大價值,可謂實至名歸。
簡單地回顧歷史,可以看出,對于設計的概念原點,無論實踐者還是理論家,盡管有不同的解釋和看法,盡管在不斷地調整變化,但都沒有將形式審美作為設計的唯一立足點。好設計的標準,設計的終極指向,始終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不斷豐富和擴展。無論是Beauty、Nice,還是Good,歸根結底,設計之本,還是立足于人類自身與造物之間的關系,立足于生存、生產與生活的美好。
結語:設計學科的間性特質
方曉風教授曾經撰文指出設計學的兩大屬性:綜合性與實現能力。[15]其中,綜合性,或者說跨學科性是設計學科最顯著的特征,但同時也是導致其自身極為容易迷失方向的特征。祝帥在文章結語中也總結到:“在不同的語境中提出不同的對策,強調設計學學科構成中的不同側面,這并非立論者的自相矛盾,也并非意在爭取哪一種學科范式在設計學中的主體地位,而恰恰說明了設計學自身在不同學科之間‘變動不居,周游六虛’的定位。這是設計學交叉學科特點的必然表現,它也彰顯出設計學‘學科間性’的存在已經成為學科建設與發(fā)展中的一種新常態(tài)。”[1]這說明,祝帥也意識到了設計學的綜合性和模糊性的矛盾問題。但是筆者還想進一步在此基礎上強調設計學的間性特質的重要性,因為這實際上也是設計學的“自我意識”。不論其如何“周游六虛”,自我認知與自我展示仍是學科立足的根本。
筆者認為,要理解設計學的間性特質,必須要回到間性問題提出的本初載體——文化間性以及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他者”上來。巴赫金曾經說過:“構成自我意識最重要的行為取決于跟他者的關系。”那么,這種關系的性質是什么?自我又如何在這種交互關系中得以呈現?蔡熙指出:“一方面,文化在與“他者”交往中發(fā)生意義重組才有價值,一個文本的現實意義是在與“他者”的互動中生成的;另一方面,文化間性要求進行文化對話,倘若沒有“他者”,那就只能是獨白話語。”[16]王才勇也認為:“跨文化一詞在西語中所指的并不是單純地相遇在一起的不同文化,而是不同文化相遇時發(fā)生的那種交互作用,它指向的顯然不是這些文化的自為存在本身,也不是單純地參與到該交互作用中去的各自文化部分,而是這些部分相遇時發(fā)生意義重組的交互作用過程。”[17]不難看出,這兩句話的關鍵都在于“意義重組”。從文化間性類推到學科間性,筆者的理解是,同樣不能孤立地將設計學的間性特質看作是一種靜態(tài)的概念,而是要將它們放到與“他者”(即其他學科)發(fā)生關聯的動態(tài)過程中去看。即當面對具體問題或真實情境,設計學與其他學科相遇并發(fā)生交互作用時所顯現出的動態(tài)特質。從這層意義上看,設計學科范疇的開放性,導向的豐富性、多樣性,以及其強大的解決問題的實現能力反而會成為跨學科交互作用中之鮮明特征。否則,如果只是單一地依賴參與其中之各學科既有的、固定的思維導向與行動模式,就只能解決或滿足一般的、已有的問題或需求,而在面對當前現實中更復雜的、全新的所謂“抗解問題”時,便無法真正介入其中。這也是設計學科最重要的間性特質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