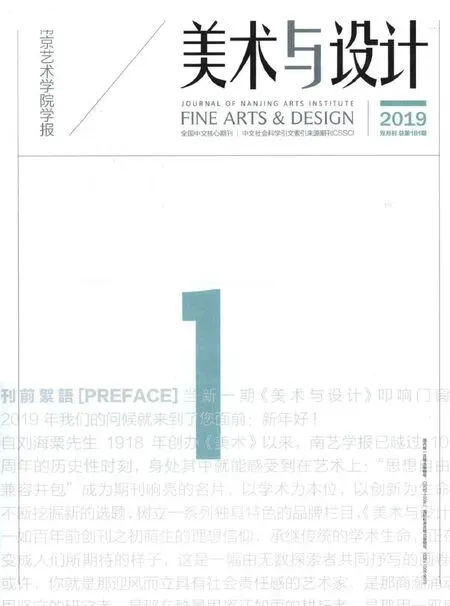《華燈侍宴圖》的政治意涵探究
陳 勁(山東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山東 濟南250100)
南宋宮廷專設畫院與北宋畫院一樣,專門負責為宮廷作畫,其代表畫家有馬遠、夏圭、李唐、劉松年等人。馬遠,號欽山,祖籍河中,靖康后遷居錢塘,其山水皴法蒼勁雄奇,樹法瘦硬如鐵,墨法簡率淋漓,常用渲染手法展現虛曠的景色,并將主景布于畫面一角,意境深遠,因此被稱為“馬一角”。馬遠的傳世作品有《華燈侍宴圖》《踏歌圖》《山徑春行圖》《寒江釣艇圖》《松下高士圖》等。尤其以《華燈侍宴圖》為代表,忠實描繪了南宋宮廷夜宴的場景。我們通過分析馬遠的《華燈侍宴圖》,將政治史與美術史的研究相結合,以期判斷南宋院畫所體現出來的政治意涵,從而在美術史的研究方面增添新的價值。

一、馬遠生卒年再考
首先需要確定一下《華燈侍宴圖》作者馬遠的生卒年。
現下十分流行的觀點認為,馬遠是生活在光宗和寧宗兩朝的畫院待詔。然而,根據南宋時人周密《齊東野語》的記載道:
“理宗朝待詔馬遠畫《三教圖》,黃面釋子一跌枷上座,猶龍翁儼立于旁,吾夫子乃作禮于前,蓋內令作此以侮圣人也。”
“宋理宗朝巨珰有侮吾夫子者,令馬遠畫一佛,中坐老子,側立孔子問禮于前,俾江古心子遠贊之,子遠立成曰:‘釋迦趺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1]
宋理宗(1224-1264期間在位),可見馬遠應當至少活到了寧宗嘉定十七年(1224)之后。查閱資料,宋理宗一朝的大珰(大宦官)唯董宋臣囂張跋扈,且無視禮教,其活躍時間約在1255年左右,若根據以往馬遠生年1140年推斷,此時的馬遠已在110歲上下,必不符合常理。
對這個問題,傅伯星先生早在20年前就做了一番較為正確的論斷。
“馬遠的生年應定在約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定卒年為約宋孝宗(有誤,當為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也許較為合理。”[2]
但是,傅伯星先生在此有一個疏忽,南宋詩人張镃對馬賁乃是馬遠祖父的記載略有錯誤。
宋末元初的莊肅在《畫繼補遺》中認為,馬興祖是馬賁的裔孫,“賁之裔孫,紹興間隨朝畫手,高宗駐蹕錢塘,每獲名蹤卷軸,多令辨驗”,未說清馬興祖與馬賁之間的確切關系。
元代末年《圖繪寶鑒》所描述之“佛像馬家”世系,也只是稱馬遠祖父馬興祖乃“賁之后”,并未詳細說明馬興祖是否是馬賁之孫或之子,故存疑。現將其世系列舉如下,茲供參考。
“馬賁,河中人,宣和待詔。工畫花鳥、佛像、人物、山水,尤長于小景。[3]87
“馬興祖,河中人。賁之后,紹興間待詔,工花鳥、雜畫,高宗每獲名蹤卷軸,多令辨驗。[3]104
“馬公顯,弟世榮。興祖子,俱善花禽、人物、山水,得自家傳。紹興間授承務郎,畫院待詔,賜金帶。世榮二子,長曰逵,次曰遠,世其家學。[3]101
“馬遠,興祖孫,世榮子,畫山水、人物、花禽,種種臻妙,院人中獨步也。光、寧朝畫院待詔。[3]104
“馬逵,遠兄,得家學之妙。畫山水、人物、花禽,疏渲極工,毛羽燦然,飛鳴生動之意態逼真,殊過于遠,他皆不逮。[3]104
在馬公顯是馬遠之伯父抑或其孫的問題上,夏文彥的《圖繪寶鑒》與《畫繼補遺》有較大的出入。《畫繼補遺》記載:“馬公顯,遠之孫也,傳家學,畫不逮厥祖。”而《圖繪寶鑒》記載:“馬公顯,弟世榮。興祖子,俱善花禽、人物、山水,得自家傳。紹興間授承務郎,畫院待詔,賜金帶。世榮二子,長曰逵,次曰遠,世其家學。”
兩宋之際的鄧椿在《畫繼》中記載:
“馬賁,河中人……本佛像馬家后,寫生馳名元祐、紹圣間。”[4]
與馬賁同一時代的北宋書法家米芾(1051-1107)在其《畫史》里稱:
“程坦、崔白、侯封、馬賁、張自方之流,皆能污壁。”
米芾的《畫史》約成書于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前后,而鄧椿亦是宋徽宗宣和、靖康年間人物,二人所聞見當具有一定可信度。根據鄧椿說法,馬賁馳名元祐、紹圣年間(1086-1098),以馬賁約北宋嘉祐五年(1060)左右生,至元祐、紹圣年間成名,到宣和年間為畫院待詔已是65歲左右。
綜合鄧椿、米芾、莊肅與夏文彥的記載,馬賁有可能是馬遠的高祖父甚至或是同支的高伯祖父,則馬遠祖父馬興祖的活躍時代約在靖康末年,最遲不超過紹興三十二年(1163),而馬遠之父馬世榮應該在其父于臨安穩定之后一段時間出生,約莫活躍于整個紹興時期。
在史料的記載中,馬賁與馬興祖之間的關系一直含混不清。若按照上述推斷,馬賁與馬遠祖父馬興祖之間似乎還有多人未入記載,由于山西馬氏家族在北宋時代曾先為民間畫手,地位較低,并非人人皆為宮廷畫家,可以大膽猜測,經歷了靖康之變的馬氏家族,也可能受到兵禍的無端牽連。至元明清時期,《圖繪寶鑒》和莊肅《畫繼補遺》等也只是按照畫家世系和每個畫家的擅長、畫法特征而收錄,并非調查、統計戶口的冊簿,而隨著戰亂的發生,大量資料的散落,也致使后人對這段往事不甚了解,故未能入載。
所以,馬遠高祖馬賁約于1080年-1090年前后生馬遠曾祖父馬某。即,馬遠與曾祖馬某相隔三代人,年齡差大約在100年左右,那么馬遠的卒年下限不會超過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生年上限則有可能更晚一些,可能在宋孝宗淳熙七年到淳熙十二年(1180年-1185)前后。①對馬遠的生卒年,國外亦有漢學家如美國密歇根大學教授Richard Edwards在How Real is Real: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ainter's Eye文中直接將馬遠生卒年定為1190-1235.然而Richard Edwards教授忽視了史料對馬遠的記載,也并未系統分析馬遠卒年定在這個時間段的具體原因。
現下有種觀點認為:“馬賁寫生馳名元、紹間必在60歲左右。”[5]但比馬賁略晚一段時間的畫院待詔王希孟,年僅18歲就已享譽中外,其青綠山水《千里江山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更是流傳千古,為人所共賞。更何況“佛像馬家”是馬賁世傳家學,不用人稱道就已馳名江湖,所以其年齡并非問題。
而史錄馬遠乃“光、寧朝畫院待詔”,恐是誤載,實則馬遠成為待詔后的主要活躍范圍是宋寧宗、理宗二朝,絕非光、寧時期。
二、《華燈侍宴圖》的宴會性質和地點

圖2 南宋臨安皇城圖 據《咸淳臨安志》
宋代宮廷宴會分為官方宴會和私人宴會。從北宋起,有三種類型的官方宴會,春秋、圣節和飲福大宴。
“宋代官方宴飲名目較之前代更為繁多,就宴飲性質而言,可分為國家大宴、君臣共宴和君民共宴三個類別。”[6]
“在宋代豐富多彩的官方宴飲活動中,隸屬國家大宴的春秋、圣節和飲福三大宴即產生于北宋初期。”[7]
“宋制,嘗以春秋之季仲及圣節、郊祀、籍田禮畢,巡幸還京,凡國有大慶皆大宴。”[8]2683
私人宴會有曲宴、聞喜宴和節日賜宴等,較為隨意和輕松。每一種宴會都有其特殊的禮儀和規制,官方宴會中的春秋大宴在北宋滅亡前就已經消失,圣節和飲福宴則一直延續到南宋后期。且圣節是皇帝的生辰,每年接受大臣及金使賀表舉辦一次,不受時間的限制。
因此,首先可以排除馬遠《華燈侍宴圖》所描繪的并非是春秋兩次的國家大宴。那么有沒有可能是宋寧宗的圣節大宴?
“惟正旦、生辰、郊祀及金使見辭各有宴,然大宴視東京時亦簡矣。”[8]2691
“國朝故事,帝、后生辰皆有圣節名。后免之,只名生辰,惟帝立節名。”[9]
雖然南宋時期的圣節大宴已經變得相對簡樸,但圣節大宴的規模也應該不亞于春秋兩次的國家大宴。據史料載,宋寧宗時期的圣節稱“瑞慶節”。
“乾道四年十月丙午,生于王邸。”[10]713
“九月己巳,命趙汝愚朝獻景靈宮。……甲戌,下詔撫諭諸將。改天佑節為瑞慶節。”[14]716
在宋寧宗統治的十七年間,已知較明確的就有過五次罷瑞慶節大宴。
第一次是太上皇宋孝宗紹熙五年(1194)崩,按照宋朝祖制行三年大喪。因太上皇宋孝宗趙昚無遺詔,遂按照宋太祖祖制和《儀禮》規制,分別對外服二十七日和對內服三年大喪。
“紹熙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以皇帝在重華宮大行至尊壽皇圣帝(宋孝宗)喪次,請聽政。凡三上表固請,乃允。”[11]
“十一月……辛亥,雨木冰。詔行孝宗三年喪制,命禮官條具典禮以聞。”[10]717
而慶元三年十一月六日,太皇太后吳氏崩,下詔宋寧宗服喪三日,以日易月。按照禮部和太常寺的記錄,實際仍為憲圣太后服喪三年。
“三年十月,后寢疾,詔禱天地、宗廟、社稷,大赦天下,逾月而崩,年八十三。遺誥:‘太上皇帝疾未痊愈,宜于宮中承重;皇帝服齊衰五日(應為三日),以日易月。’詔服期年喪。”①以日易月:古代喪禮.父母之喪,服喪三年,自漢文帝始以日易月,縮短喪期,謂之”易月”.晉書`禮志記載: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污隆,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
“慶元三年十一月六日,壽圣(降)[隆]慈備福光佑太皇太后崩于慈福殿,遺誥皇帝成服三日聽政。九日,釋服。十日,宰臣京鏜等上表請還內聽政,三表乃允。二十一日,復請御殿,復三上表固請,始詔權御后殿。”[11]
“(慶元)五年六月十九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憲圣慈烈皇后大祥②大祥:十三月小祥祭,二十五月大祥祭。前,禮例合塑制神御,于大祥后迎奉赴景靈宮后殿,于憲節皇后神御之次奉安。”
故慶元元年至六年,因為宋孝宗和太皇太后吳氏的相繼去世,南宋宮廷應無慶賀宋寧宗生辰之宴會,
第二次是因為太上皇宋光宗的突然駕崩,依例三日聽政,對內服三年大喪。
⑦支撐氣袋的鋼閘門作為氣袋的護盾,保護氣袋,避免被浮木、礫石、冰塊等雜物破壞,使用壽命長,通常的使用壽命都在30年以上。
“(慶元)六年六月四日壽仁太上皇后(宋光宗皇后李鳳娘),八月八日圣安壽仁太上皇帝(崩)。”[12]225
“(慶元六年)八月庚寅,以太上皇(宋光宗)違豫,赦。辛卯,太上皇崩。”[10]727
慶元六年(1200年),太上皇后李氏、太上皇宋光宗以及宋寧宗的第一任皇后韓氏相繼去世,故三年內無圣節大宴。
第三次罷于“開禧北伐”初期的開禧二年(1206)。
“冬十月戊申朔,詔內外軍帥各舉智勇可將帥者二人。辛酉,以將士暴露,罷瑞慶節宴。丙子,金人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10]742
第四次則是韓侂胄北伐失敗之后的開禧三年。此年,宋軍大敗于金軍,謝太后崩。
“開禧三年五月十六日壽成惠圣慈佑太皇太后(謝蘇芳)崩,亦如之。……嘉定二七月成肅皇后大祥禮畢,亦如故事。”[12]224
“宋制,……凡國有大慶皆大宴,遇大災、大札則罷。”[8]2683
在一個國家和社會出現動蕩和災異的情況下,身為一國之君的宋寧宗絕不可能為自己慶祝圣節,這是符合祖制的做法。
綜上所述,慶元元年到開禧三年,宋廷因宋孝宗、太皇太后吳氏、宋光宗、太上皇后李氏、恭淑韓皇后和太皇太后謝氏的相繼去世,舉行瑞慶節大宴的可能性較小。而自宋寧宗嘉定九年開始,金宣宗突然發動對南宋的侵略戰爭,開始了長達十余年的宋金交戰,南宋陷入內外交困之境。同年二月起至十月,四川諸州連震不斷。嘉定十年,金朝因蒙古壓迫,大舉攻宋以拓展戰略空間。四月,宋金交戰,金軍大敗;六月,宋寧宗下詔伐金。自嘉定九年至嘉定十七年,宋金兩國連年征戰。在此期間還發生了歷史上著名的棗陽之戰(1217-1219)。正是因為涂炭生靈的戰爭以及各地的天災人禍,南宋朝廷不得不取消圣節宴會。在嘉泰三年到開禧元年的3年里,嘉定三年到嘉定八年(1207-1215)的4年間(除去嘉定六年),楊桂枝已成為皇后,且此時朝廷無喪,因此這七年有可能辦過圣節大宴。
但是據史料所載,北宋徽宗時期的一次圣節,僅參與者就不下千名,且有樂舞相伴。
“第五盞御酒,.....參軍色執竹竿子作語,勾小兒隊舞。小兒各選年十二三者二百馀人,列四行,每行隊頭一名,四人簇擁,并小隱士帽,著緋綠紫青生色花衫,上領四契義束帶,各執花枝排定。…… 第七盞御酒慢曲子,宰臣酒皆慢曲子,百官酒三臺舞訖,參軍色作語,勾女童隊入場。女童皆選兩軍妙齡容艷過人者四百馀人。”[13]
“徽宗以十月十日為天寧節,定上壽儀:皇帝御垂拱殿,群臣通班起居畢,分班,從義郎以下醫官、待詔等先退。知引進司官一員讀奏目,知東上閣門官一員奏進壽酒,由東階升,舍人通教坊使以下贊再拜,奏圣躬萬福,又再拜,復位。……贊拜,舞蹈,又再拜,西出。親王以下赴紫宸殿立班。引進官宣‘進奉出’,天武奉進奉以出。閣門復立殿上,教坊使贊送御酒,又再拜,教坊致語訖,贊再拜,退。次樞密官上壽,次管軍觀察以上上壽、進奉并如儀。內侍舉御茶床,舍人贊教坊使以下謝祗應,再拜訖,閣門側奏無公事。”[8]2689
而馬遠《華燈侍宴圖》中記載,僅有十余位舞女,規模遠遠小于圣節大宴,必然不是宋寧宗“瑞慶節”的畫面。
《華燈侍宴圖》圖寫了南宋宮廷夜宴的場景,然而重點并不是夜宴,而是侍宴,為我們展現了當時的政治生態。其題畫詩更是直接描述了當時宴會的情形。目前針對該題畫詩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屬宋寧宗真跡;著名書畫鑒定家徐邦達先生曾在《南宋帝后題畫書考辯》[14]文中認為,《華燈侍宴圖》題畫詩是寧宗真跡,卻沒有直接證據,故存疑。另一種觀點認為是宋寧宗第二任皇后楊桂枝的真跡。這類觀點較為普遍,尤其以臺北江兆申先生的研究最為詳細,他以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楊皇后題畫及書法作品互為參照,論據充分[15]。
馬遠、馬麟父子的畫作往往由楊皇后題之,甚至有些署名楊妹子。經過歲月變遷,在這個問題上,元明清三代部分學者還造出了一樁公案,明代陶宗儀在《書史會要》中收錄、評價了“恭圣仁烈楊皇后”的書法特點,卻又別立“楊氏”條目,稱:
“寧宗皇后妹,時稱楊妹子,書法類寧宗,馬遠畫多其所題。”[16]
明代復古派巨擘王世貞道:
“畫凡十二幀……其印章有楊娃語,長輩云,楊娃者,皇后妹也……按遠在廣寧朝后先待詔藝院,最后寧宗后承恩執內政,所謂楊娃者,豈即其妹耶?”[17]
對楊皇后、楊妹子、楊娃、楊婕妤之間的關系,啟功先生在二十年前曾進行過一番詳細論述。啟功先生根據宋代的史料和馬遠、馬麟畫后的印章內容提出反駁,確定這種觀點是陶宗儀和王世貞等人的誤讀,楊皇后和楊妹子、楊娃、楊婕妤實為一人。
古人認為畫寫物外形,詩傳畫中意,題畫詩的功能可以彌補畫作的不足并借以敘述、傳達畫作想要表達的內涵。《華燈侍宴圖》的題畫詩為我們提供了有用的信息,有助于我們分析“華燈侍宴”到底是什么類型的宴會,可能有哪些身份的人參加此次宴會,并嘗試分析其體現的政治內涵。題畫詩內容如下:
朝回中使傳宣命,
父子同班侍宴榮。
酒捧倪觴祈景福,
樂聞漢殿動驩聲。
寶瓶梅蕊千枝綻,
玉柵華燈萬盞明。
人道催詩須待雨,
片云閣雨果詩成。
此詩系楊皇后所題七言律詩。題畫詩首聯中“父子同班”一句,暗示次宴會的性質,是一次較為隨意的私人宴會。而頷聯和畫中的宮女表明這是一次有樂舞助興的宴會。
“曲宴。凡幸苑囿、池籞、觀稼、畋獵,所至設宴,惟從官預,謂之曲宴。”[8]2691
宋代宮廷私人宴會,一般而言是曲宴。皇帝舉辦曲宴賦詩、賞花、飲酒等活動,以起到加深主仆之間關系的作用。曲宴的規模不大,僅限于室內進行,且沒有舞蹈。但也有例外。
“次宴紫宸殿,小宴垂拱殿,若特旨則不拘常制”[8]2683
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
“召宰相近臣賞花于后苑,上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詞臣各賦詩。’賞花賦詩自此始。”[18]
宋徽宗時期的曲宴已有樂舞助興,而且隨意性很大,并非全部按照規制進行。從現今所流傳的《德壽宮舞譜》來看,內廷舞蹈發展到南宋時期已經摻雜了許多民間藝術形式,且基本以雜劇和戲曲為主。可見南宋宮廷的欣賞趣味和民間已經逐步趨同,而作為圣節舞蹈的大曲比如鼓板也逐漸由民間傳入宮廷。由此窺知,《華燈侍宴圖》中的十六人舞蹈很可能并非是沿襲禮樂的傳統舞蹈,而是由南宋教坊使自制,為了適應南宋宮廷政治和審美需求的樂舞,其功用是專門服務于曲宴等類型的私人宴會,而不用做圣節、祈福、郊祀大宴的端莊和正式場合。
頸聯“寶瓶梅蕊千枝綻”,此句隱喻了多重含義。
首先是此次宴會所舉辦的時間應當在一年中的歲末或初春,正是梅花盛開的時節。另外,題畫詩中“寶瓶”的出現應作何解釋,從圖中來看,梅花環繞宮宇,并沒有出現寶瓶的身影,而對照下一句“玉柵華燈萬盞明”,似乎可以解釋為對仗而作。但也許將它理解成保證和平、保證平安更為妥當。這說明此次宴會可能在某次戰爭前后舉行。開禧二年(1206),韓侂胄北伐,此時韓侂胄的侄女韓皇后雖然已經去世,但韓侂胄在朝中卻仍然大權獨攬,一手遮天。在戰備不足的情況下,韓侂胄貿然發動了對金朝的戰爭。朝野上下皆認為將帥庸愚,軍民怨恨,不可輕舉妄動。北伐前一年,韓侂胄集兵權財權于一身,位高權重,早已聽不進一切建議。
而對頷聯“梅蕊”的解釋也有兩種。
首先,梅蕊是梅花的蓓蕾,于臘月前后綻放,古人常常詠梅、寫梅、畫梅,梅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高尚和堅強的品質。頷聯所謂“寶瓶梅蕊千枝綻”,似乎讓人不經意聯想到楊皇后的閨諱——桂枝,語氣十分喜悅,可見這次宴會的氣氛應該非常融洽,而且對楊皇后十分有利。
其次,《華燈侍宴圖》中描繪的宴會場景可能是簪花的過程。簪花風俗由來已久,從隋唐時期開始就有了女子簪花的習俗。至宋真宗以后蔚然成風,無論男女老少,上至皇帝嬪妃、大臣宦官,下到平民百姓、強盜流氓,都有頭上簪花的習慣。甚至有人以頭滿花為自豪,韓侂胄的三夫人就被譽為“滿頭花”。
宋代宮廷中既有簪假花的習慣,也有簪生花的風俗。簪花種類的不同象征著皇帝的權威和大臣的等級。同時,梅花亦是兩宋百姓和宮廷所喜愛的重要簪花花種之一。南宋陸游、范成大、楊萬里等人有大量詩句描繪民間簪梅花、賞梅花的習俗。
“春情閑過野人家,邂逅詩人共晚茶。歸見諸公問老子,為言滿帽插梅花。”
根據記載,南宋宮廷中大規模種植梅花的場所是德壽宮后苑(原秦檜府邸)。
“以人工開鑿的占地十余畝的小西湖為核心,亦會東、西、南、北四‘地會’布置,每‘地會’均有自己的特色。……東區以賞名花為主。香遠堂賞梅花,清妍堂賞酴醾,清新堂賞桂花集木香,芙蓉閣賞芙蓉……其間栽以菊、松、竹,環成三條小徑,宛如一個繁花似錦、四季飄香的花囿。小西湖內種有千葉白蓮,湖中筑一堂稱至樂堂,可容教坊樂舞。”[19]
香遠堂周邊是小西湖的荷花池,在香遠堂附近有一處梅坡,遍栽梅花。周必大《玉堂雜記》云:
“宮中分四地分,隨時游覽。東地分香遠堂(梅)、清深堂(竹)、月臺、梅坡、松菊三徑(菊、芙蓉、竹)、清妍(酴醿)、清新(木犀)、芙蓉岡。”[20]
而《華燈侍宴圖》中所描繪的宮殿也與德壽宮所處的地理位置相吻合。據南宋度宗咸淳四年《臨安志》的記載,恭圣仁烈皇后的住宅位于臨安城西部的清波門附近,德壽宮則位于臨安城東部的望仙橋和新開門之間。
據《宋會要輯稿》載:
“(紹熙二年四月十六日)詔:臨安府傳法寺并燒毀居民去處,其寺面南街道為俯近重華宮宮墻,比舊展退北一丈,經燒民居不許搭蓋。”[21]
周必大《玉堂雜記》云:
“某嘗自德壽宮后偶趨傳法寺,望見一樓巍然。朝士云,太上名之曰聚遠。”[20]
2006年,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對南宋德壽宮遺址進行了發掘,可得知,德壽宮為坐北朝南的布局。
“從德壽宮的布局來看,南面是大門,北面是后圃,坐北朝南與大內一致。”[22]
由此可見,德壽宮整體坐北朝南,聚遠樓在北,香遠堂恰好面對著南宋皇城方向的和寧門與東華門,在德壽宮的東部。且《華燈侍宴圖》中大殿背后有一座山峰,應為德壽宮的芙蓉岡或是臨安城外的高山(同樣的高山景色在踏歌圖中也有出現)。因此,根據德壽宮的走向整體呈現東西方向和《華燈侍宴圖》大殿的朝向以及右側走廊的趨勢來看,圖中右側走廊應該通往德壽宮月臺。
不過,德壽宮是孝宗以前舊稱,自孝宗、光宗之后德壽宮改為慈福宮、壽慈宮,但整體形制應無大的改變,楊皇后應該也常在此地舉辦宴飲活動,至宋度宗時期,德壽宮逐漸荒廢。
但凡兩宋宮廷宴會都有簪花的禮儀,甚至較為隨意的私人宴會也會隨手簪花。北宋“四相簪花”的典故就是一次較為隨意的私人宴會上,韓琦將園中盛開的芍藥花分別插在四人頭上,以應祥瑞。《華燈侍宴圖》中只有三位在殿內等候的官員,其具體場景應該是在宴會中途簪梅花、賜梅花的過程,然而圖中沒有出現宋寧宗、楊皇后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簪花習俗“中途更衣”的規制。
而且宋寧宗早在幾年前就已對鋪張浪費、大操大辦的宴會產生了厭惡心理:
“寧宗上元夜,嘗熒燭清坐,小黃門奏曰:‘官家何不開宴?’上愀然曰:‘爾何知!外間百姓無飯吃,朕飲酒何安?’。”[23]
宋寧宗愛惜民力,對舉辦宴會深惡痛絕,他有可能并未參加此次宴會。而楊皇后為了宣示對楊次山父子的寵幸,也為了對內、對外昭示楊氏父子皇親國戚的身份和威權,使用了宋寧宗的御制雙龍璽,又令馬遠事后記錄下了這一重大時刻。乾隆皇帝曾在看過《華燈侍宴圖》的題畫詩之后認為“當時作此圖,以侈一時盛事”,可見彰顯榮寵的成分較多。
“皇家宮廷的藝術通常是用來使觀者相信統治者的德行及其統治的穩固和繁榮。”[24]
雖然我們不能完全確認《華燈侍宴圖》描繪的到底是什么類型的宴會,其有可能是私人宴會,比如賞花、賦詩的曲宴,但也不排除是楊皇后臨時起宴,而又由于楊皇后個人掌有皇帝御筆之權、能,皇帝龍璽亦由楊皇后掌握,想必不通過宋寧宗召集一次宴會并非難事。綜合分析當時的社會背景、宮廷形勢,以及作畫時朝廷內外的政治態勢,這幅畫明顯體現了楊皇后處心積慮想要掌控朝政的政治涵義。
三、《華燈侍宴圖》的作畫時間
針對《華燈侍宴圖》的作畫和題畫時間,有日本學者板倉圣哲認為當定于1198年-1201年之間[25]。他所依據的是《宋會要輯稿》的記載:
“三年十月六日,宰執進呈內批婕妤楊氏親侄、承節郎楊谷等差充合門看班祗候。京鏜等奏:‘兩人未曾呈試,莫若候來春試中而后與,庶不礙法’。”[26]
然而,板倉圣哲先生忽略了這句話的后半段:
“上曰:‘未呈試,于法有礙。’遂已。”[26]
整句話的記載只是針對楊次山的兩個兒子楊谷和楊石,顯然并沒有凸顯題畫詩中“父子同班侍宴榮”的喜悅之情,更未表現出宋寧宗對楊氏父子的特殊榮寵和高貴待遇,雖然這條詔令的背后可能暗含著楊婕妤對宋寧宗的要求,卻由于楊氏二子不符合晉升條件作罷。板倉圣哲先生還認為,整幅畫面上沒有皇后專屬的坤卦印,所以《華燈侍宴圖》應該是楊桂枝成為皇后之前所題。對這個問題,從今傳楊后所題馬遠代表作《十二水圖》以及馬麟之作來看,其大部分均沒有坤卦印,所以我們不能憑此武斷地否定這些畫作不是楊皇后在位時所題。
那么,《華燈侍宴圖》的大概作畫時間是什么時候呢?眾所周知,慶元至嘉泰年間,權臣韓侂胄及其孫女韓皇后一手掌控著內外朝政。雖然恭淑韓皇后于嘉泰元年(1200)去世,朝廷上下仍被韓侂胄把持,就連皇帝御筆也常常是韓侂胄所作。
“初時,御筆皆胄矯為,及是皆慈明所書。”[27]
所以按照常理,此時楊桂枝羽翼未豐,其兄次山雖“沾恩得官”,卻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帶御器械,斷不可能在禁中如此張揚,還讓畫院把賜宴之事記載下來,豈不授人以柄,讓有心之人抨擊楊貴妃與外戚勾結,早早就被韓侂胄盯上,葬送了政治前程?而且,慶元黨禁影響未消,開禧北伐禍端將開,怎能如題畫詩中所描述的那樣氣氛融洽?《宋史》評價楊次山稱:
“次山能避權勢,不預國事,時論賢之。”[28]
又,楊后在淳熙十六年(1189)左右進入慈福宮,慶元元年(1195)封郡夫人,這六年中絕無任何可能題畫。紹熙五年(1194)“紹熙內禪”發生后,宋寧宗以韓同卿之女崇國夫人韓氏為皇后,次年封楊桂枝為郡夫人。楊桂枝才有可能被宋寧宗委以代筆書寫的重任。此類嬪妃以宋高宗“專掌御前文字”“善寫宸翰字”的劉夫人為代表,她因書法出類拔萃寫得像宋高宗,故深得宋高宗喜愛。
“皇后、嬪妃中有不少善書者,有的仿效帝王‘奎畫’,有的酷肖‘官家’筆法,而且可能因此而見寵。”[29]
皇帝身邊的嬪妃有善書者,能夠仿效皇帝御筆,甚至代替皇帝題畫。因此,即便楊桂枝在郡夫人、婕妤、婉儀和貴妃期間,均有代宋寧宗題畫的可能。
但是,楊次山父子在慶元三年(1197)之前還沒有受到恩寵,且馬遠剛剛成年,似乎沒有理由讓楊婕妤為一位未成年的孩子擔保,而且此時南宋宮廷中幾位重要人物還未去世,若題畫,似乎還輪不到地位卑微的楊婕妤。至嘉泰元年(1201),詩人張镃記錄了令馬遠做“林下景”的故事。這說明至少從嘉泰元年開始,約20歲的馬遠已經被眾人所認可。嘉泰二年(1202)楊桂枝正式冊立為后。開禧三年(1207),楊皇后、史彌遠遣夏震在玉津園誅殺權相韓侂胄,而張镃素與韓侂胄有仇,也積極參與謀劃了楊皇后、史彌遠等人誅殺韓侂胄的行動。《齊東野語·誅韓本末》記載:
“于是,楊次山與皇后謀,俾王子榮王曮入奏言:侂胄再啟兵端,謀危社稷。上不答。皇后從旁力請再三,欲從罷黜,上亦不答。后懼事泄,于是,令次山于朝行中擇能任事者。時史彌遠為禮部侍郎、資善堂翊善,遂欣然承命。錢參政象祖嘗以諫用兵貶信州,乃先以禮召之。禮部尚書衛涇、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張镃,皆預其謀。議既定,始以告參政李璧。……彌遠聞之,大懼,然未有殺之之意,遂謀之張镃。镃曰:勢不兩立,不如殺之。彌遠撫幾曰: 君真將種也,吾計決矣。時開禧三年十一月二日。侂胄愛姬三夫人號滿頭花者生辰。張镃素與之通家;至是,移庖侂胄府,酣飲至五鼓,其夕,周筠聞其事,遂以覆帖告變。時侂胄已被酒,視之曰:這漢又來胡說。于燭上焚之。初三日,將早朝,筠復白其事,侂胄叱之曰:誰敢?誰敢?遂升車而去。甫至六部橋,忽有聲諾于道旁者,問為何人?曰:夏震。時震以中軍統制權殿司公事,選兵三百俟于此。復問:何故?曰:有旨太師罷平章事,日下出國門。曰:有旨,吾何為不知?必偽也。語未竟,夏挺、鄭發、王斌等以健卒百余人擁其轎以出,至玉津園夾墻內,撾殺之。”[30]
楊皇后矯詔遣禁軍趁韓早朝時在玉津園“槌殺之”,事后有人向寧宗皇帝稟報韓仛胄死訊,“帝不之信,越三日,帝猶謂其未死”。
“謀悉出中宮及次山等,帝初不知也。”[31]
在“嘉定和議”(1208)前后的這段時間內,楊皇后宴請楊次山父子是為了鞏固自己在朝中的權勢。此前,權相韓侂胄在朝中勢力極大,韓侂胄也曾一度強烈反對宋寧宗立楊桂枝為后。他不僅對楊桂枝出身頗有微詞,甚至直接向宋寧宗獻言不可立楊氏。誅韓侂胄之后,大權才真正落入楊后等人手中。此年,楊皇后46歲,馬遠大約27歲,以古人18歲左右生子,其子馬麟應當在9歲上下。故結合文字與圖像的分析,《華燈侍宴圖》的作畫時間應該在1207年-1209年,也就是開禧北伐結束后,韓侂胄伏誅的三年間,楊次山進封永陽郡王,此時的朝野環境對楊皇后較為有利,比較符合題畫詩中歡愉的氛圍。
結 論
《華燈侍宴圖》富含了深刻的政治內涵,它是在宮廷斗爭和南宋伐金失敗的背景下產生的以題畫詩與山水畫相結合的一幅作品。南宋畫院的馬遠忠實地記錄下了這一隆重的皇家事件,而沒有自己絲毫的感情發揮,即《華燈侍宴圖》象征著帝后對臣子的絕對權威和寵信。賜宴則代表著帝國最高統治者絕不容許任何人對自己進行挑戰;從另一個角度說,賜宴人和赴宴者是鞏固帝國權力的一體兩面,赴宴者獲得與帝后私人宴會的機遇,必定是帝后最為信賴之人;尤其是宴會的私人性質和題畫詩的輕松氣氛讓人感受到畫作贊助人想要向人傳達出一種擁有絕對統治權的自信心,《華燈侍宴圖》中,楊次山父子形象的出現即是這種帝國統治體系的表達和傳遞的中間人,同時也意味著這種帝國統治力在不斷持續鞏固和上升。
總之,《華燈侍宴圖》是在帝國統治者亦即恭圣仁烈楊皇后的授意下,為了恢復由宮廷內亂和開禧北伐帶來的對國家政權信譽和實力的創傷和損害,并借機宣示無上的權力、展示皇家宮廷的審美趣味時刻與民間同步,而且政權是穩固踏實的,以此安撫朝廷之沸議和泱泱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