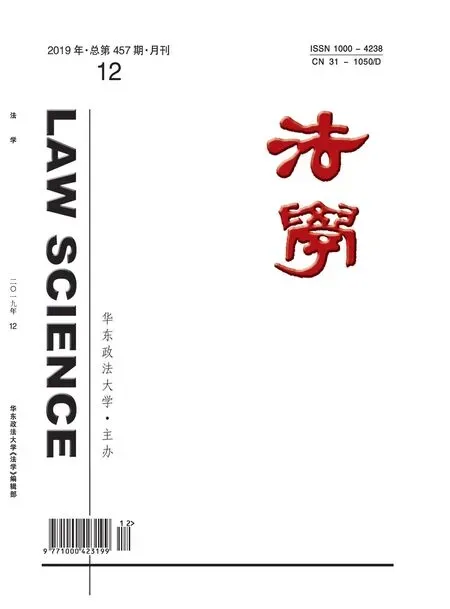法院調取通話記錄不屬于憲法上的通信檢查
●杜強強
一、通話記錄的性質:實踐中的爭議
所謂通話記錄,也稱通訊記錄或者通話詳單,一般是指通信用戶的通話行為在運營商交換機里記錄的各種信息,如通話機組各方的號碼、通話時間、通話時長、用戶姓名等。法院在民事、行政訴訟中能否調取當事人的通話記錄?此類案件在我國時有發生,其所引發的問題值得探討。2003年,湖南省益陽市南縣法院在審理一起行政訴訟案件時,要求該縣移動通信營業部提供某通信用戶的電話詳單,但通信企業以《電信條例》第66條〔1〕參見《電信條例》第66條:電信用戶依法使用電信的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電信內容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對電信內容進行檢查。為由予以拒絕,法院遂對該營業部處以3萬元罰款。之后,湖南省移動通信有限公司向湖南省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提出申請,請求就法院是否有權檢查通信用戶的通信資料作出法律解答。湖南省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認為: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是憲法所賦予的一項基本權利,該項權利的限制僅限于憲法明文規定的特殊情形,也即只有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才有權對通信進行檢查。移動用戶通信資料中的通話詳單清楚地反映了個人的通話對象、通話時間、通話規律等大量個人隱私和秘密,是通信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屬于憲法所保護的通信秘密范疇。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訴訟法調查取證時,應符合憲法的規定,不得侵犯公民的基本權利。湖南省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并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予以解答。2004年4月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作出“答復”,同意湖南省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的上述請示意見。〔2〕參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編:《法律詢問答復(2000—2005)》,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頁。這實際上否定了法院有調取公民通話記錄的權力。
當然,按照憲法和《立法法》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并不是正式的法律解釋機關。雖然2000年《立法法》第55條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工作機構可以對有關具體問題的法律詢問進行研究予以答復”,但這種答復并不具有嚴格意義上的法律效力,不能拘束其他國家機關。從實踐看,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作出上述答復之后,法院因調取通話記錄遭拒而對通信公司進行處罰的案件依然不斷發生。例如,2005年10月,江蘇省東臺市法院因查詢電信用戶機主資料遭拒,而對常州電信分公司某營業廳、常州電信分公司各處罰款3萬元。2006年8月,湖南省江永縣法院請求移動公司協助查詢用戶的通話詳單遭拒,法院對移動公司罰款3萬元。〔3〕參見陳祁陵:《對通信企業拒絕法院調查取證事件的思考》,http://china.findlaw.cn/info/xingzheng/zhianchufafa/cqcf/txzy/102574_2.html#p2, 2019年7月 9日訪問。2017年,湖北利川市法院因調取通話記錄遭拒,對中國移動利川分公司罰款50萬元,并對利川移動公司綜合部信息查詢負責人罰款2萬元。〔4〕參見《拒絕法院調查取證中國移動利川分公司被罰50萬》,http://news.youth.cn/sh/201708/ t20170803_10437257.htm,2019年7月2日訪問。此類案件的頻發,也足見該“答復”實未能解決實踐當中的問題。〔5〕類似案件參見《法院能否向通信公司調取公民身份信息》,http://www.xjcourt.org/public/ detail.php?id=10538,2019年7月2日訪問;《究竟法院有無權力向通信公司調取用戶通訊短信?》,http://glzy.china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16/08/id/2389047.shtml,2019年7月2日訪問;《法院調取當事人通話記錄是否違憲》,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4/05/id/118175.shtml, 2019年7月2日訪問。
饒有趣味的是,在2006年的一個案件中,法院還曾具體闡明了處罰的依據和理由。2006年,江西省銅鼓縣法院到江西宜春移動公司調取案件有關當事人的手機通話記錄及相關資料,該公司工作人員當場出示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上述“答復”的復印件,拒絕提供通話記錄,銅鼓縣法院對該公司罰款3萬元。移動通信公司以《憲法》第40條和《電信條例》第66條為據申請復議,宜春市中級人民法院復議認為:憲法保障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不受任何組織和個人的非法侵犯,但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不是絕對的,還要受國家司法權的必要限制。人民法院調查有關人員的通話記錄并不違反憲法,恰恰是對憲法保障的司法權的貫徹落實。此外,查詢手機的通話記錄及相關資料,并非監聽電話,亦不會對公民的通信自由和秘密構成威脅;同時,從法的效力等級來看,《民事訴訟法》是基本法律,而《電信條例》屬于行政法規,兩者發生沖突時應當以法律為準,因此移動公司的申請復議理由不能成立。〔6〕參見《江西宜春移動公司拒不協助法院調查被罰3萬》,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 /detail/2006/04/id/ 201982.shtml,2019年7月2日訪問。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在此只提到了《民事訴訟法》和《電信條例》的位階關系,而似有意無意回避了《民事訴訟法》與《憲法》第40條的位階關系。《民事訴訟法》誠然要優越于《電信條例》,但《電信條例》第66條不過是《憲法》第40條的翻版,況且電信企業在提出訴求時明確提到了《憲法》第40條,并將其作為拒絕協助的依據。電信企業認為,按照《憲法》第40條的規定,只有法定機關依照法定職權和法定程序,才可以對電信用戶的通信進行檢查,而憲法所列舉的有權主體當中不包括法院。同時,只有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才能依照法定程序進行檢查。因此,法院要求電信公司提供用戶資料于法無據。電信企業的人士認為,法院動輒對電信企業予以罰款,也不利于維護憲法的尊嚴。〔7〕參見薛興華:《法院有權查詢電信用戶資料嗎》,《通信企業管理》2006年第3期。顯然,在法院是否有權調取通話記錄這個問題上,法院和通信企業各執一詞。這場爭議事關對《憲法》第40條上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理解,也牽涉《民事訴訟法》和憲法的位階關系及其優先適用問題,因此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本文接下來首先梳理一下學界對這個問題的討論,然后闡發本文的基本觀點。
二、法院調取通話記錄是否違憲:理論上的討論
(一)合憲與違憲之爭
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作出前述“答復”后,《人民法院報》曾邀請若干學者進行了討論。〔8〕參見張國香、寧杰:《法院調取當事人通話記錄是否違憲——對電信條例“拒絕”法院取證的不同認識》,《人民法院報》2004年5月26日。從討論情況看,學者們對此問題也有不同的觀點,主要有合憲說與違憲說。合憲說認為法院調取通話記錄的做法符合憲法。例如,江偉教授認為,憲法對通信權利的保障并非絕對。不能孤立、片面地理解《憲法》第40條;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除了受《憲法》第40條規定的限制外,還要受國家司法權的必要限制。在民事案件中,法院為審理案件或者執行的需要,可以合法地“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涉案人員對此有容忍司法權介入的義務。蔡定劍教授亦認為,雖然憲法在通信檢查主體上沒有列上法院,但這不排除在特殊情況下(司法訴訟中)經法律授權(民事訴訟法)賦予法院這個權力。只有結合民事訴訟法的規定,才能完整地理解司法權,即一般情況下,法院不得對相關電信資料實施檢查,但在訴訟過程中,法院在取證階段有查閱電信資料的權力。
違憲說則認為法院調取通話記錄的做法未必符合憲法。例如,卓澤淵教授認為,從總體上說法院具有向電話公司進行調查的調查權,但不能越過法定的限度。具體而言,法院只能經由通信公司查詢被執行人的所在地,以便找到被執行人并對其執行,而不能調取通話詳單。因為移動用戶通信資料中的通話詳單清楚地反映了一個人的通話對象、通話時間、通話規律、通話費用等大量個人隱私或秘密,它們都是通信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屬于憲法和法律保護的通信秘密的范疇,對此法院不能調取。姜明安教授認為,憲法的位階高于法律,電信條例雖然在形式上與民事訴訟法不一致,但符合憲法。在解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調查取證權時,就應將調查取證的范圍解釋為不及于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否則,就得修改民事訴訟法。
(二)《憲法》第40條上的加重法律保留
如何從學理上評判上述理論紛爭呢?還是有必要回到我國憲法文本,并以其為據進行討論。《憲法》第40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憲法》第40條在這里明確列舉了通信檢查的特定事由和特定主體,這種條款在理論上屬于“加重法律保留”。〔9〕參見陳新民:《德國公法學基礎理論》下,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1頁。“加重法律保留”屬于法律保留的一種類型。法律保留可以理解為是憲法對立法機關的授權,立法機關因此得以制定限制基本權利的立法。〔10〕參見張翔:《基本權利的規范建構》,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頁。而“加重法律保留”是指憲法對立法機關雖已作出授權,但憲法卻又同時限定立法機關所制定的法律在內容上必須符合憲法所預定的條件,〔11〕或許正因為如此,所以也有人將其稱為“憲法保留”,參見吳庚、盛子龍:《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88頁。不過,從理論上說,憲法保留與加重法律保留仍有不同。如憲法在這里對通信檢查主體的限定。憲法既將通信檢查的主體限定于“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則即便立法機關也不得在其制定的法律中授權“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以外的機關來做通信檢查。〔12〕蔡定劍教授似乎認為,只要有法律的授權,法院就可以合憲地調取通話記錄。參見蔡定劍:《憲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頁。這是“加重法律保留”的應有之義,否則《憲法》第40條對通信檢查主體的特別限定就毫無意義了。毋庸置疑,法院顯然不是這里的“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事訴訟法》第67條雖然授權法院有權向有關單位和個人調查取證,但在涉及通信時的確與《憲法》第40條的精確規定之間存在不盡相符之處。〔13〕正是基于此種理由,有學者即主張《民事訴訟法》第65條構成“適用違憲”,也即《民事訴訟法》第65條有關法院調查取證權的規定在通常情況下符合憲法,但如涉及對通話記錄的調取,則存在違反《憲法》第40條的可能。參見翟國強:《憲法判斷的方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219頁。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法院在民事、行政訴訟過程中調取通話記錄的行為必定違憲。本文認為,對此問題的討論不能只聚焦于法院是否得到了憲法上的授權,而應當在通盤理解《憲法》第40條的基礎上再下判斷。《憲法》第40條是一個基本權利條款,對它的分析宜遵從憲法學上基本權利問題分析的基本框架。〔14〕參見張翔:《基本權利限制問題的思考框架》,《法學家》2008年第1期。從憲法學理論上說,每一項基本權利都保障一個特定的生活關系,這被稱作基本權利的“保護范圍”。就基本權利問題的分析而言,必須先確定某種生活關系是否落入《憲法》第40條的保護范圍,這是分析基本權利問題的“門檻條件”,〔15〕See Robert Post, Recuperating First Amendment Doctrine, 47 Stan.L.Rev.1249,1250 (1995).具有邏輯上的前提性。只有在邁過這個門檻后,才有必要進一步討論國家的某項限制措施是否構成對基本權利的不當干預。這個邏輯上的先后次序不能顛倒。而之前人們對法院調取通話記錄合憲性的討論,似乎太過關注于通信檢查主體這個后續問題,而忽略了其前提,也即通話記錄是否屬于《憲法》第40條保護范圍的問題。實際上,如果通話記錄根本就在《憲法》第40條的保護范圍之外,則完全沒有必要再討論法院調取是否有侵犯通信權利問題,因為這與通信權利風馬牛不相及。因此,本文首先分析討論《憲法》第40條的權利結構,并重點討論通話記錄的定性問題,之后再對法院調取行為的合憲性進行論證。
三、《憲法》第40條的權利結構和保護范圍
按照《憲法》第40條的規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我國憲法學理論通常將其稱為“通信的自由和秘密”,〔16〕參見許崇德主編:《憲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頁。此似嫌冗長;有的簡稱為“通信自由”,〔17〕參見胡錦光、韓大元:《中國憲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76頁。但通信自由只是此項權利的一個方面,似不宜如此簡稱。為了論述的便利,本文權且稱其為“通信權”。這項權利看似渾然一體,但實際上它有著不同的保護范圍。要討論通話記錄是否屬于《憲法》第40條的保護范圍,則有必要先對它的權利結構予以分析。
(一)《憲法》第40條的權利結構
從詞義看,通信本來是人們之間互通消息的載體或者途徑,〔18〕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149頁。但它從一開始就具有私密的性質。例如,即便在造紙術發明之前的秦漢時期,人們也要把寫好的簡牘用泥封住,簡稱“封泥”,以防私自開拆。〔19〕參見辭海編輯委員會編:《辭海》(歷史分冊·世界史、考古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年版,第309頁。造紙術發明后,人們用書信來傳遞信息,書信同樣存在一個密封以及達到后開封的過程。唐代詩人張籍“復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的詩句,〔20〕參見[唐]張籍:《秋思》,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唐詩選》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頁。就表明了書信的這種私密性。盡管隨著社會和技術的發展,通信的載體和形式多有改變,但它的私密性卻一直保持未變。這種不變的私密性應該就是通信的“事物的本質”。法律對通信的保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通信私密性的保護,這也是對人類生活私密性的保護。1954年《憲法》第90條雖只簡單規定“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但因為它涵蓋了通信的私密性,因此自有其理,制憲過程也未見對此有什么爭議。〔21〕參見韓大元:《1954年憲法制定過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88頁。
不過,只強調通信的私密性,卻未必能保護公民在通信方面的全部正當權益。例如在現實生活中,明信片也是一種通信方式,但它具有內容公開的性質,并無秘密可言。〔22〕張明楷教授在闡述《刑法》第252條上的侵犯通信自由罪時即指出,“明信片是隱匿、毀棄的對象,但不能成為非法開拆的對象”。參見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27頁。設若當事人隱匿或者毀棄他人發出的明信片,則嚴格說來并未侵犯通信秘密。對于普通信件而言,行為人單純隱匿或者毀棄他人發出的信件,而不拆封查看信件內容的情形也多有發生。既然未曾拆封信件,就不能說此種行為侵犯了通信秘密,但它毫無疑問是對公民通信利益的侵害。因此,現行憲法將“通信自由”納入保護確有其必要,它更像是一個“兜底條款”,可以涵蓋通信秘密以外的其他通信利益,從而能為公民的通信權提供全面的保障。從這里可以看出,通信秘密保護的是通信的私密屬性,而通信自由保護的是通信私密屬性之外的其他利益。正如許崇德教授所說:“如果只承認通信自由權,而無通信秘密權,公民的通信自由還是得不到保障;相反,如果只承認通信秘密權,而無通信自由權,公民的通信權也就無法實現。因此,這兩個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二者結合起來構成了一項完整的通信自由權利。”〔23〕許崇德主編:《中國憲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22頁。
(二)通話記錄是否屬于《憲法》第40條的保護范圍
由于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有著不同的保護范圍,則在討論某種通信信息的法律屬性時就不能一概而論,而需要分別檢視。有的生活關系可能僅受通信秘密的保護,有的生活關系可能僅受通信自由的保護,有的可能受雙重保護。為了行文方便起見,這里先討論通話記錄是否屬于通信自由的保護范圍,然后再討論其是否屬于通信秘密保護范圍的問題。
在當今電信技術發展迅猛的時代,通話記錄附著有當事人的諸多個人信息,如機主的姓名、地址、身份證號等。從一個人的通話記錄甚至可以判斷一個人的社會交往情況、生活習慣等,當事人對此顯然有著較高的隱私期待。盡管如此,通話記錄仍不屬于通信自由的保護范圍,對它的調取也不存在干涉通信自由的問題。這是因為,從技術層面上說,通話記錄是對通話行為有關信息的記錄,而不是對通話內容的記錄。雖然歸功于通信技術的發達,通話行為與通話記錄幾乎同步發生,但人們仍不妨設想在通話行為與通話記錄之間存在“邏輯上的一秒”:實際上,也只有在通話行為結束之后,方能產生一份完整的通話記錄。而在實踐中,對通話記錄的調取也都是在通話結束之后進行的,既然通話已經結束,則這種調取不致發生對通信自由的干涉。
不過,雖然調取通話記錄不構成對通信自由的限制,但它是否屬于對通信秘密的干預而有違反《憲法》第40條之虞呢?具體來說,通話記錄附著有當事人重要的個人信息,而調取通話記錄顯然意味著這些個人信息被他人所知曉,這是否有違《憲法》第40條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需要從傳統書信的特征說起。傳統書信,除了書信的內容外,也包括信封。顯而易見,信封上的信息,如收信地址、收信人姓名、發信人地址等雖然附屬于書信,但它并不屬于通信秘密的保護對象。這些信息是公開的,并無秘密可言——至少對郵政工作人員并無秘密可言,因為郵政工作人員只有憑借此類信息,才能將信件順利投遞。而且在很多地方和單位,普通書信都存放于固定的收發室,任人查找,此更彰顯了其非秘密的性質。質言之,此類信息盡管也屬于通信信息,〔24〕參見劉素華:《論通信自由的憲法保護》,《法學家》2005年第3期。但它不屬于通信秘密的保護對象。這也可以從刑法的有關法條設計中得到確證。刑法第253條規定了郵政工作人員私自開拆郵件罪的刑事責任。按照刑法的規定,只有“開拆”郵件方構成犯罪,而信封卻不存在“開拆”的問題。既然如此,信封上的信息也就不屬于刑法上的“郵件”,不屬于通信秘密的保護范圍。
通話記錄具有類似的性質。也就是說,通話記錄類似于傳統書信上的信封,它盡管透露了當事人的某些個人信息,但它依然不屬于通信秘密的保護對象。這是因為,雖然傳統信件與電話通信在形式、速度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它們都須通過必要的媒介才能完成。信件必須通過郵局的投遞,而通話則必須經由電信局的接轉。人們在通信時就已經知道郵局會知曉信封上的信息,人們在日常通話時也會預知自己的號碼等信息會留存在電信局的服務器上。在當代的信息化社會,這是一個無須太多電信知識,而憑借日常生活經驗就能作出的判斷和認知。信封上的信息對郵政工作人員而言不具有秘密性,則通話記錄對電信工作人員而言也同樣不具有秘密性。對照《刑法》第253條,如果說信封不屬于“郵件”的范圍,則通話記錄也不屬于“通話”的范圍,非屬通信秘密的保護對象。既然如此,則法院調取此類信息也就不存在侵犯其通信秘密的問題。
四、嚴格解釋《憲法》第40條保護范圍的必要性
如上所述,通話記錄不屬于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保護對象。這也說明,在日常生活看來屬于通信信息的事物,未必就屬于《憲法》第40條的保護對象。換言之,《憲法》第40條雖然使用的是人們所習見的日常用語,但實際上卻是一種技術語言,其含義卻未必等同于其日常意義。這種日常用語與技術語言之間的差異在法律上十分常見。〔25〕See Frederick Schauer, Speech and “Speech”-Obscenity and “Obscenity”: An Exercis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stitutional Language, 67 GEO.L.J.899 (1979).當然,將通話記錄排除于通信權保護范圍的理由并非僅限于此,它更涉及如何妥當界定通信權保護范圍的問題。本文認為,從《憲法》第40條的主旨看,基于下述理由,對其保護范圍的界定宜采取嚴格主義的做法。
(一)通信內容與外在信息的區分
從理論層面來說,一項基本權利的保護范圍大體上與其保護程度成反比的關系。〔26〕“基本權利的規范領域愈廣,則其保護程度愈低;規范領域愈窄,則其保護程度愈高。”參見杜強強:《基本權利的規范領域和保護程度》,《法學研究》2011年第1期。《憲法》第40條對公民通信權的保護程度甚高,因此不宜過分擴張其保護范圍。《憲法》第40條宣告:“除……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憲法在這里連續使用了兩個“任何”,其強化通信權保護的意旨溢于言表,其語氣之強烈在整個憲法中似再無出其右者,難怪在憲法修改過程中曾有人對此提出不解。〔27〕1982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討論憲法修改草案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馬識途對草案中的通信自由條款發表意見說:“這條寫得特別長,理由是什么,令人不解為什么有這樣詳細的注解。可改為‘非依法律不得妨害’。”參見許崇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11頁。如前所述,《憲法》第40條預設了通信檢查的具體理由和特定主體,屬于“加重法律保留”。因此,即便立法機關制定的限制性立法,也必須符合《憲法》第40條所預設的條件,而不能訴諸《憲法》第51條寬泛的公共利益原則,〔28〕參見張翔:《基本權利的體系思維》,《清華法學》2012年第4期。這已經大大壓縮了立法機關的形成空間。在這種情況下,設若還要對其保護范圍做寬泛的界定,則將使立法者的形成空間受到兩個方面的雙重擠壓,此恐不符合憲法的意旨。
有不少學者曾主張,諸如通信地址、郵政編碼、郵戳時間、電話號碼等都屬于通信權的保護范圍之內,〔29〕同前注〔24〕,劉素華文;周偉:《通信自由與通信秘密的保護問題》,《法學》2006年第6期;韓大元主編:《憲法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頁。此種觀點恐怕不符合事理,也有違于人們的日常經驗。例如就電話號碼而言,它的私密性也就是最近十幾年才逐漸發生的事情。實際上,即便在20世紀90年代,人們還能經常看到各地郵局編印的“黃頁”,里面就“公然”陳列著眾多個人的私人電話。但即便在那個時代,甚至在更早之前,電話竊聽就已經被認為是對公民通信自由和秘密的干涉了。〔30〕例如在1982年憲法修改過程中,在討論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條款時,憲法修改委員會中有的委員就明確提到了電話竊聽的問題。同前注〔12〕,蔡定劍書,第265頁。在當今信息化社會,雖然個人的電話號碼變得越來越具有私密性,但個人的電話號碼被泄露與個人在通話時遭到竊聽,這兩者之間仍然有著重大的區別,需要在立法政策上予以區別對待。〔31〕2017年重慶市江津區人民法院在發給中國移動通信集團重慶有限公司江津分公司的司法建議書中明確指出:電話號碼并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0條所規定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范疇。參見重慶市江津區人民法院津法建(2017)3號司法建議書。這個司法建議書的判斷甚為妥當。進一步說,設若不顧通信內容與外在信息之間的這種重要區別,而將電話號碼、通話記錄等外在信息一概納入《憲法》第40條的保護范圍,這與其說是提升了對外在信息的保護,還不如說是降低和稀釋了對通信內容的保護。因為設若承認法院可以調取通話記錄,也就不得不承認它也可以調取通信的內容。〔32〕例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歷來都將商業廣告作為“商業言論”來保護,有論者即指出將商業言論納入憲法保護會稀釋憲法對政治性言論的保護。See Frederick Schauer, Commercial Speech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First Amendment, 56 U.Cin.L.Rev.1181,1194(1988).例如,周偉教授既主張將諸多外在信息納入《憲法》第40條的保護范圍,他也就不得不認為法院與公安、檢察機關一樣可以檢查公民的通信了。〔33〕同前注〔29〕,周偉文。此誠非對《憲法》第40條的妥當解釋。
(二)立法者的判斷
從立法層面看,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在有關立法中對通話記錄的性質問題作出了判斷。2004年修改后的《證券法》第180條明確授權證券監管機關有權查閱、復制與被調查事件有關的通訊記錄等資料,2012年修改后的《證券投資基金法》第113條也有類似規定。這里的“通訊記錄”,即等同于“通話記錄”。從立法審議的情況看,在《證券法》(修訂草案)對此做了規定后,有關地方和單位即提出了不同意見。這個意見指出,“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屬于事業單位,法律賦予其……查閱、復制有關的通訊記錄等權力是否合適,建議再作研究。”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認為,法律有必要賦予中國證監會相應的權力以提高監管效能,〔34〕王以銘:《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修訂草案)〉修改情況的匯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2005年第7期。修改后的法律即延續了草案的規定。可以看出,立法者在這里的討論并沒有提到《憲法》第40條。不過,與其說這是立法者在審議時忽略了《憲法》第40條,還不如說是立法者認為這個問題與《憲法》第40條無關,因此無須對其另做專門闡述。這可以從《證券法》修改后,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直接參加《證券法》起草、修改的人員編寫的釋義書中看出來。按照其解釋,由于《憲法》第40條已有明文規定,因此《證券法》第180條上規定的“通訊記錄”,是指“通話時間、通話對象等資料,而不包括有關的通訊內容”。〔35〕《證券法釋義》編寫組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釋義》,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頁。
從某種程度上,可以將立法者的這個判斷當作立法者對《憲法》第40條保護范圍的解釋。它的要義,在于區分通信內容和通訊記錄,也即只有通信內容才屬于憲法保護的對象,而通訊記錄則被排除于《憲法》第40條的保護之外。反過來說,若將“通訊記錄”解釋為受《憲法》第40條的保護,則在加重法律保留的前提下很難對《證券法》等法律做合憲化的處理。〔36〕有學者曾對此提出合憲性的疑問,參見邢斌文:《論法律草案審議過程中的合憲性控制》,《清華法學》2017年第1期。換言之,這種寬泛解釋將導致《證券法》第180條的無效,這恐怕是此種解釋所不能承受之重。因為違憲宣告影響到一國的憲法體制,而不像宣告一件民事合同無效或者撤銷一個行政行為那樣簡單。〔37〕參見翁岳生:《法治國家之行政法與司法》,月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60頁。當然,不能因為后果嚴重就諱言違憲,但既然通信內容與通訊記錄在私密程度上本來就有重大不同,則立法者將通訊記錄排除在外的這個判斷并非不合理。在這種情況下,尤其是在立法者接連通過法律授權行政機構檢查通訊記錄的情形下,妥當的做法是尊重立法者的判斷,而不是將其宣告違憲。所謂尊重立法者的判斷,具體而言就是在對《憲法》第40條的保護范圍存在不同解釋,其中一種解釋將導致立法違憲,而另一種解釋能促成立法合憲的情形下,應當優先選擇那種能促成法律合憲的解釋。〔38〕這種解釋方法被稱作“合法憲法解釋”,參見蘇永欽:《合憲性控制的理論與實際》,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93頁。
五、作為個人隱私的通話記錄
(一)通話記錄與個人隱私
當然,將通話記錄排除于《憲法》第40條的保護范圍,并不意味著此類信息就不受憲法的保護;因為即便通話記錄不能落入通信權的保護范圍,但這也并不妨礙它可以成為其他基本權利的保護對象。本文先前曾將通話記錄和信封信息類比,并論證其均非屬于通信權的保護范圍,但切不可因此認為本文會忽略通話記錄和信封信息之間的重要差異。通話記錄雖然和信封信息一樣都不具有通信秘密的性質,但它們兩者在私密性上還是有很多差別。何以言之?信封信息具有很高程度的公開性,它就像內容公開的明信片一樣,很難說人們對它有什么隱私期待。而通話記錄則不同,通話記錄只保留在電信企業的服務器上,第三人無法隨意獲得,具有較強的排他性。更重要的是,隨著通信技術的發展,電話號碼(尤其是手機號碼)附著了公民幾乎所有重要的個人信息,如身份證號碼、銀行賬號、電子支付手段等,因此人們對它的隱私期待相當高。從規范層面看,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即將“通信通訊聯系方式”作為刑法第253條之一規定的“公民個人信息”。我國司法實踐也是對此類信息提供民法保護的,認為通信企業對此類信息負有保密的義務。例如,在2013年南京市棲霞區法院審理的一個案件中,當事人的通話記錄被用人單位調取,當事人向法院起訴后,法院裁判認為,用人單位獲取并披露原告通話記錄的行為不具有合法性,已構成侵權,應承擔相應民事責任;南京移動對用戶的通話記錄信息負有安全保密的義務,其未能舉證證明對原告的通話記錄被用人單位獲取沒有過錯,故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39〕參見孟亞生:《員工通話記錄,單位有權查詢嗎?》《檢察日報》2014年9月3日第05版。
從這個意義上說,通話記錄雖不屬于《憲法》第40條的保護對象,但因為人們對它的隱私期待較高,屬于憲法隱私權的保護對象。從理論上說,隱私權雖屬基本權利,但它和《憲法》第40條上的通信權有所不同:通信權屬于憲法明文列舉的權利,而隱私權屬于憲法未列舉的權利。由于隱私權屬于未列舉的基本權利,從理論上看,公權力措施對它的限制只要符合單純法律保留的要求即可。單純法律保留是法律保留的另外一種類型,它是指國家只需制定法律(也即形式法律)就可限制基本權利,且憲法對限制性法律的內容沒有額外的要求。〔40〕同前注〔9〕,陳新民書,第351頁。也譯作“簡單法律保留”,參見[德]康拉德·黑塞:《聯邦德國憲法綱要》,李輝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254頁。這是它不同于加重法律保留的地方。就此而言,法院調取通話記錄雖然構成對隱私權的干涉,但它完全合乎單純法律保留的要求。《民事訴訟法》第67條規定:人民法院有權向有關單位和個人調查取證,有關單位和個人不得拒絕。《行政訴訟法》第40條規定:人民法院有權向有關行政機關以及其他組織、公民調取證據。第41條還規定:與本案有關的下列證據,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的,可以申請人民法院調取:(二)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的證據……這兩部法律均授權法院可以調取涉及個人隱私的證據,符合單純法律保留的要求,因此不存在所謂民事訴訟法違憲或者“適用違憲”的問題。總之,法院在民事、行政審判過程中調取當事人的通話記錄,沒有憲法和法律上的任何障礙。
(二)隱私權的保護程度
還需要指出的是,將通訊記錄排除于《憲法》第40條而將其歸入隱私權的保護范圍,雖然降低了保護程度,但并非不能達到對此類信息的有效保護——憲法對隱私權的保護程度雖不及對通信權的保護,但依然有著“門檻”,并非能隨意跨過。例如在201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在一項“專項審查”中,發現甘肅省人大常委會2011年通過的《甘肅省道路交通安全條例》存在違法嫌疑。該《條例》第76條規定:“因調查交通事故案件需要,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可以查閱或者復制……交通事故當事人的通訊記錄,必要時可以依法提取和封存相關信息、資料,有關單位應當及時、如實、無償提供,不得偽造、隱匿、轉移、銷毀。”2013年《內蒙古自治區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辦法》第50條也有類似規定。從其規定看,這兩部地方性法規只是授權交通管理部門到“有關單位”調取通訊記錄,而非直接檢查當事人的手機,因此與法院到通信企業調取通話記錄并無兩樣。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審查認為,“上述規定涉及公民通信自由及通信秘密,缺乏法律依據”,法工委“已向兩地人大常委會發出審查意見督促糾正”。〔41〕參見劉嫚:《交警可查通話記錄?糾正!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備案審查室研究認定“缺乏法律依據”》,《南方都市報》2019年3月2日A04版。亦參見朱寧寧:《備案審查劍指道交管理法規規章》,《法制日報》2019年1月29日,第5版。可以看出,法工委依然秉持其2004年“答復”中的觀點,認為通訊記錄屬于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范疇。實際上,正如本文所論證的那樣,通訊記錄只是隱私權的保護對象,與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無關,但即便對隱私權的限制仍須符合單純法律保留的要求。甘肅、內蒙古兩地的人大常委會在沒有法律明確授權的情況下,以地方性法規的方式限制當事人的隱私權,應屬不當。
由此也可以看出,通信權與隱私權有所不同。我國憲法學界一直有種觀點認為,隱私權雖非憲法所明文規定,但它卻暗含于我國憲法當中,如憲法對通信秘密的規定就隱含了隱私權。〔42〕參見李步云主編:《憲法比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87頁;參見張千帆:《憲法學講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74頁;屠振宇:《“群租”整治令與憲法隱私權》,《山東社會科學》2008年第4期;參見范進學:《我國隱私權的立法審視與完善》,《法學雜志》2017年第5期;參見柳建龍:《論基本權利競合》,《法學家》2018年第1期。這種主張容易使人誤認為通信秘密與隱私權有著共同的規范基礎,甚至認為兩者是一回事,其實這是值得商榷的。當然,從私法的角度看,將通信秘密視作隱私權來保護并沒有問題,因為《侵權責任法》第2條所規定的保護對象只有隱私權,而沒有提到通信秘密。因此,如果當事人的通信秘密受到他人的侵害,其當然可以主張隱私權受到侵害而提出損害賠償,〔43〕參見王利明主編:《民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731頁。實務中也是這么操作的。〔44〕參見“孔紅蘭與奧克坦姆系統科技蘇州有限公司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糾紛案”,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蘇中民終字第02259號民事判決書。法院判決認為,“奧克坦姆公司新任總經理……要求與會員工展示其手機通訊記錄內容供其查看的行為,是……侵犯員工個人隱私的行為”。不過從憲法的角度看,必須嚴守通信秘密與隱私權之間的界限。《憲法》第40條的保護對象只是通信權,不是隱私權。〔45〕1982年憲法的一個正式的英譯本將《憲法》第40條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譯為“the freedom and privacy of correspondence”,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外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頁。道理很簡單,因為基本權利所拘束的對象是國家公權力,由于各個基本權利的保護范圍和程度都有不同,因此對國家公權力的拘束程度亦有不同。由于《憲法》第40條屬于“加重法律保留”條款,對國家公權力的拘束程度甚高,因此只應適用于憲法有明文列舉的權利;而隱私權屬于憲法未列舉的權利,所以只有單純法律保留原則的適用。
六、結論
綜上所述,通話記錄雖然也是通信信息的一種,但并非屬于《憲法》第40條的保護范圍,而只是隱私權的保護對象。《憲法》第40條屬于加重法律保留條款,憲法預定了通信檢查的具體條件;而隱私權屬于憲法未列舉的權利,公權力對它的限制只需要符合單純法律保留的要求即可。法院在民事、行政訴訟中依據訴訟法的規定調取通話記錄,與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無涉,符合單純法律保留的基本要求,不存在違反憲法的疑慮。這是本文的基本結論。
將通話記錄從《憲法》第40條的保護范圍中排除,實際上是對通信權在外圍上的一種類型化處理,從而使得通信權的保護范圍有所明晰。由于信息化時代的通信類型繁多,與當事人個人生活的關聯亦有緊疏之別,因此似有必要對通信權做進一步的類型化,將非屬于通信權保護范圍的其他信息排除。例如就《證券法》上規定的類似調查而言,在很多時候僅僅調取通話記錄似仍于事無補,而需要調取通訊的內容(如電子郵件、短信信息等)。就事實而言,此類信息雖然均由個人發出,但它卻與個人的私人生活無關,而屬于商業通信,對此類商業通信似無必要給予《憲法》第40條的高度保護。〔46〕例如日本《破產法》即規定破產財產托管人可以開拆和批閱破產人的郵件和電報,參見林來梵:《從憲法規范到規范憲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頁。《憲法》第40條保護的是“公民的通信”,企業的信件即便經由公民之手收發,也不能使其轉變為公民個人的通信。憲法學說曾將言論區分為政治性言論與商業言論,而主張對商業言論提供較低程度的保護。〔47〕參見趙娟:《商業言論自由的憲法學思考》,《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因此也有必要將通信區分為個人通信與商業通信,《憲法》第40條的高度保護只適用于個人通信,而對商業通信只提供較低程度的保障。〔48〕周偉教授也主張職務通信不受《憲法》第40條的保障。同前注〔29〕,周偉文。當然,如何區分個人通信和商業通信仍屬不易,正如政治性言論與商業言論亦難區分一樣,對此還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