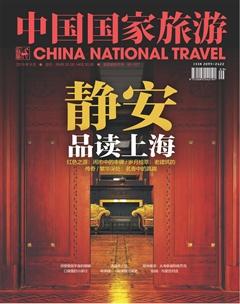迷航的飛行員
安托萬·德·圣-埃克絮佩里
我忘不了一次夜航遇險的經歷。
整個夜里,從撒哈拉中途站發來的無線電定向數據都是不準確的,使報務員和我受害不淺。當我看到海水在濃霧的縫隙下閃閃發亮,馬上掉轉機頭往海岸方向飛去;也不知道朝著外海方向扎進去已有多長時間了。
我們也沒有飛抵海岸的把握,因為汽油可能不夠。而且,即使到了海岸,我們也還要搜尋中途站。這時已是月落時刻。再不掌握角度數據,我們這些已經聾了的人,又會慢慢變成瞎子。在雪原似的一長溜濃霧中,月亮終于隱熄了,像一塊蒼白的炭結。我們頭頂上的天空烏云密布。從那以后,我們夾在這堆烏云與這團濃霧之間,在這個漆黑一團、空無一物的世界上飛翔。
原來向我們拍發信號的中途站,已放棄向我們提供情況:“方位不明……方位不明……”因為我們的聲音從四面八方傳到他們那里,反而哪兒都不是。
我們已經灰心喪氣的時候,突然在左前方的地平線上,冒出一點亮光。我內心又感到一陣騷亂的喜悅,報務員也向我俯身過來,我還聽到他在哼歌呢!這只能是中途站,這只能是中途站的導航燈,因為撒哈拉到了夜晚,漆黑無光,成為一片死亡的土地。亮光還閃耀了一下,然后又熄滅了。我們已經轉身朝著一顆星飛去,這顆星消失在地平線前是可以看到的,但是也僅僅幾分鐘,當它夾在濃霧和烏云之間的時候。
可是,我們又看到其他亮光也閃耀起來。我們暗中抱著希望,輪流朝著每一顆星光飛去。當星光歷久不衰時,我們冀求著生的機會。報務員向錫茲內羅斯中途站發出命令:“前面的火光,熄滅你的導航燈,然后再亮三下。”錫茲內羅斯把導航燈熄滅了,又亮了起來,我們目不轉睛地盯著,但是這顆狠心的火光沒有再眨一下——公正不阿的星星呵!

盡管汽油逐漸耗盡,我們還是每次要去咬那只金色釣餌。每次它都是導航塔的真正信號,每次它都是中途站和絕處逢生,然而每次,我們不得不轉向另一顆星光。
從那時開始,我們感到自己迷失在太空中,在成百顆遠不可及的星球中間,搜尋著那顆真正的星球,我們的那一顆,唯有這一顆星上有我們熟悉的田野,我們親切的房舍,我們的溫情。
我將向你們敘述那時出現在我眼前、可能在你看來是幼稚可笑的景象。但是身處險境時,人還是有人的煩惱,我感到口渴,我感到饑餓。
如果我們找到了錫茲內羅斯,加油以后,立即可以繼續我們的航程,在清晨涼爽的空氣中降落在卡薩布蘭卡。工作完啦!報務員和我可以走到城里,在黎明時,找一家已經開門營業的小飯店……報務員和我將坐在餐桌旁,前面擺著熱的羊角面包和牛奶咖啡,萬無一失,笑談前一夜的經歷。報務員和我將接受生命賜予的清晨禮物。年老的農婦也是通過一幅圖像,一枚樸實的圣章,一串念珠才接觸到她的上帝。要我們了解,也應該講一種簡單的語言。因而,生的喜悅對我來說,就集中在這一口芬芳、熱氣騰騰的牛奶、咖啡和小麥的混合物里,從而接觸到寧靜的牧場、異國植物和莊稼,從而接觸到整個大地。在這些紛紜眾多的星球中,唯有一顆能在黎明時,做成一碗香噴噴的早點,獻到我們面前。
但是在我們的航機和這個有生命的地球之間,橫亙著不可逾越的距離。世界上所有的寶藏都積聚在迷失于群星之間的這一粒灰塵中。報務員相信星相,為了辨認出這粒灰塵,總是不停地在祈求星星。
突然,他一拳打得我肩膀一晃。順手遞給我一張紙,上面寫著:“一切平安。我收到了一條了不起的電訊……”我等待著,心怦怦地在跳,他終于給我帶來了可把我們救出險地的五六個字。終于,我收到了這份天賜的禮物。
這份電報是在前天傍晚,從我們離開的卡薩布蘭卡發出的。轉發時耽誤了,突然當我們飛出兩千公里以外,夾在烏云與濃霧之間,迷失在海洋上空的時候,這份電報找上了我們。這份電報是國家代表在卡薩布蘭卡機場拍來的。我看到:“圣-埃克絮佩里先生,我有責任向巴黎提出給你處分,從卡薩布蘭卡起飛,你盤旋轉彎時離機庫太近。”我盤旋轉彎時離機庫太近,這是事實。這個人生氣完全出于恪盡職守,這也是事實。如果在機場辦公室內,我挨這頓訓斥一定會負疚抱慚。但是,如今它在不該找到我們的地方找到了我們。在這幾顆稀落的星星,這一片濃霧,這兇險逼人的大海之間迸了出來。我們肩負著自己的命運,郵件的命運,我們航機的命運。

我們費盡心力進行操縱才活了下來,這個人卻對著我們發泄他那小小的怨氣。但是報務員和我,不但沒有惱怒,反而感到極大的歡悅。在這里我們才是主人,還是虧了他的提醒我們才發現這一點。這個二等兵難道沒有朝我們的袖章看一眼,我們已經是上尉啦!我們從大熊座莊重地踱步走向人馬座時,唯一值得我們操心的是月亮的變幻無常,這時他居然來打斷我們的沉思……在出現這個人的地球上,唯一刻不容緩的義務是向我們提供確切的數據,好讓我們在星辰之間計算位置。現在數據都是錯的。至于其他一切,目前來說,這個星球還是免開尊口。報務員給我寫道:“他們不把我們領到一個地方,卻在這些蠢事上鬧……”對他來說,“他們”是指地球上所有的人類,以及他們的議會,他們的參議院,他們的海軍,他們的軍隊和他們的皇帝。這個不明事理的人還要跟我們糾纏不清;我們一邊讀著他的電報,一邊朝著水星側飛而去。
是一件離奇不過的巧事救了我們。終于到了這么一個時刻,我們已經放棄一切抵達錫茲內羅斯的希望,朝著海岸方向斜插過去,決定保持這個方向不變,直到汽油耗盡為止。這樣我還可能碰上運氣,不至于沉落在海里。不幸的是,我的那些撲朔迷離的導航燈,早把我們引導到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地方;還有不幸的是,茫茫黑夜迫使我們闖入了彌天大霧,要想著陸而不機毀身亡,這樣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但是,我們已經沒有選擇的余地。
當時的情境十分明顯,所以當報務員塞給我一條早到一小時或許可救我們出險的信息,我只是凄然地聳聳肩膀,信息說:“錫茲內羅斯決定向我們提供方位。錫茲內羅斯指出:疑為二百一十六度……”錫茲內羅斯不再埋在云霧中,錫茲內羅斯在那里,在我們的左方,不是虛無縹緲的。不錯,但是多少距離呢?報務員和我簡略地交換了幾句。太晚了。我們兩人意見一致。若往錫茲內羅斯飛去,更增加我們失去海岸的危險。報務員的回答是:“油只夠用一小時,繼續九十三度航向。”
然而,中途站一個接著一個蘇醒了。我們的對話中也夾雜了從阿加迪爾、卡薩布蘭卡、達喀爾傳來的聲音。每個城市的無線電站向各個機場告警,機場場長又向各個飛行員告警。慢慢地他們聚集在我們周圍,像聚集在病人的床邊。這份熱情無濟于事,但終是一份熱情。毫無作用的指點,但是那么親切!霎時間,圖盧茲出現了,圖盧茲這個遠在四千公里外的起飛站。圖盧茲一下子闖入我們中間,開門見山地說:“你駕駛的飛機不就是F……”(我已經忘了編號。)
“是的。”
“那你們還有兩小時的油量。這架飛機的油箱不是標準油箱。往錫茲內羅斯飛。”
就是這樣,隨著一個職業而來的種種需要,可以改變世界的面貌,豐富世界的內容。并不一定總要有這么一個夜晚,才使航班飛行員發現這些司空見慣的景象還有一層新的含義。單調的田野令旅客生厭,但在飛行員眼中卻不一樣。這片浮云擋住了視線,對他來說,絕不是一種景致而已,它牽動他的肌肉,向他擺出問題。他已經在思索對策,周密審度,一種真正的語言把他倆聯結在一起。這里一座山峰,還在遠處,然而會露出什么樣的面目?逢上月明之夜,這是一個容易辨認的標志。但是飛行員盲目駕駛,抑不住飛機的漂移,又懷疑山峰的位置,山峰頓時會變成一堆炸藥,整個夜空充滿了殺機,猶如在水面下的一顆炸彈,隨波逐流,使整個海洋令人望而生畏。
大海也是這樣變幻莫測。對于普通旅客,風浪是看不見的。從這樣的高處俯視,波濤顯不出起伏,一簇簇浪花也似乎凝聚不動,唯有巨大的白色海濤向前展伸,浪沫水紋也像封在冰層之中。但是根據機組人員的判斷,這個海面無論如何是不能降落的。這些波濤對他們來說,好比巨大的毒花。
即使這次航行是一次幸運的航行,飛行員在他的某一段航程上駕駛,閱歷到的也不是一種單純的景色。絢麗多彩的土地和天空,風吹粼粼的海面,金黃色的晚霞晨曦,他們一點也欣賞不到,而只會引起他們的深思。就像農民到田頭巡視,從蛛絲馬跡預見到春光的流轉,霜凍的威脅,雨水的來臨。職業飛行員也是這樣,要辨認雪的跡象,霧的跡象,幸福之夜的跡象。這架飛機初看似乎是把他們拉開,實際是更為嚴格地要他們順從這些重大的自然現象。滿天亂云猶如一座廣大無垠的法庭,這位飛行員孤懸在中央,為了維護他的飛機,要與三個原始神道進行角逐,那是高山、海洋和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