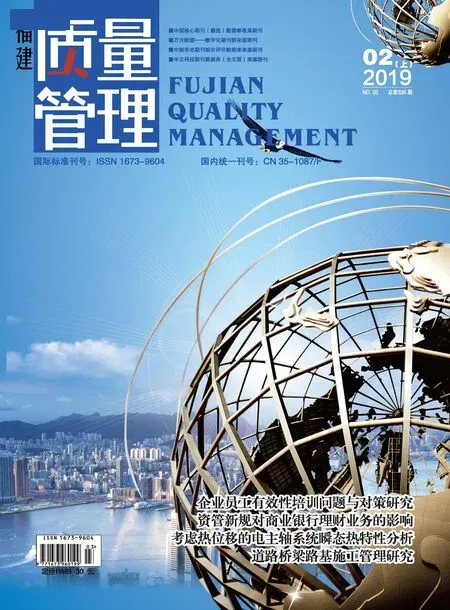淺談建筑內噪聲對人體影響研究的現狀
(青島理工大學環境與市政工程學院 山東 青島 266033)
一、噪聲對人體主觀及客觀的影響
(一)噪聲嚴重影響建筑室內環境和人體舒適度,針對噪聲的研究,國內外許多研究人員從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進行大量實驗探究。國外研究人員Miller采用不同頻率的噪聲對實驗室內的受試人員進行煩躁度評價研究,發現人員在低頻噪聲下的煩躁感要高于10000Hz純音,當噪聲的聲強級加大,人員的煩躁感增速也隨之加快[1]。Clausen、Carrick和Fanger在不舒適的室內環境中,研究了噪聲、溫度和空氣質量在影響方面所占的相對比重,發現每改善3.9dB的噪聲水平,就相當于提升1℃的空氣質量。Witterseh、Wyon和Clausen針對開放式的辦公環境做了溫度與噪聲的多因素研究,得到結果顯示高聲強級的噪聲環境會使人體疲勞感顯著增加。Subedi利用低頻噪聲進行人體煩躁度實驗,將低頻噪聲分離成復音和低頻的純音,發現純音下人員的煩躁度受噪聲中的不同成分影響,而復音條件下的煩躁程度與每個成分的頻率和水平有重要關系[2]。Pellerin和Candas將相同著裝的受試人員設放在不同的環境,對環境變量進行單獨的控制,研究人員噪聲對人員舒適度的影響,發現男性相對于女性來說更加傾向于低噪聲環境。
(二)國內研究者對噪聲的研究也十分關注。重慶大學的王嬌琳對不同的噪聲進行了采集,作為刺激源對人員進行實驗,檢測受試人員的生理參數,發現交通和生活噪聲的成分主要以低頻為主,并且同一實驗工況下,男性人員相對于女性人員對噪聲更加敏感,煩躁度更大[3]。浙江大學的施麗莉對人體主觀舒適度進行研究,通過低頻噪聲的刺激,得出結論:人體主觀煩躁度與噪聲聲強級有密切關系,噪聲聲強級越大,人員煩躁感評分越高(評分越大越不利),環境滿意度評分越低(評分越低越不利)[4]。廣州職業病防治院的張維森對長期處于噪聲作業下的工人進行醫學檢測,發現工人心率異常改變率較高,男性感音性耳聾和竇性心動過速者患高血壓的風險顯著增加[5]。首都師范大學的王立雪對不同類型的噪聲進行現場檢測,通過計算和人體測試,發現噪聲能量大都集中在人類聽覺的靈敏頻帶,會使人的聽閾發生暫時性上移,聽力變遲鈍,引發聽覺疲勞[6]。
二、噪聲對人員工作效率的影響
身處噪聲環境中的人員由于心理和生理上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危害,隨之而來的就是工作效率受到影響。從上個世紀開始,研究人員就已經開展了對噪聲下人員認知水平和心理變化的探究[7]。Jones和Broadbent通過研究低水平噪聲(55dB)和高水平噪聲(80dB)下的校正任務績效,發現人員在高水平噪聲下,人員文字閱讀能力明顯下降,對錯誤的辨別能力減弱,同時辨別錯誤的概率增大[8]。Jones的實驗結果表明,強度為50-70dB的噪聲下,校正任務績效與聲強級無關,而是與背景聲音所包含的意義有關。辨別拼寫錯誤的能力在有意義的背景聲音下會降低,但這種聲音不會對閱讀速度有影響。Boyce對200名室內辦公人員進行調研,發現電話鈴聲對他們的工作會產生很大干擾,Banbury的研究同樣證實了無人接聽的電話鈴聲比話語聲等其他噪音更具干擾[9]。Smith研究了噪聲與任務績效的關系,認為不能確定兩者之間存在直接關聯,指出研究人員需要確定噪聲的類型,噪聲的強度以及所選任務的類型,具有針對性的分析噪聲影響[10]。室內辦公環境的噪聲一般為50-75dB,大多數研究的樣本都是高水平噪聲,對于辦公環境的噪聲,國外研究相對較少,Witterseh、Wyon和Clausen的研究結果顯示人員加法計算任務的速率在低聲強級噪聲下會降低3%。Delay和Mathey將噪音從50dB逐漸升高到80dB,發現人員時間估算任務的績效隨之上升。Evanes與Johnson利用打字任務探究低聲強級噪聲帶來的影響,沒有發現兩者之間存在關聯[11]。張樂通過數字短時記憶研究,發現交通和生活噪聲以及三種聲音強度(40.7dB、56dB和73.3dB)對測試沒有影響[12]。
三、結論
綜合來看,噪聲對人影響的研究開始較早,范圍較廣,但相對于國外研究來說,國內研究范圍較窄。同時,國內與國外的社會人口情況差別較大,尤其是噪聲對建筑室內辦公人員工作效率的影響,并沒有太多的資料文獻可循,因此需要進一步加強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