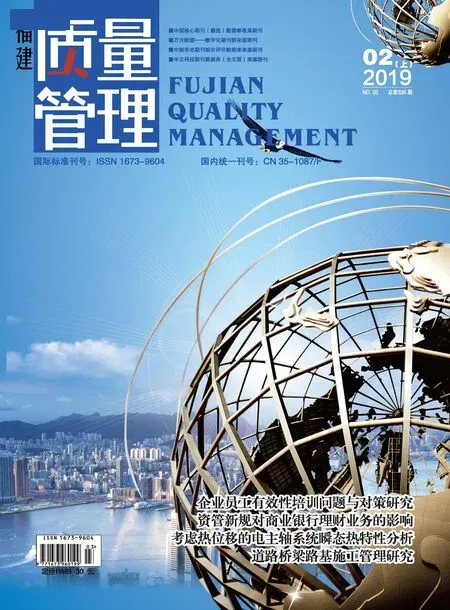強制壟斷下經營者法律責任研究
——基于《反壟斷法》第36條的規范分析
(華東政法大學 上海 200063)
圍繞第36條,筆者將主要分析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該條的體系定位。主要是關于第36條與第32條到第35條的關系,第36條與第37條的關系,第36條與第2章、第3章、第4章的關系。第二,關于強制的認定。“強制”是第36條最為核心的一個詞匯,能否準確界定“強制”的含義是正確理解與適用第36條的關鍵。第三,經營者法律責任的認定。主要是關于經營者被強制從事壟斷行為,應否承擔責任,以及承擔何種責任。而第二個與第三個問題又是緊密相關,“強制”的準確界定就是為確定經營者法律責任而服務的,在筆者看來,經營者有無“受到強制”是其承擔責任的分水嶺,所以強制的準確界定至關重要。
一、第36條的體系定位
1、第36條與第32條到第35條的關系。第36條規定的是行政機關強制經營者從事壟斷行為,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并非由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權力所直接達成,而是以經營者作為中介間接造成的。第32條到第35條,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則是由行政機關直接造成。所以說,第36條規定的是間接行政性壟斷,第32條到底35條規定的是直接行政性壟斷。
2、第36條與第37條之間的關系。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既有抽象行政行為又有具體行政行為,那么經營者受到來自行政機關的強制,是基于具體行政行為還是抽象行政行為,亦或是兩者皆有之?第37條規定了抽象行政性壟斷,因為第37條與第32條到第36條并列規定,所以解釋上應認為,當行政機關實施抽象行政行為,行政機關受第37條規制而反壟斷法承擔責任;當行政機關實施具體行政行為時,行政機關受第36條的規制而承擔責任。而就經營者責任承擔層面,因第37條僅規制行政機關,無法實現第36條于第37條對經營者的并列規定,所以解釋上應當認為經營者受到來自行政機關無論是具體行政行為還是抽象行政行為,均應受到第36條第規制。問題是抽象行政行為能否達到強制的目的?此一問題,將在“強制”的具體界定上予以澄清解決。
3、第36條與第2章、第3章、第4章的關系。第36條規定強制經營者從事本法規定的壟斷行為,本法規定的壟斷行為主要就是第2章到第4章所規定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壟斷協議行為、經營者集中。所以,在認定是否符合第36條的構成要件時,必須審查經營者所為之行為是否符合第2章、第3章、第4章中的相關規定,若經營者的行為并未滿足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壟斷協議行為、經營者集中等壟斷行為的構成要件,即使受到行政機關的強制,也沒有適用第36條的余地。
但是有兩個規范性法律文件卻做了這樣的規定。一個是《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制止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規定》第3條,另一個是《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實施細則(暫行)》第17條。這兩份規范性法律文件窮盡列舉了行政機關強制經營者從事的壟斷行為,即壟斷協議行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而無經營者集中。似乎在此兩規范性文件制定者看來,行政機關似乎不能強制經營者從事經營者集中,事實并非如此。
2008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先后發布了數個規范性文件,旨在加快煤炭資源整合,啟動了中國規模最大的煤炭企業重組行動,涉及兩千余家的國有、民營、私人煤炭企業。在山西省此次對小煤礦的兼并重組中,經濟補償問題是資源整合中最關鍵的問題。根據2008年9月山西省國土資源廳《關于煤礦企業兼并重組所涉及資源權價處置辦法》的規定,被兼并重組的煤礦可按規定獲得經濟補償,也可按照資源資本化的方式,折價入股,作為其在新組建企業的股份。然而,經過調查后發現,當地政府在制定和實施資源整合方案中,不顧中小煤礦投資者的呼聲,強制小煤礦接受整合,甚至還使出了停產限產拖時間等手段。[1]
本案中,行政機關以限產、停產的手段,迫使經營者參與集中,嚴重違背了經營者的生產、經營自由。所以行政機關也可以強制經營者從事集中行為。但是在課堂展示,鐘老師點評說本案需要壟斷行為與產業政策之間的關系,能否認定本案屬于行政性壟斷還有值得商榷的空間,這確實是筆者一開始所忽略的內容。但由于本案涉及面廣,原始資料信息難以全面搜集,也并沒有經過反壟斷執法機構的調查,也沒有經過任何訴訟程序,所以現在已經難以判定本案是否超出產業政策范圍而進入到《反壟斷法》的規制領域。
二、強制的認定
行政機關的行為需要達到何種程度才能構成強制?強制的內涵是什么?被強制的經營者是否完全喪失營業自由?行政限定、行政授權是否屬于行政強制?行政機關通過制定、發布行政規定等抽象行政行為,能否達到強制的效果?這些問題的答案,需要通過案例的分析研究,才能得出契合實際的答案。
通過研究分析“上海市交通委強制黃浦江游覽行業游船企業達成并實施了固定或者變更服務價格協議案”與“北京市住建委強制企業統一執行質量控制價案”,我們總結出: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權力在客觀方面表現為,行政機關通過組織引導等方式授意經營者實施壟斷行為,繼而,行政機關通過各種具體行政行為保障壟斷行為的順利進行。
在“人民銀行合肥中心支行參與銀行業金融機構達成市場分配固定價格協議案”中,行政機關組織、引導了經營者達成壟斷協議,并下發通知確定市場分配方案、統一價格,但并未進一步采取措施保障該壟斷協議的履行。行政機關的行為并未達到“強制”程度,而經營者也有自由從事經營活動的空間。即使經營者拒絕實施該壟斷協議,也不會遭到現實的不利益。因此行政限定并未達到強制的程度,不屬于第36條的調整范圍。
對于行政授權而言,行政機關授權給經營者,使他享有從事壟斷行為的“權力”,這種情形下,經營者可以實施壟斷行為也可以不實施壟斷行為,享有充分的營業自由,并未被行政機關強制。在行政機關制定、發布行政規定,要求經營者從事壟斷行為,經營者面臨的不利益并不是即刻就到來的,他依然有行動的自由,只有行政機關依據行政規定,通過具體行政行為,才有可能構成強制。行政限定與制定、發布行政規定最主要的區別為一個是具體行政行為,一個是抽象行政行為,但都沒有使經營者完全喪失行動的自由,達到第36條所規定的“強制”的地步。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又可以得出,強制經營者從事壟斷性行為在主觀方面表現為:經營者從事壟斷行為必須是違背其自身意愿,被迫做出的。經營者如不實施壟斷行為,將會面臨現實的不利益。
綜上所述,第36條所言之“強制”,應當從兩個方面(即客觀方面與主觀方面)、兩個角度(即行政機關角度與經營者角度)予以觀察。在客觀方面,行政機關對經營者實施壟斷行為提出明確要求,并通過各種行政手段監督、保障壟斷行為的實施;在主觀方面,實施壟斷行為并非經營者出于自愿,而是被迫實施。而在認定方面,應從行政機關的客觀行為出發,在客觀方面滿足“行政機關對經營者實施壟斷行為提出明確要求,并通過各種行政手段監督、保障壟斷行為的實施”,即可推定構成“強制”。如有證據證明經營者也有實施壟斷行為的主觀意圖,可以推翻對“強制”的認定。
三、經營者法律責任的認定
《反壟斷法》第46、47、48、50條對經營者實施壟斷行為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進行了規定,包括停止違法行為、沒收違法所得、罰款等行政責任和損害賠償等民事責任。在經營者被強制實施壟斷行為時,其應否承擔法律責任以及承擔何種責任,將是本部分討論的重點。
在“云南省通信管理局牽頭組織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和中國鐵通四家的云南分公司達成壟斷協議案”中,經營者被強制實施壟斷行為,最后被處以巨額罰款,對此筆者有不同看法。行政機關通過行政命令等具體行政行為,使經營者違背自身意志實施壟斷行為。面對行政機關的強制,作為理性人的經營者別無他法,只有實施壟斷行為才是其所處困境的最優解。如果經營者拒絕從事壟斷行為,他將直接面臨來自行政機關的現實不利益。法律不能強人所難,在經營者喪失營業自由的情況下,不應當對其處以罰款,這與民法、刑法上的緊急避險制度非常類似。
從法律責任的功能出發,筆者將進一步對反壟斷法上的經營者責任與刑法、民法上的法律責任進行功能性比較。《反壟斷法》所規定的罰款與刑法上的刑罰所具有的功能都是懲罰行為人,罰款是較輕的懲罰,刑罰是較重的懲罰。《反壟斷法》上的損害賠償責任與民法上的損害賠償責任,都是為了填補受害人的損害。在《刑法》第21條規定緊急避險是行為人免于承擔刑罰責任的違法阻卻事由,在《民法總則》第182條與《侵權責任法》第31條規定了緊急避險可以使行為人免于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基于法律責任功能上的類似性,經營者被強制實施壟斷行為,也應當免于承擔罰款與損害賠償責任。
《反壟斷法》上的責令停止違法行為與民法上的停止侵害(《民法總則》第179條)都是要求停止正在進行的違法行為;《反壟斷法》上的沒收為違法所得與民法上的返還財產(《民法總則》第179條)都是要求行為人將本不屬于自己的財產交出來。停止侵害、返還財產又都是著眼于行為人的客觀行為,而不過問行為人主觀心理態度如何;換言之,只要行為人實施了某項違法行為,就可以要求他承擔停止侵害、返還財產。因此,基于功能上的相似性,只要經營者實施了壟斷行為,就可以責令他停止違法行為,沒收他的違法所得。因此,筆者認為,當經營者被強制實施壟斷行為時,其不應當承擔罰款、損害賠償這兩種法律責任,但應當承擔停止違法行為與沒收違法所得這兩種法律責任。
四、反壟斷執法建議
綜上所述,當經營者被強制實施壟斷行為時,其不應當承擔罰款、損害賠償這兩種法律責任,但應當承擔停止違法行為與沒收違法所得這兩種法律責任。具體到上面提到的云南省通信管理局強制壟斷案,不應對四個經營者處以罰款,而應當對其處以沒收違法所得。但是在反壟斷執法實踐中,沒收違法所得的比例非常低,根據《中國反壟斷行政執法大數據分析報告(2008—2015)》[2],在發改委處理的175個經營者實施壟斷行為的案件中,僅有8件沒收經營者的違法所得。究其原因,沒收違法所得,違法所得額的計算非常復雜。反壟斷執法機關如果要處以沒收違法所得,將會耗費大量的執法成本。相比較之下,罰款是一個簡單、高效、便捷的處理方法。但是執法機關的這種處理方法明顯缺乏合理性,也與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馳。
因此筆者建議,執法機關不能為了處理上的方便,而簡單地以罰款替代沒收違法所得。反壟斷執法機構應當提高自身執法水平,在執法過程中逐步發揮罰款、沒收違法所得等法律責任本身所具有的功能,而不能張冠李戴,通過罰款使主觀上無辜的經營者受到懲罰,而對其違法所得視而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