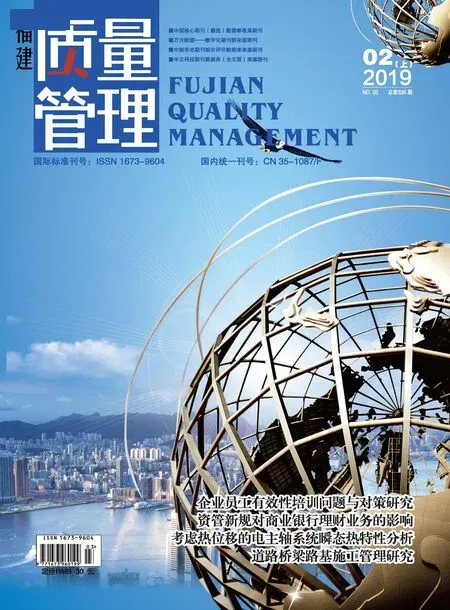論我國侵權責任法上之監護人責任
(華東政法大學 上海 200042)
一、問題的提出
我國自《民法通則》中明確規定監護人責任以來,學界對監護人責任的性質一直爭論不休,各種觀點甚至是尖銳對立的。司法實踐中,法院在適用《民法通則》第133條、《侵權責任法》第32條時也存在不一樣的理解。本文將簡要論述之。
二、學界爭議
(一)監護人責任的性質
學界對監護人責任性質主要形成了兩種觀點:自己責任說與替代責任說。
自己責任說認為監護人之所以“承擔”被監護人致害的賠償責任,其基礎在于監護人對被監護人存在監管義務。被監護人致使第三人受有損害結果的發生,監護人未盡到其監管義務、未能限制和教育被監護人的不法行為,故而本應屬于義務違反所生的自己責任,我國實務中眾多判決即證此觀點。[2]
替代責任說認為從對《侵權責任法》第32條第1款的文義解釋出發,實施加害行為的人是被監護人,承擔侵權責任的人是監護人,行為人與責任人發生了分離,屬于替代責任。[3]李永軍則更進一步地指出我國監護人責任是屬于廣義的替代責任,非嚴格意義上的替代責任。[4]
(二)侵權責任法第32條第1款與第2款的關系
學界主要有四種觀點:
1.平行關系說。該說認為當被監護人無個人財產時適用第1款之規定,有個人財產時適用第2款之規定,兩款規定系平行關系,相互獨立,互不影響。[5]
2.一般與例外關系說。該說認為第2款系針對第1款特殊的例外規定,被監護人致人損害時由監護人承擔賠償責任,只有在監護人自身的過錯顯著輕微,承擔責任對自己的生活將造成重大的不利,而且選擇從被監護人的責任財產中支付賠償費用對被監護人的生活和成長不會產生明顯不利的情況下,才能夠適用該款。責任承擔主體仍然是監護人。[6]
3.一般與補充關系說。該說認為第1款為監護人利益而特設的減輕責任規范,造成了被侵權人可能得不到完全賠償的救濟漏洞。故第2款基于衡平思想強加了一種公平責任。即如果因監護人獲得減輕責任的機會而得不到周全保護時,被侵權人可要求有責任財產的被監護人就監護人減輕的部分承擔獨立的責任,如果被監護人的財產仍不足以完全賠償受害人的損失,監護人需無條件地第二次承擔賠償責任。[7]
4.外部與內部關系說。該說認為第1款與第2款實際上分別規定監護人對受害人承擔責任的外部關系和監護人與由責任財產的被監護人之間就賠償費用如何分擔的內部關系。第1款后句屬于監護人賠償責任減輕規則,系屬于無過錯責任下的減責事由,在外部關系中若減責事由成就而使被侵權人受償不足,該受償不足部分應當由其自行承擔。
如果她孕前體重為50千克,BMI為18.4,建議孕期增重12.5~18千克。她可以用72-50=22(千克),即孕期增重22千克,但這是理論上的數值,基于不超過18千克的最高限,如果她年齡超過24歲的話建議孕期增重16千克,即66千克是她的分娩時的建議體重。
(三)我國侵權責任法監護人責任價值取向
可以看出,學者對監護人責任進行分析時體現了較強的價值傾向。侵權責任法本旨在權衡行動自由與權益保護兩項法價值[8],當兩項價值發生沖突之時,必須要做傾向性的選擇。具體到監護人責任,保護不具備責任能力的非完全行為能力人,即側重于行動自由;盡最大可能地填補被侵權人之損害即側重于權益保護。我國大部分學者受德國法影響,都主張應當保護未成年人的利益,同時以公平責任兼顧被侵權人利益;[9]部分學者受法國法影響,強調應更加注重保護被侵權人的利益,其中朱廣新的觀點具有代表意義,他認為《侵權責任法》第32條第1款不僅明顯忽視了對受害人權益的周全保護,而且過分容忍了事實上具有意思能力的被監護人的行為自由;同時相對于《民法通則》第133條第1款第2句,《侵權責任法》第32條第1款后句刪除了“可以適當減輕他的民事責任”中的“適當”,減輕了監護人的替代責任,增大了受害人的救濟漏洞。[10]
三、監護人責任的性質
在分析監護人性質之前應當首先明確監護人責任之基礎或者說監護人責任的制度功能。我國監護人責任中最重要的條文規范包括《侵權責任法》第32條及其沿用的《民法通則》第133條,除此之外尚包括《侵權責任法》第9條第2款以及《民通意見》第158至161條。從《侵權責任法》第32條的演變上來看,其承緒的《民法通則》第133條是為了與1957年《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29條和1980年《婚姻法》第17條銜接。前者并未存在“責任能力”之概念,無論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還是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抑或預見到自己的行為可能造成危險結果的非完全行為能力人及因意外致人受損的非完全行為能力人,均一體存在我國侵權責任法上之“過錯”,其監護人均需承擔侵權責任。我國侵權責任法在監護人責任上的責任分配難謂公平。
從特殊情況條文的內容上來看,《民通意見》第161條第1款明確以“責任財產”之有無來確定侵權責任承擔主體,可直見監護人責任中側重保護被侵權人利益的立法導向。在司法實踐中即有此種情況之案例,均由原監護人承擔侵權責任。
四、監護人的范圍
筆者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三十二條”及“監護人盡到監護責任”為檢索條件,檢索到了具有代表性的案例(2015遂中民終字第515號):A系B之生父,早年因A與B之生母離婚,B隨其生母居住。A患有精神分裂癥,A胞兄弟為其申請了五保待遇,但村委會未將A弟指定為監護人,平日A由A弟C照料。某日A產生幻覺將本案兩名被害人殺害。被害人家屬將A、B、C作為共同被告訴至法院,要求侵權損害賠償。一審判決B、C承擔侵權責任。B在上訴中主張自己從小未與A共同居住,不是A的監護人,A的實際監護人為C,應當由C承擔全部的監護人責任。
本文討論的是監護人責任,必須明確的是誰應當作為監護人承擔該項責任。《民通意見》第159條后段似乎是解決了此問題,“監護人不明確的,由順序在前的有監護能力的人承擔民事責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監護人人選的確認是以本人進入監護程序為前置條件的,也即如果成年人未進入監護程序即未有監護人。
在比較法上,成年人未經宣告不得作為被監護人,[11]我國法上雖然沒有監護宣告制度,但我國法定監護的監護人除了法院選任、村委會居委會指定外,還存在協議確定的方法以及國家擔任監護人的兜底方法。可以明確的是我國已有明確的監護人產生機制,未通過前述四種路徑產生監護人而直接將B、C作為監護人的做法存在兩個問題:第一,邏輯解釋上走不通,因為此刻A并未有監護人,也就無法由“監護人”承擔“監護人責任”;第二,要求未與A共同生活居住的B承擔此“監護人責任”,過分苛刻,是將監護人責任“保護權益”的價值取向發揮到了機制,而忽視了侵權責任法的預防與平衡價值。
即使在案件裁判時適用的《民通意見》第159條即使合理且合法,根據規范也應僅由第二順位的子女B承擔侵權責任,C是順序在后的。裁判仍要求第三順位的C承擔侵權責任的理由是因為C是A的日常生活照料人,有管束A之時間與空間可能性。該案法官既遵守了《民通意見》第159條的規定,又肯認了監護人責任基礎在于監護人對“被監護人”在日常中有教育和管理義務,因“被監護人”對第三人造成侵害,故而監護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帶有《民法通則》時代混亂的價值取向特點,在我國《民法總則》已經頒布實施的情況下,監護人責任認定應當首先確認是否存在監護,其次被告是否屬于監護人,以確保《民法總則》與《侵權責任法》之間體系的一貫。
五、監護人責任減輕規范
“監護人證明自己盡到監護職責的,可以減輕其侵權責任”是我國監護人責任中無過錯歸責原則里的減責規范。對于盡到監護職責的認定標準,有法官認為,“是否盡了監護責任,與監護人過去如何盡心盡力沒有關系,法律上只考慮在被監護人造成他人損害行為發生時監護人是否盡了監護義務”[12]然而從監護人責任的性質與司法實踐來看,監護人很難證明自己盡到了監護職責。
因為監護人責任屬于無過錯責任,被監護人一旦致他人受損即成立侵權行為,被監護人的過錯不予評價連帶地監護人的過錯也無需評價。其內在邏輯為如果監護人平時和行為發生時盡了良好的監管義務,那么侵權行為怎么可能發生。監護人證明自己盡到了監護責任是極其困難的。
臺灣判例上有兩則代表性判決:第一則周某雖為其子法定代理人,但分隔兩地,對外地之子縱加監督,亦仍不免發生損害;第二則蔡某A與他人在學校教室內游戲,致他人人身傷害,法院認為其法定代理人對于蔡某A之監督,亦無疏懈可言。此二則案例的共通之處在于致害行為發生時,監護人對被監護人并無監管之空間可能性。然而教育機構內發生的對第三人致害行為,監護人對行為發生的“當時當刻”不具備監管之空間可能性,仍然被法院判令承擔侵權責任。其根本原因在于現行監護人責任并非以保護非完全行為能力人的利益為主導,而是以周全填補被侵權人損失為主要價值導向的。
從這一點而言,我國《侵權責任法》第32條第1款后句實則已經淪為具文,不具有啟動適用之可能性,更加不會產生某些學者所言的未成年人及其監護人通過這一條款逃脫侵權責任,造成被侵權人權利無法周全救濟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