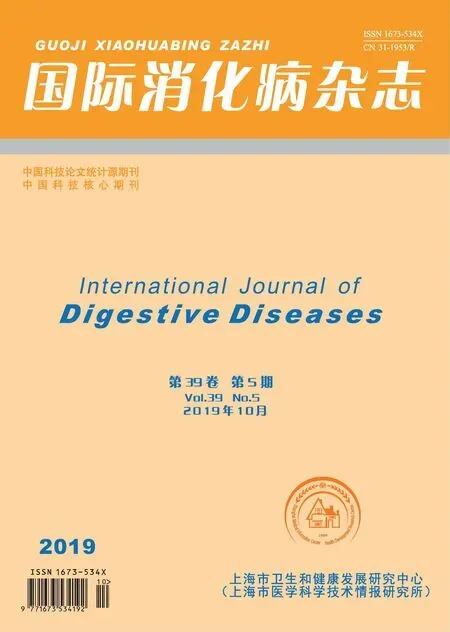藥物性肝損傷與非編碼RNA的研究進展
肝臟是藥物代謝的主要場所,大部分藥物在肝臟中代謝,最終轉化為無活性的代謝產物排出體外,部分藥物或其代謝產物具有肝臟毒性,可造成肝臟損傷,即藥物性肝損傷(DILI)。中國各地醫療水平發展不均,部分地區存在用藥不當的情況,DILI發病率呈現逐年升高的趨勢。DILI的發病機制尚不明確,如何對DILI進行早期診斷、有效控制病情進展、減少肝衰竭的發生以及優化病情監測成為了國內外研究者討論的熱點。非編碼RNA(ncRNA)參與基本的細胞生理過程,在DILI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本文就DILI與ncRNA的相關研究進展作一綜述。
1 DILI
有多種藥物可引起DILI,包括抗生素類藥物(抗結核病藥物、大環內酯類、四環素類、磺胺類、抗真菌類等)、非甾體抗炎藥、抗精神病藥、抗抑郁癥藥、鎮靜催眠藥、抗腫瘤藥、抗心律失常藥、降脂藥、部分口服降糖藥及中草藥等。超過1 000種藥物與肝損傷相關,有300余種已被證實與肝損傷明確相關[1]。其中,以抗生素類藥物引起的DILI較為常見,在西方國家青霉素類抗生素所致DILI較多見,亞洲則多因抗結核病藥物聯合用藥所致[2-3]。在印度,抗結核病藥物是DILI最常見的致病因素,在中國是第二常見的致病因素[4-5]。此外,在印度,由抗結核病藥物引起的DILI是急性肝衰竭(ALF)的主要原因。在中國、韓國、新加坡、日本等亞洲國家,因中草藥引起的DILI的發病率逐年升高[6]。中國的一項回顧性研究指出,中國大陸每100 000人中每年的DILI平均發病數為23.80例,遠高于西方國家[7]。近年來,非甾體抗炎藥對乙酰氨基酚(APAP)引起的DILI逐年增多,約占美國及部分歐洲國家ALF患者誘因的50%[8-9]。此外,目前APAP已廣泛應用于建立DILI動物模型,用以研究其發病機制、開發治療藥物等[10-12]。
DILI涉及環境與非環境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這些因素共同影響藥物及其代謝物的積累,并可導致藥物在肝臟中的應激促進作用[13],例如年齡[14-15]、性別[16]、妊娠狀態[17]、基礎疾病[18-19]、遺傳因素[20]、藥物因素[21]等。DILI的發病機制復雜,包括直接肝毒性和特異質肝毒性。藥物的直接肝毒性可引起內源性肝損傷,與藥物劑量直接相關。APAP攝入量若高于每日最高推薦量(4 g)即會引起DILI[22]。藥物的特異質肝毒性與肝細胞中線粒體受損、氧化應激等生物學過程相關,發病機制尚未明確。細胞色素P450(CYP450)主要參與肝臟藥物代謝的Ⅰ相反應,有研究發現,CYP1A1和CYP1B1啟動子CpG島甲基化,上調Toll-樣受體4(TLR4)和細胞外調節蛋白激酶(ERK)表達、下調過氧化物酶體增殖物激活受體-γ(PPAR-γ)表達,促進異煙肼誘導的氧化應激和炎性反應[23]。
臨床上,診斷DILI屬于排他性診斷。根據2015年修訂的《藥物性肝損傷診治指南》,在確認存在肝損傷的前提下除外其他肝臟疾病,結合患者藥物史,最終診斷為DILI。診斷標準:(1)用藥史;(2)病程與用藥時間的關系;(3)肝損傷的生物化學指標;(4)排除其他肝臟疾病;(5)RUCAM量表確定藥物與肝損傷之間的因果性和相關性[24-25]。
2 ncRNA
ncRNA是一類不編碼蛋白質的RNA,包括長度大于200 bp的長鏈ncRNA(lncRNA)及長度小于200 bp的小分子ncRNA(sncRNA),其中sncRNA包括微RNA(miRNA)、小干擾RNA(siRNA)及與PIWI蛋白相互作用的RNA(piRNA)等。
人類基因組數據顯示,約75%的基因轉錄為RNA,其中超過20 000個為蛋白質編碼基因,轉錄后翻譯成為蛋白質,但在總基因組序列中僅占2%,其余大多數被轉錄為ncRNA,不翻譯成蛋白質,在RNA水平作為基因調控因子直接發揮作用[26]。ncRNA參與多種生物學過程,其表達異常與多種疾病的發生密切相關[27-29]。因此,ncRNA成為了目前生物醫學領域的研究熱點之一,而在眾多ncRNA中,以miRNA和lncRNA較受國內外研究者的關注。
miRNA是一類長度約為22 bp的內源性單鏈短序列ncRNA,通過抑制部分信使RNA(mRNA)的形成發揮基因調節功能。1993年在秀麗隱桿線蟲體內發現第1個miRNA——lin-4,并證明miRNA通過堿基互補配對原則與其靶基因轉錄形成的mRNA的3′或5′非翻譯區(UTR)特異性結合,進而通過抑制翻譯及降低靶向轉錄物的穩定性在轉錄后調控靶基因表達[30-31]。大量研究表明,miRNA在多種器官、多種生物學過程中發揮重要的調控作用,如細胞生長發育、細胞增殖、細胞凋亡、細胞自噬等[32-34]。與其他內源性小RNA不同,miRNA來自具有獨特發夾結構的轉錄物,與mRNA配對,靶向抑制mRNA的翻譯過程,或通過mRNA的去腺苷酸化作用使其降解,以及靶mRNA的去穩定作用影響蛋白質表達[35-36]。
與miRNA相似,lncRNA同樣可以影響靶基因的表達。有研究表明,lncRNA能夠通過建立染色質結構域,直接募集組蛋白修飾酶至染色質[37]。此外,lncRNA還能影響組蛋白H3的結構,調節目的基因表達[38]。lncRNA與多種疾病的發生機制密切相關,有發展成為疾病生物標志物或藥物靶向分子的潛能[39]。然而,目前已明確報道的lncRNA的功能很少,大部分功能仍不明確[40]。
3 DILI與ncRNA的相關性研究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關注ncRNA在DILI的發病機制中所發揮的作用,其中涉及ncRNA的種類越來越多,不同ncRNA的作用也不盡相同。
3.1 miR-122
miR-122是一種在肝臟中大量特異性表達的miRNA,來自肝臟單核細胞及庫普弗細胞,約占肝臟總miRNA的70%,是在有關肝臟疾病與ncRNA之間聯系的研究中涉及較多的miRNA之一[41]。miR-122與脂肪性肝病、肝細胞癌及病毒性肝炎等肝臟疾病密切相關。miR-122在肝細胞中大量表達而在其他細胞中表達很低甚至不表達,因此備受國內外研究者的關注[42-45]。有研究者對DILI患者肝臟及血清中的miR-122和miR-192水平進行了檢測,結果顯示在經APAP處理后,它們的表達水平在血漿中升高,在肝臟中降低[46]。在肝損傷早期,循環miR-122的水平對肝臟疾病的敏感度和特異度均明顯高于血清天冬氨酸氨基轉移酶(AST)和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T),有望成為早期檢測肝損傷的生物標志物[47]。循環miR-122的水平在健康成人個體間存在變異,將miR-122轉化為臨床診斷指標仍需要進一步研究。
3.2 miR-155
來源于肝臟庫普弗細胞的miR-155是一種肝臟特異性來源的miRNA,可參與多種免疫調節過程[48]。在樹突狀細胞的成熟過程中,miR-155作用于TAKI結合蛋白2(TAB2)分子,抑制下游的白細胞介素-1(IL-1)信號通路[49]。2016年一項關于miR-155的研究顯示,在APAP誘導的DILI中,miR-155通過抑制核轉錄因子κB(NF-κB)信號通路中的關鍵分子IKKε,有效減輕肝損傷及炎性反應[50]。另一項關于全氟辛烷磺酸鹽(PFOS)誘導肝損傷的研究發現,miR-155通過阻斷Nrf2/ARE信號通路,在PFOS誘導的肝毒性和細胞氧化應激損傷中起重要的調控作用[51]。在發生DILI時,肝臟及血清中的miR-155水平均顯著升高,有望成為臨床上診斷APAP誘導的肝損傷的生物標志物[50]。
3.3 miR-223
有研究指出,miR-223是中性粒細胞中含量較高的miRNA,能發揮調節粒細胞生成及成熟中性粒細胞穩態的生理作用[52]。此后的研究發現,miR-223可作為抗炎因子發揮作用,并通過控制多種靶基因調節肝細胞增殖及膽固醇代謝等[53-55]。APAP代謝的中間產物可誘發氧化應激損傷,同時,壞死肝細胞的線粒體DNA釋放,能夠促進Toll樣受體9(TLR9)與中性粒細胞結合,使中性粒細胞被募集并過度激活而促進炎性反應,加重肝臟損傷[56-58]。有研究發現,miR-223在APAP誘導DILI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負反饋調節作用,壞死肝細胞中線粒體DNA的釋放促進TLR9激活中性粒細胞,同時上調miR-223的表達,通過負反饋調節抑制中性粒細胞的過度激活并且靶向抑制NF-κB的上游激酶IKKα作用,有效抵抗炎性反應,從而減輕DILI[59]。miR-223在多種肝臟疾病中表達失調,包括DILI、肝炎病毒感染、酒精性肝損傷、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肝硬化和肝細胞癌,其診斷特異性較差,不適合作為診斷DILI的生物標志物。miR-223通過影響中性粒細胞浸潤、巨噬細胞極化及炎性體激活等影響DILI的進展,有望成為DILI的治療靶向分子。
3.4 miR-106b
miR-106b-25簇由miR-106b、miR-93及miR-25組成,在多種腫瘤的發生發展過程中發揮重要的調節作用[60-62]。2014年的一項研究發現,miR-106b能夠影響信號轉導和轉錄激活因子3(STAT3)的活化,小鼠在經氟烷處理后形成的DILI早期,miR-106b在肝臟組織中的表達發生了一定的變化,繼而通過STAT3影響下游輔助性T細胞17(Th17)的分化,產生IL-17等多種促炎因子[63]。與miR-223相似,miR-106b在DILI的炎性反應中發揮著重要的調節作用,有望成為DILI的治療靶向分子。
3.5 其他相關miRNA
除了上述典型的miRNA之外,另有部分miRNA在DILI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肝臟特異性來源的miR-192在APAP給藥后的小鼠血清中表達增加,并且具有劑量依賴性特點[46]。循環miR-192水平在APAP使用過量的急性肝損傷患者中具有相似變化[64]。最近有報道指出,與APAP在肝臟代謝中直接相關的兩種Ⅱ期酶的表達受miR-324-5p調控,考慮miR-324-5p抑制劑可作為解毒劑降低APAP的肝毒性[65]。miR-561能夠通過促進DAX-1基因表達誘導肝細胞核因子-4α激活,最終活化CYP3A4基因,而APAP在代謝過程中可抑制miR-561的調控作用,進而誘發DILI[66]。2016年日本研究者Mitsugi等[67]對曲伐沙星誘導的DILI進行了相關研究,結果表明miR-877-5p受曲伐沙星作用而表達上調,其下游與凋亡相關的重要蛋白磷酸烯醇丙酮酸羧激酶表達上調,引起肝細胞凋亡而加重肝損傷。
4 結語和展望
以ncRNA為核心對DILI進行的研究分為兩類:一是明確ncRNA在DILI的發病機制中發揮的作用,從而尋找治療DILI的靶點;二是探討循環血中ncRNA的表達水平對于患者評估病情等方面的臨床價值及應用前景。然而,現有研究對DILI發病機制的解釋仍不清晰,DILI的發病機制較為復雜且影響因素眾多。ncRNA的靶點尚不完全明確,且部分ncRNA的作用靶點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需要進一步研究,為臨床診斷、治療用藥及預后評估提供更為重要的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