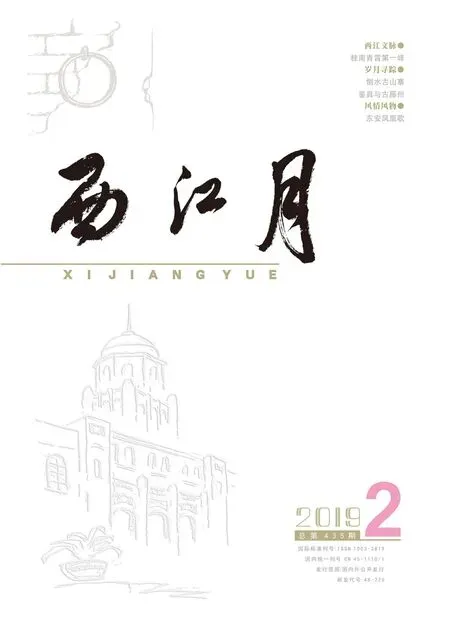十年不磨一劍 半夜窗寒自知
學畫于我,是個曲折的過程。
之所以說曲折,并非說我學畫有多大的波折,而是一路走來并非順暢。我本科讀的是美術教育專業,那時候很羨慕讀繪畫專業的同學,總感覺美術系的老師比美師的要好,估計這種錯覺只是學生時代的專業自卑。我的學習成績在班里算中等,屬于沒有天賦的那類學生,一度也曾經懷疑自己不適合學這個專業。這種感覺并非我獨有,借用伍小東先生的原話“國仕,老實說大學時候我真沒看上你”,這就足以證明我并不是一塊好料。估計在錄取研究生時選擇了我,伍先生也是頭疼的——這個家伙是怎么調劑來的?
好在本科畢業幾年后,我還是一如既往地追隨了伍先生,拜入語華庭園門下。不過我可沒少給先生帶來煩惱。舉個例子說,畫竹子是拿來理解畫理與筆墨虛實轉換的,一般資質好的同學一兩周就能解決了,我是屬于偶爾做得對、然后又犯迷糊的那種人。等到我真能把這個東西弄清楚,三年的研究生生涯已經過半。雖然伍先生看到我畫的那批六尺條屏的竹子高興得請我吃了一頓餃子,但是飯飽之余還是念念不忘地送了我一句“進步太慢了”。
雖然剛剛得到表揚,但是那會兒我的枕頭下面放的并不是藝術理論或者畫法研究之類的書,而是《子平命理》和《黃帝內經》。對于這樣不務正業的學生,伍先生也是拿我沒辦法,甚至到了要碩士畢業展的時候,我還拿著臘肉去拜師學太極拳,現在想來也是醉了。




我所學的東西五花八門,時間就這樣流逝,用在繪畫上的時間真的很少。不過也算我有福分,從讀碩士到離開南寧去北京讀博士,整整十年間我基本上都呆在伍先生身邊。雖然生性愚魯且駁雜不專,但長時間的磨合卻也使我能較為深刻地體會先生的教學套路與畫境追求。對于先生的語匯習慣、形象邏輯慢慢開始有進一步的認識。雖然這十年中的點滴改變很多都來自先生無奈的嘆息,不過對于專業的敬畏心我卻沒有減少,直到碩士畢業三年后,伍先生還語重心長地說:“這應該是你碩士畢業的水平才對。”想來,我忽略了先生的多少良苦用心。
真正學會用筆頭研究,是到了北京以后。北京的學習資源很多,看到的都是真跡,這無疑給我很大的刺激。而伍先生講的很多理論,也在我看過很多真跡之后才慢慢理解透徹。自己在實踐的過程中,也慢慢印證了之前的所思所想,以研究代創作的方法成為了近年來作畫的習慣。到了拜入陳綬祥先生門下,我的情況又不一樣了。陳先生沒有伍先生那樣溫文爾雅,很多時候都是聲色俱厲,他執拗的脾氣天下人皆知,以至于我初入師門之時,一直都是戰戰兢兢的,話也不敢多說,生怕用錯了詞而陷入老先生無窮無盡的思辨邏輯。那種緊張而壓抑的氣氛只有經歷過的人,才知道有多痛苦。雖然我是陳先生門下唯一一個實踐類博士,但是他很少看我的畫,甚至說過三年不許我畫畫這樣的言語。陳先生更多的是關注我讀的書與寫的字,搞得我畫畫往往都是“偷偷摸摸”進行的。
而對“文”的把握與對“理”的明晰,是陳先生茶余飯后常常用來衡量我們是否進步的重要標準,也是經常拿來敲打我們腦殼的利器。三年的博士學習,老先生主要是在思維方式與人格品質上影響我。而我對畫的認識得以慢慢提高,那是被他用“文”洗禮過的結果。一直以來我都不喜歡文人的酸腐氣,現實中對談不來的小文人翻臉拉黑的脾氣也一直還有。不過對于“文”的理解,我近來總算有些許自身體會。“文”在一定意義上,是一種克制。克制身上無時不有的“野”,雖然,追求率野一直是我寫文寫詩努力的方向,不過這個“野”的表面,應當蘊含“真”的品質,否則就因粗野而陷入了粗俗。而還原到自己的繪畫作品上,“文質彬彬”依然是我追求的最高目標。這個兩千年前的文化法則,依然適用于當下我們的文化追求。在琢磨點畫之間,我也慢慢把握了畫作的情、境、意、態,這種磨人的學習方式與磨畫的創作過程,慢慢地使我在心手相應的實踐當中略有所得。而在自我判斷的提升與對文化品格的把握上,我治學與作畫的文化源頭無疑在陳先生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