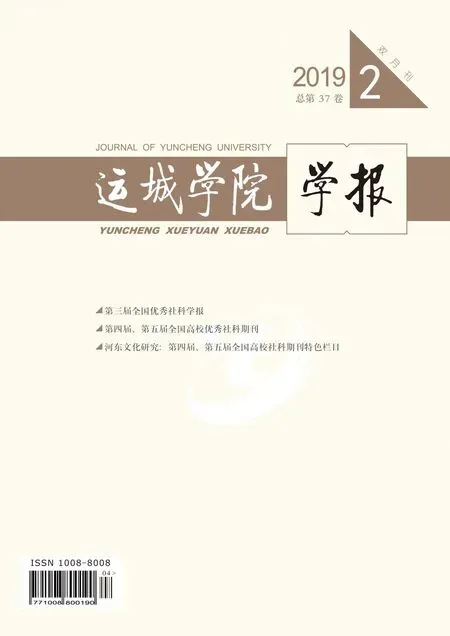儒家的真道統(tǒng)
楊 德 春
(邯鄲學(xué)院 中文系,河北 邯鄲 056005)
一、孔子秘傳與道統(tǒng)問題的產(chǎn)生
《春秋公羊傳》序疏:“案《孝經(jīng)·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jīng)》’是也。”[1]3《春秋公羊傳》隱公第一疏:“答曰:《孝經(jīng)說》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jīng)》屬參。’”[1]3《孝經(jīng)·鉤命決》、《孝經(jīng)說》就是《孝經(jīng)緯·鉤命訣》,《孝經(jīng)緯·鉤命訣》是漢代的緯書,根據(jù)文獻(xiàn)學(xué)的基本原則,緯書的文獻(xiàn)學(xué)價值要低于經(jīng)書和正史,即緯書不可靠。但是,《孝經(jīng)緯·鉤命訣》畢竟是漢代的緯書,漢代去先秦未遠(yuǎn),當(dāng)有歷史的影子。關(guān)鍵是單就此二條材料而言,根據(jù)文獻(xiàn)學(xué)的基本原則,當(dāng)然不可靠,如果有其他的佐證材料,則另當(dāng)別論,此二條材料恰恰是有其他的佐證材料,所以,此二條材料是另當(dāng)別論的緯書材料,對于認(rèn)識和理解孔子思想和儒家的發(fā)展變化具有重要意義。
何休《春秋公羊解詁》序引用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jīng)》。”[1]3這是孔子自言,是第一人稱自述;《春秋公羊傳》序疏:“案《孝經(jīng)·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jīng)》’是也。”[1]3《孝經(jīng)·鉤命決》卻是第三人稱的敘述,不是孔子自述。這值得注意,顯然,何休不是引用《孝經(jīng)·鉤命決》,而《孝經(jīng)·鉤命決》必然是對于孔子自述的轉(zhuǎn)述,則《孝經(jīng)·鉤命決》必然不是“志在《春秋》”、“以《春秋》屬商”等等說法的源頭文獻(xiàn),而“志在《春秋》”、“以《春秋》屬商”等等說法的源頭文獻(xiàn)也就絕不是緯書,而應(yīng)當(dāng)是先秦文獻(xiàn)(包括口述文獻(xiàn)),因為是秘傳,所以一般情況下當(dāng)不會見載于經(jīng)史,但是,《春秋公羊傳》口說流傳,至漢景帝時始著于竹帛,東漢何休此說當(dāng)為師傳。如果何休此說源于師傳,《春秋公羊傳》與《春秋穀梁傳》同源,《春秋穀梁傳》在先秦即有古文文本流傳[2]3,《春秋穀梁傳》從先秦流傳至西漢的古文文本或當(dāng)有記載和師傳,總而言之,何休之說和《孝經(jīng)·鉤命決》之說必有一個共同的先秦的文獻(xiàn)源頭,這就使何休之說和《孝經(jīng)·鉤命決》之說的文獻(xiàn)性質(zhì)發(fā)生了改變。
《春秋公羊傳》隱公第一疏:“答曰:案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jīng)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1]1《史記·孔子世家》:“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3]1944《春秋公羊傳》隱公第一疏:“答曰:《孝經(jīng)說》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jīng)》屬參。’”[1]3以前均是孤立地看待以上三條材料,我認(rèn)為應(yīng)該把以上三條材料聯(lián)系在一起看待,子夏不僅是孔子秘傳《春秋》的傳人,而且參加了孔子為《春秋》的資料收集工作,據(jù)“使子夏等十四人”的表述,子夏當(dāng)是孔子為《春秋》的資料收集工作的參加者和領(lǐng)導(dǎo)者。孔子為《春秋》的資料收集工作結(jié)束后九個月經(jīng)立,在九個月的立經(jīng)之時,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說明子游、子夏侍奉左右,為什么子游、子夏侍奉左右呢?因為文學(xué)子游子夏,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還說明孔子為《春秋》有微言大義,連有文學(xué)和文獻(xiàn)特長的游夏之徒都不能贊一辭,這就需要秘傳親授,孔子在游夏之徒中最后選擇了子夏,對其秘傳親授《春秋》。子夏參與了《春秋》的資料收集、侍奉編寫、秘傳親授的全過程,由十四人到二人,由二人到一人,子夏一步一步走到了最后,孔子以《春秋》屬商是符合邏輯的,是合情合理的,也就是可能的,此其一也。《史記》是正史,正史的材料與兩條緯書的材料相互聯(lián)系、相互關(guān)聯(lián),說明了或曰證明了這兩條緯書材料的一定的可靠性和可信性,此其二也。
孔子于晚年秘傳之前以詩書為教,沒有單獨傳經(jīng),不存在傳授系統(tǒng)問題,孔子晚年秘傳《春秋》和《孝經(jīng)》,因為是秘傳,所以才需要傳授系統(tǒng)以確保真?zhèn)鳎髞恚缎⒔?jīng)》失傳,《春秋》雖存,但是又發(fā)生了分裂,分裂為《春秋穀梁傳》、《春秋公羊傳》等,如此則不僅需要傳授系統(tǒng),而且道統(tǒng)問題也產(chǎn)生了。
二、堯、舜之前的道統(tǒng)
《漢書·藝文志》云:“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shù)家之傳。”[4]1701這條材料明確指出因為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所以《春秋》分為五。
《漢書·楚元王傳》云:“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zé)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圣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yīng)聘。自衛(wèi)反魯,然后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jì)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zhàn)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shù)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jīng)書,殺儒士,設(shè)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shù)由是遂滅。”[4]1968這條材料也明確指出了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
圣帝明王之道術(shù)原來是全的,至孔子,道術(shù)分裂難全,歆未言百家爭鳴,是其局限性。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所以,自衛(wèi)反魯然后禮樂正,歆在此言孔子與六經(jīng)的關(guān)系,如果不是“自衛(wèi)反魯,然后禮樂正”,則六經(jīng)獨缺禮,孔子與六經(jīng)的關(guān)系就不全,所以,此處歆是化用《論語》成句,承上文必有禮字,此文在流傳過程中因涉《論語》成句而誤脫禮字,由乃字也可知歆為化用《論語》成句,而非引用《論語》成句,樂前當(dāng)有禮字。孔子與六經(jīng)有關(guān)是為了紀(jì)帝王之道,也就是紀(jì)圣帝明王之道術(shù),只是沒有紀(jì)全,圣帝明王之道術(shù)分裂了,出現(xiàn)了百家爭鳴。孔子之學(xué)是圣帝明王之道術(shù),即帝王之術(shù)。《史記·李斯列傳》:“乃從荀卿學(xué)帝王之術(shù)。”[3]2539孔子之學(xué)和荀子之學(xué)都是圣帝明王之道術(shù),即帝王之術(shù),但是,由于繼承、理解、取舍等的不同,孔子之學(xué)和荀子之學(xué)的不同也就是必然的了。實際上,圣帝明王之道術(shù)就是五帝三王之學(xué),既然是五帝三王之學(xué),道統(tǒng)中的堯舜只是二帝,道統(tǒng)在堯舜之前應(yīng)當(dāng)依據(jù)《史記·五帝本紀(jì)》補(bǔ)入黃帝、顓頊、帝嚳,即道統(tǒng)要從黃帝開始。
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jì)》:
太史公曰:學(xué)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fēng)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fā)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非好學(xué)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jì)書首。[3]46
司馬遷對于關(guān)于五帝的材料進(jìn)行過去偽存真的選擇,著為本紀(jì)書首,當(dāng)可信;《書》缺有間矣,當(dāng)以《史記·五帝本紀(jì)》作為補(bǔ)充。
《史記》以黃帝為五帝之首,即《史記》以黃帝為歷史記載的起點,《史記》對于中國的歷史文化具有重要意義,所以,黃帝對于中國的歷史文化也具有重要意義。中國人為炎黃子孫,中國的文字產(chǎn)生于黃帝時期。黃帝第一次使分散的中國文化的因素實現(xiàn)了初步的整合。黃帝最早形成了中國文化的核心的地理范圍和進(jìn)一步發(fā)展的地理基礎(chǔ)。這個核心的地理范圍中的人都是黃帝子孫,黃帝子孫后來發(fā)展為不同民族仍然都是黃帝子孫。黃帝是最早的中國文化核心地理范圍的最高統(tǒng)治者,可以說黃帝是中國外王之道的開創(chuàng)者。黃帝以最高統(tǒng)治者而與炎帝稱為炎黃,謙虛禮讓,尊重他人才能尊重自己,讓他人活自己才能活,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dá)而達(dá)人,可以說黃帝是中國內(nèi)圣之道的開創(chuàng)者。黃帝既是中國外王之道的開創(chuàng)者,又是中國內(nèi)圣之道的開創(chuàng)者,從而形成了中國文化最初的特色,反映到學(xué)術(shù)上就是最初形成了帝王之道,所以,黃帝對于中國文化和儒家文化均具有重要意義,黃帝應(yīng)當(dāng)列于儒家道統(tǒng)之中。
黃帝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中華民族的各個組成部分都是黃帝的子孫,即中國的各個民族有一個共同的祖先黃帝,即黃帝是中國的各個民族的歷史的、文化的、民族的、血緣的真正祖先,中國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崇拜上帝,中國文化是崇拜祖先、重視孝道,如果對于黃帝持歷史虛無主義態(tài)度,中國文化的最初的老根就被刨掉了,后果和危害極為嚴(yán)重。司馬遷《史記》以科學(xué)的嚴(yán)謹(jǐn)態(tài)度去偽存真,以黃帝為五帝之首,以黃帝為中國的各個民族的共同的祖先,具有極為重要的學(xué)術(shù)意義、文化意義、歷史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一定要充分認(rèn)識到考古學(xué)的局限性,一切歷史記載都要經(jīng)過考古學(xué)的證明是不可能的,在對于司馬遷《史記》記載的第一個重要歷史人物黃帝沒有否定的證據(jù)、也不可能有否定的證據(jù)的情況下,對于司馬遷《史記》關(guān)于第一個重要歷史人物黃帝的記載要予以尊重。
僅僅因為道家尊黃老,就將人文初祖黃帝排除在道統(tǒng)或儒家道統(tǒng)之外,這是數(shù)典忘祖。墨家尊大禹,大禹仍然在儒家道統(tǒng)之內(nèi),以此例彼,對于人文初祖黃帝就不公平,這就表明韓愈所構(gòu)建的所謂的儒家道統(tǒng)局限性很大,不足為訓(xùn)。既然道統(tǒng)存在重大問題,則所傳之道必然也存在重大問題,絕非真正之道。
三、孔子之后的道統(tǒng)(上)
《漢書·藝文志》云:“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shù)家之傳。”[4]1701《漢書·楚元王傳》云:“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4]1968
以上兩條材料還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即仲尼沒而微言絕,但是,七十子尚傳有仲尼關(guān)于六經(jīng)的大義,七十子喪而仲尼關(guān)于六經(jīng)的大義乖,只是乖,仲尼關(guān)于六經(jīng)的大義有可能沒有絕,七十子中得到仲尼關(guān)于六經(jīng)的大義者只可能是秘傳者,子夏是秘傳者之一,可能傳仲尼關(guān)于六經(jīng)的大義。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3]2202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3]2203
《史記·儒林列傳》:“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yè)于子夏之倫,為王者師。”[3]3116
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5]
洪邁《容齋續(xù)筆》“卜子夏”條曰:“魏文侯以卜子夏為師。案《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后一年元王立,歷貞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為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為大夫二十二年而為侯,又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為諸侯師,豈其然乎?”[6]242
文侯為大夫二十二年,后人以文侯代其名,子夏在西河教授,于文侯為大夫之時為文侯之師,其時子夏八十多歲,后子夏弟子也在魏活動,故子夏在西河教授,曾為魏文侯之師的記載是可靠的。但子夏在西河教授的《春秋》只是籠統(tǒng)的《春秋》闡釋之學(xué),還沒有形成后來的《春秋穀梁傳》和《春秋公羊傳》。
現(xiàn)存《春秋穀梁傳》的實際情況卻是:現(xiàn)有材料無法確考穀梁子以前的無名氏和子夏,子夏與《春秋》的關(guān)系現(xiàn)無直接證據(jù),基本上屬于傳說性質(zhì),不是很可靠的,也不是完全不可靠的。退一步說,就算《春秋》是由子夏傳出的,子夏所傳之《春秋》也只是籠統(tǒng)的《春秋》闡釋之學(xué),其中既有《春秋穀梁傳》的因素也有《春秋公羊傳》的因素。所以,真正意義上的《春秋穀梁傳》當(dāng)始于穀梁子。穀梁子從傳說的子夏所傳之籠統(tǒng)的《春秋》闡釋之學(xué)中分離出來,形成了《春秋穀梁傳》最初的學(xué)術(shù)特色,《春秋穀梁傳》所闡發(fā)的孔子的《春秋》的微言大義只能看成是《春秋穀梁傳》自己的思想。
惠棟《九經(jīng)古義·穀梁古義》:
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jīng)于子夏矣。古人親受業(yè)者稱弟子,轉(zhuǎn)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子于子夏,猶孟子之于子思。故魏麋信注《穀梁》以為與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勛言“穀梁為經(jīng)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7]
“弟子”與“門人”古可通用,但惠棟認(rèn)為東漢應(yīng)劭《風(fēng)俗通》“穀梁為子夏門人”與楊士勛《春秋穀梁傳集解序疏》“受經(jīng)于子夏”(即親受業(yè)于子夏)是不同的,即惠棟認(rèn)為親受業(yè)者稱弟子,轉(zhuǎn)相授者稱門人。惠棟認(rèn)為:從東漢桓譚《新論》所言穀梁赤撰《春秋穀梁傳》在《左傳》“行世百余年后”,則從時間上穀梁赤必然不是子夏親傳弟子。既然從時間上穀梁子生活的年代與子夏相距過遠(yuǎn),則穀梁子只能受學(xué)于子夏之弟子。惠棟此論僅僅從《春秋穀梁傳》傳授系統(tǒng)上著眼,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沒有考慮孔子晚年秘傳的道統(tǒng)問題,孔子于晚年秘傳之前以詩書為教,沒有單獨傳經(jīng),不存在傳授系統(tǒng)問題,孔子晚年秘傳《春秋》和《孝經(jīng)》,因為是秘傳,所以才需要傳授系統(tǒng)以確保真?zhèn)鳎髞恚缎⒔?jīng)》失傳,《春秋》雖存,但是又發(fā)生了分裂,分裂為《春秋穀梁傳》、《春秋公羊傳》等,如此則不僅需要傳授系統(tǒng),而且道統(tǒng)問題也產(chǎn)生了。即《春秋穀梁傳》的傳授系統(tǒng)不僅僅是傳授系統(tǒng),還具有道統(tǒng)的意義,所以,在年代上跨度大,在傳承人代數(shù)上有跳躍性,也就是省略了一些不重要的傳承人,具有道統(tǒng)的特點。《春秋穀梁傳》具有道統(tǒng)性質(zhì)和特點的傳授系統(tǒng)影響相當(dāng)深遠(yuǎn),首先影響了《春秋》分裂后剩余部分的傳授系統(tǒng),即《春秋公羊傳》傳授系統(tǒng),影響了孟子建立道統(tǒng)論,然后影響了古文經(jīng)學(xué)各個傳授系統(tǒng)。
荀子確為《春秋穀梁傳》傳人。但是還有一個問題,《荀子·非十二子》云:“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8]105《荀子·大略》云:“言而不稱師謂之畔,教而不稱師謂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內(nèi),朝士大夫遇諸涂不與言。”楊倞注:“畔者,倍之半也。教人不稱師,其罪重。故謂之倍。倍者,反逆之名也。”[8]506《春秋穀梁傳》若由子夏傳出,子夏乃荀子先師,荀子不會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我認(rèn)為有兩點需要說明,其一,子夏傳《春秋穀梁傳》只不過是傳說,并不是十分可靠。其二,荀子所罵只不過是子夏的不肖弟子,荀子對子夏還是尊敬的。《荀子·大略》云:“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fù)見。柳下惠與后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8]513可證荀子對子夏人格之敬重。
洪邁《容齋續(xù)筆》“子夏經(jīng)學(xué)”條:
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諸經(jīng)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為與它人不同矣。于《易》則有傳,于《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xué),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于《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為之訓(xùn)說。于《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于斯矣。公羊高實受之于子夏,穀梁赤者,《風(fēng)俗通》亦云子夏門人。于《論語》,則鄭康成以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后漢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fā)明章句,始于子夏。斯其證云。[6]397-398
范曄《后漢書·鄧張徐張胡列傳》記載徐防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fā)明章句,始于子夏。”[9]1500經(jīng)起于孔子而解經(jīng)起于子夏,子夏由獲得孔子之道的解釋權(quán)而成為孔子之道的直接繼承人,子夏必然為道統(tǒng)中人。曾子與此無關(guān),即曾子失去了或沒有得到孔子之道的解釋權(quán)也就不可能染指孔子之道的繼承權(quán),也就與道統(tǒng)毫無關(guān)系可言。
《禮記·檀弓上》: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吊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10]202-203
其一,子夏相信天命,以其無罪而喪其子、喪其明質(zhì)問于天;曾子實不相信天命,以喪明為喪子所導(dǎo)致,已經(jīng)背離了孔子的學(xué)說,比疑子夏于夫子之罪更重,也沒有天罰,曾子放膽發(fā)怒,一如小人之肆無忌憚,所謂子思、孟子之學(xué)不可能由曾子而來。其二,曾子指控子夏之一二二罪,涉及敬師孝親,與孔子以《孝經(jīng)》屬參暗合。其三,曾子怒責(zé)子夏,實際上是曾子與子夏相爭之反映,而且是曾子與子夏相爭失敗后氣急敗壞之反映。子夏必然為道統(tǒng)中人,而曾子非也。
四、孔子之后的道統(tǒng)(中)
《漢書·藝文志》云:
《孝經(jīng)》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jīng),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jīng)》。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jīng)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4]1719
博士江翁、安昌侯張禹等皆為荀子之學(xué)的傳承人,《孝經(jīng)》當(dāng)為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所傳。《孝經(jīng)緯·鉤命訣》中有孔子之言“吾志在《孝經(jīng)》,行在《春秋》。”“以《春秋》屬商,《孝經(jīng)》屬參。”由此可知孔子傳經(jīng)于子夏與曾子二人,曾子傳子思,但是,子思并未傳孟子,孟子是自己從當(dāng)時所能接觸到的子夏、穀梁子一派的儒者處學(xué)習(xí),自己取舍,自己獨立思考,逐步歸向子思學(xué)派的。問題的關(guān)鍵是曾子傳子思后,這一派的學(xué)問就失傳了,漢代復(fù)出的《孝經(jīng)》不是曾子所傳,而是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所傳,這是問題的關(guān)鍵所在。《大戴禮記》之內(nèi)容是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所傳,《大戴禮記》中的關(guān)于曾子的文獻(xiàn)自然也是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所傳。《小戴禮記·曾子問》言天無二日,《小戴禮記·坊記》也言天無二日,《孟子·萬章上》也言天無二日,皆出于《春秋穀梁傳》所載孔子之微言大義“大上故不名”,證明《小戴禮記》之內(nèi)容也是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所傳,這也再次證明孟子學(xué)習(xí)過《春秋穀梁傳》,關(guān)于孟子學(xué)習(xí)過《春秋穀梁傳》的其他證據(jù)見楊德春《葵丘之會天子禁令考》[11]。《孝經(jīng)》中關(guān)于天子之孝的內(nèi)容應(yīng)當(dāng)是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的思想,而絕不是曾子、子思學(xué)派的思想。孟子是從子夏、穀梁子一派的儒者處學(xué)習(xí),自己取舍,自己獨立思考,逐步歸向子思學(xué)派的,也可以說曾子子思之學(xué)失傳后,孟子在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所傳之學(xué)說和文獻(xiàn)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和重新構(gòu)建了曾子子思之學(xué),這一套學(xué)問后來被稱為思孟之學(xué),這一學(xué)派后來被稱為思孟學(xué)派。
《孟子》最后一章《盡心下》第三十八章:
孟子曰:“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余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余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余歲,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遠(yuǎn)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12]408-409
孟子實際上提出了儒家的新的道統(tǒng)觀,堯、舜、湯、文王、孔子,孟子以孔子之繼承者自居,但是,未明言。孟子的這種道統(tǒng)觀實際上就是來源于并且針對《春秋穀梁傳》或《春秋》的傳授系統(tǒng),因為孔子晚年僅傳二經(jīng),而其中之一《孝經(jīng)》失傳,至漢復(fù)出,為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所傳,有傳授系統(tǒng)的只有《春秋》,在《春秋》傳授中,孟子受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的《春秋穀梁傳》影響最大,孟子在《孟子》最后一章提出新的道統(tǒng)觀,將自己學(xué)問的來源直接上接孔子,以孔子私塾弟子自居,也以孔子學(xué)說的繼承人自居,黜落子夏、穀梁子,這也從反面證明孟子之學(xué)來源于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所傳之學(xué),自己取舍,自己獨立思考,孟子在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所傳之學(xué)說和文獻(xiàn)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和重新構(gòu)建了曾子子思之學(xué)。
韓愈繼承和發(fā)展了孟子的道統(tǒng)觀,韓愈《原道》:“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13]18韓愈《原道》正式提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統(tǒng)說,影響深遠(yuǎn)。韓愈把黃帝、顓頊、帝嚳和子夏、穀梁子、荀子等排斥于道統(tǒng)之外,則韓愈所謂之道統(tǒng)可商也,絕非不可修正之最后定論。
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jì)。”[3]510《索隱》:“荀況、孟軻、韓?皆著書,自稱‘子’。宋有公孫固,無所述。此固,齊?韓固,傳詩者。”[3]511宋之公孫固,不僅無所述,而且是春秋時期之人,《春秋》尚未成書,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九無從談起。如此則司馬遷《史記》此處之公孫固當(dāng)與荀卿、孟子、韓非一樣為戰(zhàn)國時期之人。《索隱》以為此固指齊?韓固,為傳詩者,然傳齊詩者為齊人轅固,非為韓固,《索隱》之韓固之韓當(dāng)為轅之形訛。轅固又稱為轅固生,可見轅固為復(fù)姓,即固非為名,如此則與公孫固無關(guān)。韓非為荀子之學(xué)生,荀子是子夏一派正統(tǒng),孟子也受到子夏一派影響,故附于荀子之后。這不僅僅是司馬遷的看法,而是當(dāng)時學(xué)術(shù)界的一般看法。
王充《論衡·對作篇》:“或問曰:賢圣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黨,下至荀、孟之徒,教訓(xùn)必作垂文。何也?”[14]1177孔墨,墨生于孔,荀孟,孟源于子夏一派。
孔子、荀子、孟子三圣關(guān)鍵是荀子以及荀孟的次序,我主張孔子是先圣,荀子直接相對于孔子稱為后圣;因為是荀孟,所以孟子相對于荀子稱為亞圣或附圣,即孟子是附于道統(tǒng)之后的圣人。
五、孔子之后的道統(tǒng)(下)
胡適《中國哲學(xué)史大綱·荀子以前的儒家·大學(xué)與中庸》
個人之注重我從前講孔門弟子的學(xué)說時,曾說孔門有一派把一個“孝”字看得太重了,后來的結(jié)果,便把個人埋沒在家庭倫理之中。“我”竟不是一個“我”,只是“我的父母的兒子”。例如“戰(zhàn)陳無勇”一條,不說我當(dāng)了兵便不該如此,卻說凡是孝子,便不該如此。這種家庭倫理的結(jié)果,自然生出兩種反動:一種是極端的個人主義,如楊朱的為我主義,不肯“損一毫利天下”;一種是極端的為人主義,如墨家的兼愛主義,要“視人之身若其身,視人之家若其家,視人之國若其國”。有了這兩種極端的學(xué)說,不由得儒家不變換他們的倫理觀念了。所以《大學(xué)》的主要方法,如上文所引,把“修身”作一切的根本。格物、致知、正心、誠意,都是修身的工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修身的效果。這個“身”,這個“個人”,便是一切倫理的中心點。《孝經(jīng)》說:自天子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大學(xué)》說: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這兩句“自天子至于庶人”的不同之處,便是《大學(xué)》的儒教和《孝經(jīng)》的儒教大不相同之處了。[15]204-205
胡適已經(jīng)指出孔子傳曾子的這一派學(xué)說有致命的缺陷。《大學(xué)》的儒教和《孝經(jīng)》的儒教大不相同,實際上否定了《大學(xué)》由曾子而來。
我認(rèn)為,《孟子》所反對的楊朱的極端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或曰為我主義,恰恰是由孔子傳曾子的這一派學(xué)說而來,這一方面表明孟子所學(xué)絕非來自曾子的這一派學(xué)說,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絕對不可靠,另一方面表明孔子傳曾子的這一派學(xué)說的致命缺陷必然導(dǎo)致孔子傳曾子的這一派學(xué)說的衰亡,真理并非只有孟子能夠認(rèn)識,孔子的其他弟子和曾子的學(xué)生必然有人能夠發(fā)現(xiàn)孔子傳曾子的這一派學(xué)說的致命缺陷而改換門庭或改換師門,曾參的兒子兼學(xué)生曾申改換門庭或改換師門而就學(xué)于子夏即是明證,連曾參的兒子兼學(xué)生曾申都背叛了師門和孝道,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16]10曾參尚在,曾參的兒子兼學(xué)生曾申就已經(jīng)改于父之道了,孔子傳曾參的這一派不衰亡反而奇怪了,曾參和曾申共同的學(xué)生吳起也改換門庭而就學(xué)于子夏,孔子傳曾子的這一派必然衰亡。兼愛主義的或曰極端的為人主義的墨家恰恰是從儒家分出來的,是孔子提倡孝的必然結(jié)果,又鑒于子夏培養(yǎng)了墨家的禽滑釐。再鑒于孔子曾經(jīng)就學(xué)于老子,孔子晚年的另一個秘傳之人子夏培養(yǎng)了田子方,田子方培養(yǎng)了莊子。又鑒于子夏培養(yǎng)了李悝、吳起,而李悝、吳起開創(chuàng)了法家,又鑒于子夏的再傳弟子荀子培養(yǎng)了韓非、李斯,使法家文化登峰造極。即墨家、道家、法家均來源于儒家。
《莊子·天下篇》言道術(shù)分裂,孔子曾經(jīng)就學(xué)于老子,所學(xué)當(dāng)是道術(shù)尚未分裂的道術(shù),自孔子之后道術(shù)分裂。所以,中國文化的復(fù)興或曰現(xiàn)代化不是僅僅使作為中國文化的主體部分的儒家文化復(fù)興或曰現(xiàn)代化,還要解決道術(shù)分裂的問題。解決道術(shù)分裂的問題要以最早的道術(shù)分裂所形成的儒家為基礎(chǔ)而整合百家,在實現(xiàn)中國文化的整合中實現(xiàn)中國文化的復(fù)興或曰現(xiàn)代化。
儒家的真道統(tǒng)應(yīng)該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子夏、穀梁子、荀子、孟子。由于孟子是從子夏、穀梁子這一派學(xué)習(xí),獨立出去后恢復(fù)或重建了子思之學(xué),所以附于荀子之后。鑒于道統(tǒng)的嚴(yán)肅性、權(quán)威性和局限性,我主張道統(tǒng)僅限于先秦,先秦之后無道統(tǒ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