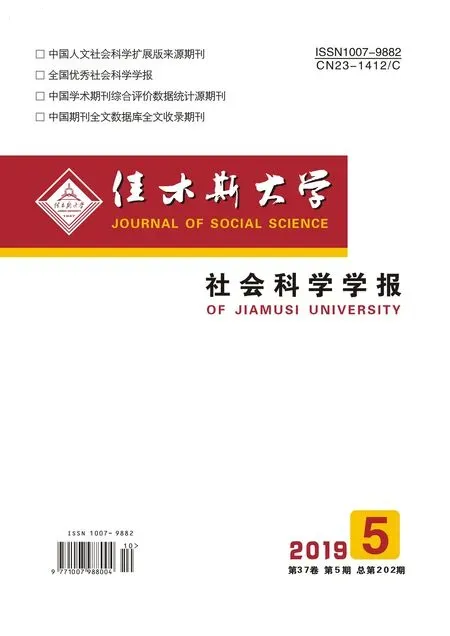葉燮《原詩》對蘇軾詩歌的評點
李 倩
(陜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陜西 西安 710119)
唐宋時期是中國詩歌創作的輝煌時期,在此之后的學詩者不出于唐即歸于宋,很難突破這兩座高峰。明代前后七子力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主張,以唐詩為典范,對宋詩則棄之如敝屣,多有詆毀,影響力之大波及整個明代詩壇。雖然明代詩學發展到嘉靖后期,公安三袁、競陵派鐘惺、譚元春等相繼起而掊之,欲革除明詩積弊,同時為宋詩辯護,且于宋代詩人中極力推崇蘇軾,卻最終矯枉過正,有失公允,但也使得尊唐風氣稍有逆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記載:“詩自太倉、歷下,以雄渾、博麗為主,其失也膚;公安、竟陵,以清新、幽渺為宗,其失也詭。學者兩途并窮,不得不折而入宋”[1]5205,使得清代詩壇的詩學宗尚逐漸轉向宋詩。清初詩論家吸取明代七子派學詩獨尊盛唐以至走向極端的教訓,在詩學主張上不再分唐界宋,而是唐宋兼宗,既肯定唐詩的價值,也不貶斥宋詩。葉燮作為清代前期重要的詩學批評家,論詩主張唐宋兼宗,在其詩學理論專著《原詩》中對明代稱詩者只談唐詩,恥言宋詩的現象進行了批判,以“變”為核心,從詩史演進的角度論述了宋詩在唐詩基礎上的繼承與發展,能事益精,將宋詩置于詩歌發展的頂點,極力推崇宋詩,尤其推尊蘇軾,在蘇詩上著墨較多,對其給予極高評價,為我們研究蘇軾在清代前期的接受情況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文獻,以下詳而述之。
一、蘇詩創變之功
宋初,詩歌發展與晚唐五代一脈相承,仍襲唐音;到梅堯臣、蘇舜欽出現,旨在廓清晚唐弊端,主張詩體革新,詩歌面貌才有所變化,逐漸更為宋調;發展到蘇、黃主導詩壇時期,宋詩面貌基本定型,呈現出以意為主,重議論,尚理趣的風格特征。在這一宋詩區別于唐詩,最終能夠在中國詩歌史上與唐詩平分秋色的過程中,蘇軾對宋詩的創變有著關鍵性作用。然而,對于蘇詩創變之功的評價,歷代詩學批評家多持否定意見。
南宋張戒在《歲寒堂詩話》中將歷代詩歌分為五等:“國朝諸人詩為一等,唐人詩為一等,六朝詩為一等,陶、阮、建安七子、兩漢為一等,《風》、《騷》為一等。學者須以次參究,盈科而后進,可也。”[2]451其中將宋詩置于最末的位置,同時對詩歌發展中幾個關鍵人物予以評價,認為“自漢、魏以來,詩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壞于蘇、黃”[2]57,對曹植、李白、杜甫給予高度贊揚,對蘇軾則是給予嚴厲批判,其原因在于張氏認為蘇軾作詩喜歡使事用典,講究押韻,而將詩歌從《詩經》發端到唐詩以來力主詠物、言志的傳統遺棄,本末倒置,致使詩歌的風雅精神蕩然無存。明代胡應麟在《詩藪》中云:“永叔、介父,始欲汛掃前流,自開堂奧,至坡老、涪翁,乃大壞不復可理。”[3]209認為宋代詩歌在歐陽修,王安石時掃除晚唐詩歌積弊,開宋詩一代風氣,而到了蘇、黃主導詩壇時期卻走向下坡路,對二人進行嚴厲批評。
葉燮對于歷代詩人的評價,完全是以他們在詩歌史上的創變程度為衡量尺度的,因此,對蘇軾于宋詩發展中的創變予以高度肯定,并將其與杜甫、韓愈并稱,為古今一大變。可以說,宋代詩歌真正區別于唐詩的獨特風貌,到蘇軾才真正形成。在《原詩·內篇》上稱“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于筆端,而適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韓愈后之一大變也,而盛極矣”[4]9,蘇詩境界之大,盛極一時。又在《原詩·外篇》上中對蘇軾詩歌的獨特面貌進行概括,認為“舉蘇軾之一篇一句,無處不可見其凌空如天馬,游戲如飛仙,風流儒雅,無入不得,好善而樂與,嬉笑怒罵,四時之氣皆備:此蘇軾之面目也。”[4]50蘇軾作詩無所不有,森羅萬象,世間萬物經其陶鑄,皆為上乘之作,是庸夫俗子無法領悟的。以才學為詩,擅長使事用典,并且能夠恰到好處。葉燮從蘇軾作詩擅長使事用典的淵源入手,指出其來源于杜甫,而又有所創造。然后對其具體的使事用典習慣進行說明。與韓愈用事習慣于根據自己的意愿將舊事更換一二字以出新意不同,蘇軾用事經常是一句中用兩事或三事,這并不是賣弄文墨,炫耀才學,而是其“力大”所致,廣泛涉獵,博觀而約取后無不可入的詩歌創造能力使然。而一句只用一事,并非不可,但是不能以之為準繩,要求詩歌創作必須遵循此規則,要靈活變通,否則不是在作詩而是在記事。而那些堅持一句只能用一事者,如井底之蛙,是沒有見過韓愈、蘇軾與杜甫如何使事用典的人,由此可見葉燮對蘇詩的使事用典不止于一事的行為是頗為贊同的。
二、蘇軾“自然”論文藝觀
文學理論中強調“自然”的美學風范早已有之,其淵源于先秦時期老莊的“自然”論哲學,強調萬事萬物的本來狀態,非外物使然。到魏晉時期玄學盛行,人們圍繞“名教”與“自然”的關系展開論辯,“自然”觀逐漸為時人所接受,開始運用到文藝領域。南北朝時期的劉勰在其批判理論巨著《文心雕龍》中多次將“自然”一詞引入其文學理論體系中探討文學的起源,如《明詩》中云:“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5]65,指出文學作品是人們有感于物,抒發自我情感的載體,劉勰在文學批評時對文學起源論——“自然”觀的闡發逐漸演變為一種文藝觀念,至此以后,許多文學批評著作在談及文學時,時常以“自然”準則為論詩衡文的審美風尚。與劉勰同一時期的鐘嶸在《詩品》中更是提出詩歌 “吟詠情性”的本質屬性和“自然英旨”說,主張詩歌創作以“自然”為最高美學原則,很明顯是從劉勰處發展借鑒而來。唐代皎然《詩式》中言“律家之流,拘而多忌,失于自然,吾常所病也”[6]204,對律詩嚴格講究聲病,而喪失自然本質的特點多加指責。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專列“自然”一品,足可見其重要性。
蘇軾論詩同樣崇尚“自然”,葉燮在《內篇》下卷中提到蘇軾有言:“我文如萬斛源泉,隨地而出。”[4]23與自己的詩學理論相互參證,同時霍松林先生對此則詩論進行校注時又提到蘇軾的其他言論來與葉燮的理論相發明,摘錄如下: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4]38
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4]38
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云霧,草木之有華實,充實勃郁而見于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4]38
從以上幾句我們可以洞察出蘇軾論詩追求自然,這種“自然”在這里主要體現在創作緣起和創作法度兩個方面。從創作緣起來看,蘇軾主張“無意為文”,與劉勰提倡的“為情而造文”如出一轍,“能為之”與“不能不為之”的區別就在于作者是否帶有功利目的,蘇軾拿自然萬物作比,山川之所以有云霧繚繞,草木之所以會開花結果,是因為它們充實蓬勃不得不發的結果,非外力強制。作文亦如此,情志充實于內心到了不得不抒發的緊要關頭,這種情況下創作出來的詩文自然工巧雅致。從創作法度來看,蘇軾主張為詩為文要順應事物的自然規律及內在秉性,不要被法度所限制,要行于所當行,止于不可不止,這樣創作出來的詩文自然是符合事物的本來特征而生動形象的。
葉燮在這里援引蘇軾的觀點是為了闡發自己詩學理論“理事情”三要素中“情”這一要素。“情”指的是客觀事物的感性情狀,不僅具有客體意義,同時經過審美主體的感性處理融入了主體之情,因此在葉燮這里,作為詩歌反映對象的“情”既表現為客體之情,也表現為主體之情,將主客體有機地聯系起來,通過以泰山云彩變化作比,意在表明詩歌創作必須隨物賦形,為表現客觀事物的不同情狀而形態各異。既然作為表現客體的事物變幻萬千,那么創作也必須遵循自然之法,以表天地萬物之情狀。由此可見,葉燮這一理論是對蘇軾詩論觀點的繼承和發展,二者可以互相參證發明。
三、蘇軾其人之學識與道德修養
文學作品作為主客觀結合的產物,其品質的高下優劣與作家主體學識修養的高低密切相關。這種學識修養由作家在閱讀實踐過程中積累而成,并在潛意識中作用于文學創作的全過程,集中表現為才、學、識等方面,古代文學理論批評中多有提及。東漢品評人物的風氣風靡一時,逐漸影響到文學批評中對作家的要求,魏晉時曹丕在《典論·論文》中即提出“文以氣為主”[7]158,“氣”指的是人的氣質個性,表現在文學創作上就是人的才能本性,并且指出只有“通才”才能諸體兼備,創作起來游刃有余。陸機《文賦》中云:“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7]170,窺見作品中用心之處,對才識之士欣賞有加。嚴羽在《滄浪詩話》開篇即指出“夫學詩者以識為主”[8]1,強調了作家學識修養的重要性。如此種種,不勝枚舉。唐代史學家劉知己在《史通》中論述史學家的學識修養時說道“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9]75,理想的史學家應是“才”“學”“識”三者兼備,三者缺一不可,然而很少能有人達到如此程度,因此真正優秀的史學人才很少,這一看法得到后代批評家的普遍認可。葉燮在此基礎上發揮創造,遷移應用到文學創作理論上來進行詳細說明,提出了“才、膽、識、力”四要素,從而對創作主體的主觀條件進行系統性理論性闡述。“大凡人無才,則心思不出;無膽,則筆墨畏縮;無識,則不能取舍;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4]16,四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葉燮論詩人于唐代最推崇杜甫和韓愈,于宋代最尊崇蘇軾。在葉燮的批評中,對蘇軾的才力予以高度贊揚,將其與左丘明、司馬遷、賈誼、李白、杜甫和韓愈等古之才人并舉,其共同點在于這些人都是集“才、膽、力、識”于一身。葉燮認為蘇軾作詩作文,以才學為詩,運天地萬物于筆端,無所不入,全在于其“力大而才能堅”[4]27,因此他的作品才能歷經百代而流傳千古。
考察文人品德修養與文學創作的關系同樣是文學批評家關注的重點之一。《論語·憲問》中言:“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10]144,孔子已然強調德行的重要性。《左傳》提出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說法,并且將立德放在首位,足可見其重要性。劉熙載更是以“詩品出于人品”的論斷為準則進行其文學批評,葉燮詩學批評中亦有涉及。在《外篇》上中稱“每詩以人見,人又以詩見”[4]52,詩歌是詩人內心的寫照。韓愈、蘇軾、歐陽修等人都是文、詩和人品相統一的,意在表明人如其詩,詩如其人,接著又提出了“古人之詩,必有古人之品量。其詩百代者,品量亦百代”[4]52,一個人的詩作能夠流傳百代,那么他的人品同樣傳承下去。蘇軾對其門人黃庭堅、秦觀、張耒等人都愛之如己,非常賞識有才學的人,因此到其門下求學的人門庭若市。葉燮對于蘇軾這一人格魅力是高度贊揚的,由此可以看出其對詩品與人品相一致的提倡。
四、對蘇軾評詩話語的引錄
蘇軾作為宋代最具影響力的文人之一,其成就是多方面的,不僅在詩、詞、文等文學創作與繪畫、書法等藝術領域造詣極高,在文學評論方面也成就頗豐。這些有關詩詞文的批評散見于他的記、序跋、書信等實用性文體中,都體現了作者自己的獨特見解。葉燮在進行具體的批評實踐時亦有提及,主要表現在葉燮評孟浩然和白居易二人時,引述蘇軾的評語,并通過蘇軾的評語表明了自己的觀點。
首先體現在葉燮評孟浩然詩的實踐過程中。中國詩歌史上自王維孟浩然開創山水田園詩派伊始,后世詩人和批評家便時常對二人進行比較,尤其發展到北宋時期,這種比較愈演愈烈,走向極端,出現了明顯的“王孟優劣論”劃分,或揚王抑孟,或揚孟抑王,而蘇軾可以說是發起此議論的第一人。蘇軾堅持“孟不及王”,對王維詩進行高度贊揚,而對孟浩然之詩則多加貶斥。陳師道在《后山詩話》中記載了蘇軾評價孟浩然的一段話,其云:“子瞻謂孟浩然之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爾。”[11]308成為后代評詩者評價孟詩時的一個重要參照,或認同而在此基礎上繼續展開議論,或反對而加以指責。葉燮在對孟詩進行具體的批評時,也引用了這一評語,說道:“孟浩然諸體,似乎澹遠,然無縹緲幽深思致,如畫家寫意,墨氣都無。蘇軾謂‘浩然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誠為知言。后人胸無才思,易于沖口而出,孟開其端也。”[4]65葉燮認為孟浩然的各體詩歌作品,看似恬淡廣遠,實則缺乏深意,原因在于孟浩然心中無才,作詩時易脫口而出,不假思索,給其后學詩作詩者作了不好的示范。葉燮對蘇軾評孟詩這一話語予以了肯定,由此可見葉燮詩學思想中詩人之“才”對創作主體的重要性。
其次是葉燮評白居易詩。白居易作詩多通俗易懂,這一特點常被后人譏諷,在清初以王士禎為代表的神韻派主導詩壇時,追求典雅與神韻,對元、白詩派尚俚俗的詩風多有詬病,從葉燮開始,這一情況才稍有好轉。葉燮在批評白居易詩時,指出歷代文人稱白詩“老嫗可曉”,并且引述了蘇軾的一句評語“局于淺切,又不能變風操,故讀之易厭”[4]66作例進行他的分析批評,從中我們可以同時看出蘇軾和葉燮兩人的詩論觀。蘇軾論詩崇尚“枯淡”美,他在《評韓柳詩》一文中對“枯淡”一詞做了詳細說明:“所貴乎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淡,亦何足道!”[12]2109-2110蘇軾論“枯淡”時,將“枯”與“膏”并置,枯淡之詩在外在形式上給人一種了無生趣之感,然而內在卻是十分豐滿,暗含精華的,枯以實為前提,實是枯的升華,二者相生相成,辯證統一,看似平淡,實則精美。如果整首詩都給人一種平淡的感覺,那么這種詩是不值得被人稱道的。由此觀之,蘇軾對白居易詩的這一評價是源于其一味追求俚俗而無變化而發出的,可謂直中要害,與其追求“枯淡”的審美風格是相統一的。葉燮認為蘇軾的這一評價有一定的道理,但這只是針對白詩中那些失口而出之作,白詩中還有一部分寄托深遠,耐人尋味的作品,并且通過《重賦》《不致仕》《傷友》《傷宅》等作品來舉例論證,言淺而理深,于俗處見雅,具有強烈的諷諭效果,因此蘇軾這一看法有失偏頗,應該對白詩進行全面觀照。葉燮對白居易的這一評價扭轉了時人貶斥白詩的風氣,為白詩在清中葉詩評家中重新定位其詩史價值開風氣之先。
葉燮詩學思想掃除明代詩壇“詩必盛唐”積弊,論詩唐宋兼宗,將宋詩放在與唐詩齊平的位置,為宋詩張目,且于宋詩中最推崇蘇軾,不僅在于其與蘇軾有著相似的思想基礎,深受釋道兩家影響,追求自由淡泊,更在于其詩學思想上的共鳴。葉燮對蘇軾詩歌詩論的評點,既有對其詩歌成就的高度贊揚,也有對其缺陷的補充完善。對蘇軾于宋詩發展中的創變予以高度肯定,以才學為詩,擅長使事用典,使得宋詩真正區別于唐詩,并呈現出與唐詩不同的獨特風貌;援引蘇軾崇尚“自然”的詩論主張,與自己詩學思想互相參證,表明其對蘇軾詩學思想的繼承與發展;推崇蘇軾其人的學識修養與道德修養,充實自己“才膽識力”的詩學理論;在評價孟浩然詩歌中引錄蘇軾對孟浩然的評價,并對其予以肯定,表明詩人之“才”的重要性,而在對白居易詩評價時,能夠指出蘇軾評白詩只看到了其缺點,而忽視了價值較高的那一類作品,在此基礎上對白詩進行全面評價,盡顯批評家的公正態度。綜觀葉燮對蘇軾詩歌的批評,對我們重新認識蘇軾于宋詩的價值,以及了解其在清代的接受有很大的幫助,意義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