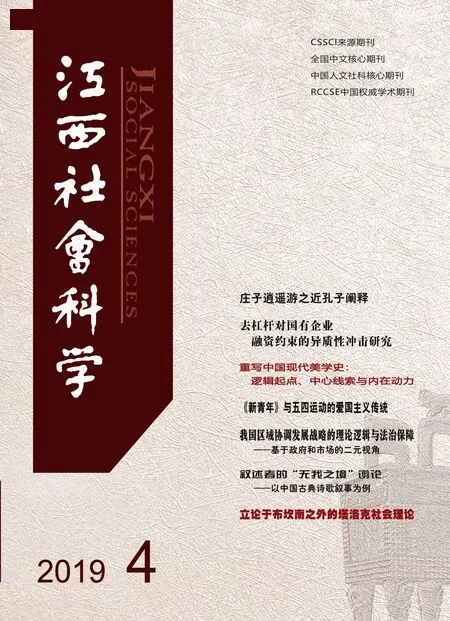《新青年》與五四運(yùn)動(dòng)的愛(ài)國(guó)主義傳統(tǒng)
“解放”是《新青年》的關(guān)鍵詞,也是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精神核心,引導(dǎo)青年從封建專制思想文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lái),為民族強(qiáng)盛、國(guó)家富強(qiáng)而奮斗。晚清以降到新文化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中國(guó)思想文化的變遷演進(jìn)大體可分為四個(gè)時(shí)期:“第一期名之曰船堅(jiān)炮利時(shí)代。第二期名之曰變法維新時(shí)代。第三期名之曰立憲革命時(shí)代。第四期名之曰‘個(gè)人'‘社會(huì)'時(shí)代。”[1]《新青年》以陳獨(dú)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為代表,積極倡導(dǎo)人的解放,選取科學(xué)與民主作為思想武器,把個(gè)人潛意識(shí)中的生命沖動(dòng)和強(qiáng)力引上個(gè)性解放的道路,反抗封建專制思想文化,改造和沖擊封建專制思想文化模式,批判封建綱常禮教,抨擊封建倫理道德,推倒千古偶像,把人從封建專制思想文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lái),用自我存在的“醒過(guò)來(lái)的人”的理念,置換“為君而存在,為道而存在,為父母而存在”的封建專制思想文化觀念,革除自身封建專制思想文化因素,奮發(fā)圖強(qiáng),形成中國(guó)現(xiàn)代史上第一次聲勢(shì)浩大的思想解放運(yùn)動(dòng),所以,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個(gè)人'的發(fā)見(jiàn)。從前的人,是為君而存在,為道而存在,為父母而存在的,現(xiàn)在的人才曉得為自我而存在了”[2](P205)。這種“發(fā)見(jiàn)”奠定“新青年”的“人的解放”的歷史地位。
新青年社團(tuán)透過(guò)《新青年》《新潮》《每周評(píng)論》等媒介與文學(xué)作品,通過(guò)傳播新思潮,喚醒年輕一輩的愛(ài)國(guó)心;還借助俄國(guó)社會(huì)主義革命及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勝利的重大事件影響力,宣傳勞工團(tuán)結(jié)的力量戰(zhàn)無(wú)不勝,高度關(guān)注勞工的群體解放,輸入社會(huì)主義思潮,并發(fā)掘?qū)W生這股崛起的新生力量,從鼓吹人的個(gè)體解放轉(zhuǎn)變?yōu)楹粲趺褡宓慕夥牛讶说慕夥排c社會(huì)變革相結(jié)合,強(qiáng)調(diào)個(gè)人的解放服從民族的解放,激發(fā)學(xué)生的愛(ài)國(guó)激情,推動(dòng)五四運(yùn)動(dòng)的發(fā)生、發(fā)展,并成為一座鮮明的思想里程碑。在此之前,《新青年》致力文學(xué)革命,輸入新思潮,反抗封建專制思想文化,進(jìn)行思想革命,再造新文明,并在五四運(yùn)動(dòng)時(shí)達(dá)到高峰;五四運(yùn)動(dòng)后,各種西方新思潮逐漸退潮,社會(huì)主義思潮成為推崇對(duì)象,并對(duì)中國(guó)社會(huì)產(chǎn)生實(shí)際影響,人的解放服從民族的解放運(yùn)動(dòng),為民族強(qiáng)盛、國(guó)家富強(qiáng)犧牲個(gè)人,奠定五四運(yùn)動(dòng)的愛(ài)國(guó)主義傳統(tǒng),《新青年》與五四運(yùn)動(dòng)因此成為文化/政治符號(hào),成為一種精神的載體。
一
《新青年》輸入西方新思潮,進(jìn)行文學(xué)革命和思想革命,反抗封建專制思想文化,解放人的個(gè)性,影響了中國(guó)現(xiàn)代史發(fā)展的進(jìn)程,成為“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時(shí)代的重要媒體。胡適就說(shuō):“二十五年來(lái),只有三個(gè)雜志可代表三個(gè)時(shí)代,可以說(shuō)是創(chuàng)造了三個(gè)時(shí)代。一是《時(shí)務(wù)報(bào)》,一是《新民叢報(bào)》,一是《新青年》。”并特別突出強(qiáng)調(diào):“《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學(xué)革命與思想革命”[3](P217),破除僵死的封建專制思想文化,造成人的解放高潮,凸顯傳播新思潮對(duì)新青年產(chǎn)生較大影響,推動(dòng)中國(guó)從封建專制思想文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lái),融入世界的歷史發(fā)展進(jìn)程,由此認(rèn)定《新青年》的主題是人的解放,副題才是科學(xué)與民主。
史家認(rèn)定科學(xué)與民主是《新青年》與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主題和旗幟,主要依據(jù)陳獨(dú)秀《本志罪案答辯書》這一段話:“本志同人本來(lái)無(wú)罪,只因?yàn)閾碜o(hù)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hù)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duì)孔教,禮法,貞節(jié),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hù)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duì)舊藝術(shù),舊宗教;要擁護(hù)德先生又要擁護(hù)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duì)國(guó)粹和舊文學(xué)。大家平心細(xì)想,本志除了擁護(hù)德、賽兩先生之外,還有別項(xiàng)罪案沒(méi)有呢?若是沒(méi)有,請(qǐng)你們不用專門非難本志,要有氣力有膽量來(lái)反對(duì)德、賽兩先生,才算是好漢,才算是根本的辦法。”[4]陳獨(dú)秀的這段“答辯”被史家反復(fù)征引,證實(shí)《新青年》的兩大主題是科學(xué)與民主。陳獨(dú)秀咬定,封建專制思想文化與科學(xué)、民主格格不入,追求科學(xué)與民主就必定要反抗封建專制思想文化。《新青年》高舉科學(xué)與民主大旗,必定無(wú)情揭露批判封建專制思想文化,反抗封建倫理道德傳統(tǒng),因此受到維護(hù)封建專制思想文化的舊勢(shì)力的攻擊;反對(duì)《新青年》、攻擊《新青年》實(shí)質(zhì)就是反對(duì)科學(xué)與民主,背離歷史發(fā)展潮流,維護(hù)封建專制思想文化。
晚清以降,追求科學(xué)與民主價(jià)值觀成為主流話語(yǔ),確立了威權(quán)地位,無(wú)人敢公開(kāi)挑戰(zhàn)。1923年,胡適曾總結(jié)道:“這三十年來(lái),有一個(gè)名詞在國(guó)內(nèi)幾乎做到了無(wú)上尊嚴(yán)的地位;無(wú)論懂與不懂的人,無(wú)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duì)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tài)度。那個(gè)名詞就是‘科學(xué)'。”[5](P196)民主在各界人士心中的地位比科學(xué)更重更高。1922年10月,《東方雜志》就強(qiáng)調(diào):“我們所占著的時(shí)間,既然是被科學(xué)精神和民治主義兩大潮流所支配的二十世紀(jì),則我們估定一切言論和智識(shí)的價(jià)值,當(dāng)然以對(duì)于這兩大潮流的面背為標(biāo)準(zhǔn);斷沒(méi)有依違兩可,在時(shí)間軌道上打旋的。”[6]并明確宣布:《東方雜志》衡量一切言論和智識(shí)的價(jià)值標(biāo)準(zhǔn)是科學(xué)與民主。1934年6月,蔡元培總結(jié)中國(guó)的文化運(yùn)動(dòng)演變時(shí),同樣以科學(xué)與民主為“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評(píng)價(jià),認(rèn)為:“直至辛亥革命,思想開(kāi)放,政治上雖不能實(shí)行同盟會(huì)的主張,而孫中山重科學(xué)、擴(kuò)民權(quán)的大義,已漸布潛勢(shì)力于文化上。至《新青年》盛行,五四運(yùn)動(dòng)勃發(fā),而軒然起一大波,其波動(dòng)至今未已。那時(shí)候以文學(xué)革命為出發(fā)點(diǎn),而以科學(xué)及民治為歸宿點(diǎn)(《新青年》中稱為賽先生與德先生,就是英文中Science與Democracy兩字,簡(jiǎn)譯)……我們用這兩種標(biāo)準(zhǔn),來(lái)檢點(diǎn)十余年來(lái)的文化運(yùn)動(dòng),明明合于標(biāo)準(zhǔn)的,知道沒(méi)有錯(cuò)誤。我們以后還是照這方向努力運(yùn)動(dòng),也一定不是錯(cuò)誤。我們可以自信的了。”[7](P422-423)可見(jiàn),陳獨(dú)秀選擇高舉科學(xué)與民主大旗,公開(kāi)叫板“非難”《新青年》的人,等于宣稱:非難“本志”便是反對(duì)科學(xué)與民主。陳獨(dú)秀高舉科學(xué)與民主大旗,為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畫龍點(diǎn)睛,“德、賽兩先生”不僅成為當(dāng)時(shí)的口頭禪,而且成為社會(huì)團(tuán)體、政治勢(shì)力標(biāo)榜文明進(jìn)步的共同的合法的思想依據(jù)及行為指南。
胡適并不認(rèn)同陳獨(dú)秀的《新青年》“兩大‘罪案'”說(shuō)。胡適回憶說(shuō):“陳獨(dú)秀先生為《新青年》所寫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那篇文章的時(shí)候,他說(shuō)《新青年》犯了兩大‘罪案'。第一是擁護(hù)‘賽先生'(science科學(xué)),第二是擁護(hù)‘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可是那時(shí)的陳獨(dú)秀對(duì)‘科學(xué)'和‘民主'的定義卻不甚了了。所以一般人對(duì)這兩個(gè)名詞便也很容易加以曲解。……但是在我看來(lái),‘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習(xí)慣性的行為;‘科學(xué)'則是一種思想和知識(shí)的法則。科學(xué)和民主兩者都牽涉到一種心理狀態(tài)和一種行為的習(xí)慣,一種生活方式。”[8](P355-356)由此可見(jiàn),陳獨(dú)秀與胡適這兩位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主帥對(duì)科學(xué)與民主并沒(méi)有達(dá)成共識(shí)。《新青年》打出科學(xué)與民主旗號(hào),只為批孔非儒,反抗封建專制思想文化,為解放人的個(gè)性提供重要的思想資源。金沖及就認(rèn)為:“《新青年》喊出的最響亮的口號(hào)是‘民主'和‘科學(xué)',那時(shí)又叫作‘德先生'和‘賽先生'。……‘民主'和‘科學(xué)'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民主的對(duì)立物是專制,科學(xué)的對(duì)立物是愚昧和迷信,這正是中國(guó)幾千年封建統(tǒng)治的惡果。”[9](P148)
當(dāng)代學(xué)者解讀“《新青年》上發(fā)表的文章”,也認(rèn)為除科學(xué)與民主大旗外,“《新青年》同人再也找不到‘共同的旗幟'。《新青年》上發(fā)表的文章,涉及眾多的思想流派與社會(huì)問(wèn)題,根本無(wú)法一概而論。以《新青年》的‘專號(hào)'而言,‘易卜生'、‘人口問(wèn)題'與‘馬克思主義研究',除了同是新思潮,很難找到什么內(nèi)在聯(lián)系。作為思想文化雜志,《新青年》視野開(kāi)闊,興趣極為廣泛,討論的課題涉及孔子評(píng)議、歐戰(zhàn)風(fēng)云、女子貞操、羅素哲學(xué)、國(guó)語(yǔ)進(jìn)化、科學(xué)方法、偶像破壞,以及新詩(shī)技巧等。可以說(shuō),舉凡國(guó)人關(guān)注的新知識(shí)、新問(wèn)題,《新青年》同人都試圖給予解答。因此,只有這表明政治態(tài)度而非具體學(xué)術(shù)主張的‘民主'與‘科學(xué)',能夠集合起眾多壯懷激烈的新文化人”[10]。陳獨(dú)秀創(chuàng)辦《青年雜志》是“以編輯為生”,最“直接的原因是緣于生活的無(wú)奈選擇。將雜志命名為《青年雜志》,其良苦用心是確定青年是雜志面對(duì)社會(huì)尋求對(duì)話交流的主要對(duì)象,因?yàn)槊癯醯纳虾2坏侵袊?guó)最繁榮的商埠,也是中國(guó)最具革命意識(shí)的城市。‘近代上海,如果不算租界內(nèi)西方的政治模式所建立的一套管理制度,只就華人而言,通過(guò)地方自治,新聞?shì)浾撟杂傻龋虾H讼硎艿浇裰鳈?quán)利無(wú)疑比中國(guó)其它地方相對(duì)地要多一些'。最向往民主、科學(xué)的又是青年,所以,《青年雜志》確定青年為對(duì)話對(duì)象,把青年學(xué)生作為雜志生存與發(fā)展的根基”[11]。陳獨(dú)秀完全預(yù)想不到《新青年》會(huì)發(fā)起一場(chǎng)“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創(chuàng)造一個(gè)新時(shí)代,自然也就更不可能設(shè)計(jì)一批議題。站在歷史的語(yǔ)境解構(gòu)《新青年》,可以發(fā)現(xiàn)影響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議題,幾乎都是在辦刊過(guò)程中逐漸“尋覓”、“發(fā)掘”和“策劃”出來(lái)的。有些話題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也有些話題沒(méi)有得到反應(yīng)。
當(dāng)代主流史學(xué)更是充分肯定“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基本口號(hào)是所謂‘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學(xué)。當(dāng)封建主義在社會(huì)生活中占據(jù)支配地位的時(shí)候,提倡民主、反對(duì)獨(dú)裁專制,提倡科學(xué)、反對(duì)迷信盲從,有著歷史的進(jìn)步意義。但是,據(jù)這個(gè)口號(hào)的倡導(dǎo)者陳獨(dú)秀的解釋,民主,是指資產(chǎn)階級(jí)的民主制度和資產(chǎn)階級(jí)的民主思想;科學(xué),‘狹義的是指自然科學(xué)而言,廣義是指社會(huì)科學(xué)而言'。他強(qiáng)調(diào)要用自然科學(xué)一樣的科學(xué)精神和科學(xué)方法來(lái)研究社會(huì),可是詹姆士的實(shí)用主義、柏格森的創(chuàng)造進(jìn)化論和羅素的新唯實(shí)主義這類用某些自然科學(xué)成果裝飾起來(lái)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當(dāng)時(shí)在他心目中也被認(rèn)為是科學(xué)。他提倡民主和科學(xué),是為了‘建設(shè)西洋式之新國(guó)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huì)',即建設(shè)資產(chǎn)階級(jí)共和國(guó),發(fā)展資本主義,‘以求適今世之生存'。這表明,初期的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實(shí)質(zhì)上仍是資產(chǎn)階級(jí)的新文化反對(duì)封建階級(jí)的舊文化的斗爭(zhēng)”[12](P7-8)。
但是,立足《新青年》的文本,還原《新青年》的歷史語(yǔ)境,確定科學(xué)與民主為《新青年》和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兩大主題,肯定不能準(zhǔn)確還原《新青年》的“新青年”敘事,更不切合《新青年》的歷史語(yǔ)境。篩選、評(píng)估確定《新青年》主題,必須立足《新青年》文本及歷史語(yǔ)境,從解構(gòu)《新青年》文本入手。
《新青年》包括“通信”、“隨感錄”、編輯部通告等各類文字,總計(jì)發(fā)表各類文章1529篇。其中專門討論“民主”(包括“德謨克拉西”、“德先生”、民本、民治、民權(quán)、人權(quán)、平民主義等)的文章,只有陳獨(dú)秀的《實(shí)行民治的基礎(chǔ)》、屈維它(瞿秋白)的《自民主主義至社會(huì)主義》和羅素的《民主與革命》(張崧年譯)等3篇。涉論“科學(xué)”的文章也不過(guò)五六篇(主要討論科學(xué)精神、科學(xué)方法以及科學(xué)與宗教、人生觀等)。運(yùn)用大數(shù)據(jù)技術(shù)計(jì)量分析《新青年》詞的出現(xiàn)頻度,統(tǒng)計(jì)結(jié)果①顯示:
出現(xiàn)頻度最高的詞是“個(gè)人”,出現(xiàn)在536篇文章中,涉及1690段,總共出現(xiàn)2590次;“個(gè)人主義”出現(xiàn)在49篇文章中,涉及96段,總共出現(xiàn)138次;“個(gè)性”出現(xiàn)在51篇文章中,涉及80段,總共出現(xiàn)117次;“個(gè)人”、“個(gè)人主義”、“個(gè)性”三個(gè)關(guān)鍵詞合起來(lái)統(tǒng)計(jì),總共出現(xiàn)在636篇文章中,涉及1866段,總共出現(xiàn)2845次。
第二名是“自由”,出現(xiàn)在359篇文章中,涉及1146段,總共出現(xiàn)1923次;“自主”出現(xiàn)在53篇文章中,涉及66段,總共出現(xiàn)74次;“自由”、“自主”二個(gè)關(guān)鍵詞合起來(lái)統(tǒng)計(jì),總共出現(xiàn)在412篇文章中,涉及1212段,總共出現(xiàn)1997次。
第三名是“科學(xué)”,出現(xiàn)在384篇文章中,涉及991段,總共出現(xiàn)1907次;“賽先生”出現(xiàn)在3篇文章中,涉及4段,總共出現(xiàn)6次;“賽因斯”出現(xiàn)在2篇文章中,涉及2段,總共出現(xiàn)2次;“科學(xué)”、“賽先生”、“賽因斯”三個(gè)關(guān)鍵詞合起來(lái)統(tǒng)計(jì),總共出現(xiàn)在389篇文章中,涉及997段,總共出現(xiàn)1915次。
第四名是“解放”,出現(xiàn)在162篇文章中,涉及413段,總共出現(xiàn)629次。
第五名是“民主”,出現(xiàn)在65篇文章中,涉及180段,總共出現(xiàn)260次;“德謨克拉西”出現(xiàn)在46篇文章中,涉及121段,總共出現(xiàn)193次;“德莫克拉西”出現(xiàn)在4篇文章中,涉及4段,總共出現(xiàn)4次;“德先生”出現(xiàn)在4篇文章中,涉及6段,總共出現(xiàn)8次;“民主”、“德謨克拉西”、“德莫克拉西”、“德先生”四個(gè)詞合起來(lái)統(tǒng)計(jì),總共出現(xiàn)在119篇文章中,涉及311段,總共出現(xiàn)465次。可見(jiàn),在總字?jǐn)?shù)超過(guò)541萬(wàn)字的《新青年》雜志中,“民主”關(guān)鍵詞的出現(xiàn)頻度并不高。
出現(xiàn)頻度是確定關(guān)鍵詞的主要證據(jù),但結(jié)合文本內(nèi)容也非常重要。《新青年》中雖“個(gè)人”、“個(gè)人主義”、“個(gè)性”三個(gè)詞合起來(lái)統(tǒng)計(jì)出現(xiàn)頻度最高,卻不能確定為關(guān)鍵詞,理由是《新青年》使用這三個(gè)詞,指向都是強(qiáng)調(diào)“個(gè)人”或人的“個(gè)性”獲得解放;“個(gè)人主義”則突出強(qiáng)調(diào)個(gè)人須沖破束縛,解放自己,自由自主地發(fā)展,核心也是個(gè)人獲得解放;因此,我們確定“解放”是《新青年》關(guān)鍵詞,“個(gè)人”“解放”是《新青年》的主題。
確定“解放”是《新青年》關(guān)鍵詞,不僅考慮了其在《新青年》中的出現(xiàn)頻率,最重要的是《新青年》的“解放”目標(biāo)指向非常明確——“解放”“個(gè)人”。“個(gè)人”是“解放”的內(nèi)核,“解放”是“個(gè)人”的形態(tài),所以,“解放”與“個(gè)人”緊密相連,密不可分,因此推定“解放”“個(gè)人”是《新青年》與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主題。殷海光就說(shuō):“中國(guó)早期的自由主義者多數(shù)只能算是‘解放者',自己經(jīng)歷的是解放,向人傳播的也是解放。”[13](P257)
二
“解放”是《新青年》的關(guān)鍵詞,以個(gè)人主義(個(gè)性主義)為思想武器推動(dòng)人的覺(jué)醒、個(gè)人的解放。因此,所謂“新青年”就是從中國(guó)封建倫理道德的專制思想文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lái)的個(gè)人。
漢語(yǔ)的“解放”一詞最早出自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shù)》:“十月中,以蒲蹧裹而纏之;二月初乃解放。”指對(duì)受束縛的物質(zhì)的解開(kāi)、放松。《新青年》的“解放”指解除束縛,得到自由或發(fā)展,反義詞是束縛、奴役、約束。“個(gè)人”的“解放”特指擺脫精神的桎梏,如政治、宗教、文化、倫理等給人的枷鎖,成為思想解放、個(gè)性自由自主發(fā)展的獨(dú)立個(gè)體。
《青年雜志》創(chuàng)刊號(hào)的正文第2頁(yè)就頻繁出現(xiàn)“解放”一詞。陳獨(dú)秀的《敬告青年》是綱領(lǐng)性的文章,主旨就是鼓勵(lì)青年追求個(gè)人的解放。陳獨(dú)秀指出:“近世歐洲歷史為‘解放歷史':破壞君權(quán),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認(rèn)教權(quán),求宗教之解放也;均產(chǎn)說(shuō)興,求經(jīng)濟(jì)之解放也;女子參政運(yùn)動(dòng),求男〔女〕權(quán)之解放也。”開(kāi)宗明義,把歐洲歷史概括為“解放”的歷史,并把“解放”置放于文明進(jìn)步的最高位置,然后才進(jìn)一步具體闡述“解放”。陳獨(dú)秀說(shuō):“解放云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認(rèn)他人之越俎,亦不應(yīng)主我而奴他人:蓋自認(rèn)為獨(dú)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權(quán)利,一切信仰,唯有聽(tīng)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wú)盲從隸屬他人之理。”[14]陳獨(dú)秀突出強(qiáng)調(diào)“解放”就是解除約束,得到充分的自由,獨(dú)立自主地發(fā)展。這種闡釋大大超過(guò)中國(guó)此前所有的思想家,奠定中國(guó)現(xiàn)代思想家理解“解放”的范式。《新青年》這樣“旗幟鮮明地提出以‘個(gè)人'為價(jià)值之源,公開(kāi)宣揚(yáng)個(gè)人本位,由此揭開(kāi)了‘個(gè)人'和‘個(gè)人觀念'以現(xiàn)代性的姿態(tài)在現(xiàn)代中國(guó)出場(chǎng)的大幕。五四前后的個(gè)人觀念,既是對(duì)晚清以來(lái)思想變動(dòng)的承接,又是對(duì)民國(guó)初期中西兩大思想資源的生發(fā)、重構(gòu)和轉(zhuǎn)換。這一階段,‘個(gè)人'無(wú)論作為術(shù)語(yǔ)還是概念,其自身現(xiàn)代意義上的外延、內(nèi)涵和概念要素已齊備;而‘個(gè)人觀念'無(wú)論作為思想陳述還是價(jià)值評(píng)判,其現(xiàn)代性、多元化的觀念形態(tài)得以真正形成”[15]。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中,個(gè)人觀念的變革由于知識(shí)精英的進(jìn)一步推動(dòng),不僅逐步擴(kuò)大了社會(huì)影響,而且其形態(tài)和性質(zhì)也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轉(zhuǎn)化。具體表現(xiàn)為:一方面,個(gè)性解放思潮漸漲漸高,個(gè)性、自我等在五四前后一度成為時(shí)代的流行詞匯;另一方面,明確提出了個(gè)人本位,個(gè)人主義在五四前后一度成為主流的思想傾向。簡(jiǎn)單地說(shuō),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啟蒙作用最突出的一點(diǎn)就是告訴人們:個(gè)人是獨(dú)立的存在,獨(dú)立的自我最有力量”[15]。
陳獨(dú)秀選擇以個(gè)人的解放為突破口闡釋“新青年”思想,不僅具有強(qiáng)烈的戰(zhàn)斗精神,而且一矢中的封建專制思想文化的核心。中國(guó)封建專制思想文化以培養(yǎng)奴隸人格為價(jià)值標(biāo)準(zhǔn),不關(guān)注和重視個(gè)人,認(rèn)為只有融入社會(huì)共同行為的人才具有較高的人格價(jià)值,才能受到社會(huì)的肯定和尊重,從而奉行宗法專制、等級(jí)特權(quán)。統(tǒng)治者既掌政權(quán),又掌教化,左手刑刀,右手教鞭,皇權(quán)主義深入人心,造成一元化的思維,沉淀成一元化的封建專制思想文化、封建倫理道德,美化、神化皇權(quán),以“三綱五常”扼殺人性,禁止獨(dú)立思考,由服從而迷信,由迷信而喪失自我,由自我的喪失導(dǎo)致濃厚的奴隸意識(shí)。陳獨(dú)秀認(rèn)為:“吾國(guó)自古相傳之道德政治,胥反乎是。儒者三綱之說(shuō),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為臣綱,則民于君為附屬品,而無(wú)獨(dú)立自主之人格矣;父為子綱,則子于父為附屬品,而無(wú)獨(dú)立自主之人格矣;夫?yàn)槠蘧V,則妻于夫?yàn)楦綄倨罚鵁o(wú)獨(dú)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為臣,為子,為妻,而不見(jiàn)有一獨(dú)立自主之人者,三綱之說(shuō)為之也。緣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詞——曰忠,曰孝,曰節(jié)——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為以己屬人之奴隸道德也。”[16]陳獨(dú)秀指出,“奴隸的道德”造成“奴隸人格”,極大地滿足統(tǒng)治者“牧民”、治民的心理需求。陳獨(dú)秀因此嚴(yán)厲批判“忠孝節(jié)義,奴隸之道德也;德國(guó)大哲尼采(Nietzsche)別道德為二類:有獨(dú)立心而勇敢者曰貴族道德(Morality of Noble),謙遜而服從者曰奴隸道德(Morality of Slave)。輕刑薄賦,奴隸之幸福也;稱頌功德,奴隸之文章也;拜爵賜第,奴隸之光榮也;豐碑高墓,奴隸之紀(jì)念物也;以其是非榮辱,聽(tīng)命他人,不以自身為本位,則個(gè)人獨(dú)立平等之人格,消滅無(wú)存,其一切善惡行為,勢(shì)不能訴之自身意志而課以功過(guò);謂之奴隸,誰(shuí)曰不宜?立德立功,首當(dāng)辨此”[14]。陳獨(dú)秀以尼采哲學(xué)為準(zhǔn)繩,有力地揭露批判封建專制思想文化的核心就是“奴隸之道德”,受這種“忠孝節(jié)義”的“奴隸道德”思想文化熏陶的中國(guó)人,沒(méi)有“個(gè)人獨(dú)立平等之人格”,奴隸當(dāng)?shù)眯臐M意足。一部中國(guó)歷史,看不到有“獨(dú)立平等之人格”的個(gè)人,只充斥著“奴隸之幸福”、“奴隸之文章”、“奴隸之光榮”、“奴隸之紀(jì)念物”。
個(gè)人的“解放”也是李大釗的重要價(jià)值理念。李大釗認(rèn)為,“解放”就是使人脫離少數(shù)人的專制奴役,伸張人的個(gè)性,反抗壓迫,實(shí)現(xiàn)個(gè)性自由,社會(huì)對(duì)個(gè)人的“壓制之程度愈進(jìn),解放之運(yùn)動(dòng)愈強(qiáng)”,追求“個(gè)人”的“解放”,保證人人獲得自由。李大釗說(shuō):“近世之文明,解放之文明也。近世國(guó)民之運(yùn)動(dòng),解放之運(yùn)動(dòng)也。解放者何?即將多數(shù)各個(gè)之權(quán)利由來(lái)為少數(shù)專制之向心力所吸收、侵蝕、陵壓、束縛者,依離心力以求解脫而伸其個(gè)性復(fù)其自由之謂也。于是對(duì)于專制主義而有民主主義,對(duì)于資本主義而有社會(huì)主義,是皆離心力與向心力相搏戰(zhàn)而生之結(jié)果也。”[17]追求個(gè)人的解放、個(gè)性的自由自主獨(dú)立發(fā)展,不僅成為李大釗最高的人生價(jià)值理想,并且與其生命本質(zhì)緊密結(jié)合,構(gòu)成其思想深處最為深厚的人生理性。李大釗還說(shuō):“西諺有云:‘不自由毋寧死'。夫人莫不惡死而貪生,今為自由故,不惜犧牲其生命以為代價(jià)而購(gòu)求之,是必自由之價(jià)值與生命有同一之貴重,甚或遠(yuǎn)在生命以上。人之于世,不自由而生存可也,生存而不自由不能忍也。試觀人類生活史上之一切努力,罔不為求得自由而始然者。他且莫論,即以吾國(guó)歷次革命而言,先民之努力乃至斷頭流血而亦有所不辭者,亦曰為求自由而已矣。……蓋自由為人類生存必需之要求,無(wú)自由則無(wú)生存之價(jià)值。”[18]按照李大釗的觀點(diǎn),爭(zhēng)取解放就是追求自由,是人類社會(huì)的價(jià)值目標(biāo)。一部人類的文明發(fā)展史,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為爭(zhēng)取解放、獲得自由而進(jìn)行斗爭(zhēng)。
陳獨(dú)秀與李大釗的“解放”思想相通,突出個(gè)人的“解放”,重視個(gè)人的解放、獨(dú)立、個(gè)性自由,“一切操行,一切權(quán)利,一切信仰,唯有聽(tīng)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wú)盲從隸屬他人之理”[14],吹響人的覺(jué)醒和人的解放的革命號(hào)角,強(qiáng)調(diào)青年必須追求個(gè)人的解放,“尊重個(gè)人獨(dú)立自主之人格,勿為他人之附屬品。以一物附屬一物,或以一物附屬一人而為其所有,其物為無(wú)意識(shí)者也。若有意識(shí)之人間,各有其意識(shí),斯各有其獨(dú)立自主之權(quán)。若以一人而附屬一人,即喪其自由自尊之人格,立淪于被征服之女子奴隸捕虜家畜之地位”。所以,“新青年”必須培養(yǎng)個(gè)人的自主意識(shí)和創(chuàng)造精神,堅(jiān)持“人間百行,皆以自我為中心”[16],追求個(gè)人的解放,反抗封建道德文化,認(rèn)清“舊社會(huì)之道德不適今世者,莫如尊上抑下,尊長(zhǎng)抑幼,尊男抑女。舊社會(huì)之所謂不道德者,乃不尊其所尊,抑其所抑者耳,未必有何罪惡可言(如婦人再醮之類)。吾人今日所應(yīng)尊行之真理,即在廢棄此不平等不道德之尊抑,而以個(gè)人人格之自覺(jué)及人之群利害互助之自覺(jué)為新道德,為真道德”[19]。
胡適評(píng)價(jià)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也突出“解放”的主題,強(qiáng)調(diào)新文化運(yùn)動(dòng)追求“這個(gè)那個(gè)人的解放”。胡適提出:文化運(yùn)動(dòng)的唯一目的就是“再造文明”,保證解放風(fēng)俗制度,解放思想文化,解放個(gè)人:
文明不是攏統(tǒng)造成的,是一點(diǎn)一滴的造成的。進(jìn)化不是一晚上攏統(tǒng)進(jìn)化的,是一點(diǎn)一滴的進(jìn)化的。現(xiàn)今的人愛(ài)談“解放與改造”,須知解放不是攏統(tǒng)解放,改造也不是攏統(tǒng)改造。解放是這個(gè)那個(gè)制度的解放,這種那種思想的解放,這個(gè)那個(gè)人的解放,是一點(diǎn)一滴的解放。改造是這個(gè)那個(gè)制度的改造,這種那種思想的改造,這個(gè)那個(gè)人的改造,是一點(diǎn)一滴的改造。[20]
胡適不相信能根本改造社會(huì),更不幻想畢其功于一役建起人間天堂,所以高度警惕各類放之四海而皆準(zhǔn)的真理,一生反對(duì)尋求一攬子解決的主義,而只相信“這個(gè)那個(gè)人的解放,是一點(diǎn)一滴的解放”的漸進(jìn)之路。
因此肯定,“解放”個(gè)人不僅是《新青年》主題,也是《新青年》團(tuán)體的共識(shí),只有個(gè)人獲得“解放”,鑄造獨(dú)立自主的人格,對(duì)社會(huì)有個(gè)人獨(dú)立、有“良知”或“理性”的判斷,國(guó)家才能得救,所以尋找近代中國(guó)前途的關(guān)鍵是個(gè)人的“解放”,“這個(gè)那個(gè)人的解放”,所以,《新青年》高舉“解放”的大旗,目的就是把個(gè)人從封建思想政治文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lái),“求解脫而伸其個(gè)性復(fù)其自由”,“解放”的立足點(diǎn)和出發(fā)點(diǎn)是個(gè)人和個(gè)人主義。胡適認(rèn)為中國(guó)現(xiàn)代思想的發(fā)展演變就以1923年為界:“(一)維多利亞思想時(shí)代,從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側(cè)重個(gè)人的解放。(二)集團(tuán)主義(Collectivism)時(shí)代,一九二三年以后,無(wú)論為民族主義運(yùn)動(dòng),或共產(chǎn)革命運(yùn)動(dòng),皆屬于這個(gè)反個(gè)人主義的傾向。”[21](P257)
陳獨(dú)秀還指出,人的“解放”不要“多在名詞上說(shuō)空話”,而要投入實(shí)際的行動(dòng),就是“道理真實(shí)的名詞”,如果“離開(kāi)實(shí)際運(yùn)動(dòng)”,也就沒(méi)“有什么用處”,所以,個(gè)人不要只高喊“解放”的口號(hào),完全沒(méi)有“解放”個(gè)人的實(shí)際行動(dòng),因?yàn)閭€(gè)人的“解放重在自動(dòng)”:“解放就是壓制底反面,也就是自由底別名。近代歷史完全是解放的歷史,人民對(duì)于君主、貴族,奴隸對(duì)于主子,勞動(dòng)者對(duì)于資本家,女子對(duì)于男子,新思想對(duì)于舊思想,新宗教對(duì)于舊宗教……況且解放重在自動(dòng),不只是被動(dòng)的意思,個(gè)人主觀上有了覺(jué)悟,自己從種種束縛的不正當(dāng)?shù)乃枷搿⒘?xí)慣、迷信中解放出來(lái),不受束縛,不甘壓制,要求客觀上的解放,才能收解放底圓滿效果。自動(dòng)的解放,正是解放底第一義。”[22]
“個(gè)人”的“解放”不僅是《新青年》的主題,而且是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目標(biāo),這正如胡適所說(shuō):“現(xiàn)在有人對(duì)你們說(shuō):‘犧牲你們個(gè)人的自由,去求國(guó)家的自由!'我對(duì)你們說(shuō):‘爭(zhēng)你們個(gè)人的自由,便是為國(guó)家爭(zhēng)自由!爭(zhēng)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guó)家爭(zhēng)人格!自由平等的國(guó)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lái)的!'”[23](P511-512)胡適極為精辟地揭示個(gè)人解放與國(guó)家強(qiáng)盛的密切關(guān)系。只有每一個(gè)人都獲得了“解放”,個(gè)性自由發(fā)展了,爭(zhēng)取到了“個(gè)人的自由”,獲得充分的思想自由,才能“為國(guó)家爭(zhēng)取自由”;每一個(gè)人都具有獨(dú)立的自由個(gè)性,爭(zhēng)得了“自己的人格”,才能“為國(guó)家爭(zhēng)人格”,因?yàn)椤白杂善降鹊膰?guó)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lái)的”。
《新青年》推動(dòng)“解放”“個(gè)人”的思想啟蒙,不僅造成一個(gè)思想解放的《新青年》時(shí)代,成為五四運(yùn)動(dòng)的思想資源,而且培養(yǎng)了具有獨(dú)立的自主個(gè)性、獨(dú)立的思想的“新青年”,為五四運(yùn)動(dòng)儲(chǔ)備了一支特別能戰(zhàn)斗的強(qiáng)大隊(duì)伍。
三
《新青年》北遷北大編輯后,改變?yōu)樾虑嗄晟鐖F(tuán)[24]“公同”刊物[25],輸入新思潮、再造新文明成為其辦刊宗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勝利和俄國(guó)的社會(huì)主義革命,給中國(guó)社會(huì)送來(lái)了兩股新思潮:一是“民族獨(dú)立和自治”;二是社會(huì)主義。受這兩股新思潮的沖擊,新青年社團(tuán)的思想也發(fā)生變化,追求民族獨(dú)立和自治,大力宣傳勞工的群體解放,輸入社會(huì)主義思潮,輔導(dǎo)新青年理解“俄國(guó)式的革命是社會(huì)革命”[26],把追求個(gè)人的解放融入民族的獨(dú)立和自治的解放運(yùn)動(dòng)。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 “使得革命思想遍及殖民地”,“喚起了帝國(guó)主義國(guó)家統(tǒng)治之下的民族的希望,推動(dòng)了民族覺(jué)醒。和平締造者反復(fù)提到民族自決概念,威爾遜公開(kāi)提出在處理殖民地問(wèn)題時(shí),‘考慮歐洲政府意愿的同時(shí),也同樣應(yīng)該考慮當(dāng)?shù)厝说睦?。看起來(lái)威爾遜倡導(dǎo)的正是民族獨(dú)立和自治。民族主義者在組織反帝組織的斗爭(zhēng)中,也從蘇聯(lián)那里尋求鼓舞,蘇聯(lián)領(lǐng)導(dǎo)者譴責(zé)各種形式的帝國(guó)主義,宣稱支持獨(dú)立運(yùn)動(dòng)。總的來(lái)說(shuō),就是反對(duì)帝國(guó)主義的控制”。[27](P1028-1029)這些思潮影響并激發(fā)北京大學(xué)的學(xué)生“反對(duì)帝國(guó)主義的控制”、爭(zhēng)取“民族獨(dú)立和自治”的斗志,向往俄國(guó)社會(huì)主義革命,希望“從蘇聯(lián)那里尋求鼓舞”,實(shí)行“俄國(guó)式的革命”,徹底改變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形態(tài),爭(zhēng)取民族獨(dú)立,實(shí)現(xiàn)民族富強(qiáng)。
1918年11月15日,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勝利的消息傳到中國(guó),各界一片歡騰。政府放假3天,北京萬(wàn)人上街慶賀,舉行一系列慶祝勝利的大會(huì),“學(xué)界舉行提燈。政界舉行祝典”[28]。北京大學(xué)的師生更是歡欣鼓舞。“11月14、15、16日,北大放假三天,為慶祝協(xié)約國(guó)勝利,在天安門外舉行講演大會(huì)”,傾全校之力宣傳。“十天以后,又在中央公園(即現(xiàn)在的中山公園)舉行了連續(xù)三天(28、29、30日)的講演大會(huì)。參加講演的有蔡元培、李大釗、陳獨(dú)秀、陶孟和、陳惺農(nóng)、胡適以及學(xué)生代表江紹原等。講演者大都按照美國(guó)總統(tǒng)威爾遜的調(diào)調(diào),宣傳協(xié)約國(guó)的勝利是什么‘公理戰(zhàn)勝?gòu)?qiáng)權(quán)',是‘正義'、‘平等'、‘互助'的勝利。……惟有李大釗不同凡響,他發(fā)表了題為《庶民的勝利》的著名講演……不是著眼于協(xié)約國(guó)的勝利,而是著眼于俄國(guó)十月革命的勝利,把十月革命看作是第一次大戰(zhàn)產(chǎn)生的一個(gè)重要結(jié)果,這就明顯地反映了他的無(wú)產(chǎn)階級(jí)傾向和對(duì)歷史發(fā)展的深刻洞察力。”[29](P82-83)
北京大學(xué)組織的三天講演大會(huì),雖先后有七人登臺(tái)演講,但《新青年》只選刊了蔡元培、陶孟和、李大釗三人的演講稿,并冠題為“關(guān)于歐戰(zhàn)的演說(shuō)三篇”。蔡元培的演講題目為《勞工神圣》,突出“勞工神圣”,強(qiáng)調(diào)“此后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30]陶孟和的《歐洲以后的政治》提出:“歐戰(zhàn)”勝利警示中國(guó)政治須打破四種觀念:一是秘密的外交、二是背棄法律、三是軍人干政、四是獨(dú)裁政治。這四種東西“在國(guó)內(nèi)要擾亂國(guó)內(nèi)的治安,在國(guó)外要釀起世界的紛爭(zhēng)”。[31]陶孟和雖是針對(duì)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政治現(xiàn)實(shí)紀(jì)念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勝利,論點(diǎn)有一定現(xiàn)實(shí)意義,但終究沒(méi)有獨(dú)特的新見(jiàn)解。
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強(qiáng)調(diào)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不是協(xié)約國(guó)的勝利,不是武力的勝利,也不是一般所謂“公理、正義”的勝利,而是一種新的理想、新的主義、新的制度的勝利,是勞工的勝利。李大釗說(shuō):“這回戰(zhàn)勝的,不是聯(lián)合國(guó)的武力,是世界人類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國(guó)的軍閥或資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們慶祝,不是為那一國(guó)或那一國(guó)的一部分人慶祝,是為全世界的庶民慶祝。不是為打敗德國(guó)人慶祝,是為打敗世界的軍國(guó)主義慶祝。”李大釗演講的最大亮點(diǎn)是揭示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的真正原因,指出:“這回戰(zhàn)爭(zhēng)的真因,乃在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國(guó)家的界限以內(nèi),不能涵容他的生產(chǎn)力,所以資本家的政府想靠著大戰(zhàn),把國(guó)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國(guó)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國(guó),成一個(gè)經(jīng)濟(jì)組織,為自己國(guó)內(nèi)資本家一階級(jí)謀利益。”李大釗用馬克思主義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決定上層建筑的原理闡釋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真因”,并指出戰(zhàn)爭(zhēng)的結(jié)束全賴勞工的覺(jué)悟,協(xié)約國(guó)的勝利完全是庶民的勝利。李大釗沒(méi)有追逐主流輿論話語(yǔ),贊頌協(xié)約國(guó)的勝利,也不就“戰(zhàn)爭(zhēng)”論“戰(zhàn)爭(zhēng)”,而是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放在革命的延長(zhǎng)線上,贊頌“庶民的勝利”,并熱烈歡呼這種“庶民的勝利”,向往“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社會(huì)“變成勞工的世界”,人人都有“變成工人的機(jī)會(huì)”,消滅不勞而獲的剝削階級(jí),并強(qiáng)調(diào)這種“革命”構(gòu)成一種潮流,“這種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每一個(gè)人都“應(yīng)該準(zhǔn)備怎么能適應(yīng)這個(gè)潮流,不可抵抗這個(gè)潮流。人類的歷史,是共同心理表現(xiàn)的記錄。一個(gè)人心的變動(dòng),是全世界人心變動(dòng)的征幾。一個(gè)事件的發(fā)生,是世界風(fēng)云發(fā)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國(guó)革命,是十九世紀(jì)中各國(guó)革命的先聲。一九一七年的俄國(guó)革命,是二十世紀(jì)中世界革命的先聲”。[32]李大釗突出強(qiáng)調(diào),社會(huì)主義思潮將“是二十世紀(jì)中世界革命的先聲”,對(duì)社會(huì)主義充滿必勝的信心。
《庶民的勝利》限于篇幅及演講題旨,沒(méi)有展開(kāi)談俄國(guó)十月革命,李大釗又寫《Bolshevism的勝利》詳細(xì)論述十月革命,明確提出世界大戰(zhàn)的結(jié)局是“人道主義的勝利,是平和思想的勝利,是公理的勝利,是自由的勝利,是民主主義的勝利,是社會(huì)主義的勝利,是Hohenzollern Bolshevism的勝利,是赤旗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jí)的勝利,是廿世紀(jì)新潮流的勝利。……我們對(duì)于這樁世界大變局的慶祝,不該為那一國(guó)那些國(guó)里一部分人慶祝,應(yīng)該為世界人類全體的新曙光慶祝;不該為那一邊的武力把那一邊的武力打倒而慶祝,應(yīng)該為民主主義把帝制打倒,社會(huì)主義把軍國(guó)主義打倒而慶祝”,最后,熱烈歡呼“赤色旗到處翻飛,勞工會(huì)紛紛成立”,高度贊揚(yáng)“俄羅斯式的革命”就“像這般滔滔滾滾的潮流”,“挾雷霆萬(wàn)鈞的力量摧拉”障阻的力量,掃蕩“歷史上殘余的東西,——什么皇帝咧,貴族咧,軍閥咧,官僚咧,軍國(guó)主義咧,資本主義”,徹底改變世界,“由今以后,到處所見(jiàn)的,都是Bolshevism戰(zhàn)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Bolshevism的凱歌的聲”。[28]李大釗激情澎湃,筆力千鈞,充滿堅(jiān)信社會(huì)主義必勝的信念。
李大釗挖掘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俄國(guó)社會(huì)主義勝利的進(jìn)步意義,深刻改寫了中國(guó)人對(duì)“十九世紀(jì)文明”和“二十世紀(jì)文明”的感覺(jué)與把握,把“個(gè)人”“解放”的思想啟蒙運(yùn)動(dòng)推動(dòng)成為民族解放的運(yùn)動(dòng),造成一個(gè)民族、社會(huì)“解放的時(shí)代,現(xiàn)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人民對(duì)于國(guó)家要求解放,地方對(duì)于中央要求解放,殖民地對(duì)于本國(guó)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對(duì)于強(qiáng)大民族要求解放,農(nóng)夫?qū)τ诘刂饕蠼夥牛と藢?duì)于資本家要求解放,女子對(duì)于男子要求解放,子弟對(duì)于親長(zhǎng)要求解放。現(xiàn)代政治或社會(huì)里邊所起的運(yùn)動(dòng),都是解放的運(yùn)動(dòng)”。李大釗熱烈歡迎“解放的時(shí)代”的來(lái)臨,倡導(dǎo)個(gè)人解放緊密相連“大同團(tuán)結(jié)”。李大釗說(shuō):
解放的精神,斷斷不是單為求一個(gè)分裂就算了事,乃是為完成一切個(gè)性脫離了舊絆鎖,重新改造一個(gè)普通廣大的新組織。一方面是個(gè)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團(tuán)結(jié)。這個(gè)性解放的運(yùn)動(dòng),同時(shí)伴著一個(gè)大同團(tuán)結(jié)的運(yùn)動(dòng)。這兩種運(yùn)動(dòng)似乎是相反,實(shí)在是相成。[33]
李大釗強(qiáng)調(diào),個(gè)人的解放并不意味個(gè)人欲望的放蕩不羈,也不意味個(gè)人可以隨心所欲。個(gè)人的解放具有一種內(nèi)在的方向性規(guī)定,衡量標(biāo)準(zhǔn)即是否有利“大同團(tuán)結(jié)”,是否有利于社會(huì)整合。只有與“大同團(tuán)結(jié)”的方向相一致的個(gè)人解放,才是真正的個(gè)人的解放。個(gè)人的解放與“大同團(tuán)結(jié)”的內(nèi)在價(jià)值判斷,“是以適應(yīng)他們生活的必要為標(biāo)準(zhǔn)”。因?yàn)橹粡?qiáng)調(diào)個(gè)性的解放,必將削弱群體的凝聚力,甚至導(dǎo)致群體的渙散;一味強(qiáng)調(diào)“大同團(tuán)結(jié)”,勢(shì)必壓抑束縛個(gè)人的個(gè)性獨(dú)立自主的發(fā)展,甚至導(dǎo)致以群體性替代個(gè)性,破壞人的解放的價(jià)值觀,因此,必須在個(gè)人解放與“大同團(tuán)結(jié)”間尋找一個(gè)合理的契合點(diǎn)。這個(gè)理想狀態(tài)“就是一個(gè)新聯(lián)合”。
李大釗的思想直接影響了北京大學(xué)的學(xué)生,不僅成為五四運(yùn)動(dòng)的思想資源,而且為五四運(yùn)動(dòng)儲(chǔ)備了人才資源。因?yàn)樗麩嵝闹铝π?nèi)校外的社團(tuán)工作,熱心扶助學(xué)生的社團(tuán)活動(dòng),通過(guò)學(xué)生社團(tuán)與學(xué)生親密接觸,在學(xué)生中有相當(dāng)大的影響力。1918年秋,傅斯年、羅家倫、徐彥之等學(xué)生發(fā)起成立新潮社,編輯為傅斯年、羅家倫,李大釗擔(dān)任顧問(wèn)。②《新潮》創(chuàng)刊號(hào)刊發(fā)《今日之世界新潮》稱頌十月革命:“這次的革命是民主戰(zhàn)勝君主主義的革命,是平民戰(zhàn)勝軍閥的革命,是勞動(dòng)者戰(zhàn)勝資本家的革命!總而言之,以前法國(guó)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后俄國(guó)式的革命是社會(huì)革命。”[26]這種論點(diǎn)與李大釗《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觀點(diǎn)、用詞極為相近,受李大釗思想的影響非常明顯。李大釗努力引導(dǎo)《新潮》成員關(guān)注民族解放和獨(dú)立運(yùn)動(dòng)的大趨勢(shì),傳播社會(huì)主義新思潮。顧頡剛回憶說(shuō):“李大釗同志曾給過(guò)《新潮》很多的幫助和指導(dǎo)。他雖不公開(kāi)出面,但經(jīng)常和社員們聯(lián)系,并為《新潮》寫稿。”[34](P125)
李大釗與《國(guó)民》雜志社的關(guān)系最密切。《國(guó)民》編輯為許德珩、陳劍修等,在李大釗指導(dǎo)下,發(fā)表了很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突出強(qiáng)調(diào)反對(duì)日本對(duì)中國(guó)的侵略。李大釗也常在《國(guó)民》發(fā)表文章,尖銳揭露日本侵略中國(guó)陰謀。第五期還發(fā)表了《共產(chǎn)黨宣言》中譯本的前一部分,是中國(guó)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中譯本。許德珩回憶說(shuō):“李大釗是《國(guó)民》雜志社的總顧問(wèn),我們有事都和他商量。”[35](P224)國(guó)民雜志社有成員189名[34](P9-14),培養(yǎng)了一批初步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骨干力量,如北京大學(xué)的學(xué)生鄧中夏、許德珩、高君宇、黃日葵等,都得到李大釗的直接教育和精心培養(yǎng),成為進(jìn)步力量的代表,“在‘五四'運(yùn)動(dòng)中曾起過(guò)中堅(jiān)的作用。該社的負(fù)責(zé)人周長(zhǎng)憲、吳迪恭等,均是北大法律系學(xué)生。周還是《國(guó)民》雜志的主編之一。國(guó)民雜志社的成員遍及北京國(guó)立八校,在北大的會(huì)員尤為眾多”。他們團(tuán)結(jié)在李大釗周圍,成為“一批追求進(jìn)步、立志社會(huì)改革或思想激進(jìn)的青年”[36](P279),對(duì)北京的學(xué)生有很大的影響,大多數(shù)成員在五四運(yùn)動(dòng)中都成為積極的參加者、組織者和領(lǐng)導(dǎo)者。因?yàn)槔畲筢摰挠绊懀逅倪\(yùn)動(dòng)前夕,“《新青年》、《新潮》、《國(guó)民雜志》就開(kāi)始合流,而在文化運(yùn)動(dòng)和救國(guó)運(yùn)動(dòng)之間做媒介的,是李大釗先生”[36](P285)。
1919年5月3日凌晨,蔡元培從汪大燮處獲知,巴黎和會(huì)上中國(guó)外交受挫,德國(guó)是戰(zhàn)敗國(guó),但它在山東的租界的權(quán)益沒(méi)有歸還中國(guó),而是被劃給日本,中國(guó)外交代表團(tuán)將被迫簽約。蔡元培把消息分別告知傅斯年、許德珩等人,北京大學(xué)的學(xué)生群情激憤。北京大學(xué)曾“以歐洲和美國(guó)為楷模、懷有改革中國(guó)理想的年青人和知識(shí)分子殷切地盼望著1919年巴黎和會(huì)會(huì)取得好的結(jié)果。他們希望美國(guó)政府支持取消這些不平等條約,恢復(fù)中國(guó)的完全主權(quán)。然而,當(dāng)這些和平的締造者同意日本繼續(xù)干涉中國(guó)的時(shí)候,這些希望破滅了,這一決定導(dǎo)致了五四運(yùn)動(dòng)的爆發(fā),充當(dāng)先鋒的是中國(guó)城市的學(xué)生和知識(shí)分子”[27](P1065)。這些“充當(dāng)先鋒”的學(xué)生就是《新潮》社和《國(guó)民》社的學(xué)生。3日下午1時(shí),北京大學(xué)“貼出通告,召集本校學(xué)生,于晚間七時(shí),在法科大禮堂開(kāi)會(huì)。是晚參加的北大學(xué)生,有一千多人”。“這個(gè)轉(zhuǎn)變了中國(guó)命運(yùn)的五三晚間大會(huì),是在感情激昂的氣氛中進(jìn)行的。大會(huì)主席易克嶷,湖南長(zhǎng)沙人,為當(dāng)時(shí)《國(guó)民雜志》主干,為理本科化學(xué)門一年級(jí)生。他主持會(huì)議時(shí),態(tài)度沉著,口齒清楚。”學(xué)生們?nèi)呵榧崳白詈蟠髸?huì)決議,通告各校學(xué)生,于明日(即四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大會(huì),會(huì)后游行”[37]。傅斯年是五四游行總指揮,許德珩用文言文起草《北京學(xué)生界宣言》;羅家倫臨時(shí)受命,用白話文撰寫《北京學(xué)界全體宣言》,喊出振聾發(fā)聵的“外爭(zhēng)主權(quán),內(nèi)除國(guó)賊”口號(hào),敲響全民警世鐘:“中國(guó)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guó)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guó)亡了!同胞起來(lái)呀!”這份宣言精悍有力,更具煽動(dòng)性,氣勢(shì)如虹,振奮人心,傳誦至今,“反映了文學(xué)革命的效果,一般人都認(rèn)為它是青年知識(shí)分子的精神最好的表示”[38](P151-152)。《新潮》《國(guó)民》的“主干”發(fā)起和領(lǐng)導(dǎo)五四運(yùn)動(dòng),《新青年》的影響功不可沒(méi)。
由此可知,五四運(yùn)動(dòng)是青年學(xué)生基于愛(ài)國(guó)心理,要求外爭(zhēng)領(lǐng)土主權(quán)、內(nèi)除國(guó)賊而發(fā)起的,是一場(chǎng)純潔的愛(ài)國(guó)運(yùn)動(dòng)。這場(chǎng)“運(yùn)動(dòng)喚醒了這個(gè)國(guó)家,喚起這個(gè)國(guó)家的各個(gè)階層反抗外國(guó)尤其是日本的干涉。運(yùn)動(dòng)的領(lǐng)導(dǎo)者在演講、報(bào)紙和小說(shuō)中發(fā)出誓言,要求擺脫帝國(guó)主義對(duì)中國(guó)的控制,重建國(guó)家的統(tǒng)一”[27](P1065),奠定了五四運(yùn)動(dòng)“是我們的愛(ài)國(guó)運(yùn)動(dòng)”[39]的思想資源及優(yōu)良傳統(tǒng)。
四
新青年社團(tuán)通過(guò)《新青年》《每周評(píng)論》影響、聯(lián)系和團(tuán)結(jié)了進(jìn)步知識(shí)青年讀者,緊密聯(lián)系學(xué)生,引導(dǎo)學(xué)生,發(fā)展革命力量,推動(dòng)了五四運(yùn)動(dòng)的發(fā)生、發(fā)展。李大釗親自組織、指揮學(xué)生運(yùn)動(dòng),胡適、錢玄同參與學(xué)生的游行活動(dòng),胡適還與劉半農(nóng)及傅斯年、羅家倫多次親赴警廳保釋被拘學(xué)生,保護(hù)學(xué)生,支持學(xué)生。陳獨(dú)秀以《每周評(píng)論》為輿論平臺(tái),不僅影響并推動(dòng)學(xué)生參與運(yùn)動(dòng),而且大造輿論聲援五四運(yùn)動(dòng),還親自參加街頭游行抗議活動(dòng),引導(dǎo)運(yùn)動(dòng)的深入發(fā)展,推動(dòng)“民族主義情緒在中國(guó)蔓延”[27](P1065),奠定五四運(yùn)動(dòng)反抗帝國(guó)主義、爭(zhēng)取民族獨(dú)立自主的愛(ài)國(guó)主義傳統(tǒng)。
新青年社團(tuán)是五四運(yùn)動(dòng)的重要推動(dòng)力量,影響著五四運(yùn)動(dòng)的發(fā)生、發(fā)展進(jìn)程。“五四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五四之前,有蔡元培校長(zhǎng)領(lǐng)導(dǎo)之下的北京大學(xué)教授與學(xué)生出版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評(píng)論》所提倡的文學(xué)革命,思想自由,政治民主運(yùn)動(dòng)。五四之后,有全國(guó)知識(shí)青年熱烈參預(yù)的新文藝運(yùn)動(dòng)、新思潮運(yùn)動(dòng),和各種新的政治運(yùn)動(dòng)。”[40]這場(chǎng)運(yùn)動(dòng)因而烙有鮮明的新青年社團(tuán)印記。此外,五四運(yùn)動(dòng)領(lǐng)袖傅斯年、羅家倫都是新青年社團(tuán)重要成員。他倆致胡適的信就說(shuō):“在外人看起來(lái),《新青年》的分子是一體,幾個(gè)人的行動(dòng),還是大家共負(fù)責(zé)任。”[41](P4)
錢玄同親臨五四運(yùn)動(dòng)游行現(xiàn)場(chǎng),并始終陪伴學(xué)生參加游行,是北京大學(xué)為數(shù)極少的幾個(gè)參加五四游行、保護(hù)學(xué)生的教授。5月4日下午,游行學(xué)生前往東交民巷使館區(qū)抗議受阻,憤而轉(zhuǎn)向曹汝霖宅,一路高呼“外爭(zhēng)國(guó)權(quán),內(nèi)懲國(guó)賊”,并發(fā)生“痛毆章宗祥,火燒趙家樓”事件,成為五四運(yùn)動(dòng)的高潮。這一天的學(xué)生大游行,北京大學(xué)的教師“沒(méi)有參加游行,但表示同情,始終陪著學(xué)生走的也有,如錢玄同先生,即其中之一”[42]。錢玄同“始終陪著學(xué)生”,支持學(xué)生,保護(hù)學(xué)生,不僅代表新青年社團(tuán)從只重思想革命走上干涉政治的社會(huì)革命的轉(zhuǎn)變,而且表明“從這一天起,北京大學(xué)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帶著我們都不能脫離政治的努力了”[43]。
北京大學(xué)學(xué)生大游行,蔡元培是重要的推動(dòng)者。游行學(xué)生被捕后,蔡元培積極組織營(yíng)救,保護(hù)學(xué)生。“為了援救被捕學(xué)生,五月五日上午,北大召開(kāi)了學(xué)生大會(huì),蔡元培校長(zhǎng)也出席了。會(huì)上,決定成立統(tǒng)一的北大學(xué)生干事會(huì),決心把斗爭(zhēng)堅(jiān)持下去,進(jìn)一步爭(zhēng)取全市學(xué)生的聯(lián)合行動(dòng)。”隨著運(yùn)動(dòng)的深入持續(xù)發(fā)展,學(xué)生們的行動(dòng)更加過(guò)激,“反動(dòng)政府也著了慌。五月七日,被捕的同學(xué)全部獲釋,但是軍閥政府又提出‘追查肇事學(xué)生、依法懲辦'和‘嚴(yán)禁學(xué)生擾亂社會(huì)秩序'等,進(jìn)一步迫害愛(ài)國(guó)學(xué)生,而對(duì)賣國(guó)賊卻不予懲辦。學(xué)生們繼續(xù)堅(jiān)持斗爭(zhēng),外出講演,罷課抗議”[36](P281-282)。
李大釗是五四運(yùn)動(dòng)直接指揮者。5月1日,李大釗發(fā)表《五一節(jié)May Day雜感》,第一次公開(kāi)提出采取“直接行動(dòng)”[44]進(jìn)行斗爭(zhēng),推動(dòng)群眾的革命行動(dòng)。五四運(yùn)動(dòng)發(fā)生時(shí),雖沒(méi)有親臨五四游行現(xiàn)場(chǎng),但北大圖書館主任室是五四運(yùn)動(dòng)的指揮中心,學(xué)生代表穿梭往來(lái)交流信息,討論每一個(gè)行動(dòng)方案。為擴(kuò)大五四運(yùn)動(dòng)的影響,李大釗建議北大學(xué)生干事會(huì)派黃日葵、許德珩到天津、濟(jì)南、南京、上海等地聯(lián)合學(xué)生運(yùn)動(dòng);派鄧中夏先到長(zhǎng)沙,再到上海;同時(shí)發(fā)動(dòng)北京的學(xué)生堅(jiān)持罷課請(qǐng)?jiān)福ⅰ敖M織了很多露天講演隊(duì),勸國(guó)人買國(guó)貨,宣傳對(duì)日的經(jīng)濟(jì)抵制。全國(guó)各地的學(xué)生也紛紛響應(yīng)”[40],不僅罷課聲援北京學(xué)生,還發(fā)動(dòng)工商界罷工罷市,支持五四運(yùn)動(dòng)。
5月4日,胡適不在北京,而在上海迎接杜威訪華,沒(méi)有親歷五四運(yùn)動(dòng)。5月7日,陳獨(dú)秀致信胡適,通報(bào)4號(hào)當(dāng)天的情況,不僅希望胡適利用其影響力支持五四運(yùn)動(dòng),而且建議胡適為新青年社團(tuán)的“自衛(wèi)記”,必須盡快“想出一個(gè)相當(dāng)?shù)霓k法”。[3](P42)陳獨(dú)秀還運(yùn)用《每周評(píng)論》的輿論影響推導(dǎo)運(yùn)動(dòng)的方向。5月4日,學(xué)生游行時(shí)悲憤激昂的情緒,《每周評(píng)論》做了詳細(xì)報(bào)道,并全文刊登《北京學(xué)界全體宣言》。
胡適雖在滬陪杜威訪華,但高度關(guān)注學(xué)生運(yùn)動(dòng),積極尋機(jī)參加學(xué)生的游行活動(dòng),用實(shí)際行動(dòng)支持學(xué)生,影響運(yùn)動(dòng)的深入發(fā)展。5月7日,上海在公共體育場(chǎng)召開(kāi)國(guó)民大會(huì),支持北京學(xué)生的愛(ài)國(guó)運(yùn)動(dòng)。胡適也擠在與會(huì)人群中,參加學(xué)生游行大會(huì)。他說(shuō):“我要聽(tīng)聽(tīng)上海一班演說(shuō)家,故擠到臺(tái)前,身上已是汗流遍體。我脫下馬褂,聽(tīng)完演說(shuō),跟著大隊(duì)去游街,從西門一直走到大東門,走得我一身衣服從里衣濕透到夾袍子。”[45]
胡適陪同杜威回到北京后,聽(tīng)到數(shù)百學(xué)生被捕的消息,極為震驚,馬上與學(xué)生代表聯(lián)系,全心投入營(yíng)救被捕學(xué)生,保護(hù)學(xué)生,決心與游行學(xué)生共命運(yùn)。5月12日下午,傅斯年“先到文科會(huì)同胡適之、陳百年、沈士遠(yuǎn)、劉半農(nóng)四先生同赴警廳,交涉‘五七'被捕同學(xué)事”[46]。
6月9日,胡適又與劉半農(nóng)、陳大齊、羅家倫等一起到警廳保釋被捕學(xué)生。胡適去探望學(xué)生的路上,看到“北河沿一帶,有陸軍第九師步兵一營(yíng)和第十五團(tuán)駐扎圍守。從東華門直到北大第三院,全是兵士帳棚”[40]。胡適還對(duì)輿論界表示,被拘禁學(xué)生的待遇十分悲慘,缺少被褥和食物,受傷和生病都得不到醫(yī)療。胡適夸大部分事實(shí),故意激發(fā)社會(huì)情緒,激起社會(huì)輿論關(guān)注學(xué)生,支持五四運(yùn)動(dòng)。
陳獨(dú)秀更是大力支持學(xué)生運(yùn)動(dòng),并在《每周評(píng)論》大造輿論,支持、宣傳五四運(yùn)動(dòng),激發(fā)北大學(xué)生的斗志。《每周評(píng)論》連續(xù)出版了第21號(hào)(5月11日)、22號(hào)(18日)、23號(hào)(26日)三期“山東問(wèn)題”特號(hào),激情高漲地談?wù)危M織輿論聲援五四運(yùn)動(dòng),推動(dòng)運(yùn)動(dòng)更加激烈地發(fā)展。陳獨(dú)秀還刊發(fā)評(píng)論,公開(kāi)贊頌學(xué)生的行為是愛(ài)國(guó)行動(dòng)。陳獨(dú)秀說(shuō):
國(guó)民發(fā)揮愛(ài)國(guó)心做政府的后援,這是國(guó)家的最大幸事。我們中國(guó)現(xiàn)在有什么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國(guó)民團(tuán)結(jié)一致的愛(ài)國(guó)心,或者可以喚起列國(guó)的同情幫我們說(shuō)點(diǎn)公道話。人心已死的中國(guó),國(guó)民向來(lái)沒(méi)有團(tuán)結(jié)一致的愛(ài)國(guó)心,這是外國(guó)人頂看不起中國(guó)人的地方,這是中國(guó)頂可傷心的現(xiàn)象。現(xiàn)在可憐只有一部分的學(xué)生團(tuán)體,稍微發(fā)出一點(diǎn)人心還未死盡的一線生機(jī)。僅此一線生機(jī),政府還要將他斬盡殺絕,說(shuō)他們不應(yīng)該干涉政治,把他們送交法庭訊辦。像這樣辦法,是要中國(guó)人心死盡,是要國(guó)民沒(méi)絲毫愛(ài)國(guó)心,是要無(wú)論外國(guó)怎樣欺壓中國(guó),政府外交無(wú)論怎樣失敗,國(guó)民都應(yīng)當(dāng)啞口無(wú)言。[47]
陳獨(dú)秀旗幟鮮明地支持學(xué)生運(yùn)動(dòng),認(rèn)為中國(guó)要“抵抗外人”,必須“全靠”學(xué)生“團(tuán)結(jié)一致的愛(ài)國(guó)心”,愛(ài)國(guó)力量就隱藏在學(xué)生中,而五四運(yùn)動(dòng)就是學(xué)生“做政府的后援,這是國(guó)家的最大幸事”。
5月18日,李大釗公開(kāi)著文指責(zé)北洋政府賣國(guó),號(hào)召推翻軍閥統(tǒng)治:“全因?yàn)楝F(xiàn)在的世界,還是強(qiáng)盜世界。那么不止奪取山東的是我們的仇敵,這強(qiáng)盜世界中的一切強(qiáng)盜團(tuán)體、秘密外交這一類的一切強(qiáng)盜行為,都是我們的仇敵啊!我們?nèi)羰菦](méi)有民族自決、世界改造的精神,把這強(qiáng)盜世界推翻,單是打死幾個(gè)人,開(kāi)幾個(gè)公民大會(huì),也還是沒(méi)有效果。我們的三大信誓是:改造強(qiáng)盜世界,不認(rèn)秘密外交,實(shí)行民族自決。”[48]
5月19日,北京中等以上學(xué)校總罷課,參加學(xué)生達(dá)2.5萬(wàn)余名,提出“和會(huì)不得簽字”,日本歸還山東權(quán)益,“懲辦國(guó)賊”。全國(guó)各地的學(xué)生紛紛響應(yīng),造成全國(guó)學(xué)校罷課。北大學(xué)生還組織講演團(tuán),走出學(xué)校,到“街上演講宣傳,成心讓警察抓去,然后再派更多的學(xué)生出來(lái),使其抓不勝抓,最后好迫使政府無(wú)法善后,而讓步妥協(xié)”[36](P267),造成一場(chǎng)轟轟烈烈的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6月3日,北洋政府開(kāi)始鎮(zhèn)壓學(xué)生運(yùn)動(dòng),抓捕的達(dá)900人之多。陳獨(dú)秀描述這天如此的陰慘黑暗:“民國(guó)八年六月三日,就是端午節(jié)的后一天,離學(xué)生的‘五四'運(yùn)動(dòng)剛滿一個(gè)月,政府里因?yàn)閷W(xué)生團(tuán)又上街演說(shuō),下令派軍警嚴(yán)拿多人。這時(shí)候陡打大雷飐大風(fēng),黑云遮天,灰塵滿目,對(duì)面不見(jiàn)人,是何等陰慘暗淡!”[49]陳獨(dú)秀之所以強(qiáng)調(diào)6月3日“陡打大雷飐大風(fēng),黑云遮天”,全因?yàn)檫@天逮捕的學(xué)生是以街頭演說(shuō)、抗議示威、罷課等罪名,也就是言論罪、思想罪、表達(dá)罪、行使憲法權(quán)利罪等罪名抓捕學(xué)生,造成中華民國(guó)有史以來(lái)最黑暗最恐怖的一天。
6月3-4日兩天,北京逾千名學(xué)生被捕,引起陳獨(dú)秀的高度關(guān)切。6月8日,陳獨(dú)秀發(fā)表《研究室與監(jiān)獄》,鼓勵(lì)學(xué)生。陳獨(dú)秀說(shuō):“世界文明發(fā)源地有二:一是科學(xué)研究室,一是監(jiān)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了監(jiān)獄,出了監(jiān)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yōu)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fā)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jià)值的文明。”[50]字里行間洋溢著戰(zhàn)斗的激情和革命樂(lè)觀主義的精神,對(duì)學(xué)生是極大的贊揚(yáng)和支持。
陳獨(dú)秀不僅以《每周評(píng)論》為輿論陣地,推動(dòng)五四運(yùn)動(dòng)發(fā)展,運(yùn)動(dòng)高昂的政治激情也促使他更加激進(jìn),在社會(huì)革命的路上奮勇前進(jìn)。陳獨(dú)秀“的性情一貫地急躁,反對(duì)北洋軍閥尤其激烈。有一天,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③,大約有十幾條。交由胡適,把它譯成英文”[51](P61)。6月11日,他親自去散發(fā)《北京市民宣言》。“1919年6月12日,陳獨(dú)秀[終因政治活動(dòng)]被捕入獄。陳氏是在發(fā)散他那自撰并出資自印的反政府傳單之時(shí)被捕的。”[8](P353)陳獨(dú)秀是看到五四運(yùn)動(dòng)進(jìn)入膠著狀態(tài),需要有人犧牲才能推動(dòng)運(yùn)動(dòng)進(jìn)一步深入發(fā)展時(shí),他決心犧牲自己,達(dá)到喚醒民眾的目的。陳獨(dú)秀認(rèn)為:“五四運(yùn)動(dòng)的結(jié)果,還不甚好。為什么呢?因?yàn)闋奚《Y(jié)果大,不是一種好現(xiàn)象。”[52]
13日,北京《晨報(bào)》首先披露陳獨(dú)秀被捕的消息,全國(guó)各地報(bào)紙都相繼報(bào)道,輿論界震驚,各省各界紛紛為陳獨(dú)秀辯白,引起全國(guó)各界人士的關(guān)注,吁請(qǐng)政府當(dāng)局立予開(kāi)釋。北京大學(xué)守舊派教授也奔走營(yíng)救陳獨(dú)秀。“劉師培聯(lián)合北京大學(xué)、民國(guó)大學(xué)、中國(guó)大學(xué)馬裕藻、馬敘倫、程演生、王星拱、馬寅初等數(shù)十位教授,領(lǐng)銜致函京師警察廳,要求保釋陳獨(dú)秀。”[53](P274-275)陳獨(dú)秀在《北京市民宣言》中提出的政治目標(biāo),受到廣泛支持。
五四運(yùn)動(dòng)因有陳獨(dú)秀和逾千名學(xué)生被捕,激發(fā)全國(guó)各界的強(qiáng)烈抗議,支持五四運(yùn)動(dòng),反抗政府壓迫,政府面臨巨大的政治壓力,陷入嚴(yán)重的政治危機(jī)。6月28日,北洋政府拒簽《巴黎和約》,并在此前罷免了曹汝霖、陸宗輿和章宗祥的官職。五四運(yùn)動(dòng)取得勝利,陳獨(dú)秀的政治聲譽(yù)也空前高漲。
總之,五四運(yùn)動(dòng)深受新青年社團(tuán)的影響,反過(guò)來(lái)又推動(dòng)《新青年》“干涉政治”,造成《新青年》色彩逐漸變紅、變得更加激進(jìn),終于發(fā)展成為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的黨刊。歷時(shí)近兩個(gè)月的五四運(yùn)動(dòng)“轟動(dòng)了全國(guó)的青年,解放了全國(guó)青年的思想,把白話文變成了全國(guó)青年達(dá)意的新工具,使多數(shù)青年感覺(jué)用文字來(lái)自由發(fā)表思想感情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不是極少數(shù)古文家專利的事,經(jīng)過(guò)了這次轟動(dòng)了全國(guó)青年的大解放”[40],不僅為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做了總結(jié),也為創(chuàng)建中國(guó)共產(chǎn)黨準(zhǔn)備了思想資源及人才隊(duì)伍,成為20世紀(jì)深厚的愛(ài)國(guó)主義思想遺產(chǎn),拉開(kāi)中國(guó)長(zhǎng)達(dá)半個(gè)世紀(jì)的社會(huì)革命運(yùn)動(dòng)。《新青年》與五四運(yùn)動(dòng)因此成為一種文化/政治符號(hào),成為中國(guó)各階級(jí)都可以接受的一種精神載體,奠定其愛(ài)國(guó)主義傳統(tǒng)。
注釋:
①此數(shù)據(jù)根據(jù)北京大學(xué)未名科技文化發(fā)展公司、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青年》光盤檢索統(tǒng)計(jì)。
②《新潮》創(chuàng)刊號(hào)刊發(fā)《啟事》:“本部敬請(qǐng)圖書館主任、庶務(wù)處主任為顧問(wèn),所有本志印刷、登廣告、發(fā)行及其他銀錢出入事項(xiàng),即由兩主任分派出版部雜務(wù)課、會(huì)計(jì)課事務(wù)員執(zhí)行之。”(《北京大學(xué)日刊》1918年12月3日。)《啟事》所說(shuō)的“圖書館主任”就是李大釗。
③《北京市民宣言》(1919年6月9日)印刷成一張A4紙的篇幅,上半為漢文,下半為英文,全文如下:“中華民族乃酷愛(ài)和平之民族。今雖備受內(nèi)外不可忍受之壓迫,仍本斯旨,對(duì)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1)對(duì)日外交,不拋棄山東省經(jīng)濟(jì)上之權(quán)利,并取消民國(guó)四年、七年兩次密約。(2)免除徐樹(shù)錚、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段芝貴、王懷慶六人官職,并驅(qū)逐出京。(3)取消步軍統(tǒng)領(lǐng)及警備司令兩機(jī)關(guān)。(4)北京保安隊(duì)改由市民組織。(5)市民須有絕對(duì)集會(huì)言論自由權(quán)。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達(dá)此目的。倘政府不顧和平,不完全聽(tīng)從市民之希望,我等學(xué)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dòng),以圖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內(nèi)外士女諒解斯旨(各處接到此宣言,希即復(fù)印傳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