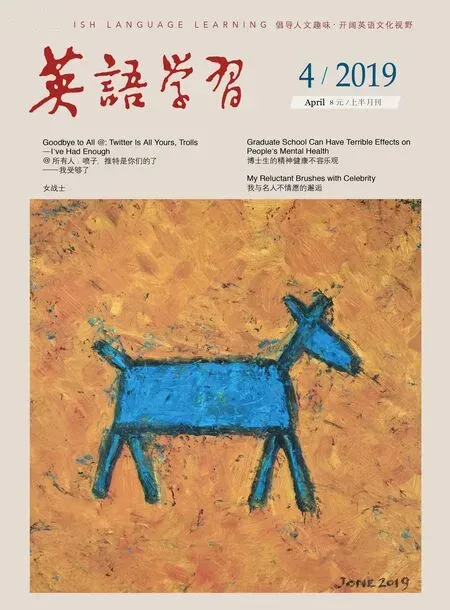閱讀感評
∷秋葉 評
二十年前,我成為了一所著名大學的博士生。經過整整六年的寒窗苦讀和導師的苛求與批評(我的專業就是文學批評,但對于施加在自己頭上的過多的批評,回想起來還是有些灰心喪氣),雖然勉強抵達了終點,可謂浴火重生,但攻讀博士之路就像游子漂泊在外,急于要找回自我的歸鄉之路。這六年生涯,恰如費翔在《故鄉的云》中所唱的,“踏著沉重的腳步,歸鄉路是那么的漫長/我已是滿懷疲憊,眼里是酸楚的淚/我曾經豪情萬丈,歸來卻空空的行囊!”我后來知道,讀博經歷成為人生永遠之痛的,實在是不乏其例。與我同系同專業的一位學長,在讀博期間罹患不治之癥,完成論文并答辯通過后,人生也走到了終點。我還認識一位已屆中年的女博士生,在原單位已晉身為教授職銜,但在讀期間與導師不和,論文遲遲得不到實質性指導,無法提交答辯,后患上狂躁抑郁癥,與導師溝通中數次采取極端手段,最終被開除學籍,遣返回家。
從原文里的調查數據來看,美國博士生的精神狀況應該要更為嚴重。據稱,在美國八所精英大學的約500名經濟學博士生中,18%有焦慮與抑郁癥狀,是社會平均值的三倍以上。另外,在哈佛大學的博士生中,有十分之一的人在過去的半個月中有過自殺的想法,而且半數是在入學后才出現此精神健康危機的。美國博士生在此方面與中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顯然與他們在學業與經濟上所承受的更為沉重的負擔有關。在學制上,我國博士培養期限一般為3—6年,而在美國要長達7—12年,同時,在各個環節的把關上,我們往往有著更多的人情照顧因素,而他們卻更為嚴格,只認事不認人。這也就是為什么美國博士生真正畢業的不足入學數量的一半,而在我國這種情況則比較罕見。在中國,一位學生不間斷地從小學入學直至博士畢業,通常要歷經寒窗二十多載,風雨后見彩虹之時已近而立之年,而在美國,更是早已步入中年了。王國維提出做學問有三種境界,依次為:“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前面兩種境界,相信絕大部分的博士生們都經歷了,但“驀然回首”時,等待他們的卻往往并不美妙。近幾年來在中國,這些所謂“最強大腦”畢業生(super-smart graduates)要在高校與研究機構謀得體制內的教職與研究職位,難度已越來越大。即便謀得一個較為理想的職業,待遇也很有限,生活會相當清苦,在城市里要成立家庭、安居樂業實為不易,而他們的本科或碩士階段的同學恐怕早已有房有車有家庭了,他們之間的差別就是“讀還是不讀博士”。“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這句前幾年在我們社會上流行的話真是對他們的很好概括!而在美國,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投入與產出更是倒掛嚴重。
在美國,大部分博士生靠獎學金,靠當助教或助研以及申請學生貸款來支付學費與生活費,甚至有的還需動用家庭、個人甚至配偶的存款。有調查發現,大約13%的美國博士生畢業時,其累積的助學貸款高達七萬多美元,文科學生更是加倍。然而更糟的是,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在畢業時債臺高筑,卻工作無著。一個2014年的調查顯示,美國博士畢業生中無法找到固定職業的已占到40%左右。高期望與低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往往深深地刺痛了他們的內心,更讓他們感覺無法向家人、配偶甚至多年苦讀的自我有個完滿的交代。有美國朋友告訴我,在這些年,你如果冒昧地問一位臨近畢業的博士生是否找到了工作,得到的回應很有可能是其“驟然爆發的類似恐慌的癥狀(instant panic-like symptoms)”。在動物界,達爾文已概括出“survival of the fi ttest(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但愿在高度文明的人類學術界,為求生存與發展,不至于如此殘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