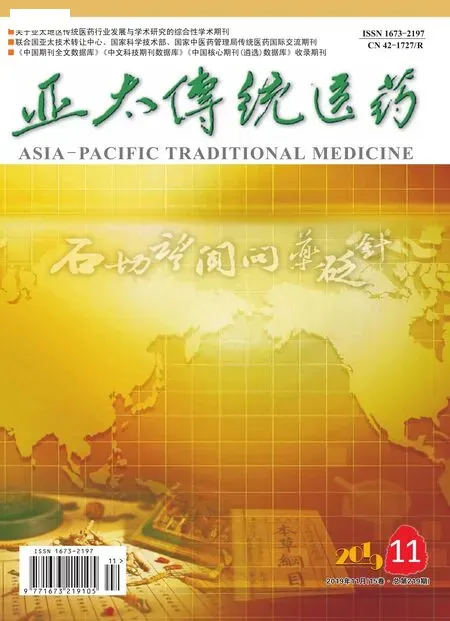“熱證可灸”的思想發展及現代研究
沈翠翠
(無錫市第二人民醫院,江蘇 無錫 214000)
灸法是借灸火的熱力給人體以溫熱性刺激,通過經絡腧穴的作用,以達到治病、防病目的的一種治療方法[1]。《本草從新》云:“艾葉苦辛……純陽之性,能回垂絕之陽。”艾葉性溫,因此利用灸火的溫熱作用可以起到通經活絡、去除陰寒、回陽救逆等多方面的作用。然而,對于艾灸是否可以用于治療熱證,一直存在爭議,也使得灸治熱證的臨床運用困惑重重。本文擬對古代文獻及現代研究兩方面對“熱證可灸”的歷史源流作梳理,以說明之。
1 秦漢《內經》及《傷寒論》對灸治熱證的論述
1.1 《內經》未明確指出熱證禁灸
熱證不用灸法的記載最早見于《靈樞·始終》篇:“人迎與脈口俱盛三倍以上,命曰陰陽俱溢,如是者,不開則血脈閉塞,氣無所行,流淫于中,五臟內傷,如是者,因而灸之,則變異而為他病矣。”脈盛而灸之,非但無效,反而促使疾病產生變異,是以為灸不可為。脈盛常見于熱證,故作為“熱證忌灸”的淵源。
然而,通考《內經》全文,不僅無“發熱不能用灸”的條文與字樣,而且特別重要的是有“熱病二十九灸”之說[2]。《素問·骨空論》曰:“灸寒熱之法,先灸項大椎,以年為壯數,次灸撅骨(尾窮)以年為壯數,視背俞陷者灸之,舉臂肩上陷者(肩髃)灸之,兩季脅之間(京門)灸之,外踝上絕骨之端(陽輔)灸之。足小趾次趾間(俠溪)灸之,踹下陷脈(承筋)灸之,外踝后(昆侖)灸之,缺盆骨上切之堅痛如筋者灸之,膺中陷骨(天突)灸之,掌束骨下(陽池)灸之,臍下關元三寸灸之,毛際動脈(氣沖)灸之,膝下三寸分間(三里)灸之,足陽明跗上動脈(沖陽)灸之,巔上一(百會)灸之,犬所嚙處灸三壯,凡當灸二十九處。”現代臨床上利用熏灸大椎為主治療流行性出血熱也取得了很好的療效,這說明艾灸對病毒感染性疾病有一定的治療意義,并可否定“熱證忌灸”之說。
此外,《靈樞·壽夭剛柔第六》云:“黃帝曰:刺寒痹內熱奈何?伯高答曰:刺布衣者,以火焠之;刺大人者,以藥熏之。”營衛寒痹,寒極生熱,根據腠理疏密采用的火療法,滲透了“火郁發之”的治療思想,這說明艾灸等火療方法對寒邪入里化熱有一定的治療意義。
1.2 《傷寒論》中“火逆”“火害”的重新思考
《傷寒論》中關于“火逆”和“火害”的敘述成為后世認為“熱證忌灸”的主要根源。仔細觀之,書中所言火逆及火害有其禁忌證,如《辨太陽病脈并治》中云:“微數之脈,慎不可灸。因火為邪,則為煩逆,追虛逐實,血散脈中,火氣雖微,焦骨傷筋,血難復也。”此外,如果聯系張仲景的生活背景,東漢末年,戰爭不斷,利用直接灸、化膿灸、瘢痕灸等治療方法,灸創難愈,反復感染化膿,預后多不良甚至死亡;同時,張仲景一方面在告誡人們要注意火逆,一方面自己也是時有應用[3]。如在太陽病脈癥中云:“太陽病二日,反躁,凡熨其背而大汗出,火熱入胃,胃中水竭,煩躁,必發譫語,十余日振栗自下利者,此為欲解也。”此外,張仲景十分重視灸法的發汗效果,如《辨太陽病脈并治中》云:“太陽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經不解,必清血,名為火邪。”灸本可發汗,但由于對灸的量及時間把握不當,本為“發汗之火”卻反變為新的治病因素,仲景也是借此說明灸應適當。
此外,縱觀《傷寒論》,論及灸法5處,熏法4處,熨法2處,燒針4處,溫針5處,對熱證并非專忌灸。因此,在臨床中,我們要客觀地看待《傷寒論》中火逆證與禁灸法,不可拘泥于“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的條文,吸取古書中灸法經驗,認真辨別與密切關注患者在施灸過程中的反應,提高患者對艾灸的接受度,使灸法發揮更大的臨床治療作用[4]。
2 唐·孫思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明確提出熱證可灸
孫思邈集唐代以前灸法作用,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明確提出了“熱證可灸”,并且將灸法的應用擴大到急證、癰疽瘡瘍,對臨床應用作出了重要貢獻。其中,灸法用于實熱證最多,如《備急千金要方·卷六》中提到:“自有肝中有風熱,令人眼昏暗者,當灸肝俞……風癢赤痛,灸人中近鼻柱二壯,仰臥灸之。”《備急千金要方·卷十八》云:“腸中臚脹不消,灸大腸俞四十九壯。大腸有熱,腸鳴腹滿,挾臍痛,食不化,喘,不能久立,巨虛上廉主之。”這說明,艾灸有一定的抗炎抗過敏作用,并且能夠提高機體免疫力。
此外,書中對于虛熱證及濕熱證也有論述,前者如《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一》中云:“消渴,口干不可忍者,灸小腸俞百壯,橫三間寸灸之”,為治療陰虛有熱。后者如《備急千金要方·卷十》中云:“巨闕穴,在心下一寸,灸七壯,治馬黃、黃疸、急疫等病”,這是治療濕熱黃疸。
3 宋金元對熱證可灸的繼承
宋·王執中《針灸資生經》所治熱證也不少,如實熱證有臟腑之熱、濕熱發黃、熱毒瘡瘍等。如治療“五臟熱及身體熱”“熱陽風”“三焦、膀胱、腎中熱氣”“熱毒風盛,眼睛痛”“忽兩眼大小眥俱赤”“小兒口有瘡蝕,眼爛臭穢沖人”“腦熱疼”“黃疸”等病證皆用灸法。其灸治熱毒瘡瘍包括“發背”“疔瘡”“乳癰”“乳腫痛”等。虛熱證用灸者有“勞瘵”“骨蒸”等[5]。書中所提及對于一些熱證仍需慎灸,但也并未說對于熱證要禁灸。
金元四大之一的朱丹溪作為滋陰派的創始人,不僅提出灸法有補火和瀉火之分,更進一步完善了熱證可灸的理論依據,提倡在臨床中將灸法運用于熱證治療[6]。對于實熱證,他認為當取艾灸的火熱之性以火郁發之,從陽引陽;對于虛熱證,艾灸的目的則在于通過陽生陰長而益氣生津。
4 明清時期灸法的發展
明代針灸學家楊繼洲在其家傳《衛生針灸玄機密要》的基礎上,匯集諸家針灸資料編成《針灸大成》,其中對灸法應用于熱證的論述也頗多。如對實熱證,云:“赤痢,灸小腸俞”“灸寒熱之法,先灸大椎”。《針灸大成·諸家得失策》云:“夫何喜怒哀樂心思嗜欲之淚于中,寒暑風雨溫涼燥濕之侵于外,于是有疾在膜理者焉,有疾在血脈者焉,有疾在胃腸者焉。然而疾在胃腸,非藥餌不能以濟;在血脈,非針刺不能以及;在腠理,非熨焫不能以達。”這里的熨焫運用在腠理,是針對“寒暑風雨溫涼燥濕”之邪,并未說不可用于熱證,由此看來,楊繼洲也不反對灸法在熱證上的應用。醫家汪機則在《針灸問對》及《外科理例》中提出“熱證可灸”,艾灸對瘡瘍等熱證具有托里消毒的作用,促進瘡瘍的愈合,但在施灸前強調需要對患者進行辨證分型,掌握好施灸的時間及刺激量[7]。
5 熱證可灸的現代研究
現代研究表明,灸法通過灸瘡的應激反應、輕微創傷所致的疼痛刺激及熱輻射刺激三個方面的作用從而達到退熱的作用[8]。艾灸的鎮痛及抗炎效應在實驗及臨床中已經得到證實,有學者提出用“艾灸嘌呤”這一概念總結了艾灸通過對體表穴位的溫熱刺激,在各種致痛/鎮痛、促炎/抗炎因子及各種信號通路效應器的作用下而產生抗炎鎮痛的效應[9]。唐照亮等[10]復制了急、慢性炎癥及細菌和病毒感染等5種大鼠熱證表現的模型,通過艾灸腎俞穴,結果發現,在福氏完全佐劑建立的大鼠佐劑性關節炎模型中,艾灸能有效抑制諸如TNF、IL-1等炎癥細胞因子的釋放,尤其是針對中后期炎癥效果明顯;艾灸腎俞可以減輕NO的過量產生和釋放,糾正NO的自由基損傷和毒性作用,同時還能夠提升SOD活性;灸治能夠降低大鼠胸腺細胞凋亡率、抑制其細胞凋亡,從而增強或調整機體的免疫功能;此外,艾灸還可通過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上調NE、5-HT腦內含量,降低NO水平,影響中樞神經遞質的釋放,促進內環境的穩定。艾灸可調整和增強機體的免疫功能,并可顯著提高白細胞數。臨床方面,潘伯驍等[11]對頑固性瘡瘍患者皮損局部及鄰近部位進行拔罐及艾灸治療,其臨床總有效率(85.0%)顯著高于常規清創處理(59.3%)。吳敏等[12]對比了常規換藥、象皮生肌膏及象皮生肌膏聯合艾灸對Ш期壓瘡(氣滯血瘀證)合并糖尿病患者壓瘡的臨床療效,對比第7、14、21天3組愈合率,結果象皮生肌膏聯合艾灸及常規換藥創面愈合率均高于單純象皮生肌膏,且象皮生肌膏聯合艾灸耗材費用較低,更適于推廣。石江龍等[13]記錄了艾灸治療急性踝扭傷案例一則,懸灸局部青紫腫脹處及局部穴位,每日艾灸1~2次,每次20~30 min,治療1周后腫脹基本消除,關節活動基本恢復正常。
6 結語
綜上所述,通過對古代文獻的推敲以及現代研究的發現,與現代艾灸療法相比,古代艾灸的概念應當更加廣泛,主要體現在:①操作方式多樣:包括艾灸、藥熨、燒針、火熏等;②刺激強度較大:如《備急千金要方》云:“腸中臚脹不消,灸大腸俞四十九壯”“消渴,口干不可忍者,灸小腸俞百壯,橫三間寸灸之”等;③適應證廣泛:包括癰疽、狂犬咬傷、黃疸等感染、傳染性疾病。現代研究也支持艾灸對急、慢性炎癥及細菌病毒感染疾病的治療作用。當然,這并不說明灸法就可用于一切熱證,其作為中醫的一種特色療法,是與中醫的辨證思想體系一脈相承的,所以對于灸法的臨床,仍然需要在辨證與辨病的基礎上使灸法作用的發揮達到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