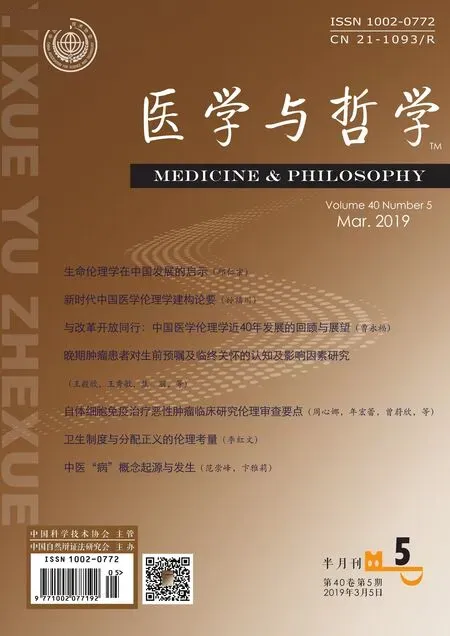現(xiàn)象學(xué)視角下的方證知識(shí)顯現(xiàn)*
鄧 燁
①中山大學(xué)哲學(xué)系 廣東廣州 510275
《傷寒論》中的方證知識(shí),將“辨證”和“論治”結(jié)合在了一起。某某湯證,一詞兩意:其既是證的名稱,也是方的名稱,兩者可以稱為并列關(guān)系[1];當(dāng)我們辨出是什么證的時(shí)候,方藥也就可以跟著寫出來了。這里會(huì)引發(fā)出一個(gè)問題:張仲景及后世的諸多名醫(yī)(后文統(tǒng)稱為“醫(yī)者”),他們運(yùn)用方證知識(shí)來診療患者時(shí),其瞬間的思維意識(shí)是如何運(yùn)作的呢?當(dāng)然,我們并非要研究意識(shí)的物質(zhì)基礎(chǔ)和生物傳導(dǎo)反應(yīng),我們只想了解,從意識(shí)的顯現(xiàn)結(jié)構(gòu)層面,醫(yī)者業(yè)已掌握的方證知識(shí)是如何在實(shí)際臨床中顯現(xiàn)給自我的。為解答這一問題,筆者對(duì)現(xiàn)象學(xué)哲學(xué)做了進(jìn)一步的學(xué)習(xí)和研究。本文即嘗試運(yùn)用胡塞爾學(xué)術(shù)生涯后期“發(fā)生現(xiàn)象學(xué)”的一些方法和結(jié)論,對(duì)此問題進(jìn)行探討。
在具體闡述前有三個(gè)前提:首先,自然態(tài)度下客觀世界的“身體”不是筆者討論的對(duì)象;哲學(xué)(現(xiàn)象學(xué))所關(guān)注的純粹邏輯是普遍的、絕對(duì)的,完全獨(dú)立在具體心理事實(shí)上的。其次,筆者根據(jù)現(xiàn)象學(xué)“無前設(shè)原則”、“面向事實(shí)本身”的原則,把既往預(yù)設(shè)的所有科學(xué)理論和成果排除掉。最后,筆者討論的東西都是可以對(duì)其“本質(zhì)”進(jìn)行純粹直觀把握的——經(jīng)過還原和排除,直觀行為以及在直觀行為中的被給予物,會(huì)被明見地直觀到[2]。
為了方便闡述,筆者根據(jù)《傷寒論》的原文,虛擬一位患者就診的場景:患者進(jìn)入診室,頭頸有汗,穿衣較常人多,本能地躲避空調(diào)或風(fēng)扇的直吹;患者說自己頭痛、身體有發(fā)熱,并且怕風(fēng)。醫(yī)者四診合參后,開了桂枝湯。這一患者的癥狀體征表現(xiàn),屬于典型的太陽病桂枝湯證:“太陽病,頭痛,發(fā)熱,汗出,惡風(fēng),桂枝湯主之。”[3]醫(yī)者如果學(xué)過《傷寒論》,可以快速開出桂枝湯的方藥;即便醫(yī)者沒有學(xué)過《傷寒論》,他也可以就“惡寒發(fā)熱”這一癥候診斷出寒證,根據(jù)“自汗”這一體征診斷出表虛證……最后,根據(jù)中藥四氣五味藥性特征,也可以自擬出類似桂枝湯這樣辛溫發(fā)散、益氣解表的方藥。
通過理性分析、運(yùn)用中醫(yī)理法推演出方藥是常規(guī)的診療和教學(xué)過程,這一過程完全可以通過歸納總結(jié)、理論演繹、邏輯推理甚至人工智能實(shí)現(xiàn)——這些不是本文討論的領(lǐng)域。因?yàn)樵诂F(xiàn)實(shí)中,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有些名醫(yī)在長久的臨床經(jīng)驗(yàn)積累后,已經(jīng)具備了“望而知之”、瞬間開方的水平(如臺(tái)灣已故中醫(yī)張步桃可日診七百人),他們顯然沒有花時(shí)間在診療時(shí)進(jìn)行推演,或者說,他們推演的過程太過迅速以至于超越了常規(guī)理性需要思考的時(shí)間。這些“望而知之”、“脈而知之”的醫(yī)者,他們?cè)谙露ㄔ\斷結(jié)論、確定診療方法的瞬間,其思維意識(shí)的過程,即是本文研究的重點(diǎn)。
1 癥候直觀的被動(dòng)發(fā)生
胡塞爾把意識(shí)的發(fā)生劃分為主動(dòng)的構(gòu)成(主動(dòng)發(fā)生)和被動(dòng)的發(fā)生。在《笛卡爾式的沉思》中,他把主動(dòng)發(fā)生界定為:自我的行為是生產(chǎn)性的[4]105。具體來說,生產(chǎn)性的行為是在預(yù)先被給予的對(duì)象基礎(chǔ)上,原初地構(gòu)造出來新的對(duì)象。例如,我們對(duì)“虛”的概念意識(shí),是在“自汗”這一信息對(duì)象的基礎(chǔ)上構(gòu)造出來的。那么醫(yī)者獲取的“自汗”這一癥候本身的意識(shí),是主動(dòng)發(fā)生的嗎?
胡塞爾[4]107通過還原的實(shí)施,逐步揭示了意識(shí)被動(dòng)發(fā)生的領(lǐng)域,他認(rèn)為“生活中作為此在著的簡單物……在對(duì)被動(dòng)經(jīng)驗(yàn)的綜合中被給予的。作為這種東西,它被預(yù)先賦予了那些由主動(dòng)的把握開始的精神的主動(dòng)性”。在直觀中,意義給予(或稱統(tǒng)握)體現(xiàn)了主體的主動(dòng)性,“對(duì)象是對(duì)象化的自我成就之產(chǎn)物”,而“對(duì)象化總是一種自我的主動(dòng)作用”[5]80。但是,在生產(chǎn)性的主動(dòng)發(fā)生層次,意義給予所體現(xiàn)的主動(dòng)性,實(shí)際上被置于被動(dòng)直觀之下。生產(chǎn)性的行為一旦消逝之后,其產(chǎn)物則在意識(shí)中沉淀下來,成為被動(dòng)給予的直觀素材。另外,意義給予并不能任意地作用在質(zhì)料上。雖然它起初是主動(dòng)性,也體現(xiàn)了意指活動(dòng)的自由,但也要依據(jù)質(zhì)料的本質(zhì),進(jìn)行統(tǒng)握,給予其意義。胡塞爾的還原方法,所要做的也是讓意向?qū)ο蟮默F(xiàn)象自身如其所是的那樣被揭示、被描述、被看到[6]。意向活動(dòng)不僅構(gòu)成了對(duì)對(duì)象的指向,也構(gòu)成了意義。沒有意義的給予,就無法“看”到一個(gè)對(duì)象。仍以醫(yī)者看到患者有“自汗”為例,如果說,把“頭頸流出汗珠”這一視覺圖像看作是我們想研究的質(zhì)料,它是醫(yī)者在抬頭望向患者的一瞬間,外在空間景象給予他的視覺材料之一,它和患者的穿著、姿勢、裝扮等一樣具有同等地位,此時(shí)并不具有意向性的特征。但緊接著,醫(yī)者看到了患者頭頸出的汗珠,這是意向性的體現(xiàn),是他作為醫(yī)者,中醫(yī)的職業(yè)本性(如果是服裝設(shè)計(jì)師,此時(shí)意向性可能在患者的服飾上)。但是,從“頭頸流出汗珠”轉(zhuǎn)化到“自汗”,并非理所當(dāng)然的,也非邏輯性的,而是統(tǒng)握、意義給予的功能體現(xiàn)。這是因?yàn)椋骸邦^頸流出汗珠”是一個(gè)單純的三維圖像式的材料;統(tǒng)握和意義給予,則給予它靈魂,成為一個(gè)具有內(nèi)涵的現(xiàn)象——“自汗”。因?yàn)樵谝饬x給予之前,如果運(yùn)用自覺理性,一個(gè)人身上“頭頸流出汗珠”的現(xiàn)象,至少存在以下幾種可能:(1)剛剛跑步或運(yùn)動(dòng)結(jié)束,運(yùn)動(dòng)導(dǎo)致的流汗;(2)空氣溫度高,人體散熱需要導(dǎo)致的流汗;(3)剛剛洗澡或洗面結(jié)束,未擦凈導(dǎo)致殘留的水珠;(4)淋雨或其他意外導(dǎo)致的身上有水珠;(5)無任何外界前提原因,自然出汗。
可以看出,醫(yī)者瞬間做出“自汗”的判斷和領(lǐng)會(huì),是多種客觀因素的綜合:天氣很好很涼爽,沒有下雨或炎熱;該患者一個(gè)小時(shí)前就來就診了,在診室坐了一個(gè)小時(shí)了,沒有去運(yùn)動(dòng)、洗澡、跑步等,這幾個(gè)因素,完全可以排除患者“頭頸流出汗珠”的前四種可能性。醫(yī)者對(duì)“自汗”的認(rèn)知,是在外界環(huán)境(氣候、診所附近沒有淋浴室)、局部環(huán)境(診所內(nèi)部一小時(shí)以來的人群分布)等意蘊(yùn)空間下,對(duì)患者“頭頸有汗”下的統(tǒng)握,給予了這一現(xiàn)象是“自汗”的意義。此時(shí)的外界、局部環(huán)境等,胡塞爾稱其為“知覺的場景”或“周圍世界”:“單個(gè)的對(duì)象是從預(yù)先被給予性的場景中凸顯的,是從我們的周圍世界中,對(duì)我們發(fā)出刺激的。”在我們將意向性射向“頭頸流出汗珠”之前,在醫(yī)者抬眼的一瞬間,醫(yī)者意識(shí)就被具有結(jié)構(gòu)性的場景施加了影響,被給予了豐富的信息。這些信息并非如我們主觀意識(shí)流那樣隨時(shí)間流逝而堆積,它們是內(nèi)在時(shí)間意識(shí)施加的綜合作用,過往的信息并沒有消逝,而是作為“滯留”,停留在當(dāng)下,和當(dāng)下直觀的質(zhì)料一同顯現(xiàn)了。具體機(jī)制在胡塞爾[7]另一部著作《內(nèi)時(shí)間意識(shí)現(xiàn)象學(xué)》有詳細(xì)論述。縱然醫(yī)者可以在事后講解時(shí),像我們前面分析的那樣,對(duì)自己“看”到自汗進(jìn)行理性分析。但,意識(shí)瞬間的成就,沒有經(jīng)過這一過程,它只是瞬間主動(dòng)與被綜合性的把握。
2 方證知識(shí)的被動(dòng)聯(lián)想
那么,醫(yī)者在接收到患者頭痛、發(fā)熱、自汗、惡風(fēng)等信息后,桂枝湯是如何顯現(xiàn)的呢?這里,要用到胡塞爾被動(dòng)發(fā)生領(lǐng)域的基本規(guī)律:“聯(lián)想”。現(xiàn)象學(xué)的聯(lián)想不是我們慣常思維認(rèn)識(shí)下心理學(xué)式的主動(dòng)聯(lián)想,現(xiàn)象學(xué)聯(lián)想屬于被動(dòng)聯(lián)想。《邏輯研究》中,“聯(lián)想”意味著“重新喚起”,是基于一定秩序和鏈接中的“一物指向另一物”;兩物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并不是外在地任意加在兩物之上的,而是其自身給予意識(shí)的;這一自身給予指引了某物之現(xiàn)象,使其被現(xiàn)象學(xué)般地顯示出來。被動(dòng)聯(lián)想是一種純粹的內(nèi)在關(guān)系,不具有傳統(tǒng)形而上學(xué)的因果關(guān)系;它屬于經(jīng)過還原后的純粹領(lǐng)域,完全擺脫了客觀存在的前提[8]。
舉例來說,現(xiàn)實(shí)中的某人在街上閑逛,突然在路上看到了一個(gè)貌似熟悉的人的面孔,瞬間,在他的意識(shí)中,出現(xiàn)了和這個(gè)面孔相似的一個(gè)朋友的形象。他的朋友并沒有在當(dāng)下現(xiàn)實(shí)地出現(xiàn)在面前,他也沒有故意去回想朋友的形象,是什么把朋友的形象在那瞬間帶到意識(shí)面前的呢?胡塞爾[5]91-95回答說,這就是被動(dòng)聯(lián)想在起作用。聯(lián)想此時(shí)起到了兩個(gè)角色作用:喚醒者和被喚醒者,而這種作用的發(fā)起基礎(chǔ)是:相似性。由于路人的面孔相似于朋友,當(dāng)前在場的對(duì)路人的意識(shí)把已經(jīng)沉淀在意識(shí)之中的朋友的形象喚醒了。朋友的形象,這一被喚醒的結(jié)果,作為聯(lián)想的結(jié)果突然降臨。聯(lián)想,此時(shí)體現(xiàn)了一種原初的被動(dòng)性,因?yàn)樵诖诉^程中,主動(dòng)的自我并沒有參與,但自我對(duì)于被動(dòng)的聯(lián)想的結(jié)果是接受性的。聯(lián)想喚醒的既往沉積的東西,會(huì)加入到現(xiàn)實(shí)意識(shí)的意義構(gòu)成中,參與到當(dāng)下知覺的意義給予,例如,路人會(huì)被某人構(gòu)建成“像某某朋友的人”,其對(duì)這一朋友所有印象(外貌、舉止、言行、性格),也會(huì)作為“被期待者”參與到這個(gè)路人進(jìn)一步的形象構(gòu)建中。
聯(lián)想并不只是涉及相似性,還涉及非相似性的對(duì)比。胡塞爾[5]91-95說:“所有原始的對(duì)比,都以聯(lián)想為基礎(chǔ);不同的東西是從共同的基礎(chǔ)中凸顯出來的。”非相似處的凸顯,幾乎和被動(dòng)喚醒同步出現(xiàn)。“哦!這個(gè)路人的眼睛比我朋友大一點(diǎn)。”有趣的是,如果某人同另外一個(gè)也認(rèn)識(shí)該朋友的人一同閑逛,他們都注意到了這個(gè)路人,該人和同伴說:“你看,前面這個(gè)路人是不是和某某很像啊!”同伴卻說:“有嗎?一點(diǎn)兒都不像啊。”原因就是:不同的人,對(duì)同一人/物的綜合把握是不同的,在另外一人意識(shí)中,面前這個(gè)路人和他記憶中的某某,沒有共同的基礎(chǔ)印象,或者,該印象的“喚起力”偏弱。因?yàn)椋覀儗?duì)人/物的認(rèn)識(shí)并非如計(jì)算機(jī)般嚴(yán)格的各個(gè)維度參數(shù)記錄,而是意識(shí)的被動(dòng)綜合作用,其起源甚至可以溯源于嬰幼兒時(shí)期,所以也會(huì)因人而異。當(dāng)然,《被動(dòng)綜合分析》中,胡塞爾[9]提到:“這樣的喚起具有趨向的特征,因此,也具有強(qiáng)度的等級(jí)性:它能像力那樣被增強(qiáng),也可能被減弱。”
回到中醫(yī)診療的問題。醫(yī)者面對(duì)患者,最終是要開出一張完整的治病的處方,經(jīng)方大家或經(jīng)驗(yàn)豐富的中醫(yī)大師,其方證辨證式的思維結(jié)構(gòu),即以本文以上篇幅所論的意識(shí)結(jié)構(gòu)為主。
仍以桂枝湯為例,通過書本學(xué)習(xí)、跟師臨證、自我實(shí)踐、反思總結(jié)……種種過程中的每一個(gè)環(huán)節(jié),都有聯(lián)想的被動(dòng)綜合的意識(shí)結(jié)構(gòu)起作用。方證對(duì)應(yīng)的表象,是醫(yī)者看到了“頭痛、發(fā)熱、自汗、惡風(fēng)”,開出了桂枝湯。但這一過程并非自我在腦海里搜尋到這幾個(gè)癥候詞語所對(duì)應(yīng)的方證條文的結(jié)果,即并非面對(duì)一個(gè)現(xiàn)象,總結(jié)這個(gè)現(xiàn)象,想起一個(gè)條理(條文),進(jìn)而運(yùn)用這一條理(條文)的過程。而是,在醫(yī)者的意向性投射到該患者的瞬間,被動(dòng)聯(lián)想就開始起作用了。醫(yī)者見到患者,如果患者沒有先開口,首先可以望診到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神情、自汗(頭頸流出汗珠)、惡寒(衣服多)等。患者具有的這些癥候,可能已經(jīng)瞬時(shí)觸發(fā)了桂枝湯方證這一記憶知識(shí)所蘊(yùn)含的人物場景。醫(yī)者瞬時(shí)腦海中浮現(xiàn)了“桂枝湯”這一條方證知識(shí)。在此,醫(yī)者對(duì)患者暫時(shí)只有視覺上的感知,但這一感知不只是對(duì)患者的一般意識(shí),而是一種突出的方式意識(shí)到了是桂枝湯證型的患者。患者的信息作為觸發(fā)點(diǎn),觸發(fā)了醫(yī)者腦海中所把握的桂枝湯的本質(zhì)概念。患者所表現(xiàn)出的外在形象,不再是作為一種單純的符號(hào)和映象被給予;在這樣的意境中,是醫(yī)者自身擁有的,對(duì)人的外在形象有把握的、有中醫(yī)意義的形象,是醫(yī)者自身給予的。仿佛如前面所舉的例子中他根本沒有或者不需要看到這一路人的完整身體——也許只露出嘴角和鼻孔的一個(gè)側(cè)臉,就完全可以觸發(fā)這一被動(dòng)聯(lián)想——朋友形象的顯現(xiàn)。同理,醫(yī)者對(duì)于桂枝湯的整體把握,必然是理法方藥全面的;但患者自汗、惡寒,這兩個(gè)局部、側(cè)面的癥候表現(xiàn),完全亦可以觸發(fā)聯(lián)想的被動(dòng)給予。誠然,患者接著的主訴:頭痛、發(fā)熱、惡風(fēng)等,可以進(jìn)一步佐證桂枝湯的正確,這既可以再次進(jìn)入意識(shí)的被動(dòng)聯(lián)想路徑,也可以完全由自我主觀思維來思考、核對(duì)了。如果患者接下來的主訴與桂枝湯所應(yīng)有的方證相矛盾,那么更多的信息可以綜合而觸發(fā)另外一條方證知識(shí)的被動(dòng)聯(lián)想;醫(yī)者也可以隨時(shí)進(jìn)入自我理性的思維過程,進(jìn)行回憶、選擇、邏輯(中醫(yī)基礎(chǔ)理論的邏輯)推理、判斷和決策。但后者不是本文討論的主題。筆者所關(guān)注的醫(yī)者瞬間的被動(dòng)思維。在一個(gè)方證對(duì)應(yīng)的病例場景中,它已經(jīng)完成了。
在中醫(yī)診療中,醫(yī)者對(duì)患者瞬間望診的把握,觸發(fā)了醫(yī)者對(duì)某一方證既有的把握,這一把握,既包括理論的學(xué)習(xí),也包括對(duì)世界之中日常生活的理解,畢竟中國傳統(tǒng)思維方式是古人以日常生活世界的理解為根本構(gòu)建起來的,是生活經(jīng)驗(yàn)的抽象[10]——在經(jīng)方中,方證,就是對(duì)應(yīng)著處在生活世界的人。
本文對(duì)中醫(yī)診療中瞬間的思維過程做了現(xiàn)象學(xué)的還原,以描述性地手法,進(jìn)行了純現(xiàn)象學(xué)式的演繹,避免了既往類似研究只停留在概念提取和類比的階段[11]。最終結(jié)論為:在部分快節(jié)奏的診療中,瞬間的思維并非主觀自我辨證推理的過程,而是被動(dòng)聯(lián)想綜合給予的過程。這一結(jié)論可以為中醫(yī)眾多懸而未決的問題,提供一條現(xiàn)象學(xué)哲學(xué)的解決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