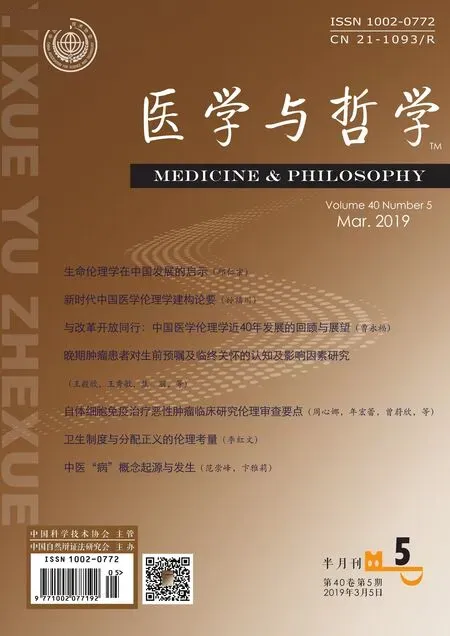醫患之間的共情與病痛敘事*——青海莫多寺曼巴扎倉的醫學民族志研究
范長風
①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 上海 200241
始于17世紀末的曼巴扎倉(寺院醫學院)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開辦的醫學院和醫療機構,迄今已有300年歷史。曼巴扎倉的醫學教育制度是藏傳佛教和藏醫藥融合而生的產物,經過格魯派的傳承、發展,目前主要分布在甘青川的安多藏區。我們調研的青海莫多寺曼巴扎倉的獨特性在于:它既是第一個寧瑪派寺院的醫學教育基地,又隸屬于國家衛生系統,同時擁有社會公益慈善屬性。來自藏區各地各民族的患者以及在大醫院沒有治愈的疑難病癥患者,每年冬天來至草原深處的曼巴扎倉就醫。這些以牧民為主體的貧困患者在曼巴扎倉以極小的代價或者免費獲得醫僧們充滿愛心的治療和照顧。與城市大醫院存在的醫患緊張關系不同,在青藏腹地的曼巴扎倉存在著一種仁愛、共情的醫患關系。我們發現曼巴扎倉的醫療模式或許能為現代醫療體系遭遇的醫患困境貢獻出一些有價值的思想。
1 引論
批判醫學人類學有兩個頗富啟發性的觀點。第一,西方醫學院的醫學訓練存在著去人性化和過分強調技術的問題。學者認為醫療霸權可以通過教育體系、宗教機構和媒體發生作用[1],反過來說,藏醫文化復興同樣也可以通過教育、宗教和大眾媒體而得到強化。人類學家呼吁在診斷和治療方面應增加社會因素,減少生物醫學技術的普及推廣,鼓勵傳統治療手段的使用。第二,患者體驗是社會的產物,無論健康幸福還是病痛疾苦,都是由地方文化體系、社會權利關系和政治經濟權力來建構和定義的[2]。雖然個體體驗對醫療霸權和制度性不平等無能為力,但患者體驗對于治療,對于醫療制度性缺陷可以做出積極反應從而引起醫療政策的變革。批判醫學人類學并非以解構現有醫療制度為專長,它本質上是回歸以患者為中心的建構主義。批判理論和文學研究為醫患共情在臨床實踐中進一步發揮作用提供了資源。
病痛是書寫在身體上的歷史,醫學人類學家索達斯說用于強調語言和身體(符號和心理)存在著神奇的關聯,即意義和療效不可分離[3]。在現象學對人文學科的持續影響下,人類學、民俗學都建立了自己的敘事理論,其中包括文化治療的研究。在醫學人類學領域,凱博文和卡倫對敘事醫學做出巨大貢獻。凱博文將敘事醫學劃分為“疾病敘事”和“病痛敘事”[4]。也就是說,疾病和病痛分屬于不同生活世界,疾病是醫者的話語和工作對象,是醫者觀察記錄、尋找病因和治療方案的客觀世界;而病人的世界則不同,他們感受和體驗病痛,有表達心理和社會苦痛的需要,而他們敘事的文本也主要來自主觀感受,因而醫患之間的理解通常是默契合作和治療的基礎。
古希臘的醫學有三大法寶:語言、藥物和手術刀。今天人類最初的語言和敘事能力被醫療器械和現代生物醫學技術大大削弱了。如何培養臨床醫生對患者的理解、共情和親和能力?卡倫基于系統研究和長期醫學實踐建立起“平行模式”,即在醫生書寫醫療病歷之同時增加一份人文病歷,記錄患者主觀的病痛體驗,就像人類學的田野筆記一樣書寫病患故事及人文觀察所得。平行病歷要解決的問題是醫患之間因不同敘事而產生的緊張關系,它強調醫療應回歸理解、共情和親和。
從凱博文和卡倫的醫學敘事研究及臨床實踐來看,病痛敘事的主要目標是獲得醫患共情。但是共情理論在醫學教育和臨床實踐都面臨許多挑戰:共情可以教授和獲得嗎?有什么辦法保證書寫的敘事與病人的真實相一致,而不是對病人故事簡單地記錄而變為職業流程[5]。共情模式存在某些限制因素,既不必也不能保證好的治療[6];共情理論傾向于把患者對象化為展示醫者美德及其抑制疾痛的個體。
2 托美活佛與曼巴扎倉
2014年是藏歷馬年和藏族人的轉山之年,此所謂“馬年轉山,羊年轉湖”。是年八月,項目組一行五人在開展三江源環境保護項目工作之際,按照傳統路線騎馬游覽阿尼瑪卿山。此時藏醫學家、莫多寺的托美活佛率100多位阿尼(女僧)亦朝拜神山。也許是轉山的功德,我們有幸在興海縣邂逅托美活佛,并且跨過藍色的曲什安河,走進草原深處的曼巴扎倉。
興海縣曾經是歷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位于青海湖與阿尼瑪卿山之間,黃河自南而北穿境而過。托美活佛是莫多村人,小時多病,在果洛遇一神醫,把脈開藥,藥到病除,遂立志學習藏醫以濟蒼生。托美活佛早年在當地的塔洞寺院為僧,19歲遍游藏地寺院學習佛法和藏醫,先后依止四位上師并跟隨他們學習佛經和藏醫學。托美活佛在佛法和醫學上的精進和仁者之心,使他在30多歲就被認定為活佛,并在果洛住持一個寧瑪派寺院。1999年莫多村的老人鑒于當地牧民缺醫少藥和缺少宗教服務的情況懇請活佛回村。作為佛教徒,他深感自己家鄉仍是佛法不傳的邊鄙之地(佛教用語),人民遭受缺醫少藥之苦,從而產生宗教使命感和醫者的共情。在鄉政府的支持下,托美活佛當上了每月拿1 000元的鄉村醫生,村里人為活佛蓋了小經堂和衛生室。這小經堂就成了莫多寺的雛形;名不見經傳的衛生室也成為曼巴扎倉及其門診的前身。
2003年活佛和僧人遞交報告向政府申請成立寺院,同年9月獲準成立“扎西達塘寺”(莫多寺)。2007年莫多村整體搬遷至曲什安河(黃河支流)以北的山谷中。活佛用120萬元搬遷費和自籌經費初步建立起經堂、僧房、曼巴扎倉及門診,還有30間簡易平房當作住院部。此時僧人已有40多位,小和尚60人,阿尼50人,醫學生90人,在這些人中,孤兒、患病者和貧窮無靠者占70%以上。寺院初成便具有慈善機構的性質。2008年青海省衛生系統認定莫多寺曼巴扎倉為海南州衛生職業技術學校。雖然寺院不以佛教徒的標準要求學生,但醫學院采取宗教修行與學醫并重的管理方式。托美活佛和曼巴扎倉承擔4項重要工作:
其一,講經論道與傳授醫學知識。莫多寺就像一個宗教社區,其人群依次為寺院僧人、阿尼、醫學院學生、牧村的村民、住院部的病人和病愈后定居下來的外來者。寺院、曼巴扎倉、醫學院和阿尼寺院有不同層次和內容的修學任務。其二,公益醫療服務是曼巴扎倉的中心內容,治病救人作為他的修行一部分占據了活佛1/3的時間。其三,舉辦慈善事業是佛教徒踐行慈悲心的修行方式,在莫多寺曼巴扎倉更成為日常化工作。寺院接納來自藏區各地孤兒70多人,孤寡老人20多人。這些人的生活主要靠寺院開辦的小型藏服廠獲取的利潤支持。其四,參與社會(社區)管理。在莫多寺社區,社群類別包括僧尼、醫學生、小商販、當地牧民和住院病人,活佛的管理涵蓋以上所有社群。每一個外來者都能感覺到,整個社區洋溢著一種遠離塵世喧囂的寧靜、秩序、仁愛和文明的氣息。
3 曼巴扎倉的醫學敘事
3.1 沒有共情何以敘事:笑唄
青海省共和縣牧民尕藏加患甲狀腺功能亢進13年,在縣、州、省各級醫院都治過。當問及為什么最后選擇莫多寺治療時,尕藏加說他患病的頭幾年不能走路,眼睛突出,由于語言溝通問題,縣醫院沒能確診。確診后在西寧的人民醫院治療7年,花費39萬元尚未治愈。
大醫院很專業,但我聽不懂漢話,也不識字,不知道他們在說什么。他們就一直笑,那就跟醫生笑唄。就這樣,我和醫生的交流基本上是有禮貌的笑。一個小瓶子的藥打一只800元,要是一年半載還能堅持,大夫說我的病還要七八年才能好。如果再花七八十萬,錢吃不住了。我是個牧民,原來有460只羊,生病住院時就賣了一半,那時候一只羊500元~600元,三年就把錢花光了。
去年年底才有了醫保,去大醫院看病可以報銷,但是省醫院要先交錢才能治療,我再也拿不出錢墊付了。而且快到復查的時候,路也走不了,身上抖得厲害,需要人照顧。來到莫多寺,和曼巴交流特別舒暢讓我有了信心,眼睛不腫了,身體也不抖了。一個月才花30元,如果需要幫忙,給曼巴說一聲就是了。
興海縣回族商人馬振華四肢腫痛,醫院診斷為關節炎,在西寧三個醫院治療,花費八萬元,沒有任何效果。安多藏區有許多在大醫院治療無果的病人來到莫多寺求治。該曼巴扎倉擅長治療骨質增生、關節炎、肺結核以及精神性疾病,即當地人所謂的“臟病”。
當地醫生看了我的病狀,說是得了臟病,遇到什么不干凈的東西。大醫院治不了,活佛曼巴有辦法。曼巴給我做了艾灸,開了藏藥,念經驅邪。現在好多了,消腫以后可以慢慢走路了。一個月的藥才50塊不到,治療基本上是免費的。今天來就是讓活佛看看,鞏固一下。
青海貴南縣中學教師云丹的父親患肺癌晚期住在曼巴扎倉,活佛說他的父親可能來日不多。于是他特地趕過來最后照顧一下父親。
我父親在省醫院看過,不過大醫院人多,幾百人排隊掛號、取藥。他可能意識到自己的病沒救了,整個人無精打采的,打完針就去睡覺,不愿和人說話。對于我來說,父母親這么大年紀,去大醫院我們不放心,但在莫多寺曼巴照顧得十分周到,我心里特別感謝。
在莫多寺看病,活佛讓他一邊服藥,一邊鼓勵他參加寺院的開示和法會。可能是受活佛的教化,他完全放開了,感覺他有精神了,人也開朗了,有時還和我母親開開玩笑。
在15份訪談資料中,藥費虛高、去人性化和缺少共情是大醫院為人詬病的地方,而曼巴扎倉在這些方面卻比大醫院做得好,更有公益心和人性化。在曼巴扎倉,病人的醫療費人均50元,住院部提供的病房每間60元。對于那些貧困無靠和孤寡老人,醫藥、住宿全部予以豁免,且無償提供燃料和食物。這就是為什么在醫保覆蓋90%以上藏區人口的情況下人們還涌向曼巴扎倉治病的原因。中國現代醫院存在的社會性醫患關系緊張有著歷史文化原因,亦有西醫全球化帶來的弊端,但主要原因是現代醫療體系存在的技術-人性分裂引起的問題。
傳統時期的中國醫療在文化上受陰陽五行學說的影響,但醫療組織形式缺乏國家和社會團體的支持。于賡哲所做的一項中國古代醫患關系研究表明(見表1),古代醫者的生存缺乏宗教團體的支持,經濟上主要依賴患者市場和上層有權者,因而在醫患關系的鏈條中處于被動地位,故而采取迎合患者、無序競爭以及技術密不外傳等措施[7]。這種受生計驅動而無社會約束力的患者主導模式,成為醫患關系沖突頻發的歷史基因。當下中國醫療推行的西醫管理被人詬病的非人格化、技術化和體制僵化,加上現代醫院在思想上和物質上不具備公益醫療的條件,反而利益當先,此種狀況實乃歷史與現實的雙重原因作用的結果。
表1藏醫、中醫和西方教會醫學的歷史文化比較

比較內容藏醫中醫中世紀教會醫學管理方式寺院管理市場調節教會管理醫療觀念受藏佛影響,三因說受中國哲學影響,陰陽受基督教影響,罪孽觀醫療組織形式小規模醫院,全科大夫私人診所,全科醫院,分工合作醫患關系模式醫生主導,和諧患者主動,有沖突醫生主導,有沖突醫療效率較低較低較高交流與傳播寺院舉辦醫學教育密不外傳,無學術對話醫學交流渠道通暢
宗教-醫學的醫療體系,比如曼巴扎倉和西方的教會醫學,對醫患沖突的發生有天然的抑制作用。醫學與宗教信仰的結合為醫學體系提供了解釋框架,由此起到規范醫患行為的作用。該模式從信仰和文化傳統方面減少了醫患沖突的可能性。首先,醫者身兼教徒和醫生雙重身份,加之這種醫療體系的公益醫療性質更易獲得患者的理解和尊重。藏醫與西方教會醫學在某些方面具有文化相似性。兩者的醫學教育、醫療機構都由宗教團體來管理,這非常有利于醫學知識的交流和傳播,又具備向貧困人群提供醫療服務的公益性。另一重要方面,宗教團體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去規范醫患關系中的患者的醫療行為。西方教會醫學使用基督教“罪孽”觀去解釋醫療事件,死亡歸之于罪孽,治愈歸之于懺悔,從而使醫生在醫患關系中處于主動地位。如果從文化發生學角度來看,現代醫療情景下的醫患關系問題有著各自的歷史文化根源和文化邏輯。
3.2 用儀式敘事:撫慰心靈的治療法會
曼巴扎倉的醫僧所進行的儀式治療與藏族民間法師有所不同。民間法師無論在私人場合還是公共場合,治療方式都傾向于驅邪表演或象征性暴力手段;曼巴扎倉的儀式治療方式總是表現為經院式的誦經法會,用禪修的能力和密咒打敗魔障。2015年8月我們在莫多寺曼巴扎倉目睹了儀式治療的場景。那天艷陽高照,活佛主持灌頂儀式的消息很快吸引了住院部的病人和村民前來參加。一些病人跪拜在活佛的腳下,眾人圍坐在診所的院落里。過度勞累的活佛在午后強烈的陽光里念平安經,身上大汗淋漓。灌頂用的容器是各種飲料瓶和一個類似于澆花的噴壺,年輕人將其清洗干凈,灌滿清水。活佛舉瓶,一邊念經一邊吐氣,每個人謙卑地低著頭。兩位醫僧接過活佛念過經的水灑在人們的頭頂上,眾人雙手捧水入口,洗漱后吐掉,如此循環往復。多位男子袒胸露臂,一位70多歲的藏族婦女也脫掉上衣,在右乳房的位置留下一塊傷疤,曼巴把清水噴灑在患病部位。在活佛的誦經聲中,醫僧們手持經書用力拍打眾人的頭部和背部。第四次賜水,在活佛低沉的誦經聲中眾人雙手合十,臉上掛著憨厚的微笑,如同等待甘露降臨。眾僧對著每個水瓶吹氣,然后分賜予每位參與者,人們雙手捧起,一飲而盡。
藏醫醫療體系深植于社會文化系統中。藏醫的三因說是從病理學來講的,認為隆、赤巴和培根在人體內不協調從而導致疾病。貪、嗔、癡的概念是從藏族文化和藏傳佛教來講的,認為“三毒”是導致疾病發生的根本原因。其實文化塑造疾病和治療還存在一種另類形式,相信惡鬼、邪靈和不潔之物會導致產生邪病或臟病,與之相應還存在諸如驅鬼這樣一種文化治療方案。這幾乎是一個存在于世界各地的跨文化現象。莫多寺托美活佛對此類疾病和治療方案這樣說:對于魔病需要以念經為主,治療為次;而對于生理性疾病則以藥物治療為主,以念經為輔。古今中外關于邪病與驅邪的現象,無論是前西方還是非西方的醫療體系均能給出治療方案,一般是儀式治療。
在西方生命語境中,身體是一個封閉或有邊界的肉體,因而治病就限定身體本身。在非西方的身體認知中,身體與更大范圍的社會語境相聯,治病則與更廣泛的社會情景聯系在一起。 西醫善于施治在生物層面界定清晰的個體化身體,而許多非西方治療體系更喜歡把個體的身體置于社會語境中去處理。在疾病的診斷方面,西醫關注的是“生物身體”,而非西方醫學除了診斷病理本身,還會在“社會身體”方面尋找病因,比如家庭或社會成員,甚至將病因歸咎于超自然力量的憤怒,故而在家庭或者社區范圍內舉辦驅邪儀式,或者在公開的文化儀式中安排治療環節(比如中國的迎神賽會)以圖恢復正常的社會關系或平息神靈的怨怒。索達斯強調語言和身體(包括心理)有著強大而神奇的關聯,把療效與語言實踐聯系起來,發展了植根于文化現象學的治愈理論。
從民族醫學的治療方式看,把自然與超自然,精神與身體,醫療與文化放在一起的整體論思想是民族醫學的基本特征,也是其力量所在。在我看來,儀式治療是某種形式的文化認同。患者通過文化表演、轉經、誦經和醫療法會去體驗生命存在的價值,從而獲得深層心理撫慰和治療信心。
儀式治療的療效問題一直是民族醫學遭受質疑的問題。人類學早就發現這種象征性表演的治愈作用。列維·斯特勞斯稱之為“象征效用”(the effectiveness of symbols),通過社區信仰的共識(consensus)和融貫(coherence)而發揮作用[8]。共識和融通保證了人們對社會角色及其權力的確認從而產生合作,就像無線話筒與攝像機同步工作的原理一樣,若要正確拾音就必須對上頻道,聲音與畫面才會產生音畫同步的效果。綜上可知,文化治療的效果問題不能也不應該用現代醫療檢測手段去衡量,因為西醫的評估體系不是針對包涵著儀式、語言、象征和敘事的民族醫學而設置的。文化治療無論發揮了“安慰劑作用”,還是產生了列維的“象征效用”,有一點是肯定的:其神圣敘事、特殊的語言和象征性動作引發了醫患共情。
3.3 曼巴的親和,不止于語言敘事
親和是醫者敘事和患者敘事的融通,即把醫者認知疾病的客觀世界和患者感受病痛的主觀世界相互打通而呈現的境界。語言是達致這一境界的手段之一,我們的觀察發現曼巴扎倉的醫者不僅能夠借助語言敘事與患者發生共情,而且超越語言付諸公益行動以緩解患者的疾痛。
2000級曼巴扎倉第一屆醫學生久麥多杰,32歲,梳著一個略顯花白的小辮子,他在共和縣開了一家藏醫診所,當曼巴扎倉的病人太多時他就回來分擔活佛壓力。他回顧10年的學醫生涯時說:
活佛把醫學和佛經結合起來,給我們講《四部醫典》。他告誡我們,對待病人就像對待母親一樣竭盡全力。即便是半夜出診,也不能心有怨言,更不可看重錢財。活佛教育我們,行醫時不能隨便增加醫藥費。病人因此耽誤病情,就等于謀財害命。
真誠的話語就像太陽一樣溫暖人心。治療中好言好語容易做到,傾聽病人的感受則不太容易做到。一個好曼巴應該把病人當作家人朋友那樣說話。
2010級的醫學生久太加從曼巴扎倉畢業后在西寧藏醫院工作了3個月,還是放棄了大城市的工作,回到曼巴扎倉做實習曼巴,負責住院部的工作。他是一個喜歡唱歌、注重發型的小伙子。我們見到他時,他正在用三輪車給住院部運水,病人和家屬紛紛拿出水桶排隊接水。久太加的褲子、鞋子都被水打濕了,發型也遭到破壞,然而在大家的目光和語氣中久太加是好樣的。久太加每天下午五點去住院部查房噓寒問暖,了解病情,有時候還為病人唱上一曲。這就是曼巴扎倉的醫患關系,親和得讓人覺得不真實。
下面的訪談資料講述的醫學敘事和共情,發生在作為醫者的活佛和作為患者的學生之間。曼巴扎倉的學生有3種情況:一是有志于藏醫的農牧民子弟;二是寺院收留下來的孤兒;三是因病學醫者。德欽是來自恰卜恰一個單親家庭的姑娘,跟母親過。她患有先天性心臟病。
我心臟不好,一個人的時候總想哭。有一次發作,活佛抱著我的頭,我埋在活佛的懷里哭。雖然我的父親不跟我生活在一起,我不知道父愛是什么,但在我心里,活佛比父親還要親,所以我也是很幸福的。
課余時間我們都喜歡和活佛聊天,活佛也喜歡聽學生、病人訴說心事。每天晚上都會有學生求班長約見活佛,哪怕10分鐘也好。我想聽聽活佛的開導,讓自己平靜下來,我想病人也是這樣想的。可是當我知道活佛的作息時間時我有點后悔。
7:00-9:00 上師起床、念經、早飯;
9:00-14:30 給僧人講經、開示,學生、村民和病人均可參加;
15:00-18:00 門診看病問診;
18:00-21:00 處理寺院事務,會見學生、病人;
22:00-00:00 給醫學生上《四部醫典》;
00:00-2:00 聊天、念經、睡覺。
有一次我生病,難受時想家想媽媽,打電話把媽媽叫來陪我。活佛知道后過來照顧我,罵我沒良心。“媽媽獨自一人在家支撐這個家庭,還要干活,又苦又累,你還讓她跑這么遠。”其實活佛身體也不好,患有高血壓,原因是他勞累過度,坐久了腳面浮腫得厲害。大家都有很多話要跟活佛講,也想看望他。停電是聊天的好機會,我們就會一邊聊天一邊給他捏捏腳,這時候是最幸福的。
病痛敘事和共情是一種能力和技巧,毫無疑問能力和技巧是可以訓練和習得的東西,而能力如何使用則是與醫學倫理相關。作為醫學和藏佛融為一體的《四部醫典》,為藏醫教育和醫療實踐提供了病痛敘事和共情的思想資源。藏醫教育強調在身、語、意3個方面嚴格要求自己,并在臨床醫學中體現出來。曼巴扎倉的資料說明,病痛敘事和共情的發生是有條件、有語境、有限制的。托美活佛所做的努力正是創造條件,重建語境,突破限制。首先,藏傳佛教對曼巴扎倉的加持確保學習者把慈善作為內在修行的要求,把公益心落實到外在的公益行動上。這是病痛敘事的思想條件。其次,曼巴扎倉還致力于恢復藏族傳統文化,并在醫學教育中增加禮儀訓練,這些傳統知識可以獨立發揮作用,同時也有助于病痛敘事的展開,亦對醫患共情有所裨益,因為有共享價值的雙方更容易溝通。
4 結論
現代社會的種種醫療衛生問題究其根源都與醫學教育有關。那么現代醫學教育究竟有什么根本問題呢?西方醫學史專家羅伊·波特(Roy Porter)的研究發現西方醫學院的最大問題是去人性化、過分技術化、體制化,熱衷于醫學的職業發展而非病人的利益[9]。曼巴扎倉把醫學人文教育視為藏醫教學體系中的靈魂,病痛敘事并非空中樓閣,其敘事傳統源于這部偉大的經典——《四部醫典》,它提出了藏醫學的公益原則高于市場,公益性是藏醫具備醫學敘事的思想基礎。曼巴扎倉的醫學教育的顯著特點是強調敘事,但不限于語言敘事,象征性的儀式、人性關懷的行動也都成為醫療敘事的一部分。共情也是曼巴常用的技能之一,在文化治療和臨床醫療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曼巴扎倉的醫學實踐表明,病痛敘事和共情能力的激活需要傳統文化及其空間、語境的支持,因此曼巴扎倉所做的恢復傳統文化的努力就顯得頗有價值,應當把曼巴扎倉作為醫學領域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來看待和保護。
醫患關系的緊張從歷史淵源和跨文化角度看,文化在其中起到深層和內在的作用。曼巴扎倉的醫學人文教育模式就是用宗教文化培育曼巴的公益心,塑造患者群體的醫學認知,從而有效地避免了城市醫院頻發的醫患緊張關系。因此曼巴扎倉的公益精神和醫學人文教育是人類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和精神財富,也是敘事醫學的靈魂。它的醫療實踐模式和人文教育經驗對于解決現實生活中的醫患關系具有重要的探索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