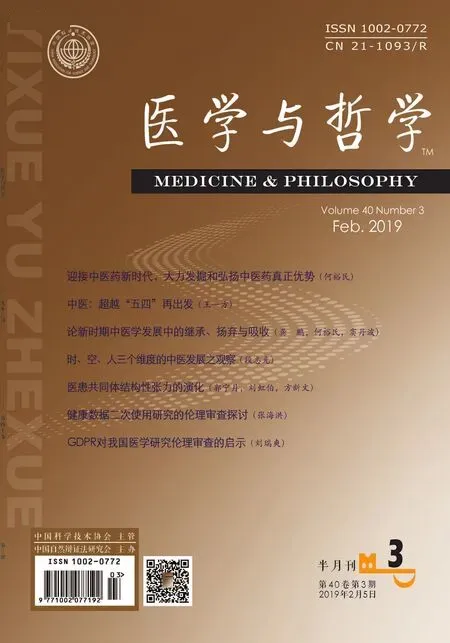迎接中醫(yī)藥新時代,大力發(fā)掘和弘揚中醫(yī)藥真正優(yōu)勢*
何裕民
1 引言
隨著全國中醫(yī)藥大會的召開,與若干年前相比,中醫(yī)藥已迎來了極其優(yōu)渥的外部生存條件。如除此次大會外,它還獲得世界最高級別科學獎,進入權(quán)威的《國際疾病分類》,出臺《中醫(yī)藥法》,頒布《中醫(yī)藥發(fā)展戰(zhàn)略規(guī)劃綱要(2016-2030)》等。然而客觀地說,這些,或是歷史積淀(如屠呦呦受啟于歷史經(jīng)驗,破解傳染病之難題;中醫(yī)疾病分類則純是歷史經(jīng)驗);或是政策等外部條件,都很重要,但并非決定性的。推動學科發(fā)展的決定性因素是學科自身的內(nèi)生性動力機制。對此,應引起學界的高度重視。
2007年3月17日國醫(yī)節(jié)當天,筆者等中醫(yī)人士與一些力主“告別中醫(yī)”者在北京協(xié)和醫(yī)學小禮堂激辯甚烈,火藥味十足,誰都說服不了誰。最后筆者下“休戰(zhàn)書”——“別無謂爭辯了,給中醫(yī)10年~20年寬松氛圍”,斷言“中醫(yī)界能以實際成就”證明自身價值……。轉(zhuǎn)眼10多年過去了,諾貝爾獎拿了,中醫(yī)疾病分類進入《國際疾病分類》而被世界接納了。筆者解讀:之所以召開空前規(guī)格之專業(yè)大會,背景性動機不僅是把中醫(yī)藥當成一大寶庫、五大資源,更是提升到彰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力爭借中醫(yī)藥發(fā)掘中國傳統(tǒng)文化潛在優(yōu)勢,開拓新局面,令其發(fā)揚光大,以推進大同世界日趨美好和諧,且更加豐滿而多樣化的普惠層面。
因此,從毛澤東力倡中西醫(yī)結(jié)合算起,走了一甲子坎坷路的中醫(yī)學,今天既是最好的發(fā)展時代,也是難得的最后契機,因為時不再來!尤需業(yè)內(nèi)學者認真發(fā)掘?qū)W科內(nèi)生性動力機制,乘東風良機,鼓帆前行,融入并助力于現(xiàn)代世界發(fā)展大潮之中。而意欲如此,首要之舉是形成清晰的新思維。
2 倡導“底線”思維,講究包容性發(fā)展
客觀地說,60余載的中醫(yī)學發(fā)展之途,時而炙熱,時而沉寂;更多的是業(yè)者的迷茫,爭執(zhí)于哪種路徑方向?困惑于路在何方?如關(guān)于發(fā)展之爭,貼標簽,提主義,比口號,層出不窮,不下幾十種提法。但實質(zhì)性成果乏善可陳,研究重大突破頗為罕見。“擱置爭議”是當年鄧小平提出的發(fā)展中國之創(chuàng)舉。當今的中醫(yī)學發(fā)展也可以借鑒。鑒此,在中醫(yī)發(fā)展及應用問題上,建議應倡導“底線”思維,學術(shù)共同體先尋求“最大公約數(shù)”,擱置細節(jié)爭執(zhí),講究包容性的“條條大道通羅馬”。
筆者認為:當今中醫(yī)學研究及運用,只要不違背醫(yī)學倫理底線,不以純商業(yè)動機“消費”中醫(yī)學,并遵循科學與人文精神,以客觀結(jié)果說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不僅能看好病,解決對象身心疾苦,且對方接受度、傳播度、滿意度都尚可,又能恪守原有的中醫(yī)優(yōu)勢(體現(xiàn)為簡便廉、真善美,手段綜合、“自然”且無創(chuàng)傷),都應予以包容及肯定,無需問“英雄出自何方”!能兼具發(fā)展前瞻性的更好;若能在機理機制、方法手段上有創(chuàng)新且言之成理者,尤其應予嘉獎;而以中醫(yī)思路引領(lǐng),能開創(chuàng)新局面的(盡管尚稚嫩),也應允許和鼓勵。總之,對迥異于強勢主流且日漸沉寂的一類舊學術(shù)體系,講究包容性發(fā)展,強調(diào)守住底線前提下的百花齊放、百舸爭流是上上策。但不能忽略、放棄或漠視醫(yī)學的利他、人道、倫理、科技及有用等的基本屬性。且每位業(yè)者不宜過分執(zhí)迷于自己所信奉那一套,以此為據(jù)排斥他者。因為作為資深醫(yī)師,若干年臨床工作后總有一些患者療效不錯,但不等于說就你的方法是對的、唯一的;他人的就是錯的、不當?shù)摹.斎唬侄螒M可能是自然的,體現(xiàn)中醫(yī)本然特征的。再者,作為一大學科體系,強調(diào)“道”(觀念/原則)、“學”(學理/科學)、“術(shù)”(方藥/技術(shù))的綜合及兼顧也至關(guān)重要。否則,就不是學科的整體發(fā)展,更無從談及五大資源的開發(fā)及現(xiàn)代弘揚。
3 中醫(yī)學“以不變應萬變”的真正優(yōu)勢何在?
上述只是構(gòu)成新時代意欲大力發(fā)掘和弘揚中醫(yī)藥事業(yè)的底線和包容性發(fā)展之基本訴求。然而,醫(yī)學的主體畢竟是實用的科學技術(shù)。科學技術(shù)是具有鮮明時代性的,每每隨著時勢變遷和基礎(chǔ)性背景因素之更新而需有所調(diào)整適應。人們已認定當今社會是人類歷史上少有的快速發(fā)展之“大時代”。一切皆在瞬息萬變中。醫(yī)學的基礎(chǔ)條件及背景(包括人們的生活工作方式、多數(shù)人體質(zhì)、疾病譜系及常見病性質(zhì)表現(xiàn)、臨床癥狀及機理,甚至蕓蕓大眾用藥后的機體反應)等,也都發(fā)生著嬗變;有些甚至是根本性裂變,如又苦又澀的湯劑,再讓年輕人咕嚕嚕喝下去,顯然很多人會未喝即吐的。
“古方新病不相能!”早在宋金時期就有此說。而那時,新舊世紀變化遠沒如今之強烈。因此,上述只能說是從事中醫(yī)學工作的最低訴求。欲卓有成效地迎接新時代,亟需清晰的新思維;且此新思維須高瞻遠矚,具有頂層設(shè)計屬性,兼顧中醫(yī)學歷史積淀、現(xiàn)實優(yōu)勢(可以是潛在的或顯現(xiàn)的)、實用意義及大眾生理需求和病癥特點等綜合考量,并充分參照“他者”(現(xiàn)代醫(yī)學等)短長的,同時顧及變革大時代眾人及疾病可能演變趨勢之理性分析。故這是一項頗具挑戰(zhàn)性的腦力激蕩。筆者愿就此作一嘗試,以拋磚引玉。
很顯然,這命題涉及對中醫(yī)核心價值及其真正優(yōu)勢之挖掘、認可、把控、提煉、轉(zhuǎn)型等。作為一大類龐雜的知識體系,中醫(yī)學的核心價值及優(yōu)勢并非一兩個要素可概括,其本身是一多層次體系。筆者主持的國家“十二五”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課題發(fā)標時就以“中醫(yī)文化核心價值體系”來標注。更何況學術(shù)界對此龐大命題見解紛呈,眾說紛紜,表述并不一致。有學者強調(diào)中醫(yī)“以人為本”,而非“以病為主”,呵護“人”遠在治其身上患的“病”為先;有學者認為中醫(yī)優(yōu)勢在于綜合處置,而非就事論事;有學者認準指導中醫(yī)臨診操作的哲學思維極具優(yōu)勢,遠較機械且形而上的西方臨床思維來得合理;也有學者主張中醫(yī)藥的辨證論治恰好與西方臨床按病給藥可以互補,相得益彰;更有學者認定中醫(yī)的處置手段(包括中藥、針灸、手法等)往往是自然的、綠色的、無傷害的,故優(yōu)勢明顯……。這些挖掘整理,都有一定的依據(jù)及意義。然似乎并沒完全抓住問題之實質(zhì)——面臨科技高速發(fā)展,新療法/新藥物層出不窮,疾病譜業(yè)已明顯改變之現(xiàn)實,人們對醫(yī)學及醫(yī)療的企盼及要求也日新月異的當下,中醫(yī)的“真正優(yōu)勢”——具有統(tǒng)領(lǐng)全局性質(zhì)、涵蓋基本特征,且能夠為明天效如桴鼓地解決臨床難題,從而為蕓蕓大眾普遍欣然接受之優(yōu)勢,究竟何在?在這里,強調(diào)的是實實在在,不是大約或可能的;不是支離破碎的,局部的;不是自吹自擂的;不是哲學理念或概念的,而是實質(zhì)性可操作的;更非閉門造車想象的;也不是自我管窺之見而“他者”難以認可的。這一結(jié)論之獲得,只能借助理性的深刻反省分析,在歷史的、邏輯的、哲思的比照考量中,結(jié)合對現(xiàn)實的、未來(諸如疾病變遷大勢、科技進步趨向等)的綜合預測及展望中,方能初見端倪,有所領(lǐng)悟。而且,理想的還應兼顧深層次理論剖析辯駁——為什么中醫(yī)學得以形成此等真正特質(zhì)?其歷史的、邏輯的必然性何在?……只有明晰這些基本問題后,相關(guān)討論才能深入進行。
4 盡可能借本然方式,努力維護“自愈力”
筆者認為:中醫(yī)文化核心價值是一大龐雜的體系。就觀念而言,涉及自然觀、生態(tài)觀、生命觀、生活觀、醫(yī)學觀、道德觀等多層面;以比照方式,東西方(中西醫(yī))的價值差異可從不同層次歸納出十余條[1];但核心的是認定生命乃大自然演化產(chǎn)物,自然本身具有智慧;“人生一小宇宙”;生老病死皆有其規(guī)律;“康寧”則是中國古賢對生命及生活目的和價值的集中之指向;可視其為此價值體系之核心[2];“真氣從之,病安從來!”則是慎養(yǎng)生命(養(yǎng)生)之要旨。就臨床操作言,注重人自身隨演化而逐步獲得的“正氣/真氣”(此“正氣”很難用簡單詞匯加以概括,它包括協(xié)調(diào)、統(tǒng)攝、抗病及自愈等的機能和力量);遂有“正氣存內(nèi),邪不可干”等經(jīng)典闡述。總之,中醫(yī)真正的特質(zhì),可表述為尤其關(guān)注每個個體自我內(nèi)在之力量(正氣/真氣);拳拳于以自然手段,呵護并調(diào)動這類內(nèi)在力量,努力促其回歸本然之平衡,以維持或增進健康,解決疾病及不適等偏差。前面那些特點更多地屬中國哲學,而非關(guān)注生命/健康之具體醫(yī)學的。中醫(yī)學并不看重借助外力,人為地重建一套新(哪怕是最科學的)模式或平衡機制(也許是能力受限,但秦漢后這種演變成傳統(tǒng)。如漢朝雖有外科術(shù),卻未能得以發(fā)展就是例證),而是強調(diào)“謹察陰陽所在而調(diào)之”,恪守“以平為期”,且手段方法更傾向于本然的。“天人相應”、“人生小宇宙”、“陰陽平衡”、“整體觀念”等,都從不同側(cè)面折射出這一宗旨。針灸按摩之所以最早盛行,食療何以初期就是中醫(yī)主要組成部分,都與此相關(guān)。雖古希臘醫(y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也曾有“自愈力”說,與“正氣說”異曲同工,但“自愈力”早已被近現(xiàn)代西方學者遺忘,而“正氣說”等卻依然熠熠生輝。可以說,傳統(tǒng)中醫(yī)迥異于西方醫(yī)學之處,就在于關(guān)注機體內(nèi)在自然力之協(xié)調(diào);而不只是依賴醫(yī)療干預(且往往需借助外力)之一隅,而后者正是標榜為科學的現(xiàn)代醫(yī)學最有特色、最為人稱頌的進步和貢獻之處。
本文絕對無意否定現(xiàn)代醫(yī)學充滿高科技的醫(yī)療干預之巨大進步意義。沒有這些高科技干預,人類就無以基本控制致命的細菌性/感染性疾病;緩解世界曾普遍存在的營養(yǎng)不良狀態(tài)也是奢望(當然,這不只是醫(yī)學之功);更不可能有效降低從心血管、糖尿病,到中風、癌癥等的死亡率。然而,隨著相對單線條的感染性/傳染性疾病之控制,營養(yǎng)不良狀態(tài)改善,以及較為單純的一些慢性病之緩解,似乎純以外力進行干預的征服性醫(yī)療對策及其效用也開始出現(xiàn)瓶頸現(xiàn)象——當今,雖借助醫(yī)療干預尚能捉襟見肘地解決一些臨床難題,但一方面它的成本及代價越來越大,抗生素的“紅桃皇后”效應就是典型;另一方面,積極醫(yī)療干預之尷尬,也日趨凸現(xiàn);如在癌癥治療中常規(guī)化療的應用就十分窘迫,靶向藥的耐藥問題也令人頭疼。或許人們可寄希望于更精準干預,但理性反思早已登上頭條。人們?nèi)找嬉庾R到:純以高科技干預(即便是精準的),已不可能從根本上杜絕目前多數(shù)尷尬的健康及疾病(尤其是慢性病)難題。同時,因醫(yī)療干預過度還帶來一連串新的醫(yī)學痼疾:如多數(shù)靶向藥嚴重的副作用令人望而生畏。這些,業(yè)內(nèi)外的吁請及批評已不絕于耳,無需贅述。很顯然,現(xiàn)代醫(yī)學需要“突圍”,而不只是依賴“征服性干預”之一隅。
其實,近年興起的人道醫(yī)學、治療性(心理)教育、敘事醫(yī)學等,都可以看作是現(xiàn)代醫(yī)學尋求“突圍”之努力。盡管這類趨勢都有向后看、向傳統(tǒng)學習之旨趣,但都是奮發(fā)掙脫過分依賴“征服性干預”強勢羈絆之努力。
5 兩類易趣的應對模式
人們公認“醫(yī)學是一種回應他人痛苦的努力”,然怎么回應痛苦,卻方法手段眾多,各有短長優(yōu)劣,且常大相徑庭。而從哲理層面,也許我們可把各類回應(應對)之策進行高度概括。而不少學者最終概括為兩大類。
例如,1995年曾因?qū)憽墩l來養(yǎng)活中國人》而惹得中國人不善待的美國學者、世界經(jīng)濟觀察所所長布朗(L·Brown),2003年又寫下《B模式,拯救地球延續(xù)文明》,推崇類似中國傳統(tǒng)的、量入為出、有所節(jié)制(一如《素問》前幾章所闡發(fā))的傳統(tǒng)生活模式(布朗稱為“B模式”)。他認定世界上應對模式可分兩類:“人類的”和“自然的”——“人類的”指流行于當今主流社會(典型如美國)、以征服/改造為宗旨、貪得無厭并違背生態(tài)的行為模式,他稱其為“A模式”;認為沿襲A模式,文明將遭滅頂之災,人類難以為繼;他痛心地說“人類一直在典當未來”,“我們不知道還剩下多少時間,大自然在給地球掐表,但我們看不見這個秒表的表現(xiàn)”[3]。“自然的”則體現(xiàn)為回歸本然、有所克制、對原樣的“最大保護”,在給定條件內(nèi)盡可能達到大而多樣化的有機結(jié)構(gòu),以恢復協(xié)同共生。這才是世界真正的未來。作為環(huán)保主義杰出代表,布朗發(fā)展了羅馬俱樂部觀點,在世界激起了巨大反響;在中國也廣受關(guān)注和好評。
類似的,北京大學樓宇烈教授的見解如出一轍。他是在討論中國哲學特點時區(qū)分出“自然合理”與“科學合理”兩大類[4]:后者是受西方影響產(chǎn)生的,認定“只有科學才能合理”,故汲汲于“尋找到事物的本來面貌后……要去掌控自然,去改造這個自然,去改變事物本來面貌”,樓宇烈對此持保留態(tài)度。而“自然合理”主張“凡是合理的必然是自然的,凡是自然的必然是合理的”。此自然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本然。“就是合乎事物的本來面貌,要尊重事物的本來面貌”;“只有根據(jù)事物的本來面貌去做才是合理的,任何違背事物的本來面貌去做,都有問題,是不合理。”
樓宇烈教授不只是在討論生態(tài)/環(huán)保等問題時做此論述的,更是就中西方精神思想實質(zhì)而言的。其實,類似看法似已成為研究中西方思想史的共識。如石海兵等[5]以“天人合一”、“順應自然”與“征服自然”作為中西方自然觀的最大易趣之處。曹孟勤等[6]認為西方科學技術(shù)之思路是“改造”,西方醫(yī)學重在“征服”,“征服”及“改造”都是超越自然的;并認定按西方模式,隨著科技/醫(yī)學的發(fā)展,人類將無所不能。但實際上這種模式只適合處理線性的簡單問題,遠非解決所有難題之良策。故主張要從西方的“征服自然的自由,走向生態(tài)自由”。后者其實是對注重本然的一種高層次回歸及升華。
筆者看來,不同應對之策背后,核心差異在于是否承認并敬畏自然/生命,且認定其是有智慧的;此智慧遠在人類目前所理解之上,故需學會遵奉!科學探索目的之一是努力發(fā)掘這類智慧或機制,為人所用,從而企盼進入“無為無不為”境界。而不是刻意狂妄地人為改造它,重建它。
6 慢性病:尤需兩端切入,合理適度掌控
很顯然,稱“科學合理”、“自然合理”模式也好,“自然”、“人類”應對也好,既然是歷史發(fā)展中逐步形成的,就各有存在的合理性,各有長短優(yōu)劣,各有最適范圍及適用邊界和局限性。而在醫(yī)學臨床筆者主張“要在兩者間保持必要張力。”并認為“也許,對急性病的積極干預性治療,甚至矯枉過正,付些代價,可以理解原諒。但慢性病則不然!不管從哪個角度,慢性病的過度治療都有違底線,屬不契合其理的魯莽行為。”[7]故在慢性病領(lǐng)域更應擅長運用“自然合理”應對模式。
由于西風東漸,人們迷信“科學合理”已成時弊,往往本能地排斥“自然合理”應對模式。梳理明晰后一模式意義所在,似乎十分關(guān)鍵。
筆者曾與兩代心血管權(quán)威/院士有交往,都是資深的西醫(yī)臨床專家。年老的70多歲時已被確診為冠脈狹窄,需安裝支架,但臨床癥狀并不明顯。他決意奉行“自然合理”模式為要,以慢跑、上下樓梯、控制飲食等為主,保守治療,輔以定期復查。十多年過去了,他一切都好。另一位50多歲的心血管院士,筆者曾引用過他的觀點:“若心臟50%狹窄,原則上無需放支架,強調(diào)‘這是鐵律’;狹窄75%時如沒有癥狀,仍不建議放支架;認為只要把危險因素控制好,嚴重狹窄是有可能消失的”[7]。
筆者臨床專注腫瘤,對兩套應對模式都頗為信奉,認為就像左右手一樣,都有不可替代之意義,問題在于如何合理適度地運用。不久前,應即將召開的“醫(yī)療干預與人體自然力的保護與扶植”學術(shù)會議之邀,寫下了“‘標本緩急’視域下應對癌癥的人為干預及自身修復辯證關(guān)系之解析”一文。文中借案例對照法,比照三組案例——病種/病理/病期均相似,且有可比性——一組為抽煙后的晚期肺癌,都是某機構(gòu)領(lǐng)導,且是前后任,均沒法手術(shù);一組是類同職務(wù)的胰腺癌,一位手術(shù),一位因不知情且同時被確診為多個癌而無法手術(shù);最后一組是女性透明細胞類型卵巢癌,病理/病期一致,都做了手術(shù)和化療。這些患者都接受筆者的中醫(yī)藥治療,差異只在于比照中一方創(chuàng)傷性療法結(jié)束后,堅定不移地恪守“自然合理”之對策,從容坦蕩地生存著;另一方雖也認同“自然合理”,但總認為缺失了重要“殺手锏”,時不時地追加更積極(同時也是創(chuàng)傷性)的醫(yī)療干預手段(如不斷地增加靶向治療、化療等),認為這樣做可以更保險。但幾年后的結(jié)局卻令人驚愕和唏噓不已,后三者都很尷尬,幾乎兩三年后都離世了;而前三位卻都活得很好。如晚期肺癌患者沒用靶向治療,最后因高齡而亡,活了16年。這些,耐人尋味!折射出對包括難治性癌癥在內(nèi)的慢性病,“自然合理”為主之對策,自有其相當?shù)钠平怆y題之效用。
筆者的學生曾對臨床4萬多例癌癥患者數(shù)據(jù)進行總結(jié),得出相同結(jié)論。且即便對最兇險的癌種也一樣。例如,博士們聯(lián)合做的系統(tǒng)總結(jié)提示:在筆者診治過的數(shù)千例胰腺癌患者中,百余例晚期患者沒法進行創(chuàng)傷性治療(即無奈地放棄“科學合理”對策),僅以中醫(yī)藥為主,統(tǒng)計時活著的66例,一年生存率53%,三年生存率20%,五年生存率10%。而國外權(quán)威數(shù)據(jù)表明,未行手術(shù)的胰腺癌患者,一年生存率為0%[8]。
眾所周知,今天慢性病已成為最主要的醫(yī)學難題。而對諸多難治性慢性病,經(jīng)驗豐富的中醫(yī)師都會有得心應手之體驗。故只要不心存芥蒂地客觀看問題,以守護及增進自我內(nèi)在機能(自愈力)為要旨的一整套操作,是中醫(yī)學真正的臨床優(yōu)勢(尤其是慢性病)所在。故有“慢性病找中醫(yī)”之坊間定見。這也是中國民眾至今仍熱愛中醫(yī),有難治性病癥好找中醫(yī)的歷史積淀及社會根基所在。
確切地說,作為中醫(yī)學真正特質(zhì),關(guān)注個體自我內(nèi)在之力,努力加以呵護,促使其盡可能回歸本然——是其歷史優(yōu)勢及活潑的盎然生機所在,且具有進一步拓展之現(xiàn)實意義。如能妥善地協(xié)調(diào)“科學”與“自然”兩大模式,像每個人得心應手地運用自我左右雙手一樣,那么,人類對于許多困頓世界的難題,就多了一套或能加以破解的模式。
7 推廣之:凡事該出左手出左手
審視當今社會,人們驚嘆這是一個高科技及深層次危機蜂擁而至、資訊/信息爆炸卻多半無用的復雜時代:互聯(lián)網(wǎng)、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生態(tài)/資源危機、核能力等都具多重特性——一如人工智能,既能導向人類進一步解放,但又將加劇貧富兩極分化,甚至可令人工智能操控人;核能力開發(fā)既可擺脫對石化資源依賴(可控核聚變),但徹底毀于核戰(zhàn)爭陰影也揮之難去。幾十年后,人類及醫(yī)學將走向哪里?這是須未雨綢繆做出思考的哈姆雷特式難題。而挖掘源自中國傳統(tǒng)精神,在中醫(yī)“正氣說”等中得到充分彰顯的、注重自然本身具有的智慧及內(nèi)在能力,講究協(xié)調(diào)、適應、共存、共榮等,至少是非常值得重視的一大類應對之策。努力就此做出彰顯,將對未來人類(不僅僅醫(yī)學)或許是一大幸事。當然,在此過程中,需強調(diào)與干預性的征服及替代對策等相互補充,相得益彰。就像是嫻熟地運用每人自己的雙手一樣,該出左手時出左手!
——中醫(yī)藥科研創(chuàng)新成果豐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