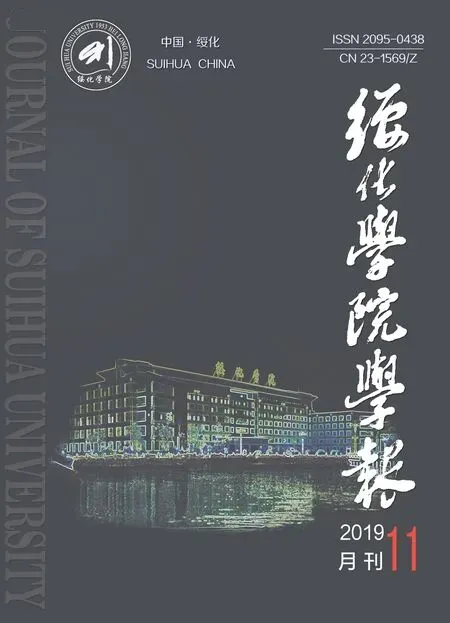柳宗元貶柳期間境遇研究
趙曉芳
(淮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旅游學院 安徽淮北 235000)
柳宗元(773—819年)是中唐時期杰出的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唐順宗時期,柳宗元因參與王叔文、王伾倡導的政治革新運動失敗,被貶至永州,元和十年二月(815年)被復召回京。此時,反對王叔文一派革新的宰相武元衡仍掌握朝中大權,“諫官爭言其不可,上與武元衡亦惡之。”[1](P7708)“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1](P7709)直至“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時年四十七”,[2](P4214)未能再重歸于廟堂。其在柳州雖僅四年,但創作詩文百余篇,占《柳宗元集》近1/5。其時柳州文教昌明,政績斐然,對柳州百姓之貢獻不勝枚舉。
一、元和時期的柳州
柳州,即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位于廣西中部。西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漢武帝在此設置潭中縣(屬郁林郡),即為柳州之開端。此后,數易其名。開皇十一年(591年)隋文帝將潭中縣改為桂林縣,后又改為馬平縣。天寶元年(742年),唐玄宗將馬平縣改名為龍城郡,屬嶺南道。乾元元年(758年),唐肅宗使龍城郡復名柳州,并沿用至今。據《元和郡縣圖志》載:“柳州,龍城。元和戶一千二百八十七,鄉七。”[3](P926)地處嶺南道的南部,遠離京城,東南為駕鶴山,西南為仙奕山,崇山峻嶺隔絕了其與中原的直接交流,加之又是少數民族(以壯族、瑤族、苗族和侗族為主)聚集地,由此形成了別具一格的自然、文化與政治環境。
就自然環境而言,柳州地處嶺南,唐人多以為瘴鄉蠻俗之地。南方地卑且土薄(地卑,故陰氣常盛;土薄,故陽氣常泄),[4](P6)使得嶺南一年中暑熱過半,晨昏多霧,春夏雨霪,一日之內天氣變化多端。《馬平縣志》載:“五嶺以南,號曰炎方……若城依巖谷,或近卑濕,崎嶇厄塞,有近午方見日著。至若蠻溪、僚峒,草木蔚薈,虺蛇出沒,江水有毒,瘴氣易侵。”[4](P6)清代時柳州自然環境仍如此惡劣,可想而知在將近一千年前唐朝的狀況。柳宗元在赴任柳州途中所作《嶺南江行》亦云:“漳江南去入云煙,望盡黃茆是海邊……射工巧伺游人影,颶母偏驚旅客船。”[5](P466)描述了嶺南的奇異景象漳江、黃茆、射工、颶母等,足見當時嶺南地區的荒涼落后與環境艱險。
就文化氛圍而言,嶺南地區崇山峻嶺的天然阻隔使其文化發展具有一定的獨立性,與中原文化存在較大差異,呈現出落后、封閉的特性。《馬平縣志》載:“但拙于治生,鮮有蓋藏……語言、服食、婚姻、喪祭之事,與漢民迥異。至雞骨占年,鵝毛御臘,信鬼崇巫,其積習也。”[4](P19)柳宗元任刺史后在所作《柳州復大云寺記》中提及:“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偭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孽。”[5](P310)可見,柳州之地鬼神巫術盛行,教化仁義不得伸張,風俗習慣很是落后。故其在《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中寫道:“惟柳州古為南夷,椎髻卉裳,攻劫斗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5](P54)
就政治環境而言,由于嶺南地區地處窮荒、環境惡劣且文化落后,便成為被貶官員的去處之一。唐朝對貶官處置十分嚴酷,“諸刺史、縣令、折沖、果毅,私自出界者,杖一百。”[6](P185)規定官員不得擅自離開貶流之地,違反規定者,處罰嚴酷,常有性命之憂。憲宗元和十二年(817年)四月,明確規定了對擅自離開州縣官吏的處罰,“應左降官、流人,不得補職及留連宴賞,如擅離州縣,具名聞奏。”[7](P546)所以被貶官吏只能恪盡職守,積極參與地方事務的管理。如唐貞元十五年(799年)長安人韋丹到廣西任客管經略使兼容州(今廣西容縣)刺史,他“教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民貧自鬻者贖歸之,禁吏不得掠為奴……教種茶、麥,仁化大行。”[8](P7)從而促進了容州的發展。
二、柳宗元被貶柳州時的生活環境
柳宗元于元和十年(815年)六月到達柳州,元和十四年(819年)去世,年僅47。從永州再度被貶至柳州,柳宗元在柳州生活的期間,要面對比永州更為惡劣的環境。
(一)身體狀態。嶺南地區“陰森野葛交蔽日,懸蛇結虺如蒲萄”,[5](P458)自然環境十分惡劣。柳宗元在進入嶺南道,前往柳州的途中給韋珩寄了一首長詩,其中提到“炎煙六月咽口鼻,胸鳴肩舉不可逃。”[5](P458)以此來述說自己周身疲乏,忍受不了在炎熱氣候趕路卻又逃脫不了的狀態。初到柳州后,柳宗元還生了一身的疔瘡,雖然死里逃生,但不久又染上了一種劇毒。《寄韋珩》提及“奇瘡釘骨狀如箭,鬼手脫命爭纖毫。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攪腹戟與刀。邇來氣少筋骨露,蒼白瀄汩盈顛毛。”[5](P458)可見,柳宗元被貶柳州后虛弱的身體狀態。元和十二年(817年),柳宗元在《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中以“病來方外事多違”[5](P468)向浩初上人說明因自身多病而未能應邀前往觀仙人山。《柳州寄丈人周韶州》中寫道“越絕孤城千萬峰,空齋不語坐高舂。印文生綠經旬合,硯匣留塵盡日封。”[5](P465)表明柳宗元到柳州后因身患疾病而終日臥床不起,官印因久不用而生綠,硯臺因久不磨而積塵,從側面反映了柳宗元在柳州期間身體虛弱、多病纏身的情況。
(二)戚屬情況。柳宗元到達柳州后,不僅身體多有不適,且陪伴在身邊的親人亦寥寥無幾。關于柳宗元子嗣的情況,韓愈《柳子厚墓志銘》記載:“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9](P182)此文雖寫于柳宗元逝世之后,但我們也可以了解到柳宗元在柳州期間,其孩子們仍很年幼,需要有人照料。
柳宗元的追隨者們情況也不樂觀。其堂弟宗直自柳宗元永貞革新失敗被貶后,歷經永州、柳州十余年伴隨其左右,然到達柳州僅二十天后,于七月十七日因病去世。柳宗元在《祭弟宗直文》和《志從父弟宗直殯》云:宗直生“剛健好氣”,“作文辭,淡薄尚古,謹聲律,切事類”,[5](P135)“汝生有志氣,好善嫉邪,勤學成癖,攻文致病,年才三十,不祿命盡。蒼天蒼天,豈有真宰?知汝德業,尚早合出身,由吾被謗年深,使汝負才自棄。”[5](P441)表達了對宗直英年早逝沉痛的惋惜、悲痛,也悔恨由于自己遭貶而連累宗直,使其有才而無用武之地。另一親屬宗一隨柳宗元至柳州后,于元和十一年(816年)赴江陵,到湘鄂之地安家。為此柳宗元作詩文一首《別舍弟宗一》:“零落殘魂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5](P468)表達了其與宗一的手足情深及依依不舍之情。
隨柳宗元來柳的追隨者中,宗直早逝,宗一遠去,只留盧遵一人。“葬子厚于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9](P182)“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有終者。”[9](P182)盧遵陪伴柳宗元直至其病歿,且負責辦理喪事、經管家產,足為柳宗元之摯友也。
(三)交友情況。柳宗元一生交友甚多,與官員、文人志士交往密切,與僧侶也有往來。其在柳州期間所作詩文中不乏與舊友來往詩文的情形,其中有兩人是不可不談的,即劉禹錫和韓愈。
柳宗元與劉禹錫在思想上有共識,在文學上也有同好,所以二人很早就成為知交,后來又共同遭遇貶謫,更是患難出真情。在赴任柳州途中,柳宗元以“二十年來萬事同,今朝岐路忽西東。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為鄰舍翁”[5](P464)來表達其與劉禹錫之間難分難舍的情誼。柳宗元在柳任職期間也有許多作品是贈給劉禹錫的,如《重贈二首》《疊前》《疊后》等,足見二人情誼之深厚不移。甚至柳宗元在臨死之前還寫信給劉禹錫,委托他幫忙編撰自己全集的事宜。
柳宗元的另一摯友是韓愈,其雖與柳宗元在政見、文學主張等方面不盡一致,但并不影響二人成為至死不渝的朋友。柳宗元病逝前將自己的子女托付給劉禹錫和韓愈,足見其關系之親密、感情之深厚。柳宗元逝世后,韓愈為緬懷好友、寄托哀思,親自寫下《柳子厚墓志銘》。三年過后,又為紀念柳宗元而建的羅池廟宇題寫碑文《柳州羅池廟碑》。
此外,柳宗元在柳州期間與僧侶來往亦十分密切。根據《柳宗元集》記述,柳宗元曾與僧侶賈鵬、方及、浩初、談康、令寰、退思、道堅等有直接交往。[10](P2)其到柳州不久,賈鵬便前來拜訪。柳宗元寫了《酬賈鵬山人郡內新栽松寓興見贈》二首來酬和賈鵬所贈的詩《郡內新栽松寓興》。浩初和尚與柳宗元在永州時已交往密切。其云游南方,便專門從臨賀到柳州看望柳宗元。他們一同登山望景時,柳宗元寫下《與浩初上人同看寄京華親故》,表達自己的悲苦愁緒及思鄉懷友的復雜心情。在《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詩中不僅表達了自己不能同去的遺憾之情,也體現了作者對超凡脫俗的出世生活的羨慕。柳宗元與僧人的交往以及其對佛學的接近,可能是其減輕精神苦悶、擺脫沉重憂患的一種方式。
綜合以上,柳宗元在柳州期間身體孱弱、多病纏身,既有年幼的孩子需要撫育,又無摯友陪伴、傾訴,仕途上的郁郁不得志都使他的內心承受著莫大的痛苦。
三、柳宗元被貶柳州后的心理境遇
“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外行。”[5](P463)柳宗元滿懷希望回到長安,不料等待他的卻是再度出貶,從而成為其心理境遇的一大轉折點。在永州時他仍存有一絲北上的希望,但經過一詔一貶,其僅存的希望破滅了。再次貶謫對柳宗元來說無疑是一種精神的流放,其心理境遇可歸納為如下特點。
(一)遠離政治中心的被拋棄感。貞元二十一年(805年)九月,柳宗元被貶永州,雖然也是孤寂難耐、環境惡劣,但當時柳宗元年紀較輕,政治前途尚存希望。然元和十年(815年)再貶柳州時,他已疾病纏身,希望渺茫。如果說柳宗元在永州時尚存一絲幻想,盼望能再次進入朝廷實現政治理想,從而表現得較為積極樂觀,那么柳宗元在柳州則表現出更深的被拋棄感。其在永州時寫下《江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5](P484)借寒江獨釣的漁翁形象來抒發自己孤獨的心情,但也表達出即使在寂寞冷清的環境中也仍要堅持自我的心志。此后,官場失意、貶謫南夷,回京機會渺茫,其在柳州期間所寫:“宦情羈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轉迷。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5](P468)借著南方特有的天氣現象,使自我與景物交融,淋漓盡致地抒發了凄黯迷惘的心情,表達其無盡的憂愁與被拋棄感。
(二)失去自由的被拘囚感。貶謫詩人的被拘囚感主要是由三種因素決定的:一是自然環境的包圍困鎖;二是朝廷律令的嚴格限制;三是謫居時間的久長。[11](P4)當時的柳州遠離政治中心,路途遙遠且交通不便,如柳宗元托銅魚使寄書信時所描述“行盡關山萬里余,到時閭井是荒墟。附庸唯有銅魚使,此后無因寄遠書”[5](P470)以及“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5](P465)的哀怨與感慨。其在《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中也以“春風無限瀟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5](P472)來表達自己渴盼自由而得不到的無奈。
被囚之感常常在思鄉之時又變得更為強烈,每當思鄉之情涌上心頭,柳宗元都恨不能“若為化得身千億,散上鋒頭望故鄉”[5](P459)。其在《登柳州峨山》更是直抒胸臆:“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州。”[5](P466)柳宗元本是懷著思鄉之情登峨山望長安,以排解心中憂郁,但滿眼的景象卻不能遠及長安,不由發出了“西北是融州”望鄉無期的哀嘆。
柳宗元在永州時并未心如死灰,仍希冀著有朝一日能重返故土,所以那時的作品常能在哀怨中看到對未來的希冀和偶有的生活情趣。反觀詩人在柳州,這種生活情趣卻變成了“若為化得身千億,散上峰頭望故鄉”[5](P459)凄厲的哀怨與絕望。這種變化處處流露出柳宗元在柳州時期更為強烈的拘囚感,心理上的壓抑和處境上的無自由感,愈發沉重,難以自拔。
(三)一時的生命荒廢感。柳宗元在政治上再受挫折,處境上的被拋棄感及拘囚感使他產生懷才難施的生命荒廢感。他向好友韋珩述說:“圣恩倘忽念行葦,十年踐踏久已勞。幸因解網入鳥獸,畢命江海終游遨。愿言未果身益老,起望東北心滔滔。”[5](P458)表達被貶蠻荒之地的孤苦難熬之感。
雖然荒廢感強烈,卻難以掩蓋柳宗元要以負弩前驅的精神去治理柳州、造化一方的堅韌決心。他在到達柳州不久給劉禹錫寫的贈答詩中以“負弩啼寒狖,鳴枹驚夜狵。遙憐郡山好,謝守但臨窗”[5](P466)來鼓勵自己的好友兼戰友要有所作為。雖然與當地少數民族在生活習慣、語言、風俗等方面存在差異,但他仍表達了“欲投章甫作文身”[5](P467)的意愿,要克服困難與當地百姓一起推行政務的決心。
柳宗元的再貶之地是較永州更偏遠荒蕪的柳州,此時被拋棄感和拘囚感更為強烈,甚至促使其產生了一時的生命荒廢感。但柳宗元在柳州亦并非一味消沉逃避,他仍堅持并努力實踐“吏者民役”“澤加于民”的吏治主張,盡心盡力為柳州百姓造福,給柳州留下了珍貴的財富。
四、柳宗元被貶柳州期間的作為
柳宗元從永州再被貶到柳州,再一次受著沉重的打擊,雖然滿腔悲憤、愁腸寸斷,但他仍認為“不可自薄自匿以墜斯時”[5](P376),只要對造福百姓“茍有輔萬分之一,雖死不憾”[5](P376)。雖遠離廟堂,不能在政治上施展遠大的抱負,但他卻以“從此憂來非一事,豈容華發待流年”[5](P466)來表明自己不會坐以待日、虛度年華。加之他任柳州刺史,主政一方,與在永州時不得干預政務的閑職不同,故到達柳州后,柳宗元努力實踐其“利安元元”的理想。
(一)為官清廉,福澤百姓。柳宗元在柳州任職的四年里,德政累累,兩袖清風。其初到柳州,便“蒞政方初,庶無淫枉”,[5](P437)誓要“廉潔自持,忠信是仗”,直到其去世后僅留托付給好友劉禹錫的遺文稿一束,至于“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5](P458),子女也只能委托其好友來照顧,如此清風亮節,足以彪炳千秋。
韓愈寫下《柳州羅池廟碑》來頌揚柳宗元任柳州刺史的政績,云其“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9](P182)以禮法經治百姓,“于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9](P197)韓愈稱之“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9](P198)足見其對當地百姓及地區的深遠影響。
此后,歷代柳州地方官員對柳宗元的政治表現心懷憧憬,紛紛撰寫詩文,既為歌頌,也為標榜。如崇寧五年(1106年)進士黃翰(后任柳州知府)在《祭柳侯文》中寫道:“一麾出守,惠此南方。龍城雖遠,勿敢怠荒。動以禮法,率由典常……生能澤民,死且不亡。”[5](P567)柳州人民也傳頌著歌謠“柳色依然在,千株綠拂天”來表達對柳宗元的感激及懷念之情。
(二)釋放奴婢,以文化民。柳宗元到達柳州之前,柳州“民貧,以男婦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9](P197)典賣平民為奴的現象非常普遍。面對那些因負債無力償還而成為私奴的人,柳宗元根據元和四年(809年)、八年(813年)憲宗的兩次特旨來推行釋奴政策,即用以工償債的方法,恢復那些奴隸的平民身份。
柳宗元在《寄韋珩》一詩中云:“到官數宿賊滿野,縛壯殺老啼且號。”[5](P458)《柳州復大云寺記》亦載:“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偭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5](P310)描述了柳州當時“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的社會風氣。面對此種情形,柳宗元以“興孔子之道”為己任,“饑行夜坐設方略,籠銅枹鼓手所操”,[5](P468)不僅重修崩塌了的孔廟,撰寫碑文來大力弘揚儒家思想,而且勇于提掖后進,“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5](P361-362)以使百姓能“人去其陋,而本于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5](P54-55)老百姓經過慢慢積累,愚昧落后的觀念遂逐漸消弭。
(三)身體力行,重視生產發展。柳州人本不飲井水,傳統的習慣是背著瓦罐去江邊舀水飲用。“始州之人各以罌臬瓦負江水,莫克井飲。”[5](P241)“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涂則滑而顛。”[5](P241)足見取水之艱難不易。柳宗元親自組織挖井,打破百姓“恒為咨嗟,怨惑訛言,終不能就”[5](P241)的狀態,以造福后人。柳宗元亦將“疇肯似于政,其來日新”[5](P241)的利民精神推廣到其他方面,引導人們從事農林生產,親自在荒地上種植柑樹和在柳江河畔種柳樹,并寫下詩文。此外,柳宗元還大力指導發展牧副業、修路等,使柳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
結語
元和十年(815年)柳宗元在滿懷希望中從永州被貶至更為偏遠的柳州,遭受了政治上的又一次打擊。在柳州期間,他一方面忍受著暑熱過半的氣候和疔瘡等疾病的折磨,另一方面又面臨政治上的失意及與親朋好友的分離。在此背景下,柳宗元生出些許遠離政治中心的被拋棄感、失去自由的被拘囚感以及一時的生命荒廢感都是在所難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其在柳州雖僅四年,仍能在惡劣與孤寂的環境中堅持“輔時及物”“利安元元”的政治理想與抱負,為官清廉,釋放奴婢,以文化民,發展生產。柳州的艱難際遇無意中成為柳宗元文學創作的一大源泉,促使其留下了許多傳誦至今的詩文,時至今日人們稱之為“柳柳州”,足見柳州際遇對其人生影響之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