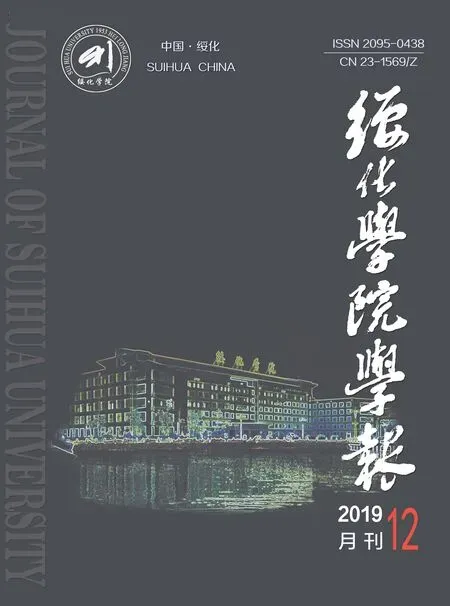《活著》:小說與電影的對比性解讀
張少嬌
(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 遼寧大連 116081)
一、生命寄寓載體的置換
《活著》為作家余華帶來了極高的榮譽,獲得了意大利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最高獎項、法蘭西文學和藝術騎士勛章等多種獎項。并且每年都以一個驚人的數量在加印,成為了當代純文學文本的一個神話。張藝謀在1994年將之改編成了電影搬上了大熒幕,電影《活著》引起了極大的關注與討論,也為張藝謀帶來了一系列的榮譽,如第47屆戛納國際電影節人道精神獎、第48屆英國電影學院獎最佳外語片獎、全美國影評人協會最佳外語片等獎項。但是對小說和電影做一個對比就會發現,電影對小說做出了許多的改動。
在諸多的改編的細節當中,生命寄寓載體的置換是張藝謀對《活著》改的最重一筆。在小說中,福貴賴以活著的是土地。而在電影中,福貴謀生是靠著皮影戲。余華給福貴的身份是農民,這個在中國社會中最傳統、最普遍的身份,恰恰有著這個民族最本質、最深刻的特性。而張藝謀塑造了一個藝人福貴,皮影戲雖然伴隨了福貴的一生,成為電影中最重要的意象。但這個生命寄寓載體,消解了小說文本中的普遍性。
張藝謀是一個有著國際夢想的導演,在他的作品里能夠看到醒目的東方元素,這既是他個人一種深厚的東方情結,也是向世界遞出去的一張東方名片。他的作品里經常能夠看到放大的東方元素,比如:《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的點燃又熄滅的紅燈籠;《菊豆》中那口四四方方、深不見底的染井;《紅高粱》中豪放的祭酒儀式等等。它們構成了一道獨屬于張藝謀的“東方奇觀”。皮影戲帶著濃烈的民族色彩在電影《活著》中貫穿始終,甚至提升為福貴的生命寄寓載體。
張藝謀精細雕琢了皮影戲這個意象。在電影開場時就埋下了伏筆,賭場里,福貴嫌龍二的皮影班子戲唱的差,上場一亮嗓子便博得了喝彩,這就為后來皮影戲成為其謀生手段合理化。故而,在福貴輸光了家產去找龍二借錢時,龍二以“救急不救窮”的說辭,不借錢而借給福貴皮影。福貴開始組織皮影班子并以此謀生,在這里就將福貴的生命寄寓和皮影戲緊緊的捆在了一起。后來被抓壯丁、給解放軍唱戲、大躍進時期為煉鋼群眾唱戲助興、文革中皮影被燒毀、存留下來的皮影箱子給外孫養小雞為結,皮影貫穿了福貴的一生。從最初福貴將皮影當作一個消遣的玩意兒,到日后福貴依賴皮影謀生,憐惜皮影,愛護皮影,整個過程是福貴將自己的生命依托一步一步加深在皮影身上的遞進歷程。
而余華原文中,福貴的生命寄寓載體是土地。小說中龍二惦記的是福貴家里的百畝良田,福貴敗落后去找龍二租了幾畝田為生。小說中的福貴過的是傳統中國農民的生活,即埋頭種地,靠天吃飯,這種穩定延續了千百年來傳統中國農民的生活方式。小說最后福貴和那頭老牛緩緩的走在田地里的圖景,是整個中國千年農耕社會的一副縮影。土地所承載的厚重感是中國人領悟生命的經驗方式。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說:“直接靠農業來謀生的人是粘著在土地上的。”[1](P9)土地是傳統農民用以謀生的工具,也是財富的象征。在很大程度上,農民將自己一生的心血傾注在土地上,久而久之農民和土地之間就形成了極為緊密的依附關系。“即便是在農業勞動者以理性的和經濟的方式對待土地資本的時候,他依然對土地保持著深厚的情感,在內心把土地和他的家庭以及職業視為一體,也就是把土地和他自己視為一體。”[2](P61)這種傳統的農民對土地的依附關系和深刻的眷戀之情,正是中國這個農業大國千百年來的一種歷史傳統。
生命寄寓載體的置換背后體現出的是相異的敘述主體。余華刻畫的福貴,是這片土地上最尋常的一個人,他像無數的農民一樣依戀著腳下的土地。可以說,余華將福貴這個人物形象涵蓋到了每一個中華兒女,福貴的命運,是中華民族的縮影;福貴的隱忍,是中華民族的隱忍。千百年來,這片土地上的人,都在按照福貴的方式“活著”。這是余華用“土地”這個意象的匠心。而張藝謀講述的福貴,更大程度上是一個時代的親歷者和見證者,他具象化到了一個個人福貴。皮影戲則是一個符號,它只能承擔起一個福貴個人的生命,再也不具備土地這個意象所具有的深廣性。但皮影戲卻又是一個鮮亮的符號,警醒著所有的觀眾,這個電影發生在怎樣的一片土地上。
“依照特呂弗的觀點,所謂電影作者論的第一核心要旨,便是電影創作過程的絕對導演中心。一部影片從題材的選取到剪輯制作完成,導演應成為整個過程的絕對掌控者及其靈魂。”[3](P47)為了實現絕對導演中心,首要的就是能“編導合一”。電影《活著》完全是張藝謀的敘述,他按照自己的表達需要重新寫了《活著》這個故事,完成了二度創作。張藝謀生于1950年,“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些政治運動正值他的少年時期,成為了他深刻的青春記憶。而余華生于1960年,政治運動于他而言是朦朧的記憶和上一輩人講述的故事。他們對政治運動的記憶與認知的敏感之不同,造就了文本與電影中諸多細節的差異,也指向了最大的不同——生命寄寓的載體。所以,在電影中就看不到余華對土地和農民之間深刻性的思考,而多了政治災難對民族文化沖擊的沉思,這是絕對導演中心和作家中心論的一次碰撞。相異的敘述主體在講述同一個故事時的側重不同,折射出的是對生命寄寓這個深刻命題的相異體悟。
二、死亡敘述的差異
死亡,是張藝謀對小說文本的另一個極大改動。小說中福貴最后唯剩一頭老牛與之相伴左右,親人以種種不同的方式死亡,離開了他“活著”的世界。而電影中,張藝謀留下了福貴的妻子家珍,女婿二喜,外孫饅頭(小說中名字是苦根),一家人其樂融融的吃飯。將悲劇的結尾改成了一個看起來溫馨的大團圓結尾。同時,在電影中對福貴的兒子有慶和女兒鳳霞的死亡做了一些改動。
電影中遵循了小說開始的死亡敘述線,對福貴父親和母親的死沒有做出過多的改動。從福貴兒子有慶的死開始,張藝謀開始了他的一系列死亡敘述。小說中的有慶是為了給縣長夫人獻血,幾乎被抽干了血液而死。在電影中,有慶是被春生的車撞倒的墻砸死的。電影中保留了春生和福貴的戰友經歷,增加了春生是福貴皮影班子里的成員這一情節,有了一起成長和患難與共的經歷,使福貴和春生之間的友情更為深厚,這為有慶的死加劇了倫理層面的悲劇性。但是,卻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小說中,有慶死亡帶有的一種命運無常的荒誕指向。鳳霞在小說和電影中都是難產之死,但電影中將這個死亡的原因歸在了文化大革命中下放了知識分子,醫院里沒有醫生,紅小將奪權卻不能救治病人。死亡的敘述就帶上了鮮明的時代印記和政治話語。鳳霞的死,在電影中被歸咎為政治災難,加重了時代的荒誕性對人生之脆弱性的摧殘。同時,在小說中鳳霞自然難產死亡的一種人世無常、天地不仁的意義指向被很大程度的消解,人在命運面前的無力感縮小。
張藝謀沒有讓家珍、二喜和饅頭(小說中名字是苦根)死亡,這個結局是對小說文本最大的改動。張藝謀做出這些改動,首先出于需要尊重電影是一種視聽語言,在創作的過程中就必須對預期受眾、現實受眾和潛在受眾有一個提前的判斷。將一個長篇小說的文本壓縮在兩個小時的電影中完成,實際上是電影容量和小說容量的試驗。不僅要在故事的情節上有所刪節,更要在短時間內抓住受眾的眼球,勢必不能讓電影過于沉痛,不能將電影做成死亡的展覽,這對于受眾的心理是一種極大的負擔。對此張藝謀曾經就說過:“我不希望搞出來的東西太沉重。”[4]電影結局變成了溫馨的走向,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減弱了文本講述苦難時帶有的沉重感,但是更加符合電影這種藝術樣式的內在要求。張藝謀選擇留下的這三個人物形象對福貴的生命意義非常重要,家珍作為福貴的妻子陪伴了他所有的苦難歲月,二喜作為福貴的女婿是逝去的兒子和女兒的寄托,饅頭作為福貴的外孫則是一個希望的象征。保留了一家三代的家庭模式,也保留了背負著各個階段苦難的人,在一起能經歷的、為數不多的美好。
從這個意義來看,電影在講述“活著”這個故事時候,留下的是對活著的希望與期待。這就與小說文本的指向截然而立。余華為小說命名為“活著”,但是在文本中,講述的是一個接連一個的死亡。不僅僅是福貴的親友接連死去,甚至包括龍二的死,春生的死,戰爭中一夜死去的數千名傷員。文本雖然給讀者的是一系列生的毀滅,卻是在這對生的毀滅、死的描摹中,去表現一種“活著”的本質,一種對于苦難的強大的承受能力。余華表達過他對“活著”的理解,“作為一個詞語,‘活著’在我們中國的語言里充滿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來自于喊叫,也不是來自于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5](P4)在小說里,看到的是一副活著比死更艱難的畫卷,生較之于死的異乎尋常之難,凸顯的是活著的堅韌,活著的深刻。余華不需要一個溫馨的結局給靈魂慰藉,讓疲憊奔波的心靈暫時獲得休憩。余華直接的告訴讀者,死亡是一種常態;苦難時一種常態;絕境是一種常態,唯有參透活著的哲學,才能在人生這場試煉中僥幸豁免。一旦不能領悟活著的哲學,那生命就將陷入無盡的痛苦。
對于死亡不同敘述的背后,體現出的是張藝謀和余華對“活著”這個命題的不同認知。張藝謀借助于影視這種新型的視聽語言,在電影中穿插了大量的時代信息。“文革”、“大躍進”等特殊歷史時期和皮影的關系,就是時代和福貴命運的關系。張藝謀將福貴的命運和時代的變遷聯系在一起。不難看出其中有張藝謀對歷史的回憶和思考,對民族文化經受的歷史摧殘的惋惜,對政治之于人性的打擊的一種回溯和思辨。影像之下,是張藝謀對死亡和時代、政治的感觸膠著。對余華來說,“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而不是為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6](P4)余華從容而冷靜的站在時空的遠處去描繪了福貴的一生,他充滿了死亡的一生。當死亡成為一種常態時,福貴的苦難就上升為了一種對命運無常的無力感。人在命運面前的渺小與無力,唯剩下“活著”的意志和“活著”的生活。
三、不同的敘述語言
“意大利著名電影導演、理論家帕索里尼在他的重要電影論文《詩的電影》一文中指出:電影在本質上是一種新的語言。他認為電影使用的是某種表情符號系統,這一符號系統先于語法而存在,因為世界上沒有一部形象詞典。一位電影導演必須首先創造他所需的詞匯,即選取他的拍攝對象,將其創造為自己的形象符號,而后方才進入美的創造。”[7](P3)電影作為一種“新語言”,和文字文本語言在本質上是不同的。電影更考驗導演的場面調度能力,對光影的感知,對演員情緒的把控,對背景音樂的處理,乃至對色彩的運用。每一個細節的處理都將影響到觀眾對電影的感知,張藝謀在電影的視聽語言綜合處理方面有著非常個人而又卓越的能力。
張藝謀在電影中十分注重色彩的對比性使用,這是在文字處理時難以達到的直接性視覺沖擊,紅色和黃色是他偏好的色彩。紅色代表了張揚而熱烈的情緒,秾麗的血液的象征,中華民族所特有的中華紅,這些都是紅色所能傳達出來的視覺感知。黃色這種接近土地的顏色往往有生命力的隱喻。《紅高粱》中就對這兩種色彩做出了精彩的處理。一眼望去無邊無際的野高粱地是一種蓬勃的原始生命力表征,而大紅的喜轎、大紅的新娘服乃至封酒壇子的紅色酒封,則表現出一種人的情緒的熱烈,熱烈的向往自由,熱烈的向往愛,熱烈的向往生命力。這種熱烈在《大紅燈籠高高掛》中被抽象成了一種欲望的符號,紅色燈籠懸置在色彩灰暗的高墻大院間,構成了一種對欲望的熱烈向往和對欲望的強制禁錮的對比。這種對顏色的純熟掌控能力也展現在了《活著》中,例如在有慶死的時候,黑夜里聞訊而來人群如潮水一般,黑壓壓的一片,而有慶的身上則滿是鮮紅的血,紅與黑的對比形成了強烈的沖擊。鳳霞與二喜粉刷院墻時,顏色鮮艷的標語和毛主席畫像幾乎占滿了整個屏幕,直接沖擊著觀眾的視覺感知。包括演出皮影戲時的發黑的環境、鳳霞燒皮影時的火光、鳳霞死時病床上的血跡等等都帶著張藝謀強烈的個人語言,這些是小說語言難以傳達的、為電影所獨有的視聽效果。
正是電影的這種強烈而直接的視聽效果,約束了它的審美感知,必須在一個極為短暫的時間里能夠迅速沖擊到觀眾,激發起強烈的情感共鳴,否則就面臨著觀眾走神的風險。這既是電影語言的長處,能帶給觀眾強烈的感官體驗,在短時間內大幅度調動感知和情感。但這也是電影的短板,不能在有限的時間里盡可能多的展現細節,而細節正是構成小說語言的基石,能夠給讀者以相當長時間的“余味”。張藝謀能夠運用電影語言表達他的個人情感指向,但他也不得不對原來小說中的很多細節做出割舍,惟其如此才能在兩個小時的時間內盡可能完整地講述這個故事。
張藝謀借助視聽語言完成了他的歷史性敘事,然而在影片中刪掉了那頭名字也叫做福貴的牛。小說中這頭牛是福貴最后剩下的精神寄托,在親人相繼離世之后,福貴買下了一頭垂垂暮年的老牛。人們都說這老牛看著像福貴,福貴便給老牛取名字叫福貴。這實際上是余華對富貴命運的一種隱喻性象征,福貴的一生就像這頭牛一樣,在默默的忍受,在忍受中求的生存。“活著”的常態就是忍受,這是余華對“活著”的一種認知哲學。但在電影中,這種哲學層面的深入思考,就沒有展現出來。
類似的細節還有因為饑荒鳳霞被送走,福貴幾經掙扎于思考將鳳霞要了回來。這種頗為塑造人物性格的心理成長的細節,電影藝術沒有探討到。但是張藝謀為了追求電影所應該有的娛樂性,而增加了一段小說中沒有的細節。福貴在大躍進時期每晚為煉鋼的人們唱戲助興,在之前福貴誤會了有慶,有慶端了一碗加了醋和辣椒的茶遞給福貴,福貴追著有慶滿街跑,引得眾人哄笑。這個細節的加入,一方面是為了沉郁的電影加入了一個溫馨片段的緩沖環節,另一個方面則是作為塑造人物性格的一種彌補。這一段的加入也就加深了有慶死時候的悲劇性,更能引起觀眾對有慶死亡的巨大情感共鳴。
小說通過細節塑造人物性格,通過篇幅框架歷史。余華筆下的富貴不是一個個體,他身上背負的苦難也不僅僅是一個個人的悲哀。富貴更像是中華民族這個古老的民族,經歷了滄桑巨變和苦難侵蝕,但仍然堅韌而頑強的“活著”,仍然有著對“活著”的渴望。這種苦難的隱喻是漫長的,是電影藝術在有限的時間、畫面中所不能全部容納的。電影能交給觀眾的,是那種沖擊性強而富有共鳴的片段。
結語
張藝謀和余華用不同的敘述語言講述“活著”這個深刻的人生命題,他們以自己的閱歷和思考對這個命題做了不同的答卷。借助不同形式的敘述語言能夠對一個故事產生多維度的深思,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影視改編文學的一個價值所在,但在多大程度上保留故事原型,在多深刻的意義上探討故事的立意,在多遠的距離講述這個故事都還是沒有結論的問題,仍然需要在理念和實踐的層面繼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