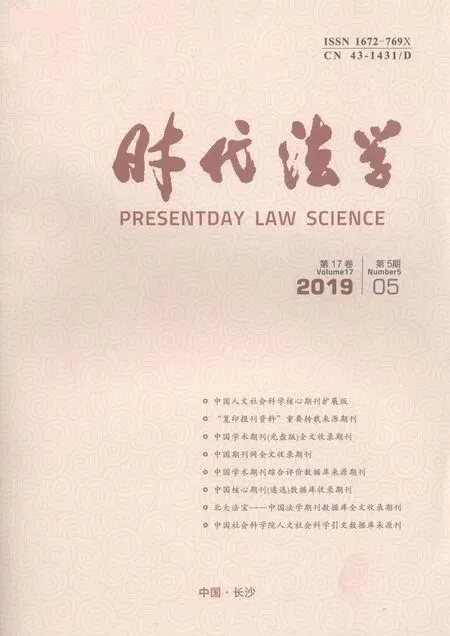無效辯護制度的正當性與建構*
楊杰輝
(浙江工業大學法學院,浙江 杭州 310023)
辯護權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重要的訴訟權利,甚至是其所有訴訟權利的總和,辯護權的保障問題至關重要(1)熊秋紅.刑事辯護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6.。對辯護權的侵害,既可能來自于公檢法等公權力,如他們干擾、阻礙辯護權行使的行為,也可能來自于辯護人,他們不盡職不盡責的辯護。但是,前者更易引起重視,而后者則更易被忽視。“法院不愿介入,檢察官見獵心喜,而被告沒有自我保護的能力,律師怠忽職守的不良代理行為成了對抗制下律師權保障的灰色地帶,其可能是影響被告權益最大的問題來源,卻是最少被著力討論的一個區域”(2)林志浩.是公平的保障還是一襲國王的新衣?——論對抗制下律師失職行為與被告律師權的保障[J]. 月旦法學雜志,2006,(10).。我國對于辯護權的保障,也更重視前者而忽視后者,辯護人不盡職不盡責而侵害辯護權的問題,已經成為我國辯護權保障的灰色地帶(3)近年來,我國出臺了一系列保障辯護權的措施,但是這些措施都是針對防止公檢法干擾阻礙辯護人行使權利的,而幾乎沒有針對防止辯護人不盡職不盡責辯護的。。本文擬對這一問題進行系統研究,在對無效辯護制度正當性分析的基礎上,研究如何建構這一制度,以預防和救濟辯護人不盡職不盡責而侵害辯護權的問題。
一、無效辯護制度的正當性
辯護權的發展經歷了享有辯護權、享有律師辯護權、享有有效辯護權三個階段(4)陳瑞華.刑事辯護的理念[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101.,無效辯護制度的出現,正是辯護權發展到第三個階段的重要標志。無效辯護制度起源并普遍適用于英美法系對抗制訴訟國家。早在一個多世紀以前,美國就出現了以辯護人不盡職不盡責構成無效辯護為由提起上訴的案例,只是那時候對辯護權的保障還處于正努力解決保障被告人“有”辯護人的階段,而辯護的質量、辯護人的表現問題,尚未被認為是重要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也就不被重視,更不可能成為制度建設的重點,對于無效辯護的認定標準、救濟程序等,根本不可能形成統一的規定和做法,實踐中被認定為無效辯護的情形,更是罕見(5)〔8〕James A. Strazzella, In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 Claims: New Uses, New Problems, 19 Ariz. L. Review, 443, 484(1977).。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上世紀60年代。在美國正當程序革命浪潮的席卷下,隨著“有”辯護人的問題得到解決,辯護的質量、辯護人的表現問題開始引起重視,實踐中以辯護人不盡職不盡責構成無效辯護為由提起的上訴呈井噴之勢,成為人身保護令申請中被援引最多的理由(6)Justin F. Marceau, Remedying Pretrial Ineffective Assistance, 45 Tex. Tech L. Rev. 277(2012).。不過由于聯邦最高法院遲遲不愿介入該問題,因此沒有形成全國統一的判斷標準、救濟程序,聯邦下級法院和各州法院在此問題上各行其是,無效辯護的判斷標準和救濟程序,五花八門,形態各異(7)吳宏耀,周媛媛.美國死刑案件的無效辯護標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58-61.。直到1984年,聯邦最高法院才開始介入該問題,在United States v.Strickland案中,確立了無效辯護的分析框架、判斷標準和救濟程序,至此無效辯護制度才得以最終形成〔8〕。同屬英美法系對抗制訴訟的英國、加拿大等國,也形成了類似的無效辯護制度(8)英國的無效辯護制度參見Marcus Procter Henderson, Truly Ineffective Assistance: A Comparison of In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13 Ind. Int’l & Comp. L. Rev. 317, 352。 (2002)加拿大的無效辯護制度參見:Dale E. Ives, The Canadian Approach to In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 Claims, 42 Brandeis L.J.(2003).。
雖然各國無效辯護的判斷標準、救濟程序不盡一致,但無效辯護制度的內涵都是一致的,即當被告人認為辯護人的辯護不盡職不盡責時,他可以以沒有保障其有效辯護權為由提起上訴,請求上訴法院撤銷原判,上訴法院經過審查認定辯護人的辯護構成無效辯護后,應當將原判決撤銷并發回重審(9)林志浩.是公平的保障還是一襲國王的新衣?——論對抗制下律師失職行為與被告律師權的保障[J]. 月旦法學雜志,2006,(10).。對于無效辯護制度的內涵,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理解:首先,它是一種專門針對辯護人表現的救濟機制。賦予被告人辯護權,不只是賦予被告人形式上能夠享有辯護權,而是實質上能夠享有有效辯護權,享有辯護權的實質就是享有有效辯護權(10)熊秋紅.有效辯護、無效辯護的國際標準和本土化思考[J].中國刑事法雜志,2014,(10).。而有效辯護權的實現,需要內外兩方面的保障,外部需要公檢法等公權力保障辯護權的行使環境,尤其不得干擾、阻礙辯護權的行使,內部則需要辯護人能夠盡職盡責的辯護。因此,對于辯護權的侵害,既可能來自于公檢法等公權力,也可能來自于辯護人。辯護權是一種程序性權利,對程序性權利的救濟,采用的是不同于實體性權利救濟的程序性救濟機制(11)〔13〕陳瑞華.程序性制裁制度的法理學分析[J].中國法學,2005,(6).,無論是對于公檢法等公權力侵害辯護權的,還是對于辯護人侵害辯護權的,采用的都是程序性救濟機制,但是由于兩者侵權主體不一樣,因而采用的程序性救濟機制的具體模式也不一樣,對于前者的救濟,采用的是程序性制裁機制〔13〕,而對于后者的救濟,則采用的是無效辯護制度,雖然兩者的后果都是撤銷原判發回重審,但是兩者在判斷標準、救濟程序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其次,它是一種上訴救濟機制。由于辯護人的表現直接關系到有效辯護權的實現,因此對其進行監管就不可缺少。對于辯護人的表現,主要有事前預防、事中監督、事后救濟三種監管方式,事前預防主要是在辯護開始前,由法官對辯護人的辯護資格、專業能力、職業道德等進行審查,如果發現其明顯不可能提供盡職盡責辯護的,則應將其排除在本案辯護之外(12)Donald A. Dripps, In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 The Case for an Ex Ante Parity Standard, 88 J. Crim. L. &Criminology.(1997).。事中監管主要是在辯護過程中,由法官對辯護人的表現進行同步監督,發現辯護人有不盡職不盡責表現時,當場提醒、警告甚至強令辯護人退出本案的辯護等(13)Heidi Reamer Anderson, Qualitative Assessments of 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 51 Washburn L.J.(2012).。事后救濟主要是在一審判決后,當發現辯護人的辯護有不盡職不盡責情形時,由上訴法院以此為由將原判決撤銷并發回重審。無效辯護制度正是這種事后救濟機制。三種監管方式各有利弊,事前預防可以將明顯達不到有效辯護人條件的辯護人排除在外,有助于保障訴訟的效率,但它也只能將明顯不具備條件的辯護人排除在外,而無法保證形式上符合條件的辯護人在辯護過程中會盡職盡責的辯護。事中監管有助于法官第一時間發現并糾正辯護人的不盡職不盡責行為,也有助于保證訴訟的效率,但由于辯護尚在進行中,難以對辯護人的行為屬于辯護策略還是屬于辯護缺陷進行判斷,如果法官貿然介入,容易侵害辯護人的獨立辯護權,扭曲訴訟的正當構造,在法官權威不高的地方,還容易引發審辯沖突等問題(14)熊秋紅.有效辯護、無效辯護的國際標準和本土化思考[J].中國刑事法雜志,2014,(10).。而事后救濟,由于辯護已經結束,上訴法院能夠綜合考察辯護人的整個辯護行為,客觀評估辯護人的表現,因而相對容易識別辯護人的行為屬于辯護策略還是辯護缺陷,而且因為是事后評估,也不會直接侵害辯護人的獨立辯護權。但是,由于事后救濟將辯護人表現的監管責任賦予上訴法院,而非一審法院,會導致一審法院對于一些明顯的、嚴重的不盡職不盡責辯護也視而不見或束手無策,而只能留待上訴法院處理,這不僅會損害一審法院的公正形象,而且會損害整個訴訟的效率(15)Galia Benson-Amram, Protect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Court: Trial Court Responsibility for Preventing In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 in Criminal Cases, 29 N.Y.U. Rev. L. & Soc. Change 425, 458(2004).。最后,它是一種程序內的救濟機制。對于侵害辯護權的,既有程序內的救濟機制,又有程序外的救濟機制。程序內的救濟機制是指通過本案訴訟程序而不是通過另行啟動其他程序進行救濟,其直接后果不是針對侵權行為人,而是本案訴訟程序,不是追究侵權行為人的個人責任,而是改變本案訴訟程序的進程和結果。而程序外的救濟機制與程序內的救濟機制正好相反,它是通過另行啟動新的程序直接針對侵權行為人,通過追究侵權行為人的個人責任進行救濟。行政紀律懲戒、民事侵權訴訟屬于程序外的救濟機制,而無效辯護制度屬于一種典型的程序內的救濟機制,它是在本案訴訟程序組成部分的上訴程序而非在本案訴訟程序之外另行啟動新的程序中進行的,它不是追究辯護人失職失責的個人責任,而是試圖撤銷原判發回重審(16)Anneiisoo.,An individual’s right to the 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 versus the independence of counsel.17 Juridica Int’l 2010.。
根據無效辯護制度,無效辯護的后果是撤銷原判發回重審,這意味著辯護人不盡職不盡責的后果與公檢法等公權力侵害辯護權的后果是一樣的。而且在兩種情形中,撤銷原判發回重審的性質也都完全一樣,都是對公權力不利對被告人有利因而在性質上屬于對公權力的制裁對被告人的救濟(17)在我國,撤銷原判發回重審既可以針對事實問題,也可以針對程序問題,針對事實問題的撤銷原判發回重審,既可能對被告一方有利,也可能對控訴一方有利。但針對程序問題的撤銷原判發回重審,則只可能對被告一方有利。辯護人不盡職不盡責與公檢法等公權力侵害辯護權,都屬于程序問題,因而撤銷原判發回重審都是對被告有利的。。兩種情形中侵害辯護權的主體不同,而其后果完全相同,這必然會影響到對兩者正當性的不同認可。在公檢法等公權力侵害辯護權時,由于侵權的是公權力,被侵權的是被告人,因此通過撤銷原判發回重審對公權力進行制裁,對被告人進行救濟,這種制度設置既符合制裁與救濟的基本原理,也有助于威懾侵權行為的發生,因而具有正當性。但是在辯護人不盡職盡責辯護時,侵害辯護權的是本屬與被告人處于同一陣營且是其仰賴對象的辯護人,而非公檢法等公權力,那么為什么也要撤銷原判發回重審,并因此而導致被制裁的不是侵權者的辯護人,而是與此無關的公檢法等公權力?該問題直接關系到無效辯護制度的正當性。對于無效辯護制度正當性的質疑,主要依據以下兩個理論:一是欠缺政府行為理論。該理論的核心含義是政府不用對其無法控制的行為承擔責任,否則對政府不公平,而且也無助于防止該行為的發生(18)McQueen v. Swenson, 498 F.2d 207 (8th Cir. 1974).。根據該理論,公檢法等公權力是否有義務和能力干預辯護人的辯護行為,就決定了公檢法等公權力應否對辯護人的不盡職不盡責辯護承擔責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即使公檢法等公權力沒有以作為的方式干涉、阻擾辯護人的辯護,也會因為其有義務干預辯護人的辯護而沒有干預這一不作為而需要承擔責任。無論是法院還是檢察機關,都負有維護審判公正的義務,而有效辯護則屬于審判公正的構成要素,因此在理論上法院和檢察機關都是有權以維護審判公正為名對辯護人的辯護進行干預的,但由于辯護人的辯護不盡職不盡責難以識別,法院和檢察機關貿然介入辯護人的辯護,很容易侵害辯護人的獨立辯護權甚至扭曲審判的正常構造,因此除了在利益沖突辯護這種較容易識別的情形之外,法律并未賦予法院和檢察機關干預辯護人辯護的義務(19)〔22〕Bruce Andrew Green, A Function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 80 Colum. L. Rev.(1980).。正因為法院和檢察機關沒有義務對辯護人的辯護進行干預,因此其自然不用對辯護人的不盡職不盡責辯護承擔責任。而反之,如果讓法院和檢察機關對辯護人的不盡職不盡責辯護承擔責任的話,那么必然會促使法院和檢察機關為了防止判決因為辯護人的表現被撤銷而會頻繁的介入辯護人的辯護,而這勢必會侵害辯護人的獨立辯護權甚至扭曲審判的正常構造,這種做法得不償失。正因為法院和檢察機關沒有義務對辯護人的辯護進行干預,也不應該介入辯護人的辯護,因此讓其承擔辯護人辯護不盡職不盡責的后果,這種做法不具有正當性。二是代理理論。該理論的核心內容是被代理人授權代理人對外代理其行使權利,代理人對外以被代理人的名義行使權利,代理的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擔。代理人與被代理人之間的內部關系,不會影響代理行為的效力,因此即使代理人在代理過程中損害被代理人的利益,該代理行為對外仍然有效。被代理人不得主張代理行為無效而拒絕承擔代理的后果,即使需要追究代理人的責任,也只能通過行政或民事的方式,而不得對代理行為本身的效力提出質疑(20)〔24〕〔25〕Charles H.Whitebread&Christopher Slobogin,Criminal Procedure 870(Foundation Press,1993).。被告人與辯護人之間就屬于代理關系,因此應該遵循代理的基本原理:辯護人的表現屬于被告人與辯護人之間的內部關系問題,該問題不應該影響代理行為的對外效力,即使辯護人的辯護不盡職不盡責,也只能追究辯護人的個人責任,而不應該否決辯護行為的對外效力,該辯護仍然是有效的,被告人不得主張辯護無效而撤銷原判發回重審。因此,無效辯護制度將一種本是內部關系的問題,賦予否決對外效力的效力,這種做法違反了代理原理,不具有正當性。
上述兩個理論雖質疑的角度不同,但它們指向同一個基礎問題,即辯護權是一種什么性質的權利?辯護權的性質不同,辯護人在訴訟中的定位也不同,政府對辯護權保障的責任也不同,因此該問題的答案,決定了應該由誰承擔辯護人不盡職不盡責辯護的程序后果,進而決定了無效辯護制度的正當性與否。關于辯護權的性質,上述兩個理論都是以辯護權屬于私權利為基礎的。該觀點認為,辯護權只是一種事關被告人個人利益的私權利,被告人因為通常不懂法律且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等原因,故通過訂立契約的形式委托辯護人幫助其行使權利,被告人與辯護人之間屬于民法上的契約關系,辯護人在訴訟中屬于被告人的代理人,代理被告人處理事務〔24〕。由于辯護權屬于被告人的私權利,辯護人屬于被告人的代理人,因此被告人與辯護人如何行使辯護權,完全由被告人決定,也因此其后果也完全由被告人承擔。對于國家來說,因為辯護權只是被告人的私權利,國家對辯護權保障的責任,只是一種消極責任:一種不得干涉、阻礙辯護權行使的責任。除此之外,國家不需要再承擔其他任何責任〔25〕。本文認為,將辯護權定位于私權利是錯誤的。辯護權不只是事關被告人個人利益的私權利,而是還關系到公共利益的公權利,因此上述觀點對辯護人的定位是錯誤的,對國家對辯護權保障責任的理解也是片面的,對無效辯護制度的質疑是站不住腳的。無效辯護制度具有正當性的具體理由如下:追訴和定罪屬于國家的權力,但由于被追訴和被定罪的后果非常嚴重,因此國家必須確保追訴和定罪的程序是公正的,這是國家在行使追訴和定罪的權力時,必須承擔的義務(21)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158.。而辯護權則是程序公正的構成要素,要保障程序公正,則必須保障辯護權。“政府啟動并展開刑事審判,憲法要求政府確保審判公平進行。而公平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就在于律師的幫助。”(22)〔28〕〔30〕〔31〕[美]詹姆斯·J·湯姆科維茲.美國憲法上的律師幫助權[M].李偉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158.4.159.由此可見,賦予被告人辯護權,不只是為了保障被告人的人身、財產、名譽等個人利益,也是為了履行國家保障程序公正的義務。“第六修正案律師幫助權與其說是為了保障被告人的個人利益,不如說是為了保障實現審判的公平公正。”而設立辯護人這個角色,也不只是為了讓其代理被告人的利益,同時還有讓其代理國家履行其保障程序公正義務的考慮,因此辯護人不只是被告人的代理人,也是國家的代理人(23)林勁松.對抗制國家的無效辯護制度[J].環球法律評論,2006,(4).。“不管是聘請的還是指定的,律師都扮演著確保公平審判的角色。”大陸法系國家將辯護人定位為立于被告人之側的司法機關正是這個考慮。正因為辯護權不只是私權利,還是公權利,辯護人不只是被告人的代理人,還是國家的代理人,因此國家對辯護權的保障義務就不只是消極義務,而負有積極義務:必須積極作為,增強辯護權的行使能力,促使辯護人盡職盡責的辯護。而如果辯護人不盡職不盡責辯護,就不只是辯護人違反了對被告人的契約義務,而且是國家違反了追訴和定罪必須按照公正程序進行的義務,因此不只是辯護人需要對此承擔責任,國家也需要對此承擔責任。而且由于追訴和定罪不是建立在公正程序基礎上的,因此該定罪必須被撤銷并進行重審。由此可見,當辯護人的辯護不盡職不盡責時,表面上侵害辯護權的是辯護人,實際上還有國家,因此撤銷原判發回重審,不是對辯護人的制裁,而是對國家的制裁,不是讓國家承擔辯護人的個人責任,而是讓國家承擔它自身的責任。“因為政府有義務提供公平的、對等的對抗制訴訟程序,所以‘第六修正案要求政府不得進行這樣的審判,被監禁的人在沒有稱職法律幫助的情況下自己辯護’,并且‘要求政府承擔律師缺陷幫助的風險’。因此,如果律師未能稱職辯護,政府還是根據審判判決被告人有罪并剝奪其自由或生命,那就違反了憲法。”
二、無效辯護的判斷標準
(一)確立無效辯護的判斷標準是個棘手的問題
無效辯護的判斷標準是無效辯護制度的核心問題,也是最為棘手、爭論最為激烈的問題。棘手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與公檢法等公權力干擾阻礙辯護權是有和無的問題不同,辯護人不盡職不盡責不只是有和無的問題,還是輕和重的程度問題。有和無的問題是一個客觀性問題,判斷標準較為客觀,相較而言易于判斷,而輕和重的問題則是一個主觀性問題,判斷標準較為主觀,較為難以判斷。對于公檢法等公權力,只要實施了干擾阻礙辯護權的行為,而不論其輕重程度如何,就都構成對辯護權的侵害,也就都應該承擔撤銷原判發回重審的不利后果。但是對于辯護人,即使有不盡職不盡責的行為,也并非一定構成無效辯護,而必須不盡職不盡責達到一定程度,才會構成無效辯護。因此,無效辯護的判斷,不僅要判斷辯護人是否有不盡職不盡責行為,還要判斷辯護人不盡職不盡責達到了什么程度,這是個難以確定的問題。其二,判斷辯護人的辯護是否構成無效辯護,首先必須判斷辯護人是否有不盡職不盡責辯護行為,雖然這也是一個有關有和無的客觀性問題,但與公檢法等公權力有無干擾阻礙辯護權的行使問題相比,該問題更難以識別、更難判斷。公檢法等公權力是否有干擾阻礙辯護權的行為,通常一目了然,容易識別,但是對于辯護人的行為是否屬于不盡職不盡責行為難以識別。因為案件千差萬別,不同辯護人有不同的辯護風格,在有些人看起來屬于不盡職不盡責的行為,可能在另一些人看來卻是絕妙的辯護策略,同樣的辯護行為,在有些案件屬于明顯的不盡職不盡責,但換在另一些案件中卻是極高明的辯護策略(24)林志浩.是公平的保障還是一襲國王的新衣?——論對抗制下律師失職行為與被告律師權的保障[J].月旦法學雜志,2006,(10).。其三,辯護人的不盡職不盡責達到何種程度才構成無效辯護,是比辯護人有無不盡職不盡責行為更難判斷的問題。就像醫療行業一樣,這一問題不能完全取決于當事人的評價以及最終的結果,不能說只要當事人不滿意、判決結果不如意,辯護人的不盡職不盡責就構成無效辯護(25)Barbara R. Levine, Preventing Defense Counsel Error An Analysis of Some In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 Claim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Professional Regulation, 15 U. Tol. L. Rev. 1275(1984).。“很難對法律工作的質量進行評估,尤其是刑事辯護工作。最終結果并不能確切地反映出工作的努力程度。在這個市場的力量完全不起作用的系統中,當事人的滿意度也無關緊要。”(26)Saundera D. Westervelt, John A. Hunphery, Wrongly Convicted―Perspectives on Failed Justice,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1,at 230.劃定構成無效辯護的辯護人不盡職不盡責的程度,既要考慮被告人有效辯護權的實現、判決的終局性、訴訟效率等問題,又要防止辯護人通過故意不盡職不盡責辯護來獲得二次審判的機會以及降低律師接受指定辯護甚至從事辯護的意愿等問題,因此過高或過低都不行,而必須盡力平衡各種利益,而這并非易事。
(二)美國的無效辯護判斷標準
雖然美國無效辯護的實踐歷史悠久,但在無效辯護的判斷標準問題上,卻經歷了曲折,至今仍然存在激烈爭論。考察美國在無效辯護判斷標準上的變遷及爭論,有助于為我國確立無效辯護的判斷標準提供啟示。美國早在一個多世紀以前就出現了無效辯護制度的雛形,但是對于無效辯護的判斷標準,卻一直處于變化之中。在早期,美國采用的是“正義的笑柄”標準,即自司法正義角度觀察,辯護人的無能致審判成為一場鬧劇,那么該辯護就構成無效辯護。根據該標準,無效辯護的認定主要不在于辯護人的行為,而在于整個審判程序,如果審判程序還沒有淪落到鬧劇的程度,那么即使辯護人再無能,其辯護行為再荒謬,該辯護仍然不屬于無效辯護,不能獲得上訴救濟。因為該標準設定過高,只有極少數的案件才能符合該標準,被認定為無效辯護,而很多明顯的、嚴重的不盡職不盡責辯護,未被認定為無效辯護,該因此標準對辯護權保障的作用微乎其微。正因為如此,該標準沒有存續多少年就被廢除了(27)〔37〕〔38〕William J. Genego, The Future of 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 Performance Standards and Competent Representation, 22 Am. Crim. L. Rev. 181(1984).。隨后聯邦下級法院和許多州法院開始采用“合理勝任”標準,即辯護人提供的辯護必須符合一個能夠勝任的辯護人提供的水平,否則構成無效辯護。但是對于什么是合理勝任,該標準并不明確,不同司法區域有不同理解,有的認為必須達到“當時當地通行的標準”,有的認為必須達到“一個合格辯護人提供的辯護”等(28)吳宏耀,周媛媛.美國死刑案件的無效辯護標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61.。但是這些解釋并未解決該標準不明確的問題,由于標準不明確,導致實踐中無效辯護的判斷完全取決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而由于法官出于種種顧慮而不愿意介入審查辯護人的行為,導致對無效辯護從嚴認定。從實踐情況來看,該標準與正義的鬧劇標準相比,被認定為無效辯護的情形并未有顯著變化,被認定為無效辯護的情形仍然非常罕見〔37〕。但是該標準的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它要求辯護人的辯護必須合理勝任,傳遞了一個非常強烈的信號,即法院開始關注辯護人的行為,開始要求辯護人提供符合基本要求的辯護〔38〕。
無論是鬧劇標準還是合理勝任標準,都是在聯邦下級法院或州法院相關司法實踐中形成的標準,而作為最高司法機關的聯邦最高法院,卻在該問題上長期保持沉默,不愿介入該問題。直到1984年,聯邦最高法院終于開始著手解決無效辯護的問題。在斯特里克蘭案中,確立了無效辯護的判斷標準,即斯特里克蘭標準。根據該標準,要構成無效辯護,必須同時具備兩個條件:一個是行為缺陷標準,即辯護人的辯護行為存在缺陷,且程度嚴重到未能發揮辯護人應有的功能;二是損害標準,即辯護人的缺陷辯護行為對審判造成了損害,且嚴重到剝奪了被告人獲得公正審判的權利。聯邦最高法院在判決中,同時還對這兩個條件的具體判斷提出了詳盡的指導:對于行為缺陷的判斷,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法院應綜合一切情況,依審判當時通行的辯護規范為標準,判斷辯護人的行為是否具有合理性。并且在判斷時,應該對辯護人的行為及決定高度尊重,假設辯護人已經提供了符合要求的辯護,或者辯護行為屬于辯護人的合理策略,而應該避免事后的判斷;對于損害的判斷,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法院應該審查是否存在合理可能性,即若非辯護人的缺陷行為,審判結果就會不一樣。而所謂合理可能性,就是指只要足以動搖對審判結果信心的可能性就可以了。被告人要主張辯護人提供的辯護構成無效辯護,必須同時證明這兩個條件的存在,否則不會被認定為無效辯護(29)Strickland v.Washington,466 U.S.688,691(1984).。斯特里克蘭案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的最為重要的案件之一,它成為聯邦最高法院眾多判決中被引用最多的判決,影響深遠(30)Donald A.Dripps,In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the case for an ex parity standard,88 J.Cimi.L.&Criminology,1997.。它確立了無效辯護的分析框架,統一了無效辯護的判斷標準,沿用至今,且尚無要更改的跡象,其意義再怎么強調都不為過。
但是,該標準自產生之時,便遭到學術界與實務界的激烈批評,批評的理由主要包括:該標準過于關注辯護行為導致的后果而忽視辯護行為本身,尤其是兩個標準不需要按照順序判斷,造成只要結果是正確的,辯護人的行為可以完全不管。它也給外界傳遞了一個有害的信號:即越是證據充分的案件,辯護人越可以不盡職盡責的辯護,而常理應該是越是難的案件,越需要辯護人盡職盡責的辯護(31)〔45〕Gary Goodpaster, The Adversary System, Advocacy, and 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 in Criminal Cases, 14 N.Y.U. Rev. L. & Soc. Change(1986).;該標準將損害要求理解為損害結果要求,限縮了辯護權的功能,辯護權的功能不只在于保障實體公正,也在于保障程序公正。所有涉嫌犯罪的人,不管其實際上有罪與否,都享有有效辯護權,但是該標準卻導致只有實際無罪的人才能享有有效辯護權,而實際有罪的人卻無法享有有效辯護權(32)Bruce Andrew Green, A Function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 80 Colum. L. Rev. (1980).;損害標準根本就不應該有,因為在當事人主義訴訟中,辯護人應傾全力在法律和道德允許的范圍內為當事人進行辯護,爭取對當事人最有利的結果,而至于該結果對社會來說是否公正,則并非辯護人的任務,因此該標準混淆了辯護制度的功能與辯護人的作用兩個問題等(33)William J. Genego, The Future of 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 Performance Standards and Competent Representation, 22 Am. Crim. L. Rev. 181(1984).。
雖然上述批評的角度不一樣,但其基本觀點都是一樣的,即都認為聯邦最高法院確立的無效辯護判斷標準過高,使得無效辯護的證明是個難以完成的任務。事實表明,批評者的擔心并非是杞人憂天,在司法實踐中,提出無效辯護請求的比例是很高的,但是最終被認定為無效辯護的比例卻是非常低的(34)Martin C. Calhoun, How to Thread the Needle: Toward a Checklist—Based Standard for Evaluating In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 Claims, 77 Geo. L. J. 413,462(1988).。那么,為什么聯邦最高法院在無效辯護問題上保持長時間的沉默,最終卻確立了一個對被告人來說仍然高不可攀的標準呢?可能的原因包括:尊重辯護人的獨立辯護權,不愿意輕易介入評價辯護人的辯護行為;擔心標準過低會導致提出過多的無效辯護請求,導致過多的判決會被推翻,從而損害判決的終局性和訴訟效率;擔心會降低辯護人接受指定辯護的意愿;擔心辯護人通過故意犯錯來獲得二次審判的機會等。這些原因表明,聯邦最高法院在確立無效辯護的判斷標準時,在面對諸多利益需要權衡時,他選擇的是優先保護國家的利益(訴訟效率、判決的終局性等)、辯護人的利益(辯護人的獨立辯護權等),而非被告人的利益(有效辯護權),因而他確立了一個對國家和辯護人有利而對被告人不利的標準〔45〕。
但是,對于該標準的評價,也沒有必要過于悲觀。雖然該標準與正義的鬧劇和合理勝任標準更為明確,但其本質上仍是一個不甚明確的標準,其具體內涵有待于法官在個案中運用裁量權進一步闡釋,并且為了適應情勢變化,其內涵也會不斷變化。“這些‘約定俗成的’‘合理的’詞語不過是空空的容器,需要我們給它們填充內在的含義,否則這些標準就沒有起到將原來‘鬧劇’標準具體化客觀化的作用,不過是將原來的問題變成了什么是約定俗成的,什么是合理的這樣的問題。”因此即使聯邦最高法院暫時不可能放棄該標準,但是如果認識到無辜者被定罪與辯護質量有關的話,他必定會放松對該標準內涵的嚴格理解,而更多的認定為無效辯護,比如將辯護人的不盡職不盡責行為更多的認定為造成了嚴重損害,或者將更多的辯護人的不盡職不盡責行為認定為屬于嚴重缺陷行為而直接推定為造成了嚴重損害(35)Adele Bernhard:Exonerations change judicial views on 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18 Crim.Just.2003.。美國無效辯護的實踐已經證實了這一判斷,雖然無效辯護的判斷標準未變,但無效辯護認定成功率在明顯增加,以前沒有被認定為無效辯護的,同樣的情形現在卻被認定為無效辯護。因此,對于美國無效辯護判斷標準的評價,不能僅拘泥于靜態的文字表述,而應該同時考察其具體適用的變化(36)Richard Klein, The 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In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 58 Md. L. Rev. 1433 (1999).。
(三)我國無效辯護判斷標準的確立
雖然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斯特里克蘭案中確立的無效辯護判斷標準備受質疑,但其采用的分析方法卻值得我們借鑒。聯邦最高法院在該案中指出,“判斷任何有效性主張的基本點必須是律師的行為是否損害了對抗式訴訟的基本功能,以至于難以依賴審判得到一個公正的結果”(37)〔52〕〔53〕〔55〕〔56〕Strickland v.Washington,466 U.S.688,691(1984).。可見,其采用的是功能分析法。這種方法是正確的:因為一方面,享有辯護權的目的是為了享受辯護權的功能,只要辯護權的功能未受損,則被告人享有的辯護權就未受損;另一方面,出于制度成本等的原因,法律不可能保障完美無瑕的辯護。這兩方面的原因決定了法律保障的只能是滿足基本辯護功能的辯護,而不可能是沒有缺陷的辯護。因此,對無效辯護的判斷,不能離開辯護權的基本功能(38)Barbara R. Levine, Preventing Defense Counsel Error An Analysis of Some In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 Claim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Professional Regulation, 15 U. Tol. L. Rev. 1275(1984).。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存在的主要問題在于:其在要求“損害對抗式訴訟的基本功能”之外,再要求“難以依賴審判得到一個公正的結果”。這是將對抗式訴訟的基本功能矮化為結果公正,是對對抗式訴訟功能的錯誤理解,對抗式訴訟的基本功能不只在于保障結果公正,也在于保障程序公正(39)Gary Goodpaster, The Adversary System, Advocacy, and 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 in Criminal Cases, 14 N.Y.U. Rev. L. & Soc. Change(1986).。
無效辯護制度是保障辯護人提供的辯護能夠滿足基本辯護功能的制度,因此,無效辯護的判斷標準就是辯護存在缺陷,且該缺陷損害了辯護的基本功能。根據該標準,構成無效辯護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辯護存在缺陷;二是辯護缺陷損害了辯護的基本功能。關于辯護是否存在缺陷的判斷,存在逐案審查與清單審查兩種觀點,兩者的主要分歧在于是否存在適合于所有案件的有效辯護行為清單,或者是否應該設立該清單(40)〔54〕Martin C. Calhoun, How to Thread the Needle: Toward a Checklist—Based Standard for Evaluating In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 Claims, 77 Geo. L. J. 413, 462 (1988).。逐案審查觀點認為,案件千差萬別,不同辯護人有不同的辯護風格,不同案件有不同的辯護策略,因此不存在對所有案件都適用的有效辯護行為清單,“沒有一套律師行為的具體詳細規則能夠令人滿意地考慮到辯護律師面臨的各種情況或者關于如何最好地代理刑事被告人的各種合理判斷。”“詳細列舉律師必須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的任何嘗試都不可能囊括職業上可接受的、有效的幫助的所有形式。”而且辯護人的職責是在法律和職業道德允許的范圍內,盡一切所能,采取一切手段最大限度的維護和爭取被告人的利益,如果設立有效辯護行為清單的話,反而會束縛辯護人的手腳,影響其獨立辯護。“這些固定的標準的危險就在于可能既是律師辯護的最低標準,也是律師辯護的全部內容。”〔52〕“任何這種詳細規則都會干擾到憲法保護的律師的獨立性,同時也會限制律師在決定辯護策略時的自由。事實上,任何詳細指導都會使律師分心,使他無法精力充沛全力以赴地為被告人準備辯護。”〔53〕因此,法官對辯護是否存在缺陷的審查,只能依據個案的具體情形進行。清單審查觀點認為,告訴辯護人應該盡職盡責的辯護,而不告訴具體應該怎樣做才算盡職盡責的辯護,等于什么都沒有說。雖然案件各異,需要獨立辯護,但辯護存有共性,這些共性要么是有助于實現有效辯護的,要么甚至是實現有效辯護所不可缺少的,他們構成有效辯護的共同規則,這些共同規則可以編制為有效辯護行為清單〔54〕。“雖然辯護工作需要靈活與獨立,但是辯護中有很多內容是最基本的,是可以接受司法審查的。”〔55〕“在與被告人協商、反對重要的可能錯誤的裁定和提交上訴聲明這些問題上,可以有一些細化的統一規則。”〔56〕法官在審查辯護是否存在缺陷時,應該參考該清單。筆者認為,一方面因為辯護之間存在共性,這些共性是有效辯護的重要保障,甚至是其前提和基礎,因而可以設立有效辯護行為清單;另一方面因為設立有效辯護行為清單,既有助于為辯護人的辯護提供指導,又有助于為法官的辯護缺陷審查提供指引。這兩方面的原因決定了,應該設立有效辯護行為清單。但是,為了防止該清單損害辯護的獨立、自由、靈活等,該清單原則上只具備指導效力,而無強制效力。不是說只要按照該清單辯護,就一定是有效辯護,也不是說,只要沒有按照該清單辯護,就一定是無效辯護。該清單只是判斷有效辯護、無效辯護的重要參考,甚至是最重要參考,但并非唯一標準,在判斷時,還需要結合考慮其他因素(41)William J. Genego, The Future of 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 Performance Standards and Competent Representation, 22 Am. Crim. L. Rev. 181 (1984).:比如對于判斷辯護人沒有調查取證是否構成辯護缺陷時,首先應該參考有效辯護行為清單。如果該清單要求辯護人調查取證的話,那么該辯護很可能會被認定為有缺陷,但也只是很可能而非一定,是否屬于辯護缺陷,還需要調查其他信息,比如他為什么沒有調查取證等。為了體現對律師行業自治的尊重,以及避免司法干涉獨立辯護權,該有效辯護行為清單應該由律師協會制定(42)Barbara R. Levine, Preventing Defense Counsel Error An Analysis of Some In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 Claim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Professional Regulation, 15 U. Tol. L. Rev. 1275 (1984).。
關于辯護缺陷損害辯護基本功能的判斷,作為一項訴訟制度,辯護服務于訴訟,因此辯護制度的功能必須從其所服務的訴訟的價值目標上考慮。“刑事辯護制度與刑事訴訟價值目標之間的關系顯然應當成為我們研究刑事辯護制度價值問題的著眼點。”(43)熊秋紅.刑事辯護制度之訴訟價值分析[J].法學研究,1997,(6).而刑事訴訟的價值目標在于實現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已經是理論和實踐上的共識,辯護制度也正是服務于這兩個價值目標。對于實體公正,在對抗式訴訟中,控辯雙方的平等對抗被認為是實現實體公正的最有效方法,而辯護制度的設置正是實現控辯平等不可或缺的基礎條件。而在職權主義訴訟中,雖然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的職權調查被認為是實現實體公正的最佳方法,但“在被告有利方面督促國家機關實踐其應然的客觀性義務,并且動搖其不利于被告事項之判斷,以便保證無罪推定原則能在具體個案中實現”也正是設立辯護制度的目的。而對于程序公正,由于刑事訴訟被認為是國家和個人之間的糾紛,而這種糾紛的后果對被告人來說非常嚴重,因此除了確保實體公正外,還必須確保程序公正,而辯護制度亦屬于程序公正最重要的保障。雖然對程序公正的具體標準尚未達成一致意見,但是被告人能夠有意義的參與訴訟以使控訴案件能夠接受嚴格的對抗式檢驗以及被告人能夠在訴訟過程中得到公平的對待是程序公正的兩個不可或缺標準。由于被告人大多不懂法律且程序日益復雜等原因,被告人能否真正有意義的參與訴訟,控訴案件能否得到嚴格的對抗式檢驗,必然取決于被告人能否獲得有效的辯護。而在公平對待方面,為了防止可能的權力侵害,法律賦予了被告人系列程序性權利,這些權利成為監督制約國家權力、獲得公平對待的工具,但是如果這些權利沒有辯護人的協助,難以實現。“律師的幫助讓被告人得以保護和行使作為公平的對抗制審判關鍵要素的其他權利。”(44)[美]詹姆斯·J·湯姆科維茲.美國憲法上的律師幫助權[M].李偉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159.正因為辯護制度的功能不只在于保障實體公正的實現,也在于保障程序公正的實現,因此在判斷辯護人的辯護缺陷是否損害了辯護的基本功能從而是否構成無效辯護時,就不能僅審查是否損害了實體公正,還需要審查是否損害了程序公正。對于損害實體公正的判斷,相對來說較為容易,主要通過審查全案證據,以判斷是否存在合理可能性,若非辯護缺陷,審判結果就會不一樣,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則屬于損害了實體公正。而對于損害程序公正的判斷,則因為程序公正較為抽象,較為不易,但至少可以通過上述程序公正的兩個標準進行判斷:一是被告人能否有意義地參與訴訟。如果辯護缺陷導致被告人沒能有意義的參與訴訟,控訴案件沒能接受嚴格的對抗式檢驗,則程序不公正。那么具體怎么判斷呢?與上述辯護缺陷的判斷類似,有些辯護行為屬于有效辯護不可或缺之要素,如辯護人沒有實施這些辯護行為,則被告人不可能有意義地參與訴訟,控訴案件不可能接受嚴格的對抗式檢驗,因而這些行為就不只是屬于辯護缺陷,而應該被直接認定為損害了辯護的基本功能,而構成無效辯護。比如辯護人從未會見被告人、從未閱卷、在庭審中未發表任何實質的辯護意見等,都不可能讓被告人能夠有意義地參與訴訟,不可能讓控訴案件接受嚴格的對抗式檢驗,因而構成無效辯護。二是公平參與。如果因辯護人的原因導致程序性權利沒有得到保障,那么意味著辯護人沒有維護程序公正而損害了辯護的基本功能,因而構成無效辯護。比如如果法律賦予了被告人申請回避的權利、反對強迫自證其罪的權利、對證人對質詢問的權利、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權利等,但由于辯護人的原因導致被告人沒能行使這些權利,那么該辯護就損害了辯護的基本功能,構成無效辯護。
三、無效辯護的救濟程序
無效辯護的救濟不僅取決于無效辯護的判斷標準,而且取決于無效辯護的救濟程序,救濟程序的設置的好壞直接影響無效辯護獲得救濟的難易。以美國為例,雖然被告人既可以直接在上訴程序中,也可以在定罪后的附隨程序中提出無效辯護請求,但由于種種原因,無效辯護請求難以成立。在上訴程序中,美國法律規定必須是在一審審判記錄中記載過的事實才能成為上訴的對象,但無效辯護通常是辯護人沒有干什么,而不是干了什么的問題,因此審判記錄上通常不會有記錄。雖然在重審中可以補充審判記錄,但由于重審的時間很短,重審階段的辯護人通常是原審階段的辯護人,他不可能自己對自己提出無效辯護請求,所以在重審中很難在審判記錄中補充無效辯護的信息。因此,在上訴程序中提出無效辯護請求很難得到法院的支持;在定罪后的附隨程序中,雖然可以進行廣泛的調查,也可以補充審判記錄,但由于附隨程序的啟動通常距原審時間長,當事人多已經沒有再提起無效辯護請求的動力,即使提出,由于附隨程序當事人沒有獲得法律援助律師的權利,在無律師幫助的情況下,他很難克服無效辯護的兩個判斷標準,即使他自己有能力聘請律師,但由于距離原審時間久遠,很多證據都已經滅失,即使是律師,也很難找出證據來證明原審辯護屬于無效辯護(45)〔62〕Eve Brensike Primus, Structural Reform in Criminal Defense: Relocating In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 Claims, 92 Cornell L. Rev. 679(2007).。正是考慮到無效辯護的救濟程序太不利于被告人,因此許多學者都呼吁美國應該對無效辯護的救濟程序進行改革,允許在上訴程序中補充審判記錄,賦予附隨程序中被告人的法律援助權等〔62〕。
無效辯護屬于程序問題,在許多國家和地區,為了保障程序的獨立價值,都設立了獨立于事實問題的程序性上訴救濟機制,該機制只解決程序問題的救濟,而不解決事實問題的救濟。如在美國,由于原則上不允許對事實問題提出上訴,而只能對法律問題提出上訴,因此其上訴程序就主要是一種專門針對法律尤其是程序問題的救濟程序。又如德國、法國實行三審終審制,第二審程序處理事實問題的救濟,第三審程序處理包括程序問題在內的法律問題的救濟。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無效辯護的救濟是在專門的程序性上訴救濟機制中解決的。程序性上訴救濟機制實行事后審查方式,上訴法院原則上只審查上訴理由所指摘的程序違法是否成立,而不得涉及案件的事實認定問題,也不得涉及上訴理由未涉及到的其他程序問題。我國實行二審終審的審級制度,沒有設立獨立的程序性上訴救濟機制,對事實問題的上訴和對程序問題的上訴,都是在二審中解決的。由于二審實行復審以及全面審查,二審實際上是對全案的重新審理,這種程序設置貌似既能對事實問題進行救濟,又能對程序問題進行救濟,救濟的范圍很廣,但是在重實體輕程序的氛圍下,這種設置必然會導致二審滑向重實體救濟輕程序救濟的境地,程序問題的救濟必定會淪為實體問題救濟的附庸。很難想象,如果二審法院發現一審判決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沒有問題,僅因為辯護人的辯護不盡職不盡責就會將判決撤銷判決并發回重審。現實的情況很可能是,即使有被告人提起無效辯護的上訴,二審法院也會在審查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是否正確的基礎上認定是否屬于無效辯護,而不大可能會在事實認定問題之外單獨對辯護人的表現進行審查,更不大可能會在事實認定正確的情況下僅以辯護人的表現為由撤銷原判。事實上,不要說在我國這種將事實問題與程序問題的救濟相統一的國家,程序問題的救濟必定會以事實認定是否準確為基礎,即使是在那些設置了獨立的程序性上訴救濟機制的國家,只要存在重實體輕程序的觀念,也難逃程序問題的救濟要受到事實認定問題影響的命運。比如在我國臺灣地區,其第三審屬于專門的程序性上訴機制,但臺灣學者王兆鵬調查后發現,事實理由是將案件撤銷發回重審的真正動機與原因,法律理由只是發回的名目與依據而已。一位法官表示:“我們先看全部卷宗資料,如果覺得沒有冤枉被告,原則上就不發回;如果覺得被告可能是冤枉的,就會找一個法律理由撤銷發回”(46)王兆鵬.刑事救濟程序之新思維[M].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10.54.。
提起程序性上訴,需要提出明確的上訴理由,需要在上訴理由中明確指出哪一程序違法,而不能籠統的表述為“程序違法”。之所以作此要求,一方面是因為程序性問題較為復雜,甚至原審法院對任何一項證據的調查行為,理論上都可能存在多種程序違法情形,如果沒有上訴理由的明確指向,籠統地對原審程序合法性的事后審查幾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是因為上訴法院主要是基于庭審筆錄對程序問題進行審查,而庭審筆錄是對于審判必要手續的完整記錄,是庭審手續的唯一證明,但它通常不會對庭審的所有內容進行完整記錄(比如有的庭審筆錄不反映證人作證的內容),因而它也就不能對發生在審判中的所有事項作出完整的說明。因此,如果上訴法院要確定是否發生了一項程序性錯誤,它就需要上訴理由的指引,從上訴人處得到準確的信息。與其他程序性上訴相比,無效辯護的上訴更需要提出明確的上訴理由,這主要是因為:其一,辯護行為繁雜,甚至辯護人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屬于辯護行為,如果沒有上訴理由的明確指向,上訴法院要對辯護人的所有活動進行審查,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其二,庭審筆錄只能記錄發生在庭上的事情,無法記錄發生在庭外的事情,而辯護不只是庭上的辯護,還包括庭外的諸多辯護,沒有這些庭外的辯護,庭上的辯護也難以達到效果。但是,庭審筆錄只記錄了庭上的辯護,沒有記錄庭外的辯護,因此如果沒有上訴理由的明確指引,上訴法院不僅基本不可能對庭外的辯護進行審查,甚至也基本不可能對庭上的辯護進行全面客觀評價;其三,庭審筆錄只記錄發生了的事情,不會記錄沒有發生的事情。對于辯護人的辯護,庭審筆錄只會記錄辯護人在庭上做了什么,不會記錄他沒有做什么,而無效辯護上訴,大多數都是針對辯護人沒有做什么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可能出現在庭審筆錄中,因此如果不在上訴理由中予以明確,上訴法院基本不可能對其進行審查。是故,提起無效辯護上訴,需要在上訴理由中明確指出辯護的具體缺陷,以及該缺陷可能對本案實體和程序產生的不利影響,如“辯護人沒有調查本案的證人某某,而該證人可能提供有利于被告人的證言而改變判決結果”,而不能籠統的表述為“辯護人在辯護中不盡職不盡責”。
雖然同屬程序性上訴,但提起無效辯護上訴要比提起其他的程序性上訴更難:其一,被告人幾乎沒有能力提出。無效辯護上訴是被告人針對辯護人的,在兩者的關系上,雖然法律上被告人是當事人,辯護人只是其輔助人,但實際上辯護人對被告人處于壓倒性的優勢地位,被告人是赤裸裸的弱者。辯護幾乎完全是由辯護人控制、主導的,被告人并沒有多少話語權。在這種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被告人要指出辯護的具體缺陷,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單憑被告人,基本不可能提出包含具體理由的無效辯護上訴(47)Scott A. Hancock, In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 An Overview, 1986 Army Law. 41 (1986).。其二,其他辯護人不愿意提出。雖然被告人可以聘請新的辯護人,但出于維護職業共同體利益、個人利益等的考慮,新辯護人通常不愿意對原審辯護人提起無效辯護上訴(48)Anneii Soo, An Individual’s Right to the 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 versus the Independence of Counsel, 17 JuridicaInt’l(2010).。即使新辯護人愿意提起無效辯護上訴,但他要找出具體的無效辯護上訴理由也是很困難的。因為只能從被告人、原審辯護人等處收集信息,但被告人基本不掌握辯護信息,而原審辯護人也不大可能會配合新辯護人提出針對自己的無效辯護上訴(49)Anne M. Voigts, Narrowing the Eye of the Needle: Procedural Default, Habeas Reform, and Claims of In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 99 Colum. L. Rev. 1103, 1137(1999).。
提起無效辯護上訴之后,應該由誰來證明呢?這涉及到無效辯護的證明問題。對于辯護存在缺陷的證明由被告人負責,這一點基本不存在異議,但對于辯護缺陷損害了辯護基本功能的證明,則存在分歧,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應該由檢察機關承擔,其主要理由是在刑事訴訟中,證明有罪的責任由檢察機關承擔,如果辯護缺陷損害辯護基本功能的證明責任由被告人承擔的話,則等于讓他自證其罪。另一種觀點認為應該由被告人承擔,其主要理由是無效辯護屬于積極辯護事由,而積極辯護事由的證明責任由被告人承擔。對于辯護人的表現,檢察機關既無能力預防,也無義務干涉,因此不應該對其無法控制的事情承擔責任(50)David Charles Kent, In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 Who Bears the Burden of Proof, 29 Baylor L. Rev(1977).。兩種觀點各有理由,體現了對不同價值的側重。筆者認為,在本文提出的無效辯護判斷標準上,可以通過以下方式解決無效辯護的證明問題:如果該辯護行為屬于有效辯護行為清單上列舉的、實現有效辯護所不可缺少的,那么就直接推定為損害了辯護的基本功能,構成無效辯護;而如果該辯護行為屬于其他情形,則被告人必須證明該辯護行為缺陷損害了辯護的基本功能,否則不構成無效辯護。
單靠庭審筆錄很難完成無效辯護的證明,而必須依靠其他的途徑,主要有專家證人和原審辯護人。就專家證人而言,主要是指被告人為了證明原審辯護屬于無效辯護,可以申請法庭通知具有豐富辯護經驗的辯護人作為有專門知識的專家出庭,就原審辯護人的辯護提出意見(51)〔70〕Charles M. Sevilla, Investigating and Preparing an In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 Claim, 37 Mercer L. Rev. 927(1986).。比如對于原審辯護人沒有調查取證的行為,該行為屬于辯護策略還是辯護缺陷,可以申請具有豐富辯護經驗的辯護人,就該案是否應該調查取證提出意見。就原審辯護人而言,由于無效辯護制度實質是對國家的制裁,而非對辯護人的制裁,因此在無效辯護上訴審中,原審辯護人的角色并非是當事人(52)Joseph H. Ricks, Raising the Bar: Establishing an Effective Remedy against Ineffective Counsel, 2015 BYU L. Rev. 1115(2015).。由于辯護人對自己的辯護行為最為清楚,由他就辯護問題進行解釋說明,有助于查清辯護行為是屬于策略還是屬于缺陷,因此他有出庭就辯護進行解釋說明的義務。雖然無效辯護的后果不直接針對原審辯護人,但會間接損害其利益,因此他有出庭就辯護進行辯解的權利。無論是履行出庭進行解釋說明的義務,還是行使出庭進行辯解的權利,原審辯護人出庭都有助于無效辯護的審查判斷。比如對于當時沒有調查取證的行為的原因,原審辯護人最為清楚,由其解釋說明或者辯護,有助于協助法官對無效辯護的判斷。但是,原審辯護人在解釋說明時,很可能涉及到當事人的秘密,而為當事人保密是辯護人的一項基本義務,因此一方面辯護人有對辯護進行解釋說明或辯解的義務和權利,另一方面辯護人又有為當事人保密的義務,兩者之間存在沖突。筆者認為,處理該沖突的基本方式應該是:原審辯護人在對辯護進行解釋、說明、辯解時,為了證明自己的辯護是有效辯護,可以陳述當事人的秘密,但僅限于與無效辯護有關的范圍,而絕對不能超出該范圍,而且只能在法庭上,在法官的監管之下進行陳述〔70〕。比如被告人以原審辯護人沒有申請某證人出庭作證構成無效辯護為由提起上訴,原審辯護人辯解之所以沒有傳喚其出庭作證,是因為被告人曾經告訴他,該證人目睹了其作案的經過。因此雖然該證人能夠提供部分有利于被告人的證言,但可能會暴露對被告人更不利的證言,正是基于這種考慮,他才選擇不申請該證人出庭作證。在本案中,證人目睹了被告人作案的經過,這是被告人與辯護人之間的秘密,辯護人有義務保密,但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辯護不是無效辯護,辯護人可以在法庭上將該秘密陳述出來,而不會違反辯護人保密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