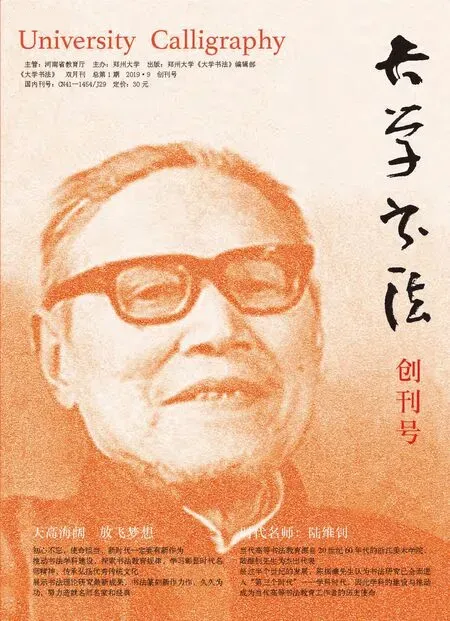費新我書《石鼓歌》長卷賞析
⊙ 李逸峰
費新我先生是以左筆書法名世、享譽當代的書法大家,82歲所書韓愈《石鼓歌》長卷,無疑是他晚年的精品。
此卷全長850厘米,高32厘米,正文前有沈鵬先生隸書題耑:“費新我書韓昌黎石鼓歌卷。”款識:“費老左筆天下所重,是卷凝重奔放,縱橫捭闔,今為張海兄得之,可不寶諸?辛未春客洛,沈鵬謹識。”正文后費新我先生自己有兩段落款,一為作品創作結束時所書:“韓愈《石鼓歌》,乙丑年白露節前三日,新我左筆,時在中州,年方八二。”一為先生四年后的落款:“余書過長卷凡四首,錄宋詞為自己展用;次錄《秋興八首》贈日友村上三島先生;再次即此卷,為張海同志所書;其后為港友蘇輝城君書了《赤壁賦》。張海致力書法事業,可謂全神以赴,與余交往,又承尊誠相待,豫中裝裱特精,此卷即出裝裱大師盧德驥之手。張海搜羅吾作尤夥,莫不什襲珍藏。余嘗戲言,百年以后,爾可刪去一部分,開吾遺作展矣。今日看來,此幅當為展品之一。一九八九年己巳冬仲,新我又志于蘇州。”
費老此作,體現出他晚年書法的典型風格,折射出他深邃的藝術思想,表現出一種積極的人生力量,承載了一段深厚的師生感情。
先說風格。此卷《石鼓歌》沉著而放逸,奇崛而自然,是一種有限度的痛快,很自然的生拙,作品完美,風格鮮明。唐陸羽《釋懷素與顏真卿論草書》提到懷素論草書有句云:“其痛快處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宋代米芾自稱“刷字”,表現出的是“風檣陣馬,沉著痛快”的書風。費老書風成熟,顯然既非懷素狂草的驚蛇飛鳥之奇,亦非米芾“風檣陣馬”雷霆萬鈞之勢。但與懷素相似之處在于左沖右突縱橫捭闔的放逸,與米芾相通之處在于沉著猶能痛快,奇正相生而不違自然。只是費老的痛快放逸是有限度的,它的筆下時時有反向拉力的約束,所有的線條如橡皮筋能夠自然彈出,如“悠悠球”可以隨時收回,是音樂的休止符,收束中積蓄力量,是潮起潮落的力度轉換,是去還復來的筆勢回環。沈鵬先生評價“凝重奔放”,此言得之。費老的自然,不是米芾右手刷字的自然流暢,而是左筆揮毫的自然生成。漢字的書寫本來是在右手執筆狀態下形成的規程與范式,但費老56歲病腕,不得已轉換為左手書寫之后,在不違背生理特點的同時,奮力追摹古人經典,成就了一代讓世人可以接受乃至贊嘆的左筆書家。這種自然是人們基于對左手書寫效果的理解,又是對古人經典學習、呈現與創作的肯定。毫無疑問,這種自然與右手的自然書寫拉開了距離,與我們平常的接受形成了隔閡,于是審美上的陌生感便形成了,這就是難能可貴的生拙。張海先生曾在紀念費老的文章中分析“費老藝術語言的獨特”是來自“被動的選擇”,形成于“因勢利導的創造”。這種因勢利導,既遵循書法藝術的規律,又順應自身的書寫生理,“創意開竅,生發自我”。費老書法風格的形成是主動思考與積極創造的結果。正是這種植根于傳統的“自我生發”,讓費老以戛戛獨造的個性面目享譽書壇。啟功先生曾題詩贊:“爛漫天真鄭板橋,新翁繼響筆蕭蕭。天驚石破西園后,左腕如山不可搖。”
次說思想。費老對于書法的理解充滿辯證法思想,其書法風格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形成的。他在很多場合都提出對書法中的辯證觀念的認識。新加坡中國書學會主席陳聲桂先生回憶費老在新加坡講課的精彩內容:“熟能生巧,順乎自然。逆—順不如,拙—巧不如,生—熟不如,奇—正不如。”這些對書法藝術的辯證理解源于《道德經》的古老智慧,“道法自然”“大巧若拙”“奇正相生”在費老的創作中運用得十分自然。求逆而不違順,求拙而不乏巧,求生卻自然熟,求奇卻反而正。思想是行動的先導,沒有深刻的認識與豐富的閱歷,無法在自己從事的工作中跳出來反思和觀照,更不能進一步用理論去指導自己的實踐。但費老對于左筆逆行的控制,對于生拙氣息的追求,對于奇正關系的處理,既從實踐經驗上升到了理論的高度,又能在創作中理性地加以運用。陸家衡、俞建良稱費老作書“富有節奏,抑揚頓挫”,“快而不滑,遲而不滯”。日本著名書法家村上三島評價費新我先生“不僅是一位藝術家,而且是一位哲學家”。一位藝術家,需要具備一定的哲學素養,費新我先生是典范。
再說力量。一件藝術作品,如果既具備出色的藝術創造能力,又有可圈可點的哲學內涵,就有可能成為經典。中國藝術還有一點很重要,即“知人論事”。尤其是書法藝術,人的因素十分重要。如果作品背后還有一位值得推崇的作者,作品與作者將會顯示出強大的力量。費新我學養多元,閱歷豐富,人生坎坷。中年右腕罹病,對于一位書法家而言可謂藝路阻絕,但他奮發圖強,不甘天命,他的左筆作品就是與命運抗爭的寫照。此卷《石鼓歌》我們看到了倔強中的奔放,拘束中的突圍。一種反向的力量在抗爭,恰恰給人以正向的引領。張海先生說他作書:“使人感受到抗爭的吶喊與勝利的豪邁。”費老求“新我”,表現出不屈的精神與堅強的意志,這種力量完美地通過左筆書法呈現出來,自然形成符合自己個性的獨特的藝術語言,這種力量將隨著歲月的沉淀,越發顯示出奪目的光芒。
最后說情感。韓愈作《石鼓歌》,章法整齊、辭嚴義密、音韻鏗鏘,詩人在描繪石鼓文書法的妙處時,運用了多種比喻,進行淋漓盡致的渲染,頗有感染力。費老一生創作了四個長卷,此為其一,專為張海先生所書。他選擇此詩進行創作,看得出來,內容方面是接受的,情感方面是喜歡的,創作過程是輕松愉悅的,表達也是淋漓盡致的,內容與形式可謂完美統一。“張海搜羅吾作尤夥,莫不什襲珍藏,余嘗戲言,百年以后,爾可刪去一部分,開吾遺作展矣。今日看來,此幅當為展品之一。”從跋語可知費老對此作寄寓的情感以及對作品的評價與期待。張海先生與費老有長達16年的交往,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此卷是這種情誼的見證。據張海先生回憶,他與費老結緣始于1974年,當時在北京榮寶齋學習,偶然的機會看到出版的《魯迅詩歌》與《人民中國》,《人民中國》上面有費新我所書毛澤東《十六字令》排在第三幅,對費老的左筆書法產生了深刻的印象。兩年后,張海先生慕名邀請費老題寫《現代書法選》書名,但費老地址不明,只好寄往江蘇美術出版社轉交。不久即收到一繁一簡兩條題簽,并稱如不合意還可另寫,令人感動。1978年,時在安陽文化館工作的張海先生邀請費老來河南講學近一個月。費老本已年邁,不便輕易出門,但張海先生寄出邀請函的同時,還匯去150元作為來程路費,并希望還能帶一年輕人照顧他。這一做法讓費老感動不已,覺得這人做事與眾不同。從此費老對張海先生十分認可,先后有九次中原之行,并帶頭捐款支持成立河南書法獎勵基金會。此后張海先生一直執弟子禮,多次為費老操辦個展,陪同國外講學,出版《費新我書法大字典》,策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紀念費新我先生誕辰110周年座談會”,積極促成費老家鄉建立“費新我書法藝術館”,并為藝術館捐贈費老遺作和自己作品。2016年張海先生在鄭州大學書法學院為廣大師生設立獎勵基金,名稱就叫“新我獎”。而費老生前對張海為人從藝的點滴進步,都寫信給予熱情的鼓勵。如1991年得知張海任河南省書法家協會主席時,他寫道:“……又聞你省書代會中,你被推為主席,這是一直盡力職責,貢獻甚大之報,可喜可賀。年事正如日中,又才能富強,前程無限。你好像說過,不想當官。我認為像你今日所為,有功社稷,最為可取的。”這種新型的師生關系所彰顯的情誼,何可勝道?
張海先生收藏費老作品不少,而對此件尤為鐘愛。值此《大學書法》創刊之際,印行此作,化身千萬,無償贈與,以饗讀者。藝術的感染力,正隨著這種師生情誼的深化與延續做著歷史的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