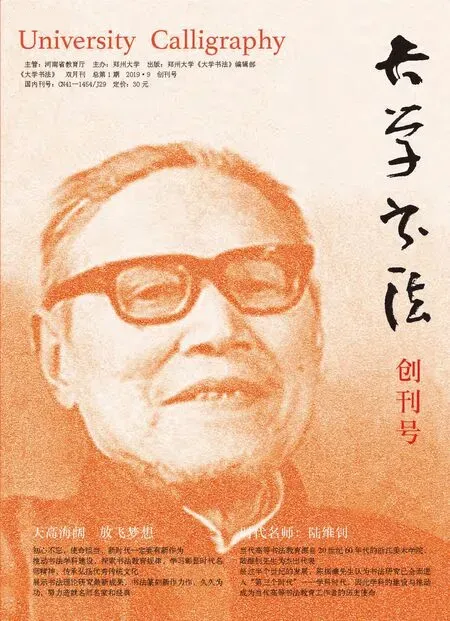內在脈絡視閾下的書法史分線教學研究
⊙ 陳榮謙
民國七年(1918),蔡元培先生于中國第一國立美術學校開學演說中云:
惟中國圖畫與書法為緣,故善畫者,常善書,而畫家尤注意于筆力風韻之屬。……甚望茲校于經費擴張時,增設書法專科。[1]
如今恰逾百年,書法學科教育已發(fā)展至博士、博士后階段,但書法史教學專門教材仍付闕如,此與高等書法教育之發(fā)展不大相類。據筆者不完全統計,書法史(專著或教材)有50余種之多,除卻近一半的斷代史之外,真正的書法通史也就20余種。從這些通史來看,其寫作方式基本上都是以時代敘書家,以書家寫作品。這樣的書法通史作為教材,盡管能夠給予學生史的觀照,但同時也存在著體系不清、理路不明的問題。故筆者不辭鄙陋,提出分線教學之構想。
一、正字規(guī)范與書法史的演進
學生剛進大一,第一學期講述正字規(guī)范與書法史的演進。此安排,由漢字基礎且重要的位置決定,樹立正確的文字書寫觀,是書法學習重要的一步。正字規(guī)范涉及篆、隸、楷、行、草五體。前三體為靜態(tài)書體,后兩者為動態(tài)書體,各有特點。此處所言正字規(guī)范,即是指官方正定并使用的文字規(guī)范。
其一,篆、隸、楷書寫規(guī)范與書法史的演進。《周易·系辭下》云:“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2]由刻符圖像經由甲骨而演至各體,文字從產生到演進,對華夏文明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以篆論,秦始皇兼天下,即“罷其不與秦文合者”[3],并交由名書家李斯正定字形,書寫范式,十二年間計有名刻《泰山》《瑯琊臺》《嶧山》《碣石》《會稽》《之罘》六處。《碣石》《之罘》雖早失,四山流傳中風韻可睹,字形既正,審美之多樣化亦同步追求,是以有《袁安》《袁敞》風格之異。唐李陽冰遙接李斯,自詡“斯翁之后直至小生”,觀其《李氏三墳記》《謙卦爻辭》《般若臺題名》等,既合規(guī)范又曲直相宜,誠當斯言。宋代趙宦光似新意獨標,而篆法之失昭然。直抵清代,考據大興而致篆書復明,始有鄧石如、吳讓之而至近現代吳昌碩、齊白石之流。東漢靈帝熹平四年(175),蔡邕以“經籍去圣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后學”[4],遂奏請正定六經文字并手書標準漢隸,刻石豎于洛陽鴻都太學門外,此為《熹平石經》。石刻完工后,“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余輛,填塞街陌”[5],足見盛況。爾后六十余載,名書家衛(wèi)覬仿此正字,書碑豎立于太學講堂西側。是碑每字皆以古文、小篆、漢隸三體寫刻,故稱《三體石經》。唐重刻《嶧山》以正篆學,然以去古遠而藝態(tài)失,故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南北朝周興嗣受梁武帝之命,將殷鐵石拓自大王書之一千不同且無序之字韻而成文,“一夕編綴進上,鬂發(fā)皆白”[6],用以教諸帝子,此即《千字文》。歷代名書家都有不少寫本流傳,宋徽宗、宋高宗、清康熙等也都有寫本傳世。明《文淵閣書目》與《晁氏寶文堂書目》所錄各體千文計有40余種。另外,漢許慎所著《說文解字》及晉呂忱《字林》、南梁顧野王《玉篇》、唐顏真卿《干祿字書》等,也均屬古代正字范本。
其二,行、草正字規(guī)范與書法史。文字發(fā)展到草、行書階段,正字規(guī)范更顯重要。以章草論,傳漢元帝時史游以章草作童蒙字書《急就章》,此后,歷代書家爭相傳摹,三國皇象、明宋克為其中高手。西晉索靖《月儀帖》為當時書信樣式和正字規(guī)范。近世書家高二適先生耗時十余年寫就《新定急就章及考證》,堪稱中國書法史和文字學研究杰作。史上名書家如智永、孫過庭、張旭、懷素、高閑、祝允明等均有草書《千字文》傳世。近世于右任先生《標準草書》,廣集歷代書家規(guī)范草書,正定字形,可視為草書正字之最高成果。而行書正字規(guī)范,歐陽詢、文徵明、董其昌、朱耷等也都有《千字文》寫本流傳。
其三,教學方式。正字規(guī)范是社會發(fā)展歷史性選擇,文字的規(guī)范和美化具有典范與美學意義。所以,《千字文》《急就章》《說文解字》是古代教育和文明的高度濃縮。正字教育,旨在樹立正確的文字和書法教育觀。繼而,要進一步深入到以名書家書寫標準樣式的核心含義:作為同時具有文本、藝術雙重意義的書寫行為,正字教育和書法藝術本身是密不可分的。這也為學生判斷和區(qū)分古代的正字范本與書法作品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古代有些作品,本是為正字而書寫的,但因其多出名家之手,故書法史著作往往劃入書法。當然,我們也不否認某些正字范本在藝術上同時達到了相當的高度,但在書法史教學中提出正字教育范本和書法作品的問題,有著重要的區(qū)分與文化意義。
二、傳承譜系的演進
有了第一學期文字與書法關系學習的基礎,使學生明白中國書法史上典范的涵義。此涵義不獨包含文字典范,亦涵蓋書家典范。書家既然形成典范,必有其清晰的傳承譜系。故第二個學期講述書家傳承譜系的演進。
第一,明文的譜系史。筆法,是中國古代書法傳授的核心,故書家傳統譜系以此展開。唐人韋續(xù)《墨藪》及張彥遠《法書要錄》所收《傳授筆法人名》、宋朱長文《墨池編》與陳思《書苑菁華》,基本勾勒出古代筆法譜系。
《傳授筆法人名》云:
“蔡邕授于神人而傳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之鍾繇,鍾繇傳之衛(wèi)夫人,衛(wèi)夫人傳之王羲之,王羲之傳之王獻之,王獻之傳之外甥羊欣,羊欣傳之王僧虔,王僧虔傳之蕭子云,蕭子云傳之僧智永,智永傳之虞世南,世南傳之,授于歐陽詢,詢傳之陸柬之,柬之傳之侄彥遠,彥遠傳之張旭,旭傳之李陽冰,陽冰傳之徐浩、顏真卿、鄔彤、韋玩、崔邈。”[7]
盧攜的《臨池妙訣》載:
“吳郡張旭言,自智永禪師過江,楷法隨渡。永禪師乃羲獻之孫,得其家法,以授虞世南,虞傳陸柬之,陸傳子彥遠,彥遠仆之堂舅,以授余。……近代賀拔員外惎、寇司馬璋、李中丞戎與方皆得名者。蓋書非口傳手授而云能知,未之見也。”[8]
解縉《春雨雜述·書學傳授》則為集大成者:
“書自蔡中郎邕,字伯喈,于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秘,遂為書家傳授之祖。……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傳其子汯,其孫樞在洪武中仕為中書舍人,與仲珩、叔循聲名相埒云。”[9]
鄒宗淼《“二王”書法譜系的藝術人類學考察》[10]中綜為《“二王”書法譜系簡表》(見表1),此為中國書法高度濃縮。
就脈絡論,書法世家(家學)、書法流派等均為譜系補充。以魏晉為例,有陸、衛(wèi)、索、王、謝、郗、庾七大書法世家,而唐代顏、殷、歐、虞、褚、薛、顏、柳等書法家學亦同。流派之中,兼師博采、和而不同,也忠實反映同一地區(qū)尊前攜后的優(yōu)良士風,如吳門書派、云間書派。古代經卷的謄錄書跡,通常歸為“經生書”,雖本于佛教傳播,而其中不乏書藝高超者,客觀上也是中國書法的重要傳承和推動力量。

表1 “二王”書法譜系簡表
第二,書家(書跡)的接受史。由于明文譜系有編撰時間、人物選擇等局限性,故傳統譜系中沒有列入的書家,我們需要作個案來講述,這就是書家(書跡)接受史教授之目的。接受史中,書家、書跡的挑選要具有藝術高度、文化典型意義。以《石門頌》為例,文中記載:“中遭元二,西夷虐殘,橋梁斷絕,子午復循,上則縣(懸)峻,屈曲流顛,下則入冥,傾寫(瀉)輸淵。”[11]凸凹不平崖石上的書寫,經由刻工、自然風化、破損等共同作用,《石門頌》的開合有度、揮灑自如、厚重粗獷的整體藝術形象得以呈現在世人面前,并對中國書法史產生重大影響。這不得不歸功于北魏酈道元,其《水經注·沔水》載:“褒水又東南歷小石門,門穿山通道,六丈有余。刻石言:漢明帝永平中,司隸校尉犍為楊厥之所開。”[12]雖酈氏據碑文中“楊君厥字孟文深執(zhí)忠伉”[13]斷楊君“厥”為其名,“孟文”為其字,但經宋代洪適《隸釋》考證,“厥”實為語助詞,可解釋為“其”或“他的”之意。同時,洪氏引《華陽國志》所載,楊君實名渙,字孟文。酈氏雖誤,致后有部分學者以訛傳訛,但首研之功不可沒。宋歐陽修《集古錄》名是碑為《漢司隸楊厥開石門頌》;趙明誠《金石錄》徑稱為《楊厥碑》;清王昶作過評述,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對碑中部分文字作過考證;方朔《枕經堂金石題跋》分析其筆法、結字、美學特點,指出“褒斜山谷地處幽險捶拓不易,故得之者少,而石亦能保永久也”。[14]翁同龢《石門頌跋》指出“此碑字疏密不齊”。[15]楊守敬《激素飛清閣平碑記》評云:“其行筆真如野鶴閑鷗,飄飄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從此出。”[16]而俞宗海《石門頌跋》有“字畫皆方,精神結構絲毫不爽”[17]之評。張祖翼《石門頌跋》更是評云:“三百年來習漢碑者不知凡幾。竟無人學《石門頌》者,蓋其雄厚奔放之氣,膽怯者不敢學,力弱者不能學也。”[18]此后康有為、李葆恂、章太炎、祝嘉于茲皆有盛譽。1949年前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辭海》封面“辭海”二字,就取自于《石門頌》。而《石門頌》現當代接受者,更不知凡幾。深度挖掘以《石門頌》為代表的書跡或書家接受史,不僅是對傳統譜系的一種補充,更是學生學書讀帖的不二法門。
第三,教學方式。教師首先要讓學生理解書法非“口傳手授”而不能是由學科特點決定,非獨神秘之渲染。加以古代藝業(yè)擇賢而授之特點,書學難免受其影響。接下來要對譜系作梳理,譜上書家要綜以史料、書風、作品、師承、游學等后,方作合理與否之辨析。此目的在于引導學生思考,排除附會與杜撰類書家。分析、總括后學生同時也會發(fā)現,古代的譜系,實則是以“二王”為綱的譜系,且多涉及行、草的書法傳授。而楷、篆、隸、甲骨以及取法碑版一路的書家基本沒有涵蓋入譜。其次,既然已經擴展到譜系本體之外,則學生視野為之開闊,書法世家(家學)、帝王統系、流派群體、經生書等即可展開教學。其三,譜系實則為書家接受史,教學中學生得以從總體上把握一個書家、一種風貌在各時代的接受、演變。此不唯提升學生學養(yǎng)與思維能力,關鍵還生發(fā)出對創(chuàng)作方向歷史性的定位和思考。
三、“書品”演進
在正字規(guī)范、書家譜系厘清之后,必然涉及古典書論之教學。縱觀古典書學發(fā)展史,也即為書品之演進史。理論家的好惡品評,不斷為后人所推衍,形成中國兩千年書品史。而其中的批評話語,不斷組成范疇體系,構成了中國古典書法美學的框架。因此,在第三學期,要逐漸脫離文字解說、書家講論之模式,最終為第四學期技道演進板塊的教學打下思辨基礎。
其一,“書品”發(fā)展史。以品論書屬古代較為科學和統系的評述范式。品鑒之風,最早見于班固《漢書·古今人表》[19],后遷及藝術。南朝庾肩吾《書品》,首開以品論書之先。庾氏以“天然”“工夫”為標準,分上、中、下三品,每品又各分三等,對漢至齊梁能真書、草書者123人進行品評,具有重要開山意義。其中,“上之上”為:張芝、鍾繇、王羲之,王獻之列為“上之中”。[20]雖僅座次排定,且無多義理創(chuàng)見,勾勒亦嫌粗略,然開創(chuàng)之功不可沒。比之于梁武帝蕭衍之評,王羲之地位有所提升。初唐李嗣真襲于此,作《書后品》,增設逸品,共品評書家82位。逸品為四品之首,李斯小篆、張芝章草、鍾繇正書、王羲之三體及飛白書、王獻之草行書及半草行書在列。李氏以“子敬草書逸氣過父”[21]而提升獻之地位,又將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與晉衛(wèi)夫人、郗鑒、庾翼、南朝宋羊欣等名家同列,足見其不薄今厚古,實為一個大膽的嘗試。他同時指出:“元常每點多異,羲之萬字不同。”[22]可見對形式與變化的關注。至張懷瓘《書斷》,首創(chuàng)神、妙、能三品概念,闡十體源流,述書家174位,又將書家歸入其所擅長之體,較以往書評的籠而統之,此大利于觀者從整體和局部把握所評書家。而朱長文仿其體例作《續(xù)書斷》,評述唐宋83位書家。列神品三人:顏真卿、張長史、李陽冰。朱氏本于傳統,既具時代特征而又不被時風左右。包世臣著《藝舟雙楫》,置神、妙、能、逸、佳五品,并提出明確標準,既繼承張氏,亦吸納唐、宋畫評方式。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于五品之外又置“高”品,楊景曾《二十四書品》唯風格之異,而無等級之別。
其二,作品風格評述。古人評述作品,寥寥數字,耐人尋味。找準關鍵詞,大便利于教學。以“媚”為例,《說文解字》云:“媚,說也。從女,眉聲,美秘切。”[23]而古代“說”同“悅”,此即“媚”之基本含義。南朝宋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云:“王獻之,晉中書令,善隸、藁,骨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24]此為較早以“媚”評書的名句。“媚趣”與“骨勢”相對的,前指陰柔,后指陽剛。南朝齊王僧虔《論書》中的“緊媚”及《又論書》中的“婉媚”皆本于羊欣。而南朝梁武帝《草書狀》中的“巧媚”則是對多種風格的統述。到唐代,書評家對“媚”則多持批評態(tài)度。唐張懷瓘《書議》云:“逸少草有女郎才無丈夫氣,不足貴也。”[25]此評雖不著“媚”字,而意指“媚”態(tài),批評大王書短于陽剛。其《書后品》的“風媚”及其《書斷》的“韻媚”、竇氏的“秾媚”“軟媚”皆屬此。獨顏真卿《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26]中的“雄媚”,賦予“媚”以新的內涵,意在追求妍美中氣格的飽滿。宋的理解近于南朝,如朱長文的“緊媚”與“媚態(tài)”、姜夔“妍媚”即是。明代,即便同一評論者,在使用“媚”時也有差異。如明項穆《書法雅言·心相》中評價趙孟頫的“妍媚”與他處使用之“妍媚”“遒媚”差異甚大。他評趙氏書法“妍媚”,主要是針對趙做人沒有氣節(jié)而言。[27]清代對“媚”的理解又更全面,如清朱履貞《書學捷要》云:“故書之精能,謂之遒媚,蓋不方則不遒,不圓則不媚也。”[28]很明顯,此處以方、圓來判斷“遒”與“媚”,屬獨創(chuàng)。錢泳《書學》云:“自右軍一開風氣,遂至姿媚橫生,為后世行草祖法,今人有謂姿媚為大病者,非也。”[29]包世臣《藝舟雙楫》云:“至于狂怪軟媚,并系俗書,縱負時名,難入真鑒。”[30]康有為用得較多,有“姿媚”“遒媚”“嫵媚”和“婉媚”,依其語境不同,意思各異。
其三,教學方式。教師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文字梳理。學生如何讀懂話語,是本線索教學的首要任務。其次,對“書品”的演進史要做體系化教授,務必厘清各時代書法品評的繼承和發(fā)展狀況,包括等級標準制定、敘列方式、風格評述等,要便于學生去系統把握。接下來進入“書品”的“關鍵詞”教學環(huán)節(jié),精選出關鍵性的語言和詞匯,著眼于其使用語境和社會背景,循此做不同時代的書論家之間的比較。最后,要分析和總結同一書家在不同時代所獲評價及其地位變化的內在文化含義。
四、書論中的“技”“道”演進
經過一年半的學習,學生在技法和理論上的都有了一定的提升,所以在第四學期,專門就“技”“道”問題設一板塊,目的在于通過教學樹立學生正確的“技”“道”觀念,讓學生真正走上“胸中有道義,又廣以圣哲之學”之路。
第一,書法中“技”的發(fā)展史。漢蔡邕在《九勢》中云:“藏頭護尾,力在字中。”[31]這是較早關于“技”的論述。《九勢》通過對用筆、結體的概括,揭示書法美感的核心在于生氣與動態(tài),這對之后的技法探究有著根本性影響。三國鍾繇“用筆者天也”[32],高度肯定用筆的重要性。同時這種總括而寬泛的描述,也賦予后人對用筆諸多的聯想和想象。東晉衛(wèi)鑠《筆陣圖》,雖仍停留于“意象”階段,而“骨肉”[33]之論已觸及用筆內質。隋釋智果《心成頌》,首次延伸到結構技巧分析,歐陽詢《八訣》《三十六法》、唐太宗《筆法訣》對基本點畫、用筆要領、結構技巧等論述頗深。唐孫過庭《書譜》道及遲速等重要問題,張懷瓘《論用筆十法》《玉堂禁經》等論筆法、字法相對全面,而且注明鍾繇、張芝、二王、歐陽詢、虞世南等用過某法,雖不無附會之意,但也在某種程度上說明其對古法的研究和理解。元陳繹曾《翰林要訣》已繼坡翁深入到筋、骨、血、肉等水墨、用筆層面。其余豐坊、宋曹不過粗涉。而真正技法論述高峰的到來是包世臣、劉熙載、康有為等人,分析較細,評述亦全,勝前較多。總之,古代技法論述著墨不多,且缺乏精細分析。
第二,古代“技”與“道”的矛盾問題。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儒學即成正統思想。而《論語·述而》所云“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34],無疑為古代書家念了“緊箍咒”。又科舉仕進的大環(huán)境籠罩下,兼漢趙壹《非草書》[35]對書法藝術的非難,書家只能如履薄冰地釋放書法熱情。唐李嗣真尊德抑藝[36],北宋石公操則直言輕視態(tài)度:“至謂書乃六藝之一,雖善如鍾、王、虞、柳,不過一藝而已。吾之所學: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也。”[37]而另一些書評家則積極為書法立身找尋注解。西漢揚雄《法言·問神》中的“書,心畫也”也由此讓他們靈光一現:抑技揚道,將道德的弘揚寓于書理之中,這既不違儒也合于封建統治階層馭臣治民之術。以至于明有文徵明“人品不高,用墨無法”的略顯滑稽可愛之論調。而遠在文氏之前,歐陽修、米芾就已經公開流露對書法的不拘與摯愛。相較而言,蘇軾還是本于書為心畫說。[38]這種方式,經由董逌發(fā)展到劉熙載總結為“書,如也”的典型的人品和書品的統一觀。而項穆、傅山及朱和羹,不過本于此論調而展開。
第三,教學方式。啟悟學生“技”的精煉表述背后所蘊含之深邃與精華,并比較與當下筆法分析的異同,是教師的首要任務。同時,列舉古代文論評述,以便學生理解古人的比況、想象等手法。接下來,教師分析儒家思想對書法的深度介入與干預,給學生展示一個更為廣闊的“技”“道”世界。囿于儒家思想和藝術處于末次的排定,古人尚缺乏以藝術立身的堅定信念。所以,在歡喜和無奈之間,找到一個合理的注解,以坦然展示書藝成為必然。書法作為道德的踐行與表達,也即成為書家普遍的贊同與附會。最后,圍繞此話題,對書論中以書觀人、以人觀書、因人廢書、書以人彰等問題即可迅速而合理地展開討論,對蔡京、趙孟頫、張瑞圖、王鐸等書家的理解也才能相應得到更客觀、深入且符合歷史真實的分析。教師需要給學生強調的是,今日書法教育之專業(yè)化和書家的職業(yè)化,乃社會文明發(fā)展之自然選擇。書法作為“末事”的身份已成過去,只有持高度負責的從業(yè)責任心和自豪感,才能推動書藝向深廣發(fā)展。
結語
通過四學期書法史分線教學,從文字、書家、風格、技道四個維度全面囊括書法史范疇。書法史教學,嚴格而言乃屬一尚未從方法論上得到充分重視的問題。分線教學研究目的在于從整個書法史內在脈絡上尋求聯系和突破,實現高等書法史教育的立體、網絡和深入、學理化。既往的書法史,主要都是在朝代下羅列書家和作品,無法良好實現書家、書跡橫向和縱向上的內在脈絡關聯。當教師把歷史知識如數羅列給學生后,零散的書史資料很難在學生頭腦中形成足夠系統的知識脈絡。因為于書法而言,如果僅僅是一部作品史、人物史,那無疑是部線條史。而單純的線條,是沒有靈魂和思想的。有鑒于此,書法史的分線教學研究,具有立足專業(yè)、寬厚、高效教學的訴求探索意義,期待以此切實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yǎng),以為將來書法學學科的進一步建設與發(fā)展夯實基礎。
當然,分線教學自身也是存在缺點與不足的。比如,教學中趣味如何開發(fā)、教師知識結構如何完善、線索如出現內容交叉如何處理等,都有待進一步研究、解決、細化與深入。而事實上,想要突破歷史教學本身,在各個學科都是非常棘手的問題,因為其板塊分屬難以彌合,必然有所重復或缺漏。尤其學生書法史觀、審美旨趣、書法獨立創(chuàng)作能力都各不相同,而這恰恰事關書法藝術未來的方向、創(chuàng)作水平與高度。然也正因如此,本文的探索才顯得尤其珍貴。在實際教學中,各高校如能視自身情況,銳意進取,為書法史的教育教學提升、創(chuàng)新而不懈努力,那么作為拋而引玉的那塊磚,本研究也屬幸甚了。
注釋:
[1]蔡元培.在中國第一國立美術學校開學式之演說[G]//北京大學出版社,蔡元培美學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77.
[2]孔穎達.周易正義·系辭下[G]//阮元.十三經注疏: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87
[3]許慎.說文解字序[G]//崔爾平.歷代書法論文選續(xù)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7:“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
[4]范曄.后漢書·蔡邕列傳第五十下[G]//二十四史(縮印本).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2013:521.
[5]范曄.后漢書·蔡邕列傳第五十下[G]//二十四史(縮印本).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2013:521.
[6]崔令欽等.歷代筆記小說大觀·教坊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88.
[7]張彥遠.法書要錄[G]//盧輔圣.中國書畫全書.第1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34-35.
[8]盧攜.臨池妙訣[G]//盧輔圣.中國書畫全書.第3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98.
[9]解縉.春雨雜述[G]//崔爾平.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499-500.
[10]鄒宗淼.“二王”書法譜系的藝術人類學考察[J].書法賞評,2012(5):45-54.
[11]孫寶文.石門頌[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3.2016:11-13.
[12]酈道元.水經注疏[M].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2307.
[13]孫寶文.石門頌[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3.2016:19-20.
[14]舒懷.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文字分典[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14:4414.
[15]童衍方.藝苑清賞·晏方品珍[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279.
[16]李檣.杞芳堂讀碑記[M].浙江:西泠印社出版,2014:426.
[17]中國碑帖名品·石門頌[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82.
[18]滕西奇.石門頌寫法與注譯[M].山東:山東美術出版社,2011:181.
[19]班固.漢書·古今人表第八[G]//二十四史(縮印本).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2013:226:“因茲以列九等之序,究極經傳,繼世相次,總補古今之略要云。”
[20]庾肩吾.書品[G]//崔爾平.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87.
[21]李嗣真.書后品[G]//崔爾平.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135.
[22]李嗣真.書后品[G]//崔爾平.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136.
[23]許慎.說文解字[M].第3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57.
[24]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G]//崔爾平.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47.
[25]張懷瓘.書議[G]//崔爾平.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149.
[26]顏真卿.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G]//崔爾平.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279.
[27]項穆.書法雅言[G]//崔爾平.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532:“若夫趙孟頫之書,溫潤閑雅,似接右軍正脈之傳,妍媚纖柔,殊乏大節(jié)不奪之氣。”
[28]朱履貞.書學捷要[G]//崔爾平.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604.
[29]錢泳.書學[G]//崔爾平.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1979:628.
[30]包世臣.藝舟雙楫[G]//崔爾平.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657.
[31]蔡邕.九勢[G]//崔爾平.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6.
[32]陳思.秦漢魏四朝用筆法[G]//崔爾平.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399.
[33]衛(wèi)鑠.筆陣圖[G]//崔爾平.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22.
[34]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G]//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481.
[35]趙壹.非草書[G]//崔爾平.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2-3:“鄉(xiāng)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講試,四科不以此求備,征聘不問此意,考績不課此字。善既不達于政,而拙無損于治。”
[36]李嗣真.書后品[G]//崔爾平.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133-134:“蓋德成而上,謂仁、義、禮、智、信也;藝成而下,謂禮、樂、射、御、書、數也。”
[37]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6[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99:760.
[38]蘇軾.論書[G]//崔爾平.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314:“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態(tài),不可掩也;言有辯訥,而君子小人之氣,不可欺也;書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