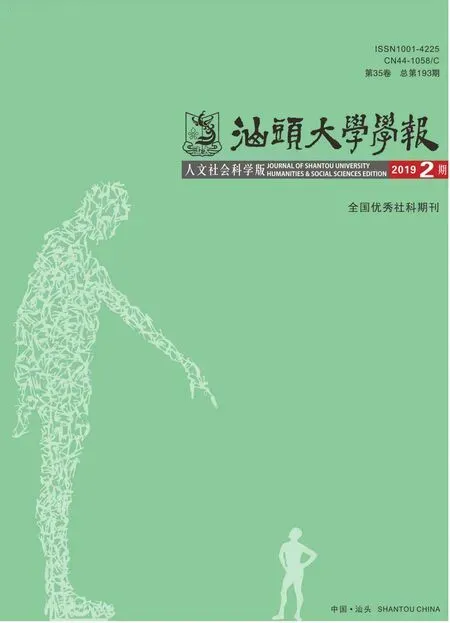“新國學”與民族文化傳統(tǒng)中的民間價值譜系
傅書華
(山西大學商務學院文化傳播學院,山西 太原 030031)
在“新國學”[1]構(gòu)建中,對民族文化傳統(tǒng)中的民間價值譜系應該給以足夠的重視。
中國的民族傳統(tǒng)文化大致可以由三個價值譜系構(gòu)成:廟堂文化、士大夫文化、民間文化。由于中國的讀書人在傳統(tǒng)社會中,一向是學而優(yōu)則仕,所以,士大夫文化與廟堂文化有著密切的親緣關系,雖然廟堂文化一向也標榜親民,士大夫文化也推崇反映民生疾苦,但由于廟堂文化、士大夫文化,以江山社稷為價值本位,以群體關懷為價值本位,而民間文化是以個體感性生命為價值本位,所以,民間文化雖然與士大夫文化也有著相當?shù)挠H緣關系,與廟堂文化也有著一定的親緣關系,但相對廟堂文化與士大夫文化的親緣性來說,民間文化與士大夫文化和廟堂文化更具有疏離性。但其卻是在汲取傳統(tǒng)文化構(gòu)建“新國學”時的最重要的價值資源。
民間文化實際地生成、存在并流變于民間的個體生命的生存形態(tài)中,作為價值形態(tài),則在傳統(tǒng)文學的發(fā)展歷程中,有著鮮明的體現(xiàn)。
《詩經(jīng)》可以視為民間文化的源頭。《詩經(jīng)》中無論是訴說男女之情,如《關睢》《邙》,還是控訴對自身利益的剝奪,如《碩鼠》,亦或是感慨于戰(zhàn)爭,如《東山》,都是站在個體生命立場上的情感與價值判斷,譬如《東山》,絕無戰(zhàn)爭獲勝后的喜悅或豪情,而是個體離鄉(xiāng)回鄉(xiāng)之后的感傷。這只要與屈原的《離騷》相對比,即可一目了然。
這樣的一種價值形態(tài),在其后的《漢樂府》中也有著充分鮮明的體現(xiàn),最典型的莫過于《木蘭辭》。木蘭打仗,既不為國家也不為民族,而是為其父親。所以,在獲勝之后,才會對將賦予自己的社會價值評判不屑一顧:“木蘭不用尚書郎”,而將其個人生活作為其價值歸宿:“脫我戰(zhàn)時袍,著我舊時裳”[2]。這是不同于大致同一時代的以清高來對比于廟堂但最終是以廟堂為旨歸的陶淵明的。
秦帝國當時能夠剪滅群雄,自是因其所建立的經(jīng)濟政治結(jié)構(gòu),相較于當時群雄,具有更大的能量,這一經(jīng)濟政治結(jié)構(gòu)所能夠生成的能量,在盛唐時代達到了巔峰,其思想精神情感的文學標志,就是唐詩。又由于在這一歷史變遷中,社會變革的力量較之于個人命運的力量更為強大,所以,吟誦對歷史變遷之感慨的李白杜甫成為了那一時代的主流詩人,對個人命運發(fā)出杰出之聲的李商隱杜牧,則只能被稱為小李杜,明顯要比李杜低一個層次。李商隱之《無題》詩,雖然常常被附會上許多政治含義,但將個人生活、情感看得高于社會風云,卻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作為社會風云的“巴山夜雨”最終也只能化為“共剪西窗燭”之時的夫妻私語的語料了。杜牧雖然也有《阿房宮賦》《過華清宮》等名篇感慨時事,但他的《遣懷》卻也可以算作他的抒懷之作。“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3]。他心心念念的,卻也更看重的是女子,這是較少受當時主流價值規(guī)范的青樓女子對他的評價。在小李杜的詩詞中,筆者分明聽到了對《木蘭辭》中“脫我戰(zhàn)時袍,著我舊時裳”的承續(xù)與變奏,也隱約可以看到《紅樓夢》中賈寶玉將瞬間女子之淚看得高于江山社稷的“癥候”。雖然他們都是作為有名有姓的文人而不同于《詩經(jīng)》《漢樂府》之無名無姓的草民,但在以個體感性生命作為價值本位這一點上,將他們視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民間價值譜系的承傳者,卻似乎也是可以成立的。更由于他們生活于李杜之后的晚唐,其對由唐入宋的中國歷史轉(zhuǎn)型也是一種先兆性體現(xiàn)。
由秦帝國所奠定的傳統(tǒng)中國的經(jīng)濟政治結(jié)構(gòu),其所能夠產(chǎn)生的能量在盛唐達于巔峰之后,終于在歷史辯證法的否定之否定定律的作用下,讓位于北宋的商業(yè)經(jīng)濟市民社會,雖然由于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經(jīng)濟與政治發(fā)展的不同步性,不平衡規(guī)律,占據(jù)北宋上層主流的暫時仍然是廟堂文化士大夫文化,但真正在社會上盛行的,卻是商業(yè)經(jīng)濟市民社會所必然帶來的民間價值譜系的個體感性生命的價值本位,所以,“凡有井處飲處,即能歌柳詞”[4],而三變之詞所遺恨的卻是“悔當初,不把雕鞍鎖”,所歌詠的卻是“向雞窗,只與蠻箋象管,拘束教吟課。鎮(zhèn)相隨,莫拋躲,針線閑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陰虛過”。不再是“聞雞起舞”而是“向雞窗……針線閑拈伴伊坐”[5],不再是因為未建功立業(yè)而發(fā)出的光陰虛過的“可嘆白發(fā)生”的遺憾與感慨,而是只有“和我”“針線閑拈伴伊坐”才是“免使年少,光陰虛過”,這可真正是對廟堂文化士大夫文化中“修齊治國平天下”理念的根本性顛覆了。
只是由于作為游牧文化的異族的武力入侵,讓正在被商業(yè)經(jīng)濟所取代的本已從巔峰狀態(tài)逐漸退下的農(nóng)耕文明得以在中國的歷史舞臺上,再次成為主角,也使得在巔峰狀態(tài)代表這一文明的廟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再次位居強勢。那一時代最具代表性的蘇東坡的兩首代表之詞《念奴嬌 大江東去》《水調(diào)歌頭 明月幾時有》一以社會時代為價值本位,一以個體感性生命為價值本位,正是那一時代士大夫文化價值譜系與民間文化價值譜系的雙峰并峙。而陸游也是在晚年既有著《示兒》這樣的憂國憂民的名篇,也有著“此身行作嵇山土,猶吊遺蹤一泫然”的感慨,這怕也不是偶然的。或許也可以視為那一時代精神特征的一種“癥候”。
雖說“崖山之后無中華”過于偏激,但作為游牧文化的異族的武力入侵,從根本上影響了中國北宋之后形成的歷史性轉(zhuǎn)型,怕也可以言之成理。作為原有文明載體的精英生命,被他殺或自殺導致的大量消失,在看到這一結(jié)局之后,在殘酷落后的生存條件下,造成了全民性的生存形態(tài)及精神形態(tài)的殘損與扭曲,從此之后,不但作為廟堂文化、士大夫文化正宗體現(xiàn)的詩歌,在宋代之后延及至清代,雖然數(shù)量不少,但在境界上再也不可企及唐詩,應是公認的事實。而民間文化也難免其辜,作為流行于坊間的民間文化載體的小說,或如《水滸傳》推崇“要當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或如《三國演義》迷信于帝王的人際爭斗之術,或如《西游記》自覺地用“天上之理”規(guī)范地上生命的感性。再也沒有了唐詩中那即使在窮困潦倒時也豪氣不減大氣不衰的旺盛精神,再也沒有了宋詞中那即使寫男女肉欲也健康清朗的飽滿情懷。唐詩宋詞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中肉成道身的生命生成中的飽滿,宋之后,則是道成肉身的生命漸漸的迷失。
好在物極必反,在傳統(tǒng)中國結(jié)束之際,有了“傳統(tǒng)的寫法都被打破了”的《紅樓夢》,有了將個體感性生命看得高于一切的賈寶玉這一“新人”的出現(xiàn),他從《詩經(jīng)》《漢樂府》小李杜、柳三變一路走來,并將與之并行而來的被視為圣人孔子一脈的賈政視為迂腐的酸儒,將與之并行而來的被視為仙風道骨的莊子一脈的賈赦視為荒淫之徒。這是民間價值譜系的大勝利,并以這一勝利結(jié)束了一個歷史時代,開啟了一個新的歷史時代。梁啟超的“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正是想籍古代中國民間性的小說成為現(xiàn)代中國文化的正宗從而讓民間價值譜系位居現(xiàn)代中國的價值主流。五四時代作為“人的文學”的時代,在其所大力倡導的“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6]中,我們可以看到《紅樓夢》中賈寶玉這一新人形象的精魂,在其所大聲疾呼的“打倒孔家店”并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主流的全面否定中,我們正可以看到《紅樓夢》中對賈政、賈赦的厭棄,五四時代之“人的文學”的邏輯起點,亦可以視為是從《紅樓夢》出發(fā)。
古代中國從農(nóng)耕文明向商業(yè)文明的歷史性的社會轉(zhuǎn)型,雖然兩次被作為游牧文明的異族的武力入侵所打斷,但在用農(nóng)耕文明收編了其游牧文明之后,在修復了農(nóng)耕文明的創(chuàng)傷之后,商業(yè)文明仍然在歷史規(guī)律的根本性的支配下,在明代在晚清末年頑強地再一次站在了中華民族歷史發(fā)展的潮頭。再經(jīng)晚清洋務運動的器物革命、戊戌變法及辛亥革命的政治革命、五四運動的思想革命,使以個體感性生命為價值本位的商業(yè)經(jīng)濟的社會模式,終于開始取代了以群體倫理為價值本位的農(nóng)耕經(jīng)濟的社會模式。在這一從古代中國向現(xiàn)代中國轉(zhuǎn)型的歷史變遷中,以個體感性生命為價值本位的民間價值譜系,在北宋時代這一向商業(yè)文明初步轉(zhuǎn)型時,曾以宋詞形式一領時代風騷,而在傳統(tǒng)中國即將結(jié)束之時,又以《紅樓夢》為載體,為傳統(tǒng)中國劃了句號,為現(xiàn)代中國劃了冒號,最終則在五四時代,與從英美而來的以個體感性生命為價值本位的商業(yè)文明,做到了無縫對接,只是我們對這一無縫對接,一向沒有給以清醒的認識與高度的重視。倒是五四時代,周氏兄弟對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與偏好,胡適在“整理國故”“保存國粹”的努力中所體現(xiàn)的用西方商業(yè)文明的價值視角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新考量,讓我們得以看到五四先賢們對中國古代民間價值譜系與西方現(xiàn)代價值譜系的親緣關系的敏感與自覺。
在中國新文學的版圖上,將傳統(tǒng)中國民間價值譜系作了有效承接并完成了現(xiàn)代性轉(zhuǎn)換的最成功者,是老舍、趙樹理、張愛玲、梁實秋。
在老舍的《駱駝祥子》《月牙兒》乃至《茶館》中,我們看到的是老舍的博大的西式的人道情懷,老舍用筆之力處在于,他總是以追求日常生活為滿足的普通人作為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并對這些主人公生命的有限性甚至殘缺性在價值論上給予了法理性的認可。從生存論的角度說,一個讓祥子、王利發(fā)這樣的有缺陷的普通人、小人物不能生存的社會不是一個健全的社會,從價值論的角度說,我們應該給祥子、王利發(fā)這樣的有缺陷的普通人,以生存、存在的價值上的認可。凡人與超凡的人,將自己的價值目標定在自己個人的日常世俗生活的生存的人,與將自己的價值目標定在為一個宏大理想而獻身的人,他們作為個體生命的社會價值的大小可以有所不同,但作為一次性的不可相互取代相互通約的個體生命,在個體生命自身的存在價值上,他們是平等的,他們都有各自生存、存在的合理性。誰又能說“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的木蘭會低于做了“尚書郎”的木蘭呢?
讀趙樹理的小說,你會時時地吃驚于,一向以白描著稱反對長篇大論地靜止地刻畫風景、人物心理的趙樹理,一旦關涉到其筆下人物的個體利益時,會不厭其煩地大段大段地把賬一筆一筆羅列得清清楚楚,較之他反對的西方大段大段的靜止的心理刻畫景物描寫,真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學界公認趙樹理筆下的“中間人物”塑造得最成功,而先進人物則總是“高大”不起來。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即是,“寫人的平常生活”的“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在那個時代的“中間人物”身上體現(xiàn)得最為鮮明突出,而其時的先進人物,則大多是“割肉飼鷹,投身給餓虎吃”。學界公認趙樹理小說最為突出的特征是“問題小說”,趙樹理所說的“問題”是農(nóng)民在“個體”“日常生存”“平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雖然這“問題”有時與“整體”貫徹自身意志中所遇到的“問題”有時一致有時不一致,但其二者的價值站位的不同卻是不能混淆的。學界公認趙樹理有著黨的干部、現(xiàn)代知識分子、農(nóng)民代表這樣三重的寫作身份,并常常為這三重身份的相互關系所困惑,但趙樹理在根本上,是站在以農(nóng)民為載體的個體感性生命為價值本位的民間的價值譜系的立場上,對所相遇的價值形態(tài),合則接受,不合則抵制,合多少則接受多少,也因之有了其寫作身份的表面上的三重性。
張愛玲對個體日常生存的重視,體現(xiàn)在她筆下女性對其細微的個體日常生活情趣固執(zhí)的追求與護守上,體現(xiàn)在面對這個體日常生活情趣在歷史滄桑巨變中不可挽回的衰敗與消失的“蒼涼”上。她站在中國從傳統(tǒng)中國向現(xiàn)代中國轉(zhuǎn)型的轉(zhuǎn)折點上,立足于個體生命,用個體利益的價值本位,解構(gòu)了以群體倫理為價值本位的傳統(tǒng)中國廟堂文化、士大夫文化所建構(gòu)起來的親情、愛情、友情等人倫之情,解構(gòu)了其所代表的國家觀念、民族觀念。相較而言,由于女性在體現(xiàn)個體生命的鮮活、豐富、微妙、瞬間性等方面,要更為典型,所以,雖然在廣度、厚重程度上,張愛玲對個體生命日常存在的揭示或許不及老舍、趙樹理,但在其深度上,卻是要比老舍、趙樹理更為深入、深刻。在中國新文學作家群體中,張愛玲這種極端的個人獨立性,那種個體的至高無上以及因此而來的對傳統(tǒng)中國人倫關系的徹底斷裂所導致的那種與人相處時的“冷漠”“孤獨”,那種心高性冷的品格,那種為文無人可比的才情,那種對個體利益的務實,對傳統(tǒng)國家、民族、階級、集體觀念的解構(gòu)與遠離,那種因無人對話而對個人寫作活動的看重,只有周作人差可與之相比肩,只是周作人立足于“自己的園地”,張愛玲則立足于對女性自身的考量。
梁實秋的重要性在于,他所代表的作為物質(zhì)生活相對充裕精神生活健康飽滿的上層人面對個體日常生活的態(tài)度與品格,這就是他的“雅舍系列”。具有這種品格,在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或者在物質(zhì)困窘的時刻,也會把個體性的日常生活過得有滋有味;具有這種品格,在腰纏萬貫聲名日隆的日子里,也會把個體性的日常生活過得健康充盈而不是喪心病狂;具有這種品格,可以在普通人家柴米油鹽醬醋茶的普通的日常生活中,讓散文化的生活過得充滿了詩意,或者說,讓人生的詩情融化于散文化的個體性的日常生活之中。中華民族,由于長期的生存的艱難,多的是“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苦難教育,多的是“天將降大任與斯人也,必將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價值資源,多的是對為了整體犧牲個體的推崇等等,少有在物質(zhì)生活豐裕后,如何過好健康的安樂的個人日常生活的價值資源,甚至對個體性的日常生活的享受不作價值性的認可。生長、成長在這樣的價值形態(tài)中,一旦個體性的物質(zhì)生活條件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無以立足的失重感的產(chǎn)生就是必然的。禁欲與縱欲,節(jié)儉與揮霍,低三下四與趾高氣揚等等,看似對立的兩極,其實卻是一體兩極,是一個銅幣的正反面。這在今天轉(zhuǎn)型期的中國,特別突出。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以梁實秋作為代表的建構(gòu)性的積極的價值資源,不可小視。
今日中國,經(jīng)濟上已儼然成為第二大經(jīng)濟共同體,國勢的強盛,呼喚著中華民族以新的文化姿態(tài)面對世界,弘揚優(yōu)秀的民族文化傳統(tǒng)的時代之聲應運而生。但如何使古代的傳統(tǒng)中國的價值資源,成為現(xiàn)代中國的價值性構(gòu)成,“新國學”的提出,可謂適逢其時。在構(gòu)建“新國學”中,由于當今的中國,還處在向市場經(jīng)濟商業(yè)文明的轉(zhuǎn)型期,而市場經(jīng)濟商業(yè)文明,是以承認個體利益作為其基本前提的。所以,依據(jù)大家都耳熟能詳?shù)鸟R克思的經(jīng)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理論學說,在構(gòu)建“新國學”時,汲取古代中國民間價值譜系的價值資源,汲取這一價值譜系在現(xiàn)代中國的現(xiàn)代性轉(zhuǎn)換的既有經(jīng)驗,應該是言之有理的,也應該是值得學界給以重視與研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