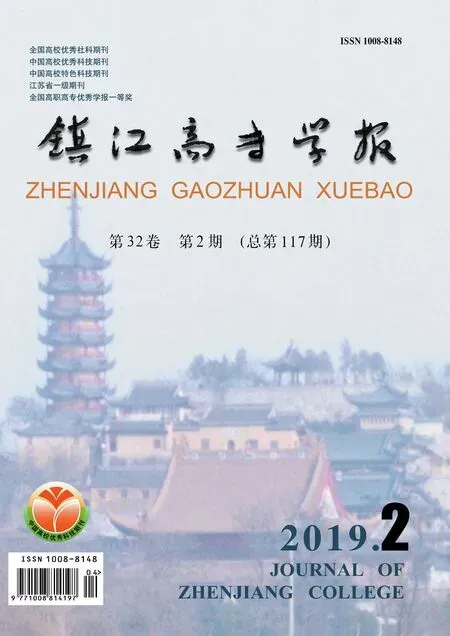蔡琰《悲憤詩》的女性悲劇意蘊研究
徐露潔
(福建師范大學 中文系,福建 福州 350007)
東漢末年的文壇出現了一批驚才絕艷、名貫古今的文人,如“三曹”“七子”“一蔡”等。在由男性作家唱主角的文壇上,女詩人蔡琰僅憑一首《悲憤詩》,占據了重要的一席之地,體現出蔡琰與其《悲憤詩》的重要地位及其獨特價值。清代詩論家張玉谷有詩贊曰:“文姬才欲壓文君,《悲憤詩》長篇洵大文。”[1]139-140目前,學術界從女性角度切入對蔡琰《悲憤詩》研究的論文為數不少,如張雷《蔡琰〈悲憤詩〉的獨特敘事角度與女性心理關照》[2]、蘇蕓《以女性眼光看待憂患與生命——從蔡琰的五言〈悲憤詩〉談起》[3]、王小波《論蔡琰〈悲憤詩〉的女性文學特色》[4]等。筆者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結合詩人的人生經歷挖掘其《悲憤詩》里女性情感的不同表達,從身世飄零、母子分離、再嫁新人三方面分析作品的女性悲劇意蘊,望能助力該名篇的傳播和接受。
1 身世飄零的女性悲劇意蘊
蔡琰身為漢末文學家蔡邕之女,自幼飽讀詩書。婚后,在父親與丈夫的愛護與庇佑下,過著安穩的生活。但世事難料,東漢初平三年(192年),董卓被誅殺,蔡邕受牽連被投下獄,不久死于獄中。失去父親庇佑的蔡琰就像一株嬌花被暴露在野外,任憑風雨吹打、烈日曝曬,毫無躲避、自保之力,她多舛人生的序幕也由此揭開。
與同時期的很多詩作一樣,《悲憤詩》也是“世積亂離、風衰俗怨”[5]333的產物,有如曹操的《蒿里行》、王粲的《七哀詩》等詩歌里對戰亂殘酷現實的描寫。在這些題材相近的詩歌中,《悲憤詩》的獨特之處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該詩是詩人親歷戰亂離苦的自述,而不是苦難的旁觀者和憑吊者的感慨,因而在描寫的真實性和情感的深切性方面會勝于其他作品。以曹操的《蒿里行》為對比,《蒿里行》中細節的典型性和史實的概括力度經常為人所稱道,但在對戰亂現實描寫的透徹度與下層百姓所經受的戰爭苦痛的深刻性方面,尚不如《悲憤詩》。其次,詩中第一次寫到現實中被卷入戰爭漩渦的女性所遭受的一切,對于婦女題材的拓寬起到了積極作用。沈德潛評說此詩:“激昂酸楚,讀去如驚蓬坐振,沙礫自飛,在東漢人之中,力量最大。”[6]61在戰亂中成為俘虜,飽受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折磨,詩中所寫的女性遭遇令人痛徹心扉。
描寫戰爭給婦女帶來的苦難是中國古典詩歌常涉及的主題。縱觀中國古代文學史,這一類的詩作多數是從思婦的角度訴說戰爭帶來的離別相思之苦。前有《國風·衛風·伯兮》《國風·周南·卷耳》等篇,后有王昌齡的《閨怨》、李煜的《搗練子令·深院靜》等。我們應該認識到,戰爭給女性帶來的影響,絕非只是情感上的煎熬,僅從身居后方、閨中含怨婦女的情感這一角度入手進行寫作,就題材領域方面來看較為狹窄,思婦情怨雖多,卻不足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悲憤詩》的出現恰恰彌補了這一缺憾。
蔡琰的《悲憤詩》第一次真實地描寫了卷入戰爭漩渦中女性的非人處境,揭示了一個女難民親眼所見、親身經歷的戰亂的可怖。“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棰杖,毒痛參并下。”淪為難民俘虜,骨肉至親相見不敢言,辱罵毒打施于其身,靈與肉的折磨無休無止,讓人痛不欲生。這一切的血腥與殘暴告訴世人:在戰爭中,相比男性而言,女性所遭受的災難深重得多。男人保家衛國,血灑沙場、馬革裹尸,稱得上英勇壯烈。女人一旦淪為戰利品,就像牛羊一樣遭到擄掠,流落異地他鄉茍延殘喘,人格尊嚴被無情踐踏,落到生死兩難的境地,身心備受煎熬。“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蔡琰是第一個把婦女在亂兵屠刀下的遭際以詩歌形式來表現的詩人,她以一位身受俘掠的女俘身份向我們展示了戰亂對女性造成的深重災難。
2 母子分離的女性悲劇意蘊
蔡琰的《悲憤詩》具有自敘傳特點,這使得她能更為細致、直接地以一個女性親歷者的視角去觀察體味女性情感世界,并以此寫出在特定情境下的女性所表現出來的骨肉分離的獨特心理感受。
蔡琰在胡地“沒于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7]124。蔡琰作為一個從小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漢族女性卻被迫委身胡人,內心有著無盡的痛苦、哀傷與無奈。“感時念父母,哀嘆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她日夜盼望回到中原故土,聽到有外來客,滿心期望地去問詢家鄉消息,卻每每失望而歸。原本以為有生之年再也回不到故鄉,就在這胡地了此殘生,命運卻在這時給了她一個回歸故土的機會,代價卻是母子分離。
建安十一年(206年),蔡琰之父的舊知曹操“憐邕無子,以金贖之”[7]124。得知消息的蔡琰欣喜若狂,但激動過后面臨的卻是人生中最為痛徹心扉的一次選擇,成全了自己,就意味著此生愧對親兒。“阿母常懷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年,奈何不顧思!”幼子不明白為什么平時仁愛溫柔的母親會狠心拋下他們,一句句不解的責問猶如長鞭抽打在身為母親的蔡琰身上,讓她痛不欲生。“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世間多少事,難得兩全法,詩人內心經過劇烈的掙扎之后,最終還是選擇回到中原,其間的苦痛自不必說,忍著痛一步一淚,獨自踏上了歸程,從此天涯路遠,不復相見。詩人字字泣血地訴說著這一人間悲劇。“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胸臆為催敗。”母子生離死別這一打擊令詩人五內崩潰、幾欲癡狂。蔡琰將母子分別的劇痛寫得刻骨銘心、感人肺腑。即便是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讀來仍震撼人心,讓人感同身受。
在《悲憤詩》之前也有不少表現母愛的詩歌,如《詩經》中的《邶風·凱風》、漢樂府中的《婦病行》等。但這些詩作所立足的角度與要表達的中心并不是母愛。《悲憤詩》在母愛這一題材領域中,第一次站在一個母親的角度來描寫母子血肉親情被生生割舍的殘酷現實,這戲劇般的發展、沖突有著震撼人心、動人心魄的力量。母愛本該是溫馨又從容的,但蔡琰筆下的母愛卻斷人心腸,她在這兩難的抉擇里飽受傷痛,她所經歷的母子分離猶如一場灼心烈焰,幾乎將她的五臟六腑化為灰燼。梁啟超先生說過:“她的情愛到處被蹂躪,她所寫完全是變態。”[8]124
3 再嫁新人的女性悲劇意蘊
《悲憤詩》在最后一部分描寫了蔡琰歸家后,遵曹操之命再嫁董祀這一事情,首次以一個再婚女子的身份展示了婦女改嫁這一過程中艱難的心理歷程。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男性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這樣的社會對婦女的貞烈觀有著難以想象的嚴苛規定。自古以來,男性對女性都有著“三從四德”“從一而終”的要求,男子可以三妻四妾不受譴責,女子卻必須接受丈夫擁有眾多妻妾的事實而不能有任何怨言,并對男方忠貞不二、從一而終,否則將受到整個封建社會的指責,甚至有付出生命的危險。女子若再嫁后,不知要經受多少非議指責。
在《悲憤詩》中,蔡琰第一次描寫一個再嫁女子的心理。“托命于新人,竭新自勖勵。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寥寥幾語,卻隱含著多少無法訴之于口的心緒。多少女子在成長過程中都有過幻想,期望得遇一良人,與他舉案齊眉,攜手一生。蔡琰作為一個名儒之女,飽讀詩書,在她初嫁河東衛仲道時,門當戶對,才子佳人,想必是有過一段幸福恩愛的時光。但一年后,衛仲道咯血身死,蔡琰夫亡且無子,只能含恨歸寧。作為一個從小受封建倫理道德影響成長起來的女子,內心的道德操守必然是遵從當時社會對女性的要求,她歸家后自然選擇為夫婿守節。如若世道安穩太平,興許能圓了她的節婦夢,可當時正值天下大亂,她又失去了父親這把保護傘,亂世中被胡兵擄掠,被迫委身匈奴人,這場突如其來的變故毫不留情地砸碎了她的貞潔夢,更把她的自尊與驕傲狠狠地踩在腳下。這成了她一生的心病,以至于多年后仍讓她耿耿于懷,倍感屈辱。因此蔡琰在面對她的第三次婚姻時,絲毫不曾有迎接新生活的喜悅之情,反而是自慚形穢不已。她不但已嫁過兩次,其中更有一次是嫁于外敵胡人,命途多舛的人生經歷與她一直所接受的教育是截然相反的,理想與現實的沖突帶來的痛苦讓她幾近崩潰。她懷著一顆憂慮與自卑的心來面對第三次婚姻,時時刻刻謹小慎微地去維持著與丈夫的關系。而他的丈夫董祀英俊多才,他本有更好的選擇,但丞相之命難違,他娶了蔡琰,但心里未必是心甘情愿。
這本是一個難以解開的局面,但好在事情出現了轉機。據《后漢書·董祀妻傳》記載:“祀為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且寒,賜以頭巾履襪。”[7]816可見蔡琰為夫“竭心自勖厲”的程度。想來,其丈夫董祀也會感念她所做的一切。
可即便如此,蔡琰依然“懷憂終年歲”,擔心不知道在哪天,被棄的命運就降落在自己頭上。蔡琰的擔心不是空穴來風。中國古代社會,針對女子制定的清規戒律不勝枚舉,比如關于休妻的“七出之條”等。女子的一生幾乎都掌控在男子手中,稍有不如意之處,即可被夫家休棄處置,這一點在漢朝尤為突出。我們可以從流傳于世的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中看出它的端倪。焦仲卿、劉蘭芝是恩愛夫妻,焦母不喜兒媳婦劉蘭芝,就可以以父母之命、孝道之理逼迫兒子休妻,而當事人卻無從反抗。蔡琰心理壓力更大:良家婦女尚且無端遭棄,更何況有著如此不堪過往的自己。蔡琰沒有一天不擔心著何時就遭“新人”拋棄。短短幾句里的復雜情緒,言有盡而意無窮。正如沈德潛在《古詩源》中所言:“托命新人四句,逆揣人心,直宣己意,他人所不能道。”[6]61蔡琰在女性特殊心理描寫這一方面的開拓可謂是第一人。
東漢末年,世道紛亂,儒學衰微,與前期儒學為尊之時相比,這個時期對于女性要更為寬容,在婦女問題上,一些傳統的觀念受到沖擊。曹操曾對他的眾妻妾說:“顧我萬年之后,汝曹皆當出嫁。”[9]474但我們據此便認為女性地位在當時有了全新的改變,那未免就言過其實,太樂觀了些。封建社會對女性的要求是“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女性是沒有獨立人格的。順者,則某種程度上安穩一生,逆者,則會遭到整個社會的打壓迫害。失去庇護的女性在當時的環境里是難以生存下去的。所以,無論是戰亂漂泊之悲慘、骨肉分離之悲痛,還是再嫁之無奈,都是封建社會婦女悲慘命運的不同表現。《悲憤詩》一早透露了這個悲劇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