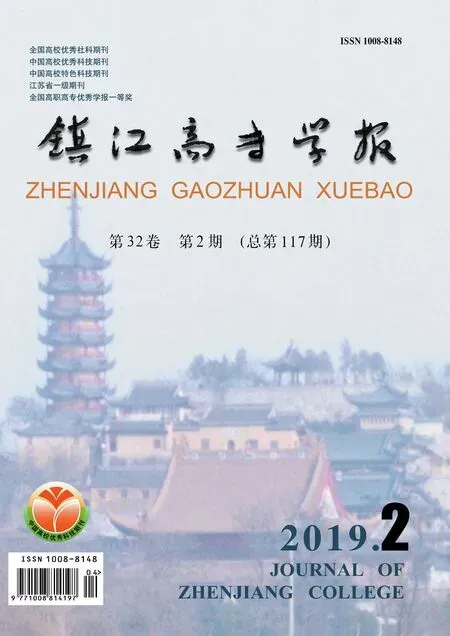紀弦詩歌意識流創作研究
李 艷
(東華理工大學 文法學院,江西 南昌 330013)
臺灣詩人紀弦是中國百年新詩史上少有的百歲詩人,也是優秀的高產作家之一,出版的詩集有20多部,在臺灣詩壇享有很高的聲譽。紀弦倡導現代派的詩歌創作,創辦《現代派》季刊,發起成立現代詩社,開啟了中國新詩發展的新階段。
紀弦的詩歌受到象征主義、未來主義、超現實主義等流派影響,多數詩作具有鮮明的意識流色彩。“意識流”一詞由美國機能主義心理學家詹姆斯提出,用來表示意識的流動性、不間斷性,也表示意識的超時空性。1918年英國女作家梅·辛克萊在評論英國陶羅賽·瑞恰生的小說《旅程》時將“意識流”引入文學界,引起了意識流文學熱。意識流文學是泛指注重描繪人物意識流動狀態的文學作品。最初意識流技巧主要被運用于西方現代主義小說創作,意識流小說以內心獨白、自由聯想為手段,淡化故事情節,圍繞人的意識活動展開敘述,給讀者以夢幻和陌生的閱讀體驗。隨著意識流技巧在西方小說中的廣泛應用,詩歌領域也逐步引入意識流手法,產生了一批具有意識流色彩的現代詩。閱讀紀弦詩歌,不難發現意識流技巧被廣泛應用其中。意識流是紀弦創作現代詩的常用手法,具體包括暗喻、感觀印象、時空跳躍和色彩渲染等。
目前對紀弦現代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紀弦的詩路歷程、現代詩歌創作觀念等方面,關于紀弦現代詩歌創作技巧研究,特別是其意識流創作方面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挖掘。
1 暗喻
暗喻是一種隱晦的比喻,不直接指出本體和喻體。意識流強調人的思維的流動性和不間斷性,它將表面上看起來毫無邏輯的意識思維串聯在一起,立體地展示思維的潛在意蘊。因此我們在意識流作品中難以發現時間邏輯和空間邏輯,只有作者創作的思維邏輯。意識流文學作品注重虛擬、含蓄、引申、擴展,所以經常使用暗喻手法。
現代派詩人戴望舒在《雨巷》里,以寂寥的雨巷比喻黑暗的社會現實,以丁香般的姑娘比喻美好理想,詩人在虛實結合的意識流中游刃自如。20世紀30年代,戴望舒第二本詩集《望舒草》出版,紀弦接觸《望舒草》后深受啟發,一改以往格律詩的風格而走上自由詩的創作之路。紀弦說:“要不是讀了他的《望舒草》,相信我還不會那么快地拋棄‘韻文’之羊腸小徑,而在‘散文’之康莊大道上大踏步地前進。”[1]75相比韻文而言,詩歌散文化更能貼近詩人內心,這就為詩人展示豐富的內心活動提供了便利。意識流正是表現人物復雜思維活動的絕佳手法。
西方意識流產生之時,生活在壓抑和苦悶中的文人們找不到人生的出路,便多用意識流手法進行創作,疏通內心情感,追尋主體精神。“西方的意識流理論深受弗洛依德的性本能學說和反理性主義哲學流派的影響,竭力強調非理性、超理性,著重反映的是潛意識、下意識、直覺、幻覺。”[2]西方文學作品中的意識流多表現為社會現實的超越。在中國文學中,意識流與現實生活密切聯系。在紀弦富有意識流色彩的詩歌中,意識來源于真切的生活,暗喻是連接意識流和現實生活的紐帶。如紀弦的詩作《過程》:
狼一般細的腿,投瘦瘦、長長的陰影,在龜裂的大地。
荒原上
不是連幾株仙人掌、幾株野草也不生的;
但都干枯得、憔悴得不成其為植物之一種了。
據說,千年前,這兒本是一片沃土;
但久旱,滅絕了人煙。
他徘徊復徘徊,在這古帝國之廢墟,
捧吻一小塊的碎瓦,然后,黯然離去。
他從何處來?
他是何許人?
怕誰也不能給以正確的答案吧?
不過,垂死的仙人掌們和野草們
倒是確實見證了的;
多少年來,
這古怪的家伙,是唯一的過客;
他揚著手杖,緩緩地走向血紅的落日,
而消失于有暮靄冉冉升起的弧形地平線,
那不再回顧的獨步之姿,
是多么的矜持[3]145-146。
《過程》一詩作于1966年,此時現代派已解散4年,《現代詩》也停刊2年。現代派作者創作水平參差不齊,加上當時現代詩中出現了一些虛無、縱欲的傾向,臺灣現代詩的發展已進入衰微階段。在此境遇中的紀弦不免失落苦悶,又難以言說,只能將壓抑的情感訴諸于詩作之中。
詩的開頭,“狼一般細的腿,投瘦瘦、長長的陰影,在龜裂的大地”,草原霸主的狼暗喻了在現代詩壇中處于領袖地位的紀弦的形象。曾是一片沃土的地方,如今久旱干枯,滅絕了人煙。這里的“沃土”,是暗喻20世紀50年代以紀弦為首的現代派詩人群體創作的現代主義詩歌在臺灣盛極一時。“久旱”而“滅絕了人煙”的“荒原”是暗喻20世紀60年代初現代派的解散和現代主義詩歌的衰微。面對如此破敗的景象,主人公只得“捧吻一小塊的碎瓦”,然后“黯然離開”。這里體現出詩人對曾經繁榮的現代詩壇的不舍,亦可見紀弦對當時現代詩壇弊病的無奈。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臺灣現代詩歌在經歷了狂飆突進的繁榮后,逐漸被新晉的鄉土文學代替。紀弦在詩中放聲發問:“他從何處來?他是何許人?怕誰也不能給以正確的答案吧?”這種發問也是詩人落寞情感的表達。曾經的繁榮只有曾與自己并肩作戰的“仙人掌們”“野草們”見證過。“他揚著手杖,緩緩地走向血紅的落日/而消失于有暮靄冉冉升起的弧形地平線。”落日余暉下,詩人漸漸遠去的身影驕傲又孤寂。
《過程》一詩用暗喻手法將作家面臨的現代詩創作現狀與詩中的意識流聯結起來,隱晦地表達出作家的孤寂與落寞。若拋開當時的社會現實和詩人境遇,就不能很好地理解詩中“狼”“荒原”“仙人掌”“野草”“落日”等意象,更不必說把握詩歌的主題思想了。紀弦將間斷的、看起來無關聯的意象串聯起來,賦予每一種意象以具體的現實意義,并將其構成一個整體。自古至今,詩中的意象從來不是意象本身,而是詩人自身意識富有情感的表現,恰如黑格爾所言,“詩所特有的對象或題材不是太陽、森林、山水風景或是人的外表形狀如血液、脈絡、筋肉之類,而是精神方面的旨趣”[4]17。在紀弦的《過程》一詩中,從開始以狼自喻的主人公的徘徊,到對如荒原般死寂的現代詩壇的發問,再至最后紀弦看清時局后孤傲而落寞地離去,意識的流動清晰可見。紀弦的其他具有意識流色彩的詩(如《寒夜》《四行詩》《世故》《新秋之歌》等)均較好地運用了暗喻手法。
2 感官印象
“感官印象再現的是謹慎的作家有時或全部省去或通過內心分析間接地表現出來的那種意識。”[5]5-6西方意識流文學作品常常運用感官印象來捕捉人物一瞬間的意識流動。“為了接近感覺,語言必須依靠從未有過的詞形和用法表達出來,這正好是多數好詩的作法。”[5]5感官印象與內心獨白相似,但內心獨白包含人的全部意識,感官印象只包含一部分意識,可以稱為潛意識或下意識。感官印象與印象派繪畫手法大致相同。紀弦早年學習西方繪畫,后棄畫寫詩,或受印象派影響,紀弦的詩作中多有感官印象的痕跡。如《預感》一詩:
大風砂之日,這都市有毀滅的預感。
囂騷的街,滾滾的流。
每一張涂抹著深重的憂郁的臉。
黑的漩渦。
歇斯底里的日子。
而且又是在狂犬病和腦膜炎流行的季節!
恐怖,不安,晦暗的天空
慘然懸著蒼白的,自殺了的太陽
一輪[3]51。
在紀弦的詩中,“為主觀情思尋找客觀對應物”是其常用的現代詩創作手法[6]。《預感》描繪了一副黑色基調的街道之景。街上呼嘯的風砂與來往行人相融合,似一股“滾滾的流”;人們憂郁的臉是這股流中“黑色的漩渦”;一向被看作是光明象征的太陽在作家筆下是“慘然”的、“蒼白的”,甚至是“自殺了的”。這種種描寫是反常態的、陌生的,甚至是有些魔幻色彩的,但正是作家彼時彼地感官印象的忠實表現。再如《火葬》一詩:
如一張寫滿了的信箋,
躺在一只牛皮紙的信封里,
人們把他釘入一具薄皮紙棺材;
復如一封信的投入郵筒,
人們把他塞進火葬場的爐門。
……總之,像一封信,
貼了郵票,
蓋了郵戳,
寄到很遠很遠的國度去了[3]111。
這首《火葬》是紀弦在目睹離世的友人楊煥被火葬的場景后所作。若拋去題目“火葬”二字,單看詩的內容,除了“把他塞進火葬場的爐門”一句點題之外,其余主要在寫一封信的郵寄過程。人的火葬如信的郵寄,這便是感官印象作用的結果。將火葬的過程比作一封信郵寄的過程(由一個國度到另一個國度),這樣的聯想頗為新穎。詩中將郵寄信的細節與人的火葬細節一一對應,讓人真切地感受到作家是在目睹了火葬的真實場面而產生獨特的感官印象后創作了此首詩歌。楊煥是當時現代派詩人的一員,其詩作頗得紀弦等人的賞識,但25歲時因意外事故離世。“寫滿了的信箋”暗喻楊煥短暫一生的豐富詩作成果和對現代詩發展的貢獻。面對友人的離世,紀弦很悲痛,但我們在詩中很難發現情感宣泄的痕跡,作家壓制情感,以平靜的筆法描述了火葬這件事。文學中的感觀印象不用作情感的載體,只展示作者當時純粹的感覺意識,并忠實于這種意識,將其訴諸筆端。這是紀弦第一次看見火葬,而且是友人的火葬,悲痛之余不免產生強烈的感官刺激,于是令人難忘的火葬印象便產生了。
“隨著文學藝術的發展,中國當代學者也在逐步重視感性素材在文學創作中的作用,認識由感覺帶來的想象與思索內涵對于深化文學創作的意義。”[7]感官印象使紀弦的詩具有了獨特的意味。感觀印象在意識流文學中應用廣泛,就紀弦意識流詩作而言,《預感》《火葬》《五月》《印象》《新秋之歌》等詩歌中都成功運用了感官印象進行創作。
3 時空跳躍
時空跳躍指作者進行創作時不遵循一定的時間或空間順序,通過時間或空間的頻繁轉換來實現其情感的宣泄。時空跳躍的手法雖使詩歌失去了時間與空間的邏輯順序,“但詩詞的‘時空感’是與生俱來的,詩人由于藝術的感召,心理的需要,希望獲得一種時間倒流、空間轉換的精神體驗,由此產生了空際轉身的穿越筆法”[8]196。時空跳躍手法與電影中的“蒙太奇”手法相似,詩人或將相同的意象置于不同的空間,或將不同的意象置于相同的空間,又或將不同的意象置于不同的空間。其中的意象來自于過去、現在或未來,具有不同的時態特征。意象與空間進行不同的組合,也就形成了各種具有不同時空特征的畫面,這些畫面不斷地轉換,便實現了時空的跳躍。時空跳躍的靈活性與多變性正符合了意識流飄忽不定的特點。脫離了時間與空間順序的束縛,更有利于詩人的意識流創作,更有利于詩人抒發自身意識中那些瑣碎的、細小的情感。如《散步的魚》一詩:
拿手杖的魚,
吃板煙的魚。
不可思議的大游船
駛向何處去?
那些霧,霧的海。
沒有天空,也沒有地平線。
馥郁的是遠方和明日;
散步的魚,歌唱[3]46。
紀弦寫魚散步,實際上在寫自己,因為拿手杖和吃板煙都是他自己在生活中的寫照。在詩的開頭,詩人以魚自喻,展開一連串的聯想,詩便隨著意識的流動而產生了。由自身聯想到魚,由魚想到游船與海,再聯想到天空和地平線,詩中沒有情感線索和連接性的語言,空間在寥寥幾行詩中頻繁轉換,這給讀者帶來一種陌生化閱讀體驗,同時也別有一番美感。這種聯想“有相當大的隨意性和跳躍性,強調表現人物意識流動的各種感受,是一種雜亂的心靈真實”[9]。然細讀便可發現,紀弦以一條魚的視角抒發了對未來的迷惘和美好的希冀。一條終日生活在大海里的魚,看見駛來的游船不免發問:它來自哪里?要駛向何處?遠方的世界是怎樣的?遠方又在哪里?而遠方被霧遮擋,這條魚看不見天空也看不見地平線。即使如此,它仍然期待馥郁的遠方和明日。想到美好的希望,這條散步的魚便唱起歌來了。從“魚”到“游船”“海”“天空”“地平線”“遠方”“明日”,這便是在空間轉換的創造手法下,隱藏其中的紀弦的意識流動。
除了空間轉換,時間轉換也是意識流作品中常見的創作技巧。“意識流小說以流動性的‘意識’掙脫時間順序,由主觀的、不確定的、甚至是不知所謂的意識流動來推動情節進程。作者將時間和事件置于人物的內心活動中,將發生在不同空間的事件通過蒙太奇的剪輯手法,并置于同一個時間點,使得時間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處于同一平面上。”[10]這便是時間轉換手法對作者進行意識流創作的意義。在紀弦的意識流詩作中,時間的轉換與西方意識流小說相似,詩人往往受某個時間點(過去、現在或未來)的事物啟發,產生意識流,意識流動忽而過去,忽而現在,忽而未來,便形成了時空的跳躍,詩的創作路徑也隨著意識的流動而向前推進。如《四月之月》一詩:
四月之月是淡淡的檸檬黃色的。
不曉得阿姆斯壯那永恒的腳印消失了沒有?
什么時候讓我到木星上去玩他一趟才好。
可是四十年后光速的宇宙船都不停小站的。
那就買他一張仙女座大星云的來回票怎樣?
從一個銀河系到一個銀河系——
冰凍了的百齡老人還有的是游興哩。
而今天,我滿六十歲,皎皎的月光下,
讓我放一個誓言在高腳杯中:我要飛![3]165
這首詩完全是紀弦的自由聯想,在聯想中時間和空間隨著意識的流動而不停地轉換。四月是春暖花開的季節,把四月稱作是檸檬黃色的,在體現四月自然之生機的同時也充滿了活力與俏皮。詩人的思維在檸檬黃色的四月的啟發下活躍起來,一會兒聯想到月球上阿姆斯壯的腳印,一會兒聯想到去木星游玩,一會兒又想買一張去仙女座大星云的來回票。詩人從現在聯想到未來,聯想到四十年后的自己,那時紀弦已是百歲,但仍要放一個誓言——我要飛!詩人創作的靈感來自活躍的聯想,而時空轉換的手法是將這些聯想訴諸筆端的重要工具。聯想、意識流與時空轉換三者的關系即:聯想使作者產生創作的沖動,時空轉換的手法將作者聯想的畫面一一呈現,作者的意識則隨著時空轉換而不斷流動并形成意識流。紀弦的意識流動在《四月之月》中較為明顯,從空間轉換到時間的跨越都在表現六十歲的紀弦的生命活力。意識流創作的優勢便是可以毫無束縛地展現作者的內心活動。時空轉化是意識流文學中常常出現的創作手法,紀弦的詩作如《一間小屋》《夢回》《夢見蒲葵》《將起舞》等都有所體現。
4 色彩渲染
“色彩是最易進入感官的內容,尤其是對于眼睛,具有某種吸引力。起著‘誘餌’的作用,較之線條更能引起人的注意。”[11]色彩對人的心理具有某種暗示作用,同時色彩本身還具有不同的情感象征,色彩渲染是意識流文學中又一常用的手法之一。紀弦曾在武昌美專和蘇州美專學習西方繪畫,對色彩比較敏感。在紀弦的現代詩作中,色彩渲染是出現頻率較高的創作手法,色彩渲染是詩人在想象空間中的意識流動,是詩人傳情達意的重要媒介。如紀弦的《筆觸》:
安得抹他幾筆金黃,橙紅,
或是石榴的明艷,
在這中年了的畫布——
灰色的,灰色的一片!
便是幾個土黃的筆觸,
棕的筆觸,赭的筆觸,
甚至黑的筆觸也好啊。
不可虛無。不可虛無![3]63
這首《筆觸》中,寥寥幾行出現了8種顏色。“色彩本是客觀事物的外在表現形態,但由于色彩的移情作用使得人們也用它來表達視覺不可見的那些抽象的內容。”[11]金黃、橙紅等是暖色調,往往代表充滿活力與朝氣的具有積極意義的事物;灰色與黑色為暗色調,往往代表消極意義的事物。土黃色、棕色、赭色等中性色彩常起著調和亮色與暗色的作用。這諸多色彩融合進一首詩中,每一種色彩在紀弦的意識里都具有其自身的象征意義。《筆觸》這首詩作于1945年。當時紀弦只有33歲,正是施展才華的好年紀,但由于生活所迫和當時社會環境的限制,他空有一腔抱負而無處施展。紀弦在《筆觸》中運用色彩渲染的手法,將自己內心的情感隱藏于各種色彩之中,隨著情感的變化和意識的流動而不斷轉換顏色,內心的苦悶隨著意識的流動一涌而出。這便是色彩的移情作用在紀弦的意識流創作中的應用。
相比于色彩帶來的視覺沖擊,色彩的情感象征是紀弦意識流詩作中的一大特色。詩人利用色彩本身的象征意蘊,將自身情感融入其中并在意識流動中表達出來。
如《黑色之我》:
我的形式是黑色的,
我的內容也是黑色的。
人們避開我,如避開
寒冷的氣候和不幸。
但我是不可思議地
黑色了的,所以我驕傲。
我把我的黑色的靈魂
裹在黑色的大衣里[3]38。
“一般而言,任何顏色,例如黑色和粉紅色本身,并不包含可以確指的內容,但他們的光波,各以其不同的波長,喚起我們各種不同的感受。粉紅色給我們以愛慕、溫柔、朦朦朧朧的幸福感。黑色給我們以嚴肅、沉重,甚至恐怖感。所以在特殊情況里,顏色也是一種象征。”[12]在這首《黑色之我》中,“黑色”反復出現,渲染了一種低沉的情感基調。《黑色之我》作于1938年,那時戰爭還沒有結束,人們生計難以維持,紀弦一家也是如此。紀弦攜家人一路流亡至香港,途中歷經艱苦。所以這一年里紀弦的詩作很少,《黑色之我》中反復渲染的“黑色”正體現了紀弦當時的境遇。詩中描寫“我”的形式和內容都是黑色的,但“我”仍是驕傲的,“我”把黑色的靈魂裹進大衣,從中不難讀出一種落魄文人的高潔。意識流文學的情感主旨與其他流派的文學相比較難把握,但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詩歌中的色彩渲染給了讀者很大的想象空間。
紀弦一生著作等身,其對現代詩的嘗試與發展作出了不遺余力的貢獻。意識流色彩是其詩作的重要特征,也是臺灣現代詩對大陸新詩的繼承與發展。紀弦的意識流詩作遠不止表現在暗喻、感官印象、時空跳躍和色彩渲染四個方面,文學的創作手法之間是相輔相成的,如自由聯想、內心獨白、圖畫建構、情緒書寫等創作手法亦與意識流創作相通,這也值得我們繼續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