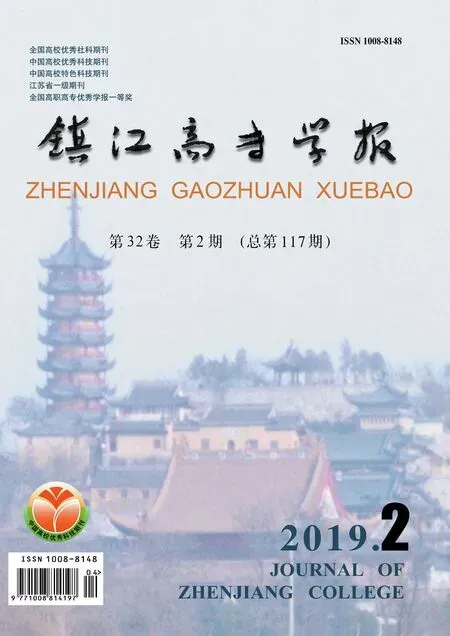鄉土貴州的呈現與守望——蹇先艾鄉土小說研究
龍麗萍
(貴州師范大學 文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20世紀20年代興起的鄉土文學為現代文學注入了活力。“鄉土文學”的概念最初由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的導言中提出,“蹇先艾敘述過貴州,裴文中關心著榆關,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的人們,無論他自稱用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土文學,從北京這方面說,則是僑寓文學的作者。”[1]10魯迅被稱為“鄉土文學”的開山鼻祖,他以《阿Q正傳》《故鄉》《孔乙己》等充滿浙東水鄉色彩的小說開拓了鄉土文學的道路。在魯迅鄉土文學的影響下,自偏遠的貴州走出來的蹇先艾(1906—1994),用彌漫著泥土氣息的文字繪制了一幅幅貴州鄉野圖景,他關注故土生活、審視故土現實,向世人呈現了貴州獨特瑰奇的地貌環境和地域風情,描繪了處于貧困中的山民野蠻、蒙昧甚至異化的精神狀態,指出罪惡的煙鹽經濟和軍閥混戰給貴州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
1 原生態獨特瑰奇的鄉野風景圖
20世紀20年代的鄉土文學一出現便表現出濃郁的“土氣息”“泥滋味”,即濃郁的地方特色,如魯迅筆下的魯鎮和未莊、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沙汀筆下的川西北村鎮。貴州峽崖險峻、山路崎嶇。一位學者曾如此描述:“貴州地表支離破碎,奇峰突起,地下溶洞發育,‘無山不洞’。貴州土地資源呈現‘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結構形態,喀斯特山地、丘陵所占比重極大,利于農業發展的溶蝕洼地即喀斯特盆地,在貴州一般稱為壩子的平整土地較少。”[2]這樣的自然環境造成了貴州交通不便、經濟落后。但福禍相依,閉塞落后的貴州也因此保留了原生態的自然風光,讓世人看到了一個獨特的鄉土世界。受到“五四”新思潮影響的蹇先艾,以一個既作為“局外人”又作為“局內人”的特殊視角來反觀自己的故土,對有著特殊地域特色的貴州山區進行了精心的塑造和描寫,將一系列貴州風、貴州景、貴州人、貴州情真實而生動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首先,作家通過精煉的刻畫讓世人看到了黔北獨特的地理與氣候環境。如小說《貴州道上》的開篇描寫:
多年不回貴州,這次還鄉才知道川黔道上形勢的險惡,真夠得上崎嶇鳥道,懸崖絕壁。尤其是踏入貴州的境界,映入眼簾的都是奇異高峰:往往三個山峰并峙,仿佛筆架;三峰之間有兩條深溝,只能聽見水在溝內活活地流,卻望不見半點水的影子。中間是一條一兩尺寬的小路,恰好容得一乘轎子通過[3]261。
地面崎嶇不平、地貌類型極為復雜,可以看出這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分布的地區。山峰連綿不斷,凸顯貴州山區面積范圍的廣大;“只聽見水在溝內活活地流,卻望不見半點水的影子”,寫出了峽谷之深;“一兩尺寬的小路”,說明山高路窄。這種復雜險峻的地勢地貌不僅讓乘客發出“行路難”的嘆息,還讓身強力壯、具有翻山越嶺本領的轎夫望而生畏。小說后面的文字中,除了介紹貴州獨特的地理環境外,還介紹了貴州特殊的氣候環境。山里經常下著蒙蒙細雨或傾盆大雨,道路常常是泥塘深坑,有時還會發生山洪。險峻的地勢加上惡劣的天氣,讓行走在道路上的人惴惴不安。作家用細膩的筆觸將雨中的山路、雨后泥濘的小道以及行路之人細微的情感都生動描摹了出來。
其次,作家贊美了貴州瑰奇的自然景色。在蹇先艾的筆下,一幅幅美麗的貴州山水圖隨處可尋、一張張動人的生活畫隨處可見。在小說《到鎮溪去》中,作家描寫了擺渡所見的秀麗景色:
船靠著左邊走,慢慢駛入峽口去,曲長的山峰并著,只看得見一線藍的天光。這里真像四川的瞿塘與巫山。谷中一片清幽的景致,沒有岸,從兩山之間,嘩嘩流出銀沫飛濺的小瀑布,像微雨似的凄零飄動,使人生幽幽的感覺。還有玲瓏秀麗的小石山,真可愛,上面叢生著綠葉紅邊的虎耳草,寄生在大的山峽之中[3]152。
連綿不斷的山峰、清幽的峽谷和清澈的涓涓流水,在船上能看得見“一線藍的天光”,瀑布濺起的水花如小雨一般零星飄動,連小石山都是如此玲瓏剔透和可愛,這仿佛是一個人間仙境。作家字里行間洋溢著對故鄉景色的喜愛和贊美之情。
在小說《鄉間的回憶》中,作者描繪了一幅幅愜意的生活圖景:金黃色的晚霞映照下,與嫂子們一起在綠綠的柳蔭下捉泥鰍、在清澈見底的河流中捉螃蟹;夕陽西下,放牛娃趕著水牛,唱著歌回家……這些正是我們古已有之的“天人合一”的和諧生活。
此外,小說《濛渡》中寫道:
連綿的微雨在天空飄飛著,天氣陰沉得看不出是什么時候。我們已經登上到處都是黃泥的腳跡的寬板渡船了,茫然望著澄碧閑靜的水,偶爾也被風掀起幾團起伏的波紋,旅客們的心頭都泛溢著舒展松快的感覺[3]440。
作者筆下連綿的微雨、陰沉的天氣,正是貴州“天無三日晴”氣候特征最真實的寫照。生活在這一方水土之上的人們,并沒有因為天氣的陰沉而感到不快,而是沉浸于澄碧閑靜的山水中,連那起伏的水波都成為人們心情舒展的緣由。作者對貴州獨特自然環境的細致描寫,讓人身臨其境、沉醉其中。
故土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已滲入作家蹇先艾的靈魂,他向世人展現了貴州“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的自然景象,勾勒了邊遠山區的奇峰峽谷、懸崖峭壁、崎嶇鳥道,描繪了山高水藍、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獨具地域特色的貴州圖景,讓世人看到自然、本真的山區原始生態環境,看到有別于其他地域的鄉土文學的美學景觀。
2 守舊鄙陋風習下麻木扭曲的人性解剖圖
如前文所述,貴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分布的地區,特殊的地理環境阻礙了貴州與外界的溝通與交流。這不僅造成了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物質上的貧瘠與艱難,還使得鄉民們思想閉塞與精神麻木、民風野蠻落后與守舊鄙陋。
魯迅一直致力于通過文藝改變愚昧國民的精神。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說:“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4]5離開故土到北京求學的蹇先艾,受到“五四”運動新思潮和魯迅鄉土作品的影響,他深刻認識到,貴州物質上非常貧瘠,但比物質貧瘠更可怕的是人們精神上的麻木與扭曲,所以他也毅然拿起筆批判野蠻落后和守舊鄙陋的風習,解剖麻木與扭曲的人性,以引起療救的注意。
《水葬》是蹇先艾鄉土小說的代表作,曾與《到家的晚上》一起被魯迅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魯迅稱:“……但正如《水葬》,卻對我們展示了‘老遠的貴州’鄉間習俗的冷酷,和出于這冷酷中的母性之偉大,貴州很遠,但大家的情景是一樣的。”[1]9
《水葬》描寫了駱毛這個阿Q式人物的悲劇,駱毛因為不守本分做了賊,被鄉人用“水葬”的方式加以懲戒。小說中寫到:“文明的桐村向來就沒有什么村長……,犯罪的人用不著裁判,私下都可以處置。而這種對于小偷處以‘水葬’的死刑,在村中差不多是‘古已有之’的了。”[3]27時間到了20世紀20年代,社會不斷發展、人類文明不斷進步,可在偏遠的貴州山區,這種陳規陋習依然存在,并且是“古以有之”,可見社會的落后閉塞,守舊鄙陋風氣根深蒂固。與這種守舊落后風氣比起來,更讓人痛心的是“看者”和“被看者”麻木扭曲的人性。前來觀看駱毛被處“水葬”的看者很多,場面不是一般的熱鬧,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媳婦和婆婆、有奶奶和孫女、有姑娘和奶娃……大家爭先恐后、擠進擠出,顧不得各種汗的味道。這個“文明”的桐村,大家平時聽到不干凈的粗話都會臉紅,會說“喪德”,可是當看到駱毛遭遇這種殘忍的懲罰時,他們只是把它當成一種熱鬧,甚至是娛樂,沒有一絲的同情、傷感和憤怒之情,可見人心的冷漠、麻木,甚至無人性。而對于“被看者”駱毛而言,死到臨頭之時,只是滿嘴臟話、粗話,用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來安慰自己,“爾媽,老子今年三十一”,“再過幾十年,不又是一條好漢嗎?……”[3]30駱毛的潛意識里是認識不到這種禮教制度的罪惡的。在這種守舊鄙陋風習的影響下,無論是“看者”還是“被看者”,他們都不會反抗,也不知道反抗,他們從不思考這一習俗的合法性,而是自覺地接受和順從,這是人性的扭曲,更是人性的悲哀。
在小說《初秋之夜》里,作家描寫了一群虛偽腐朽的官吏、文人、士紳,如縣里女子中學的校長吳惟善就是其中之一。吳校長的辦學標準是“女子無才便是德”;他不教白話文,用《女四書》當作課本;當五卅慘案發生,群情激憤,全城的學生高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時,他不準女子學校的學生參加,認為愛國不是女學生的分內之事。這么一個受封建守舊陋習影響、強調培養恪守宗法制禮教文化的校長,竟被縣長烏元富夸為“教育家”。當地許多文人、官吏與士紳對吳校長的作為是“為之感動”“大為動容”;作為地方的希望并且受到新思想影響的年輕北京學生竟然也默默地表示贊許。由此可知,封建守舊陋習已根深蒂固,人性在封建思想影響下已極度扭曲和異化。
詩人劉大白談到故鄉的山水時是滿懷眷戀與謳歌,談到故鄉的城市、故鄉的社會時充滿厭惡與詛咒。蹇先艾也厭惡生活在故土上的麻木不仁、異化扭曲的人們,憎恨他們的不覺醒。愛之深、恨之切,作家將這種守舊落后的生活原貌一一呈現,以期引起人們的注意,進而采取療救方法來改變貴州現狀。
3 煙鹽經濟與軍閥統治下的人生悲劇圖
“地理環境畢竟給人類文化的創造提供了物質材料,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人類文化創造的發展方向。”[5]17在蹇先艾的小說中,我們看到了煙鹽經濟與軍閥統治下的一幕幕苦難的貴州山民人生悲劇圖。
煙鹽經濟是造成貴州百姓人生悲劇的主要原因。貴州地處云貴高原東部,主要以山地為主,土地比較貧瘠,良田本來就少,再加上出產量比較低,導致貴州極其貧困和落后,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貴州是全國最落后的省區。當時的政府為解決財政困難,一方面慫恿民眾種植鴉片、出售鴉片甚至吸食鴉片,以此獲取暴利;另一方面,因貴州不產鹽,需要從外面特別是從鄰省購買,政府便通過收鹽稅來獲取財政收入。畸形的經濟結構產生了許多穿梭在川黔道路上的鹽巴客、轎夫,也讓許多人成為鴉片的犧牲品,越抽越窮,越窮越抽,上演了一出出人生悲劇。
在小說《鹽巴客》中,作家描寫了一群穿梭在崎嶇山道上的下力人——鹽巴客。他們干的是最苦的活,常常食不果腹、衣不蔽體;他們的地位極為低下,常常被人以擋道為由呵斥,被罵為“鹽巴老二客”;更為糟糕的是,如果遇上軍隊,他們還有可能被推下幾十丈深的懸崖。艱難的生活把他們壓得很苦,生命又沒有保障,種種重壓下,他們原本淳樸善良的性格變得暴躁、扭曲,甚至一些人做出異化的非人的行為。
在《鹽災》里,作者向我們呈現了一幅幅缺鹽成災的悲慘圖景。“今天我下坡去在村里走走,我所遇到的每一個人面貌都非常黝黑,沒有一點笑容,像喪亡了一樣;不說話,低著頭,拖著鞋,不扣衣服,無目的地亂走。”[6]3因為鹽被壟斷了,鄉下的老百姓買不起鹽,只能吃灰鹽、淡鹽,甚至只好不吃鹽,大家如行尸走肉的僵尸一般,“一點精神沒有,全身的骨頭都覺得酥軟,比沒有吃飽飯還難受。肩不能挑了,背也不能馱了,走起路來提提腳都很費力,只想坐在那里或者躺在那里”[7]。鹽災讓人精神萎靡,讓家庭變得不安寧,讓社會變得不安定,人們就在這種畸形的煙鹽經濟中受著煎熬。小說《酒家》里的張大娘有很嚴重的煙癮,為得到更多的煙錢,不惜將自己的寶貝女兒嫁給巴團長作小妾,葬送了女兒的青春和幸福。褚夢陶的父親貪戀酒色和吸食鴉片,惡劣的基因使得褚夢陶從一出生身體就很孱弱,大哥在幼年時就瘋了,二姐的身體也非常單薄。這些都是煙鹽經濟釀成的人生悲劇。
軍閥統治是造成貴州百姓人生悲劇的重要根源。掠奪性是貴州軍閥統治最突出的特征,他們毫無人性地壓榨百姓、掠奪財物。在蹇先艾的筆下,我們看到了軍閥統治給廣大民眾造成的深重災難。原本已貧困落后的貴州在黑暗的軍閥統治下變得更加民不聊生。如在《酒家》中,師范生褚夢陶勸說女友的母親不要將女兒嫁給有三妻四妾的巴團長,最后勸說不成,反遭設計陷害,被士兵亂槍擊斃。《鹽巴客》中的鹽巴客們,經常背上都是百多斤的東西,當軍隊經過來不及讓路時,便被推下萬丈深淵。小說中的“我”遇到的是一個骨頭全部跌斷的鹽巴客,還有很多像他一樣的鹽巴客,也過著同樣悲慘的生活,不僅身體要抗著重擔,連精神也要時刻緊繃著,因為這種悲劇隨時可能發生。《安癲殼》中,安癲殼原是一個體魄強健的農民,妻子被土匪搶走了,為了付客棧的房錢,只得將女兒賣給了公館當婢女,最后自己淪為乞丐。在《到鎮溪去》中,“春云棧”老板娘的丈夫王松壽,原本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壯小伙,能挑能抬,被軍閥部隊拉去干苦力后,變得又黑又瘦,最后悲慘死去。《蒙渡》中的一鄉下女人,丈夫被川軍拉夫拉去了,家里有三個孩子要撫育,婆婆又犯病了,苦難的日子壓得她喘不過氣來,她每天都祈禱自己的丈夫不要被打死……軍閥統治導致了人們物質上的貧瘠,還給人們帶來了精神上的恐慌。
在煙鹽經濟和軍閥統治下的貴州是貧窮的、黑暗的,人民生活在苦難的悲慘世界里。賈劍秋認為蹇先艾筆下的鄉土小說“集中了現代貴州各種階層、各種身份、地位的社會角色……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軍閥統治與鹽煙經濟桎梏下的哀樂苦痛、生死興衰,構成了一幅立體的20世紀上半葉貴州地方社會的現實圖景。”[7]作家關心故土的百姓,關注他們的生存狀態和人生困境,展現了一幅幅悲慘的20世紀上半葉的貴州圖景,對造成這一系列人生悲劇的煙鹽經濟和軍閥統治進行了鞭撻和控訴。
4 結束語
作為一個現實主義作家,蹇先艾一生致力于鄉土小說創作,是貴州鄉土文學的奠基人。他向世人展現了貴州山區獨特瑰奇的生態景觀,展示了貴州山區人民的生活場景以及這種生活場景之下守舊鄙陋的生活方式,刻畫了在煙鹽經濟和軍閥統治下貴州人民的悲慘命運。何光渝在《20世紀貴州小說史》中認為蹇先艾的小說“真正地直面人生,直面更為廣闊的社會生活現實”[8]73。從對原生態獨特瑰奇的鄉野風景圖的描繪,到原生態土地上淳樸自然的人文精神的展現,到造成20世紀上半葉貴州貧困落后根源的揭露,我們看到了一部20世紀上半葉貴州的社會史,一幅現代鄉土貴州圖景。作為黔之子,蹇先艾從現代知識分子的視角,以充滿哀痛而憤懣的情感,描繪了貴州的崇山峻嶺和崎嶇山道,以及在那懸崖峭壁下絕地求生的苦難人們,用充滿鄉愁的筆墨不動聲色地將一幅幅貴州的社會圖景呈現在世人面前,讓人們認識貴州、走進貴州,讓偏遠的貴州不再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