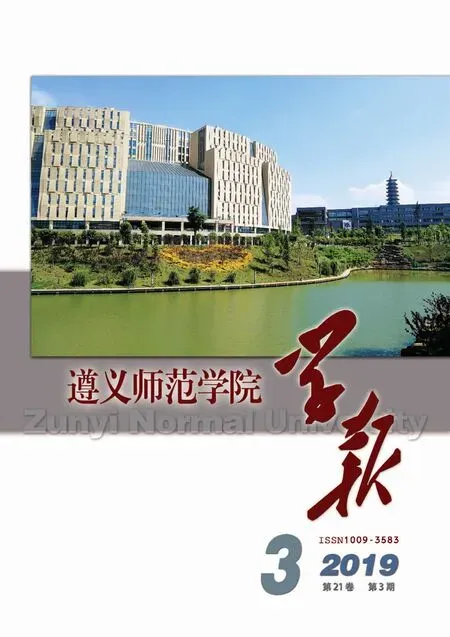“十詮”之法與馮復京詩歌創作論
丁遠芳
(a.安慶廣播電視大學,安徽安慶 246003;b.安慶師范大學文學院,安徽安慶246133)
馮復京(1573-1622),字嗣宗,江蘇常熟人,明代后期的詩學家、經學家和史學家。出生文士世家的馮復京育有三子:馮舒、馮班、馮知十,其中馮舒、馮班并稱“二馮先生”“海虞二馮”,是清初虞山派的代表人物。
馮復京生性倜儻灑脫,放蕩不羈,錢謙益有“形容清古,風止詭越,翹身曳步,軒唇鼓掌,悠悠忽忽如也。”[1]之語稱益之;一生博聞強記、勤于思考、敏于著述,其鉆研著作涉及詩經、禮教、史學、小說、音樂、詩賦以及詩歌理論等多方面。現據《重修常昭合志·卷十八·藝文志》所載,整理如下:《六家詩名物疏》五十五卷,存,有焦竑作序,四庫全書總目誤為馮應京;《說詩譜》四卷,已佚;《遵制家禮》四卷,存;《明常熟先賢事略》十六卷,現存;《明右史略》三十卷,現存;《蟭螟集》十四卷,《海虞藝文目錄》稱毛扆汲古閣書目抄本記載有珍藏秘本;《馮氏族譜》四卷,存;《常熟縣儒學志》八卷,存;《說詩補遺》八卷,存,卷末有馮舒、馮班跋,馮舒天啟三年(1623)跋文謂本書成于萬歷四十八年庚申(1620)。此書系作者精心用意,以“一生目力”寫成,完成后又謂“前所著盡,頗亦未盡。漢魏六朝,無所憾矣;初盛兩期,自謂精確;所恨者中晚之間,立言未真耳。”臨終還囑咐子輩“不得忝則”,是馮復京詩學思想的集中體現。另外,馮復京現存詩賦碑文收于《海虞文徵》。
一、馮復京與“十詮”之法
馮復京生活的時代正是明代詩學思想激蕩變幻的時期,后七子尚活躍于詩壇,而公安派的影響也正逐漸擴大,詩學思潮百家爭鳴。身處后七子與公安派詩學思潮爭論之中,馮復京對二者的詩歌創作和詩歌理論多有不滿,加上自身于詩學用力甚勤,治學嚴謹,遍觀歷代之詩而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博綜眾家之學說,熔鑄于心,精心用意寫成了其詩學論著《說詩補遺》。作為“新一代之耳目”,馮復京感于“凡今之人,守瑯琊之卮言,尊新寧之品匯,羽北海之詩紀,信濟南之刪選,謂子美沒而天下無詩”之論,于是“歷觀唐人諸集”兼及漢魏六朝之作,以辨體辨格入手,“用一生目力”,從詩歌的本質、流變、審美、創作等方面詳細論述,成《說詩補遺》。全書共八卷,卷一總論詩體、詩格、詩思、詩韻、詩病等方面,卷二至卷八以詩歌史的形式論按時代論述,其中卷二至卷四論唐以前之詩,卷五至卷八論唐詩。通過對歷代詩歌具體分析,馮復京指出一代有一代之詩,不必法漢魏,宗盛唐,鄙薄齊梁陳隋,對前代之作,不必句字摹擬,從而否定了七子詩有定格、句字摹擬的論調。他認為唯有獨創而不摹擬,表達真情實感的作品,才可以動天地,感鬼神,震心魄,駭耳目。
馮復京《說詩補遺》從第五則到第三七則在辨析各體詩歌源流的基礎上,對各體詩歌的創作規律也進行了總結。馮復京把詩歌的創作活動理論化地概括為十大要點,即“十詮”之法。
詩有恒體,予既備著之矣。神用之妙,可得而詮。一曰達才,二曰構意,三曰澄神,四曰會趣,五曰標韻,六曰植骨,七曰練氣,八曰和聲,九曰芳味,十曰藻飾。(《說詩補遺》第三八條)[2]P3841。
“十詮”之法涉及詩歌創作的多個方面:即創作主體修養的“達才”“練氣”;詩歌創作構思的“構意”“澄神”;詩歌審美的“會趣”“芳味”;詩歌韻律要求的“標韻”“和聲”;詩歌語言文辭要求的“植骨”“藻飾”。
二、“十詮”之法與詩歌創作
馮復京的“達才”“構意”“澄神”“會趣”“標韻”“植骨”“練氣”“和聲”“芳味”“藻飾”主要涉及詩歌創作的主體素質、藝術構思、詩歌聲律、詩歌語言文辭以及詩歌審美風范五個方面,下文分述之:
(一)“才”“氣”兼備的創作主體素質
“十詮”之法對創作主體提出“達才”和“練氣”兩點要求。所謂“達才”即“盡己之才”,而“達才”的基礎是“有才”,惟“有才”方能“達才”,因此馮復京對創作主體的知識積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博學多聞以積“后天之才”。“練氣”側重于創作主體的精神氣質培養,他所說的“氣”實則孟子之“浩然正氣”,自魏晉以降,詩論者對此多有論述,馮復京在此加以重新闡釋。
1.“才”與“學”——博學多聞的知識儲備
馮復京主張詩人應該多積累、多讀書,博學多聞,以豐富的才學來矯正捻須苦吟的創作方法和粗俗鄙陋的詩風,追求詩歌的含蓄蘊藉之美。
馮復京對于當時“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空談學風甚為不滿。《說詩補遺》第二則提到:“靈趣雄才,得自天授。精思妙詣,必以學求。然天授之奇者,不可以不學,學力之至者,未必不可以勝天也。”馮復京對當時浮游空疏學風的批判大膽而深刻,他告誡子輩們要多讀書,對有疑惑的問題要自己求證,不要被已有的成見所誤導:“王李李何,非知讀書者,吾向為所欺,汝輩不得忝則,凡言王李者,讀者其詳之”。“夫博綜者,文章之戶牖。精釜者,人物之權衡。故彌綸折衷,當窮千古之聞見,而不可矜一察之聞見也。當求此心之是非,而不可徇前人之是非也。”馮復京晚年著述《說詩補遺》一書時常常手不釋卷,還常和子輩馮舒等討論評價歷代詩人,直至去世前還研讀《薛能集》,其潛心學術,用心鉆研的精神實在難能可貴。為了能“新天下之聞見”,馮復京對歷代詩歌都進行了仔細研究,不循前人之成見,真正做到了求“此心之是非”的批評原則。對歷代優秀作品的學習,馮復京繼承了宋代嚴羽的“熟參”的思想。馮復京說:“梁陳浮淫,其韻俗,中唐空踈,其韻淺,試取熟參,當自超悟。”要求詩人通過“熟參”眾制,有所突破性的領悟,進而確立優秀的詩歌典范。
2.“才”與“體”——量才適體
馮復京于前文中提出將“才”與“學”結合起來,要求創作主體博聞強識,系統全面地繼承前人的文學傳統,同時,“達才”亦有“才”盡體用之意,即選擇最為擅長之詩歌體式,將個人創作上的特點和才能融入詩歌中去:
一曰達才者,予向云凡為其體,須以某為正宗,以何為極則,此標的之大凡也。……能此體,正不必兼彼體。工我法,正不必用他法。試以古作者評之,枚李以古詩鳴,沈宋以近體著,陳思之清綺不為魏武之莽蒼,杜陵之渾融,不效東山之飄逸。然而名家各擅,何必具體大成哉。[2]P7173
因各人的先天條件不同,故而后天的努力學習尤其重要。“達才”不僅要養“才”,更要“適”才。后天的學習實踐中,因各人知識儲備和性情涵養的差異,故而所擅長的詩歌體式不盡相同,所展現的詩歌風格也大相徑庭。選擇最為適合創作的“體”,亦成為“達才”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點上恰恰體現了馮復京細致入微之處。
3.“才”與“氣”——主體精神氣質培養
“練氣”,即側重于創作主體的精神氣質培養。馮復京主張創作者必須要“練氣”,也即是養氣,他所說的“氣”實則孟子之“浩然正氣”。作為善于養氣的創作者要“必留有余,無使困乏,主暢遂無至郁,淤循檢格,無流淫放。休天鈞,無傷儁逸。澄神思,無陷流俗。礪鋒穎,無墮卑陬,斯可注滿于噴玉之中,環周于貫珠之內矣。”[2]P7176“氣”對文學評論和批評鑒賞十分重要,創作者只有培養好自己的精神狀態和氣勢,才能盡力施展才華,創作出風格氣勢俱佳的作品。
(二)“意”“神”俱凝的藝術創作構思
陸機《文賦》早有構思想象特點的分析,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篇亦有相關論述。相對而言,馮復京對創作構思階段的理解更加細致,即把構思階段分為“構意”和“澄神”。馮復京所言之“構意”與歷代論述大致相當:“文術萬變,思路一揆。近取衿帶之前,冥搜象系之外,興來神答,則濡翰聯翩。理伏景幽,則含毫渺默。”[2]P7174此處形容構意的思維特點與《文賦》、《神思》大致相同,然馮復京又有新的創見,即將“構意”分為不同層面,指出“意遠者,格必高。意醇者,體必正,意壯者,氣必雄。意精者,詞必簡”。[2]P7174而相反,“意煩則亂,意盡則貧。……意深則隱,意浮則散。”[2]P7174馮復京所言之“意”即藝術創作構思中思維想象,詩歌作品“格高”“體正”“意壯”“氣雄”“詞簡”與藝術構思之“意”之“遠”“醇”“壯”“精”密切相關,將藝術創作構意與詩歌藝術造詣緊密結合起來。
“構意”后并不立刻進行創作,要使主體的心緒進入一種不可言說的澄明之境,即“澄神”階段:“無象可求,無方可執,造化不能秘,鬼神不能思”。然而如何才能達到這種境界呢?馮復京認為必須要“必澡雪靈臺,涵濡學府,內不煩黷以損和,外不纆牽以縈惑。天機洞啟,真宰默酬,從容于矩矱之中,邂逅于旦暮之際,庶幾乎罄澄心妙萬物者也。”如此之后,創作者的構思階段才算完成,為接下來組織語言、表情達意做好準備工作。
(三)“聲”“韻”相和的詩歌韻律要求
馮復京總論詩道,唯“格律、才情”二者,將詩體格律形式要求與創作主體的才情看作是詩歌創作最為重要的部分。
“學詩之始,先辨體式”,這種強烈的詩歌辨體意識反映到詩歌創作上即謹遵詩歌體式要求:“《虞書》曰:‘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裔是而降,夏歌浩衍,商頌沈深,國風優柔,雅頌典則,有不循軌度者無有哉。”馮復京援引《尚書》之言,強調詩歌創作應循“軌度”而行,“猶制器,至圓不加于規,至方不加于矩。”馮復京對聲律的要求十分嚴格,以聲辨體,于《說詩補遺》第六四提倡“古體用古韻,惟取諧合”古體詩必須用古韻,“若拘沈約之四聲,反落唐格近體,用唐韻貴在緊嚴,若越禮部之一字,即成宋體。”由此可見,每一種詩歌體式都在用韻上有不同的要求:古體詩、唐格近體詩、宋詩用韻的不同,若不嚴加辨析,一字越韻即成別體。不僅如此,各體詩歌用韻還得注意基本準則,即“用古韻不宜過奇,奇則陷于鴃舌。用唐韻不宜過巧,巧則流入詼諧。排律百韻不已,則唇吻告勞,歌行兩韻則遷,則轉折多躓。”
詩歌用韻,自成定式,一首詩歌“全在音節、格調,風神盡具音節中”。馮復京以為古人為詩,心中必有“金石”之音韻,具體說來又有個體、時代的差異性:
詩之有韻亦猶是耳。漢風韻藏于意表,魏制韻溢于格中,嗣宗之韻沖曠,太沖之韻孤高,淵明之韻自然,靈運之韻清遠,子美之韻沉深而有味,太白之韻飄舉而欲仙,王孟之韻閑淡而絕塵,高岑之韻秀令而近雅,靡不旨趣無窮,芬芳可佩,作者雖已會,眾條必待斯成品矣。梁陳浮淫,其韻俗,中唐空踈,其韻淺。[2]P3843
不同時代詩人在遵循基本韻律進行詩歌創作之時,因時代風氣以及詩人性情等個體因素不同而表現不同的風格,這是客觀存在的。若片面拘泥于聲律而忽視創作主體用韻的風格差異,謹奉“四聲八病”為詩歌創作的金科玉律,則亦不可為。顯然,馮復京已經意識到“詩多拘忌”之弊,故而援引鐘嶸、皎然以及本朝王世貞、胡應麟諸人“辨失”之論,認為聲律之法“宜加檢括”,認為詩歌創作應以“和聲”為目的,不應以音律限制作者“神思”,最終達到“試取熟參,當自超悟”的境界。
(四)“植骨”“藻飾”的語言文辭要求
在詩歌語言方面,馮復京提出了“植骨”“藻飾”。“骨”,最早來自魏晉對人物的評議品鑒,后被引入詩歌批評之中,《文心雕龍·風骨》即有:“《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于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故練于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此處之“風”,一般指詩歌中表現出的充實、感人的情志力量,以創作主體的“意氣駿爽”為前提,其基本特征是清、明;而“骨”,則意謂文章在語言表現上呈現的剛健風格。至于詩文的“藻飾”,劉勰亦有“若風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若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4]P1052-1064《文心雕龍風骨第二十八》
值得注意的是,馮復京對于古詩的古雅質樸十分贊賞,但是在“質”與“文”的辯證分析上,他還是明確提出不可盲目追求質樸而墮于鄙陋。《說詩補遺》第一四一則云:“古詩甚質,然太羹玄酒之質,非槁木朽株之質也;古詩甚文,然云漢為章之文,非女工纂俎之文也。”鑒于初學者的特殊寫作基礎,馮復京告誡:“字句與其浮響倒裝,不如沈實平正。與其學杜陵之蒼老危仄,不如學王李之風華秀朗。與其為大歷之清空文弱,不如為景龍之縟蒤豐腴。”[2]P3836
可見,馮復京吸收了劉勰對風骨和藻采的辯證認識的基礎上,注重創作過程中詩歌語言要素,把“植骨”和“藻飾”并提,為的也是防止偏重其中一方面而導致失衡,最終實現其理想的詩歌范式。
(五)“趣”“味”相投的詩歌審美風范
在詩歌審美上,馮復京特別提出了“味”和“趣”給人帶來的審美感受,他認為優秀的詩歌必然要“會趣”、有“芳味”。這是“十詮”之法的要求,實際上,馮復京對詩歌創作實踐的要求并不限于此,他還提出了“中正”“含蓄”的審美要求。
“趣”在明代詩歌審美范疇中處于較為核心的位置。馮復京把“趣”和骨氣神韻才力看得同等重要,他認為“趣”是詩歌創作成功與否的關鍵性因素:“由是章句櫛比,聽真宰以就班;音調鏗鏘,循天鈞而赴節。骨氣神韻,趣味才力,則主張旋運於章句音調之中,以贊成厥美者焉。”[2]P7163馮復京強調的“趣”更主要的是體現在詩歌審美的方面:“蓋詩以道性情,性情所向,涉則成趣。上溯漢魏,下迄盛唐,善鳴諸家,莫不以興趣為主。”[2]P7175馮復京認為“趣”的生成來源乃是“性情”,“趣”是情感注入的產物,是性情的呈現,屬于主體層面的范疇,是審美修養和審美追求的產物。《說詩補遺》第二云:“靈趣雄才,得自天授。精思妙詣,必以學求。然天授之奇者,不可以不學,學力之至者,未必不可以勝天也。”第七三則又道:“非沉思曲換,去故就新,天趣橫生,高唱郁起,而可以成家者,未之有也。”可見,“趣”是審美主體的天賦,是主體天賦生機靈動的體現,而“靈趣”則具有自然天成、不可強求、生機靈動的特質。因此,生機、靈機、天真直露乃得趣之要。
馮復京將“芳”的嗅覺感受與“味”覺感受聯系在一起,提出“芳味”說:“氤氳郁烈,嗅之觸鼻者芳也;醰粹豐腴,嘗之雋永者味也。然辟芷幽蘭,豈曰不芳,太羹玄酒,豈曰無味,又芳而無味,則山澤之癯瘦,味而不芳,則河朔之羶肥矣。”要求詩歌既能呈現出濃烈芬芳的嗅覺美感又要給人以豐腴雋永的味覺美感,在詩歌審美層面上將各種感官的深層體驗直接納入詩歌的品閱之中。一首詩歌的內蘊千姿百態,理趣韻致也是變化萬千,但好的詩歌必須要有內在的活力生趣、情理韻致。馮復京所說的“芳味”正是詩歌內在的活力生趣、情理韻致的審美風范。
三、結語
馮復京的“達才”“構意”“澄神”“會趣”“標韻”“植骨”“練氣”“和聲”“芳味”“藻飾”之詩歌創作“十詮”之法,是其詩學理論著作《說詩補遺》的重要組成部分。馮復京在系統地梳理漢魏六朝以及唐代詩歌發展流變史的基礎上,飽讀歷代詩歌,以辨析詩歌體格入手,從詩歌本質論、流變論、審美論、創作論等方面建構詩學理論,在綜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十詮”之法。
“十詮”之法雖為詩歌創作而論,然其舉要則涉及詩歌創作的主體素質、藝術構思、詩歌聲律、詩歌語言文辭以及詩歌審美風范等多個方面:詩歌創作主體應該多積累、多讀書,博學多聞,以豐富的才學來矯正捻須苦吟的創作方法和粗俗鄙陋的詩風,還應“量才適體”以各人之知識儲備和性情涵養的差異選擇最為擅長的詩歌體式,同時亦要培養好自己的精神狀態和氣勢,創作出風格氣勢俱佳的作品;在藝術創作構思上,注重“構意”和“澄神”,使主體的心緒進入一種不可言說的澄明之境,為接下來組織語言、表情達意做好準備工作;在詩歌聲韻要求上,一方面嚴格要求創作者遵循詩歌韻律法則,同時亦注重詩歌用韻的各體和時代差異性,要求不應以音律限制作者“神思”,應當“試取熟參,當自超悟”;在詩歌語言方面,馮復京吸收了劉勰對風骨和藻采的理論觀點,注重創作過程中詩歌語言要素,把“植骨”和“藻飾”;而在詩歌品讀審美接受上,馮復京以“會趣”“芳味”論之,要求詩歌既要呈現濃烈芬芳的嗅覺美感又要給人以豐腴雋永的味覺美感,在詩歌審美層面上將各種感官的深層體驗直接納入詩歌的品閱之中,“趣”“味”執著,正是馮復京追求的自然天成與內在的活力生趣、情理韻致相統一的詩歌審美風范。
就一般文人而言,其創作自覺地將個體生命價值與外在環境緊密聯系在一起[5],作為一介布衣文士,馮復京一生仕途坎坷。然其出生文學世家,一生博聞強記、勤于思考、敏于著述,其學術視野相對開闊。馮復京主要活動于明代萬歷年間,其詩學思想受七子派影響較深,但是馮復京能夠做到兼收并蓄,去粗取精。馮復京在認識到了七子派的詩歌創作和詩學理論不足的基礎上,嚴厲批評其遺風流韻種種弊端,并積極探索,在前人優秀創作傳統和創作經驗的基礎上加以總結批評,提出詩歌創作的“十詮”之法。“十詮”之法,是馮復京詩歌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明代詩學理論史不可忽視的一環,對梳理明代詩學理論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