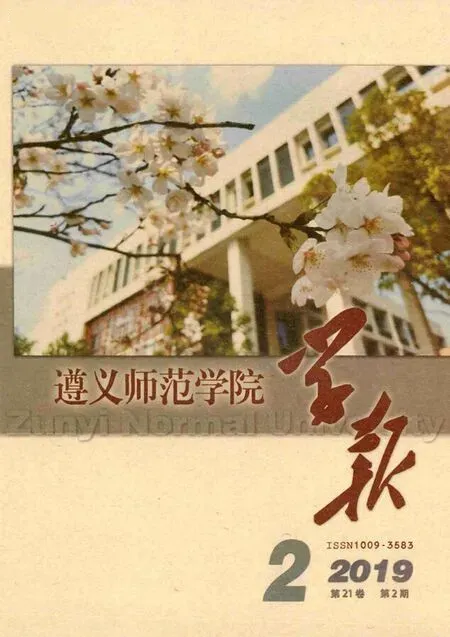《東邪西毒》環形敘事視角下的解讀
陳 玲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江蘇南京210000)
1994年絕對是難以逾越的電影年,出現了一大批電影杰作,如中國的《重慶森林》《東邪西毒》《活著》《霸王別姬》《陽光燦爛的日子》等,西方的《阿甘正傳》《肖申克的救贖》《低俗小說》《獅子王》等。《東邪西毒》是王家衛光影世界中濃墨重彩的一筆,環形敘事結構諭示永世不得掙脫的人性循環,時間對人的意義消失殆盡,空間對人成為一種束縛與框定,人物最終在虛無的黑洞中無力地自我消耗與消亡。
一、環形敘事結構
環形敘事結構電影是非線性敘事電影中比較特殊的一類,它把故事分割成保持某種關聯的敘事片段,再采用蒙太奇手法把敘事片段依據某個主題拼貼成電影;與此同時,把敘事片段拼貼為互為因果的段落,最終使故事結局呈現出無始無終的藝術效果。這類電影的橫向文本時間猶如首尾相銜的“圓圈”,縱向的文本時間呈現為一堆時間碎片。
在敘事結構上,《東邪西毒》也是一部環形敘事結構電影。電影根據環形人物關系(桃花、慕容嫣/燕愛慕黃藥師,黃藥師卻愛著歐陽鋒大嫂,大嫂愛著歐陽鋒,歐陽鋒卻逃避并在桃花與慕容嫣/燕的身上想象大嫂)將故事分為關于愛情親情友情的幾個敘事片段,但是這些敘事片段并不是以因果關系維系而以循環人物關系為線索。然后利用循環人物關系將敘事片段進行多線索的交叉的拼貼敘述,此處是五組參差交錯的人物關系(歐陽鋒-大哥-大嫂-慕容嫣/燕-桃花,黃藥師-大嫂-慕容嫣/燕-桃花,慕容嫣/燕-歐陽鋒-黃藥師,盲武士-桃花-黃藥師,村姑-弟弟-洪七)進行交替拼貼敘事,使得影片結構上呈現為一幅斑駁零散的圖景。參差交錯的人物關系環環相扣,故事始于歐陽鋒雇傭殺手,中間卻是糾纏不清的愛戀關系,桃花與慕容嫣/燕愛慕黃藥師,黃藥師卻愛著歐陽鋒大嫂,大嫂愛著歐陽鋒,歐陽鋒卻逃避并在桃花與慕容嫣/燕的身上想象大嫂,故事又終于他雇傭殺手。故事結尾即是開頭,一切又回到了原點。最終,電影形成一個首尾呼應的環形結構,所有的人物都被困在感情的圓圈之中。時間與時間在零碎斑駁的影像中化為灰燼與碎片,人物在時間荒漠與空間碎片中自我沉醉、絕望與耗盡。
二、時間灰燼——后現代的能指游戲
(一)理論背景
“我們可以設想一部只是純粹延續時間的電影,即一部畫面至始至終都是空白的影片。”[1]馬塞爾·馬爾丹斷言,電影是關于時間的藝術。的確,任何藝術都離不開時間,任何一部電影也離不開時間,雖然對時間的體驗與表達千變萬化。
在傳統社會,人們對時間的體驗是一種具有終極意義的時間,它指向彼岸世界而具有解脫與重生意義,并給人一種安全感與神圣感。進入現代社會,神圣時間是可以精確計算的機械的鐘表時間,喪失了原本的神圣感而變得越發冰冷。進入后現代社會,時間從精神與機械轉向人的身體,從歷時性轉為了當下的瞬間性,這種轉變導致人類與本源時間不斷變得隔離疏遠。時間的加速而越發輕盈快捷,冷漠地穿梭在任何一個空間角落;時間不再指向終極意義與永恒價值,而轉向注重體驗瞬間快感,所以臨時性與短暫性成為個體快樂幸福之源。這種美學思潮反映在環形敘事電影之中時,電影利用審美化手法將客觀時間變成一種圓形時間,解構時間的線性特質與歷史性,導致時間可以被任意改造而喪失嚴肅性變為一種支離破碎、破敗殘碎的能指游戲。
(二)人與時間的矛盾和對抗
王家衛的電影對時間格外敏感,像《重慶森林》中警察223的保質期獨白,《阿飛正傳》中阿飛講述“無根鳥”,《東邪西毒》英文譯名為“Ashes of Time”(時間的灰燼),都是關于時間的哲理思考與藝術表達。電影利用沙漠、鏡子、醉生夢死酒等意象表達對時間的隱喻與象征。洪七問西毒:“沙漠的后面是什么?”歐陽鋒回答:“只不過是另一個沙漠。”然后歐陽鋒獨白:“每個人都會經過這個階段。看見一座山,就想知道山后面是什么。我很想告訴他,可能翻過去山后面,你會發覺沒有什么特別。回頭看,會覺得這邊更好。但是他不會相信,以他的性格,自己不試過是不會甘心。”是的,洪七會去尋找時間的意義,他在對抗時間。我們用沙漏去計算與測量時間,它代表過去、現在與未來而并且自身成為一種時間象征。電影中的遼闊無邊的沙漠則是一個靜止的巨型沙漏,所有人被困在時間荒漠又難覓出路。時間無所謂客觀還是主觀,也不是機械時間或生命時間,而是冷漠無情的后現代時間,它是一個裹挾眾人的巨型沙漏。巨型沙漏的單調重復、無邊無際、死氣沉沉喪失了勃勃生機而成為眾人沉重而永久的懲罰。無論是與時間抗爭的洪七,還是對時間無望的歐陽鋒、黃藥師等人,終將被期待時間的絕望所吞噬。
明鏡照物,妍媸畢露,鏡子的原本作用是讓自己看到自己形象。電影中出現鏡子的地方是歐陽鋒大嫂對銅鏡的自言自語:“我覺得有些話說出來就是一生一世,現在想想,說不說也沒什么分別。有些事會變的。我一直以為是我自己贏了,直到有一天看著鏡子,才知道自己輸了。在我最美好的時候,我最喜歡的人都不在我身邊。如果能重新開始那該多好?”鏡子是提醒人們時間的一種工具,對人既是催促也是壓迫,它提醒西毒大嫂再美好的時光也必將散盡天涯;再次目睹鏡中容顏,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酒和時間又有何關系?歐陽鋒嫂子托黃藥師給歐陽鋒帶去一壺醉生夢死酒,并且囑咐:“喝了之后,可以叫你忘掉以前做過的任何事。人最大的煩惱就是記性太好,如果什么都可以忘了,以后的每一天將會是一個新的開始,那你說多開心?”黃藥師喝了醉生夢死,忘記很多事,但記得自己愛過一個叫桃花的女子,于是前往桃花島居住。歐陽鋒喝了醉生夢死,經常會望著白駝山,后來醒悟“其實,醉生夢死只不過是嫂子跟他開的一個玩笑。越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忘記的時候,反而記得越清楚。”醉生夢死酒讓人忘記煩惱,其實是人與記憶的博弈,本質上是人與時間的矛盾與對抗。但記憶是一種很磨人的東西,該隱瞞的總清醒,該遺忘偏記得。
電影的情節時間從驚蟄篇1——立春篇——夏至篇——白露篇——驚蟄篇2,貌似不同的首尾實則是一個節氣。《夏小正》曰:“正月啟蟄,言發蟄也。萬物出乎震,震為雷,故曰驚蟄。是蟄蟲驚而出走矣。”驚蟄一到,所有人開始忙于春耕。時間悄無聲息地從一個驚蟄流轉到另一個驚蟄,目睹了巨型沙漏中眾人的渺小卑微與徒勞掙扎。從桃花與慕容嫣/燕愛慕黃藥師,黃藥師卻愛著歐陽鋒大嫂,大嫂愛著歐陽鋒,到歐陽鋒逃避并在桃花與慕容嫣/燕的身上想象大嫂的拒絕與被拒絕的痛苦折磨始終未曾停止。一個驚蟄開始,下一批苦情的人又將在西毒的客棧上演。
三、空間碎片——喪失意義的后現代空間
(一)理論背景
隨著生產力發展與人類思維能力增強,空間之于人最初的意義——給與我們生存活動的邊界與范圍,早已面目全非。20世紀以來,空間問題引發了很多學者的關注。愛德華·W·蘇賈認為:“對空間的重申以及對后現代地理學的闡釋,不僅僅是經驗性考察的一個聚焦點,也是對這樣一種需要的回應:對具體的社會研究和熟悉情況的政治實踐中的空間形式,需要加強注意。”[2]他將空間問題上升到了本體論的地位,足見他對這個問題的重視程度。的確,空間問題早已不是地理學意義上的空間,而是一個哲學問題了。如今,依賴科技迅猛發展,我們深深體驗著時間加速度帶來的壓迫與擁擠之感;天南地北也是一抬腿的事情,但這科技進步卻不是普惠性的,是以能否支付相應的服務費用劃分社會等級的。“由于技術因素而導致的時間/空間距離的消失并沒有使人類狀況向單一化發展,反而使之趨向兩極分化。它把一些人從地域束縛中解放出來,使某些社區生成的意義延伸到疆界以外——而同時它剝奪了繼續限制另外一些人的領土的意義和賦予同一性的能力。”[3]因此,擁有更多的時間和更快的速度已經成為一種權利與身份地位的象征,這反而導致空間貶值。
從前現代、現代到后現代社會,我們對社會變化的體驗不僅僅涉及客觀物質與思想觀念,其中對時間感與空間感的體驗也是一個十分突出的線索。由于占有空間意味著權利的彰顯,所以現代社會對時間與速度的追求目的在于征服更加廣袤的空間。但隨著科技發展導致時間加速度,后現代社會以追求高速度為榮,空間喪失原初地位;并且,時間加速將空間擠為碎片,空間意義漸漸喪失。
電影的空間是一種“由音樂,由特定的蒙太奇組合節奏,由風格化的色調與構圖所喚起的遼闊、幽遠的空間聯想”[4]。這種思潮反映在電影美學之中,電影空間已不是一種單純為故事服務的物理空間,更不是傳統的以因果邏輯維系的影像空間,而是一種喪失因果邏輯旨在表現人物內心體驗的零碎片段的后現代空間。
(二)喪失意義與人浮于世
《東邪西毒》的影像空間是典型的后現代空間,空間因為喪失因果邏輯的維系而失去了線性感,導致影視人物猶如漂浮穿梭于各個空間碎片,同時流露著一種不知身在何處的飄零之感。電影時間經歷驚蟄篇1——立春篇——夏至篇——白露篇——驚蟄篇2,每個篇章之間不以因果邏輯貫通而是散文化拼貼,以及非線性時間連綴的空間變得破碎不堪。因此,電影感染人心之處不是這個新穎的詩意的非武俠故事,而是一個場景、一句臺詞或者某個人物,整部影片都彌漫著一種碎片化的朦朧曖昧之感,令人感覺意義喪失與人浮于世。顯然,人物都在自己的空間里安生與逃避,除了灑脫自在的洪七公之外,其他人物都有一個共性:心事重重、郁郁寡歡。每個人所屬的空間都是個人的、排外的、焦慮的、孤獨的,所有人都難以逃避時間荒漠的煎熬與精神層面的孤獨。
電影采用奇峻多變的攝影角度、多樣復雜的廣角鏡頭、傾斜變動的畫面構圖營造出一個孤獨荒涼的影視空間。每個人物既有自己的空間領域,也被空間束縛規定。人物以空間命名而彰顯權利地位,東邪西毒南帝北丐的名稱不僅是身份權利,也是性格特征。為情所困的歐陽鋒困于沙漠孤獨神傷,愛而不得的慕容焉/燕蝸居窯洞心性變異,移情別戀的桃花在五彩河中寂寞難耐,灑脫自在的洪七四海為家,孤苦無依的孝女唯有依靠枯木,這些囚禁肉身的空間不僅是一種物理空間,更是他們人物特征的強化與見證。
四、思想意蘊——虛無的黑洞
德國現代思想家恩斯特·布洛赫在《希望原理》問到:“我們是誰?我們來自何方?我們去往何處?我們在期待什么?什么在期待我們?”[5]這些問題我們耳熟能詳,但卻始終無解,或許時間才是一切謎的謎底。
歐陽鋒深愛大嫂卻躲入沙漠,黃藥師愛戀西毒大嫂又移情別人,慕容嫣/燕因愛生恨欲殺黃藥師,桃花移情別戀而獨受煎熬,這群人渴求愛情又害怕被拒絕,寧愿忍受煎熬也不肯去面對,最后白白折磨自己。正如“那沙漠后面會是什么呢”,是另一座沙漠,也是現代人漫無邊際的情感荒漠。最后主人公都有了自己的綽號,東邪西毒南帝北丐,被空間定義限制,終身漂泊于天地四極。
“在這里,不再有對世界的有意義的整合,也不再是從‘有意義的眼睛’出發進行對無意義的世界的批判,有的只是蛻化為純粹呈現性的‘眼睛’的單純呈現本身。這就是后現代的荒誕。”[6]《東邪西毒》中,人物的生活動機與結果沖突、現象與本質相反,透露著一股荒誕氣息。在一個無精神寄托的虛無時代,無所謂意義和價值,也沒有對意義喪失的控訴憤怒,只是著眼當下的嬉戲。像環形敘事電影《東邪西毒》,人物原是為了追求美好的愛情,最后卻事與愿違,越是抓緊不放,越是痛苦難熬。堅持只能帶來痛苦與煎熬,索性,歐陽鋒黃藥師選擇逃避,慕容嫣欲殺阻止自己去追求愛情的哥哥“慕容燕”(實為自己的另一個身份)。折騰糾結半生,最后發現又回到了當初的原點——驚蟄2。影片最后沒有明顯的愛恨情仇,有的只是空洞平面之上的無力、頹廢與游戲。
《東邪西毒》中的時間不再是單純的展開敘事的手段,而是被敘述的主題之一,還是攜帶無限循環色彩的圓形時間。本質上,該片反映的時間灰燼問題也是自古以來困擾人類的時間問題。《東邪西毒》中猶如達利《軟鐘》的時間荒漠,反映了時間高度加速、空間無限拓展的事實。此處反映了后現代時間的瞬間化和極速化體驗,以及給人產生的一種壓迫之感與無所寄托之感。時間癱軟無力化為一望無垠的漫漫荒漠,空間破碎殘破化為一種充滿隔閡的束縛與限制;對于心事重重的歐陽鋒、黃藥師、慕容嫣/燕而言,時間是一種猶如無盡沙粒的喪失意義的精神折磨,空間是一種拒絕溝通與自我保護的軀殼。總之,電影使用富含詩意與意境的手法書寫后現代人的精神困境,在時間荒漠空間碎片中毫無寄托的自我耗盡與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