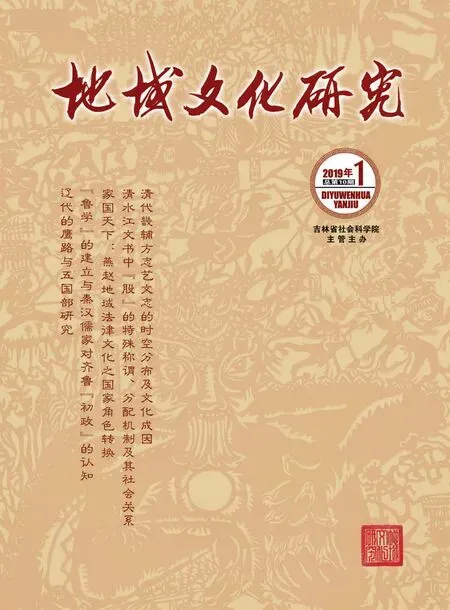遼代的鷹路與五國部研究
景 愛
遼代的鷹路與五國部,見于《遼史》《金史》《契丹國志》《文獻通考》諸書。不過均非專傳,其記事簡略,互有出入,不盡相同,這給后世研究造成了許多困難。由于鷹路、五國部涉及遼、金的興衰和中國古代對外興安嶺以南地區的管轄,故中外學者對此甚為重視,研究者不乏其人。清代學者曹廷杰、屠寄,日本學者池內宏,都曾對此進行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績。這些都給當代學者創造了條件,奠定了基礎。
然而有些當代學者,既未進行實地調查,又對古代文獻缺乏仔細研讀,其研究有欠于深入,出現了不少瑕疵。例如用推斷代替史實,證據不足遽下斷語,造成了許多混亂,在學術界產生了不良的影響。
筆者早年(20世紀80年代)研究過遼代的鷹路與五國部。30余年以后,重讀舊作,發現當年的研究不夠深入細致,故而重操舊業,吸取百家之長,以期達到正本清源的目的。
一、鷹路的由來
契丹之先,曾以狩獵為生。《契丹國志》記其“國士風俗”講:“其父母死,以其尸置于山樹之上,經三年后收其骨而焚之,酌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夏月時,向陰食;我若射獵時,使我多得豬鹿’”①(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2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21頁。。這里所記,應為契丹早期即原始社會生活之情形。遼建國以后,狩獵猶存。“遼國以畜牧、田漁為稼稻”①《遼史》卷48《百官志四》,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822頁。,“畜牧畋漁,固俗尚也”②《遼史》卷46《百官志二》,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20頁。。不過,這時的狩獵,對于契丹貴族來說已失去經濟意義,變成了激發上進精神的健身娛樂活動。遼朝皇帝有四時捺缽,在不同的季節到不同地方狩獵,“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畋獵,歲以為常”③《遼史》卷32《營衛志中·行營》,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73頁。。春天通常是到鴨子河漁獵,鑿冰鉤魚、獵取天鵝,為了順利獵取天鵝,需要有海東青幫助。海東青是獵鷹中的一種,發現空中有天鵝時,五坊擎進海東青,拜授皇帝放之,“鶻擒鵝落……皇帝得頭鵝,薦廟,群臣各獻酒果,舉樂”④《遼史》卷32《營衛志中·行營》,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74頁。。五坊是管理鷹鶻的官府,景福元年(1031)十一月“縱五坊鷹鶻”⑤《遼史》卷18《興宗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13頁。,重熙七年(1038)二月“幸五坊閱鷹鶻”⑥《遼史》卷18《興宗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20頁。。“鷹鶻”是海東青的別稱,清代尚有這種說法,遼興宗親自到五坊閱海東青,說明遼朝皇帝非常重視海東青。
史籍記載:“海東青,出五國。五國之東,接大海,自海外而來謂之海東青。”⑦(宋)佚名:《女真傳》、《大金國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89頁。“女真東北與五國為鄰,五國之東鄰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捕鵝鶩,爪白者尤以為異,遼人酷愛之”⑧(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10《天祚皇帝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2頁。。所謂“大海”指鄂霍次克海,海東青自海外飛來,首先在黑龍江下游奴兒干落地,最易捕捉。“海東青,遼東海外隔數海而至,嘗以八月十五日渡海而來者甚眾……奴而干田地,是其渡海之第一程也。至則人收之,已不能飛動也。蓋其來飲渴困乏,羽翮不勝其任也。自此然后,始及東國。”⑨(元)熊夢祥:《析津志》(輯佚本),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第234頁。“努而干”,今作奴兒干。“東國”指五國部。海東青的產地,一是奴兒干,二是五國部。
海東青從海外飛來,屬于候鳥,年年如此。海東青棲息于森林之中,所謂海外應指庫頁島、鄂霍次克海東北的半島以及北美大陸。其以海外飛來以后,先在奴兒干暫時休息,然后飛向松花江南北兩岸張廣才嶺、小興安嶺區棲息,筑巢生蛋,生育后代。
《柳邊紀略》記載:
遼以東皆產鷹,而寧古塔尤多。設鷹把式十八名。每年十月后即打鷹,總以得海東青為主。海東青者,鷹之最貴者也。純白為上,白而雜他毛者次之,灰色者又次之。即得盡,十一月即止,不則更打。若至十二月二十日不得,不復打矣……凡鷹生山谷林樾間,率有常處。善打鷹者,以物為記,歲歲往,無不遇,惟得差不易耳。視其出入之所,系長繩,張大網,雖夜優草莽中,伺之人不很行,行則驚去。⑩楊賓:《柳邊紀略》,見《遼海叢書》,沈陽:遼沈書社,1985年,第257頁上欄。
寧古塔產海東青,還見于清初流人吳振臣所著的《寧古塔紀略》:“鷹第一等名海東青,能捕天鵝,一日能飛千里。”?穆曄駿:《吉祥如意的山——張廣才嶺》,《黑龍江文物叢刊》1984年第1期。由于飛速特別快,故而能遠渡重洋,從海外飛來。寧古塔即今寧安縣,《寧安縣志》記載縣內產海東青。?《述本堂詩集·寧古塔記略》,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572頁。寧安縣北鄰依蘭縣,《依蘭縣志》記載:“鵰,猛禽。尾翎十二根。十四根者,為海青。”①民國《寧安縣志》卷3《職業·漁獵》,第12頁上。
黑龍江滿語專家穆曄駿有文稱,張廣才嶺之名來源于滿語,其義為“幸頭好”,見于康熙年間的《五體清文鑒》、乾隆年間的《三合便覽》,譯成漢語為吉祥如意的山嶺,是以山林中多珍禽異獸可以獵取得名。早在清朝初年,就把山林中捕到的海東青貢獻給皇帝。②民國《依蘭縣志·物產·鳥類》,第36頁。
世居嫩江縣(墨爾根)四站的邵奎徳著文說,這里的深山老林中多海東青,當地人稱之為“吐鶻鷹”。冬天躲在空樹筒(按:指樹洞)里避寒,夏天棲息于樹上,壘枝成巢,產卵孵育后代。1943年7月,他在山頂上用鷹籠子活捉一只海東青,全身呈鐵青色,胸前有白毛。飼養到當年10月,忽然天上有天鵝的鳴叫聲,他趕緊把海東青放出去,像箭一般拔地而起,沖入高空天鵝群,將四五只天鵝咬傷,跌落在山坡上。然后海東青揚長而去,不見了蹤影。③邵奎徳:《名鷹海東青捉放記》,《黑龍江文物叢刊》1982年第1期。
四站在清代屬于布特哈,布特哈以產海東青著名。康熙三十八年(1699)五月,黑龍江將軍薩布素致布特哈總管覺羅恩圖,“曉諭爾等所轄嫩江、納謨爾所在達斡爾等,尋找雛鷹。若捕得數只,則小心喂養,俟上供時選送”。同年六月,薩布素又咨布特哈總管覺羅恩圖,重申此事:“先前曾曉諭爾等所轄嫩江、訥謨爾所住達斡爾人等,令伊等找尋雛鷹,若捕得數只,則小心喂養,俟上貢時選送等語,咨行了。若可堪上貢,應行咨報所獲雛鷹幾只等情,為此咨行。”④樂志德主編:《達斡爾族資料集》第9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21頁、第223頁。文內所說的雛鷹,指的就是海東青。
上述四站、布特哈,都屬于小興安嶺區。寧古塔屬于張廣才嶺東麓,其地多山林。故而可知,張廣才嶺和小興安嶺,在清代民國年間是盛產海東青的。據《呼蘭縣志》《珠河縣志》《寶清縣志》,此三縣也產海東青。在遼金時代,也是如此。
張廣才嶺和小興安嶺的海東青,是從黑龍江下游奴兒干飛來的。遼朝皇帝為了得到海東青,不斷派官員帶松花江下游索取,五國部成為重點地區,這條水路便在歷史上稱作鷹路了。
在明白了鷹路的由來以后,在此基礎上方可以研究五國部,二者密不可分。五國部所在的地方,一是必須在松花江沿岸,二是其附近必須有海東青棲息的山林,二者缺一不可。
二、五國部的構成
五國部之構成,以《遼史·營衛志》的記載最為清楚和準確:“五國部。剖阿里國、盆怒里國、奧里米國、越里篤國、越里吉國”⑤《遼史》卷33《營衛志下》,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92頁。。不過在《遼史》的別處,以及后來的文獻中,其名稱稍有不同,或有很大的差異。
1.剖阿里部
《遼史·百官志》有怕里國王府、婆離八部大王府⑥《遼史》卷46《百官志二》,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59頁。;《兵衛志》屬國軍中有頗里⑦《遼史》卷36《兵衛志下》,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432頁。。陳述先生考證說:
《遼史》卷20《興宗記》:重熙十七年七月,婆離八部夷離堇虎翻等內附。卷25《道宗記》:“大安十年四月,蕭朽哥秦頗里八部來侵,擊破之”。卷26《道宗記》:“壽昌元年七月,頗里八部來附,進方物。二年八月,頗里八部進馬”。婆里即頗里,卷46《百官志》:“有婆里八部大王府,又有怕里國王府,似是復出或不同部分”。①陳述:《遼史補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1492頁。
按:《遼史》的撰寫由多人分別執筆,將少數民族語言譯成漢語時,各隨其便,每個人所選用對音的漢字自然不同,于是產生了同音異字現象,這是不可以避免的。陳述先生所言極是。在遼、金二史中,這種例證很多,讀史時必須細心分析,以免誤解。
曹廷杰指出:“遼五國部,有博和哩國。頗黎,博和哩,音同字異也”。②曹廷杰:《曹廷杰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71頁。屠寄《黑龍江輿圖》在精奇里江(結雅河)匯入黑龍江的下方,標注“博科里城”,注文曰:“即遼剖阿里國古城,今稱鄂爾多”。③《黑龍江輿圖》,光緒二十五年(1899)石印本第32頁。若此,剖阿里又可稱博科里。
按:乾隆年間成書的《遼金元三史語解》,依據《八旗姓氏通志》,將剖阿里改成博和哩,④《遼金元史語解》,《遼史語解》卷3《部族》,道光四年(1824)刻本,第8頁上。曹廷杰所記的博和哩,即本于此。《遼金元史語解》又稱:“伯里,滿洲語弓也。卷二十作婆離,卷六十九做婆離,卷二十五作頗里,卷四十六作怕里。”⑤《遼金元史語解》,《遼史語解》卷3《部族》,道光四年(1824)刻本,第10頁上。若此,剖阿里又作“伯里”,釋為滿語之“弓”。滿語出于女真語,不過并非完全相同,據金啟孮研究,滿語只有百分之七十與女真語相同。
《文獻通考》將剖阿里寫作“怕忽”⑥(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326《四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571頁。,“怕忽”當為《遼史》“怕里”之音訛。《文獻通考》為元代馬端臨所作,由遼至元前后歷三代近300年,馬氏撰此書時,尚未見到官修的《遼史》,“怕忽”不知所據,或許出自傳聞。觀《文獻通考》所記五國部只有四部(怕忽、噴納、咬里沒、玩突),鐵勤為誤入,尚缺一部,資料不足故也。
2.盆奴里部
在《遼史·百官志》諸部中,有蒲奴里部,⑦《遼史》卷46《百官志二》,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66頁。在諸王府中有蒲昵國王府。⑧《遼史》卷46《百官志二》,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61頁。《圣宗記》開泰七年(1020)九月記事有:“蒲昵國使奏,本國與烏里國封埌相接,數侵掠不寧,賜詔諭之”⑨《遼史》卷18《圣宗七》,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84頁。。蒲奴里與盆奴里同音異字,蒲奴里中之“奴里”,急讀即為“昵”,可知蒲昵即蒲奴里。
《金史·世紀》記載,景祖烏古廼時代(相當于遼興宗時期),有“五國蒲聶部節度使拔乙門畔遼,鷹路不通”⑩《金史》卷1《世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頁。之記事。此“蒲聶”為蒲昵之音變,亦是蒲奴里、盆奴里之異稱。《文獻通考》寫作“噴納”,“噴”與盆同音,“納”為奴之訛。“噴納”為盆奴里之訛,不仔細分析,很難見其間的聯系。
《遼金元三史語解》稱:“富珠里,卷十四作蒲奴里,卷三十三作盆奴里。今從《八旗姓氏通志》改正。”①《遼金元史語解》,《遼史語解》卷3《部族》,道光四年(1824)刻本,第8頁上。“富珠里”與盆奴里、蒲奴里之讀音相差太懸殊,這種改正可能不準確。
《黑龍江輿圖》在屯河(今湯旺河)畔標志有固本納城,注文曰:“即遼國五國部盆奴里古城”②《黑龍江輿圖》,光緒二十五年(1899)石印本,第5頁。。固本納即公本納,不知以何得名,其意為何。《黑龍江輿說·呼蘭城圖說》謂:“吞河既合眾水,又曲曲東流五十余里經固本納城東北,其城即金屯河猛安,元初桃溫萬戶府故城,亦即遼五國部盆奴里國,一作蒲奴里,《金史》所謂五國蒲聶部者也。”③《遼海叢書》,沈陽:遼海書社,1985年縮印本,第2051頁。
3.奧里米部
奧里米部(圖一),又稱“阿里眉國”。《契丹國志》載:“又東北至屋惹國、阿里眉國、破骨魯國。”④(宋)葉隆禮:《契丹國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13頁。阿里眉與奧里米稍異。《文獻通考》作“咬里沒”,⑤(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327《四夷四·女真》,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571頁。其讀音與奧里米差異甚大。
明《全遼志》所附《開原控制外夷圖》海西東水陸城站有奧里米站,其卷六《外志》亦記有奧里米站。⑥《遼海叢書》,沈陽:遼沈書社,1985年縮印本,第687頁。清《黑龍江輿圖》于松花江下游左岸,標注有:“鄂里米和屯,即遼奧里米國城。”⑦《黑龍江輿圖》,光緒二十五年(1899)石印本,第12頁。在黑龍江右岸一小河旁,標注有:“烏勤敏即烏里哈河遼奧里米國之水。”⑧《黑龍江輿圖》,光緒二十五年(1899)石印本,第22頁。烏勤敏為奧里米之訛。屠寄在《黑龍江輿圖說》中稱:黑龍江“又迤南五十里逕奧里米故城北,松花江東北來會。”⑨《黑龍江輿圖說·黑龍江總圖說》,見《遼海叢書》,沈陽:遼沈書社,1985年縮印本,第1025頁。
上述文中有“鄂里米和屯”,“鄂里米和屯”為滿語,即奧里米城之微改,意為鄂里米城,今稱中興故城(圖二),是以鄉鎮得名。民國年間綏濱縣設治之初,稱敖來密。現在這里有小河稱敖來密河,河畔有敖來村。1973年7月—9月,筆者與張泰湘先生實測敖來密古城,主持城郊墓群發掘期間,即下榻于敖來村。⑩詳見《文物》1977年第4期:a.《綏濱永生的金代平民墓》;b.《松花江下游奧里米古城及周圍的金代墓群》。奧來密古城,是村民對奧里米故城的一種稱謂。《文獻通考》將奧里米作“咬里沒”,不仔細玩味,很難找到語言上的對應關系。
《遼金元三史語解》之《遼史語解》稱:“鄂羅木,蒙古語‘律’也,卷十四作奧里米,卷六九訛為奧里。”①《遼史語解》卷3《部族》,道光四年刻本,第8頁上。按:奧里米訛為奧里,實為脫落了“米”字。將奧里米改為蒙古語“鄂羅木”,實在是牽強附會,不可以為據。奧里米的名字,從遼至今沒有太大的變化,令人稱奇,在五國部中僅見于此。
4.越里篤部
《遼史·百官志》有:“越里覩國王府,亦日斡離部。”②《遼史》卷46《百官志二》,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59頁。此“越里覩”即《營衛志》《越里篤國》,二者的讀音完全相同。《文獻通考》作“玩突”,《越里篤部》急讀就變成了《玩突》。
斡離部又作“幹里城”,曹廷杰稱:“三姓下三百五十余里南岸瓦里和屯,即《通志》斡離城。”③《曹廷杰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69頁。細玩味,“斡離”“斡里”可能是“越里”之訛,脫落了“篤”字所致。屠寄《黑龍江輿圖》在松花江右岸標志有宛里城,注文曰:“即倭羅郭城,即遼五國越里篤城。俗呼為瓦里和屯,亦呼為萬里和屯,亦呼為萬里和通。”④《黑龍江輿圖》,光緒二十五年(1899)石印本,第13頁。“宛里”為“斡離”“斡離”之訛,“瓦里”“萬里”與“宛里”音同字異。其與越里篤的聯系,猶可知也。
《遼金元三史語解》之《遼史語解》稱:“伊埒圖,滿洲語‘明顯’也,卷十四作越里篤。”①《遼金元三史語解·遼史語解》卷3,道光四年(1824)刻本,第8頁上。“伊埒圖”與“越里篤”語音相差太遠,未可以等同,不可以為據。
5.越里吉部
越里吉,在《遼史》中又稱越棘。遼興宗重熙六年(1037)八月,“樞密院言越棘部民苦其酋帥坤長不法,多流亡,詔罷越棘五國酋帥,以契丹節度使代之。”越里吉急讀即為“越棘”,“棘”與“吉”同音異字。
《遼金元史語解》之《遼史語解》稱:“伊呼濟,蒙古語‘已來’之謂,卷十四作越里吉,卷十八作越棘,卷三十三作越里吉。”②《遼金元史語解·遼史語解》卷3《部族》,道光四年(1824)刻本,第18頁下。將越里吉釋為蒙古語“伊呼濟”,缺乏證據,不可以為信。
三、五部不是五國部
在《遼史》中,除五國部以外,還有五國和五部。五國、五部與五國部是什么關系,是等同還是不等同,直接影響到五國部的研究。在這個問題上,存在不少模糊認識,從而導致許多錯誤的論斷,應當引起重視。
《遼史》中關于“五國”的記載比較多。例如:
重熙六年(1037)八月,有“五國酋帥”。③《遼史》卷18《興宗記》,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19頁。咸雍七年三月,有“討五國功”、“五國節度使”。④《遼史》卷22《道宗二》,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70頁。大安元年(1085)正月,有“五國酋長”。⑤《遼史》卷24《道宗四》,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90頁。大安二年(1086)正月,有“五國諸部長”。⑥《遼史》卷24《道宗四》,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91頁。上述的五國,都是指五國部而言。實際上古人的用法均是如此。《文獻通考》:“女真外又有五國,曰鐵勤,曰噴納,曰玩突,曰怕忽,曰咬里沒,皆與女真接境。”⑦(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327《女真》,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571頁。《金史》:“五國蒲聶部節度使拔乙門畔遼”。⑧《金史》卷1《世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契丹國志》:“女真東北與五國為鄰,五國之東鄰大海,出各鷹。”⑨(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10《天佑皇帝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由此不難看出,上述的五國都是指五國部而言。《文獻通考》中的鐵勒屬于誤入。
《遼史》關于五部的記載只見有兩處。其一是統和二十一年(1003)四月戌辰,“兀惹、渤海、奧里米、越里篤、越里吉等五部遣使求貢”,⑩《遼史》卷14《圣宗五》,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70頁。其二是開泰七年(1018)三月辛丑,“命東北越里篤、剖阿里、奧里米、蒲奴里、鐵驪等五部歲貢貂皮六萬五千,馬三百。”?《遼史》卷16《圣宗七》,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84頁。
從行文來看,前面引證關于“五國”的記載均無“等”字,說明五國系指一個整體而言;后面引證關于“五部”的記載多了一個“等”字,說明不是一個整體,是五個部落的并列。
其次,引文中的“兀惹”“渤海”“鐵驪”都是獨立的部落,與五國部無關聯。
渤海指渤海國滅亡以后的遺民,他們聚集在一起,有如一個部落,接受遼朝的統治,要定期遣使貢方物。其居住地不明,很可能是在渤海上京龍泉府舊地。其非為五國部成員,是顯而易見的。
兀惹與鐵驪是兩個相鄰的部落。兀惹又作烏惹,金代稱兀的改,又作烏底改,元代稱兀惹野人,清代稱黑斤、赫金,是今赫哲的祖先。其分布范圍很廣,是以漁獵為生,故松花江下游、黑龍江中下游都是他們活動的地區。因此,他們自稱是下江人、下游人。
遼代的兀惹人勢力強大。統和十三年(995)七月,“兀惹烏昭度、渤海燕頗等侵鐵驪,詔奚王和朔奴等討之”,卻未能取勝、未能攻克惹城,和朔奴被削官。統和十五年(997),兀惹長武周被迫降遼進貢。①《遼史》卷13《圣宗四》,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46頁、第148頁、第149頁。開泰元年(1012),有百余戶兀惹民眾被遷往賓洲。②《遼史》卷70《屬國表》,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152頁。
鐵驪在遼太祖天顯元年(926)二月就歸附遼朝,③《遼史》卷2《太祖下》,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2頁。此后鐵驪不斷來貢獻方物,見于統和十年(992)、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十六年。貢物主要是鷹、馬、貂皮。鐵驪歸附遼朝以后,有一部分編入黃龍府兵馬都部署司的部族軍,稱鐵驪軍,④《遼史》卷46《圣宗七》,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84頁。曾抵抗女真侵邊。大康八年(1082)正月,有“鐵驪五國部長各貢方物”⑤《遼史》卷18《百官志二》,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45頁。的記事。從“各貢方物”的用語來看,鐵驪與五國部并列,顯然鐵驪不會是五國部的成員。在北面屬國官中,有鐵驪國王府⑥《遼史》卷46《圣宗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22頁。,說明鐵驪是獨立的部落遼朝廷對鐵驪國相當重視。
鐵驪貢獻的方物,主要有鷹(可能指海東青)、貂皮和馬,說明其居住在山區。兀惹與鐵驪相鄰,也居住在山區。《遼史》記載,統和十三年(995)奚和朔奴“伐兀惹,駐于鐵驪,秣馬數月,進至兀惹城。”⑦《遼史》卷85《百官志二》,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317頁。陳述先生謂:“可見鐵驪在兀惹之西.兀惹城在今通河縣附近,鐵驪居其西,正當今黑龍江省鐵力市一帶,即由黑龍江上游南至松花江下游,皆鐵驪分布地區。”⑧陳述:《遼史補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2130頁。
《契丹國志》記載:“東北至惹國、阿里眉國,破骨魯國。”⑨(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22《四至鄰國地理遠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12頁。有學者據此提出:阿里眉和破骨魯,顯即五國部中的奧里米部和盆奴里部,其中奧里米部的中心在今黑龍江省綏濱縣城附近敖來密村一帶,則可推知屋惹即兀惹地當在今綏濱縣以南的樺川富錦一帶。⑩魏國忠、朱月忱、郝慶云:《渤海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589頁。
按:破骨魯見于《遼史》,將破骨魯譯成盆奴里似不確。樺川縣宛里城(萬里和通)為越里篤部所在地,將兀惹推知在樺川一帶,恐無此可能。按日本學者池內宏和陳述先生考證,?陳述:《遼史補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2130頁。富錦附近大古城應為剖阿里部所在地,顯然也不會容納兀惹于此居住。
五國部的成員與不是五國部成員的鐵驪、兀惹、渤海同時進貢方物,是偶然發生的現象。由于他們是同日到達,恰好正是五個部落,故當值的史官用五部之名記入《實錄》之中,實屬正常。后人撰《遼史》時,沿用此說,用“五部”來稱謂。這種現象比較罕見,在《遼史》中只見有兩次而已,與《遼史》中“五國”“五國部”的多見,成為鮮明的對比。有些現代學者失察,竟誤認為“五部”即五國部,與事實相背離,由此又引出了不少錯誤的論斷。
例如有的學者將五部視為五國部以后,發現其名稱有很多不同,為了解釋這種不同的部名,竟提出這是五國部名之重出或互異。所謂“重出”本是指同一事物第二次出現而言,就是重復之意。不同的部名,是不能稱作“重出”。如果是同一事物,焉有互異之稱,鐵驪、兀惹、渤海本是與五國部名稱不同、地域也不相同的部落,其“互異”是正常的,若說此三部是五國部的“重出”,顯然是不可以的。有人提出,“剖阿里與兀惹重出,當是兀惹之一部……所以《遼史》五國部名初為兀惹,后為剖阿里”①張博泉:《金史簡編》,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頁。這種解釋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無法使人信服的。
由此可知,將《遼史》中的“五國”視為“五國部”,由于不符合事實,無法做出科學的解釋,結果是越解釋帶來的問題越多,難有說服讀者之力。
四、五國部的位置
五國部又稱五國城,最早對五國城定位的人,是清末的曹廷杰(字彜卿)。他在《五國城考》一文中提出:
查《遼史》《營衛》《部族志》五國部:博和哩國,博諾國、鄂羅木國、伊勒圖國、伊勒希國,是五國必當分居五地,必非一處可知。今自三姓至烏蘇里江口,松花江兩岸共有城基九處:一,三姓附郭舊城;一,三姓下八十余里北岸呑河圖木訥城;一,三姓下三百五十余里南岸瓦里和屯,即《通志》斡里城;一,斡里城下四十余里南岸希爾哈城;希爾哈城下約百里北岸,有大古城;一,希爾哈城下百六十里南岸富克錦地方,有大古城;一,富克錦下約百里南岸圖斯克地方,有大古城;一,額圖下約五十余里南岸青德林,即喜魯林地方,有古城基……是五國城址不外三姓下九城基也……三姓當為五國頭城,自此而東四國分據也。②《曹廷杰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69-171頁。
曹廷杰指出五國城應在依蘭以下至青得林以上的范圍內,是很有道理的。后來曹氏又撰《勃利考》,加以補充。后人研究五國部,多遵循曹廷杰之說,不過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見。
1.剖阿里城
曹廷杰《勃利考》稱:
唐征高(句)麗,絕沃沮千里,至頗黎。遼五國部,有博和哩國。頗黎、博和哩,音同字異也。今華人曰伯利,二字均呼力,是與唐、遼同音。則俄之克薄諾甫克,即頗黎、博和哩,似屬可據。③《曹廷杰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71頁。
曹氏所稱的克薄諾甫克,現在通譯為哈巴羅夫斯克,位于烏蘇里江匯入黑龍江處,所謂博和哩國,即遼剖阿里部。
清末,屠寄(字敬山)主編《黑龍江輿圖》在精奇里江(結雅河)匯入黑龍江下方,標志有博科里城,稱“即遼剖阿里國故城”①(清)屠寄:《黑龍江輿圖》,光緒二十五年(1899)石印本,第32頁。。這種說法與曹廷杰將剖阿里定在哈巴羅夫斯克是不同的。“博科里”是清代的稱謂,其讀音與“剖阿里”相近,故屠氏將“博科里”確定為遼代的剖阿里部。屠氏在《黑龍江輿園說》中,稱黑龍江城“五代遼屬五國部剖阿里國地”②屠寄:《黑龍江輿圖說》,見《遼海叢書》,沈陽:遼沈書社縮印本,1985年,第1029頁。,即與此有關。日本學者池內宏撰《鐵驪考》,提出剖阿里部為富錦縣治。景方昶撰《五國城》,提出:“今烏蘇里江口以東地名伯利,即剖阿里國,為五國之一地”③(日)池內宏:《滿鮮史研究》中世第1章,第154頁。。他支持曹廷杰之說。
陳述先生撰《遼史補注》,對以上不同的說法予以評價。他指出:
剖阿里為五國部之一,《黑龍江輿地圖說》以剖阿里定點于精奇里(西人稱結雅河)會入黑龍江處,去其他四國較遠。《東北輿地圖說》謂在伯利,按伯利為頗里八部,頗里不屬五國部,不合,池內宏《鐵利考》(刊于《滿鮮史研究》)比定剖阿里為今黑龍江省富錦縣,舊稱富克錦。似較前兩說略勝。④景方昶:《東北輿地釋略》,見《遼海叢書》,沈陽:遼沈書社縮印本,1985年,第1014頁。
陳先生指出伯利與頗里不同,頗里不屬于五國部,不贊成將剖阿里定在伯利(哈巴羅夫斯克),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在伯利至今沒有發現遼金古城址。曹廷杰最初提出五國城位置時,沒有將伯利列入其中,就是考慮到這里不見古城基,與其他有九處城基者不同,五國部其他四部均見有城址(詳后),而獨伯利不見城址,這種事實必須予以重視。陳先生認為池內宏將剖阿里比定于富錦市,“似較前兩說略勝”,是因為富錦(富克錦)有大古城,見于曹廷杰《五國城考》。由此看來,陳先生非常重視五國城城址的重要性,沒有城址即不可能成為五國部五國城。因此,將剖阿里確定與于伯利(哈巴羅夫斯克),證據不足,難以取信于人。
剖阿里部剖阿里城,應在黑龍江富錦(富克錦)縣大古城。池內宏曾將剖阿里比定于此,將富錦市縣說成是剖阿里之所在,從大的方位看是正確的。不過稍有錯誤,實際剖阿里城不在富錦市,而是在其以西7.5千米處的大古城。此城在《黑龍江輿圖》上有標志,誤作越里吉古城。
此城最早由曹廷杰記載,將富克錦大古城列為五國部中的一部,屠寄認為是越里吉部所在,不確。富克錦大古城,民間稱作“霍吞吉里”古城,出自滿語,意為“沿江邊的城”。它北距松花江2 千米,在頭道河子南側臺地上,東距大屯村1.5千米,西距上街基鄉2.5千米。其地勢北高南低,城東北角海拔76.4米,古城呈長方形,東西950米,南北450米,周長2,250米。北墻已被河水吞噬,東、西城墻南段幾乎夷為平地,南墻無存,城墻殘高2 米,城壕隱約可見。城西南方有一斗小城,周長1,700米。⑤陳述:《遼史補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1431頁。據《黑龍江輿圖》,城南有大山,稱富克錦山。
該城瀕松花江而建,城的規模與奧里米城相仿佛,城外有小城,與奧里米城相同,證明其時代與奧里米城相同或相近,為遼代所建。城南有大山,山上有森林,可供海東青棲息。因此,將富克錦大古城推定為剖阿里城是比較穩妥的。
《黑龍江輿圖》將剖阿里部標注在精奇里江入黑龍江會合處,不知以何為據,陳述先生指出精奇里江口距五國其他四部太遠,不贊成此說,是很有道理的。或許后來有少量剖阿里部人移居于此,不妨稱作別部、分部,但其本部不在這里,而在松花江河畔的富克錦大古城。
至于伯利,即哈巴羅夫斯克,按陳述先生意見,應與伯利部有關,或為其主要居住地。勃利是黑水靺鞨的一支,黑龍江中下游是黑水靺鞨主要居住地,黑水軍、黑水府以伯利為中心。在烏蘇里江與黑龍江會合出的黑瞎子島(烏蘇里島)上,有靺鞨人的墓地,出土了唐代銅錢開元通寶、乾元重寶①張泰湘:《黑龍江古代簡志》,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頁。,證明伯力(給巴羅夫斯克)是黑水靺鞨的久居之地,很可能有官府駐此,應與勃利部有關,不過勃利不在五國部中。
2.盆奴里城
盆奴里城即今黑龍江省湯原縣固木訥城。屠寄主編《黑龍江輿圖》,將盆奴里城標定于屯河下游的固木訥城。固木訥城是公木訥城之誤,歷史上又稱桃溫城。托溫城,是以桃溫水(清代稱屯河)得名。其理坐標為東經129°43'—44',北緯46°40'—41'。海拔98米。
該城北、東北瀕臨湯旺河,湯旺河東岸為小興安嶺林區,東南為松花江沖積平原。由于松花江自清代以來不斷向北岸移動,將該城南部城墻沖毀一部分,據殘垣斷壁,該城平面作長方形,周長約2,500米,城墻上有馬面、角樓,城墻外有兩道護城壕。②宋玉彬:《俄羅斯遠東地區出土的中國銅錢》,《東北亞歷史與考古信息》1996年第1期。古城東距香蘭鄉3千米,西北至雙河村1.5千米,北距湯旺河大橋1千米。湯旺河北達小興安嶺腹心處,小興安嶺森林密布,禽獸豐富。成為獵鷹海東青的重要棲息地。盒奴里城設此與獵取海東青有關。
3.奧里米城
奧里米城,亦見于《黑龍江輿圖》,其城有二:一在松花江下游北岸,另一在黑龍江南岸,彼此相距約50千米,前者當地稱敖來城,后者著當地稱中興城,均以村鎮得名。為了記述方便,本文分別稱南城、北城。
筆者于1974年同張泰湘對南城進行實測。該城南距松花江1千米—1.5千米,有小河敖來河從西北向東南流;將南城垣沖毀。全城周長3,224 米,城垣高3 米—4 米,北城垣長912 米,有馬面18個,未見到城門。東城垣上有城門和甕城。西城垣,南城垣被傲來河沖毀,未見到城門和甕城。環城有護城壕,當時測深為1米—1.5米。城內土丘起伏,排列有序,遍布瓦礫陶瓷碎片。城外西北隅有大片古代墓群,經發掘出土了大量文物,有金器、玉器、鐵器、陶器。南城的東西側建有小城各一個,屬大城的衛城。③張泰湘:《黑龍江古代簡志》,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頁。馬翰英:《固木訥城沿革考略》,《黑龍江文稿叢刊》1983年第1期。
北城周長1,460米,約為南城之半。共設三道城垣,一主兩副,外有三道護城壕。南、北各設一門,有瓫城。城外西北、西南、東南,各有周長200米的小方城,作為衛城。城外西北隅有墓群。征集到“封全”印,“泰州錄判”字款銅鏡,墓葬出土了金銀器、玉器、銅器、鐵器、陶瓷器,畫押印,④黑龍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隊:《黑龍江畔綏濱中興古城和金代墓群》,《文物》1977年第4期。顯示出墓主身份很高。
從城池構造和出土文物來看,奧里米南北二城前后沿用的時間很長,從遼到金都住有居民。南城出土有正隆元寶,北城出土有大定通寶,分別是海陵王、金世宗時代銅錢,說明金代南北奧里米城仍住有居民。北城設三道城垣、三道城壕、三座衛城,證明其在軍事上相當重要,是扼守黑龍江的要塞。駐守此城的人,應當是身份很高的貴族。
奧里米南、北二城,均處于沖積平原上,附近沒有山嶺。不過這里古代森林很多,在墓葬中隨葬有木棺,還出土了木制品。在黑龍江同仁遺址中發現的房屋四壁有板壁,地責鋪有地板,還有木柱、木梁,證明古代這里森林多,取木料容易,經鑒定多為紅松(果松)。①黑龍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隊:《松花江下游奧里米古城及其周圍的金代墓群》,《文物》1977年第4期。在墓葬中隨葬有樺皮桶,說明生長有樺樹。紅松、樺樹是黑龍江原始森林中最常見的樹種,證明濱奧里米地區生長有原始森林,為海東青提供了良好的棲身場所。
4.越里篤城
越里篤城,即今黑龍江省樺川縣萬里和通古城。屠寄《黑龍江輿圖》,已有注明。后世學者,多取信不疑。該城建于山上,隨山而建,很不規則。北部有斷崖,下臨松花江,以江為險,不筑城垣。東、南、西三面修建城垣,高5米—6米,東、南最高處、高10米。有東、西、南3座城門,東、西二門相對,東門、南門有甕城。城內有兩道壕,作為南北走向。此城居高臨下,站在城頭之上,可以清楚看見松花江面航向的船只,軍事地位非常重要。據說,清代俄國欲謀占此城,而來能得逞。
“萬里和通”來自滿語,張泰湘說是“屠殺之城”,在此城曾發生過重大的戰斗,死傷了很多人。穆曄駿提出,“屠殺”之說不確,其意是衰敗之城、衰落之城。如果此城是由于戰爭而廢棄,則此二說可以通用不矛盾。
5.越里吉城
曹廷杰在《五國城》一文中,首次提出:“三姓當為五國頭城,自此而東乃四國分據地。”②黑龍江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考古研究所:《黑龍江同仁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6年第1期。這種說法是有充分根據的。《元一統志》記載:“混同江發源長白山,北流經建州西五十里,會諸水東北流,經上京,下達五國頭城北,又東北注于海。”又有:混同江“俗呼宋瓦江,源出長白山,北流經舊建州西五十里,會諸水東北流,經故上京,下達五國頭城北,有東北注于海。”③《曹廷杰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71頁。《明一統志》記載:“五國頭城在三萬衛北一千里,自此而東分為五國,故名。舊宋徽宗薨于此。”④《元一統志》,趙萬里輯本,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第220頁。
越里吉部是鷹路上距黃龍府兵馬都部署司最近的一部,其余四部都在其下游,故有五國頭城之城。重熙六年(1037)以后,五國部節度使駐于越棘(越里吉)部,于是,越里吉不僅是地域上的頭城,而且也是政治上的第一城。遼朝通過越里吉去征索其他各部的海東青,對于越里吉的地位和作用,應當有充分的認識和重視。
五、關于五國頭城的不同認定
五國部依次排列,其上游第一城稱五國頭城(圖三)。《元一統志》記載:“混同江,發源長白山,北流經建州西五十里,會諸水東北流,經上京,下達五國頭城北,又東北注于海。”又“俗呼宋瓦江,源出長白,北流經舊建州西五十里,會諸水東北流,經上京,下達五國頭北,又東北注于海。”①《元一統志》,趙萬里輯本,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第220頁。舊上京指上京故城,據此所知,五國頭城即金上京下游的依蘭(三姓)城,《明一統志》稱:“五國頭城在三萬衛北一千里,自此而東分為五國,故名,舊宋徽宗薨于此。”②《明一統志·遼東指揮使·古跡》。據此,五國頭城為宋徽欽二帝囚禁之地。曹廷杰亦稱:“三姓”當為五國頭城。③《曹廷杰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71頁。依蘭縣城北,舊有古城遺址,當即五國頭城故址,當為學者多持此說。
然而近年又出現了異說,認為五國頭城不在依蘭縣城,而在依蘭縣城以南的土城子(圖四)。
在依蘭縣以南45千米,有土城子一座。1958年—1959年,趙善桐、孫秀仁、朱國忱兩次到此考古調查,稱土城子在牡丹江左岸,距江約1.5千米,周長3345千米。該城不是常見的方形、長方形,而不是不規則的多邊形。有2道城墻,設西、南二門,門有隘口(按:當為甕城)。城北有天然河流,存水無多。地上見碎瓦、陶片,據說以前曾出土銅錢和鐵鍋。④黑龍江省博物館:《牡丹江中下游考古調查簡報》,《考古》1960年第4期。
近年有人提出,土城子為五國頭城,即徽欽二帝的“金國行宮”,其依據是這里的環境與徽欽二帝隨行人員記相符。牡丹江兩岸均為張廣大嶺山區,地理環境大體相似,土城子一帶別無特殊的景觀。以此為據,斷定土城子為五國頭城,其理由欠充分,沒有考慮到牡丹江水路的種種困難。
牡丹江在張廣才嶺山區,河道狹窄、曲折,兩岸多是懸崖峭壁,河道落差很大,平均比降為1.39%,而嫩江的比降為0.28%,①牛汝辰:《中國水名詞典》,哈爾濱:哈爾濱地圖出版社,1995年,第44-45頁。說明河水非常湍急。據日本學者白鳥庫吉研究,牡丹江出自滿語,為曲江之意。②白鳥庫吉:《論海西女真》,《白鳥庫吉全集》第5卷,見《長白學圃》1987年第3期。這種山區河流,河底多礁石和淺灘。據《寧安縣志》記載,牡丹江上游水深3尺至6、7丈,中游不能行舟,鐵嶺河以下可以行舟。下游水深5 尺至7、8 丈,“由鐵嶺河至依蘭,其間有滿天星(大小圓石滿江,故有是名),三道額水流勢急,船能往而不得返;雖往亦極危險,人多不敢輕視也。”③民國《寧安縣志》,鉛印本,第67-68頁。由此觀之,牡丹江是不利于航行的。
《寧古塔記略》記載,每年五月間,呼兒喀、黑斤、非牙哈三處人,“乘查哈船江行至寧古塔南關外泊船,進貂。”④(清)吳振臣:《寧古塔紀略》,見《述本堂詩集·寧古塔紀略》,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566頁。有人以此為據,提出:“牡丹江古代水量比現在大,可以同航,清代這條水路還是暢通的。”⑤梁玉多:《勿吉——靺鞨民族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68頁。《寧古塔紀略》所記的呼兒喀、黑斤、非牙哈屬于赫哲人,他們所乘的“查哈船”,系滿語對樺皮船的稱謂,又可稱作“威乎”⑥《北方文物》1992年第3期。。這種樺皮船很少見于內地,它規模小、體輕,赫哲人乘它江上捕魚,稍大一些可以用來裝運貂皮到寧古塔進貢。“查哈船”在牡丹江中航行是不會有什么困難的,然而大型的木船很難通過“滿天星”礁石群的,會面臨種種危險。
牡丹江兩岸荊棘叢生,蒿草遍地,是野獸出沒的場所。只有獵人,才敢在河岸走行,便于尋找野獸的蹤跡。古代牡丹江兩岸,沒有現成的道路,一切都處于原始狀態,清初仍是如此。
宋徽欽二帝是通過松花江水路前往五國頭城。其隨行人從數千人減少到140 人,減員的原因與松花江水道的礁石有關。在依蘭縣城附近,松花江水道比較狹窄,江底有礁石、沙灘,被稱作松花江的隘口。古往今來,都是船只航行的危險河段。江水枯瘦的季節,江水變淺,危險性特別大,徽欽二帝從韓州遷往五國頭城,是“乘舟而行”,從7月15日動身,到9月2日才到達,前后46日。此時正是松花江的豐水期,選定在此時航行,顯然是為了避開河道中的險灘、礁石,特別是牡丹江口外的礁石威脅最大。松花江尚且如此,牡丹江河道豈能容得徽欽二帝乘坐的大船進入,其道理是不言而喻的。
徽欽二帝在五國頭城居住期間,金朝廷與他仍保持與一定的聯系,據《金史》記載,在此期間至少有以下幾件大事:
1.天會九年(1131)六月壬辰,“賜昏德公、重昏侯時服各兩襲。”①《金史》卷3《太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63頁。
2.天會十三年(1135)四月丙寅,“昏德公趙佶薨,遣使致祭及賻贈。”②《金史》卷4《熙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70頁。
3.皇統元年(1141)二月已丙,“改封昏德公趙佶為天水郡王,昏侯侯趙恒為天水郡公。”③《金史》卷4《熙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76頁。
4.皇統元年(1141)十二月癸巳。“天水郡公趙恒乞本品奉,詔賑濟之。”④《金史》卷4《熙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78頁。
5.皇統元年(1141)十二月丙辰,“歸宋帝母韋氏及故妻邢氏、天水郡王并妻鄭氏喪于江南”。⑤《金史》卷4《熙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78頁。
以上五事,都是金朝廷與徽欽二帝之間發生的大事情。送衣服、送俸祿、送詔令,必須要有朝廷官員前往。如果五國頭城為徽欽二帝住所,朝廷官員往來還算方便;如果徽欽二帝居住在牡丹江中游的土城子,就會造成極大的困難,很難進行。
還有,五國頭城是金代胡里改路之治,金朝廷與各路之治之間公文、使者往來很多,自不待言。從這個角度來說,五國頭城、胡里改路之治所,也不能設在土城子。
土城子北距牡丹江口依蘭縣城45 千米。一個往返是90 千米。在古代牡丹江航行不便的條件下,人們不會舍近求遠,將五國頭城、胡里改路之治設在土城子,這個道理是很明白的。
土城子規模比較大,比依蘭縣城的五國頭城大了許多。人們多認為,古城的規模越大,其級別就會越高。對于同一時代的古城來說,可能會如此,然而根據目前掌握的資料,尚無法證明土城子必定是遼金古城遺址。
元朝初年,在松花江沿岸設有水達達路和五個軍城萬戶府。土城子很可能與上述城池有關,曾實地考察過土城子的朱國忱曾提出土城子為水達達路故城,此說是可以考慮的,不妨深入研究,以得其實。就一般而言,后代的城池規模比以前代的規模大,例如北京的元大都城比金中都城大許多,就證明了這一點。